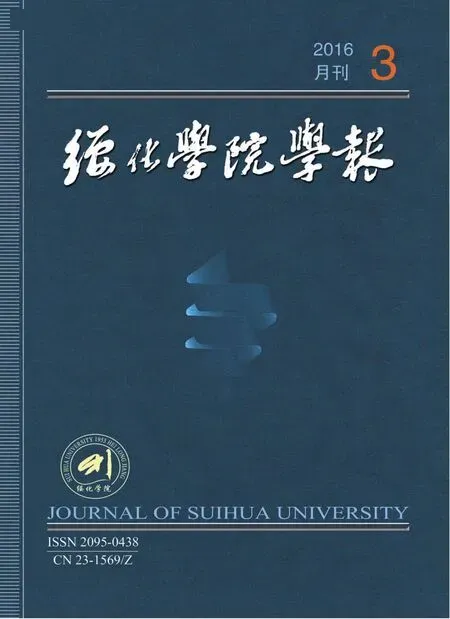深情回望:现当代文学中的小城故事
寇国庆 倪相群(.蚌埠学院;.蚌埠第一中学 安徽蚌埠 33000)
深情回望:现当代文学中的小城故事
寇国庆1倪相群2
(1.蚌埠学院;2.蚌埠第一中学安徽蚌埠233000)
摘要:现当代文学中的作家描述了众多小城故事,而且这类作品以深情回望与早年记忆展开;小城故事所呈现的风物人情与市井传奇正是作家创作的情感源泉及运用深情回望与早年记忆得以展开的背景。20世纪的中国,小城正处于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交接点上,小城故事自然成为他们寄托深刻思考与无情质疑的文化载体。显然,小城故事的出现使现当代文学具有了新的文学风格与气质。
关键词:小城故事;深情回望;早年记忆;风格气质
现当代文学中有很多经典作品是作者通过深情回望与早年记忆进行的创作,与之相伴,故事得以展现的小城进入到文学作品中来,小城故事所呈现的风物人情与市井传奇正是作家创作的情感源泉及运用深情回望与早年记忆得以展开的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城故事的出现使现当代文学具有了新的文学风格与气质,也使地域小城的历史人文内涵具有了更多的情感与个性色彩。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离开小城,走向异乡,早年的小城生活往往令作家深情回望、反视内听。几乎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小城,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鲁迅的绍兴、废名的黄梅、沈从文的凤凰城、茶侗,萧红的呼兰小城;当代作家中的蚌埠之于王安忆,海盐之于余华,这些小城“共同讲述着传统中国失落的故事”,并“最终构成了对大变动过程中的乡土中国的文化学以及人类学意义上的忠实见证”[1](P17)
一、文学作品中的小城故事
对于作家而言,早年时期的生命体验往往给他们的一生涂上一种特殊的基调和底色,并在相当的程度上决定着作家对于创作题材的选择和作品的基调。[2](P39)马原曾说到:“我们口中这个带有不愉快回忆的童年生活,实际上说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童年生活记忆。可以说,如果回忆的话,可能每个人都有关于童年的不愉快的记忆。”“它是我最初写作的一个心理依傍。”[2](P50~51)对敏感而多情的作家来说,故乡那片土地他们是满含着爱和恨,自然成了生命血肉的一部分。
因祖父的“科场贿赂”案,童年的鲁迅随着母亲和弟弟们避难乡下,寄人篱下,家庭变故使之过早地洞悉了人情世故。这就有了:“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多年后回到故乡,童年记忆的S城:“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故乡》)
湖北黄梅的田园风光、禅宗文化孕育了废名的创作,废名在作品中对故乡黄梅寄予了深深的眷恋之情,特有的佛禅文化又使生于斯、长于斯的废名从小耳濡目染,心系念之,因此,废名的创作往往醉心于沉思冥想之中的人生体验与玄思神游,将清静本心的人生旨趣化为一种虚无空蒙、适意淡泊的境界。这种浓郁的禅宗意识在他的作品中处处弥漫。
同样是京派作家,沈从文对没有受到现代城市文明浸染的湘西有着深深的眷念。他向往单纯的童真世界、渴求淳朴、崇尚自然,能够安放他灵魂的地方唯有古朴的湘西世界,在作品中一再地深情回望,他笔下的“边城”更是以风俗美、人情美和人性美寄托了他的早年记忆。
作为萧红的小城,呼兰城中的人们,不管生活怎样大家都仿佛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的沿袭惯有的风俗习惯生活,活着的死了的都没有什么能够掀起波澜,人们就这样百年如一日的活着。作为萧红的遗作,1941年7月1日发表在香港《时代文学》上的《小城三月》也成了绝唱:
“天气一天暖似一天,日子一寸一寸的都有意思,杨花满天照地飞,像棉花似。……草和牛粪横在道上,放散着强烈的气味。远远的有用有石子敲打船的声音。空空……的大响传来”。《小城三月》
在当代作家中,20世纪50年代生人的王安忆,童年与少年时代正赶上中国社会极具变动的60、70年代,社会的不幸反而成为日后的创作资源,相对于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的物质丰富而言,地处内陆的蚌埠郊县怀远就是荒寒之地,当地的贫穷让下放知青感到震惊,对于少年的她,小城蚌埠就成了这些被命运放逐的少年的心灵慰籍:
蚌埠四周的乡镇,每一个村庄都有着成群结队的知青。很多人都是冲着蚌埠的铁路来这里插队,铁路是我们的生命线,它维系着我们的家。……前途是渺茫的,在渺茫中,这却是唯一的维系。(《蚌埠》)
小说《蚌埠》写到蚌埠喧闹的渡口和嘈杂的火车站,还有干净的“人民浴池”、整齐的街道……蚌埠在王安忆眼中显得阴郁,但是在阴郁的表面之下,是一种温和、整洁与安宁。
余华的小说也同样包含了他对早年记忆的深情回顾,故乡小城中激情与盲目的青春期成长,惊喜、恐怖与骚动的青春体验,家人和朋友的相继离世,各种正常和非正常的死亡,成长中的罪恶与痛苦,医院的血淋淋的手术与阴森的太平间,这些记忆痛苦且珍贵,与此同时故乡也变成了不能轻易触碰的创伤,他的念兹在兹的小说创作在在投射了作者早年记忆。
二、小城人文与情感故事:小城故事的文学价值与意义
鲁迅笔下忧伤的S城与鲁镇,沈从文描绘的淳朴善良的凤凰与茶侗,萧红笔下的瞒顸的呼兰;王安忆的带有泥土气息的蚌埠,余华勾勒的充斥着暴力血腥的海盐……这些小城因作家深情回望被熏染了更多的诗性色彩,也使这些地理空间被赋予独有的文化。一个个小城以故事的形式展现现代与当代人的情感生活,也使人们的生活留下具体的物化见证,小城的历史也具有了丰盈的肉身。
鲁迅的百草园、私塾与戏台,这些早年的记忆,正如作品中描述的那样,迅哥和小伙伴看戏归途中远望:“回头观望逐渐远去隐在灯火里的戏台,给人的感觉和刚才来远远望去的感觉一样,但是若隐若现的却又像是不可触摸的楼台阁宇”(《社戏》),百草园、私塾与戏台在在触及了作者内心最为柔弱的部分。朝花夕拾、旧事重提:“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我独自住在位于厦门的石屋里面,……内心感觉很苦闷,……就这样开始回忆,开始创作。”[3](P354)鲁迅在回忆中再次感受到早年的纯真与单纯的爱:勇敢率真的农村少年、粗鲁愚昧充满爱心的保姆阿长、严厉负责的私塾先生、不守寺院清规戒律的和尚师傅,小城记忆得以留存。
不同于鲁迅及其以后的乡土小说家,对于京派作家来说,因对大都市有着深刻的排拒,“边城”成为他们的理想与情感的寄托:“从审美情趣上看,‘京派’小说家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心仪陶渊明,这种选择使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也表现出对田园牧歌情调的倾心向往。”[4](P269)
沈从文出身行伍,但在他看来,战争是自杀的悲剧,人类应该以理性来战胜这种愚蠢。他的《边城》《萧萧》《长河》是对失去的古典朴素的人性的一首挽歌:“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5](P201)沈从文心仪的是可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的乡土。在1942年他为《长河》所写“题记”:“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什么都不同了……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地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6]
茶侗、凤凰与湘西因沈从文的作品被赋予了世外桃源的韵致。
湖北黄梅具有独特的佛禅文化特色与传统,静谧优美、钟灵毓秀的青山绿水,而在废名身上,我们既能看到“叛徒”式的对社会现实的忧患意识与执着,又能看到禅士的沉思静观、无所住心的超脱空灵,这些都成为作家耳闻目见且‘默而识之’的经验,这自然养育了作者的不僧不俗,亦僧亦俗的审美情调,他的创作也使黄梅这座佛禅文化名城有了历史的延续。
《呼兰河传》中以大量篇幅描述“我”和祖父一起在后花园所经历的一切,在平静的笔调缓缓呈现出来的是早年生活的诸多美好回忆。萧红重新审视自己生活多年的故乡,在那个受到历史裹挟的小城故事里面,人们盲目地生、盲目地死,呼兰,一座荒寒之地的小城进入了文学史,无名的众生因小城也具有了生命。
在一系列小说中,王安忆在意的是时代风云的底色和历史变故的根基。他人看重的是主流历史的凝重宏大,她看重的是民间市井生活的细密韧劲。“在上海浮光掠影的那些东西都是泡沫,就是因为底下这么一种扎扎实实的、非常琐细日常的人生,才可能使他们的生活蒸腾出这样的奇光异彩。”[7]王安忆所书写的芸芸众生的精打细算,小悲小欢的生活史,也是蚌埠这个皖北小城的内在精神气质。
对于余华来说,无论是北京,还是上海,都注定是一座别人的城市。只有海盐,才是他心灵的栖息之地。因此,余华在一次访谈中说:“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当我不写作的时候,我才会想到自己是生活在北京。”[8](P251)这座面积不大也相对贫乏的海盐,伴随他30余年的成长、生活和创作。
人生中许多的美好都无法复制与重来。
因此,作家总会不自觉地去留恋他曾经的生活,然后在写作中运用以前的记忆。
故乡带着作家的生命烙印终其一生地影响着他们。
对于中国来说,20世纪新旧交替,连接着过去和未来,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演变的历史进程。作家们也处于矛盾的境地:一方面是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另一方面不由自主地受现代声色的吸引,又因生活的贫困依旧对外来冲击抱有成见,而小城则正处于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交接点上,所以作家的小城情结受历史的某种催化从内心意识转变成了实体,自然小城情结至此也就实现了它漫长的归路。
在这样的情景下,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回归到了内心、明心见性。他们笔下鲜活各异的小城故事虽饱含不一样的情感,然均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叙事方式和美学风格。这些作品中既呈现了小城的文化形态、文化性格和生存空间等具体内容,又执着于对人的命运、民族根性、人类生存境况以及生存目的与价值的终极叩问。
在这现代都市文化日益繁华的时代,小城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自然地走进了现当代作家的文化视野,成为寄托他们深刻思考与无情质疑的文化载体,特别对如那些深受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现当代作家而言,小城成为寄予其历史纵深感的物象表达,同时又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作品风格。
参考文献:
[1]熊家良.现代中国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马原.小说密码[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3]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黄健.京派文学批评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5]王路.沈从文———评说八十年[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
[6]沈从文.长河题记[N].大公报“战线”副刊,1943-4-23.
[7]钟红明.王安忆写《富萍》:再说上海和上海人[N].人民日报,2000-10-11.
[8]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王占峰]
作者简介:寇国庆(1970-),男,安徽凤阳人,蚌埠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当代文学与文论。
收稿日期:2015-10-04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6)03-005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