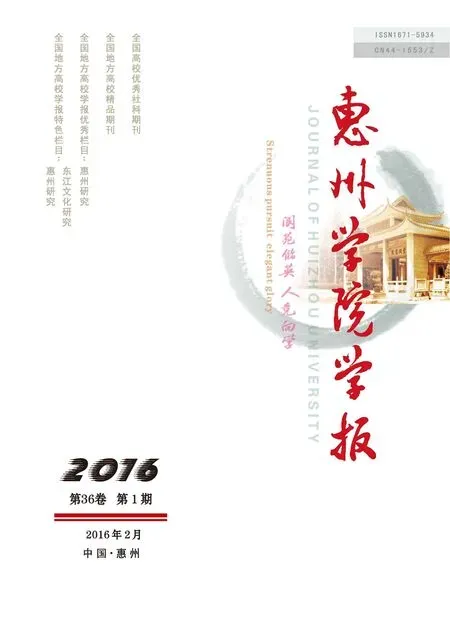香格里拉的基督化与去基督化——简论希尔顿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的宗教现象
熊练(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文化系,广东 惠州 516007)
香格里拉的基督化与去基督化——简论希尔顿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的宗教现象
熊练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外语文化系,广东惠州516007)
摘要:作为西方“世外桃源”和现代版“乌托邦”的香格里拉是一个有如西方的宗教社会,在历史上,它曾接受过基督化,然而在随后的岁月长河中,它又悄悄演绎了一场反向的去基督化。香格里拉的基督化是近代西方基督教普世化过程的缩影,但是,在理想香格里拉的去基督化,无疑体现了对基督教世界的批判。
关键词:《消失的地平线》;香格里拉;基督化;去基督化
一、引言
希尔顿小说《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描述了一个神奇的“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地处昆仑雪山,不通外界,也不为世人所知,是一个桃花源式的西方理想社会。香格里拉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的确很相像,比如它们都与世隔绝,是乱世中难得的避难所,两地都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以及淳朴、热情好客的民俗民风,还有,和桃花源一样,香格里拉也是被外人意外发现,然后又骤然失踪,终于成为那“消失的地平线”。但是可以想象,在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理想社会又是那样的不同,桃花源体现的显然是江南地方色彩,而香格里拉既有地方色彩,又有国际风范,它不仅有来自世界的人员,而且还汇聚了古今中外的文化。两地最显著的差异是:桃花源无非是中国的世俗社会,而香格里拉却是一个宗教社会,或一个有着浓厚宗教氛围的社会。
香格里拉本身是一座喇嘛庙,里面住着喇嘛和即将成为喇嘛的人(如张和罗珍),显然,他们信仰喇嘛教即佛教。香格里拉的主人大喇嘛(High Lama)曾是来自罗马的天主教徒,早年来到时将天主教也即基督教带入香格里拉。喇嘛的生活和工作都围绕宗教展开,静默、冥思、修炼或其他宗教行事。再俯首蓝月谷——也即山下(香格里拉在山上)那片由香格里拉统治的山谷。在山谷的狭长地带,除了民宅和茶坊、农田和果园,就是散布在各处的宗教机构,如佛塔、道观、孔庙等[1]165,到谷中走一走,不仅可以听到“嗡嘛呢叭咪吽”,也可以听到“赞美我主”[1]212。普通的民众或许没有特定信仰,但他们都对香格里拉的精神领袖大喇嘛顶礼膜拜[1]208-209。总之,在香格里拉及其掌管的山谷社会,无时无处不弥漫着宗教的气息。
事实上,香格里拉是一个包括佛教、道教和基督教等在内的多宗教社会,其中基督教是作为外来宗教植入的。早在两个多世纪以前,香格里拉被第一次基督化了,而且,它的确成了一家基督修道院。有研究者论述表明,香格里拉的创作原型乃《圣经》中的伊甸园[2],这无疑也使人相信,香格里拉本应是基督教的圣殿。然而,谁能料到,在最初的基督化之后,香格里拉又悄悄演绎了一场反向的“去基督化”。
二、香格里拉的基督化与去基督化
依据小说“第七章”大喇嘛的讲述,基督教是两百多年前(1719年)由嘉布遣会(天主教分支)修士佩洛特(Perrault)带到香格里拉的。佩洛特被救助来到山谷,为了达谢谷人的救命之恩,也为尽一名修士的职责,他开始传授基督教,以教化西藏异民。他获得了很大成功,不仅赢得了众多信徒,而且还动员他们在香格里拉所在的岩壁上修建了一座基督修道院。自此,基督的传统就在香格里拉生根发芽了。
在佩洛特来到之前,岩壁上原本是一座喇嘛古庙,里面的人多是佛教徒,可见,香格里拉历来有着佛教的传统。随着佩洛特的到来和基督教的植入,香格里拉就形成了大喇嘛本人所标榜的“佛教与基督的双重传统”[1]239。然而,在此后的岁月长河中,基督的传统又一点点地消逝,到康维(Conway)四人来谷的时候,所谓的佛教与基督的双重传统”实际只剩佛教一重了。
一切始于修士佩洛特本人的离经叛道。虽然在早期传教中,他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在谷中生活久了,他本人也受着山谷风俗的熏陶与同化。他渐渐沉溺于山谷的安逸生活,甚至开始吸食谷中的药草,乐此不疲。他因此得到益寿延年、起死回生,但在圣职上不可避免地懈怠了。他不再专心基督教事,而是不务正业练起了瑜伽,并为飞天做着各种尝试,这些都是涉及佛教的神秘功法[1]213,而对于一名基督修士而言无疑是对信仰的亵渎。然而,“佩洛特当时没意识到错误”[1]208,在亵渎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看来只能等待“死亡了结他的亵渎了”[1]208,而死亡迟迟不至。佩洛特更大的亵渎还在于:藐视罗马教廷的召回令,恣意留在山谷。大喇嘛解释说,佩洛特不是不愿回去,而是因为年事已高,无法翻越雪山奔回罗马。的确,收到罗马的召令时,他已89岁了,应当不宜翻山越岭,可大喇嘛不是说,香格里拉的得道之人“在八十岁,仍健步如飞,像年轻人一样爬上关隘”[1]234吗?更何况,教徒若有朝圣之心,是刀山火海也阻隔不住!大喇嘛的说辞不免自相矛盾。事实是,佩洛特甘愿在谷中蹉跎岁月。依照年份推算,他入谷时才38岁,入主香格里拉也不过53岁[1]204,正值年富力强,那时返回罗马必定可以做到,何需等到满是年纪”的时候?可见,他从未有过离谷的念头,可以说,自入主香格里拉那刻起,他就决计背叛教廷,占山为王了。至于他仍一时履行必要的宗教行事,以及给罗马送信,则不过是掩人耳目、蒙蔽上帝罢了。
佩洛特最终皈依了佛教,因为他成了大喇嘛本人。关于这件事大喇嘛并未谈及,或不愿谈及——毕竟叛教不是光彩的事,但可以推断,佩洛特皈依佛教始于他对佛教的研究。他98岁开始研究佛教,起初打算在有生之年致力于写作一部从正教(基督教)的立场抨击佛教的书”[1]209,然而在百岁之龄完成该书时,他却发现“书里的抨击十分缓和”[1]209;不难看出,随着研究的深入,佩洛特渐渐领悟到佛教的真谛,从而促使他最终走向佛门。皈依佛教宣告佩洛特彻底判离基督教。其次是信徒们的“众叛亲离”。随着佩洛特的懈怠,上梁不正下梁歪,他此前的信徒也都一个个重染了旧习,对此,他不仅不责备,反而听之任之。大喇嘛的说辞是,“谁能指望一个人仅凭一己之力,一劳永逸地根除一个纪元形成的习惯和传统呢?在他懈怠的时候,没有来自西方同仁的帮扶。”[1]208这或许是实情,但毕竟酿成了无可挽回的后果:一些人放弃了基督信仰,另一些人如果没有老朽死去,自然也都追随教主,改旗易帜,一同归在了佛陀的麾下。到康维一行来谷的时候,香格里拉只有三种人:50名喇嘛、候选喇嘛和藏族侍者[1]112,丝毫没有基督徒的身影。最后还有修道院嬗变成佛教寺院——喇嘛庙。大喇嘛讲道,在佩洛特来谷不久,就有了在山岩上“建一座基督修道院的想法”[1]204和决心,想“如果乔答摩能够鼓舞人们在香格里拉的岩壁上建造一座寺庙,那么罗马人同样可以(修建一座基督修道院)”[1]206。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成就了他的抱负——修道院建成了,只是后来,由于以佩洛特为首的众基督徒的判教,建成的偌大寺院便堂而皇之地更换了招牌。
如果说,在香格里拉佛教和基督教进行了一次碰撞[3],那么碰撞的结果是:香格里拉去基督化了。从时间上,这种去基督化的格局还将延续下去,因为大喇嘛死后康维——一个显然没有宗教情结的世俗人——将接手香格里拉[1]299。在地域上,去基督化的影响已经波及整个山谷。在香格里拉统治的这片山谷有众多的宗教机构,佛塔、道观、孔庙……[1]165但显而易见,去基督化的香格里拉并未容许谷中存在一家基督教堂或修道院。这就不难理解,在初来乍到女教士布林洛小姐(Miss Brinklow)的眼中,整个香格里拉社会是何等的伤风败俗、异类不堪!所以她决定留下来传教[1]278,也就是对香格里拉实施继佩洛特之后的第二次基督化,她会成功吗?小说并无后文。但是,修士佩洛特的经历不禁使人感到,去基督化早晚会在女教士本人身上生效。
三、香格里拉宗教现象读解
(一)香格里拉的基督化是西方基督教普世化过程的缩影
近代西方不仅推行殖民主义,而且同时推行基督教普世主义。“普世主义是基督教思想教义的一个基本原则”[4],其宗旨是使“基督教从作为犹太教一支的原始基督教向作为一种世界性宗教的基督教转变”[4],也就是使“本土以外的‘未化之民’,被动接受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从而使得原有各种地方性宗教文化被迫同化或消亡了”[4]。为推行普世主义,近代西方大量向全球殖民地、半殖民地派驻传教士,强力传播基督教文化——此时的普世主义其实已表现为宗教殖民主义。
《消失的地平线》提到,小说家卢瑟夫在汉口邂逅法国某慈善姊妹会会长,并拜访了她们设在重庆的教会医院,提到布琳克洛小姐是东方教会成员——所谓东方教会就是设在印度的基督教会,提到年轻的嘉布遣修士佩洛特,为寻觅涅斯托利教派残余,从北京徒步前往拉萨;小说中还写道,佩洛特和布琳克洛小姐到达香格里拉后都试图推行基督教;此外,大喇嘛还说,早在“17世纪时,罗马直接推动基督教的复兴,所凭借的乃是英雄的耶稣会教士……渐渐地,教堂在辽阔的地域得以确立,甚至在拉萨,一所基督教会存在了三十八年之久”[5]134。这些其实都是对近代西方推行基督教普世主义的真实写照,而香格里拉于18世纪的基督化不过是基督教普世主义的一个缩影。
(二)香格里拉的去基督化体现了对基督教世界的批判
殖民主义和基督教普世主义在19世纪末期达到了顶峰。当进入20世纪,随着西方列强在世界大战中被削弱,以及随着世界范围内反帝、反殖民运动的不断高涨,普世主义或宗教殖民主义就只能节节败退了,很多地方实际出现了去基督化,由此可见,香格里拉的去基督化在很大程度反映了这一趋势。对于西方列强,去基督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或无奈的结局,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然而,在《消失的地平线》中,一个去基督化的香格里拉却成了小说极力美化和赞美的对象,这无疑是有悖基督教伦理和西方正统思想的,小说何以有这种态度呢?笔者认为,香格里拉的去基督化恰恰能体现西方进步人士对基督教世界的反省与批判。
《消失的地平线》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初(发表于1934年),那正是两次世界大战夹缝中的特殊时期,对于当时的西方民众,第一次世界大战仍是仿佛昨日的可怕记忆,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暴再次袭来,他们怎能不相信这就是“世界末日”的来临!每当灾难来临,信奉上帝的西方人自然会求助于上帝,然而,上帝再次沉默了。人们会问,这是人类罪有应得吗?人固然有罪,应当受到惩罚,但“什么样的滔天罪行才能配得上如此具有毁灭性的惩罚?”[6]387人们从质问到对信仰的怀疑和诅咒,如战后所谓“失落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和“愤怒的青年”等都是些诅咒上帝的人,垮掉的一代J.C.霍尔姆斯扬言:“我信仰的上帝是残忍的上帝,我不膜拜他”[7]67。同样,《消失的地平线》酝酿去基督化,即否定基督教,无疑也是怀疑和批判基督信仰的表示。
客观上,基督教还应对世界大战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众所周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酿成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8]8,而“基督教(却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扩展的工具”[9]136,这个工具十分得力,1887年,英国军事占领者查尔士·华伦曾说:“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10]400。事实上,不仅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利用宗教的麻痹和绥靖作用,基督教也利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保护伞,进行它的普世化,当它们沆瀣一气,就形成西方列强所特有的政治利器:宗教殖民主义[10]400。总之,基督教对于两次大战的浩劫难辞其咎。考虑到上述基督教的尴尬角色和历史罪责,也就能够理解小说何以酝酿和美化一个去基督化的香格里拉。
这一批判基督教的立场在小说的他处还有呼应和共鸣,比如述及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凶杀、教士间流传的桃色新闻、基督教的妄自尊大等等;再如对女教士布林洛小姐的负面描写。布林洛小姐是四人之一,是虔诚的基督教士,然而,在对待这位虔诚女教士上,小说却极尽冷嘲热讽、恶意丑化之能事,如说她嘴利皮厚得理不饶、嗲声嗲气故作姿态、愤世嫉俗自以为是、一惊一乍好大喜功等等,甚至凭空污蔑她一看到佛塔就联想到雄性器官[1]165。在小说中,飞机是重要的战争意象,在那架被劫持的飞机中,女教士布林洛小姐仍能正襟危坐而无动于衷,正暗示了基督教在战争中的无所作为。所有这些都迎合了香格里拉的去基督化,一致表示出对基督教和基督世界的批判。
四、结语
香格里拉的基督化和去基督化堪称小说的一大看点!当然,《消失的地平线》有许多看点,如昆仑山无极雪峰、雪峰后的宏伟寺庙、庙里的书楼、艺术馆、音乐沙龙、讲英语的前清绅士、二百五十岁的西域喇嘛、弹古钢琴的满族妙龄女子,如此种种——香格里拉的基督化和去基督化不过是其中之一。但是,从小说的层面,香格里拉的基督化与去基督化又和其他看点不同,因为后者基本出于创作的想象。如果说香格里拉的基督化是对西方普世化历史的反映,那么,它的去基督化却是有悖西方宗教或道德伦理的,所以难以想象,它的文学出炉无疑反映了在大战的特殊环境下人们对基督教和基督世界的自觉批判。当然,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渐渐取缔了宗教专制而实行宗教宽容,尤其在启蒙运动后,反对或批判宗教不再被视为异端或大逆不道,更不会招致历史上的迫害。在世界大战烽烟再起的严峻时刻,《消失的地平线》杜撰批判宗教的去基督化,不但无罪,反而应被接受为时代的正义呼声。
参考文献:
[1]HILTON J. Lost Horizon[M]. Kunming: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06.
[2]冯涛.二十世纪的神话—评《消失的地平线》[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2006(8):56 - 60.
[3]邵亚楠,罗英.东方道德取向《消失的地平线》中佛教与基督教的对碰[J].华章,2014(5):18.
[4]陈建明.基督教普世主义及其矛盾[J].世界宗教研究,2004(2):8 - 17.
[5]HILTON,James. Lost Horizon[M]. New York:Pocket Books,1960:134.
[6]斯马特.世界宗教[M].金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87.
[7]HOLMES,J. C. Go[M]. New York:Thunder’s Mouth Press,1997:67.
[8]吴辅麟.殖民主义的恶果[M].卢丽平,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8.
[9]龚学增.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教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136.
[10]陈麟书,陈霞.宗教学原理[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赵佳丽】
Christianization and De-Christianization of Shangri-la——On Religious Phenomena in Hilton’s Novel Lost Horizon
XIONG Lian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Huizhou Polytechnic of Economics, Huizhou 51600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Shangri-la, known as the Western“Land of Peach Blossoms”and modern“Utopia”, is a west-like religious society. Once in its history Shangri-la accepted Christianization, but in the course of time it has peacefully undergone a reversed process: De-Christianization. Christianization of Shangri-la is the epitome of the Christian universalisation of the West in recent centuries, but in an idealized Shangri-la, its de-Christianization can stand as a critique of Christianality and the Christian world.
Key words:LostHorizon; Shangri-la; Christianize; de-Christianize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 5934(2016)01 - 0057 - 04
作者简介:熊练(1975 -),男,湖北黄梅人,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收稿日期:2015 - 07 -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