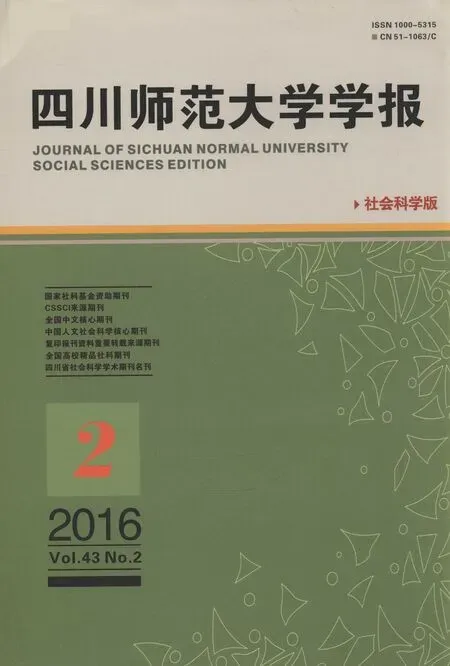大西南抗战小说的审美品格
陈思广,冯 鸽
(1.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2.西北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 西安 710069)
大西南抗战小说的审美品格
陈思广1,冯鸽2
(1.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2.西北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 西安 710069)
摘要:大西南抗战小说遵循现实主义的审美品格,与全国抗战文学一样应和着时代的脉动,以服务于抗战作为文学的最高标准(有时甚至是唯一标准),讴歌英雄,书写战歌,传递中华民族不屈的伟力,为民族的复兴与新生而呐喊。随着典型理论的重申,文学审美性的回归以及题材视阈的拓展,大西南抗战小说的审美性得以迅速提升,涌现了众多优秀的作品,甚至出现了经典作品与典型人物。现实主义审美品格也使大西南抗战小说在表现大后方积弊丛生的昏暗现实时,呈现出更为独特的艺术触角与更为尖锐的矛盾冲突,这使得大西南抗战小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学高度。这也正是大西南抗战小说现实主义审美品格高扬的集中体现,是大西南抗战小说现实主义创作走向深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大西南抗战小说为世界奉献的珍贵遗产。
关键词:抗战文学;大西南;抗战小说;审美品格;现实主义
冯鸽(1970—),女,陕西泾阳人,西北大学国际交流学院教授。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在70年前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大西南军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据统计,八年抗战期间,大西南总计征丁380多万,占全国壮丁总数的27%还多,成为抗日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来源;抗战八年,大西南共派出成建制部队约70万人奔赴前线,其中超过30万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财力物力上,大西南也曾一度承担了超过全国50%的抗战支出,可谓功盖中华[1]前言。大西南小说家在这场浴火重生的抗日战争中,自觉地肩负起历史赋予他们的神圣职责。特别是重庆被确定为陪都后,作为大后方的大西南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所共同期望的挽救民族危亡的复兴之地,大批作家汇聚大西南开创抗战建国的新未来,仅1942年上半年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文化运动委员会招待所办理登记补助和在渝工作的文艺工作者就达200多人。老舍、巴金、茅盾、张恨水、沙汀、艾芜、吴组缃、阳翰笙、姚雪垠、齐同、司马文森、蹇先艾、李广田、林语堂、碧野、陈铨、靳以、路翎等一批小说家,以他们超凡的才华与精湛的小说艺术写下了抗日战争中文艺战线上最恢宏的历史篇章。
中国现代小说兴起于新文化运动,无论是陈衡哲的《一日》还是鲁迅的《狂人日记》都显示出现代小说的新质素与萌芽。“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冲击,“人的文学”观的确立,特别是鲁迅之后的一系列小说所开创的启蒙范式,将现代的意味推到极致,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开启了新的纪元。之后,以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为代表的新文学社团,将“为人生的艺术”与“本着内心”的艺术主张发扬光大,“问题小说”、“私小说”成为风行一时的创作思潮。由于中国的现实境况,也由于“为人生”本身具有更广阔的现实基础和写作视阈,“为人生”的审美诉求遂成为时代的主潮。与此同时,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小说等现代主义创作思潮在夹缝中悄然生长,革命加恋爱的左翼文学也在与现实的搏击中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中国现代小说在多元交融的格局中发展、壮大,成为抗战前期最有实绩的文学体裁。
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这一格局的走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现代小说的审美诉求迅速向文学的政治化转向。这一历史的必然正如《光明》社同人所说:“一旦清算血债的大抗战爆发,我们也不否认文艺的功用,也不要求每人都抛弃笔杆。不过那时笔下所写的应成为前线的冲锋号,应成为后方的动员令!”而“文艺上‘要求的技巧,是钢的锻炼,是铁的熔冶’”[2]。也如同《抗战文艺》的《发刊词》所宣称的那样:“在震天动地的抗战的炮火声中,必须有着和万万千千的武装健儿一齐举起了大步的广大的文艺的队伍;笔的行列应该配布于枪的行列,浩浩荡荡地奔赴前敌而去……在我们钢铁的国防线上,要并列着坚强的文艺的堡垒。”[3]这种要求文艺应成为“前线的冲锋号”,“后方的动员令”,要求“笔的行列应该配布于枪的行列,浩浩荡荡地奔赴前敌而去!满中国吹起进军的号声,满中国沸腾战斗的血流,以血肉为长城,拼头颅作爆弹,在我们钢铁的国防线上,要并列着坚强的文艺的堡垒”的呐喊,不仅是《光明》、《抗战文艺》同人们的心声,也是全中国爱国志士的心声。于是,文学服务于现实、服务于抗战这一政治目的成为时代的需求,也成为爱国作家们自然遵循的审美法则。虽然此后还有不同的审美诉求在蜿蜒生长,但丝毫无妨现实主义审美诉求成为创作的主潮。因为“抗战的烽火,迫使着作家在这一新的形势底下,接近了现实:突近了崭新的战斗生活,望见了比过去一切更为广阔的,真切的远景。作家不再拘束于自己的狭小的天地,不再从窗子里窥望蓝天和白云,而是从他们的书房,亭子间,沙龙,咖啡店中解放出来,走向了战斗的原野,走向了人民所在的场所,而是从他们生活习惯的都市,走向了农村城镇;而是从租界,走向了内地……使文学活动真正的放到了战斗的生活原野中去”[4]。相应地,小说的选材、主题、人物、手法等都在抗战的宗旨下发生了重要的转化。当然,这一审美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放大了文学的审美功利性,但它符合特定时代的文学诉求,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必然。对此,朱声就说:“中国抗战文学乃历史必然法则在某阶段之反映,乃中国历来反帝国主义反封建残余之新文学运动发展中更高、更伟大之阶段。继承过去之战斗任务,批判接受过去之战果,如:‘五四’之文学革命启蒙运动,‘五卅’以后之革命文学运动,‘九一八’以后之‘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现实主义运动等发展所得之战斗内容;大众化运动与现实主义运动之成绩;西洋文化之影响与民间文艺之发掘成绩;若干典型创造之成绩……等等。”[5]在这一创作大潮下,其它形式的审美诉求如现代主义、浪漫主义等或退隅一角,或自然消匿,直到战争结束后才渐有起色。
大西南抗战小说当然也不例外。遵循现实主义审美品格的大西南抗战小说,与全国抗战文学一样,应和着时代的脉动,以服务于抗战作为文学的最高标准(有时甚至是唯一标准),讴歌英雄,书写战歌,传递中华民族不屈的伟力,为民族的复兴与新生而呐喊。艾芜的《萌芽》写青年林志超志愿当兵,从军抗日,却引起了那些时刻想逃逸、抓壮丁被征来的军人的疑惑、嘲笑和猜忌,但后来大家在林志超满怀信心、力争救国的信念的影响下,逐渐明白保卫家乡的道理,决心奋起抗日。小说通过对新人新兵形象的塑造,表现了国家意识在乡土民间群体中的逐渐觉醒与自我救赎的历程。《两个伤兵》通过描写火车上两个伤兵和勤务兵之间的对话,透露出抗战士兵缺水断粮,常常食不果腹,身涉险地,随时有生命危险,但是抗战热情丝毫不减,充满了胜利的决心。司马文森的《一个英雄的经历》同样写了一个二等兵在敌强我弱、艰险危难中活捉日本兵的故事。这个二等兵虽然出身农民,入伍不久,却朴实勇敢,冲破敌人机关枪的扫射,在烽火硝烟中立下了大功。蹇先艾的《两个老朋友》刻画了李寿翁、月波两位老人虽然身陷沦陷区不得不靠变卖字画维持生计,但却始终坚信抗战一定胜利——“这不过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难道我们中国的军队就没有打回来的一天吗?”[6]235而《牧牛人》中的河南人王全德在日军占领汉口后流亡贵州给他人放牛,但父亲却在逃难途中去世,为了给亲人报仇,王全德毅然投身到抗日队伍中。许多作家甚至放弃原有的创作个性,努力践行抗战文学的新目标,即是如此。但不久读者就发现,这种激情式的写作所带来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也是显在的。虽然有人以时代的急促、客观的需要为由,认为只要“差不多”就不必苛求,甚至主张为“差不多”三呼万岁[7],但人们还是清醒地看到,战争的残酷性与长期性远超乎人们的想象,中日两国的军力差距也大大超乎中国作家的想象,仅凭一时的激情与呼喊并不能带来战局的转变,而那些大量掩埋于事的抗战小说又因文学性的丧失很快褪去了原有的光泽。于是,冷静代替了急躁,客观代替了主观,将抗战文学本质上看作是文艺而不是宣传[8],倡导文学审美性的诉求,呼吁抗战文学回归文学——即以“写人”为终极目标的声音又回响文坛。茅盾就指出:“现在众所诟病的‘差不多’,批评家所指出的‘不够深入’与未能创造典型人物,我以为大半是为了这本末倒置的缘故。”[9]于是,写人,写战争中的人,就成为作家们追求文学本性的自在诉求。“只有多读‘人’,多研究和分析‘人’,才能表现和反映生活在现实社会里面的‘人’”[8]。同时,关于什么是抗战文学的内涵也扩大了许多,即不再将抗战文学仅视为表现战争、战场、战役的文学,而是将表现当下与中国抗战现实生活有关的都视为“抗战文学”[8]。这或许有些扩大,但毕竟开拓了抗战文学的创作视阈,为抗战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打开广阔的艺术空间。巴金1941年12月于桂林完成的短篇小说《还魂草》就表现了战争中人的内心诉求,小说以作家在重庆的一段生活为素材,讲述了轰炸下的重庆房屋坍塌、店面倒闭、难民横尸街头、流离失所的悲惨遭遇,同时表现了孩子间真挚、深厚的友谊,成为战争中点燃希望的光热,抚慰了作者灰暗、悲怆的内心。主人公黎先生,寄居在一位开书店的朋友家,战争的空袭、浓重的烟雾、凌乱的生活以及与朋友敏的失联让他心情沉重、压抑,朋友的女儿利莎善良的心地、纯洁面孔和天真的笑容给他带来了快乐,渐渐驱散了他心头的阴霾,尤其是利莎和朋友秦家凤之间纯挚的友谊深深地感动了他。两个女孩常常缠着黎讲故事,他把有人为了救活朋友就用自己的血培养出了一种还魂草的民间传说讲给她们听,两个女孩听了大为震动。后来秦家凤遇难身亡,利莎痛苦不已,要用自己的血浇灌出一株能救活朋友的还魂草。黎在感动之余,更深切地感受到了巨大民族灾难中的一点光亮,抗战的信念正像还魂草一样给了人们生存的希望和爱的力量。黎的朋友望着轰炸后的一片废墟,说,他的书店还会重建的。作家以一个平凡的故事,一点微弱的光、热,输出的一点能量,抚慰着战争中悲苦的人们。
典型理论的重申、文学审美性的回归以及题材视阈的拓展,使得大西南抗战小说的审美性得以迅速提升,涌现了众多优秀的作品,甚至出现了经典作品与典型人物,如《在其香居茶馆里》的邢幺吵吵等,这是大西南抗战文学的重要收获。联保主任方治国相信新任县长一定严治兵役的承诺,遂向县里密告,于是县里派人将镇里有些声望的邢幺吵吵的二儿子抓丁,这让邢幺吵吵很没面子。邢幺吵吵倚仗着他哥哥及舅子是县里有影响的人物的关系,已躲过了四次兵役且没有交半文壮丁费。但这次不同了,一是人已经被抓走,二是新县长宣称要严肃役政,是真是假尚不清楚,邢幺吵吵只好在茶馆里找方治国“算账”。正当双方各不相让,从动口到动手以至于要上县城告状之际,传来了邢幺吵吵的二儿子因报数报错而被责打后放回的消息,一场正剧以闹剧收场。“它恰如一幕经过精心构思的绝妙的讽刺喜剧,淋漓尽致地揭穿了抗战时期国统区在兵役问题上的黑幕,尖锐而深刻地暴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大后方’豪绅集团的横行不法,以及他们互相争斗又互相勾结,尔虞我诈、营私舞弊的丑恶本质”[10]。小说人物对话简明传神,矛盾冲突起伏有致,选材以小见大,构思精妙奇绝,在不动声色中戛然反转并收尾,将沙汀讽刺小说的艺术推向了顶峰。
更值得称道的是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它所体现出的现实主义的审美品格,不仅是新文学长篇小说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新文学现实主义成熟的重要标志。小说把战争和历史事件作为生活流程的底色背景,避开了自己不熟悉的内容,没有直接描写惨烈的战争和战场。从“七七”事变开始,到抗战胜利,虽然记述了一个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如“七七”事变、松沪会战、太原会战、台儿庄大捷、汪伪政权建立、珍珠港事件、日本投降等等,但这些事件都是通过人物的活动、所见所闻和思想来叙述的,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平民的日常生活细节性的状态来书写宏大历史,产生了一种具有可触感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效果,使宏观的文化反省在具体细节中表现出来,将人性、传统文化、日常生活等都置于“战争”框架中审视,从而使社会、历史、文化、人性等都呈现出了非常极致的形态,产生了一种反观效应,将战争从文学、文化的角度进行了认识和剖析反思。其实,这也是老舍擅长熟悉的市民世界在战争中的表现。
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沦陷的北平为背景,描写了小羊圈胡同中的住户在沦陷八年间屈辱偷生的生活遭遇、家庭变故和人事沧桑。其中以四世同堂的祁家为中心,以祁家长孙祁瑞宣的心路历程为主线,表现北平民众在日寇铁蹄下的挣扎与抗争。透过老北京祁老人从一个目光短浅的自私老人一步步被逼成了反抗者,表现了国家民族的命运和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关系以及文化的改变,描绘出市民社会的封建理想家庭模式四世同堂在民族灾难到来之时崩毁的过程,由此对以北平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国社会基层组织家庭、胡同社区、邻里群体等单位结构深入剖析家庭与国家、个人与民族、生命与自由等问题,对民族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剖析了国民性的弱点,具有明显的民族图存意识和社会批判意识。“祁家”这个复杂的封建大家庭,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具体象征。可以说,小说延续了抗战前老舍对于国民性的反思,进入到一个更为宽广的、深入的、理性的反思境界。
“四世同堂”的小说题目,明确表明了其反封建礼教家族文化的批判姿态。在战争冲击下,对家国关系进行了生动诠释,鲜明地指出“没有国就没有家”的真理。“国家”和“家”产生紧张的冲突时,对“小家”的过分执著,导致对国家利益的麻木与漠然。可以说,《四世同堂》是抗战文学中对家国关系进行诠释的代表作品。
老舍自己曾说:“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作洋奴。这两种认识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11]637正是基于这样的批判意识,老舍对民族性的关注尤为深刻,对侵略者的罪行尤为痛恨,笔下处处流露出国家残破的刻骨之痛。也正因为这种文化反省,才有了对众多小人物屈辱、悲惨的经历以及抗战中惶惑、偷生、苟安的社会心态细致的描写,也才有了对文化重建的期待,再现了这些人物在国破家亡之际缓慢、痛苦而又艰难的觉醒过程。
战争将平民的生活和国家的命运之间的距离消弭掉了,他把每个人都卷进来了。祁瑞宣是小说中的重要角色,始终在彷徨中矛盾着,一面是民族大义让他应该离开家庭投身抗日,另一面却是家庭的责任、孝道义务使他不得不在沦陷区屈辱生活。当抗战爆发后,血与火的洗礼才使他深刻地理解到了国家对个人、家庭的意义时,他接受了地下党的任务,成为了抗日志士。还有独善其身的诗人钱默吟,战前吟诗作赋,苟安懒散,但儿子的牺牲、自己的被捕以及周围人物的遭际激发了他的爱国情结和民族情感,一身正气,不甘忍受屈辱,即使被捕、坐牢、被严刑拷打,也决不失节,开始从事地下抗日工作。清朝侯爷的后裔小文夫妇、汉奸女儿高第、姨太太桐芳、里长李四爷等都被迫从自己狭小的世界走出来,也开始敢于同侵略者相拼,宁愿站着死,决不跪着生。这些表明了北平市民的觉醒,在抗战炮火的洗礼中,他们不断清除精神上的积尘污垢,摆脱了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开始了新的生活,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逐渐觉醒,迸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最后,表面上毫无英雄气概的人们成了胜利者,他们宁死不屈,顽强抗争,迎来了胜利。《四世同堂》还通过对祁瑞全等理想新人的描写,表达了作者对战后重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希望和想象。祁瑞全这一代人的国家民族意识已经和老一代人完全不同,勇敢坚定,打破了传统家族观念,而将国家的荣辱存亡当作他的生命价值之所在。这些具有民族国家意识的中国人都是抗战的脊梁。老舍的结论是:中国人民觉醒了,中国大有希望。在抗战期间,中国的一般民众成为了真正的民族主义者。这才是八年抗战的历史胜利意义。
这种文化剖析和反省,是充满爱,充满民族正气、现代意识和自我批评精神的。这是一种在否定旧传统文化后积极重建新文化的努力。要指出的是,老舍的抗日,是属于市民阶层的抗日,他描写了他们的善良平和、他们的软弱和痛苦、他们的苟且偷安等性格弱点和局限,也写出了他们的抗争、觉醒。他述说了一个民族在战争中、在侵略压力下被迫逐渐认识自我,反省自我,走出千年古国的梦魇,开始觉醒,开始反抗,最终在血腥的侵略战争的长期抵抗中觅回了个人的以及国家民族的尊严,中国人终于站起来了。相对于他在写《猫城记》时对中国的绝望,此时的老舍没有了悲观心理。老舍知道,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子具有巨大的精神韧性和民族凝聚力,在抗战时期,它便是为国牺牲、保卫国家独立与尊严的反抗战斗精神的来源。他的抗日小说,是反省中国现代市民的国民性的一种极致表达,也是中国现代民族解放斗争的一面镜子。
遵循现实主义审美品格使大西南抗战小说在表现大后方积弊丛生的昏暗现实时,呈现出更为独特的艺术触角与更为尖锐的矛盾冲突,也使得大西南抗战小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学高度。1938年4月,张天翼发表了著名的讽刺小说《华威先生》,引爆了国统区关于“讽刺与暴露”的论争,虽然争论有分歧,但在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面前,大家还是认同讽刺与暴露的现实意义。沙汀也认为:“我们的抗战,在其本质上无疑的是一个民族自身的改造运动,它的最终目的是在创立一个适合人民居住的国家,若是本身不求进步,那不仅将失掉战争的最根本的意义,便单就把敌人从我们的国土上赶出去一事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出乎情理以外的幻想。”“既然如此,那么将一切我所看见的新的和旧的痼疾,一切阻碍抗战,阻碍改革的不良现象指明出来,以期唤醒大家的注意,来一个清洁运动,在整个抗战文艺运动中,乃是一桩必要的事了。隐瞒和粉饰固然也是一种办法,可以让热情家顺顺当当高兴一通,但在结果上,却会引来更坏的收场。”[12]
蹇先艾的《破裂》就写了一对年轻夫妇张琴玉和朱明方之间感情破裂的故事。逃难途中失去女儿的两人历经千辛万苦来到K城,丈夫朱明方却在腐败的大后方生活中整日抽烟、喝酒、赌博,梦想着怎样投机取巧、发国难财,成为一个行为堕落的小官僚。最终两人感情破裂。两人的分道扬镳其实来自对民族大义的不同理解,张琴玉离开后寄回信说:“至于我离开你的理由,没有别的,便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已经分道扬镳,我不能跟着你被那种霉烂的生活再霉烂下去,我需要一个新的,有刺激性的前途。”[13]而《春和客栈》写作者因撤退而夜宿客栈,遇见了农村妇女王腊妹,二人围炉夜谈。王腊妹的丈夫被拉壮丁去打日本,但国军抗战不力、军队溃散,丈夫也下落不明。王腊妹对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深有怨气:“你不要瞒到我,我听到好多人说,他们打个鬼仗,日本鬼子来了,跑都跑不赢。”[6]274艾芜的《某城纪事》描写一位某商会会长兼任抗战后援会的会长,一面高唱抗战,一面寻欢作乐,刻画了一个“抗战不忘娱乐,娱乐不忘抗战”的国统区腐败官员的典型形象。而《荒地》中的村民由于无力上缴田租而被迫迁居到荒山野地,开垦荒地,书写了国统区乡村农民深重的苦难,暴露了国统区民不聊生的凄凉景象。不过,在大西南抗战文坛中,表现大后方积弊丛生的昏暗现实最为有力的作家是沙汀,他以一个清道夫的姿态,以《在其香居茶馆》、《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等力作为代表,向世人揭示了地处西南一隅偏僻乡村小镇上的基层官员与各类村民们,由于根深蒂固的文化浸淫和思想的麻木与愚昧,千万百计地抵制、阻挠民族解放战争赋予每个公民的责任与义务,并以之为荣、以之为职、以之为生的丑恶现实。他们以家庭、血缘、裙带关系为轴心,以权力为纽带,层层欺诈,个个挤压,甚至不惜扑向身处更底层的孤独者,这就使得那些身处最底层的无助者只能承受命运的摆布,无助而无奈,凄苦而惶然。《防空——在“堪察加”的一角》写抗战开始,面对敌人可能来临的轰炸,愚生看到了做防空任务的重要性与机遇。经过短期培训后,他做了县里第一任防空主任。这一轻闲而又得钱的工作被别人所嫉妒,于是督学将农民在地里发现的未爆的炸弹拿来,看他如何处理。愚生被炸弹可能爆炸的后果吓怕了,听从了家里人的意见,借故有雨而没有及时前去处理。几天后,当他去公园看炸弹时,发现已被同样参加培训的小老板做了相应的处理,也由此赢得了县长的信任,愚生的防空主任一职由小老板代替。作家讽刺了愚生的机敏、投机但却胆小无能的性格,实际上也告诫那些想依靠投机与小聪明谋得一己之利的人是不可取也是不长久的。《联保主任的消遣》写川西北某县的联保主任幽居于山城一隅整日饮酒、品茶、吃牦牛肉,听曲、逗乐、找消遣,坚守着人生享乐主义,毫无抗战意识,置国家危亡于不顾,不仅如此,而且胡乱派发救国公债,昏聩无能,使得民怨难息。作家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享乐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揭示。巴金同样如此,其《寒夜》通过对抗战期间小公务员曾树生与汪文宣命运的书写,把罪恶的战争打破了普通家庭的平衡状态,使他们最本质、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都直接暴露在了一种特殊的极端环境下,并且放大,挤压,终至无力把握,只得漂流、只得承受的悲剧命运暴露在人们面前,将自己对战争吞噬人生、毁灭理想、摧残青春与生命的愤怒体验入木三分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无疑是大西南抗战小说现实主义审美品格高扬的集中体现,是大西南抗战小说现实主义创作走向深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大西南抗战小说为世界奉献的珍贵遗产。
大西南抗战小说在现实主义审美品格的滋养下成长、壮大,成为中国抗战文学中一道永不磨灭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
[1]周勇.西南抗战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
[2]本社同人.我们的宣言(二)[J].光明,1937,(4).
[3]发刊词[J].抗战文艺,1938,(创刊号).
[4]罗荪.抗战文艺运动鸟瞰[J].文学月报,1940,(创刊号).
[5]朱声.中国抗战文学论[J].斯文(半月刊),1941,(14).
[6]周明.蹇先艾文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7]郭沫若.对于文化人的希望[N].救亡日报,1938-02-19.
[8]罗荪.漫谈抗战文学[J].学习生活,1942,(1).
[9]茅盾.八月的感想——抗战文艺一年的回顾[J].文艺阵地,1938,(9).
[10]唐沅.波澜迭起巧铺排——《在其香居茶馆里》结构艺术赏析[J].名作欣赏,1983,(1).
[11]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M]//老舍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12]沙汀.这三年来我的创作活动[J].抗战文艺,1941,(1).
[13]蹇先艾.破裂[J].文学创作,1943,(4).
[责任编辑:唐普]
Aesthetic Characters of Novels about Wars of Resistance in Southwest China
CHEN Si-guang1, FENG Ge2
(1.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2.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9, China)
Abstract:Novels about wars of resistance in southwest China follow realistic aesthetic characters, accord with the highlight of times with other anti-war novels, hold the highest standard (sometimes even as the only standard) of serving wars of resistance with literature, sing high praise for heroes, write epics for wars, reflect unyielding perseverance of Chinese nation and yell for its renaissance and reborn. With the reiteration of prototype theory, regression of literary aesthetic quality and expansion of themes, aesthetic quality of novels about wars of resistance in southwest China is quickly promoted, many good novels, even masterpieces came out and many typical characters are built. The realistic aesthetic character makes those anti-war novels full of sharp conflicts and special artistic quality when revealing the dark reality in rear areas, which enable them to come to an unprecedented literary height. Those epitomize the realistic aesthetic character of anti-war novels, symbolize the deepening of realistic literary creation of anti-war novels and become the precious legacy of anti-war novels to the world.
Key words:Literature about wars of resistance; southwest China; novels about wars of resistance; aesthetic character; realism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2-0121-06
作者简介:陈思广(1964—),男,四川南充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2015-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