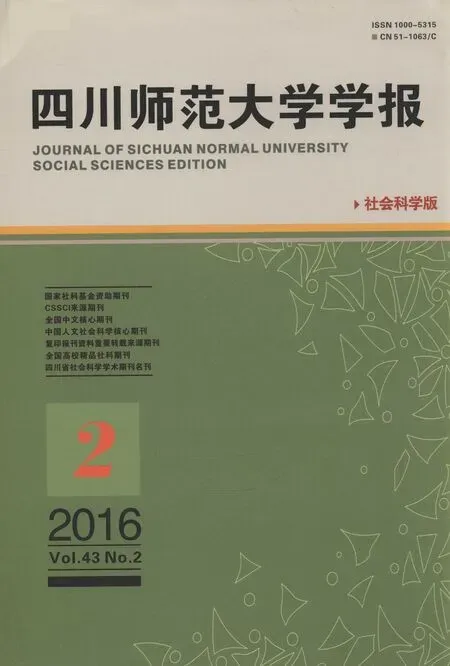“要人命”的教科书——小论黄晦闻的“广东乡土教科书”
石 鸥,李彦群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037)
“要人命”的教科书
——小论黄晦闻的“广东乡土教科书”
石鸥,李彦群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037)
摘要:中国漫长的教育历史里,谁都无法轻视小小的课本。教科书的每一次“出格”都会立即引来高度的社会关注甚至焦虑。即便离各种高厉害考试很远的、相对边缘化的乡土教科书,一旦它跨界乡土,触及敏感问题,就可能会惹出不小的麻烦。黄晦闻编著的《广东乡土教科书》即为一例,它不但掀起了一场关联一大族群的身份认同的风波,甚至还因它出了人命,最终逃不脱被禁止的命运。该教科书事件表明,薄薄的乡土教科书竟然有足够的力度穿透乡土社会沉寂的外壳,激荡起乡村民众炽热的民族情感,建设有厚重底蕴的乡土教科书对于修补已破坏殆尽的乡土社会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该教科书事件的发生,或因为无知(不了解教科书这一文本的独特性),或因为轻视(以为学术自由、文责自负,怎么写都不会有什么关系),或因为权力(包括学术的霸权),警醒我们教科书文本的编撰必须慎重对待。
关键词:乡土教科书;广东乡土教科书;黄晦闻(黄节);教科书风波;族群认同
中国漫长的教育历史里,谁都无法轻视小小的课本。教科书占据了教育文化的中心地位。教科书的每一次“出格”都会立即引来高度的社会关注甚至焦虑。即便离各种高厉害考试关系很远的、相对边缘化的乡土教科书,一旦它跨界乡土,触及乡民的敏感问题,比如身份认同问题,就会惹出不小的麻烦。黄晦闻编著的《广东乡土教科书》即为一例。
一大学者和小课本:黄晦闻的“广东乡土教科书”
黄晦闻(后改名黄节)①,清末民初大名鼎鼎的学者,既有严重的反清情绪,也对新文化运动不屑,既淡泊名利,又有多房妻妾,更以嘲讽梁启超、漠视胡适等新派学者著称。身为北大教授,他一向教学认真。据弟子萧涤非回忆,黄晦闻开过一门选修课,只有两个人选修,有时候一人请假,课堂上就只剩下萧氏一人,黄照讲不误,依然声如洪钟,隔壁教室也能听见[1]5。1935年1月病逝于北京寓所,其哀悼会以“国师”的规格在南京召开,追悼会由蔡元培等发起,行政院长汪精卫亲临主祭,章太炎、胡适等撰写挽联,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将逝者生平言行著述宣付国史馆立传。胡适在追悼会上说:“我同晦闻先生前后共事二十多年,虽则没有个人交谊,今天我参加追悼会,是我心中有其人,敬仰他学问和品格。”[2]282事实上,黄、胡二人的学术观点和思想倾向冲突颇大。可就是这个名头响亮、严谨而极富个性的大学者,却也有在阴沟里翻船的隐痛,尤其令人难堪甚至想不通的是,起因竟是在毫不起眼的乡土教科书上,对他来说,也许会认为实在是牛刀小试的事情。
乡土教科书也称乡土教材。一般是以学校所在地的自然、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民族、民俗等为内容编写的补充教材。多由学校或者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或个人编写。1904年,晚清政府推行癸卯学制,仿照西方与日本,尝试在初等小学校开展乡土历史、地理、格致教育,以培养忠君爱国思想,由此掀起了推行乡土教育、编撰乡土教科书的热潮。
就全国而言,其时推动乡土教科书最力者为颇有反满倾向的国学保存会。该学会是黄晦闻与章太炎、邓实、马叙伦、陈去病、刘师培等在上海创立的,以“保种、爱国、存学”为宗旨,阐发学术传统,宣传反清思想。而国学保存会的乡土教科书建设中,又数刘师培、黄晦闻等最为努力。有研究指出,20世纪初年的乡土历史教科书约有16种,其中由国学保存会编印、乡土教科书发行所发行的有7种,刘师培编著了其中的三种(《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安徽乡土历史教科书》和《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都系1907年出版[3]129。其实,刘师培不但编撰了乡土历史教科书,还编撰了若干种乡土地理教科书以及其它教科书。除了刘师培,在乡土教科书中成绩显著者就算黄晦闻、陈去病(陈庆林)等人了。
1907年始,推崇旧学的黄晦闻,先后出版了新式教育倡导的多种乡土教材,包括《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广东乡土格致教科书》等,均由国学保存会编辑印行。其编辑形式和体例,与刘师培所撰《安徽乡土教科书》相似,线装竖排,内容组织也颇为接近。《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含沿革、总论、区划、海岸、山脉、河流、潮汐、人种、丁口、田赋、通商港、铁路、航路、驿路、电线、邮政、电话等内容。该教科书的绘图者是他的好友、画家潘铁苍。
黄晦闻的《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似乎只出了第一册,“专备广东省初等小学第一二年级第三年上一学期地理教科之用”,“初等小学第一二年,讲乡土之道里建置,附近之山水,以及本地先贤之祠庙遗迹等类。第三年上一学期,讲本县本府本省之地理山水”[4]1。该书还类似于广告一样宣称该书的后几册即将出版发行,但一直没有发现乡土地理其他几册的实物(“乡土历史教科书”续出了后两册),我们推断其实并未完成出版。国学保存会的其它乡土教科书也多有这种情况,如刘师培的乡土教科书也说后几册马上出版,但事实上并没有出版[5]215。
二因“人种”而出“人命”的“乡土教科书”
正当黄晦闻信心满满地推出自己的乡土教科书时,坏消息接踵而至。先是他编的《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遭到地方士绅的反对和上诉,结果是他的这两本书均没有被学部审定通过。不能通过审定,就意味着不能进学校、不能进课堂,而教科书不能进学校进课堂简直就是教科书命运的终结。不但他的教科书没获审定通过,而且还被禁了,不能进图书市场零售。该书还频频引出纠纷,越闹越大,最终竟然要了一个人的命。这都是因为他的教科书中出现了敏感内容,即:客家人不是汉种。
黄晦闻在《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第12课)中介绍了广东的“人种”。就是这一课,他把客家人说成是非“汉种”,这一下等于捅了马蜂窝,一片哗然。书中写道:
粤中有单纯之汉种,则始自秦谪徒民处粤,自秦以前,百粤自为种族,旧有君长臣服于越,越为夏少康庶子无余之苗裔,故少康种族有分徒岭南者是为汉种,于百粤种混合之族名之曰獞。今犹有獞、猺、獠、黎、蜑族、客家、福狫诸种,散处各方。[4]6-7
课文最后用图表形式把“汉种”与“百粤诸种”、“外来诸种”并列开来。这等于将客家人划出“汉种”以外,属于与“汉种”并列之“外来诸种”范围里(还有福狫、蜑族),也与其他带“犬”字旁的各少数民族并列(属于“百粤诸种”),如“獠”、“猺”等(显然这些都是对少数民族的藐视,但这也不能责诸黄晦闻,这些字并不是他创造的)②。
黄晦闻这篇课文,涉及一个由族群到民族的身份认同的大事,必然引起极大关注,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特别是引起了客家士子的极度愤慨,部分客家士子对黄晦闻乡土教科书反应之强烈前所未有,甚至有客家士子因此一度气绝身亡。
当时的《兴宁县乡土志》述及当地一位客家士子胡曦时说:胡曦(字晓岑,1844—1907),岁丁未(1907)卒,先卒前数日,见广州某编乡土史,诋客族非汉种,群起与争,尚考证客族源流,洋洋万言,后与友人纵谈至夜半,旋瞑目,年六十四[6]。这里“广州某编乡土史”应该就是指黄晦闻编著的乡土教科书。
历史学家罗香林为胡曦撰写的年谱上亦提到此事:“上海国学保存会顺德黄节晦闻,撰地理教科书,于客族源流,多所误解。粤中客属人士,闻之大哗,多为文与辩。并呈大吏,禁止刊行。经广东提学使,牌示更正。兴宁兴民学校诸教习,乞先生为粤民考,以示信将来。先生为文数千言,详实称最。未几即婴疾不起,盖绝笔矣。”[7]163
黄晦闻自己恐怕也没有想到,自己一辈子著书讲学,思想广布,未料想因为他的一本毫不起眼的薄薄的乡土教材的一种特定说法,在一定程度上竟然让人激愤而死,活活送了一条性命。
而当时的客家士人,真的有那种如果不为客家人就是正宗中原汉人(进而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正名就死不瞑目的气概。当然,也许落在任何一个族群,都会这样。因为这涉及“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向何处去”等系列根本问题的回答,即身份认同的问题,本质上也是民族认同的问题。这种认同给人一种存在感、安全感,涉及的是个体的社会关系,关注的是个人或特定群体心理层面的归属感,其本质是心灵意义上的归属,强调情感依附与心理安全的保障。
客家人的身份认同危机是受到以学者黄晦闻的教科书为代表的系列冲击而产生的。黄晦闻的教科书显然是要打破或分解这些所谓“客家人”的“汉族身份”的认同,通过外在的某种形式,不承认他们是汉种,消解其属于汉种的合法性存在,而汉人(族、种)是能够为他们提供一种家园和根基感的共同体,他们对汉人、对中华民族也有着高度的民族忠诚和自我认同。这种主动的自觉的由族群向民族的身份认同的努力,与西方的情况大不一样。这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极大包容性的体现,是中国人最宝贵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结。黄晦闻这样做,也许并非有意为之,也许仅仅是当时一种认识的反映。客家学研究权威罗香林先生二十多年后,也相信“黄先生著乡土史时,当不至存有若何不良目的”[8]27。但后果却是一样的,甚至更严重。因为这种冲击或造成这种危机的原因是以教科书的形式出现,即出现在学堂,在师生手上,这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学堂之书,圣贤之书,一言九鼎,只可背记,不可置疑,意义非一般书籍可比。罗香林对此是认同的,他认为,因为“其书为普通教科所用,故深为当时客家人士所不满”[8]27。于是,以死抗争就在所难免。
因了这本薄薄的乡土教科书,除了生命抗争的极端情形,其他形式的抗议更可谓一波接一波。当时广东法政学堂的客家读书子弟邹鲁③是抗议队伍中的主要代表。邹鲁联合其他客家士人包括丘逢甲等,成立了“客族源流调查会”,以证明客家人确属“汉种”无疑。邹鲁在回忆录中写到:
入学不久,看到黄晦闻先生所著的两本书:一本是《广东乡土历史》,一本是《广东乡土地理》,里面竟有客家和福佬都非汉族的言论。我认为他抹煞史实,有伤同胞感情,便挺身出来作文辩斥,同时请客家和福佬的知识分子注意。结果所有客家和福佬主持的劝学所,都一致附从,竟得到了全省的大半数。于是共同推举我领衔交涉,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直到把那错误的言论修正了才罢。[9]18
1910年,邹鲁与张煊更是出版《汉族客福史》一书,申明客家人和福建人汉族源流的纯粹性,该书有丘逢甲的序,力陈以黄晦闻为主的乡土教科书作者将客家人和福建人划为非汉种的荒谬。此书后来在1932年邹鲁任职中山大学校长期间,由中山大学再次出版,邹鲁作序时又重提黄晦闻一事[10]。可见此事的意义。此外,张资平、古直、罗霭其等人分别从语言、起源等多角度申明客家人来自中原,论证客家人与中原汉人同祖同宗同源。
三结局:审查不予通过,逐出学堂,禁止发行
由于黄晦闻在《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中将汉人和獞、猺、獠、黎等少数民族做了划界,把这些少数民族排除到“纯种”的汉人之外,对于当时身为客家人的各路学者、官僚而言,简直就是挖祖坟的事情,群起而攻之势所必然。
当时的轩然大波先在学校闹,再到地方闹,一级一级闹,最后一直闹到清政府学部。由于问题敏感,有关各级教育当局不能不介入,都对此事给予了极大关注。因为此书是上海国学保存会出版的,所以苏省学务公所图书课在审查时就认为部分内容“因种族之别致启争竞之风”,“甚非和平之福”,因此案呈提学司,要求“书肆更正,方准售卖采用”,并得到了提学司的同意,当即牌示更正[11]。接着,两书呈报学部,学部“批令改正后再呈部校阅”,处理相对较轻。然而,时任广东潮州府大埔县劝学所总董饶熙向广东提学使提出申诉,由广东提学使将此事汇报给学部,而且把问题性质说得很严重:用该书教学,“几酿事端”,于是学部查禁了该书。令称:
学部为咨行事。兹据广东大埔县劝学所总董廪生饶熙等禀称:上海国学保存会所编广东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书中以客家、福老为非汉族,拟为周官职方七闽之族,荒谬无稽,该省法政学堂曾本是书宣讲④,几酿事端,请将原书版权撤销等。因查是书,前经呈部已将书中谬误之处逐条籖出,批令改正。今据所禀各节与原籖出者略同,亟应改正。相应咨照贵督请即札饬上海道,饬令亟行改正,其原书应即禁止发行可也。[12]
两江总督接到申诉,处理结果经由学部向广东方面做了传达,处理结论的核心是“停止原书发行”,并转各地实现,理由是该书“以客家、福老为非汉种”,“荒谬无稽,恐启妄分种族之祸”[13]。最后,黄晦闻所编撰的乡土教材,因无法通过审定,而被逐出了学校。
尽管《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是由国学保存会出版和知名学者亲自编撰的,确实有独特价值,但事关族群团结,故不仅没有被学部审定通过,而且还被禁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颁行的《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高等小学暂用书目表及暂用教科书》,在“凡例”中公布了光绪三十三年国学保存会出版的“广东乡土教科书”未能审核通过的理由是:“考证固疏,且因种族之别致启争竞之风,甚非和平之福”[14]。引起民族纠纷,“启争竞之风”,“甚非和平之福”,事关重大,是很严重的错误,焉能通过。学部审查不予通过,完全可以理解。这与百年后今日教科书审定标准之一的强调民族团结是高度一致的。
这一乡土教科书风波的发生,是有其深刻历史背景的。广东地区广府人和客家人长期在经济和政治上存在冲突,有关客家人族群身份的讨论,历来都十分突出。不少社会人士在口头或书面上称客家人为“客贼”,认为其“非汉种,亦非粤种”,是“退化、野蛮部落之民”等等;在一些地方志中,客家人经常被称为“匪”、“贼”。例如,明崇祯《东莞县志》称客家人为“獠”;《新会县志》甚至在客字旁加个“犭”;宣统元年(1909)出版的《新宁乡土地理》,作者站在广府人立场,每论及客家人士时,多以“匪”字称之:“……大隆山:谨案:……客匪常据此山为乱,图新宁之治安者,不可不预防也。”[15]12直至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乌尔葛德(R. D.WOLCOTT)版的《英文世界地理》,其中“广东”辞条下还赫然写着:“其山地多野蛮的部落,如客家等等便是”[16]132。这一切引起了各地各领域的广大客家人的强烈不满与反对,也促使客家人从文化方面来阐明自身族群的渊源。一批客籍贤达纷纷撰文著书,以笔为刀枪,撰述客家历史和文化,为客家人正名立论。
这一乡土教科书风波的发生,也许还与国学保存会这一机构的定性和组成这一机构的人员有一定关系。国学保存会的定位与目的就是保存国学精粹,其代表人物刘师培等人在清末是力主排满兴汉的,他通过自己的历史研究想方设法证明满人和汉人不是一家,满人非中国之臣民,满清是外族夺权,汉人应该奋起反抗;由于对当时执政不满,他还曾参与实施对当时的执政者的暗杀行动,后来在安徽避难于中学,授学之余编撰乡土教科书,不久又逃亡日本,受到日本社会思潮的洗礼;辛亥革命之后思想转向保守,反对革命,这是后话。至少从清末的历史节点上来看,国学保存会及刘师培等人的民粹主义是有历史渊源的,他们将这种种族对立的思想带进了乡土教科书。了解了国学保存会这一段历史,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的教科书在族群问题的处理上是这样的态度,以及他们的教科书为什么无法通过清廷审定之缘由。
旗帜鲜明的国学保存会和黄晦闻本人后来也不得不修改《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避开了这个敏感的内容,将图表上有关客家部分全部删去。只是它再难全面进入广东学堂了,因为清政权的崩溃迅即到来,蔡元培主掌的民国教育部废除了一切清教科书。
四结论:慎对教科书
清末社会,强弩之末,山雨欲来风满楼,知识分子可以痛快谩骂,指点江山的文字俯拾即是,然而黄晦闻万万不会想到,他的很边缘的、学者们不屑一顾的乡土教科书为什么就会惹出这么大的麻烦与风波?社会上不是一直有这些说法吗?是的,社会上可以说,著书立说可以说,就是教科书不能说。黄晦闻忽略了教科书这一特殊的文本,和他一样低估了教科书引起的震荡、一定程度栽在教科书上的学者还有不少人,比如吕思勉,比如顾颉刚等等。
黄晦闻的乡土教科书事件令我们惊讶的是,该书光绪三十三年正月首版,出版地是上海国学保存会,三月底就已经沸沸扬扬闹到广东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且要求其“改正”,四月初一已经见报,七月更是被学部批判和查禁了。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着这么多、这么复杂的事件,竟然都得到了有效解决,晚清教育行政当局的办事效率还是很高的。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系列认知。首先,它表明当时教科书出版印行后能够在最快的时间进入学堂(正月印,估计二月就到了粤地学堂,开学就使用上新教材了,只有使用了新教材,才会发现问题,惹起纠纷),教科书供应渠道非常畅通。其次,说明当时的学生对教科书有很大的发言权。该教科书是被学生掀开其抗议帷幕的,而且这种抗议的表达一路升级,言路至少是畅通的。第三,表明晚清教科书审定制度并不严格。教科书可以先用后审或边用边审,这一缺陷导致清末教科书一度混乱,一本一本的新式教科书,甚至有民主、革命思想的教科书进入学堂,进入大众层面,为清政权埋下了一颗一颗的炸弹,只等谁来点燃它们了。当然,这一缺陷逐渐被各执政者注意到;进入20世纪后半叶,这种对教科书审定的松疏现象完全被杜绝。制度的完善本质上是对教科书控制的加强。
黄晦闻的乡土教科书事件让我们欣喜的是,薄薄的乡土教科书竟然有足够的力度穿透乡土社会沉寂的外壳,激荡起乡村民众炽热的民族情感,检验着乡土文化的核心内涵。这是多么值得期待和欣喜的社会现象。中国长时间里是个乡土社会。乡土,从古至今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主要载体。中国传统社会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所有文化都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乡土教科书正是这一社会本质的体现和弘扬。有乡土教科书读响的地方,不管政治如何、政局如何、物质生活如何,一定是人们心灵安宁、乡村平和、故乡温馨、文化厚重的地方。乡土教科书犹如一支风向标和体温计,插在乡土社会的肌体,测定乡土社会的健康和走向。乡土教科书只能氤氲在浓浓的乡土气息当中。而乡土教科书的枯萎或缺失,只能因为乡土社会的衰落,并加速乡土社会的衰落。如此,仅仅依靠金钱的投入以及这也祭孔那也祭孔的花哨仪式,并不能真正振兴失落的乡土社会和故乡情怀,必须借助文化的力量,要有乡土教科书的书写和阅读,使乡土就在课本中,故乡就在课本中。失去乡土教科书,就意味着失去了乡土,失去了故乡。建设有厚重底蕴的乡土教科书,对于修补已破坏殆尽的乡土社会,具有难以替代的价值。这也许是今天寻找故乡、重振乡村的出发点,如果能够寻找和重振的话。
黄晦闻的乡土教科书事件给我们的启迪是,教科书的作者身份不同,会发生对教科书话语的掌控问题。本为学童而设的乡土教材,往往会从政府推行爱国主义的阵地以及传承乡土文化的载体变成地方上掌握话语资源的群体捍卫自己利益的角斗场。黄晦闻如此写作乡土教材,如此对待所谓少数族裔,和不准《背影》进入课本一样表现出傲慢与偏见,一般只能出自如下三个因素。1.或因为无知,即不了解教科书这一文本的独特性。这恰如二十年后戴季陶批评顾颉刚的教科书一样,“民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学者们随意讨论是许可的,至于书店出版教科书,大量发行,那就是犯罪”[17]45。这实际就是教科书的学术性(科学的求真标准)和意识形态性(在正面程度上包括道德的求善标准)冲突的标志或表现。2.或因为轻视,即以为没有什么关系,学术自由,文责自负。黄晦闻忽略了一点:几乎所有教科书,包括乡土教科书本质上都是政治教科书,都是德性教科书。这导致教科书比任何文本都更能够引起社会关注,教科书作者比任何作者承担的风险都大。这一特性被阿普尔等人总结为:“教材的出版商承受着巨大而持久的压力,他们需要在教科书中加入更多的内容”[18]12。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只能失败。从古至今,谁都无法轻视教科书。教科书的书写变更,会引起社会神经的痛,从百姓到官方。3.或因为权力(包括学术的霸权)。作者自己以及他的团队——国学保存会及章太炎、刘师培这样的人物——以为他们的如椽大笔既然可以指点江山,可以横扫千年,荡涤一切,怎么就不能够任由自己在教科书中尽情挥洒展示呢?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以如此响亮的名头,黄晦闻和国学保存会恐怕从来就没有预计到小小的乡土课本,竟然引起如此大的骚动,并让自己栽倒于此⑤。事实上,教科书绝不等同于作者的学术著作。作为学者的黄晦闻,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另一方面还要介入学堂教育,这本身就是悖论,很难达成“和谐”的。我们的研究发现,教科书文本的教诲性或意识形态性使得某些思想、某些内容必须让路[19]92-97。知识分子有时想利用教科书,到头来会发现他们被教科书利用了。在各方的对峙中,学者往往是弱者,他们的学术追求根本无法有效挑战教科书的意识形态本质以及政治化运作的模式。
我们怀念并铭记此类教科书及其作者,不是因为它是多么的不朽,也不是因为其作者有多么巨大的成就,而是为了提醒我们,薄薄的教科书确是一种烫手的文本,必须慎对。原因在于:它们形塑一代代年轻人!由此,它们形塑国家的未来!
注释:
①黄晦闻(黄节,1873—1935),广东顺德人。1911年秋,广东光复,黄晦闻出任广东高等学堂监督。1923年,孙中山由沪返粤,被推举为大元帅,讨伐北洋军阀,任命黄晦闻为大元帅府秘书长。不久,黄辞职而去,仍回北京大学任教。1928年,应广东省长李济深之聘,回粤担任教育厅厅长。后辞职复任北大教授和清华研究院导师。黄晦闻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授书终生。
②关于本课的文字内容和图表,令人纳闷的是出现了两种不同版本,表述有显著不同,特别是在客家人等敏感表述以及图表上,两个版本不一样,但版权页显示均为1907年正月首版,且均为第12课“人种”,均为国学保存会出版发行。这是一个未解的谜。难道是为了逃避追责,而专门付印了若干“修订本”,只把敏感字眼和图表抽出,以应付审查?或者仅仅是印刷错误?怎么可能错得那么巧呢?这也许是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有误的重要原因。关于此书的出版时间、册数、课文内容,尤其是“人种”一课等的叙述,一直以来多有失误。
③邹鲁(1885—1954),广东大埔县客家人。19岁赴潮州韩山书院读书。历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资政、监察院监察委员。孙中山去世后,任国民党中央三常委之一。1925年11月,参与发起西山会议,后在国民党二大上被开除。
④很有意思的是,该乡土教材本是为小学一、二年级和三年级上的学生使用的,却被广东法政学堂采用。这意味着:首先,乡土教材很重要;其次,乡土教材奇缺;第三,该乡土教材的编著并没有完全实现其适合小学一、二年级用的意图,而是有较大的弹性空间,以至于更高年级学生也可以使用。
⑤学部审定不予通过,禁止发行,要求国学保存会和黄晦闻进行修改。但乡土教科书市场需求已经搅动起来了,它不会等待,不能等待。还等不及黄晦闻修订的教科书面世,新的《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至少有黄培堃和蔡铸两个版本,最早的黄培堃的版本就在1907年黄晦闻教科书被禁当年面世)迅速推出,抢占性地填补了这一市场,而且多次重印再版,满足了兴学的需要。教科书的文化属性和商品属性在这里淋漓尽致的展露出来。黄晦闻和国学保存会失去了一个重大机会。
参考文献:
[1]萧涤非.萧涤非文选[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2]邓圻同.诗人黄节在北京[C]//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顺德市政府文体局.岭峤春秋:黄节研究论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3]俞旦初.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黄晦闻.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第1册[M].上海:国学保存会,1907.
[5]石鸥.百年中国教科书忆[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6]罗献修.耆旧录[C]//兴宁县乡土志.1908.
[7]罗香林.胡晓岑先生年谱[C]//兴宁文史:第17辑胡曦晓岑专辑.1993.
[8]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M].兴宁希山书藏,1933.
[9]邹鲁.回顾录[M].长沙:岳麓书社,2000.
[10]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J].历史研究,2003,(4):68-84.
[11]牌示更正乡土历史教科书[N].申报,1907-04-01(11)。
[12]咨江督请札上海道饬国学保存会改正广东乡土教科书文[J].学部官报,1907,(31):45.
[13]札广东提学使广东乡土教科书己令改正,转饬大埔县劝学所总董等遵照文[J].学部官报,1907,(31):44.
[14]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高等小学暂用书目表及暂用教科书[J].学部官报,1907,(31):凡例.
[15]雷泽普.新宁乡土地理[M].1909.
[16]〔美〕乌尔葛德.英文世界地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
[17]张京华.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18]〔美〕阿普尔,等.教科书政治学[M].侯定凯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9]石鸥,等.论教科书的基本特征[J].教育研究,2012,(6):92-97.
[责任编辑:罗银科]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2-0069-06
作者简介:石鸥(1956—),男,湖南新宁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教科书;李彦群(1977—),男,河北隆尧人,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教科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课题全国教育规划项目“百年中国教科书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中的基础作用”(BAA120011)。
收稿日期:2015-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