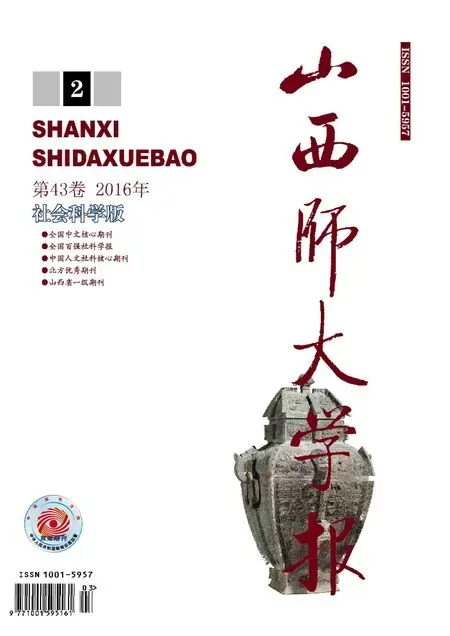抗日战争时期的教科书出版与历史使命
李 彦 群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北京 100037)
抗日战争时期 ,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国共双方军事力量的消长变化,在我国的大地上,形成四个主要的政权系统:伪满洲国、汪伪政权、国统区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战争宣传的需要,以及培养自身管辖范围内的民众对政权的支持和拥护,四个政权系统编辑出版了各种各样的教科书。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时期,教科书的出版必然有其特殊的历史使命。在短短的十四年间,教科书数量之多、品种之杂、版本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考察这一时期教科书出版的情况,以及探讨由此产生的小小的课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一、“战时”教科书的开端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扶植废帝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开始在东北地区开展奴化教育。首先着手清理正被广泛使用的国民政府教科书,连续发布多道命令,强令原有的教科书,“凡有关党义教科书等,一律废止”,但是,因时间紧迫,伪满洲国迫不得已采取了“应急编纂”,“应急改订”的政策,甚至暂时采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的教科书。[1]273这是日本侵略者有意识地以教科书蒙蔽人民、掩盖侵略事实的一种途径。1933年后,伪满洲国面临的内外形势逐渐平稳,其教科书政策有所改变,变为国定制[1]275,同时经济条件的改善也使得伪满洲国有能力大量出版教科书。1933年后,伪满洲国连续出版《初级中学地理通论教科书》《初级中学校国史教科书》《高级小学本国地理教科书》《高级小学校世界地理教科书》《高级小学校东亚史教科书》《国民优级学校满语国民读本》《国民优级学校满语算术书》等。
然而,在国统区,教科书没有为即将发生的战争付诸较多的笔墨,南京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刻意地在教科书中塑造对日本的敌意。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社都仍然依照1932年10月颁布的新《中小学课程标准》编写相应的教科书,形成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正中、北新七家出版社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的盛举。[2]103这一点与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批评国民党的对日政策有很大的反差。1933年初,日本退出国联,妄图以刺刀逼迫傀儡政权肃清教科书中相关的排日、鼓吹民族独立的内容,南京国民政府对此表示了克制隐忍的态度。[3]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采取“审定制”,与国民党的对日政策有关,[4]因为国民党一厢情愿地想把“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变化限制在东北一隅,而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共产党。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受左倾冒进思想的影响,在教科书领域制定审查制度,重点在于清除教科书中的三民主义、四书五经、基督教以及反映地主阶级思想感情的内容,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全面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2]145此外,并无大的建树,也谈不上系统地出版教科书,有时候甚至以军队使用的教科书作为小学教材。这一时期,先后出版《红孩儿读本》《共产儿童读本》《少队游戏》《少队体操》《先苦后甜三字经》等带有浓郁革命气息的教科书。[5]这些教科书文字浅显易懂,贴近生活,深受儿童的欢迎。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地出版的教科书也没有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表示更多关注,原因在于根据地此时面临了非常严重的困难,最后不得已开始长征。此时,有远见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意识到教科书领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无声无息,却比真实的战场更加残酷和复杂。毛泽东在1937年8月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指出,“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这句话虽然发表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但是它属于毛泽东长期思考的智慧结晶,因而,这项指示一问世,就迅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直接促进了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的繁荣。
二、“战时”教科书的类型和题材
较之和平时代,教科书更被看作是塑造民众的最好的利器,因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的八年时间里,教科书出版社之多,教科书类型之广,战争、国防教科书题材之丰富,舆论动员与宣传力量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国统区,大型出版社在教科书的编辑和出版方面,积累了多年的经验,他们深刻认识到教科书对于民众心理的塑造作用,用尽办法,编写了适合国统区需要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既强调了国民党的正统性,也宣传了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英勇牺牲精神和事迹。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学补充教材战时常识》[6],积极鼓动民众抗击日本侵略者,并教导学生在敌机轰炸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1938年,山东国民政府组织编写了影响最大、最系统、最完整的《战时教科书》系列,封面印有“战时”字样,当时编写完成了56册,受战时条件的限制,仅仅出版了“初级国语8册,常识8册,算术6册,高级国语4册,公民4册,历史4册,地理4册,自然4册,算术4册,共计46册”。[7]山东省出版的《战时教科书》,立足于服务抗战、宣传抗战,引导民众在国家危亡的关头,深入思考中国何以落后、怎样摆脱现状的现实问题。在国民党控制的其他区域,也都编辑出版“战时教科书”。在上海,1937年生活书店出版了《战时读本》,该教科书共计四册,由陶行知的弟子张宗麟主编,供民众及当时的小学使用。[8]在山西,作为第二战区的主要区域,在抗战形势最严峻的时候,仅仅控制了乡宁、吉县等7个县。战区长官阎锡山根据山西地区的实际情况,组织出版《兵农合一制度下战时教科书》[9],其中,仅初级小学《国语》一科即有8册。在教科书中,寓有教导民众战时为兵、闲时为农,采取农兵结合的含义。此外,一些有识之士,受传统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影响,自发地编辑教科书。如孙怒潮编的《抗敌教材》[10],焦卓然编的《中华国难教育读本》[11]。这一类教科书除传授一般知识外,还拥有大量的宣传国民党政策、鼓励人们英勇杀敌的内容,有的教科书甚至还编写了怎么制造枪弹的章节。这些“战时教科书”,促进了民族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军民的抗战构建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决捍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193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便以“中流砥柱”的身影,活跃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1937年,改编以后的八路军东渡黄河,到山西前线抗击日军。活跃在太行山地区的八路军成立了多家出版社,如太岳新华书店,以沁源县太岳山命名,先后出版《初级战时新课本》四种8册,《初级算术课本》四种8册,《高级国语课本》两种4册,《高级算术课本》两种4册,《高级历史课本》两种4册,《高级地理课本》两种4册,《高级自然课本》两种4册,《高级公民课本》两种4册。此外,八路军总政治部出版《新战士课本》[12],介绍刘志丹和高岗等领导人以及搞好卫生、反对国民党对边区的进攻等内容;晋冀鲁豫边区教育厅印行《历史课本》[13]《战时新课本——国语常识合编》,战斗出版社出版《国语课本》,晋察冀边区教育研究会出版《抗战时期初级小学国语课本》8册,《抗战时期初级小学算术课本》8册,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在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出版的《算术课本》的封三,专门印有“欢迎翻印”的字样,从侧面揭示出两种可能:一是当时教科书的编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胜任这种工作;再是囿于边区政府经济条件的限制,出版社无力印刷大量教科书,以满足学校的需要。这一点,非常类似于建国后为迅速推行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小学教科书,而采取的“租型”制度。[14]95不同的是,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并不收取任何费用。
在山东革命根据地,1938年成立“胶东国防教育委员会”,专门出版中小学教科书。该系列教科书均冠以“国防”二字,覆盖所有的小学阶段,含有国语、算术、地理、历史、政治、自然等学科。胶东国防教育委员会自1938年出版第一本“国防教科书”开始,便以出版教科书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尤其是1941年,胶东国防教育委员会更名为胶东国防教材编辑委员会后[15],更是以编辑出版教科书为唯一的工作。该系列教科书,不署编著者姓名,大量使用毛边纸,印刷质量一般,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已属难能可贵。
日本扶持下的华北、华东等伪政权的教科书出版较为复杂,汪伪政权成立之前,在北京成立以汤尔和、周作人为首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后更名为“教育部编审会”,编辑教科书,交由新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编审会,专门负责教科书的出版和编辑,[2]132—133同时着力强调汪伪政权的正统性,淡化其投敌卖国的行径,其教科书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小学期间的教科书采用国定制,规定辖区内所有的中小学必须采用政府统一编制的教科书,高中阶段的教科书采用“审定制”[16]。比较特殊的是,汪伪政权的教科书封面上印有“国定”字样,这在我国教科书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至1943年,仅初级中学教科书,汪伪政权先后出版有15种32册,共计有国文教科书1至6册,英语教科书1至3册,外国地理上下两册,本国历史1至4册,外国历史上下2册,公民1至3册,植物、动物、物理、算术、化学、代数、几何各一册(上册),生理卫生一册。如果算上小学的教科书,汪伪政权的中小学教科书将会更多。
早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前,日本帝国主义就凭借其在东北多年的垦殖,逐渐把教科书纳入了殖民统治的轨道。1934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授意下的第一期“国定教科书”编纂成功,交付康德图书印刷所和“满洲图书株式会社”出版发行。第一期“国定教科书”含有初级小学教科书5种12册,高级小学校教科书4种4册,初级中学校教科书6种14册,初级小学校科授书4种6册,共计19种36册。随后,第二期、第三期“国定教科书”相继出版发行,前后合计49种90册。[1]276伪满洲国出版的教科书承担着塑造日本侵略者所希望的国民的责任。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伪满洲国统治的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甘为亡国奴的人们以“伪装本”的形式[17]出版抗日教科书。应该说,伪装本教科书是我国教科书史上少有的一种出版形式,即教科书的封面和装帧严格按照伪满洲国的教科书要求,而其内在的内容,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英勇抗战的文字。外表看来,这类教科书与其他满州国教科书无异,而其内部却涌动着英勇不屈抗击日寇的火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科书出版,逐渐形成一个影响广泛的网络,成为宣传抗日精神、教导民众如何抗日的阵地。
三、“战时”教科书的内容和宗旨
抗日战争期间,因不同的政治需要和战争需要,不同区域的教科书呈现出巨大的反差。首先是纸张、封面、装帧等教科书的外在形式差异。一般来说,伪满洲国、汪伪政权以及国统区的教科书印刷质量较高,多为胶印版,纸张白皙,字体清楚,图文并茂,而根据地教科书印刷比较粗糙,多使用手刻油印,纸张低劣,大量使用毛边纸,没有所谓的版权,并鼓励其他地区的人们翻印。其次是教科书的内容差异。教科书为不同的政治集团服务,这是教科书本身改变不了的依附性特点所决定。教科书内容的分歧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国共两党主导下的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教科书,一是日本侵略者主导下的投降卖国的教科书。国共两党的共同目标是抗击日本侵略者,所以教科书均以抵抗外族入侵为第一要务,首先是在学生幼小的心灵中,建立起国家正处于危亡边缘的情境,让学生明了残酷的现实,激发民众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爱国情怀。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的教科书则淡化侵略,粉饰现实,为日本的军事入侵清除意识形态上的障碍。
1932年,上海“一二5八事变”之后,商务印书馆遭遇日本帝国主义轰炸,损失惨重,为激起民众的同仇敌忾之心,商务印书馆率先把目光投到抗日救国的题材上,在1933年,出版《复兴教科书》系列,当时参编的人达到210人之多。据统计,《复兴教科书》系列,共计183种738册,[18]除在国内使用以外,部分教科书还远销东南亚地区,供当地的华侨小学使用。自商务印书馆起,反映抗日内容的教科书的出版愈来愈多,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多家出版社都出版了有关抗战的教科书。1933年出版的《复兴教科书》系列中的初中公民教科书的“编辑大意”指出:“我国固有的道德,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都是我国民族的特性。”这等表述是在国民性上为中国民众注入新的精神气质,虽然“忠孝”之类的语言来自传统典籍,但是在外敌入侵的大背景下,忠孝、仁爱等具有特殊的意义。
1942年,正中书局出版的《国语常识混合编制抗建读本》,[19]其扉页的编辑大意说:“常识课包含三民主义、公民、史地、自然、卫生,以及各种有关抗战建国(如光荣战绩、兵役宣传、地方自治、生产建设)等材料,或用提示,或用表解,务使儿童养成现代国民基础知识。”在抗日战争最紧迫的时候,教科书反映了既要抗战,又要着眼未来的建设和国民性的培育思想。共产党根据地的教科书亦有相似的表述。冀太行政联合办事处出版的《高级小学国语课本》,以“民族的、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为编写的主旨,迅速将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的“平型关大捷”作为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上下两课。教科书与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迅速纳入教科书,既是与时代的呼应,也是在通讯不发达的时期,快速把战争信息传递到民众中间、鼓舞抗日军民士气的一种途径。
然而,从价值取向上说,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治需求是不一样的,国民党政权的目的是维护中华民国作为唯一的合法政权,而共产党则体现出对国民党政权既斗争又联合的思想。陕西省教育厅编著的《战时国民读本》第四册的第一课,标题为《拥护领袖》,指出蒋介石是我国的最高领袖,并将蒋介石在庐山谈话的主要观点一一罗列,其目的就是塑造蒋介石在民众心中的领袖地位,维护国民党的统治。1941年,太岳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新民主主义政治课本》,设置了《抗日要实行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政府的官吏要归老百信选》《拥护三三制》等章节,强调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必须一致对外。然而教科书是一个政党指导方针的具体体现,由于国共两党的终极目标的不同,国统区和根据地出版的教科书,所体现的教育目的是不一样的。
与国共主导下的教科书主张抵抗相比,汪伪政权和伪满洲国治下的教科书强调日本主导下的“大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2]133—134日本侵略者所描绘的虚无的谎言,堂而皇之地进入教科书,并作为主要的教育思想,刻意贯彻。1938年,日本主导下出版的教科书以“新民主义”作为总的指导方针,主张来自于《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20]表面看来,教科书是在推行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但是这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一种掩饰。所谓的“新民”,就是放弃本民族的文化意识和传统,确立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认同,最终放弃抵抗,成为傀儡政权下的顺民。伪满洲国新民书店出版的《国民优级学校满语教科书》[21]等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教科书里面赫然印有“日满共存共荣说”,“日—满—德一心论”等谬论。而稍具常识的人都明白,这一点是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因为日本人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
四、“战时”的教科书的特点
没有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就不会有众多战时教科书的涌现。显然,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小学教科书,与社会的需要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当时的教科书,先天地具有通俗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因为,抗日战争时期,物资紧缺、条件艰苦,最重要的是时不我待,历史没有留下供教科书出版部门深思熟虑的时间。教科书完全是在战火纷飞、炮声隆隆之中,撕下自己的面纱,来到这个世界的。
据调查,在20世纪30年代,按照当时的生产力,我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农业人口占据社会的绝大多数,当时的识字率大约处于10%~40%之间。[22]此时,唯有言语通俗易懂、贴近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教科书才能受到民众的欢迎,才能真切满足学堂和抗战士兵的需要。曲高和寡的教科书,非但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还会耽搁时间、浪费紧缺的物资。那时候,为了抗战的需要,不少教科书尤其是根据地教科书,十分注重语言的简洁明快、通俗易懂。如焦卓然的《中华国难教育读本》,三字一句,“苟亡国,难为力,印与韩,作前车……亡国恨,泪南挥……”文字清新,朗朗上口,十分符合时代的需要。六区战斗出版社出版的《民族革命小学国语读本》,直接使用《蚊子做汉奸》《苍蝇做汉奸》《鸽子抗日》《猫狗救国》《羊的牺牲》等做题目,蚊子、苍蝇、鸽子等都是生活里司空见惯的,形象传神,很生动地传播了抗日精神。
抗日战争时期的教科书还需要注重实用性。如世界书局出版的《战时常识丛书》[23]系列,包括《战时常识》《防空常识》《防毒常识》《防毒实施》《战时后方知识》《战时治安》《战时金融》《战时卫生》等,这些教科书有效地帮助民众了解战争的残酷,以及在战争时期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除了教导儿童抗日的小知识外,《战时常识》教科书还指出战时“大家对于国家的责任”,教导儿童在现代意义的国家里,必须知道国家和民众之间的相互权利和责任。作者以为,无论是在战争之前、之中、之后,教科书里的知识都是民众应该知晓的权利和责任。在抗日根据地,共产党1941年出版的《抗日军人文化课本》,讲述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战争的具体事实入手,剖析战争的危害,解释化解敌情的方法。此外,抗日战争时期教科书的实用性还体现在教科书的页面大小和印刷装祯上。根据地教科书出版部门印刷了很多“口袋书”——大约64K大小,有的是油印,有的是胶版。这样的教科书,便于携带,能够及时有效传播抗日知识,对老百姓而言,非常实用。
因为是战时课本,所以战争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重,比如,很多抗战时期的教科书,都加入了军事知识,即使是数学这些强调逻辑性的教科书亦是如此。[24]但是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围绕短期应用而出版的抗日战争教科书,已经不适合时代的需要,社会在呼唤新的教科书的出现。如山东省《国防教科书》,抗日战争结束后,将抗战部分剔除,改为普通的学科知识,满足中小学的需求,有的教科书甚至一直使用到1950年代。[15]山东省的做法,不是孤例,它明确地传达出一个事实:战时教科书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当国内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后,这样的教科书已经落后于时代了。
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控制的区域里,教科书的编辑和出版都由日本人控制,目的在于开展奴化教育,宣传殖民思想,美化日本的侵略。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教科书的出版也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奴化教科书退出以后留下的真空,大部分由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性很强的教科书填充。[2]167—169在东北地区,1946年8月成立了东北行政委员会,组织出版了中小学教科书;甚至为了迅速占领教科书市场,部分学校认为可以翻印抗战时期没有意识形态困扰的自然科学教科书,以达到传播科学知识的目的。在华北地区,以原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边区出版的教科书为蓝本,重新编辑出版适应新的时代需要的教科书。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的教科书承载了特殊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尽一切的可能、尽最大的努力实现自身政治集团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过于紧追时代需求的教科书,注定是短命的。只要抗日战争结束,那么这一类的教科书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日本投降后,绝大多数的战时教科书都进行了调整,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正是国统区和根据地各式各类战时教科书的出现,才在民众心里树立起了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并成为一座永不褪色的丰碑。
[1] 刘学利.伪满洲国教科书的演进阶段[A].石鸥.教科书评论(2014)[C].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 石鸥,吴小鸥.简明中国教科书史[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3] 徐冰.民国时期中日教科书纷争考略[J].日本学刊,2001,(2).
[4] 袁素莲.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转变的主观因素探析[J].齐鲁学刊,1997,(6).
[5] 吴小鸥,葛越.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革命根据地教科书发展概览[J].湘南学院学报,2010,(6).
[6] 沈百英.战时常识(低年级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7] 石鸥.课本抗战之山东《战时教科书》[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5,(7).
[8] 石鸥,曾冬平.课本抗战之《战时读本》[J].中国教师,2015,(10).
[9] 国语课本(初级小学校用)[Z].山西省政府教育厅编印.
[10] 孙怒潮.抗敌教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
[11] 焦卓然.中华国难教育读本[M].靖难书社,1938.
[12] 新战士课本[Z].第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编印.
[13] 辛安亭.历史课本(高级小学用)[Z].太岳新华书店,1944.
[14] 方成智等.教科书租型制度探析[A].石鸥.教科书评论(2014)[C].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5] 石鸥,宿丽萍.课本也抗战——《国防教科书》之研究[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5).
[16] 兰丽红.汪伪政权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制度研究[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11.
[17] 赵长海.论“伪装本”[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7,(2).
[18] 吴小鸥,徐加慧.“复兴教科书”的抗战救亡启蒙[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5,(4).
[19] 白勋生.国语常识混合编制抗建读本[M].正中书局,1942.
[20] 王士花.华北沦陷区教育概述[J].抗日战争研究,2004,(3).
[21] 张石君.国民优级学校满语教科书[Z].新民书店,1939.
[22] 陈德军.南京政府初期的“青年问题”:从国民识字率角度的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02,(1).
[23] 吕绍虞等.战时常识[M].世界书局,1937.
[24] 俞子夷.国防算术[M].正中书局,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