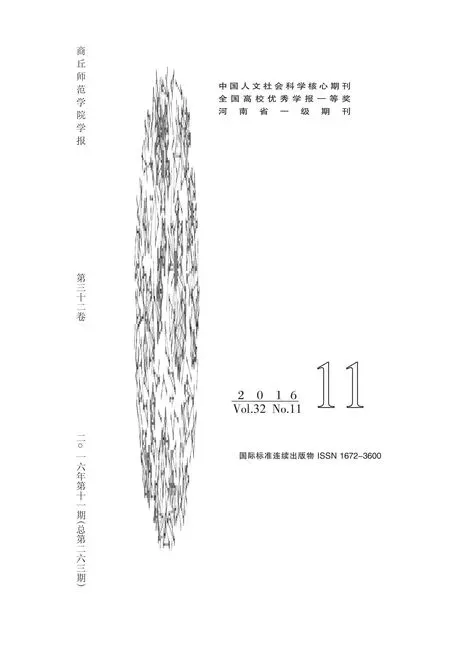城市化视域中古罗马儿童地位研究
王 振 霞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城市化视域中古罗马儿童地位研究
王 振 霞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公元前2世纪以来,古罗马在意大利和行省推行城市化运动。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化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方面改变了古罗马原有的社会结构形态,家庭的传统社会功能减弱。儿童逐渐从男性家长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他们获得自主权和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社会的变迁、传统家庭结构的演变,也导致生育观念与行为的多元化,杀婴、弃婴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古罗马;城市化;儿童
公元前2世纪至2世纪,古罗马出现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城市化运动。古罗马城市化既是一系列制度变迁过程,又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资源重新配置和重新安排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古罗马儿童地位提高,但杀婴、弃婴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
儿童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是观察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尺。古罗马儿童是指自由并合法出生,不满17岁的孩子。古罗马法律赋予父亲对儿童绝对的权力,古罗马家庭的特征是父权制。公元前451—前450年颁布的《十二铜表法》规定:子女乃父母的私有财产,父亲对子女有生杀予夺之权。父亲有权拒绝接受一个新生儿,可以结束他的生命或将他遗弃。父亲可以卖掉孩子,可以将他抵押给别人,或者让别人收养。儿子犯错,父亲有权鞭打、监禁甚至处死儿子。父亲让儿子在农场干活,按照自己的意愿为子女安排婚姻。总之,儿童在家庭中缺乏独立和自主,必须服从父亲的权威。至公元前2世纪,古罗马完成了对地中海世界的征服,为了加强统治,古罗马在意大利和行省推行城市化运动,儿童的状况有所改变。
城市化运动促进了罗马政治体系的变革。早期罗马政治建立在血缘的、狭隘的公民体系之上,“在早期的共和政治中,所有公民都认为,凡是他们作为其成员之一的集团,都是建筑于共同血统上的”[1]74。只有公民所生的合法后代才会成为公民。建立在家庭模式上的城邦政治局促在家庭的狭小角落,其施展的空间有限。可是,当罗马人征服意大利乃至地中海世界后,超越了狭隘的城邦政治框架,将城市变成了其行政制度的基础。罗马人把它的城邦政治体系扩展到各个被征服地区,他们把更多的土地划归现有城市,并建立了一批新的城市,还给予农村、神庙和部落地区以城市的权利,而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口变成了城市公民。随着罗马化程度加深,被征服地区的居民逐渐获得公民权。城市成为管理地方事务的自治单位。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议事会、人民大会和市政官员。通过建立城市并给予城市自治权的方式,罗马统治者得到城市公民的支持。
政治变化瓦解了古老的家庭制度。由于罗马公民权的扩张,非罗马人取得罗马公民独有的家庭和家长权的法律地位。至212年卡拉卡拉皇帝授予帝国境内的自由民公民权,权利义务主体的范围从贵族家长逐渐扩展到几乎全体自由人。公民权范围的扩大,有效增加了合法婚姻的数量,加速了罗马社会身份和角色的全方位流动,使罗马家庭制度以及以男性宗亲为基础的血缘关系遭到破坏。原有的以城邦为基础的狭隘公民体系发生改变,家庭不再是罗马奴隶主阶级的特权,家庭的政治性弱化。随着元首制确立,父亲已经不再是强大的力量和至高权威的代表。
城市化运动促进了奴隶制商品经济的广泛发展,对外征服改变了罗马的经济结构。早期罗马家庭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家庭经济的目的是满足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家长指挥全家人进行劳动,劳动者主要是家长本人及其家庭成员,家庭奴隶的数目很少。自公元前3世纪中叶,特别是公元前2世纪起,罗马、意大利开始在农业和手工业作坊中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奴隶制经济快速发展。罗马的军事征服加速了行省公社解体的过程,城市化使奴隶制经济向更完备的形式即中等奴隶主庄园制度发展。而从公元1世纪和2世纪初起,奴隶制田庄则开始由过去完全使用奴隶劳动逐渐向租佃制转变,从而促进了帝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经济变化瓦解了古老的家庭制度。奴隶制商品经济破坏了以家族为核心的生产模式。奴隶主阶级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摆脱出来,靠剥削奴隶生活。儿童的经济地位上升。共和晚期,由于财富急剧膨胀,手工业和商业逐渐发达,家长无力独自管理家庭财产,于是,家长将一部分财产给予子孙,让他们帮助经营作坊、店铺以及航海贸易等,这部分财产被称为特有产(Peculium)。在法理上,特有产的所有权属于家长,使用收益权属于家属。奴隶制商品经济破坏了以家族为核心的传统消费模式。早期罗马人贫富差距不大,不论平民还是贵族都满足于清茶淡饭、简朴的衣服和卑陋的住房。到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财富积聚已达到空前的规模,社会上层养成了炫耀式消费,在衣着、饮食和住宅上日益考究。贵族的衣衫越来越华丽。城市居民的饮食习惯也出现了新变化。罗马显贵的餐桌上开始出现金银器皿,烤制的面包代替了原来的熬粥,有了职业厨师。宴会成为罗马家庭生活的中心。在一般家庭里,儿童可以参加宴会,与家人一起进餐。就住宅来说,贵族除在罗马修建华丽的住宅,还在其他地方广建别墅。这些别墅大多设备齐全。公元1世纪末小普林尼在罗马城郊的劳兰汀别墅非常豪华,其设施有门厅、走廊、庭院、内厅、餐厅、客厅、内大厅、健身房、厅房、地板、暖气、起居室、预备室、冷浴室、水池、膏油室、火房、暖水室、温水浴室、网球室、储藏室、肉厨、花园、长馆廊、平台等[2]133-140。但罗马社会两极分化严重,拥有舒适家庭生活的只限于城市上层人士,包括城市无产者和乡下农民在内的广大民众的生活条件依然简陋。由于城市比乡村有更集中的生产力,更高的消费需求,城市化运动提高了儿童的生活质量。
城市化也导致休闲娱乐的集中。以罗马城为例:早期罗马人忙于作战、农耕和参与政务,娱乐活动贫乏。称霸地中海世界以后,罗马人大力推进城市建设。除了道路、桥梁、城墙和输水道等城市设施以外,城市还大量建造公共浴池、斗兽场、神庙和广场等供罗马人休闲娱乐的场所。经过几个世纪的建设,罗马城区面貌有了很大变化,城市具备了许多实用的基础设施和豪华的公共活动空间。被征服地区的城市建设大都遵循罗马城的模式。除了公共活动空间的扩展,社会分工改变了罗马公民的社会生活条件,奴隶主贵族和平民有优裕的条件和充足的时间从事休闲娱乐活动。帝国统治者为迎合民意,屡屡增加娱乐节日。据统计,1世纪时罗马全年娱乐日为66天,2世纪时增至123天,4世纪时则达175天[3]313。在节日里,由皇帝或当地政府组织各项演出,有角斗比赛、戏剧、海战、赛车等。丰富的城市公共生活提升了罗马人的精神风貌。很多场合可见儿童的身影,男孩去战神广场进行体育锻炼,也可以进剧院;儿童还经常去看马戏,或到公共浴池洗澡,或去市场。更适合儿童的娱乐活动是游戏,儿童玩各种各样的游戏。有些被溺爱的孩子,如雷古拉斯的儿子,有几匹套辕的小马,几匹会马术的马,大大小小的几条狗,几只夜莺、鹦鹉和乌鸦[2]245。还有其他的一些游戏,如铁环、陀螺、秋千和赌博游戏。奥古斯都本人对孩子严厉,也能够表现出温情的一面,他有时和小男孩一同玩掷骰子、掷石子或胡桃游戏[4]96。当然,以上大多是男孩的游戏,至于女孩,玩具娃娃是她们常用的游戏道具。
可见,对前工业文明来说,罗马城市化是影响深远的文明传播运动。它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的社会结构形态,使罗马社会的发展超越了城邦制下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家庭的社会功能日益过渡到与国家紧密相连的社会机构方面来,家庭的传统社会功能减弱。家庭功能的减退和调整实质上是社会体系中价值力量的一次重新分配,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社会发展的进步方向。
随着古罗马家庭功能的变化,罗马家庭结构的演化同时出现。古罗马家庭包括妻子、儿女等家庭成员,以及奴隶和所有的家庭财产。就人口结构来说,早期罗马家庭属于扩展式大家庭,家庭范围可扩大到直系与旁系的第六层亲属关系。公元前2世纪以后,对外扩张为罗马家庭带来了大量财富和奴隶,为家庭结构从扩展式大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奠定了经济基础。父母、已婚的兄弟及其子女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现象减少了。已婚或成年子女不与父母同住成为正常现象。西塞罗认为,一个家庭单元就应该包括父母、子女和一个共有共享的住宅[5]115。古罗马核心家庭的兴起是其家庭组织结构上重要的发展,它不仅意味着家庭由传统意义上共同居住的群体向夫妻核心主体的过渡,而且也意味着家庭在发挥其功能上被赋予了新的社会特征。
古罗马家庭的内在结构模式从家庭本位转向个人本位。父子关系是支撑罗马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关系。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和社会体制的变革,旧的家庭结构连同父权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必然瓦解,儿童逐渐从男性家长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而获得自主权。家长的男性子孙开始普遍地享有公权和财产权。到共和末期,父亲已不再是强大的力量和至高权威的代表。罗马人开始用社会道德和法律来约束父亲的行为,能够保护儿童权利的父权得到赞同,而对儿童造成伤害的父权的滥用则受到限制。如图拉真统治时期,元首甚至流放了一位虐待儿子的父亲,并让孩子获得自由[6]82。2世纪完全废除了《十二铜表法》赋予父亲对子女的生杀权。儿童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是古罗马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随着家庭政治性质消退,家庭中的血缘亲情逐渐变得重要。父子关系的基础除了强制性权力还有情感。法律逐渐将儿童从父权的压制下,从对其天性的成见下解放出来。父母对儿童的爱清晰地显现。就对儿童死亡的感情体验来说,在共和时代,人们平静地接受儿童的死亡;在有同样高死亡率的帝国时期,人们却为此感到悲痛。当尼禄不足四个月的女儿夭折时,据塔西陀记载尼禄不能控制自己的悲痛[7]526。父母在内心深处对儿童的爱流露出来,安敦尼王朝的元首马克·奥利略对孩子非常温柔和慈爱。人们开始谈论儿童的天真无邪、神圣、纯洁或者虔诚。
城市化使儿童获得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早期罗马家庭的宗教气氛浓厚,儿童参加家庭祭祀活动。父亲在进行家庭祭祀的时候,男孩和女孩都参加,男孩学习动作和祷文。在帝国时期,儿童仍然参加这种仪式,但仪式被大大简化了。接受教育是儿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罗马人实行严厉的家庭教育,父母全程陪伴孩子成长。7岁之前,母亲向儿童灌输家族及公民的美德,要他们懂得谦逊、克制、廉耻、恭敬和爱国。7岁之后,父亲对男孩进行农夫、士兵及公务人员的技能训练,男孩开始参加成人的某些公私活动。比如大加图精心培养儿子,为了让儿子掌握农业知识,编写了一百科全书式的教科书。为了加强体育锻炼,大加图教儿子剑术、投掷标枪、马术、操练兵器、拳击和游泳[8]366。男孩没有被排斥在政治活动之外。元老院议员的儿子可以陪伴父亲进入元老院,以便他们早些熟悉政事。母亲则教导女孩纺织和操持家务。
随着对东方世界的征服,视野的开阔,旧式家庭教育已经与时代脱节。在城市生活中儿童所需要的知识不再局限于全凭经验掌握的知识,学校教育发展起来。初等教育以平民子女为教育对象,中等教育以贵族及富家儿童为教育对象,以文法学校为主要类型;高等教育则是为准备担任公职的贵族子弟预备的修辞学校。女孩通常接受初等教育,共和晚期,贵族家庭的女子也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普林尼赞美妻子有很高的素养:“她脑子机灵,喜欢文学,她对我的书小心保管,认真阅读,有些段落甚至会背诵。我若当众朗诵自己的作品,她便坐在旁边的帷幕后全神贯注地倾听大家对我的赞美。她还演唱我写的诗,甚至把它们谱成曲子。”[2]298最初父亲为孩子选择老师,陪着孩子上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看管失去意义。小普林尼认为应对儿童实行宽松教育:“不要对你的儿子过于严厉。你要想到这是个孩子,你自己曾经也是个孩子。当你行使自己做父亲的威严时,别忘了你是一个人,并且是一个人的父亲。”[2]97儿童受到的管束也不那么严格了。
二
儿童的生存状态同社会的发展、家庭结构的演变密切相连。古罗马社会变迁、传统家庭结构的演变,导致婚育观念与行为的多元化,影响儿童的生存状态。在公元前2世纪到2世纪的古罗马社会中,堕胎或弃婴问题愈演愈烈,漠视儿童的事例不胜枚举,自由民人口下降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
堕胎或弃婴一直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社会议题,它的辐射面广,古罗马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思想意识都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
首先,家庭伦理和价值观的变化导致堕胎或弃婴行为。古罗马传统的婚育观形成于特定的经济、政治及文化之上。在小农经济、城邦体制下,公民个人的德行与家族的利益、国家的荣誉一致,所以罗马人将一切婚姻道德、个人情感置于家长权和国家最高权力之下。对这时的罗马人来说,结婚是一项责任,生育是婚姻唯一的目的。罗马人重视生育,因为生育事关家族的延续。儿童是未来的农夫、士兵和公职人员,国家的命运也与儿童息息相关。无论平民还是贵族,都以生育众多子女为荣。公元前5世纪,一个古罗马平民因为有9个孩子很出名,他的9个孩子给他生育了27个孙子和8个孙女,之后又有了29个曾孙。公元前221年,贵族昆图斯·凯基利乌斯·梅特卢斯在悼词中自豪地说,他的祖父生育许多儿女,在众多公民当中得到许多人的敬重[9]151。共和晚期在经历了政治、经济和价值观的变化之后,个人主义取代了传统的价值观。奴隶主贵族热衷于追求名利和感官享受,他们把生育子女当作负担,不愿意结婚成家,也不愿意生育。如在小普林尼时代,“许多人都只想着没有孩子的好处,并认为生养一个儿子都是一种负担”[2]287。在当时社会上,没有哪个阶层的人喜欢生养多个子女。罗马女性通常采取避孕方式,规避并不想生育的胎儿。
其次,堕胎或弃婴是罗马人控制人口的一种有效手段。古罗马法律允许堕胎,只要丈夫本身不想要孩子,妻子堕胎就不受任何审判。法律还允许杀死畸形儿。公元前450年,《十二铜表法》规定,对奇形怪状的婴儿应即杀之。因为在古代社会,公民的身体是公共财产,属于公共事务的范畴。生来体质虚弱的婴儿,会由其父母把他淹死或勒死。家长不仅有权杀死残疾儿童,还有权遗弃孩子。家长质疑孩子的合法性是弃婴的一个原因。奥古斯都因为孙女朱利亚伤风败俗而治她的罪,之后朱利亚生了一个孩子,奥古斯都正是因为不肯定孩子的合法性,所以拒绝承认和抚养这个孩子[4]86。每当父亲意识到婴儿将成为家庭的负担时,会将其抛入河里或下水道中。父亲死后或者父亲的遗嘱拟定之后出生的孩子,都有可能因为限制家庭人口数量而遭到遗弃。贫穷平民受生活所迫,会选择堕胎或遗弃婴儿。
第三,性别的社会认知是弃婴的缘由。古罗马是典型的男权社会,女孩被遗弃的概率很高。到奥古斯都时期,随着嫁妆制度的确立,很多贫困家庭都感到生女孩的无形压力,遗弃女婴成为当时的一种惯常做法。在一封公元前1世纪的纸草信件中,丈夫希拉瑞恩嘱咐妻子阿丽斯,“在我回家之前,如果生了男孩,就留下。如果生女孩的话,就把她丢掉”[10]295。这导致男女比例失调,帝国初期,在贵族中男性人口远多于女性人口[11]323。
最后,开放的社会风气导致堕胎或弃婴行为多发。共和晚期传统的家庭结构连同它通过家长权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瓦解,婚姻变成了私人事务。上层社会的人很少再把婚姻看作对国家、对家族负重大责任的事情。原有的贞操观念受到性自由、婚外恋行为的强烈冲击。就男子来说,他们有多元的性对象,可以与女奴隶、妓女、女自由民,甚至放荡的上层妇女发生婚外性关系。妓女卖淫和青年男子嫖娼成风。如图拉真统治时期,仅罗马城就有娼妓32000人。就女子来说,她们的性生活也趋向“自由化”。史学家萨鲁斯特说,从苏拉时代以后,罗马人沉溺于淫乱,男人玩弄女人,女人则出卖自己的贞操[12]103。到帝国时期,指责妇女伤风败俗的言论更多。婚外性关系导致堕胎或弃婴行为多发。那些受到引诱或被强奸的女孩,以及已婚又和别人有奸情的妇女,还有那些因为与主人发生关系而怀孕的女奴隶,那些不幸怀孕的妓女,她们都有遗弃婴儿的行为,或使用各种方法堕胎。
堕胎、弃婴行为会导致一系列不利的社会后果。它不但会助长不良社会风气,而且会威胁儿童的生存和发展。大多数弃婴死亡,少数较幸运的由别人收养,长大后或被作为家奴使用,或被当作奴隶贩卖,丧失了自由民的资格。自由民人口下降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
人口状况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堕胎、弃婴行为事关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罗马国家需要重视并解决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重新找回生育的价值。
首先,以法律手段鼓励生育,劝阻并惩罚弃婴行为。要鼓励生育,必须先鼓励公民结婚。奥古斯都极力维护家庭的价值,制定有关的奖惩制度。奥古斯都规定25—60岁的男性和20—50岁的女性必须履行结婚义务,对单身者处以罚款,对结婚而不生养子女的男人也处以罚款。为了鼓励生育,奥古斯都颁布法令,专门为有3个孩子的父亲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法律身份,让他们享有“三子权”。有3个孩子的元老院议员优先担任行省的最高行政长官,有孩子的父亲比法定年龄提前一年获得行政长官职位。奥古斯都还规定,如果遗产受赠人是单身,则没有接受遗产的权利,同时还必须把遗产给予立遗嘱人的有后代的孩子或亲属。但很多人以各种形式规避法律的处罚,奥古斯都发现有人在订婚时,未婚妻过于年轻;还有人经常再娶,以此逃避法律的约束;奥古斯都缩短了订婚时间,并限制离婚[4]68。法律的执行也流于形式。结果是,结婚的人并没有增多,人们仍然认为“没有继承人更好”。
弃婴、杀婴是古罗马的习俗,但随着国家不断完善和强大,必将对此加以干预。公元2世纪政府制定反堕胎的法令,堕胎的妻子将被流放,法令还禁止出售堕胎药,国家开始限制杀婴。人们同情体质虚弱的孩子,对这些孩子的父母表示同情,但父亲不能随意抛弃孩子,杀害婴儿是要受处罚的。塔西陀谴责节育和杀婴的行为,认为限制儿童的数量或者杀死出生的儿童,这些都是可耻的罪行,而要消除这些犯罪,优良的风俗习惯比法律更有威慑力[13]65。舆论认为,那些遗弃儿童的罗马人比野兽更恶毒。到公元2世纪,父亲已没有抛弃他们孩子的权力。公元374年瓦伦提尼安皇帝立法严禁杀婴,丢弃孩童可定为有罪,这是罗马历史上第一次禁止杀害婴儿的法律。
其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制定经济方面的捐助政策。为了遏制贫困家庭日益严重的弃婴现象,帝国统治者通过国库拨款设立专项基金。奥古斯都使儿童从国家得到经济捐助,他在意大利各地区巡视时,所有平民只要能证明自己有儿子或女儿,那么每个孩子都能得到1000个塞斯特银币[4]77。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也资助抚养儿童,小普林尼每年为故乡城市科莫捐款,用这笔钱抚养新出生的自由儿童[2]25。图拉真将各个时期国家的相关措施以及个人的行为系统化,规定所有的儿童必须登记在册,以便享受国家的捐赠。图拉真统治时期,有权利参加谷物分配的罗马平民有15—20万人,大约5000个自由出身的孩子名列其中,也就是说相当于有权分得谷物人口的2%—3%[2]385。政府还把相关法律条款刻在铜匾、蜡碑或亚麻布上,将其张贴在意大利小镇和偏远的行省。当地政府一旦收到任何父母因贫穷而无法抚养孩子的汇报,应毫不拖延发放食品和衣服。图拉真的后继者安敦尼和马克·奥利略都继承了图拉真的做法。但至3世纪,由于国家财政困难,对儿童的经济捐助不再实行。
城市化是个兼具建设效应与破坏效应的社会过程。古罗马城市化带来了家庭领域的诸多进步,儿童逐渐从父权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获得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同时城市化破坏了家庭的稳定和秩序,导致生育观念与行为的多元化。当前我国城市化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农村家庭同样经历着传统与现代摩擦之洗礼,古罗马儿童在城市化背景下处境的改善及其面临的问题令我们深思。
[1][英]梅因.古代法[M].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Pliny the Younger.LettersandPanegyricus[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
[3]朱龙华.罗马文化[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4][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M].张竹明,王乃新,蒋平,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5.
[5][古罗马]西塞罗.论老年 论友谊 论责任[M].徐奕春,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3.
[6]Jerome Carcopino.DailyLifeinAncientRome[M].New York:Penguin Books Press,1956.
[7][古罗马]塔西佗.编年史:下册[M].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2.
[8][古罗马]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M].陆永庭,吴彭鹏,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9][法]让—皮埃尔·内罗杜.古罗马的儿童[M].张鸿,向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0]SelectPapyri[M]Vol.Ⅰ.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2.
[11]Cassius Dio.Romanhistory[M]Vol.VI.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古罗马]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M].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
[13][古罗马]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M].马雍,傅正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责任编辑:韦琦辉】
2016-07-07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古罗马城市与城市化运动”(编号:14CLSJ15)。
王振霞(1975—),女,山东平邑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研究。
K126
A
1672-3600(2016)11-0074-05
——由厦门弃婴岛关停引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