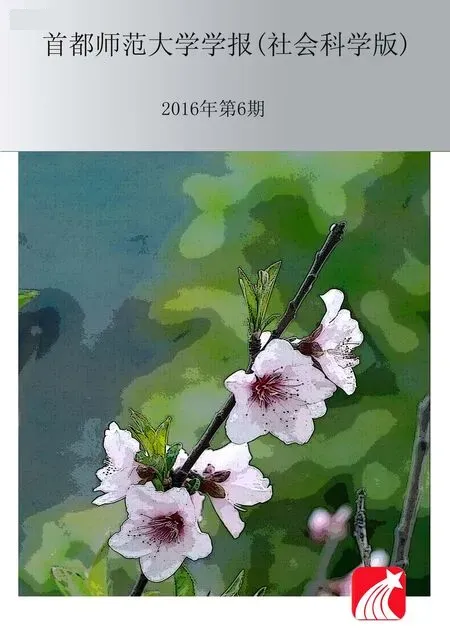缅怀齐世荣先生
李华瑞
一、我与齐先生的交往
2014年10月6日,学校举行建校60 周年庆典,齐世荣先生代表见证学校六十年成长历程的老教授发言,先生讲话言简意赅,情深谊长,思维之清晰、声音之洪亮实令人难以想象是一位88岁高龄的老人在讲话。然而真是岁月无情,仅仅过去了一年多时间,先生竟遽归道山,留下了几多哀婉,令人心痛。
我虽不是齐先生的学生,现在从事的专业也不是世界史,但是知晓齐先生的大名还是比较早。我在读本科阶段比较偏好世界史,四年级的毕业论文选题就是齐先生的强项:二战前英国的绥靖政策,做论文时也翻阅过齐先生的相关大作。可是当时英语学得不好,加之当时世界史硕士点很少,于是临考研究生阶段放弃了世界史,而改考宋史。后来知道齐先生很早就带世界史硕士、博士,还曾幻想如果当年能考上齐先生的硕士,也许我的专业道路会是另一番景象。
第一次见到齐先生是1991年六七月间,漆侠师与邓广铭先生在北京主办国际宋史研讨会,在筹办会议间歇,漆侠师带领我们一行四人,到北京师院看望于善瑞校长。于善瑞是民国风云人物于凤至的侄女,1983年至1990年在河北大学任校长,从校长位置退下来后,于善瑞校长要去美国与亲人团聚,作为过度于校长被安置在北京师院任副校长。当时北京师院的校长就是齐世荣先生。漆侠师在北京师院有好几位朋友:戚国淦、谢承仁、宁可和齐世荣。那天于校长个人招待我们,于校长也告知了齐先生和谢先生,齐先生因公务繁忙在会客室只坐了十分钟就告辞了。在席间,于善瑞校长讲起她刚到北京师院上任,当齐世荣先生得知她来自河北大学,就向她问及漆侠师的近况,于校长说你们做的不是同一专业还很熟吗?齐先生说我们认识很早,然后齐先生说我不仅认识漆侠,还相当了解他:“漆侠,学问好,脾气大”,于校长听后感慨“您真是了解漆侠先生”。漆侠师听到于校长讲到这很高兴,很认同齐先生对自己的六字评语,而后笑着对于校长说齐世荣是以他的特点说我,“他也是学问好,脾气大”。今年1月16日在齐先生追思会上,听到来自齐先生的好友、同事、学生对齐先生性格特征的描述,我感到齐先生与漆侠师有太多相似的地方,刚正不阿,正义凛然,耿直率真,豪放幽默,对后进和学生爱护有加。而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治史方面也是有共同的坚定信仰和学术操守。
再次见到齐先生已过了10年,2001年4月下旬,我第一次代表河北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评审会议,那时的中国史评委都是戴逸、李文海、林甘泉、张岂之、刘家和、陈高华、隗瀛涛等著名学者,在会上见到齐先生,齐先生当时是世界史的召集人。评审会在京西宾馆,早饭后评委们大多都在宾馆大院内散步,我瞅准时间近距离接触齐先生,自报家门,并提及1991年曾见过先生,齐先生重提漆侠师“学问好,脾气大”的话题,说漆侠师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高,希望我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2002年再次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会时,齐先生见到我主动向我询问漆侠师病逝的情况。2001年11月2日,漆侠师为缓解哮喘输液,因保定庸医给药不当而突然仙逝,当时曾震惊国内史学界。我给齐先生仔细讲了漆侠师病逝的经过,齐先生一再表示叹惋。这年五月参加中国史学会与云南大学举办的“2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学术研讨会”,又见到齐世荣和宁可先生。齐先生发言强调新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治史的重要性,声音洪亮,气场很大,所以印象深刻。
2003年以后社科规划办规定连续担任三届和年过75岁的老评委就不再担任。那年徐蓝教授被特邀参加评审会,方知道她是齐先生的高足,这是我与徐蓝教授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只是互相询问过后再没有交谈,后来到首都师大工作才知徐蓝教授很健谈。
2003年底,我因内子家庭的原因准备调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后得到宁可先生的支持。历史系主任宋杰兄让我在2004年四月下旬到系里试讲,试讲包括两部分,一是给系里老师和同学上一节课,二是给系学术委员会做一次学术报告,都限定在半小时之内。那天给学术委员会作报告,齐先生和宁先生都在场,我做了一个“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进展”的报告。齐先生听后问我为什么没有介绍日本和台湾的宋史研究状况,我说时间不够,齐先生说日本和台湾的宋史研究水平很高,我当时很惊讶,齐先生的确不愧是大家,世界史做得好,对中国断代史研究状况也很熟悉。这让我想起了坊间所传齐先生提倡做世界史要关心中国史研究的消息,看来齐先生是身体力行。
2004年调入首师大后,虽然齐先生已很少招学生,到系里来的次数也不算多,加之我也不常去系里,除了到齐先生在师大校园的住家专门拜访过两次,实际上见齐先生的机会并不多。但先生一直没有忘记我,先生每次出版新作都会签名送我一本,先后收到先生赠送的有《20世纪的历史巨变》《世界史探研》《15世纪以来世界九强兴衰史》《史料五讲》以及译作《蒙古近代史纲》。我自己出的书《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视野、社会与人物》《宋代救荒史稿》也赠送齐先生指教。
说来有点惭愧,2007年齐先生主编教育部的部编初中历史教材,请瞿林东先生主持中国史的编纂工作,虽然是初中教材,齐先生要求各断代要有优秀学者亲自执笔。一天,瞿先生给我打电话说,齐先生亲自点名初中教材宋元部分由我来执笔。我当时听了很感动,这不仅是对我的专业业务能力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我的信任。我欣然接受了任务,可是我从未编过初中历史教材,一接手才发现要写好初中教材其实不容易,不仅要求内容准确、史实无误,而且语言要生动,不能太学究气。我在写作过程中觉得丝毫不比做一篇论文容易,幸亏有叶小兵先生帮助润色才勉强交稿。追思会上许多老师都提到齐先生编写大学、中学教材是有很崇高的社会责任感的,参与这次编写工作也算是有所体悟。
二、齐先生对《学报》的关爱和支持
2012年7月,学校调我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及编辑部主任。到学报工作以后,曾专门给齐先生打电话致意,请先生赐稿支持学报。那天电话打了半个多小时,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但有两点印象很深:一是先生强调刊发的文章要言之有物,有创意,读者愿意看;二是校对要精,一定要避免出现低级的硬伤错误。其实,齐先生一向对学报工作特别重视,先生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5期撰文祝贺学报创刊20 周年《艰难的历程——从〈文史教学〉到〈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在这篇文章中齐先生对于学报的发展作了简要的回顾,实际这是一段很珍贵的学报发展史料: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于1974年正式出版(当时名《北京师范学院学报》),到今天已经二十周年了。二十年来,我们刊登了一大批文章,其中一些是很有分量的文章,在读者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为已经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的同时,我不由得想起创业的艰难。我校是在1954年创建的。建院初期,从领导到一般教师,都有人忽视科学研究,甚至认为积极搞科学研究的教师是在走白专道路。但那时也有一些有志于科学研究的中青年教师,对这种现象很忧虑,觉得长此下去,不仅科学研究本身将被埋没,而且教学质量也会日益下降。1958年,借着“大跃进”的机会,刘国盈同志(时任中文系总支书记)和我(时任历史系总支书记)冒着被戴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的危险,一而再、再而三地找当时的院领导鲍成吉同志,建议办一份学报。领导上认为时机尚不成熟,但允许先办一份内部发行的刊物。事情总算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刘国盈同志和我决定先办一份《文史教学》,由中文系的廖仲安同志负责中国语言文学稿件的编辑,历史系的谢承仁同志负责历史稿件的编辑。在没有一个专职人员的条件下,《文史教学》上马了,一共办了三期,我校的名誉教授、著名明史专家吴晗先生还热情地投了稿。不料,1959年形势一变,许多刊物下马,我们这份好不容易争来的刊物也就短命夭折了。1974年,终于有了公开出版的《北京师范学院学报》,但十几年的宝贵光阴已经浪费掉了。
齐先生在文后对学报提出了殷切期望:“科学研究贵在有创造性,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到‘唯陈言之务去’,对于那些了无新意的文章千万不要登。我祝愿,我也相信,《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将会办得越来越好,成为读者喜欢保存的一份刊物。”我想齐先生的殷切期望和教诲对于今天办好刊物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定将“对于那些了无新意的文章千万不要登”的警语作为办刊的宗旨。
2014年,学校迎来建校六十周年,学报也迎来了创刊四十周年的纪念,在此之前我打电话给齐先生约请他给学报写一篇纪念文章,齐先生欣然答应,题为《再接再厉,不矜不限——祝〈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创刊四十周年》,再次回顾了学报的发展历程,并在文后附记:“北京师范学院创办的1954年,我即来校任教,当时才28岁。明年2014年建校60 周年,我已是88岁的老人了。今年是学报创刊40 周年,学报要我写一篇纪念文章,作为一个老员工,义不容辞。但耄耋之年,体脑兼衰,实不成文,姑以应命,尚希见谅。”看到齐先生的附记,很是感动,那种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齐先生先后发表在学报的文章初步统计是15 篇,追思会上《世界历史》编辑回忆说齐先生发表在《世界历史》有14 篇文章,看来齐先生一生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文章最多。齐先生晚年德高望重,他的论文是很多刊物求之不得的,但是齐先生把晚年最有心得的几篇文章交给了学报,最近新出的《史料五讲》中的后三篇《谈小说的史料价值》《谈日记的史料价值》《谈私人信函的史料价值》都交给了学报发表,这是对学报的莫大支持。齐先生的《史料五讲》结集出版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瞿林东先生与他的学生从史学史的角度敏锐的观察到齐先生大作的学术价值,并撰文给以很高的评价,瞿先生也把文章发给了我们,这是一段颇有意蕴的唱酬佳话。
齐先生最后一篇文章《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也交给了学报。2015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在家里突然接到齐先生的电话,先生说,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他写了一篇论文问能不能用。我回答说您发给我们,我们随时给您留着版面。先生又说现在还不能给,他要看看习总书记在9月3日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讲话,看看自己的论述与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是否有冲突。我说好,那就让历史编辑杜平随时与您联系。对于齐先生的慎重,我觉得是具有高度政治责任感的反映,也是一个老党员应持有的立场。追思会上有几位学者都谈到世界现代史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现实性,历史问题往往与政治问题绾结在一起,齐先生总是能正确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其实齐先生是最早系统阐述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贡献和地位的权威专家,齐先生之所以慎重是他多年养成的风格,无论何时都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9月20号左右杜平从齐先生家里取到手稿,连夜打出来发给我,我读后顿感大气磅礴,掷地有声。如果不是先生发病住院,我们本应在2015年第五期发出来,齐先生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大作。可是齐先生发病住院,先生又极其认真,一定要亲自核校杜平打的稿件,一再延迟付梓。起初杜平问我是否请齐先生的女儿代为核校和签字,但是我知道齐先生的脾性,坚持由齐先生签字认可,所以一直到十月中旬齐先生昏迷过去,才由叶小兵教授代为核校,由齐先生的女儿齐卫华女士代为签字。我之所以这样做,除了知道先生的认真和严谨外,还基于2014年10月看到先生那样硬朗地参加学校建校六十周年庆典时表现出的精神状态,觉得先生能够挺过这次发病,然而人算不如天算,2015年12月3号凌晨齐先生就离开了我们,先生在学报上发表的文章也成了他最后的遗作。
我们一定铭记先生的教导,办好刊物,以实际行动纪念我们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