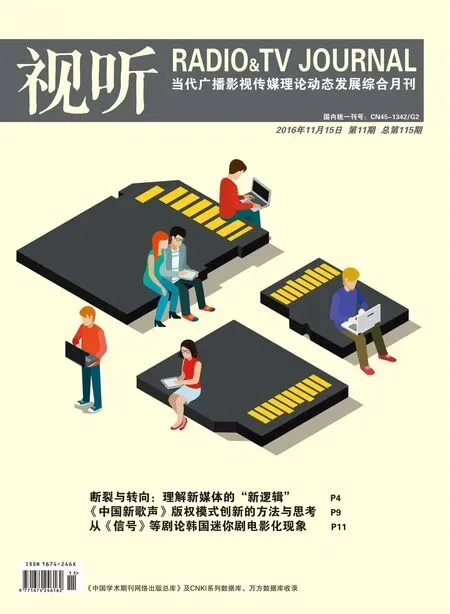朴实生动 深刻感人——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评析
□刘靖
朴实生动 深刻感人——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评析
□刘靖
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以二十四节气为时序展现杓峪村“乡景”的变化,采用三线平行交叉叙事塑造了朴实、生动、真实的人物形象,影片折射出的农村社会公共议题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纪录片;焦波;《乡村里的中国》;中国农村
2016年春节期间,一部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纪录片火爆网络。影片将镜头对准位于沂蒙山革命老区的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杓峪村,以这个小村庄为切入点,历经一年多的驻村拍摄,真实生动地描绘了村民的生存状态,展现了中国农村的巨大变迁。这便是曾以影像《俺爹俺娘》感动世人的著名摄影师焦波主持拍摄的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该片问世以来,已荣获华表奖、白玉兰奖等20个奖项。
一、节气变换中展现“乡景”,三线平行交叉叙事
2012年初,时任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的张宏森跟焦波说“找一个不大不小、不穷不富的村庄,在那里驻扎上一年,以二十四节气为结构,拍摄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纪录电影,名字叫‘乡村里的中国’”。退休在山东淄博老家种树的焦波接下了局里的这个“命题作文”,经过半个多月的考察踩点,焦波选择了离自己老家不远的杓峪村。
二十四节气古往今来与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该片以二十四节气的变化展现乡景,真实记录杓峪村乡民的日常劳作生活状况。影片开始部分的一系列镜头展示了立春时节的杓峪村景象:第一个镜头是杓峪村山水的远景,同时字幕上打出日期和节气名“立春”,交代了时间和大环境;紧接着是河水潺潺,冰雪融化,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由立春节气的景象引出人物的活动,于是便出现了作为本片主角之一的杜深忠给羊头点红、在羊圈外墙上书写红色“春”字的场景,杜深忠的妻子和老太太们缝制“春”帽的场景,以及非常热闹红火的小孩子们围着篝火进行咬“春”游戏的场景。本片片名出现之前的这一系列镜头,都展示和强调了“春”,充满活力生机的春天来了,意味着新的开始,也为本片的后续内容做了铺垫。之后的每个节气都对应着杓峪村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如小满节气村民给小苹果套袋,期待好收成,寒露节气时收获苹果,村民卖苹果却犯了难,节气和自然景观的变换是影片主要的时间叙事线,推进了片中人物故事的发展。
影片采用三线平行交叉叙事来讲述故事,三条主线分别是杓峪村的三户人家:“另类”农民杜深忠一家、大学生杜滨才一家以及村支书张自恩一家。三条主线很有典型意义,分别代表村里的文化线、情感线和政治线。影片以杜深忠家庭为叙事主线,张自恩和杜滨才家庭穿插其中,其他村民及村里鸡毛蒜皮的事充实和串联影片里的故事,每条线索中的故事都经过了精心选择。三线平行交叉叙事强化了影片的主题,即关注农村、关心农民、致敬农民。
二、人物形象朴实、生动、真实、深入人心
杜深忠,高中毕业,当过兵,担任过村支书,属于村里的“高材生”,是一个有理想、有精神追求却被迫困于土地的文化人。他与其妻张兆珍为代表的绝大多数普通农民有着很大不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精神文明和文化生活有着强烈的追求,从二十岁到六十岁依旧坚持着,他爱看新闻联播,喜欢文学创作、拉二胡、弹琵琶,写得一手好字。然而杜深忠面对的现实却与理想相距甚远,他家境贫寒,分到的土地是别人挑剩下的。张兆珍是一个很务实的农村妇女,在她眼里农村居家过日子物质生活才是更重要的。张兆珍当初看中的是杜深忠有文化,期望他将来能有所作为,然而事与愿违。这对夫妻经常因为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争吵不断,但又相互依赖。影片中二人的争吵颇具黑色幽默:村里古树被一棵棵卖去城里搞绿化,杜深忠气得跳脚,“剜大腿上的肉贴脸上”,张兆珍回应“人都富得哼哼,你还穷得吱吱。人有钱的王八坐上席,你没钱的君子下流坯。”杜深忠到底花690块钱买了琵琶,骗张兆珍说花了400来块,被识破后,他捏起一张煎饼辩解:“人活着要吃饭,精神也需要吃饭,你懂不懂?你心太小。”影片中杜深忠在教育子女时说“实际上我一开始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咱就是没办法,无奈……这个土地不养人”。“这个土地不养人”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焦波,一个农民说出了令导演意想不到的话语,土地对杜深忠的回报不是他想的那样,他说不爱实际上是太爱了,正所谓“爱之深,恨之切”。如果没有杜深忠这个人物形象,可以说影片的层次会大打折扣。
杜滨才,杓峪村的一名大学生,其父曾患有精神疾病,自幼父母离异,和父亲生活在一起。杜滨才积极上进,学习刻苦,成绩优异,获得了很多荣誉,具有文艺特长的他是杓峪村春晚的主力。由于从小缺乏母亲的关爱,在和父亲的相处中矛盾不断,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真不愿意回这个家,一回来就烦”。直到后来在婶子和焦波的鼓励下去见了离散多年的母亲,杜滨才的心结才慢慢打开。在杓峪村春晚上他以一曲《父亲》感动了在场的所有观众,当然也包括他的父亲。
张自恩,杓峪村村支书兼村主任,一年到头,村里的大事小事都牵绊着他。在影片拍摄期间,村里迎来了驻村干部魏书记,村里的几个新农村建设项目陆续启动,由于建广场砍树引发了与本家亲戚张光地的冲突,之后张光地以村里账目有问题为由三番五次找人查账和闹事,使得张自恩不胜其烦,不惜动粗骂娘。张自恩整日周旋于驻村干部、开发企业以及广大村民之间,一心致力于杓峪村的建设,然而工作的压力、微薄的薪水以及别人的不理解使得这位沂蒙汉子在年末的酒桌上不禁潸然泪下。观众通过张自恩的故事,可以了解杓峪村的全貌。
三、影片折射出的农村社会公共议题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乡村里的中国》带给观众的不仅仅是杓峪村农民们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它会引起人们对农村的关注、对农民这一社会角色的重新审视以及对新时期农村生产建设发展的思考。影片折射出的农村社会公共议题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如城乡二元分化、环境保护、新农村建设、农民的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农村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与教育问题等。
村里的古树一棵棵被连根拔起运往城里搞绿化,杜深忠生气地说那是“剜大腿上的肉贴脸上”。树木的“农转非”以及杜深忠的话引人深思,城乡二元分化体制下农村和城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在发展中城市处于主动地位,农村处于被动地位,城市的高速发展对农村往往是一个不断掠夺的过程。影片中农民将古树卖到城里,在买卖过程中农民处于很被动的地位,卖掉古树只能获得微薄的经济收入。树木的“农转非”只是城乡二元分化的一个缩影,农村的水资源、矿产资源、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城里,一方面为农村的发展迎来了契机,另一方面也为农村带来了问题,如资源的过度开发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农民土地被征用引起的纠纷问题、劳动力资源流失造成的空巢老人及留守儿童问题等。如何消除这种城乡二元分化,促进城乡融合,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影片中的有文化人农民杜深忠尽管物质生活不尽如人意但对精神文化有着不懈的追求,他的形象打破了人们对传统农民形象的既定认知,同时也引出了一个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议题: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两手抓,乡村文化建设的主力军是农民,农民素质水平的提高至关重要。
影片中最令人心痛的段落是村民张自军的丧事,外出贵州务工的村民张自军不慎从八米高的脚手架上坠落不幸死亡,留下了年迈的父母以及幼小的孩子。在张自军下葬时,他的儿子头缠孝布指着棺材问“那是俺爸爸的家吗?”,张自军的父亲答道“对了,那是你爸爸的家”,这个场景尤其让人揪心,年幼纯真的孩子此时还不明白父亲的死亡意味着什么。上有老下有小,农民为了生存,不远千里外出务工,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结局。通过张自军意外坠亡事件,反映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给农村家庭带来的重大影响,也引起了人们对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的关注。
焦波的作品根植生养自己的故土,其对家乡发展变迁的真实记录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乡村里的中国》的成功不仅体现在它的主题叙事、人物塑造,更体现在它所承载的人文关怀的现实关照上。
1.焦波.我拍《乡村里的中国》[J].党建,2016(03).
2.褚兴彪.解读电影《乡村里的中国》的农民生命观[J].电影文学,2016(15).
3.韩佳璇.从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看当下农村的公共社会议题[J].大众文艺,2016(14).
4.陈晓波,陈小妹.《乡村里的中国》的纪实叙事策略[J].当代电视,2016(08).
(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新闻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