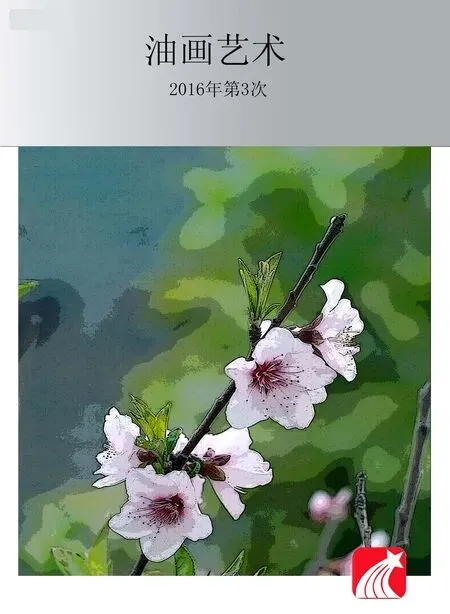中法绘画交流的几个片段
文
中国和法国在文化上具有许多相近之处,对绘画的爱好,就是诸多近似处之中相当突出的一个方面。虽然两国绘画艺术渊源不同,但近现代历史上的互相影响十分引人注目。在中国美术史上,除了对古印度美术的吸收,中法之间的美术交流堪称重要的篇章。
传教士画家进入中国宫廷
作为欧洲传统绘画形式的油画进入中国,大致可以回溯到明代欧洲传教士来华的传教活动。到清代前期,皇家宫廷画师中,已有好多位欧洲传教士,如郎世宁、王致诚等。由外国画家担当宫廷画师,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方面说明清初帝王在绘画艺术上的开明,同时也说明欧洲艺术以这种特殊的形式,越来越逼近并渗入中国传统文化系统。
与郎世宁一同到中国的王致诚(原名让・德尼・阿蒂雷Jean Denis Attiret ,1702—1768)是最早来到中国的法国画家。王致诚生于多勒的弗朗什-孔泰古城,青年时期曾到罗马进修绘画。1738年,其作为“画技熟练的”画家,由法国耶稣会派来中国。派他来中国的主要原因是给中国带去“法国国王的恩宠”,以抵消意大利人郎世宁在中国宫廷中享有的尊崇。
从绘画技艺看,王致诚是当时来华传教士中水平最高的一个,深得乾隆皇帝的赏识。但乾隆皇帝不喜欢笔触和光影突出的油画,只让他用水彩作画,这使王致诚十分苦恼,为此他愤慨地向郎世宁喊叫:“我是欧洲画派成熟的画家,我用不着到中国来学画!”当然,他必须按照皇帝的趣味调整自己的艺术技巧和风格。他画了大型纪实画《马术图》和《乾隆万树园赐宴图》,画了乾隆皇帝的肖像和多幅功臣肖像。据统计,王致诚受命画肖像画总数在200幅以上。
此外,王致诚对中国建筑和园林十分喜爱,他曾在书信中向法国人介绍中国的万里长城、圆明园、避暑山庄。他告诉法国亲友,与中国的山河、建筑相比,欧洲人崇敬的埃及古迹相形见绌。中国人在建筑艺术上表现出来的丰富想象力,相比之下,欧洲人在这方面贫乏了。他对皇家园林内的详尽介绍,为欧洲园林的中国风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王致诚为中国皇帝画画,历经30年。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乾隆皇帝曾任命他为四品官(翰林院学士、国子监祭酒的官阶)。王致诚以身为耶稣教教士难以担任世俗官职而婉拒。在郎世宁去世之后两年,王致诚于1768年病逝于北京。皇帝恩准为他以中国丧葬的排场举办盛大的葬礼,法国传教士说“它更像是一次凯旋,而不是一次丧葬”。
由于在宫廷为皇帝服务的传教士画家在艺术风格上要完全适应皇帝的个人艺术趣味,所以他们的绘画才华并没有得到充分施展。从现存作品看,他们的绘画实际上是一些亦中亦西的折中性艺术。他们花了很大精力来仿效中国工笔画家的绘画语言,而他们对中国绘画的影响主要在人像写真和工笔花鸟走兽方面。清代许多中国画家在构图、色彩和造型上吸收了传教士画家的技法。
中国文人对西方绘画的介绍
虽然欧洲绘画从明代万历年间即已进入中国,但从那时直到晚清,仍然是单方面的传播,即由欧洲向中国输入。而要使油画在中国立足,必须由中国人自己主动地去认识和吸收。在这一方面率先行动的不是画家,而是当时主张变法维新的上层文人。这些人的艺术观是从属于革新政治的主张的,他们介绍西方绘画的目的,是通过吸收新的因素和手段,来补充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这显然与外国传教士和商人传播西方绘画有着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双方对中国油画发展的影响,一在技术方面,一在艺术思想方面。而后者的影响更为深远。
1889年,以“左副都御史”出使英、法、意、比回国的薛福成,是一位关心美术的外交家,每到一地必观览藏画,并对中西绘画加以比较。他认为“西洋人之油画,专于实处见长……数十步外望之,但见真山川、真人物,气象万千。并能绘天日之光,云霞之采,水火之形,及即而谛视之,始知油画一大幅耳。此诣为中国画家所未到,实开未辟之门径”。薛福成对西方绘画并非一律推崇。他批评宗教题材绘画,赞赏从现实生活取材的绘画。他参观描绘普法战争的全景画后所写日记,即《巴黎观油画记》,文笔简洁流畅,富于感情,诵读起来朗朗上口,是晚清散文中的名篇, 被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所记诵。这篇文章在张扬油画艺术方面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欧洲传教士前赴后继的努力。
以“维新百日,出亡二十年,三周大地,历遍五大洲,经二十余国,行四十万里”自诩的康有为,对中国绘画的发展前景十分关注。康有为艺术思想的基础是“变”。时代和环境变了,艺术就不可不变,从何变起呢? “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西造新声”,“揽万国之华实,考其性质色……制以为方,采以为药”,主张“今直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这种观点对包括徐悲鸿、刘海粟在内的一代画人,都有很大的影响。
早期留学生在法国
20世纪初,开始有留学生赴法国学习美术,如1911年赴法的吴法鼎,1912年赴法的李超士、方君璧等,其后赴法留学者渐多。20世纪初期的欧洲,虽然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已经确立了画坛的地位,但在美术教育领域,特别是在像巴黎美术学校这样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学校里,占主导地位的教师仍然是艺术上的折中主义者。徐悲鸿(1895—1953),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具有多方面重要作用和影响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他于1919年到法国,在巴黎美术学校师从弗拉孟、达仰、贝纳尔(Albert Besnard, 1849—1934)、柯罗蒙等人。1928年结束在巴黎美术学校的学业返回中国。
徐悲鸿在巴黎学画的时候,毕加索、马蒂斯、勃拉克等人在法国画坛已经有稳固的地位,达达主义从美国、德国转向巴黎,并朝着超现实主义发展,但徐悲鸿对此有明确的选择,认为现代绘画浪潮只是一时性的过程,他对学院及卢浮宫以外的种种浪潮毫不动心,对于熟练的写实技巧和具有文学性、象征性作品的崇仰,成为他油画创作的不变目标,也成为他介绍西方艺术,重建中国绘画的立足点。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他的创作重心已移向中国画。而从他的艺术倾向、知识结构和技法准备看,大型的纪念性历史画才是他所想攀登的高峰,可惜他的宏图大志没有完成的时间和机会。
在学习欧洲绘画的历史过程中,颜文樑(1893—1988)的艺术经历颇具代表性。少年时期他看到欧洲传入上海的油画作品,觉得新鲜而又奇特,于是开始摸索试探油画技法,开始时曾试用烹调菜籽油调和自己磨制的颜料,后来模仿西洋绘画在市场销售。30多岁时他以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校长身份出洋留学,入巴黎美术学校,他自述“我和徐悲鸿一样,是巴黎美术学校的自由生(选科),不是正式生”。1930年年底毕业回国时,他在巴黎搜购大量石膏模型,使苏州美专拥有的石膏模型多达460余件,数量和品种都超出国内其他美术院校的总和。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各地院校教学用的石膏模型,多为他带回的石膏模型翻制而成。
林风眠(1900—1991)赴法国留学,留学法国期间,他既了解欧洲艺术的发展状况,注意研究印象主义以来的新绘画,又在法国文化环境中加深了对中国艺术传统的理解。1928年林风眠出任新成立的杭州国立艺术院院长,明确提出要以巴黎美术学校为模式,建立一所具有现代艺术倾向的最高艺术学府。自此以后,法国美术教育模式对中国美术教育的影响越来越多,直至20世纪50年代以苏联美术教学规范改造原有的美术教育。在专业美术院校之外,欧洲美术家的展览、社团活动也极大地感染了留法中国美术家。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上海、杭州、北京、广州的年轻美术家仿照法国艺术家组织的美术社团活动,涵盖了不同艺术观念的画家群体。
与林风眠同一时期在法国学习绘画,又一同到新建的杭州国立艺术院从事西画教学的吴大羽和方干民,他们被称为杭州国立艺术院西画三导师。吴大羽(1903—1988)1922年去法国,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鲁热教授(Prof . Rrouge)工作室,并曾师从布尔代尔(Bourdelle)习雕塑。1927年回国,在杭州国立艺术院任西画系主任教授。早期作品富于表现性,接近野兽派风格。后期作品受环境限制,都是以抽象性笔法描述自然的感受以及幻想和记忆片断的小幅油画。方干民(1906—1984)1926年到法国留学,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在保尔 · 罗朗斯教授工作室学习,1929年返国。他是当时留学生中少有的认真研究过欧洲现代派绘画的人,他曾说:“在巴黎我看到被官方赞美的一些学院派作品都脱离了时代,只有新兴的印象派、后印象派、巴黎派、野兽派和立体派他们的作品是真正揭示了时代的美感。”归国后他最为人注意的创作是那些具有立体派风格的作品,这些作品代表了当时中国画家在学习西方现代绘画方面所达到的高度。
去法国学习绘画的中国留学生绝大部分先后回国,但也有人留居法国,并融入法国艺术之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为早期的常玉和战后去法国的赵无极、朱德群。常玉(1900—1966)到巴黎后既不打工谋生,也不进正规的美术院校学习,而是在“大茅屋学院”随性画画,泡咖啡馆。他的绘画融合了中国文人写意与当时刚刚兴起的野兽派艺术的表现性。常玉晚年生活拮据,1966年8月因煤气中毒在巴黎寓所去世。
赵无极(1921—2013)和朱德群(1920—2014)都出自杭州艺专,受业于林风眠、吴大羽,在中国完成美术教育之后去法国,并一直居留于巴黎。他们以中国情调融入法国现代绘画,成为著名的法国画家。他们作品中那种优雅诗意,显然是中法不同的文化传统交相融汇的结果。
吴冠中(1919—2010)1947年赴法国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1950年回国,先后在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和北京艺术学院任教,以风景画家的身份在画坛露面,在色调和形式韵律方面的突出表现引人注目。对色彩和点、线节奏的敏感,是吴冠中在艺术上的优胜之处。他不是为宣传某种政策、体现某一思想、纪念某一事件而画,而是为探求绘画的形式、营造情调和意境的心态作画。他认为“油画的民族化与国画的现代化其实是孪生兄弟”,在他心目中,可以评定他创作价值的是中国的普通民众和法国的同行。这使吴冠中与同时代主流画家有明显的不同。
20世纪前期在杭州国立艺术院从事西画教学的林风眠、吴大羽、方干民,与20世纪后期他们的学生一辈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前后三人,以传薪接火的精神将中国绘画引向现代艺术之境。法国艺术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深刻。
对印象派的曲折认识
1874年,莫奈在巴黎展出他那幅著名的风景画《日出・印象》。直到1905年,中国天津的李叔同(1880—1942)去日本留学,追随日本印象派画家黑田清辉,从黑田清辉的作品和教学中了解了印象派绘画。中国早期美术教育家姜丹书记李叔同的绘画:“上人于西画,为印象派之作风,近看一塌糊涂,远看栩栩欲活,非有大天才真功力者不能也。”姜丹书提出印象派画家都是具有“大天才真功力”者,这一断语透露了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人对西方绘画的态度已经出现了根本性转变。而真正推广和实践印象派艺术的是李叔同之后的留日学生,如关良、陈抱一等。关良(1900—1986)1917年到东京学绘画,他曾回忆对印象派绘画从不理解到理解的过程。富于开拓意识的刘海粟,是印象派、后印象派的重要推介者。1919年刘海粟撰写《西洋风景画史略》介绍了印象派:“风景画法,自一千八百七十年间,印象派之画家辈出……此等画家,在户外空气之下,先行采取瞬息的自然现象,然后回室内修饰之,此为诸先达所不及之新发明也。”
对印象派绘画发生兴趣的美术家,实际上超出了西洋画界。许多从事传统绘画的画家,也从印象派的艺术观念和笔法中,感知过去国人对西洋画的了解过于狭隘。1920年,曾赴欧考察的中国画家金城,为北京艺专学生做有关印象派、后印象派的讲座。
陈抱一(1893—1945)回忆:“民七八年以后,留欧习画的人先后归来……就大体的作风倾向而说,似可分为两部类,一种是洋画上最通俗的方式;另一种是带上一点印象派风味的。”许多美术院校的西洋画教学,倾向于印象派及后印象派风格,学院风格的写实主义和印象主义基本上呈现平分秋色的局面。1929年的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中,已经出现了不少具有印象派风味的作品。评论家将全国美展中的作品风格归为六大类型,对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追随各居其一。
在印象派之后,各种绘画流派层出不穷,中国人以惯有的大而化之将其统称为“新派画”。而在艺术界之外,出现了另一种概括方式—将新派画统称为“印象派”。如果有谁看到他不熟悉、不理解的西洋画而又不想唐突褒贬时,便会说:“印象派嘛!”
使中国“新派画”的浪潮突然趋于平息的,不是学院派的抨击,而是日本军队的炮火。被视为“新派画”大本营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在战火逼近时仓皇撤退,林风眠、吴大羽这些新派画家的大作统统毁于日本军人之手。徐悲鸿甚至为战争兼可扫荡“艺魔”而大感痛快,他所谓的“艺魔”就是指印象派以来的绘画流派。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美术理论家,基本接受苏联官方对西方现代艺术的观点—印象主义是资产阶级艺术的颓废流派,印象主义是形式主义的最后避难所……实际上苏联画家并不是全都赞同这种观点,不止一个苏联画家从印象派得到形式上的启发,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油画家正是间接从苏联画家那里吸收着印象派的艺术营养。在艺术院校里,有关印象派的出版物仍然在教师和学生中流通,某些不识时务的教师仍然在宣扬法国印象派大师的作品。
1956年苏联举行全苏美术家代表大会,有美术家公开质疑对印象派艺术家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击。风声传到中国美术界,便吹动不大不小的涟漪。为印象派鸣不平的中国美术家为数不少,而当时处于艺坛边缘的林风眠却认为“关于印象派,美术史上早已经有了定论,何必又拿出讨论呢?正如同电灯泡早就用了,还在讨论着电灯泡”。随之而来的反右派运动以冷酷的惩罚手段为这场没有结论的讨论做出了结论,印象派艺术随即被冷藏20年。
印象派在中国的复苏,是在“文化大革命”收场之后。1979年夏天,“法国印象主义绘画图片展览”在北京中山公园开幕。虽然人们看到的是印刷品而非原作,但人们终于有机会一窥被妖魔化的印象派真面目。一位参观者在图片展览的意见簿上留下的参观感言:“我的妈呀!可怕的印象派原来是这么回事……太可爱了!”中国观众终于能够以正常心看待这百年前的艺术流派了。
艺术交流的新阶段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8年春天,“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作品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这不仅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的大型法国绘画展览,也是有史以来在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西方绘画展览。中国各地画家乘飞机、火车和长途汽车到北京观看心仪已久的法国油画原作。由于展览筹办阶段对外文化交流还没有摆脱极左政治思维惯性运作的干扰,使展出作品题材仅限于表现农村生活,但从了解欧洲绘画原作的角度看,这次展览给了中国油画家前所未有的机会。
1985年5月,赵无极应邀回到他的母校浙江美术学院,举办了绘画讲习班,来自全国八所美术院校的20多位青年教师参加。与20世纪50年代马克西莫夫主持的油画训练班和罗工柳主持的油画研究班不同,这是欧洲新艺术观念和赵无极个人艺术探索经验基础上的教学活动。与赵无极讲习班研究目标不同的还有沈阳鲁迅美术学院邀请法国画家克劳德 · 伊维尔举办的研究班,伊维尔从油画的工具材料和技法层面,给新一代中国美术家以具体指导。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中法艺术交流迅速扩大。近30年中法艺术交流以及中国油画家对法国绘画的研究,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衡量,都远远超过此前的规模。而中国艺术家赴法研修的形式,也与20世纪前期由“赴法勤工俭学”支持的留学潮完全不同。具有代表性的是画家吕霞光发起筹办的艺术工作室,1984年,“吕霞光夫妇画室”在巴黎国际艺术城揭幕。在这之后,巴黎国际艺术城由中国艺术家使用的工作室不断扩展。在今天,不仅画家和学习绘画的学生对法国绘画了如指掌,许多旅游者对巴黎几大博物馆收藏的名画也耳熟能详了。与这些发展同时出现的是,中国美术家对法国绘画的关注,从技法、形式层面逐渐深入到艺术观念和精神层面。中法绘画交流从百年前有限度的借鉴,到今天的高层次对话,展现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交流既是可行的,也是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