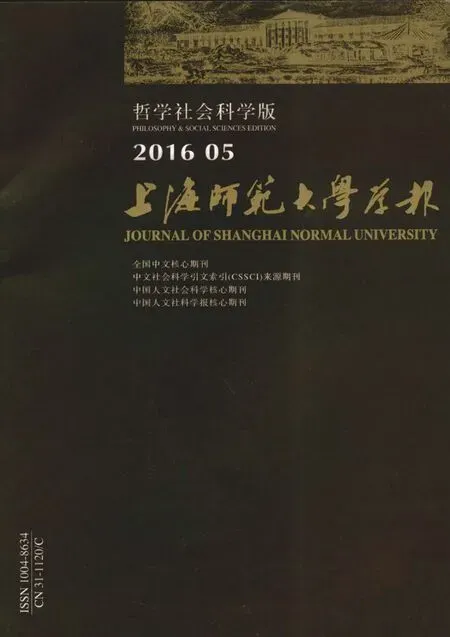诺丁斯关怀伦理思想的新意
卜玉华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上海 200062 )
一、诺丁斯的关怀伦理学想解决什么问题
1984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诺丁斯撰写的《关心:伦理和道德教育的女性视角》一书。这本书对关怀伦理学的思想框架和基本问题进行了精细的哲学式解释。此后的近20年里,诺丁斯又在思想上一脉相承地从多个角度不断地发展和丰富了自己对关怀伦理的认识,至今已陆续出版了近20本著作,发表了大量相关的学术论文。这些研究成果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并被学术界视为可与正义伦理学并立的另一种新伦理学范式——关怀伦理学。
那么,是什么样的独特贡献使得人们认为诺丁斯开创了关怀伦理学呢?她在学理上有何突破与贡献呢?
一种观点认为,诺丁斯关怀伦理学的贡献在于其研究视角:女性视角和关系视角。就女性视角而言,在卡罗尔·吉利根之前,女性主义运动已经有了较长的一段历史,诺丁斯不是女性视角的首创者。诺丁斯更看重关系视角,她认为“关系可视作我们本体性存在的基础”。[1](P3)作为人,我们生于关系中,长于关系中,不像地下长出的蘑菇那样毫无牵连。她说:“关怀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关系性。这种关怀关系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关怀者和受关怀者间的联系或遭遇……要使两人间的关系构成正确的关怀关系,双方都需要做出积极回应。无论是关怀者还是受关怀者,任何一方出了问题,关怀关系就会遭到破坏。即使双方还存在着某种联系性或遭遇性关系,但它可能已不再是关怀性关系了。”[2](P15)
另一种观点认为,关怀伦理学之所以成为一种新范式,因其将正义伦理学与关怀伦理学区分开来,彰显自身的独特性和必要性。如正义伦理学主张把世界置于自我的关系中,我与他人的关系是分离的;而关怀伦理学主张则把我置于世界之中,我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关怀的拓展。正义伦理学主张通过逻辑体系和法律制度来摆脱对个人的关系协调;关怀伦理学则主张通过关系中的交流来协调个人。正义伦理学强调我们对他人拥有权利和规则;关怀伦理学则强调我们对他人拥有的更多是责任和关怀。
的确,在当代正义伦理学主导西方伦理学界的语境下,以诺丁斯为代表的关怀伦理学的出场,在伦理学思想界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但是,这只是在比较意义上呈现诺丁斯思想的贡献,是一种外视角下的认识。认识诺丁斯伦理思想的贡献,还当从内视角即关系视角进行审视。就关系视角而言,也不乏其人。中国先人对“人伦关系”的主张,马丁·布贝尔对“我-你关系”的力荐,E·列维纳斯对具有不可还原的差异性的我—它关系的强调,以及现象学对主体间性的倡导等,都是在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那么,诺丁斯关怀伦理学之独特贡献是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质一般分为“我与你”、“我与他”和“我与它”三类,诺丁斯所要回答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关系”。这种关系是我们在日常交往世界中经常发生的关系,既可以是“我与你”的关系,也可以是“我与他”的关系。但只要你希望给对方以关怀,这时“关怀者与受关怀者”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建立的可能性。对于此种关系,一般人认为最好的答案是平等相待,而诺丁斯想回答的问题是:面对他人,仅平等相待就够了吗?我还有其他责任吗?我为什么还要关怀他人?怎样判断我是否在关怀他人?以及我怎样做才算是关怀?诺丁斯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与回答,对于我们深度认识教育中的各类关系都极富意义。
二、与他人相处时仅平等相待就足够了吗
在诺丁斯看来,人生活在关系之中,人际关系的性质决定了两类伦理学的存在。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因差异而产生不平等,但人们又渴望平等,希望彼此以平等的方式相互对待,因此,在追求平等关系的过程中便产生了正义伦理学;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的,每个人都希望被对方所接纳、承认和关爱,而不希望被抛弃、孤立,于是便产生了关怀伦理学,甚至这一伦理学更具有根本性和首要性。诺丁斯说:“关心和被关心是人类的基本需要。我们需要被他人关心。……没有这种关心,我们就无法生存下去,无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还需要被他人关心,随时需要被理解,被接受,被认同。……同样,我们也需要关心他人。”[3](P1)
诺丁斯进一步认为,回到现实,关怀作为人类的基本需要在今日更为强烈。这是由人们的生存状况决定的。她描述了今天的儿童生活:“在今天,当你走进任何一个典型的学校教室,你都会发现,孩子们来自千差万别的家庭。有的孩子父母双方全都在工作;有的孩子来自单亲家庭;有的孩子拥有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有的孩子与兄弟姐妹毫无血缘关系;有的孩子与养父母的兄弟姐妹住在一起;有的孩子根本没有父母。”[3](P6)但是,当代伦理学更多地关注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而忽视了关系,重视了正义伦理却忽视了关怀伦理的价值与意义。为此,诺丁斯指出,关怀伦理学的首要问题是我他关系。我他关系是人的一种本体性存在,其问题表述为:面对受关怀者,我拥有什么样的责任?我他之间,如何建立真正的关怀关系?
三、我为什么会关怀他人
这是有关关怀伦理的动机问题。历史上,对人的道德关怀动机的经典答案是康德的回答。按照康德的观点,这是我的“善良意志”选择的结果,是我的实践理性主动运作的结果。我的善良意志告诉我如何成为一个善的人。我的实践理性保证我是一个自律、自治的人,因为“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他不单纯是这个或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4](P46)人是目的,运用自己的实践理性为自己立法,也就是说人的道德行为出于意志自律。
诺丁斯认为,从方法论上看,我们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能只局限于主体自身。因为康德的自由意志是冷峻而抽象的,是与真实世界隔绝的,是以规则与逻辑为人立法,远离了个体的需求,不可能为道德奠基,所以,她放弃理性,认为人的关怀动机主要是基于情感而非自由意志。
诺丁斯和中国先人都承认情感是基本动力,但对情感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中国看重人的移情之心,即换位思考他人的处境,体验他人的情感,从而产生恻隐之心。如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亦即爱人之心。人皆有此心,故能推己及人。孟子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仁人即能本其不忍人之心,推其自己之所为,使他人亦能如此。仁政也是由这种恻隐之心扩充发展而来。
诺丁斯的理解与中国不同。她对将移情作为关怀动机的看法持批判态度。她认为虽然关怀动机源自情感,但“移情”(empathy)这个词具有特别的西方色彩(同样也包括东方色彩,诺丁斯似乎不大了解中国伦理思想)和男性色彩,它指的是关怀者为了更好地理解一个人而将自己的个性投射到他人的个性之上,以为他人的智性与自己一样。实际上,当关怀者将自己的个性投射到受关怀者身上,并将自己的感情赋予受关怀者的过程,是一个控制过程,而非关怀过程;我与受关怀者的关系是控制关系,而非关怀关系。她说:“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有人认为这种做法很慷慨;这种做法将我们体验到的痛苦、感情或激情毫不走样地赋予对方。确实,西方共同的民间伦理便基于这个事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在我目前进行的分析中,我将摒弃这一方法。”[5](P14)那么,不以移情作为动机,什么样的情感更为合适呢?诺丁斯认为,共情或同情(sympathy)更为合适,因为同情注重的是我与受关怀者双方情感流动的双向性。但受关怀者一定是情感共振的起点,具有特殊的首要性。在此,诺丁斯对受关怀者优先性的强调,或许是受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受关怀者理论的影响,在概念上类似于列维纳斯的受关怀者优先性。[6]为了清晰表明自己的观点,诺丁斯还援引了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 )曾举的1个例子。这个例子大意是说,在基督教第一则有关圣杯的传说中,圣杯的护卫者是一位受过重伤、3/4身体瘫痪的国王。如果第一位来到圣杯护卫者身边的人看到护卫者的悲惨状况,产生了同情心,主动问候护卫者:“你有什么困难吗?”那么,他/她就会得到这只圣杯。这时关怀者的情感是对护卫者的尊重,而是否给予帮助取决于护卫者的态度。但是,如果这个人看到护卫者,不问对方的感受,便说:“好可怜的人,我给你一些帮助吧!”那么,这个人所表达的便是移情,而护卫者很可能认为这是一种怜悯与不尊重,不接受对方的帮助,关怀关系就未真正建立起来,他/她也就得不到圣杯。[5](P14)与现实生活相联系,我们可以按诺丁斯的思路做进一步的推论。比如,一些父母、教师或长辈,时常会想当然要给晚辈一些关心,但有时非但没有获得来自对方的接受,反而可能遭到拒绝,这时父母、教师或长辈一定感觉很委屈,想不明白为何自己为对方好却得不到对方的回报。孰不知,这只是他们在移情,是情感的单向射投,并没有以晚辈的需要作为关怀的起点。
至此,这也许就是诺丁斯关怀伦理学中最为独特而有价值的一个方面,是对中国传统关怀伦理思想的一种超越。但是,在中国语境中,中国先人对移情的理解远比这复杂得多,不能像诺丁斯那样因强调受关怀者的接受状况就否定移情在我他关系中的积极作用。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移情”并非单指我与受关怀者的换位思考,而是此情此境中的换位体情。举一个例子,《庄子·秋水》: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安知”这种用语既表示“你怎知道……”,又意为“你从哪儿得知……”。但是,庄子并不只是依靠这种文字上的模棱两可而以诡辩的论点取胜。他要做出一个更有哲学意义的努力:他是想让惠子明白,使认知者独立于认知世界之外的行为是没有意义的。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Ames)对这段文字的寓意解释是:庄子对于鱼的经验是一种情境,这种情境比任何一种分离的行动者都重要。情境使庄子的世界与鱼的世界连为一体,这样,他知(按:即知鱼之乐)就是声称处于这种情境。[7](P365)因此,诺丁斯注意到了“我”对受关怀者接受愿望的忽视,却没有注意到情境为我移情的可靠性提供了大量线索和依据。
四、我这是在关怀吗
诺丁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体上有4种情况,但真正算得上关怀关系的只有1种。
第一类,“我”自私自利,漠视他人。即面向他人,主要考虑“我”的个人权益,“我”背向他人,持漠不关心态度,但从权益角度,“我”有权选择如此行动。这种情况是“自我绝对优先于他人”,很类似于诺丁斯所举的美国广为人知的案例:
国庆日,有位醉酒的租船者弄翻了船,双手逐渐抓不住船沿而最终溺死。整个过程中,提供租船服务的那些人就坐在湖边,目睹这一切的发生。马萨诸塞州高级法院审判人员一致认为:被告没有义务留意溺水者的呼救声。其他法庭案例认为,如果成人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救助显然处境危险的儿童却袖手旁观,是可以免责的。对于“无援助义务”原则的惟一例外涉及对受害者负有优先法律责任者,如父母、指定监护人等。陌生人不负有援救的义务。[5](P35)
对此,任何一种伦理学都会持否定态度。诺丁斯认为这是个人权利的滥用,是对普遍人性的应有的道德义务的否定。换个角度讲,这种自私自利在当前现实生活中大行其道,是正义伦理学主张的权利优先于善的现实表达。
第二类,“我”自以为是,关注他人。即面向他人,“我”固执、严格甚至残酷地关注受关怀者,并强加“我”的意愿,误将关注当作关怀。这种情况下,“自我优先于他人”极其类似于一些专制的父母对待子女的情况。这样的父母总是告诉孩子,说他们太贪玩,总是将别人家孩子的优点放大而让自己的孩子深感自卑。这样的父母总是告诉孩子,自己之所以严厉地惩罚他是因为爱他、为他负责,并经常喋喋不休地告诉孩子自己是他的利益保障者。事实上,这样的父母总是从自己立场出发,从未认真地倾听过孩子的声音,孩子很可能也从未真正体验过父母所给予的“关怀”。
所以,诺丁斯认为这也算不上真正的关怀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受关怀者没有受到尊重,没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和表达自己的主张,久而久之,便可能成为“我”的顺从者。
第三类,面向他人,牺牲自我。即面向他人,“他人优先于自我”, “我”对他人负有责任,应当关怀他,即使牺牲“我”自己。这时,他人的存在赋予“我”绝对责任与关怀使命,随时随地需要“我”为之做出牺牲。这种我他关系,从小处说,表现在父母溺爱孩子,宁愿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甘愿服务孩子;表现在雷锋式人物心甘情感地服务他人。从大处说,表现在军人保护国家的天职上。从更大处说,表现在列维纳斯“无限受关怀者”意义上的人类关怀上。
其实,在今天官方确立的模范人物形象上,这种我他关系仍然居主导地位。但是,大众的不屑与怀疑本身已经说明它并不符合真实人性。诺丁斯认为,这种我他关系的可贵之处在于认识到了受关怀者的存在,但仍然算不上是关怀关系,其缺陷在于没有分析受关怀者是否需要“我”做出牺牲,而把需求(want)当作“需要”(need)来处理了。她举例说,若干年前,阿富汗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地震,富国向该国运送了大量的食品和衣服。实际上,灾区急需的是建筑材料,并不缺衣少食。[5](P35)这说明,关怀者需要了解其所回应的个体或群体的状况,再做出决定。同样可以想像,如果雷锋式的人物每日早晨替环卫工人打扫了街道,那么,环卫工人也未必感谢雷锋式的人物,因为环卫工人需要工作并乐于从事这项工作,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得到更多人的尊重和理解。当然,作为战士在必要时为国家做出牺牲,这就是从国家需要出发,是一种正当的牺牲,军人与国家之间是一种关怀关系。
第四类,面向他人,对他人负责,也对“我”负责。卡罗尔·吉利根曾在女性自我观和道德观发展的研究中发现,面向他人,我们道德选择的依据是心理逻辑,而非正义伦理学依据的形式逻辑。比如,当我面对他人的需要而做出自我牺牲时,我会想:“善就是自我牺牲。”但如果这时被关怀者没有给予应有的回应,我在心理上难免会想“他人这样没有反应,我觉得被利用了,很受伤害”。的确,诺丁斯非常认同这一自我分析。她认为,面向受关怀者,我与他人是平等的,都应当被关怀,应同时考虑自己和他人的需要。如此选择,对他人负责是一种善,对自己负责则是一种诚实和现实。这时的我虽关注自己的需要,有自私的一面,但却是诚实和公平的。这证明我是一个能够更有力地做出自我决断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个更为独立的人。
当然,我与受关怀者虽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能力上一定有所差异,否则面对受关怀者,我不需要做出关怀。因此,诺丁斯认为关怀关系一定是非对称性的,即便被关怀者最初没有主动表达被关怀的需要,我也要给予主动关怀,只是关怀关系的持续发展取决于双方共同协作。她举例说,孩子一般不会主动说自己需要学习,但作为成人,应主动给孩子提供学习关怀。在学习过程中,教与学的互动质量则取决于双方的关系。
此外,人们通常理解关怀是一种品质、一种美德。诺丁斯也认为,虽然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关心别人的人,且可能长期默默地奉献关心,而另一个人却坐享其成地接受关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关心者确实需要一种美德来支持他的关心行动。但是,诺丁斯认为,仅有这并不够,“有很多人自称‘关心’别人,但是接受他们所谓‘关心’的人却感受不到关心”。[2](P18)最重要的是关怀者要能够创造一种被他人感知到的关怀关系。
诺丁斯对非对称关怀性关系的强调,使她对关怀性关系的认识与其他认识区别开来,彰显了自身的独特性,却也给予这一思想认识以局限性。比如,1984年,在她的第一本关怀伦理学著作《关怀:伦理和道德教育的女性视角》出版不久,便有人批判她的这一理论只能是领域性的伦理学;关怀伦理学即使是人类道德实践的重要基础,在形成人与受关怀者的亲密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仍然有许多并不适合运用关怀伦理,比如国家和国际政治、经济、商业以及非人际性的制度等中都不适用关怀伦理学。领域伦理学注重的是在其领域中自身独特的道德程序和道德优先性。如对教育而言的最佳道德实践方案,但对经济活动未必是最佳的。所以,有人认为,关怀伦理学更适用于具有抚养与照料关系的领域,如家庭、学校、医院等。对此,诺丁斯反驳人们狭隘地理解了关怀伦理学,认为关怀伦理学绝非领域伦理学的一种,而是一种伦理立场,具有普遍适用性。她在后来出版的若干本著作中都尽力表明关怀伦理价值的普遍性。
在我看来,诺丁斯只是关注到关怀关系中的差异性,而忽视了差异性与同质性之间的沟通。中国儒家伦理思想运用整合的方式使差异性转化为和谐性:“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使得我与受关怀者的关系是合作而不是同意,是和谐而不是一致,是协调而不是符合。在此意义上,这的确比诺丁斯高出一筹。
五、我如何才能更好地关怀
正如诺丁斯认为关怀关系的动机源于我与受关怀者之间的共情,同时这种共情并不像父母对子女的自然关怀之情那样能自然地产生,相反,它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建立。但是,关怀关系的创建从哪里开始呢?诺丁斯认为,既然自然伦理是关怀伦理的基础,自然要从家庭开始创建关怀关系;创建关怀关系是教育和家庭的基本使命之一。她说:“我们最可贵的能力是在家庭或与之相似的组织中培养起来的。”[3](P26)如果家庭中该人充分体验到关怀,那么,他很可能发展出一种可以称为关怀伦理的道德取向。
诺丁斯进一步指出,有4种基本的方法有助于发展关怀关系:一是榜样。“榜样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很重要,对于关心则是关键因素。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下,我们不去试图教导学生记住一些原则,以及如何应用这些原则去解决问题,就像教数学推理一样,相反,我们将向学生展示在自己的社会关系范围内怎样关心。……我们无需告诫学生去关心,我们只需与学生建立一种关心的关系,从而来演示如何关心。”[3](P32)二是对话。“对话是双方共同追求理解、同情和欣赏的过程”,“也帮助双方互相探索,最后达成某种意见和决定”。[3](P32)三是实践。“如果我们希望人们过一种符合道德的生活,关心他人,那么我们应该为人们提供机会,使他们练习关心的技巧。更重要的,使他们有机会发展必需的个性态度。”[3](P32)学生的关怀实践还应当走出教室。“所有的学生都应当参与关心的练习”,让他们担任管理者、环卫工人、厨师或是小学生的生活小帮手。服务机会应当延伸到社区,在“医院里、卫生之家、动物照料所、公园或生态园区”。[3](P34)社会服务包括所有“伦理理念培育中的三项伟大意义:在成人的示范下参与关心,并与成人讨论这项工作的困难和价值,在他们自己的工作中证明关怀伦理观是重要的”。[1](P187~188)四是确认。马丁·布贝尔将确认描述为对他人行为的优点进行证实和鼓励。受此启发,诺丁斯建议,“我们要向学生表明,他们自身作为伦理和智力主体有力量建立某种伦理,也有力量破坏某种伦理……”[1](P193)“我们要力争在每一个遭遇到的人身上发现也许不能被轻易发现的可取之处甚至可赞美的优点,并把他表现出来的可取之处或者优点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至少视其为道德上可接受的东西。”[3](P36)
在自然情感是人形成关怀伦理的基础这一点上,诺丁斯和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有着共识,但在如何走出自然关怀、推己及人地同样关怀陌生人的认识上有差异。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也强调以家族伦理为基础建立伦理关系。这可通过“伦”字义而知。“伦”建立的原理是“人伦本于天伦而立”。“人伦”即社会的伦理关系模式是由“天伦”即血缘关系的模式引申出来的。而“天伦”之所以被冠以“天”,是因为它出自人的血缘本能,是天然形成的。人伦关系的特点是先有一个基本的关系模式,即血缘关系模式,然后再把这种关系外“推”出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形成社会的人伦关系,从而也构成中国伦理的文化特性,赋予中国伦理以特殊的文化韵味。它使中国伦理建立在家族血缘的根基上,具有巨大的根源动力和源头活水。
诺丁斯认为培养人的伦理关怀能力需要教育和家庭的介入,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则认为自然伦理本身可形成自组织式的推己及人。用孔子的说法,这是因为人能够“能近取譬”。[9](《雍也》,第30章)用今天的说法,即人会运用类比法实现情感的迁移。这一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中国“恕”的观念上。芬格莱特(H.Fingratte)的说法很有说明力:
“恕”不会让我放弃自己的判断,以至于成为另一个人。“恕”的任务分为两部分。第一步……遇到问题时设想换一个人会怎样。第二步是问我(如芬格莱特)处在他的情形下需要做些什么?总之,“恕”让我去做别人希望我做的事。[10](P385)
两种关怀伦理思路的差异,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在西方,在以柏拉图为代表的理性逻辑思路下,总是假定存在着一个客观的、普遍有效的关系模式作为目标,有待于人们去追求和实现。教育就是以此目标为导向,逐步引导下一代趋近这个目标。所以,受此思路影响,虽然诺丁斯也强调教育的具体情境,但她强调的是抽象目标对具体情境的优先性,情境的落实只不过是实现目标的一个个具体途径。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思路下,具体个体优先于抽象整体。孔子没有像柏拉图那样从诉诸一个目标、一套理念模式开始,而是回到自身来调整具体个人的行为和性情。他说:“克己复礼为仁。”[9](《颜渊》,第1章)“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9](《卫灵公》,第21章)他所表达的意思就是,成就自己的品质靠的是自己而非别人。依靠他人是不可靠的,可靠的是自己,所以他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9](《宪问》,第42章)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君子的,这时就需要“礼”作为引导和约束了。
虽然,孔子对人性和人的自我教育能力过于乐观与自信,但他更强调具体情境中个人的伦理判断。而诺丁斯的建议虽更有现实意义和实践可行性,但属于目标导向下的伦理决断,其功利主义色彩浓厚。设想一个情境:当我看到一位盲人在过马路,如果我心里想,路上车辆很多,他需要我的帮助才能安全过马路,我帮帮他吧,不管盲人是否愿意接受我的帮助。这时,我的判断依据是此情此境,而非“我不能自私,所以我应该……”,也非盲人的求助。这是孔子的思路。但如果“我”想我不能做一个自私的人,我应当给予盲人以帮助,但盲人也许并不需要我的帮助,我先静观其变,适时做出反应吧!这便是诺丁斯的思路。
[1] Noddings, N. Caring: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
[2] Noddings, N.The Challenge to Care in school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education[M]. New York: Teacher college Press.1992.
[3] 诺丁斯.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M].于天龙,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
[4]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5] 诺丁斯.始于家庭:关怀与社会政策[M].侯晶晶,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6] Levinas,Emmanuel. Ethics as First Philosophy[A]. The Levinas Reader[C]. ed. Sean Hand,Oxford:Blackwell,1989, pp.75-87.
[7] 安乐哲.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M].彭国翔,编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
[8] Noddings,N.Philosophy of education[M].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1995.
[9] 孔子.论语[M].
[10] 芬格莱特.沿着论《论语》的“一贯之道”[A].罗思文(H.Rosemont),史华慈(B.Schartz).美国宗教学院主题学术文集:对古典中国思想的研究[C].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