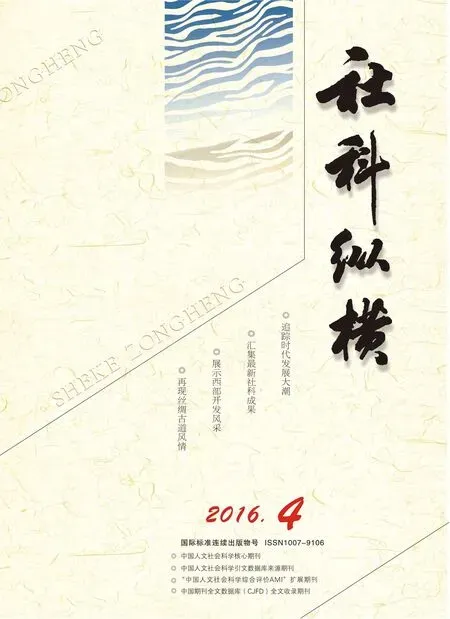从文学伦理学的视角解读《红字》
杨桂琴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国语学院 甘肃 成县 742500)
从文学伦理学的视角解读《红字》
杨桂琴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国语学院甘肃成县742500)
自《红字》问世以来,始终存在着不同意见,众说纷纭,各执己见。其实,真正使得小说具有无穷魅力的则是作品讲述的一系列伦理事件及其带来的启迪和思考。《红字》的真正意义在于霍桑成功地运用小说这一特殊文学形式,讲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伦理故事以警示后人。本文试图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出发,重点分析小说中人物海斯特·白兰、丁梅斯代尔以及齐林渥斯所遇到的伦理问题及其他们所处的伦理环境,斯芬克斯因子的体现及其伦理身份的错位和不当的伦理选择。
《红字》 伦理事件伦理环境伦理身份斯芬克斯因子
霍桑出生于马萨诸塞州一个没落的世家,他家世代都是虔诚的加尔文教信徒。1808年,霍桑4岁时,当船长的父亲患病死于荷属圭亚那。霍桑14岁时到祖父的庄园里住了一年。那附近有个色巴果湖,霍桑常到那里打猎,钓鱼,读书,充分领略自然风光。据他晚年回忆,他的一生以这段时间最为自由愉快。而他孤僻个性和诗人气质,也是在这里形成的(胡允桓1991:1)。1838年,霍桑入股参加了爱默生等超验主义者创办的布鲁克农场。1849年夏,他经受了失业以及母亲的去世给他带来的强烈痛苦和打击,全身心投入到《红字》的写作中去。虽然《红字》于1850年出版后经常受到谴责,说他的小说诲淫纵欲或表现病态,但确在英美文学界确实引起了轰动。
《红字》是霍桑的代表作,就主题思想而言,有的批评家认为,根据小说提供的历史背景和故事情节,霍桑的小说《红字》要表达的是清教的教义。那就是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但由于亚当犯了原罪,人生来皆有罪,理应受到惩罚,而要得到拯救则完全靠上帝的宽恕。对于这样一个故事,批评家和读者自然会提出许多不同的观点。实际上,《红字》的真正意义在于霍桑成功地运用小说这一特殊文学形式,讲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伦理故事以警示后人。
一、《红字》所描述的伦理环境
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寻找文学产生的客观伦理原因并解释其何以成立,分析作品中导致社会事件和影响人物命运的伦理因素,用伦理的观点对事件,人物,文学问题等给予解释”(聂珍钊2010:14)。如果重返《红字》的伦理现场,我们不难体验小说环境的那种压抑感与窒息感,进而破悉小说中一系列事件发生的动因。小说一开头,就描述了这样一幅场景:“一群身穿黯色长袍、头戴灰色尖顶高帽、蓄着胡须的男人,身着颜色灰暗的衣衫,头戴尖塔型的帽子;混杂着一些蒙着兜头帽或光着脑袋的女人,聚在一所木头大房子前面。房门是用厚实的橡木做的,上面密密麻麻地钉满大铁钉。监狱一般都远离闹市区,处于偏僻区域。尽管我们不知道这座监狱的确切位置,但是从小说描述的情况来看,映入眼帘的是陈旧与腐朽。监狱阴森,幽暗,门上铁钉锈迹斑斑,丑陋不堪。监狱与车辙之间的草地,野草疯长。小说写到:“从这座丑陋的大房子门前,一直轧着车辙的街道,有一块草地,上面过于繁茂的簇生着牛蒡,蒺藜,毒莠等这类不堪入目的植物。这些杂草显然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了共通的东西,因为正是在这块土地上早早便诞生了文明社会的那株黑花——监狱。然而,在大门的一侧,几乎就在门限处,有一丛野玫瑰挺然而立,在这六月的时分,盛开着精致的宝石般的花朵……”(胡允桓1991:34)。在现实生活中,玫瑰预示着爱情,而野玫瑰处于监狱门之旁,象征着本书描写的爱情凄婉动人,也象征着女主人公融魔鬼与天使为一身的复杂性格。
阴森的监狱是秩序的一种象征。那么它们的废弃和破败所隐喻的乃是人类文明、秩序和理性的丧失,隐喻了人类伦理道德的腐化、沦丧与困境。在小说中,牛蒡、铁蒺藜等野草,破坏了人类铺设的建筑,象征着女主人公的原始欲望和非理性。“不堪入目”说明主人公身所犯的原罪。野草的存在,恰如小说人物的欲望,脱离了理性的控制,带着破坏性的力量把小说人物逐入非理性状态。
小说最主要的伦理环境莫过于海斯特·白兰佩戴A字被示众的场面。就在我们的故事发生的那个夏天的早晨,有一种情况颇值一书:挤在人群中的好几位妇女,看来对可能出现的任何刑罚都抱有特殊的兴趣。“婆娘们,”一个满眼横肉的五十岁的老婆子说,“我跟你们说说我的想法。要是我们这些上了年纪、名声又好的教友会会友,能够处置海斯特·白兰那种坏女人,倒是给大伙办了件好事。你们觉得怎么样,婆娘们?”(胡允桓1991:35)这段话说明了海斯特·白兰所处环境的尴尬及大众的盲目。鉴于丈夫的离奇失踪,海斯特·白兰原本完整的家庭伦理结构遭到破坏,首当其冲的是身份确认的障碍。由于海斯特·白兰失去了丈夫,独自一人生活及其艰难,因此与牧师丁梅斯代尔在伦理选择中,被自己的原始欲望所驱使,无法遵守在伦理选择中对各自伦理身份的禁忌,最终导致了悲剧。但是,海斯特·白兰很快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她精心地缝制并装饰那个象征着自己罪恶的“红字”,直面自己遭受的惩罚,精心教养他与情人所生的女儿,以积极的人生态度面对她所受的惩罚,以给人做针线活谋生,内心宁静,善待穷人,帮助病人,抚慰遇难的人。但专制文化和清教法律的牺牲品不是海斯特·白兰,而是丁梅斯代尔牧师。作为清教政府权利道德、文化的代表,丁梅斯代尔牧师是一个被害者,而不是害人者,他的痛苦变成了一种美德,这种痛苦来自于他遵循道德的本性对自我的惩罚,他的痛苦比白兰深刻的多。丁梅斯代尔在强大的负罪感的压力下,过着毫无生气的生活,他采取了与白兰完全相反的赎罪方式,掩盖自己所犯的罪,因为隐瞒自己所犯的罪而痛苦。他过着苦心僧的生活,生命的气息在一天天走向枯竭。于此并行的是,作者以憎恶的笔调描写了围绕这一对“罪人”周围的大众,以及为了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探询他人灵魂秘密,折磨他人的齐灵窝斯——白兰的丈夫。作者把他塑造成一个衰老而又丑陋无比,冷酷无情的人。他富有知识却性格偏执,在复仇欲望的驱使下丧失了人性。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知识与人性扭曲的关系。受惩罚的“犯罪者”的善良、美好与那些充当着惩罚者的大众和个人的伪善、邪恶、宗教狂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红字》所阐释的斯芬克斯因子
聂珍钊认为:“从伦理意义上而言,人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组成。斯芬克斯因子是文学作品伦理表达的核心内容。”(聂珍钊2011:1)所谓的人性因子是指人类在从野蛮向文明进化过程中出现的能够促使自身进化为人的因素。人性因子可以使人产生伦理意识,实现从兽到人的转变。人性因子的核心意志体现是理性意识。主要表现为对伦理秩序,伦理禁忌等人类道德模范式的遵守。兽性因子是人的动物性本能,是人在进化过程中动物本能的残留,导致人在经历生物选择之后依然存在非理性因素。兽性因子最突出的意志体现为“自然意志”,主要表现为人的不同欲望,如性欲,食欲等人的基本生理要素和心理动态。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关键因素不是人的兽性因子,而是其人性因子。作为高级因子的人性因子如果控制了低级因子的兽性因子,人就会成为有伦理意识的人。在文学作品中,人的人性因子往往也会被兽性因子所控制,使得人的伦理意识淡漠,甚至不具有伦理意识,不辨善恶。在《红字》中,齐林渥斯等人斯芬克斯因子的不同组合和变化导致了他性格行为的变化,引发了他们彼此之间的伦理冲突,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给我们带来关于人类成长的伦理启示。
在复仇欲望的驱使下,齐林渥斯身上的兽性因子抑制了他的人性因子,阻止了伦理意识的产生。齐林渥斯身上兽性因子最突出的表现当属他对海斯特·白兰的威胁、恐吓和对丁梅斯代尔牧师内心的折磨。处于惊恐中的白兰始终无法阻挡齐林渥斯复仇的步伐;而齐林渥斯的惯常行为则是以医生的身份与丁梅斯代尔牧师住在一起,表面的理由是更好地观察他的病情,给予更好的治疗,实际上是为了折磨他,削弱他的精力和体力。最后,海斯特·白兰觉察到了齐林渥斯的罪恶图谋,向牧师提出携珠儿一同私奔,逃出这块殖民地到欧洲去建立新生活。而牧师受清教意识的束缚,认为私奔是罪,罪上加罪,故而犹豫不决。但是他最后还是勉强同意了。但令海斯特·白兰没想到的是齐林渥斯也从船长那儿弄到了船票,出逃计划宣告失败。
在兽性因子的主宰下,齐林渥斯的自然意志似一匹脱缰的野马,脱离了理性因子的引导与控制。在与海斯特·白兰一开始见面时,齐林渥斯就说出这样的悖论式话语:“既然你曾经是我的妻子,绝对不要对任何人露一点口风,说我曾经是你的丈夫……别露一点口风,尤其对你恋着的那个男人。要是你在这点上坏了我的事,你就小心点吧!他的名誉、他的地位、他的生命全都掌握在我手心里。当心点吧。”(胡允桓1991:37)这样的叙述语言初读起来颇令人费解,但细读之后,又让人觉得颇有道理。从表面上看来,海斯特·白兰确实保守住了秘密,而齐林渥斯的复仇计划在按计划进行。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当海斯特·白兰发觉齐林渥斯的复仇手段十分残忍时,即兽性因子一直在占上风,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誓言,把真相告诉了丁梅斯代尔牧师。在小说开始,齐林渥斯为了掩人耳目,以医生的身份与海斯特·白兰在牢房相见,他要她保证不暴露他真实的身份,并决心要追查出她的同犯以保仇血恨。他很快怀疑到丁梅斯代尔牧师,假意跟他建立亲密关系。牧师的良心受到谴责,但又没有勇气承认自己的罪孽,健康每况愈下。不久,齐林渥斯搬到牧师那儿与他同住,理由是更好地观察他的病情,给予更好的治疗,实际是为了折磨他,削弱他的精力和体力。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我们根本看不到齐林渥斯对牧师的体谅、关爱和帮助。与此相反,他刺激有病的牧师,故意在牧师面前探询他的隐私,嘲弄牧师的懦弱,以这种方式得到内心的满足和愉悦。
由于医生对年轻牧师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强烈的兴趣,医生以一个教民的身份与他形影相随,并且想战胜他天性中含蓄和敏感,来赢得他的友谊与信任。他对他的牧师的健康深为震惊,还急切地给予治疗,他认为,如果及早治疗的话,总不会不见疗效的。然而,“我不需要医药,”牧师说。齐林渥斯却以为牧师要轻生。但牧师依靠自己对宗教的信仰而活着,“还有一大批人——其中不少是头脑冷静、观察务实的,他们在别的事情上的见解一向颇有价值——肯定的说,齐林渥斯自从在镇上定居以来,尤其同丁梅斯代尔牧师先生伙居以来,外貌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起初,他表情安详而沉思,一派学者模样,而如今,他的脸上有一种前所未见的丑陋和邪恶,而且他们对他看的越多,那丑陋和邪恶就变得越明显。”(胡允桓1991:97)而他们认为丁梅斯代尔被装扮成齐林渥斯的撒旦的使者钻入牧师的内心,阴谋破坏他的灵魂。齐林渥斯在客观上实施了报复行为,触犯了医生对病人应尽义务的伦理禁忌。我们看不出他对牧师有任何一丝愧疚和悲伤之情。
三、错位的伦理身份,不当的伦理选择
在小说中,海斯特·白兰、丁梅斯代尔,尽管完成了人的第一次伦理选择,即生物选择,但是却面临至关重要的第二次选择,即伦理选择的考验。伦理选择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他们是否真正实现了从儿童到成人的转变。然而,由于缺乏伦理意识的有效引导,正确地完成选择,对他们而言是十分艰难的。实际上,在伦理身份的选择上,海斯特·白兰等人都犯了难以挽回的错误:第一,海斯特·白兰不仅放弃了自己作为齐林渥斯妻子的身份,选择做牧师的情人,而且,还与他生下珠儿;第二,齐林渥斯不愿海斯特·白兰公开自己的身份,而自己也不愿承认是她的丈夫,意欲复仇;第三,牧师丁梅斯代尔放弃了作为海斯特·白兰情人的身份,而甘愿自己遭受内心的煎熬,独自默默负罪,其中最为严重的莫过于身份错位所做出的错误的伦理选择,因为它直接犯了通奸的伦理禁忌。
在19世纪的文学中,女性或者是天使,或者是妖魔。前者是道德的化身,后者则是堕落的荡妇。在《红字》中,霍桑在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中,超越了传统文学中女性作为天使与妖女形象的两极分化与对立,而是将两种气质结合于一体。海斯特·白兰既是一个偷吃禁果的引诱者,她受到惩罚,这是对一个女人最坏的惩罚——带上通奸的标志,被钉在耻辱柱上;但她又具有天使般女人的特点。(陈晓兰2006:7)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把人同兽区别开来以及在人与兽之间做出身份选择。”虽然海斯特·白兰等人完成了人类的生物选择,具有人类外形,但由于他们缺乏一定的伦理意识,难以实现自己的身份认同。就海斯特·白兰而言,尽管她已是有夫之妇,却选择与牧师丁梅斯代尔相爱;就齐林渥斯而言,他尽管是海斯特·白兰的丈夫,却隐瞒自己的身份;就牧师而言,尽管他与海斯特·白兰生下珠儿,却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珠儿的父亲,直到临死前才公开忏悔自己的罪行。“在文学作品中,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从这个意义上讲,海斯特·白兰、丁梅斯代尔、齐林渥斯等人触犯了不同的伦理禁忌。在小说的结尾处,丁梅斯代尔精力充沛,精神抖擞,步履矫健,与海斯特·白兰行走在游行队伍中,丁梅斯代尔来到了他一生中空前绝后的最光辉,最荣耀的时期。他走向刑台,伸出双臂,搂抱小珠儿。他不顾齐林渥斯的阻拦,公开忏悔罪行,然后倒地死去。随着牧师死去,齐林渥斯全部智力和活动几乎全部丧失殆尽。根据他的遗愿,他把在北美和英国的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财富,留给小珠儿。而海斯特·白兰生活含辛茹苦,自我献身救助遇难的人,对他人无微不至的关心。使那胸前的红字不再是引起世人蔑视和冷嘲的耻辱的烙印,却变成了一个使人为之悲伤,望之生畏,而又让人肃然起敬的标志。终于,各人以自己的方式,回归正常的伦理秩序。伦理规则是伦理秩序的保障,一个人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就必然要受到伦理规则的制约,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四、结语
《红字》集中体现了霍桑复杂的宗教思想和人性观以及他对罪与罚的独特认识。人对自身罪恶的不同态度贯穿小说的始终。从中可以看到新英格兰的清教文化对霍桑的深刻影响。尽管霍桑在这部小说中表达了17世纪的宗教偏执与文化专制,但他并不否定“原罪”的思想。他的许多小说表现了人的罪恶以及人对罪恶的认识和态度。在《红字》中,霍桑赞扬了海斯特·白兰对罪行的坦白与承担以及积极的服罪方式,而否定了不敢面对罪恶的丁梅斯代尔牧师,但同时又否定了同样罪恶深重但以惩罚他人为目的的医生和大众。
麦克尤恩曾说:“文学在最有限和最具体的范畴内,是人类普遍本质的最好展示。”(McEwan,Ian.2006:41)《红字》通过一系列伦理事件,突出再现了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在人性中的激烈交锋以及身份确认,伦理选择上的困难,揭示了伦理意识对道德完善的重要性。
[1]McEwan,Ian.Literature,Sciene and Human Nature[A].In Robin Headlam Wells and Johnjoe Mcfadden(eds).Human Nature Nature:Fact and Fiction[C].London:Continuum,2006:41.
[2]陈晓兰,王元媛译.《红字》名家导读[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7.
[3]霍桑.胡允桓译.红字[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34-37. [4]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J].外国文学研究,2010(1):12-21.
I06
A
1007-9106(2016)04-0132-04
杨桂琴(1969—),女,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论及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