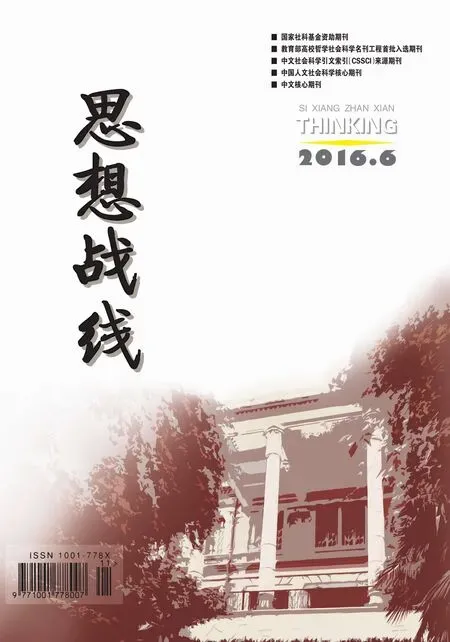李斯特谱系:一再被强调的国家和逐步被重视的社会
杨虎涛
李斯特谱系:一再被强调的国家和逐步被重视的社会
杨虎涛①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国民共享和产业协同为导向的创新驱动战略及政策选择研究”阶段性成果 (14BJL005)作者简介:杨虎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湖北武汉,430070)。[挪]赖纳特:《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卷,贾根良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与斯密传统的世界主义经济学相对,经济思想史上存在着一条清晰的重商主义理论谱系,即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格申克龙的后工业化国家、发展型国家和演化发展经济学。这一谱系强调国家利益、保护主义和竞争优势,尤其重视国家在现代化和经济赶超中的作用。与其一以贯之的“国家执念”相比,李斯特谱系对社会基础的重视程度是逐步加大的。对社会基础的关注对象,即关键行动者上,也逐步从城市资产阶级、封建贵族逐步扩展到企业组织和广大民众。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上,也逐步从单向度的国家作用发展到国家-社会互动的观点。李斯特谱系的这一变化,体现了国家、社会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渐进协同演化过程,在国家与社会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国家的专制性力量向建制性力量转化,以及建制性力量中的渗透力、汲取力和协调力的形成过程,对不同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有着不同的影响。
李斯特谱系;国家;社会;建制性力量;发展型国家
一、引 言
在国家发展的成功与失败的问题上,存在着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与李斯特的国家主义经济学两条不同的理论脉络。前者的关键词包括了静态比较优势、自由贸易和世界主义,以资源最优化配置和“交换”为主旨,在经济思想上体现为斯密、马歇尔、瓦尔拉斯、萨缪尔森等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发展谱系,后者的关键词则包括了动态竞争优势、保护主义和国家主义,以资源创造和“生产”为核心,在经济思想上体现为焦万尼·博塔罗 (Giovanni Botero)、安东尼奥·舍拉 (Antonio Serra)到李斯特、桑巴特、熊彼特、发展型国家、新熊彼特学派和演化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谱系。而在理论和实践的两个领域内,斯密谱系和李斯特谱系分别体现出了不同的支配力。虽然按照科林·克拉克的标准:“所有的理论都必须被根据观察到的事实不断地被检验,并再次被检验,那些被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必须被无情地拒绝。”①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国民共享和产业协同为导向的创新驱动战略及政策选择研究”阶段性成果 (14BJL005)作者简介:杨虎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湖北武汉,430070)。[挪]赖纳特:《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下卷,贾根良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5页。然而,尽管富国之路一再表现出斯密谱系对现实的背离,但这一谱系不仅牢牢占据了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同时也驱逐了李斯特谱系经济学,而作为成功的富国术,李斯特谱系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论尊重,尽管其政策一再被使用,理论也不断被证实。
从李斯特谱系的角度看,斯密谱系的错误在于在“夸大了世界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也因此而低估了主权国家能否调动国内资源的不同自主性和能力”。②[澳]琳达·维斯,约翰·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黄兆辉等译,长春:吉林出版社,2009年,第1页。后发国家工业化的关键在于发挥国家在调动和组织资源上的自主性和能力。在李斯特谱系中,国家对替代性前提条件的构建 (格申克龙,2009)、强力介入市场并有明确的产业计划 (约翰逊,1982,阿姆斯登,1989),选择正确的产业 (赖纳特,2008)才是成功的关键所在。然而,当李斯特谱系认为,国家在可以具备足够的“调动国内资源的自主性和能力”的同时,也意味着,国内资源的客观存在和可调动性是其理论的隐含前提,国家的作用对象和国家行动的传递机制都被视为是完备的。这就不免使其具有了某种“唯国家”的理论向度,而对国家行动的作用对象及其传递机制的分析则有所欠缺。本文的观点是,与李斯特谱系一以贯之的“国家执念”相比,李斯特谱系对社会基础的重视程度的确是渐进的,其研究对象和核心观点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出国家、社会和市场经济是一个协同演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建制性力量的形成,以及这种力量中的渗透力、汲取力和协调力,对不同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有着不同的影响。
二、一再被强调的国家
斯密谱系和李斯特谱系的分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市场笃信”和对“政府执念”的对立。从重商主义,到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以及德国历史学派,从格申克龙的后发国家到赖纳特和张夏准的演化发展经济学,直至维斯 (L. Weise,2009)等人的新国家主义,都表现出对国家作用的一再强调。更具体地说,针对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李斯特谱系一直在强调国家在统合资源和引领方向的不可或缺性。
从源头,也就是重商主义时期开始,李斯特谱系就与国家作用密不可分。因为,“重商主义者建立的主要制度就是国家”。①[挪]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8页。在时间上,维斯指出,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经济的发展,两个过程是同步进行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实际上也是一个国家将自己从私营或社会行动者的日常需求中脱离出来的过程。②维斯等人在其著作的第2、3两章中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参见 [澳]琳达·维斯,约翰·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黄兆辉等译,长春:吉林出版社,2009年。这种重商主义和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时间上的惊人一致性,并不是一种巧合,因为重商主义锻造了民族国家的汲取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而国家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成功,也进一步强化了重商主义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富国策”的地位。“在民族国家缔造过程中,经济和政治的联合规划,我们称之为重商主义”。③[挪]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5页。基于对 (普鲁士)王权干预下的重商主义制度特点的总结,施穆勒 (Gustav Schmoller)认为,重商主义的核心就是国家构建(state-making)和民族国家建立 (nation-build⁃ing),是以国家的经济组织和政策取代地方或区域性的经济组织和政策。④[德]施穆勒:《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郑学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61页。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重商主义指引下的早期国家经济发展,只是一个奢侈品、战争、领地和财富追求过程中的“无意间”结果 (unintended consequences)。但这并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是国家有目的的需求,才导致了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战争对财政的需求,从而对关税的需求才引起了保护性政策的兴起;同样还是战争的需求,导致了冶炼锻造、船舶制造等领域的创新和技术变迁。
国家利益同样也是李斯特经济学的出发点,正如基思·特赖布指出的那样,“真正使李斯特有别于斯密的地方就是他所强调的国家利益”。⑤Tribe,Keith,“Friedrich List and the Critique of‘Cosmopolitical Economy’”,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ocial Studies,vol.56,no.1(1988),pp.17~36.李斯特在批评斯密的《国富论》时指出,斯密的国家“指的是全人类所有的国家,”⑥[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20页。也即世界。李斯特的整个理论体系,按照民族国家的独立性——民族国家利益的不可否定——国家富强本质是国家 (国民)生产力的提高——而生产力最重要的部分是“精神资本”,这一逻辑脉络展开。其中,国家不仅是国家利益的载体和前提,也是提升生产力的重要推手。李斯特理论中的国家作用,不仅体现在关税保护和幼稚产业扶持上,也体现在教育、培训、基础设施、法律制度等“显而易见正确的,也不存在什么争议,因此无需过多论述的方面”。⑦[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杨春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06页。而作为先驱,李斯特的国家主导的思想也对德国历史学派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是旧历史学派的罗雪尔还是新历史学派的施穆勒,都将国家视为经济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因素。罗雪尔认为,国家是经济活动中一种不可或缺的“无形资本”。⑧魏 建:《德国历史学派兴衰述评》,《经济科学》1999年第2期。施穆勒更是指出:“没有一个坚强组织的国家权力并具备充分的经济功用,没有一个 ‘国家经济’构成其余一切经济的中心,那就很难设想有一个高度发展的国民经济。”⑨汤在新:《论历史学派》,《经济评论》1991年第2期。
在格申克龙的后工业化理论中,国家作为替代性条件的构建者,同样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所在。在格申克龙看来,落后与发展的高期望值之间的紧张关系,将构成推动工业化发展的力量,而这种力量要转化成经济发展的效果,取决于国家对经济发展所缺乏的替代性条件,如较大规模的私人资本积累,工业制成品的市场容量等替代性条件的强力构建。格申克龙认为,国家可以,也有必要通过有效的干预实现这种替代性条件。具体表现为:
通过政府的高积累或者投资银行来代替私人储蓄,以铁路建设等公共工程支出来弥补国内落后的农村经济对于工业品需求的不足,通过引进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移民来补充本土创新的缺乏和技能型劳动供给的短缺等等。①[美]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页。
这样,即使在不具备先发国家所具有的发展条件的前提下,后发国家也可以通过这种建构出的替代性条件节约时间,实现跳跃性发展。相反,如果落后国家的政府不能结合本国社会经济环境,适时地进行这种替代性条件的建构,就有可能失去其后发优势。格申克龙同时还判断,国家的这种积极作用对后工业化国家的前期发展至关重要,但对于先发国家或者工业化完成之后的后发国家,这种建设性的国家干预就不那么重要了,国家作用呈现出一种倒U型的曲线。
发展型国家完整地继承了李斯特的国家主导传统,并进一步细化了政府的作用机制、方向和运作原则。查默斯·约翰逊 (Chalmers Johnson)强调指出,“发展型国家的理论之根在李斯特及其所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李斯特坚持认为德国需要实行一种国家主导型的发展从而实现对大英帝国的赶超这一观点,正是亚洲发展型国家重要的理论来源。”②Chalmers Johnson,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1925~1975,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17.发展型国家理论的提出者们,从约翰逊到韦德,无不强调国家主导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工业化成功的关键所在。按照约翰逊的理解,东亚发展型国家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英美体系那种市场—理性的国家介入的市场经济,也即计划—理性市场经济模式。韦德和怀特等人则认为,在整个东亚成功的工业化国家中,国家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者、组织者和主要行动者,国家不仅通过产业规划、产业政策和关税政策等一系列制度手段有效地引导和组织了国民经济活动,同时也有效地保持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使市场保持了竞争性。
在对之前李斯特谱系理论系统梳理和整合的基础上,结合新熊彼特学派的创新理论,以埃里克S.赖纳特、阿诺·曼·达斯特和张夏淮等人为代表的演化发展经济学家提出,国家成功发展的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产业活动,选择怎样的产业活动是决定一国经济质量、国民实际收入、国际分工地位乃至政治结构的先决条件。而在所有的产业活动中,报酬递增行业是国家致富的基石。以报酬递增行业为带动,通过产业协同效应所形成的正反馈,可实现更多行业的生产率提高,贫穷国家应选择创新机会窗口大的产业,通过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推动自主创新,通过产业升级和生产效率的激增,最终提高国家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必须有意识地扶持且保护报酬递增的生产活动,对具有潜力的生产活动减税、提供低成本信贷、提供出口补贴,重视知识和教育,对有价值的知识进行专利保护等。穷国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如关税保护、资金支持 (政府的信贷优惠)、技术支持 (政府向国外派出工业间谍以获取技术情报)以及政策支持 (税收减免、出口补贴、专利保护、对教育与科研的投入)等来帮助自己提升价值链位置。要“在国界内创造完全竞争,并在出口贸易中创造动态不完全竞争”。③Erik S.Reinert.Increasing Poverty in a Globalised World:Marshall Plans and Morgenthau Plans as Mechanisms of Polarisation of World In⁃comes[J/OL].http://www.othercanon.org/papers/index.html.2007.
三、逐步被重视的社会
(一)国家型构与反封建:从柯尔贝尔到格申克龙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当李斯特谱系认为国家可以具备足够的“调动国内资源的自主性和能力”的同时,也意味着,国内资源的客观存在和可调动性是其理论的隐含前提。问题在于,国家可调动的资源和国家行动的对象是什么?他们是否可以被国家激励、调动和组织,国家通过什么机制调动他们?他们的被调动、被组织和被激励,又是否与国家作用之间构成循环作用关系?不难理解,这种可被调动的资源,从根本上而言只能是构成民族国家的人民,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行为主体,但更为重要也更为根本的是,他们也是国家行动所赖以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
重商主义者基本上对这一社会基础及其可能产生的反制作用没有给予讨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重商主义推行相伴随的民族国家兴起过程,本身就是欧洲社会重塑的过程,是权威形成和共同体意识形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要的斗争不是统治阶级和下层阶级的斗争,而是国家和统治阶级的斗争”。④[澳]琳达·维斯,约翰·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黄兆辉等译,长春:吉林出版社,2009年,第59页。更具体地说,是王权和民众对抗贵族的斗争。“反对封建贵族的国王与中等阶级的联盟创造了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民族国家。”①Reinert,Erik The Other Canon:“The History of Renaissance Economics”,in Reinert,Erik S.(Edited)Globalizatio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A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Edward Elgar,2004,pp.21~27。因此,本质上,重商主义政策,也是商人利益集团和王权基于共同利益的一种合谋,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在这一阶段并不清晰。在重商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同步形成过程中,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实力的增强,君主对商业财富的需求加深了王权与商人的合作,城市商人的商业观点成为王权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来源。这样,重商主义通过商人和王权的协商,将行会习俗、城市传统和商人的利润欲转化在重商主义倾向的国家政策上,而在这一过程的实施中,商人资本家在实现了对城市和商业、制造业的控制的同时,也完成了城市市民向国家公民身份的转变。重商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或出身商人家庭,或以商人自居,但同时也是官员乃至重臣的角色,如托马斯·孟、柯尔培尔、米尔斯、马林斯、米塞尔登等,这一独特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重商主义和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合作关系。②关于这一时期商人和王权贵族的关系,参见刘 程《西欧重商主义保护原则的历史探源》,《山东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刘文同时也考证了重商主义保护主义原则的起源,认为保护主义实际上是源于行会、城市等小共同体的利益保护原则,而后在经济力量的推动下逐步演化成为大共同体亦即国家的经济政策,这也同时说明了这一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演化。
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实质上是一种主体对主体利益实现的一种主张,意愿主体和行动主体本身是合二为一的,这就必然会忽视掉商人和君权之外的社会基础。③在这一点上,维斯提出了与马克思不同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国家是以贵族的名义或应贵族的要求行动的,但维斯认为,国家的形成显然经过了与贵族的竞争、合作与冲突。参见 [澳大利亚]琳达·维斯,约翰·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黄兆辉等译,长春:吉林出版社,2009年,第22页。这种建立在合二为一主体基础上的重商主义,不仅在理论体系中弱化了社会基础的重要性,而且在实践过程中,也表现出民族国家进一步的渗透能力的缺乏和行动效率的不足。在对马格努松、施穆勒和李斯特等人关于重商主义政策绩效的讨论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严鹏对重商主义研究的文献梳理表明,尽管欧洲国家在重商主义时代已经广泛采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等极具现代性的手段来管理经济,但往往效果不佳。其原因就在于近代早期的欧洲国家在相当长时间内,仍然保持着传统的政治组织形式,缺乏高效的行动能力,君主专制国家的权力也存在着“去中央集权化”与“碎片化”的现象。④更详细的文献考证,可参见严 鹏《国家作用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一个新李斯特主义的解读》,《当代经济研究,2015年第12期。
相较于重商主义者,李斯特开始关注社会基础对工业化进程的影响,但李斯特对社会基础的讨论中,更多地强调的是社会的政治结构尤其是封建残余结构对工业化的阻碍。因为“不论拿哪一个国家来说,为了它自身的特有利益,它的政治势力对于这种所谓自然趋势,总是要加以干预,使之趋向人为方向的”。⑤[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杨春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19页。身处落后的、尚未实现统一的、存在封建残余阻碍的德国,李斯特认为,德国封建贵族势力仍是当时德国最强大的政治势力,要以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替代德国的封建农业经济,就必须对旧的封建残余制度进行破除,建立一个自由的、能最大程度激发个人与社会生产力的经济社制度,因为“一切个人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国家的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的”。⑥[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杨春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年,第84页。在李斯特的理论体系中,对封建社会基础的改造是激发经济自由和经济活力的前提,激发了经济自由和经济活力,才能使他所倡导的关税保护和幼稚产业扶持等政策取得提高国民生产力的效果。这就使李斯特的观点表现出一种形式上的矛盾:既强调内部的政治与经济自由、市场整合和关税统一,又强调积极的政府干预,这种形式上的矛盾,正是基于他对德国当时社会基础中的最大阻碍因素,即封建残余的认识。
和李斯特一样,格申克龙也意识到封建性残余制度对后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作用。“只要某些可怕的制度障碍诸如农奴制度或者政治统一的普遍缺乏依然存在,就没有任何工业化的可能。”⑦[美]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2页。但是格申克龙对社会基础的分析,强调的是社会态度和社会价值,尤其是这种社会态度和社会价值观对企业家和创新的影响。“社会的作用以及促使预期的行为被实施的认可行动中再一次占据中心地位。”⑧[美]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9页。企业家的社会认可,是激发企业家活力和企业家数量的关键因素,“理论公式有令人信服的简单性,那就是对企业家活动的社会赞许极大地影响着它的规模和种类”。⑨[美]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69页。与此同时,社会价值和社会态度对后工业化改造的适合,还有助于两种形态的经济变迁。经过良好整合的社会,其中经济创新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创新过程中所产生的创造性毁灭对经济变迁的受害者产生的个人价值观,或者可以被忽略,或者通过社会将他们整合到这样的一种程度,使得甚至是这一变动过程的制度受害者也能够被彻底地纳入社会的价值标准。不过,格申克龙不仅用社会态度和社会价值替代了社会基础,也还进一步讨论这种社会变迁对国家能动性的反作用,在格申克龙看来,甚至这种对创新和企业家的社会认可,也应由国家加以主导,在讨论法国的社会不赞成对企业家活力的制约时,他写道:“也许是因为一个社会认可体系往往是过于软弱的,除非由国家的认可来施加,否则将难以实施。”①[美]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2页。
(二)政治—经济连接及其相互作用:发展型国家与演化发展经济学
发展型国家理论在社会基础上的侧重点,主要是企业组织,其突出特征就是一再强调政府与经济组织的连接。正如宋磊所强调的那样,发展型国家理论主要研究的就是“赶超过程中企业和政府的结构性特征”。②宋磊认为,关于后发国家赶超过程的结构性特征,存在两类研究。第一类研究关注赶超过程各个阶段的顺序或宏观趋势,第二类研究关注赶超过程中经济主体的特征。依据研究重点的不同,第二类研究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主要研究赶超过程中企业和政府的结构性特征的两种研究。前者的代表是经济史、经济社会学和企业史领域的一组比较研究,后者的典型则是发展型国家论。详见:宋 磊《格申克龙——道尔命题与中国实践》,《开放时代》2015年第4期。尽管不同的发展型国家理论的提出者所强调的连接对象存在差异,如韩国侧重扶持财阀、台湾地区则倚重中小企业等,但都是在强调政府与企业组织的经济连接。禹贞恩甚至直接将发展型国家定义为“政治的、官僚的和财阀势力组成的无缝网络”。③[美]禹贞恩:《发展型国家》,曹海军译,长春,吉林出版社,2008年,第1页。约翰逊所描述的国家关键因素,就着力于强调国家与企业组织的连接,如官僚与商业精英的紧密联系,信息交换与合作等;这种政治经济连接的边界是,要“把政策网络与日常个别利益集团的压力和不利于增长的要求隔离”。④[澳]琳达.维斯,约翰.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黄兆辉等译,长春:吉林出版社,2009年,第167页。在韦德的驾驭市场理论中,驾驭对象也是企业组织,通过企业实现“增值能力的制造业和增加出口业的市场占有率,并最终能够提升生活水平”⑤[澳]琳达.维斯,约翰.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黄兆辉等译,长春:吉林出版社,2009年,第168页。的目标。伊文思则提出了嵌入性自主概念,但其嵌入性仍然是针对企业和产业而言的,仍然是强调公私合作。他认为,国家在产业嵌入中可以扮演四种角色,即监护者、创造者、助产者和管理者,⑥Evans,Peter B.Embedded Aut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这些角色的差别在于国家如何运用一些政策工具来形塑国家与产业的关系。在伊文思看来,只有当国家在扮演助产者和管理者角色时,才会将嵌入性力量发挥到最大。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伊文思开始关注发展型国家的目标修正,以及国家、社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调整。他认为,发展型国家理论应当从传统的经济发展目标转向更广义的社会发展目标,实现一种阿玛蒂亚·森意义上的“人的自由”的发展,在将人的发展列为发展的更高目标的同时,也使人的发展成为提高国民生产力的手段。
同样是从东亚成功的发展型国家和失败的拉美、非洲一些国家的对比研究中,演化发展经济学家,如赖纳特等人意识到,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经济与社会结构演化的逻辑是:产业活动选择——收益分配—中产阶级形成—反制性力量与民主进程。在赖纳特看来,产业活动的性质决定了利润、工资和税收在雇员、雇主和政府之间的分配方式,也决定了国民如何获取及获得多少收入,从而直接影响了社会阶层的形成,这进而会体现在政治结构上,而政治结构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结构。因此,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会推动民主进程的发展,推动政治结构的变迁;另一方面,一国政治权力的构成对其经济发展,尤其是长期发展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赖纳特指出,“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之间这种至关重要的联系——也就是民主制度和一种不依赖于农业和原材料的经济多样化之间的联系——是另一堂重要的历史之课”。⑦Erik S.Reinert:How Rich Countries Got Rich and Why Poor Countries Stay Poor,Constable,2008,p.311.因此,在缺乏健康的经济活动前提下,盲目地推进民主进程,无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赖纳特多次以非洲为例,强调指出,在经济结构基本上还处于封建时期或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非洲,强行植入西方式的民主,只会导致无休止的政府更替与内战。从政治结构对经济的反作用看,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具体掌握在哪些人手中,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赖纳特多次以亨利七世时期英国的工商业与地主贵族的矛盾、美国内战时的南北矛盾、拉美殖民时期的庄园经济为例证,强调这一观点,并警示贫穷国家通过开明政府回避错误。赖纳特所描述的那些面临崩溃危机的国家,政治权力往往被那些从事无益于经济长期发展的报酬递减的经济活动的资本家所绑架,例如原材料行业,从而限制了国家走向正确的发展道路。
四、建制性权力的三重维度:为何李斯特谱系中的社会在不断变化?
按照维斯的总结,所有发展成功的国家都是强国家,而强国家的力量,并不是一种前工业社会的专制性力量,而是一种建制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包含了三个维度,第一是渗透,即进入社群并能与人民互动的能力,这是一种将期望转化成为行动的能力。第二则是汲取能力,即从社会汲取资源的能力,它建立在渗透性能力之上。如果一个国家的汲取能力是稳定的持久的,就说明它具有一种与社会权力组织协商的元素,这一元素就是维斯所说的最重要的第三个维度——建制性权力的协商维度。
从这种角度看,一直到18世纪,盛行重商主义的欧洲国家,基本都处在从前工业化时期的专制能力向资本主义发展所需的建制性能力的发展与转型过程中,都在获取上述三种能力的过程中。由于这一时期的国家和社会同处在一个协同演化过程中,当我们在评价重商主义者只关注“国家”时,毋宁说我们指出了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也关注了与国家同处在一个演化进程中的“社会”。只不过,这个社会,在重商主义者那里被关键行动者,如商人、贵族和王权所替代。因为“资本积累的历史就是国家建制性权力的历史,事实上,国家建制性的力量造就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同样造就了国家力量,这便构成了国家力量的根本特点,国家能够以相互合作的关系,而不是以损耗主要社会参与者的力量,来获得更大的力量”。①[澳大利亚]琳达·维斯,约翰·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黄兆辉等译,长春:吉林出版社,2009年,第65页。
与重商主义者相比,李斯特的德国和格申克龙的俄国在共同体意识上已经明显增强,因英法等先发国家的存在,格申克龙所说的“落后与发展的高期望值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德俄都十分明显,但德俄两国既非最先演化出的“通过关键社会行动者行使国家权力”②[澳大利亚]琳达·维斯,约翰·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黄兆辉等译,长春:吉林出版社,2009年,第53页。的英国,亦非在新大陆上形成的无历史记忆的美国。③在卡岑斯坦看来,美国社会诞生于现代,他并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摧毁传统社会,其社会既没有封建结构也没有贵族来阻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参见 [美国]卡岑斯坦《权力与财富之间》,陈 刚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第76页。从国家能力的意义上看,他们仍只具备维斯所说的“前工业社会的专制性力量”,而不具备国家的建制性力量。同时,两国的统一程度也十分缺乏,这必然会影响到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因为“资本主义就如同现代国家一样,需要统一的国土基础,一个分裂的国土基础,意味着所有生产要素,均处在不能流动和不自由的状态,而一个统一的国土基础就会结束所有生产要素的束缚,这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④[澳大利亚]琳达·维斯,约翰·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黄兆辉等译,长春:吉林出版社,2009年,第64页。对于德俄两国而言,影响这种建制性力量形成的主要因素,就是残余封建贵族,在没有打破这种结构之前,国家不可能形成向社会渗透、汲取和协调的力量,即,国家既不可能获得将期望转为行动的能力,也无法获得稳定的汲取能力,同时也缺乏与经济组织的有效连接和协商,动员和组织社会基础和社会资源,也就缺乏有效的传递机制。因此,当务之急是在打破封建残余阻碍之后,建立起与社会基础互动的机制。在李斯特和格申克龙看来,只要打破封建制度,社会基础就会获得自由而释放出创新活力。与此同时,这也就是李斯特和格申克龙都专注于封建残余,而不是社会大众的原因。
与重商主义者和李斯特、格申克龙相比,发展型国家对社会关键行动者的关注已经从商人、封建领主转变为企业组织,演化发展经济学则已经开始关注到中产阶级的形成以及他们对政治制度的反制性影响,这无疑已经使李斯特谱系的社会研究得到了扩展。但发展型国家并没有将社会基础推及到社会大众层面,也没有超越经济连接和有效嵌入这样的概念,而演化发展经济学家在通过中产阶级切入产业结构——政治结构的互动分析的同时,也忽视了社会基础的初始状态。从维斯等人的角度看,发展型国家的成功,的确在于他们获得了第三维度的建制性能力,即协调能力,但无论是发展型国家还是演化发展经济学,都忽视掉了建制性能力中的汲取与渗透能力的获取过程,以及这两种能力对于建制性协调能力的影响。
协调之前的渗透和汲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后发国家在面临工业化进程时,首先要完成“意愿到行动”的过渡。而对于东亚发展型国家,以及拉美和南亚等众多二战之后获得独立地位的民族国家而言,前殖民时代以及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使他们被动地获得了一种“形式上的建制性”,但实质性的建制性力量却未能形成。二战之后,东亚国家已经不同程度上地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社会结构,并具有了一定的经济组织,如地主庄园经济体等。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成功,不仅在于获得了建制性的第三维度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获取这种能力之前,通过革命、运动和改革,实现了渗透性,进而通过权力和权利的对冲机制,实现了威权引导下的工业化。房宁等学者认为,从社会的角度考察,诸如韩日这类成功的发展型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初期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经历了社会结构的较大变动,在破除原有社会的“等级高度差异”的同时,使社会出现了一种流动性较强的“扁平化”趋势。这就使其可以“采取一种导向性和约束性的特殊的政治体制及发展策略,将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流动导向了经济社会领域,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广泛而强劲的动力,同时约束了政治参与,限制了政治纷争”。①房 宁等:《民主与发展——亚洲工业化时代的民主政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5年,第13页在笔者看来,这一社会基础改造的实质,就是通过社会结构的“扁平化”使国家获得了“从意愿到行动”的渗透力。
后发国家之所以表现出与英国为代表的先发国家模式的差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建制性权力中的渗透力的获取方式不同。先发国家可以通过重商主义时期的国家建制性权力演化过程中的社会结构演化,但是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格申克龙所说的替代性条件尚有一个被忽略的前提,那就是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相适应的社会结构。这个替代性的条件,在英美这样的国家,是自然演化出来的,但是在其他后发国家就必须要通过革命、战争和改革等方式,进行一次破除式的重构,从而获得更广泛的经济主体流动性。亚洲的经验表明,亚洲的“快国家”和“慢国家”的差别,与这种渗透性力量形成的差异密切相关。菲律宾、印度等国家之所以成为慢国家,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工业化起步阶段传统的社会结构没有像东亚地区那样,被革命、内乱和改革所打破”。②房 宁等:《民主与发展——亚洲工业化时代的民主政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5年,第353页。这就使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缺乏整体性,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不仅没有“集体激活”,反而加剧了分裂,“工业化实际上把国家和社会分裂成了工业化的部分和传统的部分”。③房 宁等:《民主与发展——亚洲工业化时代的民主政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5年,第353页与之相反,东亚国家在工业化之前大多经历了一次社会基础重构,如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四民平等、韩国的新村运动等,通过这种重构充分地激发了国民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种社会基础重构,不仅渗透力得以形成,也使政府的协调力得到了提升,并且为之后三重维度的建制性权力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考察亚洲的“快国家”和“慢国家”的过程中,房宁等学者还提出了权力和权利的对冲假说。认为开放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的先后顺序,也导致了“快国家”和“慢国家”的差别。例如,菲律宾和印度等国独立后直接效仿英美体系建立宪政制度,同时开放了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但由于缺乏社会基础重构,这种“双开放”反而导致了“慢国家”的形成。而东亚威权国家则首先开放经济权利,其后再开放政治权力,由于之前进行了社会基础重构,这种权力和权利的对冲反而使其成为“快国家”,并顺利地实现了威权转型。
在笔者看来,这种权力和权利的对冲,本质上所体现的,仍然是建制性权力的差异。第一,是否进行过社会基础重构,会影响到国家建制性的渗透权力,即从“意愿到行动”的能力。诸如印度这样的“慢国家”,其传统社会结构由于限制了公民的平等权利,妨碍了国民进入工业化经济进程的机会,必然会抑制社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由于传统社会结构的存在也容易形成垄断性的分利集团,进而妨碍工业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传统经济权利获取政治权力,继而转型为现代垄断经济权力的恶性循环,比如菲律宾工业化过程中的传统地主家族。第二,是否进行过社会基础重构,将对国家建制性的协调能力是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产生影响,“快国家”建制性的协调能力主要体现为与国家与企业和产业的协调,也即发展型国家所称的经济连接,这体现出的是一种制度的生产力,而“慢国家”建制性的协调能力则必然会大量表现为与传统社会阶层的民主协调、博弈和稳定社会的努力,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非生产性的协调能力。第三,是否进行过社会基础重构,决定了经济—政治连接是走向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无论是“慢”亚洲还是“快”亚洲,一旦启动工业化进程,既定的社会基础就会开始受激,开始对权力—权利机制产生影响。在未经重构的社会基础上,原有的少量残存社会基础最容易影响经济权利的决策机制,也最易从启动的经济进程中受益,从而扩大和强化自己的经济权利,进而对政治权力产生更大的影响,从而使政治—经济进入一种有利于少数人的路径锁定。与之相反,进行过社会基础重构的国家,则由于在工业化伊始就打破了旧的社会结构,改变了经济发展导向下的分配结构,摆脱了那种有利于少数人的路径锁定,从而实现了有利于大多数的路径创造,进入一种政治—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
五、结 语
李斯特谱系对国家的一贯重视和对社会基础研究对象的不断变化,既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发展的不同路径,也反映出国家—社会复杂的协同演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虽然这一谱系始终在强调国家作用,但国家作用的对象、方式和领域一直在随着社会中的“关键行动者”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在“关键行动者”从少量贵族扩展到企业组织和普罗大众的过程中,国家的能力和内涵都在随着时间做出重大的改变。这一过程,既体现了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嬗变,也说明社会的反作用对现代市场经济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健康发展的影响力日渐增强。
(责任编辑 张 健)
List's Genealogy:The Repeatedly-Emphasized State and Gradually-Valued Society
YANG Hutao
Unlike Adam Smith's cosmopolitan economics,a clear theoretical genealogy of mer⁃cantilism exist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s-Friedrich List's national economics,Gerschenkron's post-industrialized state, developmental state and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economics.This genealogy emphasizes national interests,protectionism,competitive advantages,and particularly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modernization and economic surpass.In comparison with its long-stressed“notion of state”,List's genealogy gradually attaches more importance to social foundation.The objects of concern in social foundation,namely the key actors,extend gradually from the urban bourgeoisie and feudal ar⁃istocracy to the business organizations and general public.Its cogniza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 gradually evolves from one-dimensional role of the state to the view of the state-socie⁃ty interaction.This change in List's genealogy reflects the progressive and cooperative evolution of the state,society and market economy.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tate and society,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e's despotic power to its infrastructural power,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penetrability,suction force and coordination capacity in its infrastructural power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different states.
List's genealogy,state,society,infrastructural power,developmental state
F09
A
1001-778X(2016)06-01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