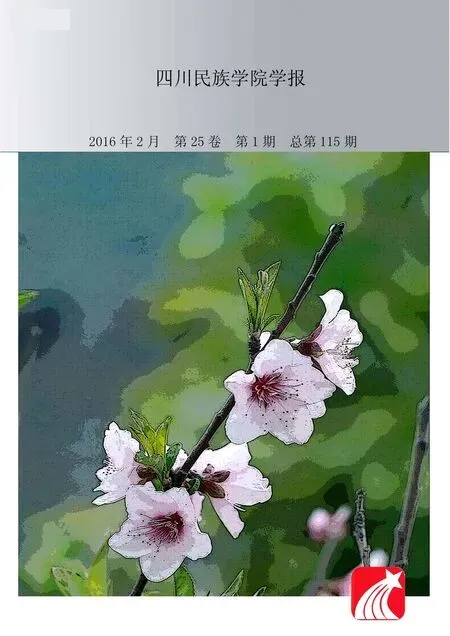乾隆前期郭罗克问题研究
李红阳
★康藏研究★
乾隆前期郭罗克问题研究
李红阳
【摘要】郭罗克是聚居在今青海省西南部的藏族地区,在清代这里经常发生劫掠往来官商的事件,清廷多次对于类似劫掠事件展开调查或者问责。通过对乾隆初年解决郭罗克问题的三种方案、清廷用兵郭罗克和郭罗克劫掠班禅喇嘛物件一案的分析和探究,并结合乾隆帝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立场,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入的理解乾隆前期在处理郭罗克问题上灵活措施。以“慎重”为基本指导原则的处理办法固然避免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但又使得这一地区的清代长期得不到稳定和安宁。
【关键词 】乾隆前期;郭罗克问题;慎重
A Research on Guoluoke Problem in the Early Qianlong Regime
Li Hongyang
【Abstract】Guoluoke is a Tibetan area around the southwest Qinghai province today. Around the area, the looting affairs often happened in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So the Qing government has adopted three methods to solve the Guoluoke problem in the early Qianlong regime. This article makes some analysis of the solutions, some cases related to Guoluoke problem, and basic principles on this issue, etc., in order to help us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lexible measures to deal with Guoluoke, among which, "Carefulness" is the basic principle, which has the dual-possibilities: avoiding the war, but lacking of long-term stability in that area.
【Key words】the early Qianglong regime; Guoluoke problem; carefulness
公元1644年,中国历史进入清王朝统治的时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版图最终奠定。清代康熙年间“郭罗克”的名字正式见诸于汉文史籍,1721年(即康熙58年)清川陕总督年羹尧得到康熙帝指示向肆行抢掠的郭罗克用兵,1723年(即康熙60年)郭罗克三部(即传统的上、中、下三郭罗克)向清廷输诚,清廷对其原有的统治者并未赶尽杀绝,而是在郭罗克地区实行土官制度。[1]1728年(即雍正6年)阿尔布巴事件发生之后,清廷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权,重要一点便是将西康东部的巴塘、理塘等地划归四川管辖,[2]郭罗克地区在此时也划归四川管辖,此时的郭罗克位于四川西北部,北界为黄河。但是在清代,郭罗克地区藏族的势力已经突破了四川,远及青海草原,他们在这一代地区放牧、生息繁衍,同时也通过劫掠往来商旅而获得生活资料。有清一代,郭罗克的劫掠问题时常被提到四川和青海地方官员以及清皇室的日程,而乾隆前期(1738年-1753年)显得格外突出,虽然清廷采取了许多措施加以管控,但最终仍没有彻底解决郭罗克问题。
一、乾隆前期对处理郭罗克问题的三种方案
乾隆初年,经过康雍两朝的积淀和正确举措,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一步得以巩固和稳定,边疆地区总体保持着和平和安宁。但是处于四川省西北部、松潘口外的郭罗克地区屡次出现劫掠往来官商的事件,典型的有1738年劫杀川南番民交纳的供马银两[3]和1740年劫掠西宁地方的蒙古账房及马匹[3]等。类似事件引起了地方官员和清廷上层的关注,分别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案,总的来看有三种:
一是以番制治番民、以汉制治番汉纠纷。这一策略是乾隆4年(即1738年)12月川陕总督查郎阿在处理郭罗克劫掠事件时提出的。查阿郎是一个拥有丰富边疆工作经验的官员,他认为此类劫掠事件如果按照汉例(即清律令)解决,可能导致反复无常的番人互相报复,进而加剧这一地区的不稳定性。因此有了“郭罗克番人与汉人争斗、抢掠等事,仍照例科断;其番人与番人有命盗等案,具照番例完结”的处理原则。这种以番制处理郭罗克地区之纠纷、以汉制解决番汉纠纷的原则充分考虑了当地藏民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心态,是历代统治者“因地制宜”进行各地区治理的又一次生动的体现。
二是异地安插,令其民务农。这一建议是在1743年(即乾隆8年)5月清大学士等经过对郭罗克问题的分析后得出的一个可行性方案。他们认为,郭罗克地方长远一沟,其居民长于上马执鸟枪,因其地贫瘠而进行抢劫度日。因此他们提出要给予其谋生之路,即将其民安插于临近的柏木桥地方进行务农,这样就可能彻底解决郭罗克问题。所谓的“柏木桥”地方,我们从现有资料中没有关于它的任何记载。但既然与郭罗克地方临近,推断其位于郭罗克东部的、有黄河支流流经的平缓地方。这种异地安插、令其民务农的方案很适合增强郭罗克地区藏民的生产能力、使其不再行劫掠。但是这一策略在之后并没有实行,至于具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三是宣谕政府政策或用兵郭罗克。相对于前两种方案而言,对郭罗克地区施加政治压力或者用兵是一种更常见、更直接的应对方案。典型的有1738年(即乾隆3年)9月四川提督王进昌针对郭罗克聚众行劫提议让其副将马化正宣谕郭罗克番首并勘察郭罗克的地形、1741年(即乾隆5年)2月四川巡抚硕色从稳定边陲的角度认为之前对郭罗克的弹压效果不明显,应该以官兵对其进行镇压。[3]其实,从中央政府稳定边陲的角度出发,宣谕政府权威及用兵的方案应该是最直接、效果最好的方案,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用兵似乎应该照顾到当地的风情民情,不然就会南辕北辙。从历史上看,用兵的方案不可能彻底解决一个地区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激进的方案只会伤害中央政府与郭罗克地区的感情。
综上,乾隆初期地方官员和清廷决策者对于郭罗克劫掠问题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从法制适用性的角度出发的;第二种方案是从改变其生活方式和生产能力的角度出发的;第三种方案是从政府控制权和使用暴力管控的角度出发的。事实上,三种方案都有其内在合理性,关键是看哪种方案适合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更能够得到清廷地方官员与中央的一致认可。
二、乾隆前期郑文焕对郭罗克的用兵及善后(1740-1744)
1740年(即乾隆五年)10月四川提督郑文焕向朝廷上奏表示,郭罗克地区藏族民众长期以劫掠为生,担心其劫掠将入藏熬茶的准噶尔人,为防备他令松潘总兵劝诫郭罗克头目,并将继续做好防备工作。乾隆帝他的留心办理表示嘉奖。这是郑文焕对于处理郭罗克问题的首次表态,即对其劫掠行径严密防备,而不是直接以兵加之。但是由于在之后两年郭罗克并没有放弃劫掠而是不断引起当地官员的反感,于是1743年(即乾隆8年)3月乾隆谕旨四川提督郑文焕赴松潘口办理郭罗克肆掠问题。[3]乾隆初年对郭罗克地区的用兵由此拉开序幕。
1743年(即乾隆8年)6月四川提督郑文焕带领官兵800名、士兵1000名以及驼马、炮兵等进军郭罗克地方,事先他已告知青海夷情副都统等严加防范郭罗克劫掠。6月抵达出皂(应为松潘口外一个地名)驻营,已被宣谕并齐集于黄胜关外的郭罗克土司头目、副头目等闻风丧胆,请求宽恕,并将劫掠物资及有关贼人交给朝廷处理,并承诺不再危害往来官商的利益。四川提督郑文焕等向各土司头目宣谕了朝廷的宽大,随即派汉、土官兵1500人赴郭罗克境内查缴相关贼人和赃物。郑文焕等在郭罗克地方追赃问责三个月后,因为准噶尔使臣即将进藏经过郭罗克地方,因此暂时停止剿除,等待准噶尔使团通过后再做定夺。在准噶尔使团通过此地期间,严密巡逻,禁止郭罗克牧民出外活动。
1743年(即乾隆9年)6月四川提督郑文焕带兵处理郭罗克问题之后,通过与有关官员商量并经朝廷批准,对郭罗克问题的善后做了如下安排:一是拣留400名汉、土官兵驻扎此地经理日常事务;二是颁布相关禁约,严嗤土官约束其民的行为。1744年(即乾隆10年)10月,郑文焕认为郭罗克各土司已洗心革面并恪守相关禁约,故经过朝廷批准后撤掉了之前在这里驻留的军事力量。至此,这次次对郭罗克地区的用兵结束,按照郑文焕的判断,收到了预期效果,当然从之后的历史来看,郭罗克劫掠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实际上,乾隆年间首次对郭罗克的武力干预并没有发生大的抵抗或者武装冲突,只是官兵在当地土司头目的许可下在其境内进行了为其三个月的追赃、追逃行动。从维持的时限来讲,此次在郭罗克地区的驻兵不足一年,也使得官兵一撤离,该地区便很快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郑文焕等清廷地方官员给郭罗克地方留下了一个善后法案,这个方案在官兵撤离后没有任何力量保持它的权威性和适用性。因此我们认为,这次用兵所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三、乾隆前期郭罗克劫掠班禅喇嘛物件一案(1751-1753)
1751年(即乾隆16年)间,班禅额尔德尼使人由京返回西藏,行至郭罗克境内时被劫掠,并造成伤亡。[3]青海夷情副都统舒明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和处理,他向郭罗克等地土司宣谕了有关事件的严重性,郭罗克土目丹增害怕并交出了部分所劫物品。1752年(即乾隆17年)到1753年(即乾隆18年)间,四川总督策楞接手调查此事,他从两方面对此事进行处理:一是要求郭罗克将劫掠所得全部归还,但是赃物并未全部得到归还;二是严厉要求郭罗克土目丹增限期将劫掠喇嘛物件的贼人捉拿归案,该土目将一名贼人交给策楞并称将很快将另一贼人捉拿归案,但是经策楞审判后发现,丹增所献出的贼人只是从犯,主谋仍然逍遥法外。[3]据此,策楞认为郭罗克之事非用兵所能解决,此时任四川提督的岳钟琪也自告奋勇为统帅,并于1753年(即乾隆18年)3月亲率汉、土官兵征讨郭罗克。由郭罗克劫掠班禅喇嘛物件一案至此完全升级,一场征讨战争似乎笼罩在郭罗克地区的土地上。
中国古代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发展到清代,已经完全确立并趋于僵化。在这样的一种政治生态下,皇帝的权利至高无上,类似于征伐他族、使用暴力等事件必须得到清廷尤其是皇帝的首肯。郭罗克劫掠班禅喇嘛物件一案也是如此,无论地方督抚的态度如何,他们只有与皇帝的态度一致才可能使他们的政治建议变为事实上的战略决策。在四川地方督抚与乾隆皇帝对待郭罗克劫掠班禅喇嘛物件一案的态度上,双方恰好出现了惊奇的不同。如前文所述,四川总督与四川提督都认为应该派兵彻底解决郭罗克劫掠问题并借此疏通西藏交通,而乾隆皇帝从以下两方面否定了他们的提议:一是任何地方的劫掠事件都不可能将全部被劫物件追回,将班禅喇嘛使人被劫物件逐一向郭罗克追要的做法不是办理此类事件的正确方法;二是地方督抚应该慎重对待国家兵马饷粮之事、要给人民以足够休养生息的机会。据此乾隆皇帝严厉训斥了四川督抚的出兵建议,“尔等错会朕意”、“严厉申饬”等用语体现了乾隆帝坚定反对此时用兵郭罗克的提议。[3]就这样,郭罗克劫掠班禅喇嘛物件一案在乾隆帝的指示精神下得以迅速解决,这种解决方式便是将已抓贼人处理和不再追缴未追回物件。实质上,对于郭罗克劫掠班禅喇嘛物件一案的处理,明显表现出乾隆帝的姑息纵容,致使此事件的处理最后只能是不了了之。
其实,刚愎自用的乾隆帝对待帝国内出现的劫掠问题表现出这样的态度是很少见的,或者说是不正常的。我们发现在郭罗克劫掠班禅喇嘛物件一案发生前后的乾隆朝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1747年(即乾隆12年)到1749年(即乾隆14年)乾隆帝挑起了清史中重要的第一次大小金川战争并以实际上的失败告终,乾隆帝对持续两年、花费庞大军费换来的战争结果并不满意,故他有意积蓄力量再次攻打大小金川;二是1752年(即乾隆17年)四川总督策楞和四川提督岳钟琪于该年8月发起了杂谷之役,这次战争持续一个月后清廷取得了镇压川边杂谷土司的胜利,这次战争一方面花费巨大,另一方面实质上为再次进行大小金川战争提供了条件。[4]第一次大小金川战争实际上强烈的打击了一代帝王的信心,一方面他需要通过新的战争来证明自己的决策和战略判断以挽回自己的颜面,另一方面也使得他不再轻易发起战争。而四川总督策楞和四川提督岳钟琪于1747年已进行了一场胜利的杂谷之役,不过一年后的1748年他们又想通过对郭罗克的战争证明自己的能力,显然有邀功请赏之嫌,这可能是乾隆帝否决其战争提议的因素之一。
从郭罗克劫掠班禅喇嘛物件一案的性质来讲,充其量不过就是小打小闹,当地方官员过问时郭罗克土目丹增认罪态度很好并配合了追缴被劫物件的行动。相对而言,大小金川土司之间为边界纠葛大打出手和杂谷土司苍旺横行乡里并拒不接受清地方官员的调解的事件显得就更加严重,四川地方官员很容易就加之以“逆谋”罪名[5],这样很可能引起清廷的不满并产生使用暴力加以管制的念想。从这个角度讲,以乾隆帝为代表的清廷心腹之患是大小金川地区,而郭罗克劫掠问题就显得微不足道而不足以让清廷动用军事力量加以控制。因此清廷对郭罗克劫掠班禅喇嘛物件一案的从宽处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符合当时清廷在治理国家中整体利益的。
四、小结
乾隆帝的执政是在继承其父雍正帝的政治遗产中展开的,雍正帝的执政风格是严刑峻法、厉行革新、倡导移风易俗,这些政策一方面使得清代政治展现出一种清明景象,另一方面又使得官员人人自危、战战兢兢。乾隆即位后对雍正帝的政治策略进行了较大调整,重要的便是被史家称为“翻案”的新政,即停止一些效果不明显的前朝新政和释放一批非政治要犯为其所用。乾隆初期在执政上坚持“宽严相济”、“刚柔相济”的思想,强调中庸协调。[6]对于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古代帝王而言,乾隆帝的施政思想和具体施政纲领是符合当时发展要求的,这在他执政前期表现的分外明显,而乾隆前期乾隆帝对于郭罗克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以柔道治理该地区的施政理念。
乾隆前期对于郭罗克问题上的态度具体体现在给地方官员的批奏上,即对郭罗克问题的具体政治思考。其集中体现为三点:一是乾隆强调四川地方官员在处理郭罗克问题时要互相协调,不要独自行事和为邀功行赏而做出错误的决断,川省官员在奏报有关郭罗克劫掠问题及其处理方案时,乾隆帝朱批往往是“于督抚和衷共理”、“与都提二臣熟商而行”等类似的话,这实际上表明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希翼地方官员和谐共理地方政务的心态;二是乾隆帝对于郑文焕在郭罗克地区用兵及善后的意见,强调对于郭罗克问题要谨慎行事,即不可姑息也不能操之过急,要求郑文焕“慎重妥算为是、永葆无事为要”、“慎重为之”,时刻留心这一地区的情形而不至于其局势激化;三是乾隆帝在面对四川提督岳钟琪提出限期对郭罗克用兵并限时进剿时,如前文所述,乾隆帝严厉斥责提议者并将其提议全部驳回。以上三点既体现了乾隆帝总览全局的战略思维,也表现出他在处理郭罗克劫掠问题时的谨慎和宽大。
实际上,乾隆前期乾隆帝对于郭罗克劫掠问题的态度可以简单的概括为“慎重”二字,即不要一味的使用国家暴力的手段处理其劫掠问题,而要充分认识到国家整体的战略布局后用合理的方案管控其可能造成的社会不安宁。我们认为乾隆前期乾隆皇帝对待郭罗克问题的态度是正确的,正因为这样才使得乾隆前期清廷虽然对郭罗克用兵却未发生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同时也使得郭罗克地区的世俗官民免于生灵涂炭。以“慎重”为基本指导原则的处理办法固然避免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但又使得这一地区的清代长期得不到稳定和安宁。总之,乾隆前期的郭罗克问题是在以清廷为代表的统治者和以土官为代表的郭罗克上层之间互相妥协而得到暂时解决,同时这种不彻底性也使得郭罗克地区在清代长期不稳定。
参考文献
[1]邢海宁.果洛藏族社会[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
[2]苏发祥.清代治藏政策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
[3]清高宗实录[G]. 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李涛.试论乾隆年间的杂谷事件[J]. 西藏研究,1992年第1期
[5]曾国庆、黄维忠编著.清代藏族历史[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
[6]冯尔康.乾隆初政与乾隆帝性格[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林俊华]
作者简介:李红阳,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硕士研究生。(陕西咸阳 ,邮编:712082)
【中图分类号】K2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824(2016)01-00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