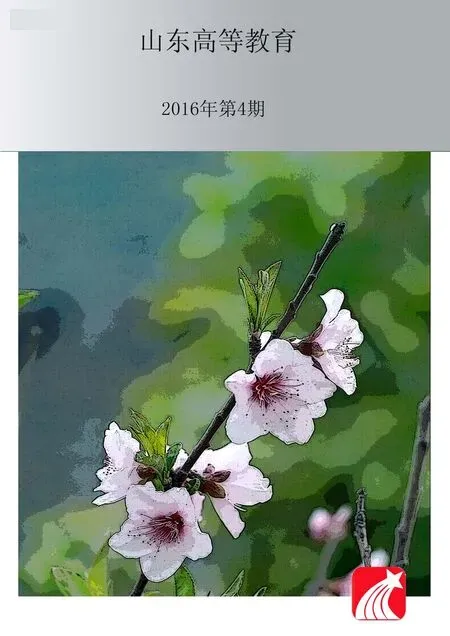抗战时期高校理科研究生教育论析
刘金生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1917年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的创设开启了近代我国理科研究生教育的先河。后经近二十年的发展,至抗战爆发前,理科研究生教育的办学规模渐次扩大,研究生的培养也日臻完善。然而抗战的全面爆发,打断了近代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良好发展势头,理科研究生教育也一度陷入困顿。鉴于战时国家对高层次理科类人才的需求尤盛,国民政府大力扶持高校理科研究所的恢复与创建,理科研究生教育迎来新机遇,谱写了我国战时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篇章。因此,考察理科研究生教育的历史背景,梳理其在战时发展的状况,总结其呈现的特点及带来的影响,既是对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也能为当前我国理科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有益参考和借鉴。
一、战时高校理科研究生教育的背景
战时高校理科研究生教育的大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根源。一是民国政府重视和加强学术规范,保证了相关政策法规的延续和完善;二是学界竭力呼吁和推动我国的学术专业化,激发了国人对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认同和需求;三是部分高校在理科研究生教育上积极实践和探索,为日后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民国政府重视和加强学术规范
民国成立伊始即着力提升国内高校的办学层次,发展研究生教育。《大学令》《大学规程》《特定教育纲要》等法令相继出台,“对大学院研究生的入学资格、修业年限、学位授予标准、大学院性质、各学院名称、教授聘任、管理方式及授予学位等做出明确规定”[1]265-378,并逐步涉及到对理科研究生教育的管理和指导。国内部分高校借此开始了理科研究生教育的探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学位授予法》《学位分级细则》《硕士学位考试细则》等法规实施,进一步规范研究院所的名称设置、研究生的培养、考核及学位授予等。其中1934年颁行的《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将理科研究机构定名为“理科研究所”,1935年颁行的《学位分级细则》将理科学位“分为理科学士、理科硕士、理科博士三级”[2]130,并对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方式、成绩评定等进行了规范。至此,近代我国理科研究生教育进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制度化发展阶段。
(二)知识分子对学术专业化的呼吁及推动
民国以降,尤其是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大批留学生学成归国,他们在近代自然科学学科建设及学术专业化上起了开创性作用。一方面,他们在高校组建和开设新式学科,大力引介西学西书,创办学术刊物,组织学术研究会及形式各异的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为实现中国学术的现代建构贡献良多;另一方面,他们积极呼吁学术独立,倡导建立各科研究所并极力强调其必要性,认为研究所可“藉作留学政策之转趋,渐达我国学术之独立”[3]。蔡元培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中更是明确了不设研究所之弊病:“一,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于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二,大学毕业生除留学外国外,无更求深造之机会;三,未毕业之高级生,无自由研究之机会”[4]13。此外,任鸿隽认为“凡没有设立毕业院或研究所的都不能称为大学”[5],并倡导通过借才异域的途径来加快我国高校研究所的建设进程。而汪敬熙则主张研究所应由本国人创办,直言“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才能创办大学的研究所,我们这民族就不配有高等教育”[6]。两者意见虽有相左,但其主张高校建立研究所,开展研究生教育的意愿却是一致的。纵观历史,彼时的学界知识分子在近代我国学术专业化的发展道路上积极建言献策,身体力行地推进了研究生教育的历史车轮。
(三)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探索与经验积累
抗战爆发前,北大、清华、南开、中央大学、燕京、金陵和岭南等7所高校,先后建立了涉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地质等5个学科的研究机构,开始了近代我国理科研究生教育的实践探索。以北京大学理科研究生教育为例,蔡元培于1917年执掌北大后,制定《北京大学研究所简章》,拟订设立理科研究所,筹商理科研究所办法,对研究所导师及任课教师的选任、课程设置、研究生的招收等事项做出规范,至1918初,所内研究生已达18人。[7]17历经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北大理科研究所在研究生的招考、培养、管理及毕业学位授予等方面已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和成熟的制度体系。至1934年教育部颁行《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后,北大理科研究所通过审核,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轨道。上述其他几所高校的理科研究所亦切实把握自身实际,积极探索,形成了特色鲜明、风格迥异的人才培养体系。从整体而言,经过近20年的努力,我国理科研究生教育的基本雏形已经建立起来,为战时理科研究生教育的继续发展壮大积累了经验,铺平了道路。
二、战时高校理科研究生教育的实施
抗战爆发后,国内高校针对自身实际,或远迁内地以避烽火,或立足本地力谋发展,他们“结茅立舍”,力求“弦歌不辍”。在政府及学界人士的不懈努力下,近代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步伐并未中断。鉴于国家对军、工、理、医等方面的科技人才需求尤甚,又本着教育服务抗战建国的原则,各高校及时调整发展规划,恢复和创建理科研究机构,着力培养高层次理科类人才。加之政府在高校研究机构创建上的大力扶持,理科研究所抓住机遇,迅速发展壮大,并在师资队伍建设和研究生的培养上呈现出鲜明特点。以下将具体论述:
(一)研究所的创设与重建
抗战伊始,身处战争前线的国立高校被迫内迁,中央大学、北大、清华和南开也在迁徙之列。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认为:“没有研究工作的大学,在教学上不但不能进步,而且一定会后退。”[8]49故而在寻得稍微稳定的办学环境后,中央大学决定再次创办“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并计划筹设9个研究部。依教育部《关于中大系科(院)设置调整办法》中批准其“原有理科研究所算学部”继续办理[9]398,中央大学理科研究所于1938年8月率先恢复运行,北大、清华理科研究所亦于次年相继恢复办理。前述设有理科研究所的七所高校,除南开大学在内迁后未能继续开办理科研究所外,其它三所教会大学在战争初期一直立足原地,竭力维持着理科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正常开展。与此同时,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和私立辅仁大学也先后创设了理科研究所,加入到培养理科研究生人才的行列。

表1 抗战时期高校理科研究所部基本信息一览
(资料来源:蒋致远主编:《中华民国教育年鉴》(第二次第二册),台中,宗青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86-88页;北大、清华、中央大学等校史相关资料整理。)
上述高校除增开理科研究所外,已成立的各研究所还努力拓展研究领域,扩大办学规模。如表1所示,至1942年,全国理科研究所部从战前的7研究所14学部,发展为9研究所26学部(1941年燕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停办),学部数增加了近一倍,为战时理科研究生教育的迅猛发展提供了载体。
(二)研究生师资队伍建设
伴随理科研究所的筹建,上述各高校也开始了研究生指导教师队伍的建设。他们不仅高薪延聘国内理科领域已取得卓越成就的专家来所执教,而且积极吸纳海外学成归来的高层次理科人才充实到教育科研的第一线。以西南联大为例,抗战期间其数学系教授队伍中聚集了江泽涵、申又枨、程毓淮、杨武之、郑之蕃、赵访熊、曾远荣、陈省身、华罗庚、姜立夫、刘晋年、蒋硕民、张希陆、许宝騄等数学界精英。虽然在研究生导师方面,主要有江泽涵、华罗庚、许宝騄、姜立夫、陈省身等大师级人物担任。但研究生的部分课程尚有其他教授承担,如“杨武之讲过数论、群论,程毓淮讲过群论和形势几何,刘晋年讲授过近世代数,申又枨讲授过复变函数”[10]273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各高校在理科研究所部主任的选任上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从其人员构成即可窥见一斑。

表2 抗战时期高校理科研究所部主任基本信息一览表
(资料来源:顾明远主编:《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名人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周家珍编著:《20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周川主编:《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辞典》,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等相关内容整理。)
从表2可知,战时高校在理科研究所部主任的选任上有如下特点:(1)都有海外留学经历。上述32人中,除了3名外国人和2名简历无从考外,其他27人均曾在一国或多国留学。其中有63%的人留学美国,53%的人就读于两所及其以上的海外大学。(2)多获得博士学位。除中央大学地理学部主任李旭旦最高学历为硕士外,其他都获取了博士学位。有此特例也说明高校在看重学历的同时亦能不拘一格,任人唯贤。(3)年龄构成合理。以1942年为例(上述理科研究所全部成立),50岁以上的有2人,40至50岁的有18人,40岁以下的有7人,形成了一个以中年人为主体,老中青相结合的梯队。此外,从其个人工作经历看,多数人都有高校任教的经历。由此可知,战时高校在理科研究所部主任的选任上,非常重视“学识”“年龄”和“经验”这三个标准。而正是这一群学通中西、掌握科技学术前沿、经过系统专业训练的留学生博士群体的不懈努力,才使得在战时艰苦环境下,近代中国的理科研究生教育仍能花繁叶茂、频结硕果。
(三)研究生的培养
战时各高校在组建起研究所后便开始了研究生的招考及培养。为便于工作开展,各理科研究所都制定了相应的研究所及学部暂行办法,对研究所的宗旨、研究生的入学、培养、毕业及日常的管理等都有具体规范和指导。
从招考方式来看:各理科研究所一般通过在各大报纸刊登广告的形式发布自己的招考信息,包括招考部别、考试科目、投考资格、呈交各件、报名时间地点、考试日期地点等内容。除原有研究生可以申请复学外,其他学生都必须参加严格的入学考试方能被录取。考试内容分普通科和专门科,其中普通科目包括国文和英文(作文及翻译),部分研究所还要求学生精通第二外语;专门科目按学部分别测试3至4门专业课。如1940年清华大学化学学部专门科目考察“无机化学及无机分析、有机化学及有机分析、理论化学”[11]4423门,而金陵大学检测“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12]2434门。除参加统一的入学考试外,研究所在招生过程中还保有一定的灵活性。如1943年同济大学校长丁文涵致信武大校长王星拱,保送其理学院数理系助教葛培根前往攻读研究生学位。经查该生的大学历年成绩单,毕业论文和毕业证书等符合入学条件,武大遂于当年免试招收其进入武大理科研究所理化学部化学门学习。[13]216-217
从培养模式来看,各研究所主要借鉴和施行英美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清华大学于1925年成立研究院时,即明确宣称“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14]378,此后虽一度停办,但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各院系必修选修学程表》中可知,清华大学理科研究所的一些指导教授如华罗庚、陈省身等,仍旧为研究生开设了部分课程。由此可见,抗战时期的清华大学理科研究所在研究生培养上,科学研究与基础知识的学习并重,其原有的学习英美的研究生培养模式被承继下来,无甚改变。北大理科研究所在战争初期采取的是以德国和日本为样板的学徒式研究生培养模式,它倡导以学生自由独立研究为主,研究题目、方向和范围由导师和学生自由商定,不重视系统课程的学习和学分的积得,而是通过拟定研究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做读书心得及研究报告、撰写论文等环节来培养和考察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15]148-149但1942年以后,“北大教授申又枨、吴大猷、米士等,分别为研究生开设了复变函数论、量子力学、区域变质等课程,”[16]256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北大理科研究所的指导教师们借鉴和吸收了其它学校的人才培养经验,培养模式开始向英美专业式研究生培养模式转变。
此外,成立时间较早的几所教会大学理科研究所,在研究生的培养上也多注重系统课程的学习,实行学分制。如1937年《辅仁大学研究所暂行规程》规定理科研究生必须修满“三十二学分四十八成绩分”[17]760;金陵大学化学部则“规定课程24学分中,至少须有16学分为化学课程”[12]243。成立较晚的几个理科研究所也都采取了科学研究与系统的课程知识学习并重的培养模式,这从各研究所的组织规程、培养计划和学程安排中即可看出。
三、战时高校理科研究生教育的特点及影响
抗战时期各理科研究所在研究生的培养上虽没有统一的执行标准,但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呈现出以下共同特点:
第一,奉行严格的人才培养原则。从招考上看,各理科研究所部都有一套完善而又严格的考选机制,从招考内容的设置,到考试程序的安排及最后学生的录取上,都坚持高标准和严要求。如1939年,北大和清华西迁昆明恢复研究生招生的第一年,两校物理学部依然奉行宁缺毋滥的原则,于众多报考学生中只招收了洪晶一人入学。从研究生的培养上看,各理科研究所部在战时艰难的岁月里仍然坚持维持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严谨性,从不以任何理由放松对学生的要求。如浙江大学数学部坚持和平时期形成的制度进行教学和科研,陈建功和苏步青等教授,在其常规的“数学研究”学术讨论班上要求极其严格,学生报告前必须认真阅读文献,仔细验算,提出问题和表达自己的见解,进行讨论。如果只停留在表面理解上,师生当场提问,“打破沙锅问到底”,往往会被“吊”在黑板上,弄得下不了台。[18]103再如清华研究院要求“研究生所修课程,无论是必修与选修都是七十分为及格线。必修课两科不及格,经补考仍不及格,即被淘汰”[19]63-63,1941年清华物理学部一名研究生即由于第一学年有3门功课都没有达到70分以上而被开除学籍。
第二,精英化色彩浓重。由于战时高校坚持奉行严格的人才选拔培养机制,各理科研究所部的招生规模都不大。以培养规模最大的物理学研究生的招考情况为例,1939至1944年间,西南联大共招收“钱伟长、许毓章、洪晶、黄授书、应崇福、凌德洪、刘普和、张守廉、杨振宁、黄昆”14名研究生[20]84,而彼时联大物理学教授有“饶敏泰、吴有训、周培源、叶企孙、吴大猷、赵忠尧、王竹溪”15名,在研究生的指导上往往可以实行双导师甚至三导师制。武汉大学理化学部于1942至1944年间连续招生,共招收9名研究生[13]223,而指导教授有胡乾善、江仁寿、梁百先、陶延桥、邬保良和高尚萌6人,师生比例保持为2 ∶1。再如1940年至1944年间,辅仁大学物理学部研究生有15人毕业。该部外籍导师有严池(Augustin Jaensch)、李嘉士(Michael Richartz)、欧思德(Francis Oster)、卜乐天(William Broil)和菲知本(P.Fitzgibbon)5名,在研究生的指导过程中,还外聘教师讲授《核子物理》和《电子物理》等课程[21]201,可见其导师和研究生的比例也超过了二比一。由此观之,战时理科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颇具精英化色彩。
第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各理科研究所秉持教育服务抗战建国的发展原则,一方面积极调整工作重心,集中精力研究应用性科学和培养高层次的应用性人才,特别注重研究成果在军事国防和工业生产等方面的转化及应用;另一方面则坚持发展原有的基础性科研项目,为国家民族复兴积聚人力智力支撑。在理科各专业中,与军事国防及工业生产最为相关的化学专业,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更加侧重研究成果的实用性。如燕京大学化学部教授蔡镏生指导的“从植物油中提取汽油”、韦尔巽指导的“麻黄类各种有机物”、窦维廉指导的“钙在机能代谢中的作用”以及由卫尔逊指导的“中国肥料之堆肥问题”等都具有很高的实用性。[22]18四川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和重庆大学应用化学研究室的各项研究工作,也是紧紧围绕关乎国计民生和战争物资需求开展的。如为工矿企业分析原料,化验成品,以及对与生产相关的问题进行研究、设计等,为中国橡胶、制酸、制碱、制药、制糖、酿造、造纸、炼油等行业的发展做了大量的科研工作。[23]177-178而算学、物理、生物、地质等其他理科专业,在战时的研究生教育中则更多地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这从研究生的论文题目中即可窥见一二。
第四,注重学术交流。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各研究所通过开设讨论班,举办学术报告、学术讲座,组建学会等形式来加强学校间、学科间以及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首先,开设讨论班成为高校培养数学类研究生的一大特色。西南联大先后开设大型讨论班有“代数讨论班、形势几何讨论班、李群讨论班、分析讨论班、群论讨论班、解析数论讨论班和拓扑群讨论班”[24]55等,其不拘形式,自由结合的小型讨论班、座谈会更是经常举行。以陈建功和苏步青为首的浙大数学研究所也非常重视讨论班的作用,在湄期间,其数学研究学术讨论班“每星期六下午均有举行”[25]296。其次,学会的组建为学术交流的开展提供了有效平台。以燕京大学韩朝佑、阎斌、张作干、唐冀雪等为首的研究生领导和组建的“生物学会”,活跃了生物系的学术活动,成为生物界的一个创举[22]243;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于1940年共同筹建的“新中国数学会”,极大地振兴了当时数学研究的风气;金陵大学研究生倡办的“化学会”和“工业化学会”等学术组织,借由化学壁报、化学魔术、化学工艺品制造竞赛等活动,营造了一股浓厚的学术空气。[26]107最后,学术报告及学术讲座的举办利于校际间的师资共享,及时传递和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如燕京大学化学俱乐部经常邀请著名学者如清华大学的黄子卿、北大的曾昭抡等做专题报告,学生一方面能汲取新的研究方法及理念,另一方面还能拓展获取信息的渠道,借由大师的视听去接触更广阔的世界。
总而言之,上述10个理科研究所在抗战时期凭借一群年轻有为、甘于奉献、勇于创新的导师队伍的不懈努力,在艰苦卓绝的战乱年代下排除万难,“结茅立舍,弦歌不辍”,对抗战建国大业的推进及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延续发展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首先,战时理科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适应了时代及社会发展需求,一方面为毕业后“有志于继续深研”的广大学子提供了进学之所,缓解了因战时出国留学名额锐减造成的激烈竞争,为更多学子接受高深学问提供了机遇和可能;另一方面则为国家、社会培养了一批即时可用之才,满足了抗战建国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据统计,1939至1945年间全国培养的理科研究生数达531人。这些高层次人才毕业后,或是进入高等教育第一线,成为大学教授和研究员,及时补充了高校师资力量,或是步入行政岗位,成为政界精英和管理骨干,还有的远赴海外继续深研,成为学科领域内的中坚,他们对中国学术研究乃至世界学术发展都做出了杰出贡献。其次,深化和完善了理科类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理科研究所经过战争期间的实践探索,在研究生的招生方式、培养模式、日常管理方法及学位授予等工作上有了进一步的调整和提高,为日后理科研究生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再次,师生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提升了近代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学术水平。理科导师群体在抗战期间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在开展教学活动,培养后备力量的同时,也注重带领学生开展学术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如钟开莱跟随华罗庚做研究,其“对于机率论与数论之贡献”的研究获教育部第二届审议会自然科学类二等奖,毕业后留校任教,并成为世界公认的20世纪后半叶“概率学界的学术教父”。最后,各理科研究所还重视和强调科学研究为抗战建国服务。他们的部分研究项目紧密地结合了当时当地的实际需求,并将研究成果及时应用到战时的工业生产和建设,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抗战建国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撑。
参考文献:
[1]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2] 教育部.教育法令汇编(第一辑)[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3] 庄泽宣.设立研究所之商榷[N].北平周报,1935,(103).
[4] 蔡元培.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J].东方杂志,1935, 32(1).
[5] 任鸿隽.大学研究所与留学政策[N].大公报,1934-12-23.
[6] 汪敬熙.也谈谈大学研究所与留学政策[N].大公报,1935-01-03.
[7] 北京大学.国立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一览表[Z].北京大学印行,1918.
[8]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东南大学文科百年纪行[M].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
[9]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上卷)[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0] 化存才等.数学应用工程研究[M].科学出版社,2010.
[11] 北京大学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3 教学、科研卷)[M].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12] 《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南大百年实录·中央大学史料选(中卷)[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3] 涂上飙.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1938—1946)[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14]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一卷)[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
[15] 李盛兵.研究生教育模式嬗变[M].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
[16] 伊继东,周本贞.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8.
[17] 王学珍,张万仓.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861—1948)[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8] 程民德.中国现代数学家传(第1卷)[M].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1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文史资料专辑)[M],内部刊印,1997.
[20] 苏国有.杨振宁在昆明的读书生活[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21] 孙邦华.身等国宝·志存辅仁:辅仁大学校长陈垣[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22] 张玮瑛等.燕京大学史稿[M].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
[23] 张培富.海归学子演绎化学之路·中国近代化学体制化史考[M].科学出版社,2009.
[24] 徐利治.徐利治访谈录[M].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
[25] 张彬.倡言求是·培育英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M].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26] 金陵大学南京校友会.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1888-1998)[M].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