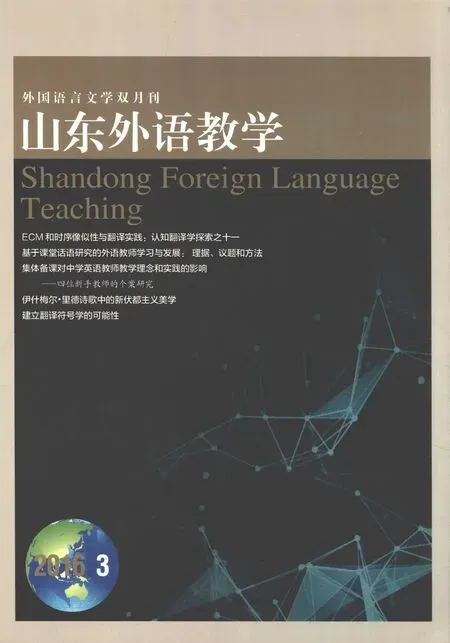帕慕克研究三十年述评
张虎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 221116)
帕慕克研究三十年述评
张虎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徐州221116)
[摘要]帕慕克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已30余年。本文试从“文化杂合与文化冲突”、“苏非神秘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呼愁、英译与跨学科研究”三方面对这一研究进行梳理与述评,最后,指出今后研究可以拓展的几个新方向。
[关键词]帕慕克;文化杂合;苏非主义;后现代主义;呼愁
1.0 引言
“一颗新星正从东方升起。”(Parini,1991:3)1991年,美国作家帕里尼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如此称赞一位作家。他的名字叫帕慕克(Orhan Pamuk,1952- ),生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代表作有《白色城堡》、《我的名字叫红》、《伊斯坦布尔——记忆与城市》等。2006年,他印证了厄普代克的预言(Updike,2004:99),因在“追求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冲突与交织的新象征”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近来,他又出版了新作《纯真博物馆》、《纯真之物》。
帕慕克的批评与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30多年来,涌现出了一批内容丰赡、角度各异的成果。为清晰、便于论述起见,本文试从“文化杂合与文化冲突”、“苏非神秘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呼愁、英译与跨学科研究”三方面进行梳理与述评,指出其中仍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探讨今后研究可以努力的新方向。
2.0 文化杂合与文化冲突
文明之间的冲突、杂合自古就有。近年来,在亨廷顿、赛义德、保罗·伯曼、穆罕默德·卡特米等人的激烈争辩中逐渐成为一个全球热门话题。土耳其地处欧亚之间,继承了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欧洲资本主义等多重文明遗产,倍感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悲与喜。因此,它自然是帕慕克写作的核心内容之一,同时也是大部分批评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不同的文化可以实现融合吗?帕曾自诩为东西方文化的“桥梁”,在访谈、著作中动辄谈及混杂、“每个人都有时是东方人,有时是西方人”(Pamuk,2007:370)等。因此,研究者们便从这一角度进行观照,阐释帕氏小说对西方、伊斯兰、文明冲突等概念的批判与否定。土耳其学者贝拉克斯肯就说,伊斯坦布尔是帕作品的主要城市背景,他生于斯、长于斯,他的写作地点就在横跨欧亚大陆的博斯普鲁斯大桥边,放眼望去,一边是东方,一边是西方,这使他获得了一种永远介于两者之间的伊斯坦布尔视力。所以,在他的笔下,人物身份流动变幻,清真寺与咖啡馆杂陈,东方画法与西方画法糅合,一切都染上了一层杂合的色彩。(Bayrakceken,2005:191-204)保罗·伯曼则以自在、散文化的语言分析了《寂静的房子》与《白色城堡》,并指出“1300年来,欧洲与中东伊斯兰的世代仇恨让它们相隔千里,但有恨之处,往往也有爱,二者是混杂在一起的……西方由基督徒主导,东方由伊斯兰主导,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不是一件简单渺小的事情”,而帕慕克创造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即“爱”。(Berman,1991:39)另外,凯茨曼、斯格沃兹等人也从不同文本出发阐述了这一问题,如“两个灵魂”(Pamuk & Gardels, 2005: 40)、“新生活的模式”(Pamuk & Skafidas,2000:21)、“东方和西方都是真主的”。(《古兰经》2,2013:115)由此,这一观点在今天产生广泛影响,甚至美国前总统布什在2004年访土时也模仿帕慕克的口吻说:“党派倾轧、文明对立、文化斗争、东西方冲突,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发现别的国家、大陆、文明中的人与你多么相像。”(Mcgaha,2008:39)国内的大部分学者也是赞同这一评价的,如杨中举说从《杰夫代特和他的儿子们》到《雪》,帕始终在追求一种“文学创作、文化发展的混杂性”,在内容上,他批判文化冲突,在形式上,兼取西方与伊斯兰文学之精华,架起了“一座沟通、横跨东西不同文化的艺术‘桥梁’”。(杨中举,2007:88)2012年,杨先生的专著《奥尔罕·帕慕克小说研究》仍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的。李卫华也称帕为主张“东方不应该只是东方,西方也不应该只是西方”(李卫华, 2008: 143)的杂合性作家,值得提及的著述还有《帕慕克在十字路口》(2009)、《镜子与孪生兄弟》、《身份界定与文化融合》等。
与这一观点相对立的是文化冲突,以威斯康辛大学的库利(David N. Coury)教授为代表,他在《“无所适从的国家”:奥尔罕·帕慕克<雪>中的土耳其与西方》一文中尖锐指出,帕的作品本质上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注脚,他获诺奖是因为政治,而非文学,他的笔下一直持续着一场激烈的东西之争,如塞拉哈亭与妻子法蒂玛的争吵、细密画与透视画的对立、苏纳伊与神蓝的交锋、妙医师与西方的对抗,等等,这恰恰证实了“在冷战后的新世界里,冲突的基本形式将不再以意识形态或经济为主……而是以文化为主”(Huntington,1993:22),尤其是那些“断层线”上的国家,将备受“无所适从”(Huntington,1996:149)之苦,在小说中,这就化作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呼愁”。给这一观点以有力支持的包括两部分成员,一是那些似乎与出版社和图书商结成利益同盟、以读者为中心的英美大众报刊,如《卫报》、《洛杉矶时报》、《雨中的士书评》、《每日星报》等,它们频频将帕与9·11、本拉登等联系在一起,渲染其作的文化冲突性:“东西方冲突渗透于土耳其的社会和个人生活中,它是帕慕克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Kenne,2004)、“在帕慕克笔下的‘东-西’之争中,新作《我的名字叫红》是最庄严、最令人赞叹的一幕”(Eder,2001:7)、“9·11之后,书商们纷纷涌向伊斯兰问题,他们的柜台上摆满这类书籍,本拉登、基地组织、塔利班……《我的名字叫红》……讨论了这一普世而永恒的问题”(Ianelli,2001),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另一类是土耳其本土的一些民族主义媒体,如专栏作家奥兹古就说帕是一个“满脑子坏水”的家伙,特别喜欢写仇杀、阴谋,“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土耳其的种种缺陷……他不在键盘上快乐地胡扯一番、写下这些玩意儿就憋得难受”。(Özgün,2005)阿勒泰则在《民族报》上称帕为“恐怖的造物”和“黑色作家”。(Mcgaha,2008:3)这些评述良莠不齐,但在大众中有巨大影响力。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持非此即彼的态度,兼取者亦不少,如古克纳、西班牙学者麦克戈哈。但是,帕慕克评论中“文化冲突与文化杂合”形成一种对立趋势已是不争事实。于是,一些疑惑便浮现于读者脑海中:帕慕克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基本认识到底如何?《白色城堡》等小说表达的究竟是什么?这与帕慕克的写作技法有何关系?
3.0 苏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我的作品、我的小说受到了双重滋养:一是西方伟大的小说艺术和写作,一是传统的苏非伊斯兰作品。”(Pamuk & Brown,2006)帕的这一陈述也概括了学界对其小说的艺术形式、文化渊源研究的基本状况,前者的阵营主要在土耳其,后者在英美、中国等地,这从侧面再次证实帕是一个兼采东西文学之英卉的作家。
先说苏非主义。苏非即suf,意为羊毛,它是伊斯兰教内部衍生出的一个神秘教派,核心教义为“人主合一”。帕的创作深受其影响。2003年,《新文学史》第1期刊登了“伊斯兰、忧伤与落魄尖塔——论奥尔罕·帕慕克《黑书》叙事的无效性”一文,作者为伊斯兰哲学专家安·阿拉芒(I. Almond),他以苏非主义在20世纪土耳其西化改革中的失落为大背景,论述了《黑书》如何表现这段历史对本土人精神生活的影响。曾经,土耳其人相信世界是一个谜,处处是谜之线索,追寻它们,便可发现自我,实现与真主合一的至福。对他们而言,这个世界是神圣、完满的,何况,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不计其数的苦行僧供人学习和崇敬。但经过凯末尔总统的一番改革后,这种精神维系断裂,每个个体都觉得空虚,备受灵魂的无所皈依之苦——这就是小说中之忧伤的现实来源。(Almond,2003)该文较早触及帕与苏非主义的关系问题,而且它从一开始就摆脱了套用比附,客观地将历史、后现代技法等问题一并纳入进行了精深论述。布隆德曼与穆宏燕读的同样是《黑书》,但结论却与阿拉芒不同。两人都认为《黑书》源于波斯诗人阿塔尔的神秘主义叙事诗《百鸟朝凤》,并运用“我即凤凰”这一思想以及神爱论、侯鲁非主义等对文本进行了细读,称主人公卡利普就是群鸟,耶拉是凤凰,如梦是“爱”的隐喻,全书讲述了卡利普如何顿悟自我、成为他人、最终实现追寻者、追寻、被追寻者的合一。因此,《黑书》“与其说是一部文学作品,毋宁说是一部哲学著作”(穆宏燕,2008:44),基本“可以将它当作一个苏非寓言来阅读”(Brendemoen,2005)。另外,“帕慕克与苏非主义”、“‘恋之奴仆’与‘纯粹之爱’”、“‘影身’:《双重人格》与《白色城堡》”、“从柏拉图到苏非”等论文也有诸多建树,它们分析了《白色城堡》与“双重真理说”、《新人生》与“照明论”的互文关系,追溯了帕爱情叙事的结构原型,即“神秘道”三段论,还对帕的后现代神秘主义书写特征及其现实意义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值得肯定。
在土耳其,帕是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他是以后现代小说家的身份崭露文坛的。他曾在《民族报》上自称为“一个快乐的后现代主义者”。(Çongar,1998:14)这是本土评论家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代表性成果如《帕慕克的英雄》、《后现代文本的自省》、《后现代之旅与后现代文本分析》、《拒绝预设》等,它们或单论主题模糊、情节散漫、人物身份不确定等某一类文本特征,或将帕与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纳博科夫等西方后现代大师进行比较,追溯其影响关系,抑或分析帕对元小说、图文拼贴、互文等实验性技法的迷恋和运用,绘制了一幅清晰的帕后现代写作地图。例如,萨拉奇格在博士论文“后现代文本的自省:约翰·福尔斯与奥尔罕·帕慕克的比较研究”中以哈琴的“自省”概念为中心,从人物、元小说、自传式书写三方面比较了福尔斯与帕慕克的异同,称帕慕克为“土耳其最激进的后现代作家”(Saraçolu,2003:2),最后,还阐述了帕慕克对隐含作者、小说与现实世界之关系的基本态度。另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奥斯曼文学专家安德烈的《黑书与黑匣子》,他以“后现代主义的两面性”为理论武器,把《黑书》喻为一个“黑匣子”(Andrew,2000:105),认为它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后现代思想,即世界是一个平坦、空虚之地,其中布满了无数的关系、线索与暗示,它们都似乎指向了一种意义,一种关于人生的意义,实际上这是一个黑色幽默和游戏,人们置身其中,一生都在寻找、挣扎、彷徨。这正是《黑书》为什么会引起争议的根本原因。当读者走入小说中,被纷乱的、没有所指的能指所迷惑,最终落入这个“专门为学者、批评家和所有阐释者所挖的陷井”。(同上)安德烈跳出自己的研究领域,给《黑书》一个后现代文本的定位,这种做法值得深思。
试问,《黑书》到底是苏非寓言还是后现代小说?苏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帕笔下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势必要解决。
4.0 呼愁、英译与跨学科研究
“呼愁”(hüzün)是帕写作的主要艺术风格,也是帕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该词在土语中意为忧伤,指人内心深处的一种失落感,在《古兰经》中,它出现过5次,两次写作huzn,3次写作hazen。先知穆罕默德把妻子和伯父的过世之年称作“senetül hüzn”,即“忧伤之年”。这一概念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帕曾在《伊斯坦布尔——记忆与城市》中单列一章对它进行过介绍和诠释,他说,呼愁有两个哲学源头,一个指出“当我们对世俗享乐和物质利益关注过多时,便会体验到呼愁”,另一个认为“‘呼愁’是因为不够靠近安拉、在这世上为安拉做的事不够而感受到的精神痛苦”(Pamuk,2006:90、90),后来,奥斯曼帝国陷落,共和国建立,呼愁的内涵就更深广了,包括西方人的眼光、民族文化的失落、土耳其人的自我认知、政治斗争等,最终它成为伊斯坦布尔乃至整个土耳其的一种独特文化。因此,也可以说,帕自己就是呼愁的第一个研究者,<呼愁>一章也成为后来的研究者们的一门必修课。这种忧伤的气息不仅弥漫于帕笔下的每一个人物身上、每一处风景和每一段爱情故事中,也深深印刻在帕本人的性格气质中。
伊斯拉·安凯(E. Akan)也是呼愁诗学最早的诠释者之一。他说呼愁由两部分构成,“一个是与失落感相伴的忧伤,另一个是不太清晰的,大致与城市的风景相连,”(Akan,2006:39)即人之忧伤与景之忧伤,前者指土耳其迁都安卡拉后伊斯坦布尔市民的心理落差和身份迷失,后者指伊城内随处可见的坍塌城墙、贫困后街、僧侣道堂、乞丐游民和空无一人的老宅邸,将二者凝合在一起的是西化改革史。在改革中,作为帝国后裔的土耳其人深负耻辱感,但又难以超越西方,最后形成一种巨大的群体忧伤情绪。这是这座布满商业大厦、购物中心、星级酒店的“国际大都市”(同上:43)背后的一种持久宝贵的文化情结。诗人泰勒戈、萨特叟、印度学者库马尔、德国学者亨斯臣等也分别对呼愁进行过解读与研究,有分析呼愁的文本表征的,有诠释呼愁与海德格尔哲学的关系的,也有研究呼愁与“伊斯坦布尔之眼”阿拉·古勒拍摄的100多张城市照片之关系的。在国内,众多学者也十分关注该问题,钟志清比较了呼愁与辛弃疾、李煜、林语堂之忧伤写作的异同,杨中举将呼愁小释为宗教与历史的呼愁、心理学与医学意义上的呼愁、西方旅人视域中的呼愁、土耳其作家笔下的呼愁4个层次,认为它是“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中历史文化的结晶”(杨中举,2009:1),李伟荣提出新的美学命题:“帕慕克的作品之美,就在其‘呼愁’”(李伟荣,2008:106),张虎(2011)等人也从个人气质、东西方文化渊源、时代内涵等各个方面对呼愁进行了细致剖析,不再赘述。尽管如此,要说清楚呼愁何以成为一种呼愁,至今仍未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帕写作的成功离不开英译这一媒介。他的写作语言是土语,至今已有五位英译者,即豪布鲁克、古恩、弗瑞丽、古克纳、迪克巴斯。在英译领域,古恩(G. Gün)是一个焦点人物。1996年她翻译了《黑书》后,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遭到一群英国评论家的激烈批评,称她的译介太美国化、句子冗长混乱、扭曲原作,安德烈·曼格与艾思姆·埃德姆还试着重译了一些段落。然而,不久后古恩在美国却获了翻译奖。1999年,古恩撰文回击道,《黑书》的语句本来就冗长杂乱,那些抱怨她的译本乱七八糟、声称她误译漏译的人,其实根本就看不懂土文,于是,“他们怎么可能知道帕慕克的原文是什么样呢?”(Gün, 1999:14)一时间,高莫里、麦克戈哈(M. Mcgaha)等众多学者与作家皆参与到讨论中来,烽烟四起,译者隐形、文化转换、市场竞争与翻译道德等问题被再次提上日程,人们为此争辩不休。最终,学界肯定了古恩的译介,正如麦克戈哈在比较了曼格与古恩的译文后所说的:“那些批评古纳莉·古恩的英国读者们一定会喜欢曼格的译文,因为他用的是‘lorries’而非‘truck’,‘tinned’而非‘canned’,‘rubbish’而非‘garbage’,‘pavement’而非‘sidewalk’,‘cashing up’而非‘going over their accounts’……”。(Mcgaha,2008:141)土耳其学生伊马兹的毕业论文“译介之旅:英语中的帕慕克”为这一领域提供了另一面自省之镜。它以安德烈·列斐伏尔和韦努蒂的翻译理论为参照,批评了帕英译、英评界的三种趋向,即畅销的帕慕克、西方作家式的帕慕克和书写文化冲突的帕慕克,认为这是一种霸权式的重写与归化,误导了该国读者对帕的理解和认知。
最后不得不提到的是跨学科研究,即“外行”们对帕的认识。这类研究在视角、方法、材料运用上常常不拘一格,独辟蹊径。如奇珂戈卢(F. Çiçekoglu)是位影视剧作家,他在“《我的名字叫红》中的分歧、图像叙事与‘视角’”中以《我的名字叫红》第1、33章为例,从肖像画与角色、行动与时间、故事与空间、视角、盲与非盲5方面分析了东西方图像叙事传统的差异,比较了细密画大师纳卡斯·奥斯曼与尼德兰画家布鲁盖尔的画风差异,之后,将这一问题引上影视创作,称伊斯兰独特的图像叙事传统让土耳其电影形成了一种缓慢的播放节奏,不适合于塑造人物,难以让人感动、震撼。但同时,他也以《我的名字叫红》的成功为榜样,表达了对土耳其电影未来的信心。(Çiçekoglu,2003a)2003年刊登于《美学教育杂志》的“双向视野教学法”则认为《我的名字叫红》包含了一部完整的图文关系史,即文为图之奴、图为文之奴、文与图的分离和合并。(Çiçekoglu,2003b)阿拉莫尔(A. Allmer)的“奥尔罕·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论建筑、叙事与收藏艺术”一文最让人眼前一亮。他是土耳其的一位建筑学博士,最早发现了《纯真博物馆》不仅是一本小说,也是一座真实的博物馆,它位于伊斯坦布尔楚库尔主麻街,设计者为伊桑·比利金,是一栋两层楼的古楼,里面陈列着小说主人公芙颂与凯末尔的画像、文中描写到的烟蒂、胭脂、耳环、衣服等各类物品。在论文中,阿拉莫尔还附上了该博物馆的剖面图、结构图与几张照片,详述了帕购买、装修这座足有百年房龄古楼的全过程。他认为,帕的这一行为与本雅明的收藏理论、威廉·米切尔的图像理论相关,实际上是帕的一个庞大计划——对文字、图像与建筑界限的跨越。(Allmer,2009)这一研究让人茅塞顿开,重读《纯真博物馆》,会发现里面确实藏着一张门票,还附了一张地图,它们是帕对读者参观纯真博物馆的一次诚邀,而且,帕在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还读过3年建筑学,他的小说在结构上也有一种建筑美,字、画、物的关系也一直是他所关注的……这一切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与深入。
5.0 存在的问题与走向
综上所述,帕慕克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慎思之,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帕是一位土耳其作家,他说:“我生来就是一个土耳其人。”(Mcgaha,2008:378)他写的是土耳其的人与事,思考的是土耳其的文化前景。但目前除古克纳外,很少有人对帕与现代土耳其的关系进行专门研究。这是今后可以努力的一个新方向,内容包括帕对“土耳其之父”凯末尔及其世俗主义改革的态度,帕与本土伊斯兰主义的关系,帕对库尔德和亚美尼亚等少数族裔形象的书写,帕对阶级分化问题的认识,等等,这些研究将为今后帕的评论提供一个坚实的起点。其次,苏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的单向度研究留下了一些批评困惑,亟待厘清,如《黑书》的文体定位、帕对东西文化关系的基本认识等。第一个问题也许可以从后现代宗教角度切入,其实,神秘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本身具有许多共通之处,如反理性、否定自我、能指游戏等,剑桥学者唐·库比特已经有过相关论述。至于是冲突还是杂合,首先要做的恐怕是剥离文学评论中过激的政治论断和民族主义心理,然后,回归文本,与帕写作的技巧、风格等结合在一起重新进行认识与观照。归根结底,现急需一系列综合性、总括性的研究。再者,土耳其妇女的独特历史、帕在小说中塑造的众多女性(如谢库瑞、法蒂玛、杰伊兰、卡迪非)和他对伊斯兰妇女问题的关注都使得从性别角度进入帕的作品成为一个有前途的学术课题。除此之外,帕的文艺理论思想、存在主义诗学等新问题目前也未能及时展开。所以,今后的研究仍是大有可为的。
参考文献
[1] Allmer, A. Orhan Pamuk’s “Museum of Innocence”: On Architecture, Narrative and the Art of Collecting [J].ARQ, 2009,(2):163-172.
[2] Almond, I. Islam, Melancholy, and Sad, Concrete Minarets: The futility of narratives in Orhan Pamuk’sTheBlackBook[J].NewLiteraryHistory, 2003,(1):75-90.
[3] Akan, E. The Melancholies of Istanbul[J].WorldLiteratureToday, 2006,(2):39-43.
[4] Andrew, W. G.TheBlackBookand Black Boxes: Orhan Pamuk’s Kara Kitap[J].Edebiyat, 2000,(11):105-129.
[5] Bayrakceken, A. & D. Randall. Meetings of East and West: Orhan Pamuk’s Istanbulite Perspective[J].Critique, 2005,(3):191-204.
[6] Berman, P. Young Turk[J].NewRepublic, 1991,(11):36-39.
[7] Brendemoen, Bernt. Orhan Pamuk and His Black Book[OL]. 2005. http://www.orhanpamuk.net/popuppage.aspx?id= 75&lng=eng.[2014-09-13]
[8] Çongar,Y. Ger?ek Tüm Dünyaya S?ylenir[N].Milliyet, 1998-4-27: 14.
[9] Çiçekoglu, F. Difference, visual narration, and point of view inMyNameisRed[J].JournalofAestheticEducation, 2003a,(4):124-137.
[10] Çiçekoglu, F. A pedagogy ofTwoWaysofSeeing: A confrontation of “Word and Image” inMyNameisRed[J].JournalofAestheticEducation, 2003b,(3):1-20.
[11] Eder, R. Heresies of the Paintbrush[N].NewYorkTimesBookReview, 2001-9-2: 3.
[12] Gün, G. Something Wrong with the Language[N].TimeLiterarySupplement, 1999-3-12: 14.
[13] Huntington, S.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J].ForeignAffairs, 1993,(3):22-49.
[14] Huntington, S. P.TheClashofCivilizationandtheRemakingofWorldOrder[M]. New York: Simon, 1996.
[15] Ianelli, E. J.MyNameIsRed[OL]. 2001. http://www.raintaxi.com/online/2001winter/pamuk/shtml.[2014-09-13]
[16] Kenne, M. A Blizzard in the East: Pamuk the Postúmodern Mystic[OL]. 2004. http://www.dailystar.com.ib/prin table.asp?art_ID=6103&cat_ID=21.[2014-09-13]
[17] Mcgaha, M.AutobiographiesofOrhanPamuk:TheWriterinHisNovels[M]. Salt Lake City: The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8.
[18] Özgün, A. Orhan Pamuk vs. Michael Moore[OL]. 2005. http://www.turkishdailynews.com.tr/article.php?enews id=6698.[2014-09-13]
[19] Pamuk, O.Istanbul:MemoriesandCity[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6.
[20] Pamuk, O.OtherColors:EssaysandaStory[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7.
[21] Pamuk, O. & J. Brown. Interview with Jeffery Brown[OL]. 2006-10-12. http://www.pbs.org/newshour/bb/entertainment/july-dec06/pamuk_10-12.html.[2014-09-13]
[22] Pamuk, O. & N. Gardels. A Europe of Two Souls[J].NewPerspectiveQuarterly, 2005,(1):37-41.
[23] Pamuk, O. & M. Skafidas. Turkey’s divided character[J].NewPerspectiveQuarterly, 2000,(2):20-22.
[24] Parini, J. Pirates, Pashas, and the Imperial Astrologer[N].NewYorkTimesBookReview, 1991-5-19:3.
[26] Updike, J. Anatolian Arabesques[J].NewYorker, 2004,(20):98-99.
[27] 李卫华. 文化冲突与文化杂合:《我的名字叫红》中的情节结构隐喻[J]. 外国文学研究, 2008,(1):138-144.
[28] 李伟荣.“呼愁”——理解帕慕克作品的一片钥匙[J]. 湖南大学学报, 2008,(4):106-110.
[29] 马坚译. 古兰经[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30] 穆宏燕. 在卡夫山上追寻自我——奥尔罕·帕慕克的《黑书》解读[J]. 国外文学, 2008,(2):44-53.
[31] 杨中举. 奥尔罕·帕慕克: 追求文学创作、文化发展的混杂性[J]. 当代外国文学, 2007,(1):88-94.
[32] 杨中举. “呼愁”: 帕慕克小说创作的文化诗学风格[J]. 东方丛刊, 2009,(2):1-14.
[33] 张虎.“影身”:《双重人格》与《白色城堡》[J]. 山东外语教学, 2011,(2):87-91.
DOI:10.16482/j.sdwy37-1026.2016-03-010
收稿日期:2014-11-13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帕慕克与苏菲神秘主义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3CWW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虎(1983-),男,山西阳高人,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奥尔罕·帕慕克与土耳其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2-2643(2016)03-0078-06
A Review of Orhan Pamuk Studie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ZHANG Hu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116,China)
Abstract:The studies of Orhan Pamuk began in the 1980s. About thirty years have passed after that.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is condition in three aspects, i. e. “cultural hybridity and cultural clash”, “sufism and postmodernism”, “huzu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he paper also puts forward some new directions of Pamuk studi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Pamuk; cultural hybridity; sufism; postmodernism; huz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