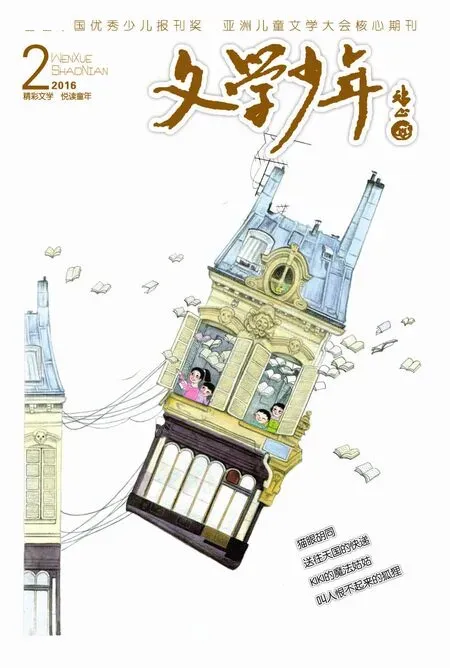马
|[日]德永直|苏 南
马
|[日]德永直
|苏南
我喜欢马。
最使我感到亲切的是驮东西的马。
我讨厌那种昂然作势、贵公子骑乘的毛色漂亮、骨架好看的马。因为它使我感到像是受了侮辱。
马里头也有性子很暴的马,还有动不动就发惊发疯的马。可是,劣马,我也是喜欢的。
样子可怜的马!
悠闲自得的马!
像暴君似的威风凛凛的马!
在旷野里放牧的马,有一种跟人亲近的地方,这是在都市里的马身上看不到的。
马比起别的动物来,有一对大得出奇的眼睛。马的深蓝色的瞳仁是很大的。
马的睫毛也长得能在瞳仁里照出影子来。当马疲惫不堪,或者要走很远的路程的时候,它把睫毛眨巴两三次,于是大颗的泪珠就把瞳仁润湿了。
看到马哭,人也会跟着一道哭起来呢!
那年我14岁,弟弟11岁。经常总是我跟父亲两个人牵着马出去干活,可是因为父亲病倒了,所以只好由我跟弟弟两个人去了。
有一天,我们在夜里10点钟左右,装了满满一车冰镇的鱼,要赶到五十几里外一个叫做“植木”的镇上去。我们的马是一匹8岁口的枣红色小马。我拉着缰绳,弟弟打着灯笼,一同赶路。
过了门前有一棵松树的茶馆,雨哗哗地下起来了。
“糟啦!”
我不安地吆喝住了马,给马披上草席,防它受凉,一面抬头望着漆黑的天空,察看云彩的方向和雨势。我看到从西面和南面天上,一片黑云来势很猛地向这边直压过来,这边只有一点薄云,还比较晴朗。根据父亲告诉我的经验,我想这会是一场大雨。
最使我担心的是道越来越泥泞了。没有赶过大车的人大概不知道这种滋味,对我们来说,再没有比道路坏更叫人头疼的了。
雨瓢泼似的越下越大。
时间虽是初夏,可是正当深更半夜,冷得沁人肌骨。
马好像也累了,不停地把脖子和脸凑到我的脸上,脚步也迟钝起来了。
可是,这场雨也不像一两个钟头就能停住的样子,下的时间越长,金钉那道难关就越难过去,这样一想,就不得不拼命拉着马缰,气喘嘘嘘地打马赶路。
我怕车上东西太沉,没有让弟弟再坐到车上去。
“紧走几步,身子就暖和啦!”
我朝着弟弟大声喊道。弟弟在烂泥里,脚下不住打滑,可是也鼓起劲走着。但他个子太小,脚一陷进深泥,身子就要栽倒,灯笼也就被他弄灭了。
“笨蛋,脚底下稳点!”
我性子很暴,虽然明知不对,还是猛地把他踢了一下。
终于来到我们赶大车的人最怕的难关金钉了。在离陡坡还有100多米远的地方,我们把马停住,歇了一会儿。
“哥,不要紧吗?”
弟弟滚了一身泥,抱着灯笼,仰起脸问我。
“没什么……”
我给他打气说。随后我从车子抽斗中取出镰刀,借着灯笼的亮光割了一点草,喂给马吃。马好像累得很厉害,只是叼了几根草,呼呼地直喘气。
“哥,马累得够呛哩!”
弟弟看见马连草也不想吃,说。我摘下帽子,从旁边的水坑舀起一帽子浑水,拿来饮马。
随后我们坐到车上,吃了饭团。腌萝卜让雨浇得水淋淋的,已经一点味道也没有了,可是我们还是吃得很香。
看到雨小了些,我又拿起缰绳来。弟弟捡来一根竹片,转到马的那面去。
“喂,加把劲啊!”
我拍打着马的脖子,马仿佛点头似的浑身抖擞一下,猛地迈出了前蹄。
“驾,驾!”
我又把缰绳绑到车辕上,再套到肩头上拉着。我想先把车拉上陡坡中间略平的地方。弟弟一面跟在车旁跑着,一面抽打着马屁股。
路泥泞得厉害,几乎车身的一半都陷在泥里了。狭窄而陡急的道路左面,稍微拐过去一点,就是一个将近二丈深的悬崖,那下面是一片泥塘似的田。
“哎,再加把劲就行啦!”
话虽这样说了,可是这时候,马也好,弟弟也好,我也好,却都累得几乎动弹不得了。
“加油!”
马拼命地拉,我死劲地喊。可是车子像被烂泥吸住了似的,一动也不动。
车上载的鱼要是天亮以前送不到植术的鱼店,就没有用处了。
车子只动了一点点。
“驾,驾!”
弟弟哭哭啼啼地用竹片抽打着马屁股。
上坡上到十分已有七分的地方,马把两只前蹄一弯,跪倒在泥里,不动了。想把车上的东西卸掉一点吧,可是沉甸甸的货包,凭两个孩子的力气是怎么也卸不下来的。
“畜生!废料!”
我发疯似的揪住马鬃往起拉,可是马像死了似的,只是摆动了一下脑袋,而弯下的两只前蹄却再也没有力气站起来了。
“哥,怎么办哪……”
弟弟哭哭啼啼地抱着灯笼坐到泥里了。马把脖子伸到灯笼的亮光底下,可以看见它那大眼睛里满是眼泪。我忍不住,跟弟弟两个人抱住马脖子抽抽噎噎哭了起来。
过了一个钟头左右,我们才得到也是往植木去的伙伴们的帮助,好不容易翻过了陡坡。真的,再也没有像马这样诚实的动物了。我现在看到拉货车的马,还打心眼里感到亲切。
马不光会哭,也常常笑。可是在东京一带,会笑的悠闲的马似乎很少见。
责编|冉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