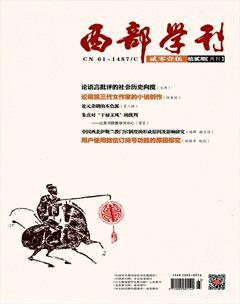毕沅《关中金石记》考论
摘要:清人毕沅于清乾隆间在陕任职达十余年,对关中金石作了较为全面的搜集整理,并在进一步系统研究和考证的基础上,编纂了《关中金石记》八卷,为陕西金石学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关中金石记》成书于清乾隆四十七年。版本除乾隆本外,尚有民国王云五主编本;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清道光二十七年,蔡汝霖等对原书进行了增附重刻;光绪十三年,大同书局据蔡刻本进行了石印;光绪三十四年及民国十三年,渭南人严岳莲于成都重刊蔡氏校本。该书保存了诸多宝贵史料,同时也有不少错讹。
关键词:毕沅;《关中金石记》;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
《关中金石记》作者毕沅(1730-1797),字纕衡,一字秋帆,自号灵岩山人,江苏镇洋(今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进士。博学多才,精通经史,旁及小学、金石、地理,擅长诗文,著述甚丰。编著有《续资治通鉴》《山海经新校正》《晋书地理志新补正》《关中胜迹图记》《长安县志》《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山左金石志》等著作。其史学成就涉及到史学理论、编修史书、整理修纂史地文献等方面,并提出了通过考据金石证经史的史学思想。毕沅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到陕,历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巡抚、陕甘总督等职,直至乾隆五十年(1785)离任,在陕任职达十余年之久。任职期间,利用公务之便,踏勘调查名胜古迹,笔耕不辍,《关中金石记》便是代表性著述之一。
清初金石学就形成了一种亲身搜求原碑的风气。早于毕沅而著录关中金石的朱枫《雍州金石记》中所收录的碑刻就都是作者在陕十年勤苦搜访所得,所得都是第一手文献资料。毕沅在陕期间更是足迹遍布各地,对陕西地区的碑石进行了系统的搜集整理。《关中金石记》孙星衍跋说:“公厮渠所及,则有随便子谷造象,得于长安;唐尔朱达墓碣,得于郃阳;朱孝诚碑,得于三原;临洮之垣,亘以河朔,公案部所次,则有唐姜行本勒石,得于塞外;梁折刺史嗣祚碑,得于府谷;宝室寺钟铭,得于鄜州;汉鄐君开道石刻,魏李苞题名,得于褒城。公又奏修岳祀,而华阴庙题名及唐华山铭始出焉。”可见其对陕西碑石的全面了解。
对关中金石搜集整理之后,在进一步系统研究和考证的基础上,毕沅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编纂了《关中金石记》八卷。该书按朝代顺序,收集汇编了自秦汉至金元的碑志石刻、摩崖造像、瓦当、鼎彝等凡七百九十七通。书中记载的碑石种类和数量远远多出乾隆二十四年(1759)朱枫所著《雍州金石记》所收一百七十余种。该志对保存在西安府学及关中地区所辖各县对所录每块碑志石刻,从碑名、撰者、书者、时代、书体、藏碑位置、保存状况、碑文字数、书法特点、碑文内容等方面予以介绍,并结合史书对所涉史事作了精确考证,为陕西金石学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毕沅纂成《关中金石记》后,作为其《经训堂丛书》的一种,于乾隆四十七年刊刻,是此书最早刻本。八卷,前有卢文弨、钱大昕序,后有钱坫、洪亮吉、孙星衍跋。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王云五主编、商务印书馆发行《丛书集成初编》,据经训堂丛书本排印此本,有句读。1985年,中华书局又据《丛书集成初编》本排印。200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续修四库全书》,据经训堂刻本影印。
道光二十七年(1847),渭南蔡汝霖、蔡锡栋与同乡人焦兴儒,①因原书不易得,对所藏本进行校勘编辑,主要是原书有些未按时间先后排列的条目进行了调整,给原书增编了目录,同时蔡氏辑录了一卷“为原书漏载或嗣出于其后者”若干种碑刻,作为附记附入原书,重新镌刻。此刻前有两蔡氏序、蔡氏新编目录、蔡氏新增金石目录,原书八卷后附蔡氏附记一卷。此本后又有光绪十三年(1887)大同书局石印本。
光绪三十四年(1908),又有渭南人严岳莲于成都重刊蔡氏校本,②此本前有卢文弨、钱大昕、两蔡氏序,毕沅原目次、蔡氏新编目录,书后有钱坫、洪亮吉、孙星衍跋三篇,后附蔡氏新增金石目录及附记一卷。此本后又有民国十三年(1924)重刻本。
二
清代金石学乃受考据学推动而勃然兴起,所以金石学对学术的贡献,首先是资经史考据之学,从而形成了清代金石学的明显特色。清代不仅搜罗金石碑碣蔚然成风,以金石文字考证经史也远过前人。卢文弨在此书的序中说: “国朝以来,为金石之学者,多于前代”,“考证史传,辨析点画,以视洪、赵诸人,殆又过之”。顾炎武是清代考据学的开山之祖,故以金石文字考证经史也由其发端。因此学术风气使然,清代金石学发展初期的著作体例,在著录碑刻时只撮其文义而节录,如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朱枫《雍州金石记》等,重在辨正误,正同异,毕沅的《关中金石记》亦是如此。
此书刊刻之初就得到了很多赞誉,钱大昕为此书所作的序称:“征引之博,辨析之精,沿波而讨源,推十以合一,虽曰尝鼎一脔,而经史之实学寓焉。”孙星衍在为此书所做跋语中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且夫欧赵之书,徒订其条目;洪都之著,第详其年代;公证古之学,奄有征南;博闻之才,通知荀勖。此之造述,力越前修,谈经则马郑之微,辨字则杨杜之正,论史则知几之邃,察地则道元之神。旁及九章,渊通内典,承天谱系之学,神珙字母之传。”认为其价值远远超过了欧、赵以来金石研究的成就。由于毕沅是一个在史地学、金石学、校勘学、方志学方面都有很高造诣的学者,“金石可证经史”是他的重要史学思想。因此本书中著录每方碑刻之后,作者均考订源流、志主、刻立时间、撰书人等,并厘定文字,对涉及史实加以考证,据笔者粗略统计,作者用以考证所引之书约有一百二十种,文数篇,资料丰富,其辨析很有学术价值。
作者对于碑刻所涉及的史事进行考辨,以碑正史,补史之缺,如薛收的赠谥唐史未载,见于《赠太常卿汾阴县公薛收碑》;《李怀让题名残字》《纪国先妃陆氏碑》《姜遐碑》等均记载志主陪葬昭陵,而《唐会要》的昭陵陪葬名录未载此数人,据之可以补入;《美原神泉诗》可补史书缺载的韦元旦、尹元凯的历官、姓字等。又颜真卿的生平、家族谱系散见史书记载,且多有龃龉之处,作者据所见《颜鲁公题名》、《颜氏家庙碑》,并结合留元刚《颜真卿年谱》、因亮《颜鲁公集行状》、令狐峘《颜真卿神道碑铭》,及唐史记载,制作颜真卿家谱,表而出之,并逐年考证了颜真卿仕历,对于颜真卿研究极有学术价值。同时,对于史书和碑刻记载不同之处,作者通过精彩考辨常能纠史之谬。如关于延唐寺,《唐会要》载,寺本名万善,为会昌六年奏改。作者则据《安国寺寂照和上碑》于开成末即称延唐,指出了《唐会要》的记载错误。
毕沅亦精通音韵之学,运用到此书碑刻考订中,时见精彩。如《舍利塔铭》条:
文云“京兆府大兴县御肃乡便子谷至相道场,建立佛舍利塔”,御肃乡即御宿川也,古肃与宿通。《祭统》“宫宰宿夫人”,注宿读为肃;《少牢馈食礼》“前宿一日宿戒尸”,注宿读为肃;《特牲馈食礼》“乃宿尸”,注宿读为肃。古文宿皆作羞,凡宿或作速,记作肃,《周礼》亦作宿。案肃与宿通,宿又与羞通,然则汉时所谓御羞苑者,义与御宿亦同矣。
从汉代的《三秦记》、《汉书》开始,史书的记载中多见“御宿”,在今长安县内,“御肃”之名目前仅见于此铭,毕沅则引《周礼》中“肃”、“宿”二字互通,而证“御肃”实即“御宿”。
毕沅此书的学术价值又不仅仅局限于以金石证史。道光年间曾校刻此书的蔡锡栋说:“且其为书,有考证史传以判得失者,有厘订文字以辨形体者,有研究反切以正音读者,旁通曲证,又不仅以金石见长也。”③此书中《篆书千字文》条,一一辨析碑字字体与古字书体不同之处,指出俗体之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条,因释家书经所用某些字历代有所不同,毕沅一一注音并标明今之读音。
另外,此书所录很多碑刻今已漫漶不存,多数为首次著录,虽然大多为后出之《金石萃编》全文收录,且后出转精,后者例来被视为清代金石学集大成的著作,向为后人所重,对于保存史料为功更大,但仔细比对两书所录同一碑刻,多有文字相异之处,如《汉中太守鄐君开石门道碑》,今存碑已多处漫漶不清,一百余字中,《关中金石记》与《金石萃编》所录有五处文字不同,有的是字形接近,有的则差异很大,如《关中金石记》所录“部掾治级王宏史、荀茂、张宇、韩岑第其功作”句,“其”字《萃编》录作“典”;“凡用功七十六万六千九百□□”,“九”字《萃编》录作“八”。因原刻已漫漶,两书所录都很有校勘价值。
三
此书的考辨也有疏忽之处,在此书撰成之后,清代学者已经对其出现的讹误进行了指责。如《内侍李辅光墓志》:
元和十年四月立,崔元略撰文,巨雅正书,在高陵。
碑云辅光为河中监军使者,盖监张宏靖军也。巨雅,元略之弟,巨雅曾为晋州司法,元略又官于中都,故撰书此志以记功德。
关于此志的书者,卢文弨在《抱经堂文集》中考辩说:“巨,姓也,后汉时有汉阳巨览,为梁商掾吏著名。碑云:‘门吏晋州司法参军巨雅,以元略长兄尝宾于北府,以元略又从事中都,俱饱内侍之德,见托为志,勒之贞石。是元略自言因巨雅之迁而作也。《关中金石记》乃云……,大误。”[1]213
今按此碑文所云北府,当和朝臣办公在皇城之南的南衙相对而言,指居于皇城北面、宦官之内侍省,据《李辅光墓志》,李辅光于德宗朝历奚官局令、掖庭局令、内寺伯等,“元略长兄尝宾于北府”句,以北府借指李辅光。又据《李辅光墓志》,李辅光终河中监军使,而河中府开元年间曾置中都,“元略又从事中都”句,又以中都借指李辅光。因此碑文是说崔元略及其长兄均曾与李辅光有旧,因此嘱托李辅光门吏巨雅为书此志,巨雅非崔元略之弟明矣。毕沅此处读志显然有误。
岑仲勉也曾指出《关中金石记》中题跋的多处讹误,如《郃阳令曹全纪功碑并阴》,毕沅认为曹全即曹宽,全与寛通。岑先生指出其误:“毕氏谓“全”与“宽”相通之误,其论曰:惟谓全宽相通。就字行文义而言,均难厥证。考碑云:‘君讳全,字景完,意传者误传其字为完,完、宽形似,先讹完而再讹宽也。”[2]48当以岑先生所论为是。
此外还有学者对此书所收金石碑刻的年代排序提出过指责,道光年间蔡汝霖校本所作的校勘工作主要就是针对这个问题。下面就笔者在校勘此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分论此书存在的讹误。
1.考述有误,如《芮定公碑》:
永徽元年六月立,李义府撰文,正书,无姓名,在醴泉西谷村。
芮定公者,豆卢寛也。《唐书·钦望传》,祖寛,高祖初擢殿中监。子怀让,尚万春公主。贞观中迁礼部尚书、左卫大将军、芮国公,卒赠特进、并州都督,谥曰定。此碑额题曰“唐故特进芮国公”,与史所称正合。文甚泐,赵氏《金石目录》以为义府所撰,当无误也。
豆卢氏,本慕容之后,有名苌者,于魏封北地王,始赐此姓。《元和姓纂》云,慕容连,北地王之后。
首先,此条节引《旧唐书》不当,致文意不清。《旧唐书·豆卢钦望传》原文为:“祖寛……髙祖定关中……累授殿中监,仍诏其子怀让尚万春公主……贞观中歴迁礼部尚书、左卫大将军,封芮国公。永徽元年卒,赠特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谥曰定。”“贞观中”云云乃指豆卢宽,非其子怀让。
其次,关于北地王的考述有误。其一,关于北地王,据《晋书》、《北史》、《隋书》等先后有后燕慕容精和南燕慕容钟,豆卢氏为何者之后,史书记载多有抵牾之处,无从确考,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豆卢条有详细辨析,可参看。另,史书记载尚有一北地王后汉刘谌,与豆卢氏无关。其二,据《北史·豆卢宁传》,豆卢宁“父苌,魏柔玄镇将,有威重,见称于时。武成中,以宁勋追赠柱国、大将军、少保、涪郡公。”苌并无封北地王事。其三,据史书记载,后燕亡后,公卿多归北魏。而豆卢氏来源,据《北史·豆卢宁传》,豆卢宁“髙祖胜,以燕皇始初归魏,授长乐郡守,赐姓豆卢氏。或云北人谓归义为豆卢,因氏焉。又云避难改焉,未详孰是。”三种说法各异,但都与燕灭于魏这一历史背景有关,当非毕沅所说始于“有名苌者,于魏封北地王”。其四,说“慕容连,北地王之后”亦为舛讹。考《元和姓纂》“慕容”、“豆卢”条,均无慕容连其人。而“豆卢”条云:“本姓慕容,燕王廆弟、西平王慕容运孙北地王精之后。入魏,北人谓‘归义为‘豆卢,道武因赐姓豆卢氏。精生犹丑,犹丑曾孙苌、永思、宁。宁生绩……永思生通,通生寛,唐礼部尚书芮定公。寛生承业、怀让。”与“连”形近者只有“运”字,然运非北地王之后,却是始封北地王者慕容精的祖父,“连”或为“运”之讹。
又如《金仙长公主神道碑》:
号年缺,徐峤之撰文,明皇行书,在桥陵。
《唐书·本传》云:“太极元年,与玉真公主皆为道士。”碑云:“丙午岁,度为道士。”丙午岁者,神龙二年也,两说不合。
按,此处所谓“两说不合”事,据现存《金仙长公主志石铭(并)序》,墓志刻于开元二十四年(736),神道碑当建于同时。墓志称其“年十八入道,廿三受法”,薨于开元二十年(732),年四十四岁。可知公主神龙二年(706)年十八岁入道,是时并未正式接受道箓,到景云二年廿三岁时才正式受法度为女冠。又毕沅所引《旧唐书·本传》后仍有一句“筑观京师”,筑观事,《唐会要》卷五十载“金仙观,辅兴坊。景云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睿宗为第八女西宁公主入道置。至二年四月十四日,为公主改封金仙,所造观便以金仙为名。”按,此处西宁当为西城,从景云元年(710)十二月睿宗下诏为二公主建造宫观,不惜巨资,工程浩大,直至三年(712),即太极元年仍未完工,期间大臣纷纷上疏谏止,景云二年有右散骑常侍魏知古、左补阙辛替否,到太极元年春仍有中书舍人裴漼、太傅少卿韦凑等进谏,睿宗终于是年四月下诏停修。则二公主正式入观修行当在景云二年年底或太极元年初。因此,碑所云神龙二年当指金仙长公主入道之年,而史书所云太极元年当指其接受道箓后正式入观修行之年,二者并无不合。
再如《诸葛忠武侯新庙碑》:
贞元十一年二月立,沈逈撰文,元锡正书,在沔县。
文称“贞元三年,府王左仆射、冯翊总师”者,谓舒王谟为荆、襄、江西、沔、鄂节度诸军行营兵马都元帅也。锡字君贶,见《世系表》。
此处所引碑文原文作:“贞元三祀,时乘盛秋,府王左仆射冯翊严□,总帅文武将佐,洎策轮突归之旅,疆理西鄙,营军沔阳。”修庙之人“严□”,名已磨泐,后人有补刻此碑者臆补为“武”,清初以来所修地方志多承其说,清康熙六年重修之《陕西通志》“诸葛武侯庙”条即载此碑为严武所修。毕沅否定严武之说,定为舒王谟,不知何据。稍后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三是碑条,首先对严武之说进行辩驳,认为两《唐书》未载严武有“左仆射”之职,且严武卒于永泰元年,不应贞元三年仍在世,此碑非严武所修无疑;同时又对毕沅之说作了辩驳,认为舒王“为沔鄂节度,在李希烈反之时,正贞元三年事,宜乎合矣,而亦未尝有左仆射之官,且与“冯翊严口”亦无着。希烈之乱在淮蔡,舒王漠为节度在沔鄂,即今湖北汉阳州,非陕西汉中府之沔县,则《关中金石记》亦不确也。”王昶之辩极是,修庙之人为谁,目前尚无其他史料可确考。今人陈显远根据史书记载,考其为严震,认为严震自唐德宗建中时期至贞元十五年一直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沔县为其所属,修庙为理所当然。[3]可备一说。
2.读碑有误,如《赠安定郡伯蒙天佑新阡表》:
延佑五年九月立,萧□撰文并隶书,篆额,姓名缺,在大荔。
碑题云:“知船桥兵马都总管万戸府奥鲁、千戸、赠朝列大夫、同知晋寜路总管府事骑都尉、安定郡伯蒙君,讳天佑,字佑之。”盖蒙君官至总管府万戸,以子怀□贵,得赠官如之也。子封安定郡伯,职亦不卑,而史传莫可考,特以惟斗文传之耳。碑甚磨泐,不可读。
万户、千户,均为元代军职,万户总领于枢密院,掌管各种军职,千户仅次于万户。知船桥兵马都总管万戸府,当为掌管船桥兵马的军事机构,据《元史》,睿宗时张万嘉努即曾任“河东南北路船桥随路兵马都总管万户”。奥鲁,元代在万户、千户下设奥鲁官,管理当役军士族属事务。据碑题,蒙氏官至万户府奥鲁、千户,非总管府万户,毕沅此处读碑有误。
3.抄录有误
如《李元谅懋功昭德颂》条,所录碑文有“北连绎台,南扺黄巷”句。按绎,《陕西通志》卷九十收《李懋功昭德颂》作“绛”。史书未见有“绎台”。绛台,《后汉书·冯衍传》引冯衍《显志赋》有“馌女齐于绛台兮”句,注曰:“绛,晋国所都,《国语》晋平公为九层之台。”可知绛台在绛州,今山西新绛。碑文此句作:“李怀光阻河拒命,窃弄戈鋋,北连绛台,南抵黄巷,选朔方之健将,保朝邑之离宫。”黄巷即黄巷阪,《元和郡县图志》云:“黄巷阪在县(虢州阌乡县)西北二十五里,即潼关路也。”据《旧唐书·李怀光传》载,泾原兵变时,李怀光率朔方军自蒲津关渡黄河,败朱泚于醴泉。蒲津关在朝邑县西南,东北为绛州,东南为潼关,正处于所谓的“北连绛台,南抵黄巷”的位置。《唐大诏令集》卷六三收《赠郭子仪太师陪葬建陵制》评价郭子仪平泾原兵变时亦有类似说法:“绛台绥四散之众,泾阳降十万之虏”。此处“绎”当为“绛”之形近而讹。
另外,此书还有引书不确的问题,如《九成宫醴泉铭》引《唐书·地理志》考仁寿宫,所引文字实出顾炎武《历代帝王宅京记》。
注释:
①蔡汝霖字雨田,渭南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中举人,同治元年(1862)进
士,官直隶知县。著有《古今丧礼》。蔡锡栋,字福堂,生平不详。焦兴儒,
字子珍,亦渭南人,生平不详。
②严岳莲,字雁峰,渭南县孝义里人。严氏幼年好学,遍读经史诗词,屡试不中,
遂淡于仕进。后致力经商,为蜀中大盐商。出巨金收集海内外精本图书五万余
卷,筑贲园书库以藏。
③道光二十七年蔡氏校本序。
参考文献:
[1]卢文弨.抱经堂文集[M].王文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2]岑仲勉.金石论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陈显远.勉县武侯祠庙碑初考[J].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84(4).
作者简介:李向菲,女,陕西临潼人,西北大学博士后,西安文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
(责任编辑:李直)
基金项目:陕西省“十二五”古籍整理重大项目子项目(SG13001·史S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