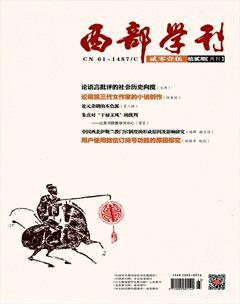个体化背景下中国乡村整合问题刍议
摘要:个体化的理论与现代性的理论是相伴而生的。中国在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在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出现了社会结构的个体化现象。在压缩现代性中完成的乡村个体化,对乡村建设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因此,要着力完成乡村伦理和生活的重构,重建乡村公共空间,活跃乡村公共生活和文化生活,实现对乡村的重新整合,使乡村社会成为互助友爱的共同体。
关键词:个体化;乡村个体化;乡村整合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个体化的理论缘起
在当代社会思想中,个体化议题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个体化理论的研究发端于国外,是自反现代性理论的一部分。“个体化”作为自反现代性的后果,他必然继承了自反现代性的特征,即一方面,个体渴望展现个性、追求自由,努力“为自己而活”;另一方面,为了应对社会风险,个体不得不向社会制度寻求依赖。贝克认为,现代化导致一种三重的“个体化”:“解放的维度,即非嵌入性,个体从历史规定的社会形式和传统语境意义上的义务中脱离出来;祛魅的维度,指与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规则相关的传统安全感的丧失;控制或重新整合的维度,个体再嵌入到一种新形式的社会义务与规则中。”[1]156可见,贝克的个体化包含着解构和重构两个方面,个体化是个体在“人的解放”过程中不再“被他人所决定”而进入“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过程,个体的重要性得到更多尊重与关照,但与此同时个体也被迫四处寻找可以重新嵌入的制度和组织。
与现代化发展相伴随而生的个体化社会中,当代一些社会学家在关注社会中个体重要性增加的同时也关注着个体如何从传统社会和道德中脱嵌,由此“抽离”一词成为社会学家研究个体化理论的重要概念。吉登斯认为“抽离”是指时间和空间的分离,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点[2];贝克认为的“抽离”是指个体从束缚它的社会群体中脱离,变成独立的个体来行动 ,[3]我们可以理解为解传统;鲍曼则用社会的流动状态来指称这种“抽离”。[4]
总之,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维度来解读个体化,但他们依然能够达成共识,他们都认为个体化是个体愈来愈从外部的社会控制中抽离,“是个体主义解脱共同体束缚的过程,是对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反叛。”[5]在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社会结构的个体化已成为高度分化社会的结构性特征。
二、个体化的中国表达及乡村个体化之路
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理论日益汇聚到我们的视野中。在世纪之交以后,集体所有制的消解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变革,我国的现代化迅猛发展,社会的新陈代谢加快,此时的中国社会加快了社会个体化的步伐。个体化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很多西欧社会的个体化现象“去传统化、脱嵌、通过书写自己的人生来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6]324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同样都会发生。但由于中西方现代化发展道路不同,中国式的个体化进程有其独特性。中国的现代化是“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必然与发生在西方社会第二现代性下的个体化不同。西方的个体化浪潮带有自反现代性特征,而中国的个体化处于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多重时空压缩并存的时代,它的进程是受传统、现代和后现代各种因素的影响,所以中国式的个体化与西方国家个体化的路径和逻辑是不同的。
(一)当代中国个体化的表征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不是单纯的复制西方个体化的路径,而是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前提条件,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中国式的个体化”。从社会整体来看,在西方,个体的抽离是为了寻求真实的自我。在中国,个体的抽离受到了国家制度政策的影响,中国的个体化进程是有国家划定的界限和规范来管理的。1978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逐步放松了对个人的控制,使个体的解放出现了新契机。在农村,随着强势国家的退出,个人从村集体的社会主义机构中解放出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个体意识大大增强。在城市,随着国企改革和城市住房制度的调整,单位不再是个人的全部所属,人们开始重新定位自我,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有了清晰的权界意识。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社会从集体时代跨入到了个体化时代。进入新世纪,原有的社会关系网伴随着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和社会流动的加快变得日渐式微,集体对个体的松绑将个体从集体主义的阵营中推向了更广阔的社会,催生个体从承受者向责任者转型,国家对个体的快速松绑使得越来越多的个体在个体化的冲击下面临更多的风险。
从个体来看,在集体所有制日渐式微和单位制日渐消解的情况下,计划经济条件下存在的“组织化的依赖性”近乎荡然无存,个体的稳定和福利随之变得不确定了。给个人松绑“个体的自由度和选择机遇空前增加;个体倾向于把个人目标的追求至于集体目标之上”,[7]“过自己的生活”成为越来越多今天中国年轻人的信条。在个体化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的流动加速,个人作为一个拥有自身权利的独立个体而存在,不再是镶嵌于共同体之中的一个个相互关联的分子,个体不得不独自面对极具竞争性和淘汰性的市场。
(二)中国乡村个体化之路
在中国乡村,个体化历程同样是在压缩现代性之中完成的。随着乡村社会个体化的发展,乡村家庭逐渐从大家庭变为核心家庭,“现代社会的个体不再愿意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相反,他们都通过家庭的运作来寻求自己的利益和快乐”。[6]11乡村社会流动性的空前增加,使得乡村中乡民卷入了大规模的外出务工潮,伴随而来的却是乡村“空心化”和“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乡村问题的出现。随着市场经济对乡村的进一步渗透,“乡民越来越执着于个体经济利益,超越家庭层面的联系与合作越来越少”,[8]长期以来聚集村庄凝聚力、体现乡民之间感情的乡村互助网络日渐消解,乡村村民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漠,“无功德个体”出现。日渐个体化的乡村社会使得原有乡村社会交往网络出现断裂,村民逐渐由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最后走向“他者”的社会。在乡村个体化背景下,乡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同时,乡村的公共文化生活却日趋消退,乡村出现了公共文化生活的“真空”。
中国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使得乡民们从传统乡村的共同体中脱离出来。但由于我国现阶段乡村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健全,脱离出来的乡民在强大的市场经济面前却不能够重新嵌入到市场经济语境中,使他们处于断层面上。当个体面临社会问题时,他们不再向社会寻求根源,而只能向个体寻找答案,这便导致了贝克所说的“组织化的不负责任”现象的出现。乡村个体化之路使“个人逐步从宗族、阶级、集体的束缚性群体性关系网络抽离出来”,[9]个体在传统乡村安全网日益消失的情况下不得不独自面对脱离而带来的社会风险。
中国乡村的个体化乡民们有着强烈的脱离动力,这源于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使个体化承载了先在的不公正,乡民们无论在集体主义时代还是改革时代都未被整合进入国家基础性福利制度,在社会责任迅速隐退的过程中,个体必须独立依靠自己以保障自己的生存和福祉。乡村个体化社会中,随着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影响,乡民纷纷离开村庄,去寻找自我发展的机会。
三、乡村社会个体化下整合的对策
国家推动了乡村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但是意外后果却是带来了乡村共同体的解体,没有共同体精神作为基础的乡村,使乡村建设失去了社区性资源的支持,对乡村建设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近几年在农村社会出现的孝道衰弱、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事件不断上升,人们越来越原子化、功利化;同时伴随着乡村社会的伦理规范日渐解体,乡民精神信仰缺失、权利义务边界意识模糊,许多人变为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无功德个体”。乡村社会在国家不断地赋权和市场经济及消费主义的渗透下,乡村治理处于困局中。这要求我们在个体化的背景下,重视乡土的重建,要着力完成乡村伦理与生活的重构,重建乡村公共空间,活跃乡村公共生活和文化生活,实现对乡村的重新整合,使乡村社会成为互助友爱的共同体。
重建乡村公共空间。乡村社会的个体化中,脱离出来的个体重新嵌入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乡村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是乡民生产生活的主要场域,乡村公共空间依旧是规范乡民言行的重要载体,是乡民规避社会风险的避风港。在乡村个体化社会背景下,人和人之间出现的原子化、疏离化以及人们对公共事物的漠不关心等现象呼唤着乡村公共空间的重建。在乡村社会个体化的作用下,乡村社会已经走上了不可逆的道路,重建乡村公共空间并非是简单线性的回归,而是要符合现代性的特点,以实现对乡村的整合。
加强乡村公共空间的建设核心是“公共性”的再造。在个体化的乡村社会,公共性的构造主要体现在“集体所有制”消解过程中,“公共性”的再造问题。个体化背景下,高度合一的总体性社会已经过去,以“政府”为主体的传统公共性转变为多元的“新公共性”。在个体化的趋势下,公共性的社会交往成为每个个体都无法回避的生活方式,人们开始意识到着力建立独立于国家、市场以外的社会支持体系的重要性,这种公共性的建设可以让人们发出面对生活的呼声,可以保障个体追求私人空间与权利的自由。“新公共性”的构建,把原子化的人群重新组织起来,使个体在面对社会急剧变化时,能够从整体和发展的角度审视自己与他人、自己与团体、自己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至失掉方向感和生存的力量,避免“无功德个体”的出现。
重建乡村公共空间要加强对乡村社会组织的培育。在乡村社会个体化的发展趋势下,乡村社会组织为乡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有效地整合乡村各种社会资源,促进乡村发展,传承乡土文化,使得乡民有机地生活在一起。同时,乡村社会组织也是乡民参与乡村事务的重要平台,使乡民达成一定范围内的共识,促进维护乡村社会的公平和稳定。因此,乡村社会组织的充分发育能够为乡民重新嵌入乡村共同体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发展乡村社会组织,要创新乡村社会组织形式,适应乡村个体化发展的要求,建立现代化乡村社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乡民的不同需求,这对改革开放后由于国家权力隐退而导致的乡村安全网络的空缺能起到一定的填补作用,有利于增强乡民对乡村共同体的认同感。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有必要重视培育乡村社会组织,以重构乡村社会的共同体精神。
重建乡村公共空间的重点是加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个体化背景下,随着市场化和消费主义对乡村传统文化的解构,传统道德的碎片化,乡民行为的功利化,使得乡村原有的共同体遭到破坏。增强乡村文化的公共性,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公共文化活动,开展集体性文娱活动,将平时来往不多甚至不来往的乡民聚集在一起,培育乡民的乡土情怀,重塑乡民间的互助精神,增强彼此间的信任感和互助感,消解乡村社会个体化出现的“功利化”、“原子化”现象,以此增强乡村共同体的凝聚力;同时要培育新乡村文化,促进乡村共同体文化上的整合,积极发展和谐乡村文化,提升乡民的幸福指数,以此唤醒乡村记忆,重建乡村认同。
参考文献:
[1](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傅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2]Giddens A.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M].Taibei: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1999.
[3]Beck U, Beck G E.Inidividualization: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and it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M].London and Thousand Oaks,CA:Sage Pubication,
2002.
[4]Bauman Z.The individualized society[M].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2003.
[5]文军.个体化社会的来临与包容性社会政策的建构[J].社会科学,2012(1).
[6]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M].陆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7]冯莉.当代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趋势及其政治意义[J].社会科学,2014(12).
[8]张良.乡村公共性解体与基督教文化发展[J].人文杂志,2014(3).
[9]徐勇.阶级、集体、社区:国家对乡村的社会整合[J].社会科学战线,2012(2).
作者简介:孙静,女,山西太原人,硕士,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理论社会学。
(责任编辑:李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