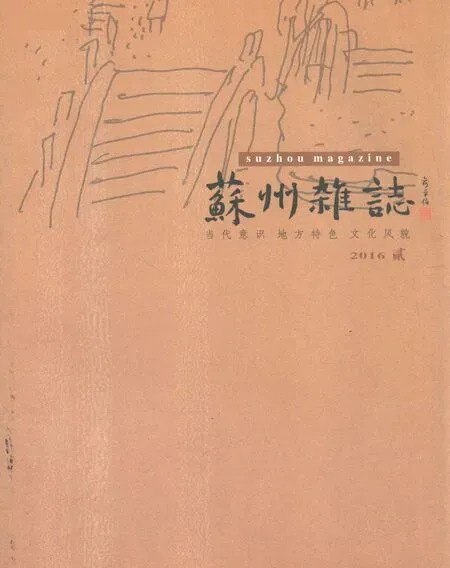重访苏城
朱秉璐
重访苏城
朱秉璐
我出生在昆山,长成在苏州,1932年随父母从昆山迁居苏州。我父亲朱豫凡祖居昆山,之所以迁居:一是受“一·二八”战争影响,二是不堪两个不肖侄辈的偷盗骚扰,三是与苏州律师周子敦共同组建起一个律师事务所。出于既适合做律师事务所又可作住家的考虑,选中了西美巷33号况公祠北邻一处宅子租住,租金大洋26元。在那个年代,这个价位算是比较高的。
这宅子的格局不同于巷内其他住宅,大门比况公祠缩进近两米,可以放两部黄包车,平日里白天大门是开着的,只关二门,常有邻居小孩在大门内嬉戏,突下急雨时也常有行人进大门内躲雨。大门与二门北侧一间房屋请一位门房老头在此居住。二门廊沿进去是一个碎块石板铺地的天井,北侧石板缝中,每到夏秋生长着一大片鸡冠花、凤仙花和夜繁花,东南角半圈L”形的矮墙,内置一缸,充作公用小便池。再进去是一个三开间大厅,中间一张可坐十人长条会议桌,四周靠墙各放桌椅可坐八人。厅内侧一排到顶木(习惯称之谓“平门”),平门只开一扇门,进去一道内廊,北端是堆放柴火稻草所在,南端装有一部电话,属事务所所有。从南端第四道门(习惯称之谓“库门”)进去是一个大大的院子,这在苏州普通民宅中是不多见的。院内房屋呈侧过来的“?”字形,靠近库门南侧单独一间是事务所两位律师和一名书记办公所在,北侧一条有顶敞廊由东一直延向西端,廊内侧一排五间住房统统北朝南。顶西端折向南又是两间房屋,外间占三分之二是厨房,内间为女佣卧室。那时,一般民宅每进主房朝向都与大门一致的,像我们这所宅子,大门朝东而内里朝南,这也是少有的,可见当时建筑设计者的匠心独运。
周子敦出身苏州望族,是我父亲的老友,两人合办律师事务所,用现时话来说含“扶上马送一程”之意,当事务所业务正常展开之后,周子敦便到威海卫法院任法官另谋发展去了,事务所虽然挂两人牌子,实际上由我父亲一人独撑。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由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业务大受影响,不得不陆续撤去门房、拆除电话、辞退女佣,转租出两间住房,紧缩开支,维持生计。
院内有一口井,供全家生活用水所需,每到盛夏,它还起到准冰箱的作用,用网兜吊个西瓜在井里,下午取起全家享用,凉爽而不冰牙,胜过如今在冰箱中冷藏的。井并不很深,不过两根多竹竿的长度即可见底,但从未枯竭,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某年苏地大旱,况公祠大门外北侧原有一口公井都曾枯竭无水,独我家的井未受影响,被全家人称之为“宝井”。我在院墙边扦插了一棵“十姊妹”,成活后长成高高一丛,每年春季都开出许多鲜艳粉红花朵。又在院中种了一棵水蜜桃,长成小树后,每年也都能结出几个毛桃。物价开涨以后,我母亲每年都要在院西边点种几株南瓜,用草绳牵引攀缘而上爬向屋顶,每年都能收获几个甜甜大南瓜。在院东侧点种了一片毛豆,虽然通风不良,结实不多,居然有小小的田园风光。住房后有一条狭长的露天夹弄,西头矮墙外就是县政府的后园,夹弄西边长满了蝴蝶花,盛开蓝色花朵。在夹弄中间部位墙边我种了一棵黄天竹,每年都结出许多供观赏的黄红色果实。东边一侧则是一溜小坛子,母亲每年都腌上若干坛“春不老”,夹弄门内一口大缸,则是每年必备的自腌雪里蕻和白萝卜条,我们都是生吃,香脆咸酸,至今回想起来,尚令人馋涎欲滴。虽曾仿制,但总不及母亲腌制的鲜美可口。
县政府后园的一棵高大梧桐树,可能已有多年历史了,就在我家房屋附近,夜间有众多乌鸦栖集其上,每到傍晚乌鸦归巢,噪聒不休,成为一道独特风景。不知那一年,可能是鸟类在大院墙边落下一粒梧桐籽,不经意间长出一棵小苗,我离家时还只有一人高拇指般粗,不想十多年后回家探亲,它已长成参天大树,绿荫满院,恰可遮夏日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公私合营高潮中,宅子为房管部门接收,宅内被支离分割住进了五户人家,一户一只煤炉,烟熏火燎,房屋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但在我记忆中,它还是原来的美好模样。
我从1932年住进这所大院,历经民国——沦陷——光复,小学、中学、大学三个阶段,到1948年初冬离开苏州进入解放区,凡十七个年头。我父母亲仍在这里居住,直到1963年父亲终老。之后,小舅又在此居住到1979年秋。其间,我不时归来探亲稍住,宅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莫不留下我的深刻印象与深厚感情。2010年秋,我以八十三高龄在子女陪护下,作怀旧之旅,重访旧屋,西美巷33号虽然位置还在况公祠北邻原处,但已变成临街浅浅两间房屋。已成苏州市会议中心下属物业公司的一个设施设备服务中心,我进去坐下休息片刻,两位办公人员听说我是这里几十年前旧住客,热情招呼、倒水招待,因他们都在忙碌,不便久坐,告辞而去,再寻访后边旧居所在,发现原来的房屋庭院、树木花草、水井、邻舍等等都已茫然无存,深挖数米,变成一个硕大的地下停车库。目睹此情此景,一种世事无常、沧海桑田的伤感不禁油然而生。从此,旧屋景象只能在梦中重现了。
旧屋,用苏州方言来说,就是“格辰光曾经住过格场化”,它是平头老百姓对较长时间居住过地方的一种称呼与回忆。不按通常习惯之谓“故居”而称“旧屋”:第一,“故居”两字一般是已逝历史名人、有大贡献大作为的历代高官、达人才适合用的,我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干部、无名小卒之辈,我父亲虽然在当时苏城律师界小有名望,但离历史名人还有很大距离,不敢妄称。第二,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2010年重访苏州,因探望亲戚途经一小巷,忽见一民宅悬挂着某原籍苏州、曾是香港艳星、现今当红、年不过四十多岁的“xxx故居”金字匾牌,既惊奇于尚未有定论的活人而称故居,又惊诧于文物部门居然也会有追星媚俗之风,不屑于随俗自捧。这也算是一己偏见,题外之话。还是回到本题。
当初我父亲选择居住西美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离我母亲的娘家和亲戚都比较近。我外祖家就住侍其巷6号。外祖父费清和去世后,由我大舅费景旦居住,因他无子认我作寄子。幼年,每逢周日母亲就把我送舅家盘桓一天。因此,县前街(现统称道前街)、司前街是常经之路。那时,县前街南侧比北侧热闹,北侧印象最深的是,温泉浴室和店背后的一个有蓬大菜场(县政府大门边和善良巷两个口子出入),南侧从西馆桥往西,先是顾客众多的云苑茶馆,楼下书场,楼上喝茶。过去几个门面一家羊肉汤店,老远就能闻到扑鼻香味,虽陈设简陋、季节性供应,但座上客常满。再往前有一家高中同学唐亮兴家开的南货店。现今南侧店铺已全部拆除,改造成临河绿化带,唐亮兴亦已作古矣。
司前街那时住宅居多,堂大舅就住在这条街上,因其在上海银行界工作,极少在苏,我们去的次数不多。留给我难忘印象的有以下几件事:一是司前街与县前街交叉口西侧那家老酱园店,因其门楼式样朴实古老,与众不同,使人过目不忘。二是司前街中段西侧那所监狱,内设有一个由犯人组成的缝纫工场对外营业,因其手艺好、价格较廉,我母亲常带料去为家人做衣裳,我也常跟进去玩。三是在我家还未迁苏时,某年外祖去世,母亲带我回苏奔丧,坐黄包车行进在司前街上,或许因车夫体衰乏力,突然脱把,母亲和我都仰天跌落车内,车夫吓得连声道歉,把我们扶起。小小年纪受到如此惊吓,自然难忘。
侍其巷与司前街丁字相交,巷内也大多是住宅,当时往西可直通老胥门万年桥,交通便利,母亲的祖宅也是四扇门的大门,进门一个天井,两侧各一间东西厢房,然后是一幢两层楼,楼下大厅正面一个香烛长台,供奉着外祖遗像,楼上住人,隔着楼板楼上人用马桶之声清楚可闻。父亲笑说:这就叫“隔层楼板隔重天”!转入厅后又是一个天井,进去还是两层楼房,楼下是饭堂、厨房和柴间,楼上前后相通,可住两户,相当宽敞。
写到此处,不由得不想到1937年8月抗战初期,日寇首次轰炸苏城的情景,那天是我读完小学四年级的暑假中,我正好在大舅家,晚饭后不久,忽然警报大作,飞机声、机枪扫射声、俯冲轰炸声接踵而至。在大舅指挥下,全家人都钻进楼下一张大铁床下躲藏起来,每当机枪射房顶瓦裂如在耳边响起,或炸弹落在近处震得地动房摇时,老好婆不住颤声念阿弥陀佛、救苦救难观世音。祈求菩萨保佑。直到警报解除才从床下出来。第二天,我家和舅家就相约一同出城逃难去了。国耻是永生不会忘记的。
大舅本是中学英语老师,沦陷期间因学校被迫改授日语,不得不另谋出路,到上海统一纱厂当一名职员,开始每到周末在沪苏两地间奔波。抗战胜利后,因大舅身体不好,全家迁居上海方便照料。把祖屋卖得十几根金条与小舅费焕成分享。小舅会计专科毕业,本是民国政府财政部一名普通职员,抗战期间随部西迁,胜利前夕,因性情孤僻,在整编减员中被解雇,爱情又失败,胜利后孤身一人落魄买舟东归,多方谋生一事无成,就靠这点金条和大舅等亲戚接济维持余生,这是后话。2010年回苏,途经侍其巷,外祖家老住屋已不存在,那一片已全部变成商店,面目全非了。现在大舅夫妇和我母亲均已相继去世,只有我保存着的大舅夫妇摄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照片,和我兄妹弟三人与表妹们摄于三十年代的两张老照片可作唯一纪念了。
前面说到,在抗战初起日寇飞机夜袭苏城,我们在大舅家床下躲着时,听到的那个地动屋摇的轰炸巨响,事后才得知炸弹就落在舅家后面复兴桥一所带花园住房几进的富家大宅上。具体位置在司前街与侍其巷交叉口往南几步过桥往西,又过小桥,一条小巷由此沿河往南,巷西侧就是这大宅。年余后恰巧我的堂兄携妻儿转辗逃难来苏,经熟人介绍就免费住在已成一片废墟,仅存的被称作复兴桥1号、河边两间经略加修缮的简陋小屋安身。当时,在遍地碎砖瓦砾中还可翻寻到一些残存的小器皿之类。堂兄是一位老资格的小学教师,一生耕耘育人,大半生贫困挣扎,解放后地位、生活才逐步改善,教学上多次受到表扬,惜乎因积劳成疾,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过早离世。所遗两子一女各有所成,奉母迁居。这次重访途经该处,已为一片新楼所替,昔日轰炸遗事已少人知道了。
我堂小舅费子章(伯外祖费玉如之子),留日医学博士,昔日苏城小有名望的内科西医,抗战前家住大太平巷乌鹊桥附近,与其内兄华医师合办的济民医院则在护龙街东中市附近。我之所以上三元坊的省立实验小学开始读一年级,就出于他的推荐与鼓动,入学测试就是由堂小舅母陪同前往的。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堂小舅和其内兄在阊门外在原三六湾买了一块空地,建成一个院落,大门内若干平房是济民医院,内里两幢独立又靠近的两层小洋楼,分别作为华、费两家住房。这在当时苏州不多见的。迁居后,母亲曾带我们去过,但毕竟路远,交通不便,来往就少了。堂小舅也于抗美援朝期间中风去世。
我堂大姨母费绛霞(伯外祖费玉如的大女儿),抗战前一直随其夫吴维清(武汉大学创始人之一、数学教授)长住武汉。抗战前夕教授积劳成疾去世,除两位年长女儿在大后方求学外,大姨母率四位年幼子女回到沦陷中的苏州,与其父合租庙堂巷靠近剪金桥巷附近的一幢二层小楼居住,相互照应。因她的推荐,我的小学五、六年级就同四表姐吴美真在剪金桥巷的升平小学读完的。表弟吴贻康也在该校就读,比我们低两班。因此常有走动。更因费玉如(原是知名律师,曾任苏州律师协会会长)是我父母的婚姻介绍人,父母常去问候,故来往颇勤。沦陷后期,费玉如老病去世,抗战胜利后,姨母大女儿吴安真返苏州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助教,因其解放后与江苏省第一任宋姓教育厅长结婚,姨母随其迁居南京,并终老于南京。去年重访升平小学,她们住过的小楼也已不复可见。
住在西美巷附近的还有一些亲戚,但写到这里时儿子回来了,问我在写什么?我把未完稿递给他看,他看毕笑着说:老爸,你真的是老了,主要是心态老了,怀旧、恋旧、伤感,这是老人的通病,沧桑变化正说明时代有进步,经济在发展,生活正提高,日子越过越好,应该高兴才是,何伤感可言?对他的话我并不完全苟同,想想也有一定道理,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