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炼”永无止境
许志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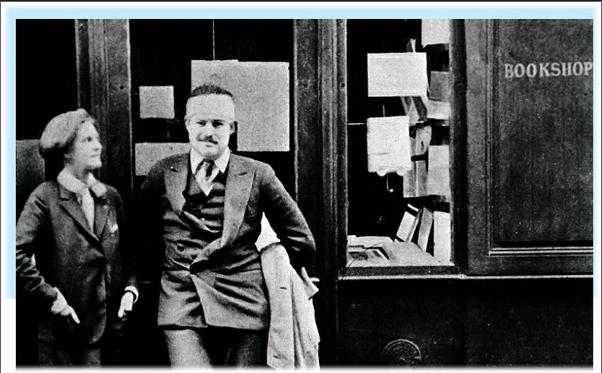
一
读比拉-马塔斯的《巴黎永无止境》(尹承东译),正好也在读扎加耶夫斯基的《自画像》(黄灿然译)以及刚出版的海涅的《佛罗伦萨之夜》(赵蓉恒译),看到那些不同时代、不同国籍的诗人,拿起笔来都要情不自禁地提到巴黎,赞美巴黎。
波兰诗人说:“我喜欢在巴黎街头长时间散步……”德国诗人说:“巴黎使我十分高兴,这是由于它那欢快的气氛……”而西班牙作家说起他的“喜欢”来,用上一连串排比句:“我喜欢巴黎,喜欢福斯坦堡广场,喜欢弗勒吕斯街二十七号,喜欢莫罗博物馆,喜欢法国诗人和随笔作家特里斯坦·查拉的陵墓,喜欢纳德哈街的玫瑰色连拱柱廊,喜欢‘抽烟的狗酒吧,喜欢瓦什饭店的蓝色正面墙,喜欢码头上的书摊……我对巴黎所有一切都是如此地喜欢,以至于这座城市对我而言永无止境。”
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把这三个文本找来,将上面引文中的省略号补全。说巴黎的好,自然是海涅说得好,他从剧场里遮挡其视线的某女士的“玫瑰红罗纱礼帽”写起,让巴黎的欢快蒙上一层“玫瑰色光”,笔调亦庄亦谐。海涅到底是海涅,毒舌毒可敌国,美言仪态万方,此乃大诗人的本色。他不像十九世纪的斯拉夫先知,总嫌花都轻佻浮薄,不像二十世纪的后殖民理论家,理直气壮地心怀不满,而是懂得那里的“空气”给予外来者的甜美祝福,欣然领受其“大度包容、广施仁爱、殷勤好客的祥和气氛”。哪怕此行收获的是空气,带回的只是一点空气,也没有理由不让自己提笔赞美一番。
好吧,让我们一起赞颂巴黎!这倒不是因为最近那个让巴黎受难的事件而必须再次予以声援。赞美巴黎本是诗人和艺术家的老生常谈,不讲国籍,不分时代。海明威的名著《流动的盛宴》,让那些还没有去过巴黎的人心生羡慕,以为“盛宴”永在,只等着你去入座,时间无论如何总还是来得及的。“一切都会结束,唯独巴黎不会”,比拉-马塔斯的书中这样写道。
此言是在呼应海明威的追忆和叙述。海明威说,他在巴黎过得“非常贫困,非常幸福”。《流动的盛宴》记录了这种贫穷而幸福的波西米亚生活,显得魅力十足。海明威之后,任何想去巴黎满足流浪癖的青年艺术家,没有理由不读这本书,一般说来也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巴黎永无止境》便印证了这一点。
作者说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第一次去巴黎,某日在一家酒吧避雨,意识到这个场景是在重演《流动的盛宴》的开篇,于是他像海明威那样,点了一杯牛奶咖啡坐下来写作,这时一个姑娘走进来坐下(像海明威曾经看见的那样),而且像海明威描写的那样,她模样俊俏,“脸色清新,像一枚刚刚铸就的硬币,如果人们用柔滑的皮肉和被雨水滋润而显得鲜艳的肌肤来铸造硬币的话”。作者说,他把雨天和姑娘都写进了正在创作的故事中(像海明威做过的那样),等到走出那家酒吧时,他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新的海明威”。
二
《巴黎永无止境》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读来让人惊讶,因为到处都有那种真假难辨的“神奇的巧合”。主人公第二次到巴黎,打算做一个定居的波西米亚艺术家,在圣贝努瓦街租了一间阁楼,房东居然是玛格丽特·杜拉斯。没错,是那个戴黑框大眼镜的小个子女人,《印度之歌》的作者,说一口让人听不太懂的“高级法语”(因为我们的主人公只能说一点让房东听不太懂的“低级法语”)。
有点奇怪是吧?但也不尽然。那间阁楼许多人曾住过,有作家、画家、异装癖女性、女演员等,“甚至还有未来的总统密特朗—在一九四三年全面抵抗时期,他曾在那间阁楼里躲藏过两天”。某日早晨,我们年轻的主人公经过房东的楼梯口,看见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年女子”在打扫房间和楼梯。她的名字叫索尼娅·奥威尔。是乔治·奥威尔的遗孀,那段时间住在玛格丽特·杜拉斯家中。年轻人打算告诉孙辈,他是“那个看到乔治·奥威尔的妻子打扫楼梯的男人”。
难怪他要说“巴黎永无止境”……
这本书有特别的亲和力。这倒不是说我有过相似的经历或愿景,而是说,由于职业和兴趣的缘故我读过一些书,记住了一些典故、轶事和名字,偏巧在读这本书时它们像老朋友一样纷纷露面了。海明威、菲茨杰拉德、马拉美、兰波、玛格丽特·杜拉斯、于连·格拉克、让·科克托、本雅明、罗兰·巴尔特、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一份很长的名单。像是在某个文学共和国中游历,或者说像是收到一份阅读书单。如果你对这些名字不仅眼熟,而且还怀有一份敬仰,你自然会觉得别有一番趣味—它们忽然都失去了距离,在书中变得格外亲切了。
说来也是,巴黎若不是和一连串文学传奇联系在一起,那还叫巴黎吗?
丁香园咖啡馆的“绿牛魔鬼”,杰拉德·奈瓦尔的故事里出现过的妖魔,能让空房地窖里的酒瓶跳舞;他化身为“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幽灵,和“新的海明威”说话—“你应该记得我曾是你的保护人……”他的笑声低哑,声音有气无力;他记得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之间的恩怨,他们那种关系的所有细枝末节。这个司职记忆的幽灵,住在几度拆迁的老地方,历经沧桑而不会老去。可爱而古怪的“绿牛魔鬼”!
还有电影和时尚。一大群异装癖女性。毕加索的女儿帕洛玛开着敞篷车在巴黎狭窄的街巷招摇过市。我们的主人公还在玛格丽特·杜拉斯举办的家庭晚会上见到了伊莎贝尔·阿佳妮,当时她刚出道。事实上,他是一见钟情!并且当众出洋相,遭到大美女冷若冰霜的奚落。“天花板上的电扇在不停地转着,但是慢得如噩梦一般”,众人将目光投向他,禁不住纵声大笑,“仿佛那个噩梦般的电扇居然转得更慢了这件事让他们很开心”,而他面对美人那道“冷冰冰的可怖目光”,只能瘫痪在沙发上。可怜的年轻人!他以为只有他才有本事发掘未来的大明星,夸口说要马上给她一个角色演演,“试图以深邃的目光目不转睛地死死盯着她”……
伊莎贝尔·阿佳妮可不像“绿牛魔鬼”,把他看作是“新的海明威”(“非常贫穷,非常幸福”),在他耳边絮叨丁香园咖啡馆的前尘旧梦。我们年轻的主人公,为晚会上的可笑举止感到痛苦,却也能找到安慰。因为葡萄牙诗人佩索阿说过,“只有那些没有体验过难忘聚会的人才是滑稽可笑的”。请注意:重点不是“滑稽可笑”,而是“难忘”。他牢记这句格言。
《巴黎永无止境》确实是在讲述各种形式的聚会,只有那个年代的巴黎才能体验到的过剩的希望与绝望。哪怕是西班牙来的无名小卒,兜里没钱,作品写得还不像样,只要房东碰巧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文艺聚会上叨陪末座的机会还是有的。如果运气好,不仅可以遇见伊莎贝尔·阿佳妮,还可以从她嘴里听到冷冰冰的讥嘲:“谢谢您这么会献殷勤。”
三
比拉-马塔斯被译成中文的三本书,《巴托比症候群》(蔡琬梅译)引起较大反响,网上可见到的书评多一些,其他两部,《巴黎永无止境》和《似是都柏林》(裴枫译),似乎应者寥寥,而这两本书写得都很有趣,值得一读。
一种可以称之为“引文写作”的写作,构成比拉-马塔斯作品的叙述动机乃至叙述织体。可以说“引文写作”是这位作家的主要特色所在,是维系并伸展其灵感、思想和情感的媒介。它大致包含两个层面的运作:一是叙述的主导动机源于对其他作品的引用,使之适用于新的语境,例如,《巴托比症候群》的主题是出自麦尔维尔的一个短篇小说,演变成对当下群体生存状态的一种喻指,而《巴黎永无止境》也是如此,它的主题和海明威的作品密切相关;二是各种引文的嵌入,小到某句格言,大到某个段落的摘引,穿插在故事情节中,而且往往是在引导或编织叙述,其密度之大,让人感到这位作家的写作极易辨认,说白了他的风格就是在掉书袋,有时会让人觉得,这是蒙田在写后现代小说,或者也不妨认为,这是本雅明的设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写一部纯然用引文和碎片构筑的作品。虽说比拉-马塔斯的作品并没有那么极端,但是一部没有大量引文的比拉-马塔斯小说则肯定会让人觉得陌生,甚至有点难以设想了。
作者谈到阿根廷流亡作家埃德加多·科萨林斯基的小说《巫毒之城》,“充满了铭文和题词式的引文,读来让人想到戈达尔那些充满引言的电影”。这本书对他影响很大,他承认他的某些作品是由戈达尔的电影引申而来,也借鉴了《巫毒之城》的结构。他认为,“这种结构中那些看上去随心所欲、别出心裁的引文和移植成分赋予语言一种绝佳的感染力:引言,或者说文化垃圾,以奇妙的方式进入作品的结构,它不是顺畅地与作品的剩余部分相衔接,而是与其相碰撞,上升到一个不可预见的强势高位,变成作品的又一个章节”。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他的风格就是掉书袋。“引文写作”的旨趣不在于卖弄博学,而是试图在作品中加入新的成分,产生某种结构性的活力和趣味,在“随时策划情节”方面对叙述产生特别的影响。这在比拉-马塔斯的小说中是不难感受到的。
以《巴黎永无止境》为例,“绿牛魔鬼”的故事富于妙趣,如果没有典故的引申,就不会有这个段落。寻访“秘密书店”的插曲也是如此,那扇让人迷乱的“白门”,是对“神奇的博尔赫斯的空间”的一种巧妙戏仿。即便是写到母亲,也会适时插进卡夫卡的一段引言,在叙述中造成奇突的结蒂(变得和卡夫卡一样有才气的母亲),一种颇为机巧的喜剧性。写这种插曲式故事是比拉-马塔斯的拿手好戏,看似信手拈来,实为精心结撰,并且由于巧妙的引申、随机的策划或成功的杜撰而显得乐此不疲。
被各种引文阻断、穿插和诱导的叙述,成了一盘后现代“大杂烩”,有哲学和文艺学,有自传和杜撰,有此消彼长的情绪和体验,有奇想怪谈和轶事;通篇读来似乎没有一个气韵完整的故事,说不清是一种什么味道;像是在没有重力的月球上练习升降动作,摆脱了寻常的紧张状态(叙述的推进所必需的精神状态)。如果是在阅读扎加耶夫斯基的一首诗,那种被空气般的冥思所抚触的景观,无论多么细节化和散文化,我们会感到其内在的法则也都不同于叙事。而《巴黎永无止境》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它的着眼点与其说是叙述,还不如说是在叙述被打断的地方;换言之,作为叙述的一个基本法则,即记忆的还原(也包含心理的还原),是被有意削弱了,而这种现象在格拉斯、库切和阿摩司·奥兹等人的同类创作中是看不到的。
书中引用博尔赫斯的一番陈述:“我努力不去想过去的事情,因为如果我去想,我知道那是我在进行回忆,脑子里出现的不是第一批形象。这让我感到悲哀。一想到也许我不会有对我青年时代的真正回忆,我就不免伤心起来。”作者对此引申道:“过去永远是一种回忆的集合体,而且那些回忆是非常不牢靠的,因为它们绝不会符合原来的事实。”
普鲁斯特之后的文学,这种对记忆还原论的质疑不能算是新鲜,而类似的质疑用之于一部自传体小说则还是不多见的。比拉-马塔斯给出的是一种独特的处理,它不是在叙述,而是在叙说,打破记忆的统一性的逻辑,使得写作和生命被片段化。将“回忆的集合体”以看似任意的方式粘贴起来,实质也是在裁定“记忆的统一性原则”所具有的任意性。因此,这个写作主体已经不是通常的传记作者或自传体小说作者,而是更接近于书中自我界定的“讲座作者”(他交代说《巴黎永无止境》是他的一个讲座笔记)。我们看到,它是完全由他本人的阅读和幻想、分析和记忆编织而成,是一种杂糅性的叙说;其文类的性质似乎改变了—用罗兰·巴尔特的话讲,它更像是主体的区分化、片段化和碎裂化的写作中导入的一种“传记素的东西”;有关巴黎生活的追忆,凸显的是写作主体的位置,渗入大量反讽和评注式的补述,而那个写作主体没有和他过去的体验完全融合起来,结果是我们并没有读到一部我们想要阅读的自传类作品,而是进入一种“你不知道它会在哪儿停下来,也不知道它是不是要结束了”的散漫叙说,一种在织锦般的“引文写作”中自我繁衍的话语体系。
一个西班牙文学青年,在巴黎度过两年的波西米亚生活,他是“新的海明威”,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房客……这是一个让人期待的故事。对自传而不是对文艺学感兴趣的读者,也许会感到某种程度的失望,因为书中多的是评析而非浪漫的体验。作者声称,写这个故事主要是“以讽刺的心态回顾我的青年时代,驱除那个时代的邪气”。也就是说,他是以理智和反讽的距离,处理写作主体的内部所纠结的、仍然过剩的希望和绝望。
四
将《巴黎永无止境》和库切的《青春》对照阅读,会发现这两部作品有不少相似之处。两位年轻主人公都是文学朝圣者,去大都市学习写作,而且都想离开“狭窄的民族主义小道”,逃离自己的国家,到“世界的中心”去做一个流浪汉,永远不要回去。他们有着相似的自我关注和疑问—“为什么现在我还不是一个优秀的作家,而是要等到将来?我还缺少什么?缺少生活和阅历吗……如果我永远成不了一位优秀的作家怎么办……”两个人的绝望感也相似—“青春是美妙的,而我的流浪生涯将一无所成,我在扼杀自己的青春”。而且他们最后都承认自己是“失败的诗人”—“本来想写出伟大的诗篇,现在已经压低了雄心壮志,甘愿做一个讲故事的人”。总之,两者的相似度之高,让人有理由认为它们是在处理同一个精神主题。
《青春》英文版出版于二○○二年,《巴黎永无止境》西班牙语版出版于二○○三年,差不多是同一时期的创作,只能说是巧合,不存在相互影响或借鉴的问题。因此,其相似性显得耐人寻味。
两者都是在写一个试炼的主题—年轻的主人公为了成为作家所经历的痛苦和考验;为了逃离母国的文化生态,为了寻找价值的确定性,不得不经受严酷的精神考验。
这个主题的基本意涵在乔伊斯的创作中可以找到,《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便是表达“试炼”主题的自传体小说的先例。扩大一点看,乔伊斯、贝克特的创作都构建了“流亡”和“试炼”的主题关联,尤其是在“分离”和“焦虑”的层面上探讨“唯我主义者”的精神体验;他们为这个主题的写作开辟了路径。库切和比拉-马塔斯的笔下都出现乔伊斯、贝克特的名字,绝非偶然。
这是一群孤立于社会而以自我为中心的作家,因其自由的选择而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作为新生的一代人,库切和比拉-马塔斯还遭遇这样一种境地:神话已然结束,“流动的盛宴”差不多收场;事实上,“新的海明威”在那个传奇的中心过得“非常贫困”又“非常绝望”。我们看到,《巴黎永无止境》的叙述尽管充满“神奇的巧合”,却也伴随着忧郁的自嘲:青春是虚幻的,阁楼里的绝望倒是实实在在;绝望尽管高雅,街头的持续徘徊却总是灰头土脸。问题在于,波西米亚艺术家的生活即便是如其所愿,我们年轻的主人公就一定能够想当然地“如其所是”吗?别忘了,逃离母国的目标不只是为了自由,还要试图成为“优秀的作家”。
母国(政治和文化生态)的分离虽已实现,而其自我意识的确定性却变得疑窦丛生。此种情形有点像是从天主教转移到新教,在缺乏有效(或外来)指导的状况下,内心的焦虑却大大增加了—你不知道如何被救赎,你也不知道是否确定会被救赎。在抵御陈规陋习的个人体验中,你不得不专注于价值的确定性,也就是说,不仅仅要成为能够写作的作家,更重要的是如何“成为其所是”。
寻找价值的确定性,其前提也就意味着“价值的未定性”,意味着“自我保证的欠缺”。用罗兰·巴尔特的话讲,这是在进入语言活动“无证据的领域”。非但自我保证没有着落,自我认识难以定型,就连写作本身也在疑虑中延宕,在希望和绝望之间徘徊。没有一种意义是充分的,没有一个标准是可靠的,没有一种意志是稳固的,没有一个时刻是入眠的……这是典型的“自我主义决疑论”的孤独。
也许疑虑本身会有助于深化,在作家身上培育敏锐的道德意识,一种绝不陈腐的感性力量,甚至在其阴郁而圣洁的精神火花中,催生神秘的召唤……但是从青春体验来看,这是一种巨大的孤独和磨难。与其说“巴黎永无止境”,还不如说“试炼永无止境”,而这就是我们在两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看到的那种压倒性的绝望和忧郁,一幅沉重的青春自画像。
同样是回溯青年艺术家生涯,构建一幅不成熟的肖像,库切的还原式叙述(尽管精简),对于孤凄情调的传达是要感人得多,而比拉-马塔斯的笔触则含有诙谐和游戏的意味,是在一个透彻的层次上所作的种种夸张,其魅力是在于保持一种清醒和反讽的距离,而其无序的实验风格仍是在呼应着卡夫卡日记中的一句话:“只有写作是无助的,它不安居于自身,它既是游戏也是绝望。”卡夫卡、乔伊斯和贝克特之后,此种“无助感”的传达逐渐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文化面向。无助,却也不乏执着,那种自我突围的英雄主义的昂奋,还有那种看似永无止境的试炼和自我救赎……
比拉-马塔斯的创作意识根植于他的世界主义立场,和现代主义美学思潮保持亲缘关系。后来他定居巴塞罗那,出版了近三十部作品,却始终声称自己是西班牙文学的“陌生人”(stranger),与现实主义和乡土观念格格不入,正如《巴黎评论》的采访人所言,其著作的中心主题是旅行(journey)—“作家总是在旅行并讲述其流离失所的状态……”而这种“流离失所的状态”(displacement)亦可视为“价值未定性”的延续而非完结。作家在垂暮之年创作的这部自传体小说,讲述的不只是年轻时代的经历,巴黎特有的文化和魅力,同样包括精神上尚未终结的流亡状态。它是一份鲜有怀旧色彩的自叙状,一种像是永远处于组合状态的解构与重构的行为。
罗兰·巴尔特在《小说的准备》中所描画的那个徘徊在“各种风格的苦恼”中的写作主体,也可以说是《巴黎永无止境》的写作主体。游离于希望和绝望、实然和应然之间,在“无证据的领域”中感受“自我保证的欠缺”,这当然是不成熟的文学青年所为,也何尝不是成熟的作家所应该做的,如果他(她)是一个真正的作家。
其实,《巴黎永无止境》的叙述并不散漫,也非无序;其复杂的“引文写作”所具有的流畅、和谐与精确,让人领略到作者掌控文体的能力。他的文学修养是引人瞩目的。他不仅善于引用,也善于评述,包括文学评论。对自传和文艺学均感兴趣的读者,会从中获得乐趣。谈到海明威的那个颇难诠释的短篇《雨中的猫》,他总结说:“我不喜欢把事情都写得清清楚楚的短篇小说。因为理解可能成为一种判决,而不理解则可能是一扇敞开的门。”谈到科萨林斯基的《巫毒之城》,他认为,作者舒舒服服地安于“局外人”的位置,这是其“混合结构”得以施展的秘密。
《巴黎永无止境》贯穿对海明威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评述,而《似是都柏林》贯穿对乔伊斯和贝克特的诠释。这些评论都很值得关注,它们从敏感的创作意识中分娩,和迂回的叙述缠绕在一起,显得透辟、欢悦而不失意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