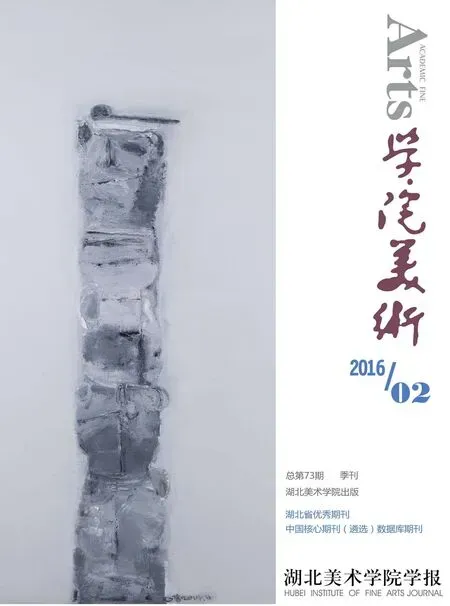石冲作品的“法”与“道”
艾 麟
石冲作品的“法”与“道”
艾 麟
摘要:石冲的作品中洋溢着对中国文化的热切关怀,和以生命为主题的形而上思考。石冲对于形而上“道”的清晰把握,并通而为一。因此在解读他的作品时需依据他使用的形而下的“法”来加以阐释和分段。本文从另一个视角总体解读石冲的艺术作品,来展现其作品中的中国文化的品格。
关键词:石冲的艺术;道通为一 ;大而化之
了解石冲的学生,一定知道他是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老师。熟悉石冲的人,也常常会通过他儒雅的言谈所透露出的睿智思想中,感受到一种理性的东方式思辩。中国文化讲:“画如其人”。石冲的作品中正是处处流露出这种东方式的形而上思辩和睿智的人生感悟,使他成为当代多元文化中为数不多的体现出中国文化品格的艺术家。
道通为一
孔子曰:“三十而立。”石冲很早就确立了自己的艺术主张。这当然得益于他的老师——尚扬。尚扬的作品同样洋溢着作者对中国文化的热切关怀,充满着一种理性思想的光辉。同样饱受楚文化的熏陶。在他们的思想中,既有敢于“问鼎中原”的艺术探索精神,儒雅而敢于担当的屈子品格;又充满老庄思想的形而上思辩以及“被褐怀玉”的超脱和达观。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如果一定要给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下一个限定,那便是儒释道合流后提出的“不阿世,不愤世,不玩世”的主张。在现实中要做到除非成为道家的“至人”或成“佛”。所以中国历代的文化精英们都是通过他们的艺术实践、艺术创作来接近或实现这个境界,这便是“无上道”。尚扬和石冲的作品,正体现出了这种“道”。当我们观看和解读他们的任何一件作品时,即使是异常尖锐的问题,在他们作品的表达和呈现方式上,看不到丝毫的阿意奉承、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的成份。作品中满是温文尔雅的理性思辩和他们对于现实人生的哲人似的感悟。
如果说石冲早期作品《盲女》及《预言家》中还隐约带有些许中西方神秘主义的元素。那么,从《被晒干的鱼》开始,石冲便确立了“道”这种完全属于中国文化思想的艺术主张,并在艺术之“道”上踽踽前行,用不同的“法”去实证自己心中所悟之“道”而从未偏离此“道”。以是观之,对待艺术石冲更像一位“行者”。
正是石冲对于形而上“道”的清晰把握,并通而为一。在解读他的作品时只好依据他使用的形而下的“法”来加以阐释和分段。
无情之情
《庄子》说:“圣人用心如镜。”神秀说:“勿使惹尘埃。”“情”就是“尘埃”,就是主观的好恶。“爱则欲其生,恨则欲其死。”过于主观的个人情绪不仅在作品中会误导读者,在现实中也会误导自己的判断。所以程颐说:“君子心普万物而无心,情顺万物而无情。”和西方式的个人情绪泛滥不同,石冲作品的形式和语言运用正体现了这种“无情”。尤其是他前期的写实作品,从主题形象到技术语言,这种“无情”无所不在。
读过王维诗和画的人,一定会深切感受到“诗佛”作品中的“无情”。这种无情,恰恰是中国儒释道文化的“用中”之道,“不偏不倚”,哲学中的“第一义”。若作品中的能指和所指带有强烈的作者主观,则一千个读者,只有几个或一个“哈姆莱特”。我们看石冲前期作品,所有的主题形象都是被原原本本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就像从一面不带任何色彩的镜子所返照出一样。鱼乎?人乎?过去乎?现在乎?未来乎?从《行走的人》一类的作品中,难道不会使人产生和顺治一样的疑问:“父母未生谁是我,即生之后我是谁?”真实乎?虚幻乎?亦真亦幻乎?欣慰乎?色乎?空乎?石冲作品的主题形象中这种超越了个人小我,升华为形而上客观的大我的看似无情的呈现,恰恰提供给观者最大的解读空间。在作品中,石冲把物还原为物本来的样子,不带任何的夸张或变形。这种手法的运用使观者更容易与客观物建立联系,使作品达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解读,而不至囿于作者的主观好恶判断。好作品是每个人都可以在作品中看见他想看见的。庄子解读得最好“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石冲作品技术语言也诠释着这种“无情”。
恰恰用心处,恰恰无心用
当大部分人都被石冲的“写实技巧”折服,想用心探讨时,石冲提出“观念先行”。可见他的用“心”并不是在于被别人所认可所关心的技术,技术对他而言绝不是问题,他早就超越了形而下的技术。但他此时的作品又需要用这种不带作者个人色彩的形象和技术语言与观者沟通,使观者还原为具有观者真实的个性色彩和认知水平的观者,以使作品得到不同的解读。所以“心有怀抱者”看见了政治,读过存在主义的看见了虚无……最后都“各复归其根”。优秀的艺术作品就应该如此吧!
许多人认为石冲被认可源于他的技术。若如此,他何不让技术更加极致,继续“保本”,而自己一变“忘本”呢?可见石冲作品之“本”不是技术。他通过几次的变化机智地暗示了出来。当人们认为他会“用心”的成为一个画干鱼“专家”时,石冲一变;当人们认为他会“用心”成为一个所谓“新写实”专家时,石冲一变。这种变化与西方强调个性化的“小我”不同。这就是“境界”。不了“道”者,往往惑于“法”。而认清道路的人,于“法”(形式以及语言)则可千变万化。所谓“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谁都可以随心所欲,但要“不逾矩”、“不违道”太难。
人们呼唤的东西,恰恰是人们最缺乏的东西。当人们都可以自由自在的呼吸清新空气时,谁会去炒作空气呢?若西方社会人人都存在感十足,哪会有存在主义呢?有多少当代西方艺术家不是抱着思想家和哲学家指出的以“社会病症”当学术呢?老子说:“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禅宗有言:不要“头上安头”。尽管是全球一体化,就算是孪生兄弟,每个人的“问题”怎会一样呢?当许多艺术家把西方社会的“主要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时,此恰恰是石冲无所用心处。他清醒的关注着我们自身的问题,虽然这样做显得不够“前卫”。中国文化中的“以天下为己任”,是在解决好自身问题的前提下。而当下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都没解决好,甚至有些还没意识到,却要以西方式的以问题为己任,是否有些好高骛远呢?石冲作品的切入点正是当下的“我们”而不是“他们”。是“你我”而不是“他者”。石冲艺术的观念——思辩性,使他的作品具有了强烈的中国文化色彩,很大程度上凸显了中国文化艺术的精神和品格。
无法之法
《孟子》曰:“大而化之谓圣”。《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孟子所谓的“充实”、“美”、“大”、“圣”、“神”都只是“道”的阶段,以“法”显“道”。当人们热情地认可石冲的《今日景观》等一系列作品的写实性时,石冲却把作品主题和形式及技术做了无情的改变,真正是“大而化之”。石冲在文化艺术思想上更加的“向上一路”,这种超脱的境界谓何,笔者不敢妄言。但此一“化”之后,他的作品确实让人有“不可知之”之感。题材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物化”成为主要的形式,所指更加不明确。然“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社会问题的现象背后,其内核是每个人内心的问题,不仅仅是社会表面现象。也许在石冲看来,“道”无处不在。阳光,空气,水……“平常心即是道”。何“物”不能表达出作者对现实人生的感悟呢?看似普通的“物语”,使各个“物”自身有了众多可解读的“妙”味,而“物”与“物”在作者看似不经意的组合后,又使解读有了“徼向”性。答案则在观者内心。“法”虽然变了,“道”还是一。石冲所求是中国文化思想之“道”。
老子说:“为道日损”。石冲正是通过减损形而下的“法”来纯化形而上的人生感悟。即使是前期作品,这种减损就在构图等“法”上多有运用。而“大化”之后,减损之法更加的明确。观者一目了然。在表达方式上,仍然贯通中国式的“无情”,而不是西方“抽打画布”式的感情宣泄和有心为之的平涂。石冲作品中这些中国文化元素的使用比比皆是且任运自如,而作品背后,所体现出的正是睿智和通达的“道心”。
石冲的作品,非“看”可了,会让你想静静的“观”,由“观”而“照”而“明”。这正是中国文化的品格。他正在“道”上行进,他已“技进于道”且在“道”澄明的途中。期待他有更多的作品,期待“观”他作品至“目击道存”“出神入化”,以使观者“内明”。
艾麟 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 讲师
中图分类号:J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016(2016)02-01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