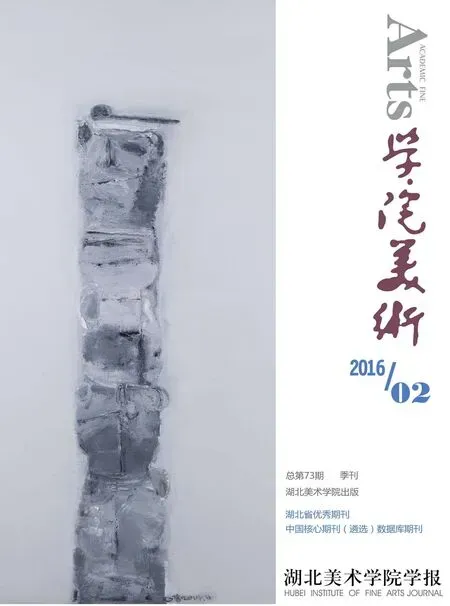时间性与绘画
桑建新
时间性与绘画
桑建新
在1995年之前的某一年的某一天,郭正善教授以“君子弃瑕以拔才,壮士断腕以全质”(唐·窦皐)之举,把一大卷他之前的全部绘画作品,从单元房楼梯边的垃圾口处,投了进去,“唰”坠下——“轰”的一声落地,然后转身离去。这一转身,不知他告别了什么,也不知他用如此方式与什么东西决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瞬间的决断投开了被遮蔽已久的本己,而回到去蔽后的内在境域的明澈中。他告别了已逝的过去,即把以过去为基础的道路截断了,从而转向了以未来为前提的绘画之路。能把未来眼前化一定是思的力量,而思是神性的艺术构境。这次“扔掉,转身离去”的事件成为他的艺术道路转向的标志。这种中断和转向,意味着超越“可靠”的流俗时间序列,预示着的安身立命的确定性而进入到以扑朔迷离的未来为基础的时间性的出离冒险境域之中。一旦脱离,如同脱胎换骨。所谓“脱胎换骨”乃是所有现有的东西都应该从根本上被克服,而不是必须被摧毁。克服就是真正战胜习惯、习得。简单地扔掉曾经拥有的东西是容易的,但克服和战胜一种惯常的绘画方式则是不易的。郭正善教授的这个举动是要从根本上克服二元论的对象性绘画模式,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扔掉了也就轻盈了。“无所待而游于无穷”(庄子)。从此,郭正善教授开始进入到非对象性艺术创作模式,即在另一层面的绘画艺术中探寻,他把自己选定的油画艺术创作道路命题为:“油画画面形态研究”,并开始了他的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至今已廿年了。至此,对这一研究方向的教学理念和方式方法以及研究生培养成果作专题研究是有其必要性和意义的。
来自于湖北美术学院油画系郭正善教授的历届和在读的38位硕士研究生此次推出的定名为《廿+绘》的绘画作品展,是一个师出同门,具有连续性的以60、70、80、90后所组成的中、青年艺术家群体联展,也是油画系A3艺术计划和研究生处联合举办的系列学术活动之一。它既是艺术家们艺术创作成就的展示,也是郭正善教授的教学理念、方式、方法和油画系人才培养成果的历史性的时现。
38位艺术家集结后的整体呈现,是一次“油画画面形态研究”学术理念历史性地同时出场与关注者的深度对话。我们看到的是弃二元论对象性绘画模式后,我们所想象不出的绘画艺术表达的多样性的呈现。艺术家们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所创作出的丰富作品使我们感动、喜欢、惊异、陌生、费解,有的作品甚至是难以接受。我们不禁要问,这些视觉经验是从何而来?有的作品打破了我们惯常的熟悉性而难以理解或看不懂。这就对了!如果所有的作品都被“看得懂”,那还要美术学院干什么?“熟知非真知”(黑格尔),我们熟悉的并不是我们已经把握的,而只是被无数人一再重复而为我们被动接受的东西。真正的艺术恰恰是要向这些东西挑战。这个群落的艺术家们就处于对西方油画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绘画模式的挑战境遇中。在他们种种的可能性、计划、感情、意欲受到各种偏见、传统、困境、规则的约束中,而能创作出陌生的东西,也许才有价值,才能生长和持久。规则对庸人来说是束缚,但对能者来说是艺术创作的契机和行走的临界点。学习他者而不崇迷于他者,学习传统而不沉沦于传统,松动一下僵硬了的传统,解除由它造成的遮蔽而向内在深渊钻研,才有原创性艺术的可能。而深渊往往是阴森恐怖的、陌生的,但又可能是严肃感人的。这样的作品是在一种更深刻的、不同于田野林间之美或流俗之亮丽层面上与我们灵魂相遇。
在同一个师门的同一研究方向中走出来的艺术创作样式的多样性是其艺术教育理念的胜利。这里展出的每位艺术家的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或寄幽思于光色,或舒豪情于气韵,或立壮志于骨法,或出神于形体,或纠缠于位置,或求精于完美,或痴迷于痕迹,或着意于制作,或借题于浮世百态,或幻化于物象,或清晰于梦境……这些作品都如同“借尸还魂”一般,重要的不在于“尸”,而在于“魂”。如果我们品味进去,每一位艺术家各自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语言特征所呈现出的多样性,在一个更深层面里得到了统一,那就是这些艺术家作品中“画面形态”所透露的艺术深刻性——“魂”。这种以非认识论才能读出的同质的艺术之魂,深刻地指向他们三年研究生学习期间,在万宝路香烟缭绕的烟雾里日复一日所得到的熏陶和在油画系乃至母校敞开的精神氛围里所得到的培养和锤炼。
“油画画面形态研究”是他们共同的油画艺术研究方向。它未显的特征所指应是:“艺术家创作状态研究”。因为“画面形态”无疑是要被艺术家的创作状态所规定。状态决定一切,因为状态决定着存在的意义。怎样的艺术创作状态决定了创作出怎样的画面形态。这就意味着它不是一个针对外在物象的对象性造型研究或绘画的技能技法研究,而是一种针对艺术家自身的时间性和身体性的状态研究。在出位状态的时间性——身体性的一招一式中,创作者重复的经验到出神入化的来临所赢获到的飘浮游历的精神自行设置入画布所带来的身心禅悦。无中生有的创造使其体验到存在的快乐,并诱惑其浸淫在物我两忘之着迷中而个别地畏着。畏着这种无对象性创作的神奇也就是畏着无,即在无中悬置的畏。其目的是要决断地去赢获绘画的精神性,以及更深远的是要去赢获艺术家存在的意义。绘画创作中的时间性体现的时效性就是艺术家存在的意义。“画面形态”的本质就是艺术家的出位状态的时间性的时现。研究绘画形态问题必须从它的源头即艺术家的时间性出位状态出发,才能得到根本的回答。“时间性”展现为出位而出离于流俗的时间,“出位状态”展现为出离自身,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迷狂或“兴奋中的沉睡”(杜威)。时间性与出位状态始终是契合在一起的。
“油画画面形态研究”方向的显然特征和方式方法乃是:崇尚绘画的精神自由和深刻表达,讲究品味地表达出超越流俗的画面感,回到画面本身而脱离具体的对象性事物、无差别、无是非、无好恶、无常形而有常理地在画面上追寻非刻意人为的本然状态而松开地让“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海德格尔),即让其自然天成。注重应手性的技艺纯粹和品质高雅以及画面的呼吸通透。以“应器量方圆”(临济)或“应物象形”(谢赫)地在动态平衡法则中,去行于当行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个画路上的人是坚定的漫游者,要有犹如行者唐僧一般的信念,“是在有与无,生与死的临界点上的行走的人”(彭富春)。无依无靠、漫无边际、初无定质、起落无端、构形不确……只有在以未来为前提的时间性出位状态中产生的存在的意义的诱惑牵引着他们,并保持在这种纯粹的牵引中来作为艺术创作的确定支点。在时间性出位中去应验“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的古老状态。“画面形态”研究何其不定,因为它没有现成的参照物,只有时间性出位状态才是他们艺术创作的依据和保证,并决定着他们艺术发展的方向和深度。“画面形态”绝不是对象性客体的实在物的形态,而是绘画的本质,即精神形态。它玄妙莫测,人不仅不能凭借感官去认识,更不能依靠理性思维去把握,甚至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于是,传道解惑以个性化的方式被寓于前理论的遭遇的经验、实践的体验、莫名的应验、智慧的卮言、循循善诱的道说、幽默的妙语、随机的拈来、旁敲侧击的修正、背景的音乐和娴熟的应手性之中。其间寄居、融注的却是艺术的本质或真谛。
选择“油画画面形态研究”方向的研究者就是选择了一条道路,是一条专注于自身内在状态方向的、可通达无限的道路,是一条艺术家与直接生命事实性的生命要求、生命充实、生命提升、生命肯定相关联的道路,更是一条切近艺术真谛的道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我深信,没有任何本质性的精神作品不是扎根于生命的源初的原生性之中”。在这条道路上,艺术家的创作特性就是能进入时间性展现的出位状态而对一切事物在一切方向上开放来消解其主体性,使之首先不是去认识事物,甚至不是去感觉事物,而是被出位的境域带着去应……去“用肚子画”。在出位的时间性的敞亮之光笼罩下,带着走进“出神入化”,穿过时间性的迷狂本身打开的开放之路,通达本源。绘画艺术具有来自生命本身的起源。它不是当代的,也不是现代和古代的,而是更源始地永在的东西。这条道路的选择,昭示着艺术家可永不停步地走下去,因为它有无碍的通达性,即只通过自身就能通达,并且没有最深,只有更深。深刻处才是艺术家应居之所。在那里,他与神同在。
从逗留于“画面形态”研究之处出发,但不是流俗意义上的“一路走来”,而是以未来为前提的“去”把绘画行为嵌入到时间性的出位状态中,以出神入化出离于流俗的时间、空间,超越平庸,并以此去获得绘画本身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从此次展出的作品中,从郭正善教授的“油画画面形态研究”的历史中解读到的东西:在艺术创作“有‘高原’缺‘高峰’”(习近平)的当下,艺术家们以“画面形态”研究创造性地构筑起他们特有的艺术之道路,朝向有着无限可能性的深渊走去——“靠探测深渊的办法来登上高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这个“深渊”不是外在于艺术家自身,而就是他敞开状态成为艺术的通道所能通达的深渊,让深渊里的东西通过此通道自行涌现、绽放。
桑建新 湖北美术学院研究生部主任 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