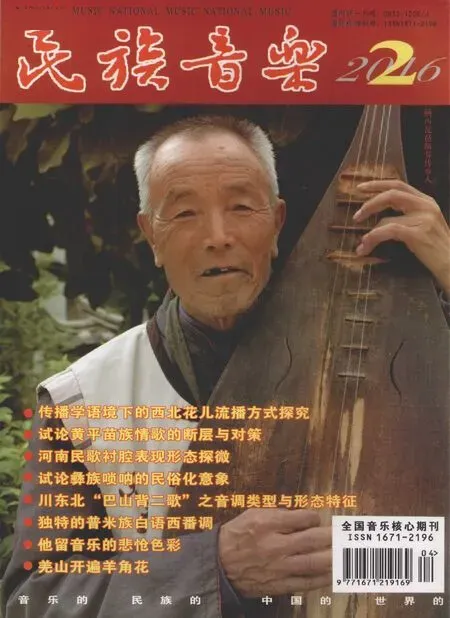传播学语境下的西北花儿流播方式探究
黄明政(绵阳师范学院音乐与表演艺术学院)
传播学语境下的西北花儿流播方式探究
黄明政(绵阳师范学院音乐与表演艺术学院)
花儿是一种山歌体裁,发源于现今青海省的湟源、尖扎、西宁、贵德、泽库、平安、互助、同仁、循化以及甘肃省的临洮、临夏、积石山、夏和、永靖、康乐、和政等十几个县,该区域明清时称“河州”地区,现主要流传在我国西北地区的青海、宁夏、甘肃、新疆等省区,在汉、保安、土、东乡、裕固、藏、撒拉、回等民族中传播和传唱,它产生的历史相当久远,可追溯到宋代以前。
花儿从产生到发展壮大,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传播过程,尽管这个过程纷繁复杂,传播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主观的因素,也有客观的因素,但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人携花走,人落花开”。归纳起来,西北花儿主要是以垦荒、迁流、做工经商、贩运等几方面为媒介进行传播的。这些流播方式,带来了花儿发源地区人口的大规模移动,与发源地各族人民相依相存的花儿也随着人们远走异乡。每一种方式虽然所承载的内容各不相同,但客观上却促进了西北花儿的流传与发展。
以垦荒为媒介进行传播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历朝历代都出现了把人口稠密地区的部分人迁移到人烟稀少的地区去开垦土地的政策,这种移民政策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上称之为“戍边政策”。不管统治阶级出于什么目的,戍边政策在客观上缓解了人口稠密地区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压力,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稳定,也便于统治阶级治理国家,发展社会经济,促进了社会向前发展。到了明清时期,戍边政策越演越烈,花儿发源地流域及其附近地区的回、汉、撒拉、东乡等族人民大量地迁往外地垦荒,有的甚至举家西移,与这些民族相伴终生的“心头肉”(花儿)也在迁往地生根、发芽、开花。据《续修导河县志》记载,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即1896年),东川庠生杜照融等100多户迁往青海省西宁的后子河。丁酉(即1897年)春,西乡军功张大观等300多户迁往平番的乱泉子;这年夏,北乡文童、他万荣等80多户迁往皋兰马家湾,还有东、南、西3乡汉族群众,也先后迁往皋、狄、金、西宁及平番各县,人数众多[1]。(注:导河,即今甘肃省临夏县。)在迁往新疆的移民中,河州人占的比重也是较大的。花儿专家夏启荣先生指出,新疆的多数回民是在清代,即18世纪以来从我国内地流入的。清乾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即1755年~1759年),清政府出兵伊犁统一了南北疆以后,就在新疆实施了大规模的戍边政策。由于新疆土地肥沃、地域宽广、人烟稀少,清政府便从陕西、甘肃等地迁来了大批的回族、汉族群众屯垦戍边,其中的回民主要安置在昌吉、乌鲁木齐一带。据统计,当时从甘肃就迁来了两万多回民,其中有五千多回民落户于乌鲁木齐县达坂城,他们和当地的维吾尔族、汉族人一起从事农牧业生产[2]。夏先生还列举了当时产生的花儿:“达坂城姑娘(者)辫子长,辫子(哈)一甩了放羊;一搭里干活(者)一搭里长,结下的情深(者) 意长。”[3]孙输文先生也说,新疆的回民大多数从甘肃而来,尤以河州地区来的较多,分散在迪化(即今乌鲁木齐)、昌吉、乌吉、乌什、焉耆、吐鲁番、哈密、绥来、伊犁等地居住[4]。
大批的回、汉、撒拉、东乡、裕固等族人民迁移到大西北从事屯田、垦荒,所带去的花儿也与当地的民间音乐、民俗文化相融合,不断发展产生出新的花儿,可谓新的花儿民歌诞生的重要人文背景之一。然而,这些垦荒的地方气候大多比较恶劣,地理环境较差,自然灾害频发,当地的地主阶级、土豪劣绅、官吏等恶势力也欺压百姓,弄得民不聊生,使得非常多的屯军、屯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老百姓不得不另寻生路,如花儿学者屈文焜先生所说,屯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新陈代谢式的人口迁移过程,随着一批又一批旧的屯垦者离去,便有一批又一批新的屯垦者来填充,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了动态的人口空间和传播花儿信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5]。
以迁流为媒介进行传播
在中国封建社会,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广大劳动人民的迁流(搬迁流动)是一种社会常态,或是自发的,或是强制的等。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最终造成了民族的大融合、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融等等。如晋人南渡,诞生了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福建南音;又如清朝时期,晋陕等汉民“走西口”的生活,诞生了二人台戏曲艺术等。河州人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迁流史,他们为了生计跋山涉水、背井离乡,有的到达了我国的新疆,有的甚至到达了现今的吉尔吉斯斯坦等地。
历史上造成河州人迁流的原因多种多样,下面仅分析三种:一种是因起义失败后而被迫迁流。河州这块土地上历来都是战事频发,特别是清朝时期各族人民反对封建地主阶级残酷统治的斗争轰轰烈烈,震惊中外。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循化撒拉族人苏四十三因不满地方官吏对当地百姓的压迫而率20余万众起义,两个月后起义军被朝廷镇压,而后包括撒拉族人在内的5万余人被清政府强行流放在西北各地;再如同治年间(1862~1874年)以马占鳌为首的回族大起义,起义军转战各地,势如破竹,多次大败左宗棠率领的清军。后起义军考虑到敌我力量终究悬殊,决定率部降清,此举使河州各族百姓免遭一场浩劫,得以数十年的休养生息,也使马占鳌保存了军事实力。清政府为了给回民以惩罚,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遂采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化瓦解”的策略,强行让10万余众回民迁入新疆等各地,这也是回族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流亡运动。另一种是因躲避战乱而迁流。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青海的回族与撒拉族之间由于教派之间的矛盾,又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清斗争,老百姓为了躲避战乱,大约有上万的河州人又一次逃难到新疆。《门源回族自治县概况》中也记载,各地的回族群众,因忍受不了封建官府和地主阶级的欺压纷纷逃到门源来谋生,从河州迁来的,多是为了躲避战乱。中华民国17年(1928年),爆发了第四次河湟事变,当时又有大批的回、汉、撒拉、保安等族人逃往西北。再一种是因遭遇自然灾害而迁流。河州这块土地可谓多灾多难,除了频发的战事,自然灾害也屡屡降临此地。如光绪十七年(1891年)至光绪十九年(1893年),循化、化隆、尖扎等地连续发生了3年大旱灾,当地各族人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为了生活只好又逃往外地;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甘肃、宁夏、青海地区又一次遭遇了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当时又有大量的回、汉等族人涌入新疆,这次迁流史上称为“盲流大军”。
历史上,河州人经常迁流,这种现象的发生还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制度、文化和政治体制决定的。尽管这种迁流带有强制性和不情愿的因素,伴随着浓浓的悲剧色彩和一幕幕撕心裂肺的悲痛场面,但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它又是造成跨文化、跨民族、跨地域传播的内在驱动力,极大地突破了地区之间封闭的状态,增大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际范围,扩大了花儿的生存空间,也为花儿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一种途径。
以做工、经商为媒介进行传播
花儿的发源地河州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中原与西域的重要交通驿站,是西北工商业的重镇,商业贸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明洪武年间,这里就是茶马互市的中心地带,明政府在这里设置过“茶马司”,专管茶马交易的一切事务。同时,河州也是西北地区茶叶的集散地和中转站,素有中国西部“旱码头”之称。
河州常年商贾云集,木工、铁匠、擀毡匠、买卖人等闻名遐迩。据明《河州志》记载,临夏城南就有客栈18座,来自各地的商人主要居住在这里。特别是清朝末年,做工的、经商的河州人可谓遍布四面八方,这些河州人常常往返于甘肃、青海、新疆、四川、宁夏、陕西、云南等地,有的甚至到达了现今的中、西亚地区,与当地人进行着以物换物等商贸活动。如《黄南藏族自治州概况》中写道,近代到黄南地区定居的部分汉族群众多是因经商等原因从甘肃临夏等地迁来的。《化隆回族自治县概况》也记载,大约在光绪九年(即1883年),有一个来自甘肃河州大河家库路湾叫“老水客”的人,经常往返于甘肃、群科贩卖木料、粮食,后定居在群科。由于经商发了财,他在群科则塘买了很多土地。后来,“老水客”将自己家乡的全部亲戚由甘肃迁到了则塘。陈志良先生也指出,从甘肃临夏和青海西宁迁入新疆的回民,分别居住在古城、阜远、阜康、迪化、昌吉、绥来、伊犁、焉耆、吐鲁番、鄯善、哈密等地,大多从事农业生产和经商。花儿学者杜亚雄先生在研究裕固族、土族民歌时发现,裕固族的花儿是从东乡族擀毡匠那里学来的;青海民和土族人演唱的花儿是从永靖莲花的木匠那里学来的。
做工、经商的范围非常广泛,路线也是很复杂的,像“黄河上渡过了一辈(呀)子,浪尖上要花(呀)子哩”“上走了西宁的碾伯(呀)城,下走了窑街的大通”“走罢了凉州了走(呀)甘州,嘉峪关靠的是肃州”“连走了三年的西(呀)口外,没到过循化的保安”“阿拉山尖上的烟瘴们大,西代唐河里的水大”“渭远县有一座八廊的桥,鸟鼠山有一座庙哩”“尕马(哈)骑上者走(呀)云南,捎带者走了个四川”“黄河上走了个宁夏(呀)了,包头的街道里站了”“泾阳的草帽是十八(呀)转,长安城打了个过站”“固原的城是个砖包的城,青石头铺下的大路”等等花儿唱词,就是对做工、经商者们的行走路线的一个粗略记载。其中,他们中的部分人就长期生活在了做工、经商的地方,花儿也就在这些地方生根发芽了。
以贩运为媒介进行传播
河州地处我国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交接处,土地贫瘠,山路崎岖不平,沟壑纵横,悬崖峭壁随处可见,陆上交通极为不便;湟水、黄河等河流也流经这里。正是这种地形、地貌造就了河州人在困难面前坚韧不屈、吃苦耐劳、敢闯敢干、勇往直前的顽强品质。过去,当地人们与外界的贸易往来主要是靠骡子、骆驼、马等牲口驮运和靠河道运输,由此脚户业、筏子客也就产生了。
脚户是西北地区人们对驾驭骡子、马、牛、骆驼等大牲口,控制并跟随驮队从事长、短途运输的人的称呼。河州脚户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出身,除农忙在家务农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吆喝着牲口在外面从事着专业的贩运。历中上河州脚户哥从事贩运的地域非常广泛,近处可以在邻近的区、县之间,远处可到达四川、云南、陕西、新疆,甚至更远的地方,如清人记有河州汉民的贩运基本上都在本地区,而回民的贩运远可到达新疆、四川及陕西等地。
脚户哥在贩运途中的生活非常艰辛,独自要面对很多常人无法克服的困难,比如恶劣的气候、匪盗打劫、伤病、缺衣少食等等,饿死、冻死、生病死、被土匪杀死、掉下悬崖摔死等意想不到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且心灵上还要承受思念(思念父母、妻子、儿女、情妹妹等)、孤独和寂寞之苦。所以,脚户哥的每一次出行都是与亲人的生离死别,妻送夫、父母送子、情妹送情哥的场面凄凄惨惨,不知道赶脚的亲人几时能回来,还能不能回来。有的脚户哥两三个月,或五六个月可以往返一次;有的甚至要一年、几年才能回家;有的一去从此杳无音信,荒凉的野外只有亲人的无限期盼!
在充满艰辛与险恶的贩运途中,一路上伴随着脚户哥的是空旷无人的荒山野地、单调的铜铃声和骡蹄声。为了排遣赶脚生活的寂寞与孤独、抒发心中的苦闷、感叹命运的不平以及思念家中的亲人,脚户哥们会不由自主地漫起家乡的花儿,以减轻压在他们心头的重负,像“霸地草要吃白砂糖,哥吆骡子去洛阳;霸地草要吃自贡盐,哥吆骡子下四川”“头骡的脚步放开了,押脚的大铃响了;脚户阿哥们想你了,心上的尕妹,不由得脚步么大了”“头帮骡子满头红,西口的大路上响着马铃;你看脚户哥们好不英,喊一声花儿痛烂心”“腿子(哈)走成个硬杆杆,支起个锣锅者吃炒面;脚痛呀腿酸者吃不下饭,你说嘛辛酸啦不辛酸”“石砭就像是鬼门关,下(哈)了驮子们者胛子上掮;百八的驮子者往肉里钻,心悬者头发根里冒冷汗。多少匹骡子(哈)滑下了砭?多少个苦命人跌下了九泉?过了呀石砭者人模子散,腰困者腿酥者四骨里软”“一买了鞭子二买了马,三买了梅花镫了;一想娘老子二想家,三想了连心的肉了”等等,真实地反映了脚户哥的辛酸生活,同时,花儿也留在了记录他们艰辛生活的弯弯曲曲的驮道上。
筏子客是西北地区人们对用羊皮或牛皮筏子从事河渡贩运的人的称呼,这些河州筏子客主要的航运路线是从西宁(或贵德)到兰州,然后再顺着黄河到达包头等地,他们与脚户哥一样多数都是当地的受苦农民,由回、汉、撒拉、东乡、保安等族人中身体强壮、精通水性的青年人担任,是一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我国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1936年搭乘回民的羊皮筏子到内蒙古采访,在皮筏上度过了五天四夜。他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写道:“西北水上交通,皮筏较木船为普遍。操纵皮筏之苦力,十之九为甘肃河州之回民,亦有西宁之方面者。”[6](注:他说的“回民”包括东乡、保安、撒拉等族的人。)
筏子客的漂流生活与脚户哥的驮运生活同样艰难、辛酸,当地的恶势力与官府勾结,在黄河、湟水等河流岸边到处设卡,过往筏子客要被层层盘剥,交纳各种苛捐杂税。有时还要遭遇土匪的打劫,有的倾家荡产也得把损失赔给货主。没有偿还能力的,无奈之下只有离乡背井,流落异乡。这些还不是他们苦难生活的全部,更要命的是:他们时刻还要面对黄河的惊涛骇浪、暗礁巨石,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1937年在兰州河口乘羊皮筏子,他在《考察西北后的感想》中说:“人坐行李上,不便转侧,波澜旁冲,裳履尽湿,泊兰州城外水北门,亲历乘风破浪之险。”[7]筏子客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干做刀口上舔血,刀尖上行走的营生,有一首歌谣深刻地阐明了筏子客辛酸的生活:“多少年黄河里漂泊,桨板儿摇粗了胳膊;多少年黄河里颠簸,挣扎在激流漩涡;出没风浪里的筏子客摇不尽寒苦的生活;风卷日月头上过,泪水儿比那黄水多!”有许多筏子客,在与黄河的急流险滩搏斗中,将生命永久地留在了河道里。
在水流比较平缓,天气晴朗的时候,伴随着黄河上那“哗啦啦”的木桨声,河州筏子客们也会苦中“作乐”,情不自禁地放开歌喉,把一首首荡气回肠的花儿唱给南来北往的过客,唱给滚滚东流的黄河:“站在筏子上扳桨哩,羊毛(哈)往包头送哩;远路上有我的扯心哩,谁人(哈)打听者问哩。芥干花开开打黄伞,胡麻花开开是宝蓝;筏子上的阿哥(哈)讨平安,回来了尕妹(哈)照管”、“黄河上耍水的筏子客,性命在浪尖上饶哩;尕妹们一天盼不黑,相思病啊早会好哩”、“中间是黄河(哈)两边是崖,峡口里站两朵云彩;云彩是搭桥者你过来哎,心里的‘花儿’(哈)漫来”、“左边是黄河右边是石崖,雪白的鸽子水面上飞;阿哥和尕妹一对子鸽子,尾巴上连的是惹人的哨子;一对对鸽子晴天里飞,他俩是天世下来的对对”、“天晴天阴河滩里爬,筏客子行户苦最大;冰碴子划下腿肚子痛,麻鞋带勒着脚肿哩”等等,这些人无意间也成了花儿的传者,花儿伴随着他们艰辛的水运生活,自西向东洒落在波涛汹涌的黄河上。
结 语
从以上几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河州人的足迹所至,花儿的种子也被他们无意间带出了家乡,带到了西北各地,使花儿赢得了“陕西的乱弹,河州的少年”的崇高美誉,这是回、汉、撒拉、东乡、保安、藏等西北各族人民广泛而持久传播的结果,这些传播者为花儿在异地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花儿的传播区域也并不是无边无际的,而是沿着一条相对比较固定的线路在进行传播,这条线路就是古丝绸之路及其辐射地带。这条开始于我国的西安,终止于现今土耳其的第二大城市伊斯坦布尔,面积40多万平方千米,横跨80多个县、市古道的开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丝路沿线各民族用脚踩出的一条通道,积淀了众多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条经济文化纽带上传递的不仅仅是商品,中原儒道文化与以宗教文化为代表的异域文化在这条古道上也得到了互补与发展。
[1]黄陶庵.续修导河县志[M].兰州:甘肃人民 出版社,2011.
[2][3][4]佚名.花儿的流传分布.http://www.chinalxnet.com/content/2009-03/12/content_4237_2.htm.
[5]屈文焜.“花儿”的空间系统[J].宁夏大学学报,1995(1):58.
[6]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7]顾颉刚.考察西北后的感想——1938年10月讲于中央政治学校附属蒙藏学校[J].西北史地,1984(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