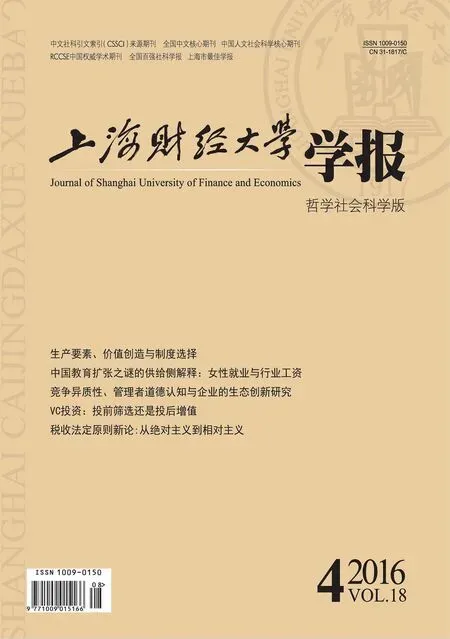税收法定原则新论:从绝对主义到相对主义
张学博
(中共中央党校 政法部,北京 100091)
税收法定原则新论:从绝对主义到相对主义
张学博
(中共中央党校 政法部,北京 100091)
税收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文明的两大基石。罪刑法定原则是对人身权的保护,而税收法定原则是对财产权的保护。学术界对于税收法定原则的研究偏重于保护公民的财产权,而忽视其保障国家财政权力的一面。现代财产法的发展已经认识到财产权并非一个单纯的私法概念,而是公民财产权和公共财产权的辩证统一。在这个意义上,税收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国家和文明的基石,是保证国家公共财产权和公民财产权辩证统一的重要原则。除此之外,如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不仅仅是个立法问题,还是一个实践问题,必须分析税收实践中的税收指标等实践问题,才不至于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才可能真正实现对国家公共财产权和公民财产权利的双重保护。正因为如此,传统的绝对税收法定原则并不能完全地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需要,而应以相对税收法定原则取而代之。
税收法定原则; 财产权; 公共财产权; 绝对税收法定; 相对税收法定
一、 问题的提出
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已初露税收法定主义的萌芽;1627年的《权利请愿书》曾规定,非经国会同意,不宜强迫任何人征收或缴付任何租税或类此负担,从而正式在早期的不成文宪法中确立了税收法定主义。①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1994年第6期。张守文认为税收法定原则包括课税要素法定、课税要素明确和依法课征三个方面的内容。这些观点最早来自于日本学者金子宏和中国台湾学者陈清秀。②[日]金子宏:《租税法》,其中译本为《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经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陈清秀:《税捐法定主义》,载于《当代公法理论》,月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589页。覃有土、刘乃忠、李刚从语义学对税收法定主义进行了研究,对“税收”、“法”、“定”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税收法定包括“税种法定、税收要素明确和程序法定”三部分内容,并希望在宪法中予以明确。③覃有土、刘乃忠、李刚:《论税收法定主义》,《现代法学》2000年第3期。有学者对于税收法定的三要素说提出了质疑,尤其是程序法定部分。张永华、肖君拥就认为:“日本学者金子宏在《租税法》一书中,将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概括为课税要素法定主义、课税要素明确主义,合法性原则和手续之保障原则……因此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只应包含税种法定、税收要素确定这两个方面的实体内容。”①张永华、肖君拥:《论税收法定主义之内涵——对日本学者金子宏学说的一点质疑》,《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1期。
围绕我国宪法是否构成税收法定原则,李刚、周俊琪从法解释的角度对刘剑文、熊伟二学者在《税法基础理论》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将《宪法》第五十六条确定为税收法定主义宪法渊源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只有正视税收法定主义在我国《宪法》中的缺失,以及由此在实践中造成的问题,并探求解决之道,才能为税收法定主义在我国《宪法》中的确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②李刚、周俊琪:《从法解释的角度看我国《宪法》第五十六条与税收法定主义——与刘剑文、熊伟二学者商榷》,《税务研究》2006年第9期。
多数学者认为税收法定原则在税法中属于帝王原则。如王怡认为:“以赋税问题作为看待财产权与宪制之关系的一个切入点,通过对财产权在先的论述……从而凸显出赋税合法性的危机。解决这一危机的方向是继续沿着财产权入宪的思路,确立‘税收法定’的赋税模式”。③王怡:《立宪政体中的赋税问题》,《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地位,有学者并不认同其他原则应低于税收法定原则之观点。如侯作前认为:“税收法定与税收公平都是税法构建的基本原则。从历史和现实的具体语境看,当今世界在税法原则构建上正发生着从税收法定到税收公平的演变……必须通过修改宪法第56条、完善税收立法、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等措施,同时实现税收法定和税收公平的构建任务。”④侯作前:《从税收法定到税收公平:税法原则的演变》,《社会科学》2008年第9期。
还有学者从更宏大的视野(财税法定)来理解税收法定。刘剑文认为:“财政法定原则的要求是财政基本事项由法律加以规定……最初表现为税收法定,并在夜警国家到社会国家的演进中扩展到预算法定,最终发展为财政法定。”⑤刘剑文:《论财政法定原则——一种权力法治化的现代探索》,《法学家》2014年第4期。从如何落实税收法定的层面,刘剑文进一步认为:“在本土语境下……一是从‘无法’到‘有法’,在改革中全面加快税收法律化进程;二是从‘有法’到‘良法’,提高立法质量,并在适当时机推动该原则入宪; 三是从‘良法’到‘善治’,将税收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全过程纳入法治框架,并在税收法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财政法定。”⑥刘剑文:《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现实路径》,《政法论坛》2015年第3期。另有学者从纳税人权利视角来思考税收法定原则。如俞光远认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实质和核心,就是维护税法尊严,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包括完善税法体系、严格依法治税以及建立健全纳税人权益保护组织和相关体制机制。”⑦俞光远:《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与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地方财政研究》2015年第11期。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政府认识到税收法定原则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基石性作用。但是学术界对于这个命题的研究集中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学理表示,而忽视了这个命题的关键在于“落实”二字。党的纲领性文件对这个命题进行的阐述,意味着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学理问题,而是要从纸面上的“税收法定”走向实践中的“税收法定”。命题已经提出两年之久,一方面学术界讨论得如火如荼,另一方面实务部门却面临经济下滑的压力,为如何完成自上而下的税收任务指标而发愁。在许多人眼中,包税制是一种罪恶的制度,因为它使得纳税人的命运被操纵在贪得无厌的包税商的手中。然而,在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包税制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因为它为国家建设提供了财政资源。同时,包税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因为它使得这些国家新兴的商人阶层与传统的权力精英都成为国家的“投资人”,从而降低了他们从这些新兴的政治实体中分离出去的动机。①马骏:《包税制的兴起与衰落:交易费用与征税合同的选择》,《经济研究》2003年第6期。此外,最近在欧美等国,一种变形的包税制又开始出现。②Sturgess G. Virtual Government. Australi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stration,1996,55:59-74.学者们固然可以指责实践部门理论水平不高,执行能力太差,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学术界对于税收法定原则的研究是否真的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真正关注了“落实”,还是仅仅停留在概念比较,从抽象到抽象呢?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首先,从实证视角,即事实而非理论出发,来考察绝对主义税收法定在中国现实中面临的困境。我们在河北省县乡村各级政府部门的大量调研发现,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几乎每一两个月都有新的文件和政策出台,但是真正落地到县乡政府的很少。中央、省级政府主要是在制定政策,地市政府主要是传达和布置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政策文件精神,真正实施法律规则和政策文件的是县乡政府和村委会。实践中县乡政府的工作方式基本上就是项目分包制和指标考核制,体现在财政税收领域就是财政收入层层分包制。从上到下,每个县乡都有以考核压力为基础的财政收入分包制。传统的财税理论研究从国外引入税收法定的要素进行几个要件理论分析,然后以此来批判中国的实践工作不符合与国际接轨的理论,然后提出系列立法修改意见。这样的研究范式在过去这些年,造成了理论与现实越来越脱节,也对实践工作如何与中央的政策对接产生了很多困扰。
其次,从历史视野来看待中国的财税实践,从而对税收法定主义的理解提出新的观点。一方面,因为我们所处于的1840年以来急剧的社会转型,背景决定了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党和政府推动型的后发追赶模式,这种快速的社会转型本身与法治有一定的内在冲突。另一方面,我们又力图通过立法的方式来推动改革,而且历史上这种成功的案例不少,国内有商鞅变法,德国有俾斯麦改革,日本有明治维新。这都使得我们的理论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深刻的历史背景,而非简单的复制国外的理论。
再次,运用现代财产权的最新理论,对如何构建税收法定主义提出了新的观点。现代财产法的最新观点,不再坚守绝对主义的财产权观点,不再把财产权视为私人财产权,而认为国家的公共财产权也是与私人财产权同样重要。传统的绝对主义税收法定建立在绝对主义的私人财产权理论基础上,所以现代财产权观点的演变也会导致对税收法定主义的重新理解。
最后,从本土国情出发,对如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提出现实路径。所有的理论都来自于实践,但一定是某个具体的民族国家的实践。比如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就是立足于德国的,美国学派就是立足于美国的。伟大的学者和学术都是立足于自身的民族国家,为实现国家的目标而努力。正是在这个前提之下,才有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说法。罪刑法定原则从绝对的罪刑法定走向了相对的罪刑法定,正是立法联系司法、理论联系实践的结果。罪刑法定原则的绝对主义,一开始正是欧洲学者提出来反对封建王权的,从而保证国内资产阶级的人身权不受侵犯,可以极大地促使当时资产阶级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有着不可否定的历史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发现绝对的罪刑法定过于僵化,既不能有效地打击犯罪,又不一定符合对公民人身权利的保护。比如,类推和溯及既往经过了一个从绝对否定到相对否定的阶段。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相互融合,执法和司法的自由裁量的不可避免,这些都促使我们对现有的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反思。税收法定原则也是如此。欧盟主权债务危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欧盟一体化极大地整合了作为共同体的欧洲,但同时也极大地约束了各个成员国的财政权力和货币权力。由于欧盟国家对于税收法定原则的严格遵守,使得现在欧盟成员国在面临经济危机时,很难采取有效的财政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应对,比如希腊、意大利都面临着这些问题。我们作为后发国家,应该汲取这些教训。公民权利毫无疑问是应该受到保护的,但是不可因此而漠视国家的财政权力。霍布斯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明确了一个观点:现代化最大的一个前提就是,只有国家的存在才可能保证个人的自由。美国的实践恰恰说明了这一点: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才可能保护个人的权利。因为一个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其对经济社会实践的解释力,而非纯粹对于抽象原则的执着。
二、 绝对税收法定的理论渊源和借鉴意义
(一)英国《大宪章》的神话
关于罪刑法定原则和税收法定原则,几乎所有学者都把源头追溯到了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实质上是英国贵族与英国国王斗争的产物。《大宪章》在要求倾听人民的呼声时,谈到了代议制政府问题。《大宪章》第12条规定,非经“大会议”同意,禁止国王向人民强加税收。①Jo seph Wro nka. Human Rights and Social Policy in the 21st Century,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8:54.1628年,在国王查理一世统治时期,英国通过了“权利请愿书”,重申了爱德华一世确认的“无同意课税法”。②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89页。今天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把《大宪章》视为英国之所以成为现代国家的重要转折点,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原则就是罪刑法定原则和税收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关于人身权的保护,而税收法定原则则被视为对公民财产权的消极保护。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口号,对于反抗国王特权有相当积极的作用。
(二)法国《人权宣言》
法国《人权宣言》对于整个世界历史的影响极为深远。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同样聚焦于人身权和财产权保护,其财产权保护分为积极保护和消极保护。其第17条规定:“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而第13条和第14条共同规定了税法原则。第13条是税收公平原则,即“赋税应在全体公民之间按其能力作平等的分摊”。第14条规定了税收法定原则,即“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认可,注意其用途,决定税额、税率、客体、征收方式和时期”。③百度百科:《法国人权宣言》,最后登录于2016年3月10日,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izZq8uGnleYX5pcJXmlFT7uGFYRwFbC4XIZ3eZuaJcpDa9ETov5OHKD6UjvRDaIJSqfnTywJBACfm1YBG pcZgK。法国《人权宣言》相比英国《大宪章》,大大前进了一步。如果说英国《大宪章》还是思想渊源的话,那么法国《人权宣言》则是以明确的解释性的语言对于税收法定原则予以明确的界定。
(三)日本税法理论
目前对国内学者影响深远的其实是日本税法学界,以北野弘久和金子宏为代表。从功能主义视角来看,税收法定原则在其历史的沿革过程中起到了将国民从行政权的承揽者——国王的恣意性的课税中解放出来的作用。税收法定原则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的机能正是在于它给国民的经济生活带来了法的安定性和法的预测可能性这两点。①[日]金子宏:《日本税法》,战宪斌、郑林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金子宏进一步认为:“税收法定原则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课税要件法定主义;课税要件明确主义;合法性原则;程序保障原则;禁止溯及立法;纳税人的权利保护。”②[日]金子宏:《日本税法》,战宪斌、郑林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9-63页。
(四)绝对税收法定对我们的借鉴意义
从1215年英国《大宪章》到1689年权利法案中税收法定思想萌芽,再到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对税收法定的解释,再到日本税法学界对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六要件阐述,完整地构成了古典的绝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内容。绝对税收法定主义与早期绝对的罪刑法定主义一样,强调对于公民财产权的绝对保护。它的思想渊源就是法国人权宣言中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国王任意侵犯贵族和平民财产权的时期,绝对税收法定主义有其明显的进步意义,对于商业文明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对于中国而言,早期的绝对税收法定主义的最大价值在于对个人财产权的尊重。从《大宪章》到法国《人权宣言》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就是,国家是建立在个人的私权利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出现之前,社会处于任何人对任何人的混乱状态。国家必须先承认个人的私有财产权,才能对个人的财产权课征税收,而依靠税收,国家的机构才能得以维持运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是很大的一件事。如果观察中国古代的税制,就会发现从税制入手,中国历史可以划分为井田制(春秋之前)——授田制(战国至南北朝)——均田制(北魏至唐中叶)——两税法(唐中叶至清)。细致分析四种税制的变化,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税制基于土地制度,唐中叶之前整个国家的税制以实物征收和服役为主,直到唐中叶之后开始向货币征收转变,历经王安石变法、张居正一条鞭法,直到清雍正摊丁入亩才彻底完成了两税法,废除了人头税,转变为财产税。贯穿于中国古代税制的核心特征包括:地权核心、公私并存、家国同构和循环往复。这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中国古代宪制的一部分。总体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是很深的,尽管在某种意义上也承认一定的私权利,如自耕农的土地使用权、继承权等,但是这些权利的保障很难得到有效的救济。也就是说,中国社会中的私权利是模糊的,随时可能受到公共权力的侵犯而无法得到救济。这也是中国商人喜欢买房置地而不愿意进行科学研究扩大再生产的原因。这种文化一直影响到现在。商人们热衷于做红顶商人,投资房地产,而不愿意进行科学研究,提高生产率,进行转型升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观念中对于个人的私有财产权没有一个基本的尊重。
首先,早期税收法定绝对主义(尤其是英国《大宪章》和法国《人权宣言》)对于我们最大的价值和意义:必须承认私人的财产权利是先于国家的,只有保证私人的财产权利不经正当程序不受任意侵犯,公民才有动力去进行科学研究,扩大再生产。所以对于税收法定绝对主义中的某些内容,今天的中国仍然要坚持,比如行政机关对于公民课征减征税收(或费)的现象必须得到有效约束,大量的红头文件随意对税收要素进行改变的情况必须得到改变,地方政府债务从长期来说都会变成纳税人的负担,也应该得到有效的法律约束。
其次,日本税法给我们最大的借鉴价值在于税收法定的具体规则化。相比英国《大宪章》和法国《人权宣言》,日本税法进一步从操作层面对税收法定进行了细化。而且日本税法理论从宪法理论中阐述了税收法定的法理依据,并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分析了税收法定的必要性。对比前述国内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国内学术界对于税收法定原则的理解基本上来自于日本学者。从日本学者的六要件选择了其中三个要件作为中国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目前实践中比较突出的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课税要件法定主义。2015年修改过的《立法法》对税收法定主义有一定突破,把税率法定列入了立法法。2015《立法法》修正案二审稿中曾经明确“税种、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但到了最后通过的修正案,“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法定三项内容则被删除了。应该说这是2015年《立法法》修改的一个遗憾,应该在下次修改时予以明确。二是1985年全国人大对国务院的立法授权仍然未被废除。这个立法授权过于宽泛,再加上国务院将这个授权经常转授给国务院直属部门,使得财政税收部门借此僭越立法权。从长远来看,应尽快由全国人大根据立法进度废除这个立法授权。
但是,今天学术界对于1215年英国《大宪章》的推崇似乎已经把这个《大宪章》过于神化了。实际上,很多文献都表明1215年英国《大宪章》主要是代表英国贵族的利益,所谓的“人民”实质上是拥有一定财产的贵族。当然随着后来世界人权运动的发展,这些本来主要是保护贵族的法律原则也被普遍适用于所有公民。但是学者们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忽视了一个基本的问题:英国大宪章以及后来的权利法案,实质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因为对于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绝对保护本身对于国家则可能是不利的,会使社会的弱势群体可能无法受到国家的照顾,所以这些披上神圣光环的原则本身是有所指向的。所以税收法定的绝对主义在实践中越来越遭遇到一些无法摆脱的困境。
三、 绝对税收法定的困境
就如何落实税收法定,学者们也设计了不同路径。刘莘和王凌光从立法保留的思路提出了税收法定的三条措施:“废止授权立法;制定税收基本法;税收法定入宪。”①刘莘、王凌光:《税收法定与立法保留》,《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陈国文和孙伯龙追溯了英国19世纪税收法定原则的发展历史,并对中国如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人大财税法案审议权的完善;人大专门财税委员会的完善;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②陈国文、孙伯龙:《税收法定原则:英国19世纪的演进及启示》,《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6期。李伯涛就2015年《立法法》的修改提出了“税收法定的立法表达”命题。他认为:“立法法修改对税收法定原则中“法”的含义作了明确界定……我国应以《立法法》修订为契机,在立法活动中全面贯彻实施税收法定主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税收法律体系,实现税收法治的目标。”③李伯涛:《税收法定主义的立法表达》,《学术交流》2015年第10期。刘剑文和耿颖重点研究了我国目前存在的授权立法失范问题。他们认为:“我国税收领域已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合法性危机,失序、失范的税收授权立法更是税收合法性的重灾区,阻碍了税制改革的健康运行、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和税收法治的全面建设……建构税收授权立法的合法性基础……统合立法授权源头的必要性、明确性与授权立法过程的程序正义、实体正义。”①刘剑文、耿颖:《税收授权立法权的合法行使:反思与建构》,《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熊伟认为:“税收法定主义是民主财政、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鉴于税收法定并非税法唯一的原则,也非最高效力的原则,还需要妥善考虑它与量能课税、实质课税、禁止溯及既往、契约自由等原则的协调。”②熊伟:《重申税收法定主义》,《法学杂志》2014年第2期。
关于绝对税收法定在实践中遇到的困境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税收立法实践层面税收法定所面临的困境。透过增值税立法试点的进程,既要看到我国税收立法的“试点模式”以往通行的必要性,又要特别关注其在合法性和合理性方面存在的不足。尤其应重视在授权立法和课税要素调整方面严格贯彻税收法定原则,防止立法“试点”对公平和效率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全面提升我国的税收法治水平。③张守文:《我国税收立法的“试点模式”——以增值税立法“试点”为例》,《法学》2013年第4期。大量的试点立法贯穿于我们的税法实践,这与绝对税收法定原则有着明显的违背。
其次,如何理解大量的税收条例和税收政策问题。有学者认为对税收法定的认识提出一些看法,认为要全面看待税收法定原则需注意几点:“一是应统筹规划、区分类别、循序渐进地贯彻落实。二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不能影响税收调节功能的发挥。三是税收立法既包括全国人大制定法律又包括国务院制定实施条例和必要的税收政策。”④王家林:《应当正确理解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中国财政》2015年第20期。按照绝对税收法定原则,则这些条例和税收政策之合法性存在很大问题。
再次,绝对税收法定原则与税收实践中的包税制、税收指标考核制脱节较大。理论本身具有先进性,但首先要对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具有解释力。深入观察中国的税收法律实践,则可以看到,一方面税收法定原则已经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另一方面则在经济压力持续下行背景下,地方税务机关对于税收任务指标的层层落实。“当代中国的征税机制,不论名义如何,实际上都是税收收入预先定额、层层分包下发的包税制。征税机构和地方政府是作为承包商和代理人角色,被处于委托人位置的中央政府、上级部门要求必须完成一定的财政收入这一承包目标,这样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出现事实上的包税制。税收任务目标的下达和完成,就是这种制度运作的特征。这种包税制在名称上并未被正式承认,却在事实上存在。”⑤李熙:《“税收定额任务”产生“过头税”》,最后登录于2016年3月15日,http://3g.163.com/news/15/0114/09/ AFTMJ6CP00014JHT.html。这意味着,在中国的税法实践中,存在两种背道而驰的规则。表面上的“税收法定”要求税务机关按照法律规定来确定并征收税收,而事实上的“包税制”则成为事实上的潜规则。因为税收指标的完成与官员的官帽直接挂钩,所以相比明面上的规则,事实上的潜规则具有更迫在眉睫的压力。事实上的“包税制”的背后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保证增长的要求。“税收法定原则”不仅仅在于其对于公民财产权的保护,而且在于其可以为整个社会提供安定性和可以预测的未来。从这一点上来说,“税收法定原则”无疑是优于“包税制”的。但中国的“包税制”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要求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而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需要稳定的财政汲取能力作为保障。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中国国民目前的纳税意识应该说总体上不强,没有一个强制性的力量来进行组织,财政收入无法保证。所以目前中国税收法定的最大困境在于理论与实践的高度脱节。绝对的税收法定主义存在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与税收实践存在太大的差距,所以需要予以适当调整。对于税收实务部门而言,如果法律规则或原则过于富有理想主义色彩,以至于在实践层面无法实施,那么他们又面临着实践中另外的考核压力,那么他们必然会选择另外一个与他们自身利益相一致的潜规则。无法完成上级税务部门层层下压的税收任务指标,那么他们自身的职务就无法得到保障。
最后,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除了有法可依之外,更大的问题在于有法不依,即税法遵从度不高。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之所在。有法不依的问题,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整个国民的素质不高,对于税收有很强的抵制心理;另一个则可能是我们的法律原则和规则与税收征管实践相差太远,使得税收征管机构无法实施。法律规则是历史的产物。每个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其法律理念应该体现其时代性。那么中国处于的这种飞速发展的转型时期,面临纵向的社会转型和横向的国际竞争两方面的压力,本身对于税制有着较强的灵活性要求。税收法定原则的绝对主义,虽然看上去很美,但无法适应今天中国的税法实践的需要。这使得我们又想起了霍姆斯:“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
四、 相对税收法定的实践意义和操作建议
(一)相对税收法定的实践意义
面临着绝对主义的税收法定原则和税收实践中的包税制,我们必须找出一条解决的道路,解决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分歧。当理论和实践出现巨大分歧时,两种都应该作出一定的让步,才可能找出最优道路。毫无疑问,包税制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税收征管体制。如果说中国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让全世界刮目相看的话,那么税收征管体制还依靠原始的包税制,则暴露了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内在不足。包税制隐含着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不信任和单方面的强制性。也就是说,政府无法依靠国民自觉的缴纳税收来维持国家治理所需要的财政税收收入,只能依靠自上而下的单方面的行政强制来实现对财政收入的组织,从而保证整个国家的运行。由于这种财政税收的组织是单方面、强制性的,税务机关与国民之间是不平等的关系。单方面、强制性、不平等都进一步降低了国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和遵从度。这反过来使得税收征管成本极度高昂,国民普遍存在偷逃税行为。从日常经验来看,公务员、教师、私企工作人员、农民工等各个社会群体都不以多缴纳税收为荣,反而以少缴甚至不缴税收为荣。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暴露了国民缺乏主人翁心理。
张怡从税收法定的发展前景来分析,把税收法定分为衡平法定和税收实质公平两个阶段。她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原生于民主并以‘议会’为权力标志决定税赋的取舍与存废,而在均衡与非均衡经济制度迥异的境况下,‘议会’权衡公平与正义之基石如何安放,岂能以泛公平论轻率涵盖之。……理论上深入反思并从实践中强化逆调整,方能在税收衡平与法定之下促成非均衡经济社会的实质公平。”①张怡:《税收法定化:从税收衡平到税收实质公平的演进》,《现代法学》2015年第3期。
首先,现实的选择是对绝对主义的税收法定原则予以相对化,赋予财政税务部门和地方人大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罪刑法定主义也经历了早期绝对主义的罪刑法定主义,到现代的相对的罪刑法定主义。这背后既是辩证法使然,也是社会生活的发展所致。没有绝对的权力,也没有绝对的权利。不论是人身权,还是财产权,都不是绝对的。公共财产权的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把财税法视为公共财产法的部分,财税法实质上就是合法的将私人财产权转化为公共财产权的法律规则。随着经济的高度社会化,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与人之间的依赖越来越强,所以不可避免地需要政府作为公共机构来进行资源配置和提供公共服务。如果遵循绝对的私人财产权观念,那么作为公共机构的政府将无法获得足够的财力来支撑其运转。所以无论是私人财产权,还是公共财产权,都不是绝对的。如果公共财产权是绝对的,那么私人财产权无存在之空间,个人将没有动力不断进行创新。因为这不符合成本收益最大化的逻辑。反过来说,对私人财产权的无限制保护,也会使得公共财产权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使得公共事业成本过于高昂,而变得难以推动。观察西方很多发达国家,今天的基础设施建设,由于拆迁成本过于高昂,无法进行。从历史和实践的双重视野来考察,私人财产权和公共财产权都是相对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只有在两者之间有一个相对平衡的转化机制,才能使得整个经济社会的运转最有效率。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实质上就是土地公有制和土地私有制的混合体。井田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块公田周围环绕着八块私田,私田的产品归农民自己所有,而公田的产品作为赋税归领主所有。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土地制度在展开。但不论哪朝哪代,都无法实现彻底的土地公有制或者彻底的土地私有制。
其次,通过税收法定原则从绝对主义向相对主义的转化,实际上是加强了公共财产权的实施主体财政税务机关的权力。表面上削弱了对纳税人财产权的保护,但是如果通过这种原则的转化,使财政税务机关能够从潜规则转入到明规则中来,纳入法治的轨道,从而实现理论与现实的有机统一,长远来讲有利于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在公共财产权和私人财产权之间获得一种平衡,即两者的转化应该是成本较低的,这也符合科斯定理的法律经济学逻辑。正因如此,文章才提出相对主义的税收法定原则。
(二)相对税收法定的操作建议
第一,完善地方的税收立法权,适当扩充税收法定中“法”的含义。目前中国的税收法定原则遇到的一大困境就是与地方财政自主的冲突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这里的“法”。按照目前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这里的“法”就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这样去理解税收“法”定必然使得包括省级人大在内的地方政府无任何税收立法权或者自由裁量权。在适当的时机,应赋予省级人大制定相关税收法规的权力,但须报全国人大备案和审查。
第二,完善目前的授权立法制度,增设全国人大对地方政府的授权立法。目前的《立法法》只规定了全国人大对国务院的授权立法权,而无对地方政府的授权立法权。法治本身与时间、空间都是相互关联的。中国的一个省基本上在土地面积与人口数量都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所以在法律规则上毫无权力不符合实际。如果明规则无法得到满足,地方政府一定会寻找变通办法。按照绝对的税收法定原则,地方政府在税收立法权上无任何之空间,包括税种、税率、税基等方面。那么在目前进行的税制改革中,就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个人所得税法改革。每个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个人所得税的具体标准上,却无任何自由裁量之权。这本身就不符合量能课税的公平原则。另外,面临同样问题的还有正在进行的环境税改革和房地产税改革。中国作为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各个省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按照“一刀切”的方式来课税,违反了税法公平原则。现在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很迫切了。比如在个人所得税法改革问题上,不同省份的差别就非常大。另外在环保问题上,不同省份的情况和阶段也千差万别,全国“一刀切”实际上是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的。所以,给予地方人大机关在税法的一些具体标准(如税率、扣除标准)等方面的规则制定权,符合税法公平原则。在未来时机成熟时,也可以考虑制定地方税法,赋予地方新税种开征权。此次《立法法》修改,赋予了地级市在市政管理等方面的法规立法权,但在授权立法方面则控制较严格。未来可以考虑由赋予全国人大对省级人大或政府的授权立法权,但这种授权立法应该是具体的、有期限的、非空白的授权。而且这种全国人大对省级人大或政府的立法授权应该是在某部单行法律中授权,即对某部法律的实施授权省级人大或政府来进行相关的法律规则制定,并在时间等程序上予以明确。
第三,关于税收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对税法解释不能一概否认其合法性。关于税收征管程序的问题,建议不要纳入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中来。目前税收征管机关对于税收征管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税法解释,尤其是关于程序问题,不宜一概否认其合法性。比如一些税收优惠政策的具体实施程序。一些非程序问题,也要视情形考虑其合法性。比如国务院制定了新能源汽车的税收优惠政策,但是具体哪些新能源汽车车型可以适用税收优惠,税务机关制定的车型目录,就并非程序问题。这种对税法进行的解释性规则,则不可一概否认其合法性。可以考虑仿效日本战后的蓝色申报制度。对于符合一定资格的纳税人,由税收征管机关授予其蓝色申报人资格。纳税人获得蓝色申报人资格后,可以按照蓝色表格进行纳税申报,并获得相应纳税之优待。这对于目前国内纳税人消极进行纳税申报的现状,是一个不错的征管方式。
第四,关于合法性原则,要与信赖保护原则相协调,符合纳税人权利,审慎处理包税问题。按照绝对主义的观点,税务机关无权就法律上予以明确的内容予以变通。然而现实生活瞬息万变,法律有限而情事在不断变更之中。所以民事法中有情事变更原则,而刑事诉讼法中有辩诉交易制度。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就纳税时间、方法达成的和解、协定一般应认定其不合法。但是如果对纳税人义务进行减免税这样一些对纳税义务者有利的行政先例法已经有先例时,税务机关则应受此约束。①[日]金子宏:《日本税法》,战宪斌、郑林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2-63页。如果固守绝对主义的税收法定原则,则税务机关毫无疑问无权对法律规定的内容予以变通。即便涉及人身权之刑法,其中尚有免予刑事处罚的规定(即当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时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实质上是赋予了司法机关刑事处罚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也是现代人权理论发展对于各个法律领域产生影响的表现。在税法领域同样如此。正是因为税法要对纳税人权利和国家的公共财产权予以有效保护,所以当税务行政机关与纳税人进行一定之约定有利于纳税人,并符合公共利益时,则不应以税收法定之绝对主义来否定其合法性。这实际上借鉴了民法和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比如涉及包税制的问题。未来我们税制改革的方向无疑是税收法定主义,但是对于既有之包税,要区分对待。如果是那种寅吃卯粮的过头税,毫无疑问应否认其合法性。如果是长期以来,税务机关基于便利原则,与纳税人或相关机构所达成的稳定的包税协议,双方一直依此而行,则构成行政惯例,不应一概否定其合法性。法律实践千差万别,一些地方税务机关征税和纳税人缴纳税收都十分不便,税务机关将相关的义务承包给其他机构,构成稳定的惯例,对于纳税人和税务机关都很便利,纳税人对此已产生稳定的预期,则从实质上符合纳税人权利之保护,也符合国家公共财产权利之保护。依此推而广之,从上到下的包税问题,也要区分对待。对于长久形成的行政惯例,如对双方都产生稳定的预期和信赖,则不可贸然否定其合法性,从而损害纳税人和国家的预期。相反,如果是遇到某种危机或外在之压力,某级政府则突然改变之前长期存在的行政惯例,要求税收法定,其实质上反而不符合纳税人权利的保护。
第五,关于禁止溯及既往原则的相对化。通常无论在刑法中,还是税法中,都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刑法中一般奉行从旧兼从轻原则。这一原则实际上也可以借鉴到税法中来。禁止溯及既往原则是一个法治的通行原则。不能用现在的法律来约束过去的行为,这是反对封建专制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发现这不是绝对的,因为新的法律不一定是对纳税人不利的。如果是对纳税人有利的新税法规则,则可以予以适用。然而这一原则的适用,仍然要涉及赋予税务机关相当的裁量权。因为纳税人的财产权与国家的公共财产权某些时候是相互矛盾的,对于纳税人的税务减轻则意味着公共财产权的减少。是否对纳税人适用此溯及既往规则,仍然要由税务机关视整体经济环境、宏观经济政策而定。所以为了防止税务机关滥用相关的权力,则有必要设置相关的税务法院,对于税务机关的行政自由裁量予以有效的监管和约束。
(责任编辑:海 林)
New Study on the Principle of Statutory Tax:From Absolutism to Relativism
Zhang Xuebo
(Political and Legal Department,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Beijing 100091,China)
Modern civilization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statutory tax and the principle of a legally prescribed punishment for a specified crime. The principle of a legally prescribed punishment for a specified crime is the protection of personal rights,while the principle of statutory tax is the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the research on the principle of statutory tax places more emphasis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property rights of citizens,but ignores the protection of the state financial powe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roperty law has recognized that the property right is not a pure concept of private law,but a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property rights of citizens and public property rights. In this sense,the principle of statutory tax as the cornerstone of the modern state and civi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of guaranteeing a dialectical unity of public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property rights of citizens. In addition,how to implement the principle of statutory tax is not only a matter of legislation,but also a practical problem.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ax index and other practical issues in tax practice to prevent from a serious discrepancy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actually achieve dual protection of public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property rights of citizens. Therefore,traditional principle of absolute statutory tax cannot completely adapt to the needs of modern economic society,and should be replaced by the principle of relative statutory tax.
principle of statutory tax; property right; public property; absolute statutory tax; relative statutory tax
OF432
A
1009-0150(2016)04-0108-11
10.16538/j.cnki.jsufe.2016.04.009
2016-04-12
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税收立法模式实证研究(1977-2015)”(15CFX050)。
张学博(1981-),男,湖北巴东人,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副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