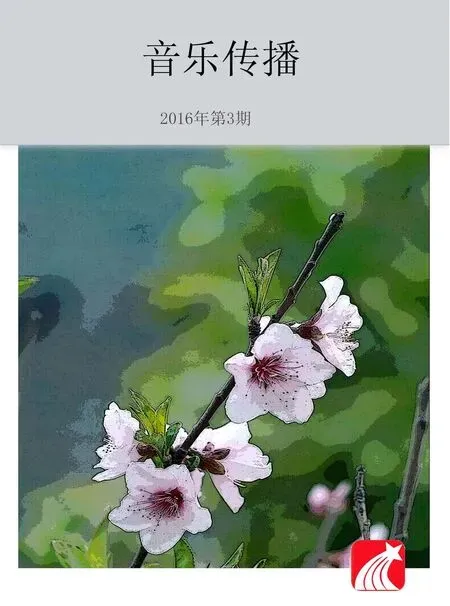音乐社会史视角下的姜夔之乐伎“小红”考
■陈四海 韩雪
(陕西师范大学,西安,710062)
音乐社会史视角下的姜夔之乐伎“小红”考
■陈四海韩雪
(陕西师范大学,西安,710062)
宋朝统治者提倡士人蓄伎,让这个时代留下很多发生在文人与伎女之间的故事,这些故事也频繁被反映在当时的诗词创作中。而在姜夔一首《过垂虹》千古绝唱的背后,又有着乐伎小红在被范成大赠予作为自己忘年之交的姜夔后是否与姜夔同归的学术争议。笔者经过研判文献,倾向于二人同归。小红作为姜夔失恋后的精神慰藉,给姜夔创作中的清冷增添了几分欢愉。然而,阶层的板结和世事的多变最终又让姜夔失去了小红,并终生怀念。该案例可期为音乐社会史研究提供一份素材。
乐伎宋词古代音乐活动姜夔范成大
姜夔(1154—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南宋文人,精通诗词、音乐、书法,是一位难得的全才。“小红低唱我吹箫”,是姜夔于绍熙二年(1191年)冬所作《过垂虹》中的诗句,他在诗中那种潇洒悠然的清客生活让许多后人羡慕。然“小红”究竟何许人?她和姜夔又有着怎样的联系?笔者在查阅前人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小红的遗迹作了进一步考证。
北宋初,宋太祖为了加强皇权统治,防止藩镇割据的再次发生,实行“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改革措施,并沿唐五代之习。此间他以高官厚禄赐予臣下,希望他们都能够安于享乐,在温柔乡中颐养天年。《宋史·石守信传》载:
帝(太祖)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
为了进一步达到目的,宋太祖还一改历代统治者对官员蓄伎的政策限制,在鼓励功臣蓄伎的同时,又大力倡导职官蓄伎。宋代李廌《师友谈记》载:
仁皇(仁宗)一日与宰相议政罢,因赐坐,从容语曰:“幸兹太平,君臣亦宜以礼相娱乐。卿等各有声乐之奉否?”各言有无多寡。惟宰相王文正公不迩声色,素无后房姬媵。上乃曰:“朕赐旦细人二十,卿等分为教之,俟艺成,皆送旦家。”一时君臣相悦如此。
宋朝蓄伎之风袭自唐代贵族们在家蓄养歌伎以供自己享乐,正如沈松勤先生所说:“与唐代一样,宋代士大夫在官府‘得以官妓歌舞佐酒’,在家则蓄养歌舞妓女,每逢宴饮,命家妓奏乐唱词,以助酒兴,成了宋代士大夫家庭中普遍流行的娱乐方式。”①沈松勤著《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宋朝社会制度与唐朝相比有所变化,在当时“重文抑武”的政策下,文人的思想异常开放。他们常与歌伎酬唱、交往,有文人更是把歌伎引为知己,这股蓄伎之风影响着宋代文学的创作和传播,也是“小红”出现在诗句中的根本原因。
一、《过垂虹》背后的疑问
“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这是《过垂虹》的全文诗句,小红因其得以传名。关于“小红”何许人,元人陆友仁《研北杂志》中的一段文献记载了其身份:
小红,顺阳公(范成大)青衣也,有色艺。顺阳公之请老,姜尧章(姜夔)诣之。一日,授简征新声,尧章制《暗香》、《疏影》两曲。公使二妓肄习之,音节清婉。姜尧章归吴兴,公寻以小红赠之。其夕大雪,过垂虹赋诗曰:“自琢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尧章每喜自度曲,小红辄歌而和之。
《过垂虹》中被人称颂的爱情故事,曾被元代陆友仁,以及“明初十才子”之一的张羽,还有文学家刘逸生、词学宗师夏承焘等写进自己的作品之中;清代张镠所画《小红低唱我吹箫》一图及画家任颐的《小红低唱图》也均传世,两幅名作皆以小红与姜夔同回苕溪的船为场景,描绘了整首词的意境。
然而,在人们赞赏《过垂虹》中这一情境时,金文明先生却在《姜夔〈过垂虹〉诗和“十四桥”试释》一文中对这首诗中小红是否和姜夔一同乘船返回吴兴提出质疑:姜夔在垂虹桥与挚友范成大告别,与他所爱的姑娘小红坐船远去,留下诗作一首这种说法,是对古代文献的误读,并不符合史实,范成大是在姜夔回家之后,没过多久派人把小红送去的。所谓姜夔与他所爱的姑娘小红坐船远去的说法,属无稽之谈。若将《过垂虹》当作一首描写男女恋情的作品来引用和发挥,就背离了作者的原意,是一种不应有的误读。①参见金文明著《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书海出版社2003年版。金先生认为不少人对《过垂虹》误读了,此说法间接否定了张羽、夏承焘、陆友仁等人的著作,若此观点成立的话,关于描述姜、红二人游船过垂虹的那两幅传世名画就纯粹是艺术想象了。金认为,关于姜夔与小红的爱情故事,最早出处即不过是陆友仁的《研北杂志》(如前面所引)。
但他又提出以下疑问:“‘姜尧章归吴兴,公寻以小红赠之’一句,‘寻’是个关键的字眼。如果范成大早在姜夔离开石湖前就把小红送给了他,那么这里只要说‘姜尧章归吴兴,公以小红赠之’就可以了,根本用不到那个‘寻’字。现在,陆友仁特地把它加上,绝非无意的赘笔。”②同上。
对于这个观点,许贵文先生写了一篇《姜夔是只身过垂虹吗?——与金文明先生商榷》,针对“寻”字作了解释:“从《辞源》《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的解释中可知,‘寻’字作时间副词用时其含义即相继、接着、顿时、不久、俄顷、旋、随等。就表示时间的长短来看,这些释义虽然没有把‘寻’字定指为是几秒、几分、几小时、几天……但前事与后事相隔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后事是紧接着前事发生的。……金先生说陆友仁写这段话时特地加上个‘寻’字,通过这个‘寻’字,就能准确无误地告诉读者,‘范成大是在姜夔回家之后,没过多久派人把小红送去的’,是取‘寻’字所含的‘不久’之义。”在此,许还指出了金的两个小问题:第一是金选择“不久”作为“寻”字的解释,“脱离了‘寻’字在引文中的具体的语言环境”。他认为金“忽视了范成大赠小红与姜夔的背景”。第二是金“孤立地解释‘寻’字,打破了整段话文义的连贯性,割裂了‘寻’字所处的文句与它后面的‘其夕大雪’一句的关系”。许认为“其”是个代词,应解释为“那个”、“那天”、“那晚”。③许贵文《姜夔是只身过垂虹吗》,载《理论界》2006年第9期,第150-152页。这样读后上下语义便通顺了,若割裂开来,则不符合作者的原意。许也提出,金并没有为自己的观点找出一些史料依据,也没有说明是谁在什么时间把小红送回苕溪。笔者认为许的观点,即将“寻”字解释为“随即”更为合理。
二、对疑问的深入思考
姜夔的《除夕自石湖归苕溪》是一组七绝,共十首,写于除夕之夜告别范成大而归苕溪的路上。《姜白石诗集笺注》载:“绍熙二年辛亥,三十七岁……除夕,自石湖归湖州,成绝句,(诗题)大雪过垂虹,作‘小红低唱我吹箫’诗。”④[宋]姜夔原著《姜白石诗集笺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页。可知,姜夔在从石湖归苕溪的路上写了《过垂虹》和《除夕自石湖归苕溪》,即这两首诗的创作时间、地点都是一样的。《除夕自石湖归苕溪》的第七首写道:“笠泽茫茫雁影微,玉峰重迭护云衣;长桥寂寞春寒夜,只有诗人一舸归。”前述金先生认为其中“长桥寂寞春寒夜,只有诗人一舸归”一句正是诗人孤身一人雪中过垂虹桥的情景写照,其难耐的“寂寞”和刺骨的“寒夜”恰恰透露出作者是只身过垂虹的,若小红此时在姜夔身边,姜恐不会写出如此孤寂悲凉的诗句。这一番旁证确实有些道理。《姜白石诗词》中又对这一句做了说明:“这里‘寂寞’、‘只有’、‘一舸’,早就将作者那种愁肠千结、感慨万端的心情和盘托出了。这确是一首情景交融的佳作。”其注释写道:“只有诗人一舸归——诗人,是作者自称。舸,见《念奴娇词注》。这句是说,只有我乘着一只船去。”①杜子庄注《姜白石诗词》,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整句解释通顺合理,难道姜夔在作《除夕自石湖归苕溪》一诗时确实是孤身一人?但是,这一组诗和《过垂虹》又是在相同的时间、地点创作的,难道我们此前持有的姜夔在作《过垂虹》时有小红在身边的论点是错的?一切看起来本已顺理成章的观点在对这句“只有诗人一舸归”的理解上被打断,所以我们不妨对这一句进行进一步考证。笔者在查阅姜夔的这一诗句时,发现大量的资料注释都将其理解为只有诗人一人乘船归去,恐多有竞相模仿之嫌,而未结合姜夔创作的风格特点对其进行深入的探究。
《姜白石诗集笺注》对《除夕自石湖归苕溪》之七的注解中写道:
《左传·哀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吴,吴子御之笠泽,夹水而陈。”《吴地记》:“松江,一名松陵,又名笠泽。”则笠泽即吴淞江。《扬州记》:“太湖一名笠,一名洞庭。”则笠泽又指太湖。②《姜白石诗集笺注》,第178页。
在对《过垂虹》的注解中写道:
范成大《吴郡志·桥梁》:“利往桥,即吴江长桥也。庆历八年,县尉王廷坚所建。有亭曰垂虹。而世并以名桥。”③同上书,第206-207页。
姜夔在过吴江时想起了发生在此的笠泽之战,这是发生在吴越两国间的一次著名江河进攻作战。诗人眼前仿佛重现出交战时的悲壮情景,又想到此时国家正处危难之际,统治者昏庸无道,而自己满腔热血却报国无门,落得靠朋友接济来维持温饱,四处漂泊,悲寂之情油然而生。此情此景,为整首诗定下了凄凉的基调。
《姜白石诗集笺注》中对“只有诗人一舸归”一句的注解为:
杜牧《杜秋娘》诗:“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按白石《庆宫春》词自序:“绍熙辛亥除夕,予别石湖归吴兴,雪后夜过垂虹,当赋诗云:‘笠泽茫茫雁影微’……”又按,白石此行,载小红同归,故以鸱夷载西子自比。④同上书,第179页。
由此,该书对“一舸”做出了正解。姜夔好用典,此处正是引用杜牧《杜秋娘》中的那句“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范蠡以鸱夷子皮自称,故鸱夷指范蠡。《史记·货殖列传》载:“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⑤[汉]司马迁撰《史记》卷一百二十九,梁绍辉标点,甘肃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956页。西子则指西施,对西施的归宿,学界一直有所争议。宋朝姚宽在《西溪丛语》卷上“西施归宿”条说:
《吴越春秋》云:“吴国亡,西子被杀。”杜牧之诗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东坡词云:“五湖间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予问王性之,性之云:“西子自下姑苏,一舸自逐范蠡,遂为两义,不可云范蠡将西子去也。”尝疑之,别无所据。因观唐《景龙文馆记》宋之问分题得《浣纱篇》云:“越女颜如花,越王闻浣纱。国微不自宠,献作吴宫娃。山薮半潜匿,苎罗更蒙遮。一行霸勾践,再笑倾夫差。艳色夺常人,效颦亦相夸。一朝还旧都,靓妆寻若耶。鸟惊入松网,鱼畏沉荷花。始觉冶容妄,方悟群心邪。”此诗云复还会稽,又与前不同,当更详考。⑥[宋]姚宽、陆游著《西溪丛语·家世旧闻》(合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
姚宽总结了西施归宿的三种可能性:一是吴国灭亡后被杀;二是随范蠡一起泛舟五湖;三是回到了会稽。从这句“西子下姑苏,一轲逐鸱夷”中可知,杜牧认为西施是随范蠡泛舟五湖去了。杜牧诗中写鸱夷、西子一同泛舟,正是代指自己和秋娘此时的情景,而姜夔诗中引用鸱夷载西子泛舟五湖的典故,应正是同杜牧诗中一样,将自己比喻成范蠡,而把同舟的小红比喻成西施,这也正暗示了自己乘舟过江时身边有小红陪同。
杜牧奉命出使扬州,途经镇江时,见到年老色衰的杜秋,听其诉说坎坷多难的一生后,写下了《杜秋娘》这首荡气回肠的长篇古诗。该诗用春秋时期的管仲、战国时期的范雎、秦朝的李斯等多个典故,诉说了政局动荡中人、事的变幻无常。诗人在感叹秋娘悲苦命运的同时,也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仕途坎坷的人生,在愤慨激昂的诗句中透露出对当朝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不满。姜夔这首诗与杜牧同样表现了对现实黑暗政治的不满,故以此为典故,来悲怀才之不遇,叹世事之无常。姜夔于同年初春,因感时事作了一首《满江红》,词中描述了山河残破、风雨飘摇中的南宋王朝,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其对国家、人民的担忧:
仙姥来时,正一望,千顷翠澜。旌旗共,乱云俱下,依约前山。命驾群龙金作轭,相从诸娣玉为冠。向夜深,风定悄无人,闻佩环。
神奇处,君试看。奠淮右,阻江南。遣六丁雷电,别守东关。却笑英雄无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瞒。又怎知,人在小红楼,帘影间。①[宋]姜夔原著《姜白石词校注》,夏承焘校,吴无闻注,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孝宗即位后欲收复中原,发动北伐,却大败于金,签订了屈辱合约——隆兴和议。姜夔作此词时,宋金和议已近30年之久,当朝统治者偏安一隅,贪图享乐,不思安危。作者痛斥了当朝统治的昏庸无道,同时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忧思。他在诗句“只有诗人一舸归”中所引典故,不但说明了他在除夕之夜泛舟过吴江时,小红在身边,也解释了整首诗凄凉基调的来由。
金先生认为《除夕自石湖归苕溪》这组诗整体表现出来的情绪较低沉,并举出了五例以作旁证:“应是不眠非守岁,小窗春色入灯花”(第四首);“百年草草都如此,自琢春词剪烛看”(第六首);“长桥寂寞春寒夜,只有诗人一舸归”(第七首);“但得明年少行役,只裁白苎作春衫”(第八首);“少小知名翰墨场,十年心事只凄凉”(第九首)。他说:“从这些沉郁低回的吟咏中,透露出来的是无限的孤寂、落寞和伤感。古语说:言为心声。此时此刻,如果姜夔身边真有一位他所喜爱的小红姑娘朝夕相伴的话,他的心情怎么会如此凄凉和消沉。”②参见《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笔者认为这一观点还可商榷,所举旁证也有以点概面之嫌,因为除了流露孤寂伤感的词句之外,这组诗中仍可以看出轻松愉悦的心情。如第一首:“细草穿沙雪半销,吴宫烟冷水迢迢。梅花竹里无人见,一夜吹香过石桥。”这是描写自湖州归苕溪的沿途风景,由写近处的细草、沙雪到渐行渐远的吴宫被烟水笼罩,生动地刻画了小舟在江中轻快远行的场景,正表现了诗人的轻松愉快。姜夔很可能是有佳人陪伴,才写了此诗。
前面提到的《过垂虹》一诗的描写也为我们作了一个实证。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宋诗鉴赏辞典》中进一步阐释了这首诗表现出的情趣意境:“携伴佳人,吹吹唱唱,一路轻舟过垂虹,诗人陶然心醉,因此虽是隆冬雪天,诗中却毫无肃杀寒意,而是气氛热烈,情趣盎然,音调谐和,意象清雅,咏之沁人心脾。”
金先生文章其实也指出:“《除夕自石湖归苕溪》十绝句中,第五首后两句曰‘已拼新年舟上过,倩人和雪洗征衣’。倩:请。不得不在一叶扁舟上度过新年,请人和雪洗去仆仆征尘。请的是谁呢?如果是姜夔‘只身孤舟’,那么唯一可请的只能是艄公了,可是船在行进中,那是不可能的,而且真若那样,恐怕也就没有什么诗意可言了。因此,所请之人便是小红无疑。”③同上。这一论据,再次有力地证明了小红在船上的可能性。
三、姜夔所在时代的乐伎文化
在宋太祖重文轻武、鼓励官员广置田亩和蓄养家伎的政策影响下,有宋一代,士大夫文人蓄伎之风尤为突出,例如南宋诗人张镃有“名妓数十辈”(见[明]田汝成著《西湖游览志馀》卷十),英名千古的文天祥也“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见[元]脱脱等撰《宋史》卷四百一十八《文天祥传》),就连豪放派诗人苏轼也“有歌舞妓数人”(见[明]陶宗仪纂《说郛》卷三十四上)。官员随着职位的升高,蓄伎的数量也越来越多,据宋代朱弁的《曲洧旧闻》卷一,宋仁宗梳头太监称:“两府(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制(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知制诰)家内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宋仁宗时任宰相的韩琦“在相府时,家有女乐二十余辈”,④[宋]江少虞辑《宋朝事实类苑》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宋徽宗时任宰相的王黼“家姬数十人,皆绝色”。⑤[宋]王明清撰《玉照新志》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范成大作为当时的“副宰相”,乐伎人数可想而知。
当时的乐伎音乐造诣很高,且通晓诗词歌赋,小红作为范成大身边最出色的乐伎,其色艺俱佳,相传她不仅能歌舞,且善吹箫,据《蕙风词话·续编卷二》载:
词人用红箫事,以姜白石侍儿小红善吹箫也。刘宾客和窦夔州见寄寒食日忆故姬小红吹笙诗云:“鸾声窈眇管参差,清韵初调众乐随。幽院妆成花下弄,高楼月好夜吹时。忽惊暮槿飘零尽,唯有朝云梦想期。闻道今年寒食日,东山旧路独行迟。”则是红箫之前,又有红笙矣。⑥[清]况周颐原著《蕙风词话·广蕙风词话》,孙克强辑考,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页。
姜夔于1187年4月经杨万里介绍结识范成大,此时的范成大在石湖居所辞官养病,已是花甲老人,而姜夔当时33岁。姜、范二人相识初期,范成大就曾写诗称赞姜夔“新诗如美人”(《次韵姜尧章雪中见赠》)。当年夏六月初四,姜夔专程从石湖赶往苏州为范成大祝寿,并创作了《石湖仙》,该词以平实自然的笔触述说了范成大不卑不亢的一生,感情真挚,表达了作者对范成大品性学识的钦佩和赞美。范成大在苏州养病期间,姜夔经常到石湖居所探望,《玉梅令》一词就描述了范成大此时的生活情境:
(小序:石湖家自制此声,未有语实之,命予作。石湖宅南,隔河有圃曰苑村,梅开雪落,竹院深静,而石湖畏寒不出,故戏及之。)
疏疏雪片,散入溪南苑。春寒锁,旧家亭馆。有玉梅几树,背立怨东风,高花未吐,暗香已远。公来领略,梅花能劝,花长好,愿公更健。便揉春为酒,翦雪作新诗,拼一日,绕花千转。①《姜白石词校注》,第88页。
据《姜白石词校注》注释,此词为“宋光宗绍熙辛亥(1191年)冬客石湖家、雪中范村访梅之作。石湖自淳熙间请病归苏州,至此已十余年”。②同上书,第89页。其小序介绍了作品的由来,是姜夔应范成大之请对其所作的曲子进行填词。姜夔从庭院景色的深静、天气的寒凉,写到范成大因病不出,作词戏于屋内的清冷。词的最后,姜夔劝范静心养病,愿他早日康复,表达了真切的关怀。
在姜夔与范成大相识的几年里,二人“雪里评诗句,梅边按乐章”(《悼石湖三首》其三),③同上书,第105页。互相交流切磋,成为忘年之交。范成大一直隐居到他于1193年9月病故。(《范成大年谱》:“秋季疾转剧,疏请致仕;九月五日卒,年六十八。”)④于北山著《范成大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01页。范既殁,姜夔专程从绍兴赶往苏州送葬,并作《悼石湖三首》来纪念这位亦师亦友的文人:“百年无此老,千首属何人”;“酸风忧国泪,高冢卧麒麟。”字里行间无不流露着对范成大知遇的感激以及失去好友的悲切。
此前的绍熙二年冬,姜夔曾在雪中去石湖拜访范成大,《雪中访石湖》就是写于此时,范成大以《次韵姜尧章雪中见赠》一诗和之。此次逗留长达月余,二人志趣相投,常在一起讨教诗词、宣泄心中悲愤,《暗香》、《疏影》两首佳作就是此时所作。这两首词均借景抒情,将对身世的悲慨、对恋人的怀念及对家国的愤懑交织在一起,哀婉之情倾泻而出。范成大命乐伎弹唱,听后赞赏有加,更视姜夔为知音,遂将小红赠予姜夔,据《本事词·卷下·南宋辽金元》载:“范之家妓善歌者,以小红为最,姜颇顾之。姜告归,范即以小红赠之。”
范成大将小红赠予姜夔,或许是因自己年事已高又有恙在身,愿为小红另寻他处,或许是想借此来安抚姜夔与合肥恋人分别后的痛楚。据夏承焘考证,姜夔于1176至1186年间在合肥有段刻骨铭心的恋情。对这段情事,通过姜夔大量的恋情词可以考证:
恨入四弦人欲老,梦寻千驿意难通。(《浣溪沙》)
一点芳心休诉,琵琶解语。(《醉吟商小品》)
为大乔,能拨春风,小乔妙移筝,雁啼秋水。(《解连环》)
姜夔所遇对象为姐妹二人,姐姐擅弹琵琶,妹妹擅抚筝。但词人所恋究竟是其中哪一位,至今未可知,我们只知这段恋情最终未成正果。《凄凉犯》小序和词中分别流露出作者对往日恋人的怀念:“合肥巷陌皆种柳,秋风起兮骚骚然”;“马嘶渐远,人归甚处,戍楼吹角”,“旧游在否,想如今,翠凋红落”,“怕匆匆,不肯寄与,误后约。”⑤《姜白石词校注》,第78页。范成大看到友人如此伤心,完全可能将小红赠予,以“慰其合肥伤别之怀”。⑥[宋]姜夔原著《姜白石词编年笺校》,夏承焘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73页。
不论范成大出于何种考虑,这对姜夔来说无疑是个意外的收获。姜夔在除夕夜别范成大,归家路上就作了那首《过垂虹》,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四、对“小红”归宿的推测
伎人地位自古以来就十分低下。那么,“小红”最终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
宋代伎女大致可划分为四类——官伎、军伎、市伎及家伎,主要是在宴饮游乐中为人们提供歌舞表演并斟酒侍奉,通常被称为侍婢。作为女性中的特殊群体,其地位低微,没有人身自由,通常容易被人们忽视。但是,在宋代一些文人眼中,她们是被尊重的群体,文人们认为她们的生活情感应该得到世人的关怀。人称“浪子词人”的柳永,尤擅写歌伎恋情之词,他从女性的视角向世人诉说了伎女坎坷的命运及百感千愁的情感生活,例如《大石调·倾杯乐》:
皓月初圆,暮云飘散,分明夜色如晴昼。渐消尽、醺醺残酒。危阁迥、凉生襟袖。追旧事,一饷凭阑久。如何媚容艳态,抵死孤欢偶。朝思暮想,自家空恁添清瘦。
算到头,谁与伸剖。向道我别来,为伊牵系,度岁经年,偷眼觑、也不忍觑花柳。可惜恁、好景良宵,未曾略展双眉暂开口。问甚时与你,深怜痛惜还依旧。①[宋]柳永原著《乐章集校注》(增订本),薛瑞生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07页。
从中不难感受到诗人对伎女坎坷命运的同情及对女性的尊重。
乐伎通常在门阀士族宴饮娱乐时满足其声色之需,或在诗酒畅谈之余为其弹唱助兴。据《陈书》卷十一载,陈大将章昭达“每饮会,必盛设女伎杂乐,备尽羌胡之声,音律姿容,并一时之妙,虽临对寇敌,旗鼓相望,弗之废也”。②[唐]姚思廉撰《陈书》卷十一,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84页。周密也记录了苏轼与友人及乐伎出游赏玩的事迹:
苏子瞻倅杭日,府僚湖中高会,群妓毕集……③[宋]周密撰《增补武林旧事》卷八“歌馆”,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0册,第7页。
守杭州,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晡后,鸣锣集之,复会望湖楼或竹阁,极欢而罢。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夹道云集观之。④《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西湖游幸”。
士大夫文人在宴会畅饮之时通常会即兴创作诗词,乐伎在旁弹唱助兴。有时会有文人写诗词送给自己喜欢的乐伎,例如,宋代张咏在宴会上就曾作词送给他中意的乐伎小英:
我疑天上婺女星之精,偷入筵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儿初失意,谪向人间为饮妓。不然何得肤如红玉初碾成,眼似秋波双脸横。舞态因风欲飞去,歌声遏云长且清。有时歌罢下香砌,几人魂魄遥相惊。人看小英心不足,我看小英心本足。为我高歌送一杯,我今赠尔新翻曲。⑤[宋]张咏著《乖崖集》卷二“筵上赠小英”,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5册,第13页。
乐伎的卑贱地位决定了她们悲惨的命运。由于侍主病逝或家族变故等原因,这些乐伎通常会被变卖或赠予他人,更有甚者会流落异乡、出家为尼。姜夔在小红的陪伴下,确实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据明代蒋一葵《尧山唐外纪》卷六十一载:“尧章每喜自度曲吟洞萧,小红辄歌而和之”。⑥贾文昭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姜夔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03页。但是。这种“辄歌而和”的日子并没有陪伴姜夔终老,五年后,即庆元二年冬(1196年)姜夔与好友同船去梁溪,夜经垂虹桥,故地重游,不免回想起五年前的冬天,也是在除夕夜,与小红同舟共度的美好时光,遂有感而发写下《庆宫春》。其词序写道:
绍熙辛亥除夕,予别石湖归吴兴,雪后夜过垂虹,尝赋诗云:“笠泽茫茫雁影微,玉峰重迭护云衣;长桥寂寞春寒夜,只有诗人一舸归。”后五年冬,复与俞商卿、张平甫、铦朴翁自封禺同载诣梁溪,道经吴松,山寒天迥,云浪四合,中夕相呼步垂虹……犹相与行吟,因赋此阙,盖过旬涂稿乃定。⑦《姜白石词校注》,第116页。
由此可知,小红此时已经离开了姜夔。姜夔这首《庆宫春》也可以看出他想念小红:
双桨莼波,一蓑松雨,暮愁渐满空阔。呼我盟鸥,翩翩欲下,背人还过木末。那回归去,荡云雪,孤舟夜发。伤心重见,依约眉山,黛痕低压。采香径里春寒,老子婆娑,自歌谁答。垂虹西望,飘然引去,此兴平生难遏。酒醒波远,正凝想明铛素袜。如今安在,唯有阑干,伴人一霎。⑧同上。
《姜白石词校注》注释中说,“垂虹西望”三句“暗用范蠡携西施扁舟泛太湖典故。太湖在垂虹亭之西。飘然引去四字,惟范蠡功成身退足以当之”。⑨同上书,第119页。诗人词中所写的西施显然如前文所述,正指小红。而“明铛素袜”显然是“女人的耳珠和足衣”。⑩同上。诗人回忆起小红当时穿戴的首饰衣物,可见小红的靓影在诗人眼中仍清晰可见。
嘉定十四年(1221年),姜夔去世。他生前四处漂泊,靠朋友接济勉强维持温饱,过着一种寄人篱下的生活,死后也是在吴潜等朋友的资助下才得以安置于名人葬处——杭州西马塍。《湖墅杂诗》卷上载:“宋时花药出东马塍、西马塍,皆名葬处,白石殁后葬此。”《城北杂记》所载的名士苏泂(一说苏石)挽姜夔诗中说:“所幸小红初嫁了,不然啼损马塍花。”(见《杭州府志》卷三十九“塚墓一”)由此可知小红在离开姜夔后便嫁人了。清代郭麐在《买陂塘》中写道:“问词人、马塍遗迹,可余花木深秀。小红嫁后青春老,剩有萧疎秋柳。”(见《灵芬馆词四种·蘅梦词》卷二)作为乐伎的小红年老色衰,技艺减退,嫁人算是她最好的归宿。魏标惋惜曰:“小红嫁了词人死,谁向荒原觅古邱”。①《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姜夔资料汇编》,第307页。而苏洞的《到马塍哭尧章》中则有这样几句:“今日亲来见灵柩,对君妻子但如痴。”“孺人侍妾相持泣,安得君归更肃宾。”“儿年十七未更事,曷日文章能世家。”(见《泠然斋诗集》卷二)这也说明,姜夔在小红离开后另娶了妻妾。他除了正妻萧德藻之侄女外,还有几位恋人侍妾,据《姜白石词编年笺校》记载,“陈谱引泂寄尧章诗‘闻似磻溪隐姓名,阿鬟仍是许飞琼’谓阿鬟即后妾之名,亦即白石次子瑛之生母”。②《姜白石词编年笺校》,第295页。
千年时光匆匆过去,姜夔《过垂虹》中对这位女子的描画,直堪傲立中国古代诗词中描写女性的佳作之林。词中神仙伴侣的惬意,也许正是如今身处喧嚣闹世中的人们所欲追寻的意境。而对小红身世及其与姜夔的交往的研究与总结,也应能为文学及音乐社会史方面的探讨尽绵薄之力。
(责任编辑:魏晓凡)
陈四海,陕西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音乐史。
韩雪,陕西师范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学专业2015届硕士毕业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音乐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