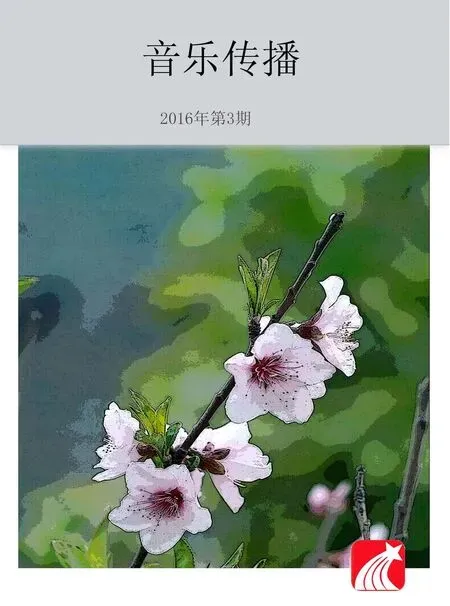中国“独立音乐”传播路径探究
■赵贺佳
(上海理工大学,上海,200237)
中国“独立音乐”传播路径探究
■赵贺佳
(上海理工大学,上海,200237)
本文从近年来国内“独立音乐”发展背景与现状、传播方式及传播路径三方面,结合国外“独立音乐”发展历史,分析概括出我国的“独立音乐”的地下形态的封闭循环、独立音乐厂牌与新媒体支持下的开放循环以及主流流行音乐的“收编”与大众媒体的开放传播这三条传播路径,旨在为中国的“独立音乐”传播提供理论支持,也为文化审查部门合理引导独立音乐发展提供参考方向。
独立音乐音乐传播传播路径
“独立音乐”这个称呼取自于英文单词independent music,主要是用来描述有别于主流商业唱片厂牌所制作的音乐,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并非一种特定的音乐类型。独立音乐的制作过程独立自主,音乐人或独立音乐厂牌往往不受商业理念的影响,坚持自我的音乐理念,因此往往具有小众化的特征。
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着巨变,城市化进程、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带来的变化催生了一批有别于流行音乐唱片工业、极具思想性和批判性、带有强烈人文精神的独立音乐作品。受到渠道和资金的限制,独立音乐长期处于小群体的传播状态。直到现今,随着独立音乐厂牌、户外音乐节、社交媒体、智能终端等软硬件的成熟与发展,独立音乐有了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传播渠道,逐渐开始被主流文化收编并进入大众视野。
一、中国“独立音乐”发展背景与现状
人们一般把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兴起、不同于当时主流音乐的某种风格的摇滚乐追认为独立音乐的鼻祖。“独立音乐的发展受到所处环境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经济条件影响和制约,这是独立音乐在世界每个地方呈现不同发展程度的主要原因。”①王均安《浅谈流行音乐中的“独立音乐”》,载《文史博览(理论版)》2007年第12期,第13-18页。中国的独立音乐发展起步时间较晚,直到近十几年,小众、独立音乐厂牌的出现,以及各种音乐节的风起云涌,中国“独立音乐”的说法才被提出。
中国“独立音乐”发展的背景与20世纪中期的美国颇为相似,2000年到2010年间,独立音乐的批判和创新精神与主流流行音乐当中泛滥的情歌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的长期萧条相比,近年来独立音乐开始受到更多受众的关注。2014、2015年《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中指出,线上销售唱片模式兴起,实体唱片市场零售价逐步提高,独立唱片成为实体唱片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报告首次将独立音乐相关演出纳入了音乐产业报告的统计体系,Live House票房总收入4 954万,“互联网+音乐演出”催生付费直播模式、视频流媒体加入抢占演出市场份额阵营等现象成为音乐演出行业的新亮点;网络音乐版权整顿及MORP数字音乐版权注册平台的运营,为独立音乐人的创作提供了版权上的保障。
在音乐作品版权逐步得到保护和规范、新媒体打通线上线下传播、数字音乐大大降低复制传播成本的前提下,以小成本、小制作生存的独立音乐厂牌和独立音乐人得到了与主流唱片公司竞争的权利,也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内地独立音乐厂牌正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其中最著名的包括“嚎叫唱片”、“摩登天空”、“十三月唱片”、“口袋音乐”等。“摩登天空”旗下的陈珊妮、牛奶咖啡、新裤子,“十三月”厂牌旗下的万晓利、谢笑天、苏阳,树音乐旗下的张楚、窦唯、废墟乐队等音乐人/组合,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欣赏。
二、中国“独立音乐”的传播方式
在国内,独立音乐主要通过室内音乐展演空间(惯称为Live House)、户外音乐节和数字音乐等几种方式传播。
(一)室内音乐展演空间(Live House)
室内音乐展演空间,即“Live House”,全称为“Live music house”。它起源于欧洲,前身是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欧洲独立音乐潮流而兴起的Rock Pub,即现场摇滚乐的展演地。著名的甲壳虫乐队(The Beatles)、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爱尔兰U2乐队等都曾以本地的Rock Pub作为根据地。而20世纪70至90年代,“Live House”先后在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兴起与发展,并融入了地区流行音乐产业发展的全过程之中,促进了两地流行音乐产业的发展。
在内地,Live House出现得较晚,从“育音堂”(上海)、“愚公移山”(北京)、“VOX”(武汉)、“小酒馆”(成都)、“坚果俱乐部”(重庆沙坪坝),到后来的“MAO”、“星光现场”等,到了2014年,已发展出大大小小几百家。很多乐队和歌手通过各地区的Live House完成自己的巡演,催生了一大批喜欢原创音乐的粉丝。各大Live House在经营中形成了自己的擅长的音乐风格,以专业的定位吸引有特定音乐风格偏好的受众。
从演出方式来看,不同于传统演出场馆按座位确定价格的做法,在独立音乐中,音乐人与观众近距离面对面的交流打破了流行音乐偶像高高在上的地位,使得整场演出更像是一种思想和精神的传达;Live House站立式观看演出的形式可以让观众释放出心底的那一份激情。以北京“星光现场”音乐厅为例,其现场最多能够容纳1500人,歌迷与歌手的最近距离达到1米,最远也不过15米,台上演唱者的一颦一笑,歌迷都尽收眼底,可以近距离清晰地体会到真正完美的现场音乐,并可以与歌手近距离地交流。观众还可以随着音乐的节奏扭动自己的身体,可以高举双手为台上的歌手欢呼助威,歌迷与歌手达成完美的互动。演出实行的统一票价,让大家彼此平等,不再有大型场馆演出中的观众等级差别。
(二)户外音乐节
户外音乐节作为西方的舶来品,最初的演出内容并非摇滚乐而是民乐、爵士乐、古典音乐等中产阶级所推崇的音乐。直到20世纪60年代,摇滚乐以批判和思考的精神参与各种社会议题并成为年轻人标榜的对象。80年代的“红楔”、“四海一家”等运动为音乐与政治的结合提供了各种可能的样板;90年代至今,面对全球化、环境污染、种族主义、霸权主义等更加复杂的社会议题,摇滚乐在丰富自身形态的同时,也呈现出越来越多样的反抗姿态。①参看张铁志著《声音与愤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户外音乐节成了音乐人表达这些积极态度的重要平台。
户外音乐节最典型与知名的两个鼻祖是美国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与英国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前者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因“和平与音乐”的反战主题而带上了浓重的历史文化意义,后者规模宏大并在音乐与各式多元文化的交融上堪称典范。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众对于消费文化产品的趣味和审美倾向也逐渐产生了变化。伴随着摇滚乐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不断流行,年轻人对非主流价值观以及另类的生活品味的认同,以及对更加自由开放的文化氛围的追求等,共同促成了中国内地户外音乐节的诞生与不断发展。对于承受着巨大的学习压力以及社会压力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而言,户外音乐节所带给他们的是自由的感觉、自我释放的体验和对存在感的追寻等,这使得近几年,中国内地的户外音乐节的消费群体逐渐庞大,也助长了中国内地户外音乐节市场的繁荣。在国内,20世纪90年代,摇滚乐曾被看作意识形态的对立物而被相关部门极力回避甚至压制,现在则成了音乐产业链中新的增长点,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地方政府也鼓励开展音乐节并对其进行场地支持,以拉动旅游消费、聚集人气、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宣传文化部门对摇滚乐态度的转变,一方面源自近几年国家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鼓励,另一方面则由于逐步认识到摇滚乐迷并非“暴力分子”,而摇滚音乐节也远非充斥反叛和暴力的集会活动。十年间,政府相关部门对户外音乐节的态度已经有了质的转变,推动了户外音乐节在中国内地的快速发展。
国内音乐节从开端到现在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从2000年北京迷笛音乐学校的一场摇滚乐队演出发展到今天,在音乐的风格多元化,以及相关的艺术与文化创意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音乐节的举办数量从2007年的24个增长到2012年的89个,顶峰时期的2013年达到了150个,增长速度飞快。近年发展趋势有所放缓——2014年为148个,2015年减少到了110个。①参看道略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中国户外音乐节发展研究报告》(2007—2015)。其主要原因在于音乐节背后的支撑是音乐作品本身,虽然独立音乐在十多年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作为一种年轻人追捧的亚文化,其优秀作品相对有限。而独立音乐的受众有着狂热性高、黏性大等特点,演出阵容、地点、音乐风格等都会对受众的选择产生影响。因此在经历了高速发展的两年之后,出现了数量下降是市场的理性反应。与此同时,举办时间较长的音乐节已经有效地形成了其品牌优势和固定的受众群体,也成了举办地一年一度的文化地标。随着音乐节数量的连年增长,音乐节举办地也出现了从原先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城市扩展的趋势。
(三)数字音乐
在新媒体尚未发展成熟之前,实体唱片是受众可以获得音乐内容来源的主要渠道,也只有具有强大资产背景的唱片公司才能完成整套出版发行流程,独立音乐人通常承担不起制作和发行过程中的高昂费用。
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以光盘为传播介质的局面,为独立音乐人和小成本音乐厂牌提供了大量复制传播音乐作品的渠道,有效地降低了音乐出版发行的门槛,也将主流唱片公司和独立音乐厂牌拉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尤其是长期制约着中国内地音乐产业发展的网络音乐版权问题,其相关工作在2015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7月,国家版权局发布《关于责令网络音乐服务商停止未经授权传播音乐的通知》,随后三个月内大量侵权内容被下架,国内音乐服务商们纷纷出手向唱片公司购买版权。这一举措有效地重新构建了良性循环的商业模式。2016年IFPI《全球音乐市场报告》指出,“中国正走向真正的交易型音乐市场。2015年,随着几大音乐平台的建立和扩大,交易型音乐市场在中国首现。与此同时,相关主管部门加大了删除侵权内容、打击盗版的力度,国际唱片公司加强了对当地艺人和曲目的挖掘和投资”。②参见国际唱片业协会网站(IFPI)网站文章China:Moving towards paid services,截至2016年9月15日。http://www.ifpi.org/China.php以及IFPI,2016 Global Music Report,Zurich: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the Phonographic Industry,2016,p.17.
三、中国“独立音乐”传播路径
我国“独立音乐”的传播路径,可归纳为以下三种:地下形态的封闭循环、独立音乐厂牌与新媒体支持下的开放循环,以及主流流行音乐的“收编”与大众媒体的开放传播。
(一)地下形态的封闭循环
独立音乐之所以有“地下音乐”或者“非主流音乐”的别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发源于缺乏文化监管的“地下”。在欧美,对地下音乐的监管相对较为宽松,尺度较大的音乐作品同样可以在备案后在音像唱片市场上公开传播。但在中国,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不能触碰到政治、色情、暴力这三条底线,所以传播内容在中国其实是受到很多限制的。因此,文化部在2015年8月开展了对内容违规的网络音乐产品的集中排查工作,共排查出120首内容存在严重问题的网络音乐产品。这些网络音乐产品含有宣扬淫秽、暴力、教唆犯罪或者危害社会公德的内容,违反了《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已被列入网络音乐管理“黑名单”,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提供。名单中不乏一些知名独立音乐人的作品。与此同时,对没有下架但带有明显的颓废、暴力、色情等负面倾向的已上架音乐作品也进行了从音乐服务商自检到文化部门定时抽查等层层审核。
文化部门对公开发行的音乐作品的监管很大程度上是对大众传播、网络以及公开的经营性演出的监管。大批独立音乐人最初和最主要的演出场所是带有浓厚地下色彩的Live House、现场酒吧等小型演出现场。这些演出场所受到的监管较为宽松,以多元、开放和小众的状态为独立音乐人提供了表演其作品的舞台。这也给了音乐人更多的音乐表达空间,带有消极、焦虑、情欲、性爱色彩的信息得以在地下状态完整展现。正如弗洛伊德所认为的,这些在现实生活中被超我压抑的“力比多”——即性欲内驱力——是人的一切精神活动的能量来源。“本我”总是遵循快乐原则,迫使人们满足它追求快感的种种要求。从整个社会的观点看来,这些要求往往是违背道德习俗的。于是,在“本我”与社会现实环境之间出现了一个调节者“自我”。“自我”的任务是尊重现实原则,在这个基础上帮助“本我”实现要求。“自我”既要防止过度的压抑给人造成伤害,又要避免和社会道德公开冲突。这些被“自我”压抑的心理能量通过独立音乐找到合适的场所宣泄。虽然这些内容无法在大众媒体中传播,却在地下获得了众多受众的支持。
独立音乐的地下传播形式构成的封闭循环可以作为积累受众的原始方法,但可以预见的是,一旦进入网络或者大众传播渠道等公开传播环境,地下状态的音乐内容会需要再次受到相关审核。
(二)独立音乐厂牌与新媒体支持下的开放循环
在独立音乐从地下状态进入公众视野的过程中,独立音乐厂牌和新媒体起到了传播渠道的作用。
独立音乐其本身的主要特点在于音乐人对自身音乐作品的控制权,不受主流商业化音乐的左右,以工匠的姿态打磨和创新音乐作品。在没有专业音乐团队的帮助下,自己发行传播唱片会耗费极大的精力,因此大多数独立音乐人会选择签约一些独立音乐厂牌。这些厂牌有一整套发掘、协助、召集独立音乐人(乐队)完成唱片制作、发行、宣传等一系列事宜的团队,并且提供法务、版权等多方面的专业支持。这些团队有的已正式注册为公司,有的则以尚未经审批的个人或民间组织形式存在,前者目前已经发展初具规模并且形成了明显的品牌效应和厂牌特色,如独立厂牌标杆“摩登天空”、小作坊式运营小众音乐人的“十三月”、专攻摇滚的“飞行者唱片”和“嚎叫唱片”、实验色彩浓厚的“兵马司”等等。各独立厂牌各有特色,也挖掘和发展着能突显厂牌特色的音乐人。后者能够得以存活也与目前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缺乏完善的相关管理制度有关,如民间民谣组织“麻油叶”。
在独立厂牌的运作下,不少独立音乐人从Live House起步成了场馆演出级别的独立音乐人。在小型演唱会领域,越来越多的独立音乐人将首次尝试全国剧场巡演,如2014年,宋冬野、好妹妹乐队、野孩子乐队等独立音乐人剧场巡演取得了良好的市场效果。受其带动,越来越多的独立音乐人将尝试大规模全国剧场巡演。例如,程璧启动5场全国剧场音乐会;李志、谢天笑等从小众膜拜逐步“攻陷”千人剧场、万人场馆,寻找更大的空间。和偶像歌手演出迅速出票不同,独立音乐人的粉丝大多是文艺青年,他们买票不是为一时炫耀或者跟风,而是趋于理智。由于独立音乐人的粉丝增长速度相对较慢,他们进万人规模的体育场开唱有一定难度,但是市场的稳定性很强,在万人体育馆演出票房有一定的保证。
独立音乐开放传播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是新媒体。根据CNNIC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6.8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3%。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有90.1%的网民通过手机上网。只使用手机上网的网民达到1.27亿人,占整体网民规模的18.5%。手机、电脑、智能电视、平板电脑等终端的普及,带来的是更多的对接受众的渠道,这也同样降低了受众获得独立音乐作品的难度。
就目前的发展情况看,手机、电脑、智能电视均出现了独立音乐类的应用程序(APP)而且取得了不错的发展成绩。笔者将这些独立音乐类的产品分为了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发展完善的社交平台的新整合和延伸,如“豆瓣”、“微博”等。前者作为一个带有群组产品概念的网站,其主要目的是为用户提供一种服务——这种服务不针对特定对象,而是帮助用户找到符合他们口味的东西。其主要受众为18至25岁的年轻群体,他们喜爱发表评论、观后感,文学素养及鉴赏能力相对较高。针对年轻人的口味,豆瓣推出了“豆瓣音乐人”频道,为所有音乐人、厂牌和播客提供数字音乐服务,协助音乐内容生产者分享好音乐、与乐迷沟通交流。豆瓣音乐人小站分为三种,分别是“音乐人小站”、“厂牌小站”和“播客小站”,将音乐人、独立音乐厂牌、乐评人、Live House与希望进入群组的受众对接。
第二类是面向独立音乐人建立专业传播平台的音乐APP。如“虾米音乐”和“网易云音乐”。与众多音乐类APP不同的是它们将目光聚焦在了音乐人身上,以直接与音乐人签订协议的方式,邀请音乐人加入其平台。它们从理清歌曲版权入手,进而建立可持续的收费下载模式。“虾米音乐”于2013年7月上线了“虾米音乐人”,对音乐人完全免费,从平台上产生的下载收益将100%属于版权所有者。“虾米”的专业性在于其在面向市场初期就以其专业的音乐分类、完善的曲库将众多小众音乐收入其中,吸引了大量小众音乐爱好者。“虾米音乐人”为独立音乐人提供了音乐人标签、专属域名、Demo区和小组,让音乐人可以制作上传Demo和专辑。更关键的是,“虾米音乐人”用户可以对音乐下载进行自主定价。从而实现了小众音乐受众与音乐人的对接,而且有效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音乐人的版权问题。
与主打小众的“虾米音乐”不同,用户群庞大的“网易云音乐”也随后推出了“网易音乐人”,以用户为资源,以其大数据云计算为技术,根据用户偏好,精确向用户推送定制歌单,并且有一套专业的团队制作PGC(User-generated Content,意为“用户生产内容”)平台,使用户可以从音视频、文字等多角度介绍独立音乐人及其作品。对独立音乐人而言,“网易云音乐”为他们提供了高度曝光和接触受众的机会。如“云音乐”独家发布独立音乐人陈粒的单曲数字专辑《爱若》,以1元的价格在线售卖,短短一个月,销量突破10万张。独立音乐以平台优势证明了其音乐的价值,也有效培养了付费音乐市场。
第三类是各大互联网媒体联手线下音乐节进行的网络直播。从2003年国内出现第一个音乐节至今的十多年里,户外音乐节的盈利主要靠门票、赞助商、周边延伸商品以及各地政府赞助。户外音乐节的规模和数量在不断壮大,但举办地相对集中于中东部城市且独立音乐作品相对稀缺,导致受众很难完全按照自身喜好参加偏好的音乐节。互联网直播打破了地域和距离限制,使乐迷可以足不出户欣赏各地音乐盛宴。音乐节主办方通过出售直播权的方式在扩大受众的同时增加了音乐节盈利的新渠道,同时还可以对音乐节音视频进行二次开发。目前音乐节网络直播分散在传统视频门户网站(如“腾讯视频”)、智能终端平台(如“乐视网”)、在线直播平台(如“虎牙”)。三类网站中独立音乐特色最突出的是打通“三屏”并拥有智能终端优势的“乐视网”,其直播内容囊获多数国内外知名主流音乐节,并且开设专门的音乐节和“LIVE生活”频道,是众多独立音乐爱好者的选择。
第四类是独立音乐的互联网众筹。“互联网+”的概念向独立音乐延伸之后产生了独立音乐的众筹模式。众筹从表面上看是一种集资出版的手段,其本质是音乐人从音乐项目出发与乐迷之间的情感沟通。支持音乐项目的人本身就是艺人的歌迷、粉丝,该人群本身就是带着情感去支持项目。音乐人一方面可以了解市场,了解乐迷是如何看待自己的音乐等等,另一方面则真实地知道了自身受众的情况。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众多众筹网站包含着独立音乐人项目的开发。但专门开展音乐产品众筹业务的并不多,“乐童网”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脱离单纯的预售模式和固定筹资模式,“乐童网”更像是一个专注于音乐行业的项目发起和支持平台,涉及内容从帮助艺人发唱片、做演出到音乐周边、版权维权等等,并且发起了校园原创音乐“种子计划”和发展基金,从根源开始挖掘内地原创音乐,形成了一整套独立音乐项目的开发模式。
(三)主流流行音乐的“收编”与大众媒体的开放传播
内地的独立音乐的发展可以从起步较早的我国台湾省的同类型音乐中获得参考。在台湾流行音乐圈内,不少歌手曾是从Live House里走出来的独立音乐人,其中包括陈绮贞、苏打绿乐队、张悬等后来在内地也获得很高知晓度的音乐人。与被唱片公司直接发掘和培养的艺人不同,这些签约主流唱片公司的音乐人,在被主流流行音乐“收编”后,仍保持着音乐创作上的相对独立性。唱片公司更多的是对其进行商业包装、市场宣传及版权法务上的支持。从目前的趋势上来看,不少独立音乐人在唱片公司无法满足其创作要求时选择离开,自行建立音乐工作室或者重回地下状态。可见独立音乐所代表的亚文化对支配文化天生的对抗性。与台湾地区的音乐人不同的是,内地的音乐人偏向于自行建立工作室,或者签约独立音乐厂牌、民间音乐组织。
近年来,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发展将独立音乐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带入了公众视野。由于独立音乐本身具有可能流行的内在属性,当小众的独立音乐作品被大范围传播后,流行音乐受众很容易将这些作品视为新鲜事物而接受和传播。学者曾遂今教授就曾从音乐的流行心理出发提出了“求同”、“求异”转换模式,①参看曾遂今编著《音乐社会学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7-99页。认为音乐的流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趋群的人类共性会使受众选择从众,使个体适应某个群体的心态和行为方式以使心理获得平衡感和归属感。而个体因其自我情感实现的需要,也会产生试图脱离群体的一种“求异”心理。个体在满足求同心理后选择求异,导致被孤立和异化,并出于群体的压力,会再次选择求同从众,使音乐的流行达到高潮,并迅速在群落中进入饱和状态,完成一个循环。正因如此,当符合大众偏好的独立音乐被主流流行音乐收编之后,很容易出现独立音乐的流行现象。
中国内地主流流行音乐对独立音乐的收编是从音乐真人秀类节目开始的。若干年前,歌手左立在《快乐男声》里翻唱民谣音乐人宋冬野的作品《董小姐》,一时间“董小姐”、“一支兰州”成了年轻人中的流行符号。后来,一批独立音乐作品借助《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歌曲》等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反响。马頔、贰佰、赵雷、杭盖乐队等先前大众比较陌生的独立音乐人(乐队)开始被认知和挖掘。彼得·约翰·马丁在其著作②[英]彼得·约翰·马丁著《音乐与社会学观察——艺术世界与文化产品》,柯扬译,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中指出精英主义控制下的主流文化,是以流行音乐为介质对社会阶层进行划分,流行音乐的基本功能在于“确认”大众社会的价值观和标准化模式,使芸芸众生得以服从于他们作为劳动者及消费者的存在方式。通过简单的旋律和脱离现实的幻想,流行音乐教导人们去接受他们的社会现状。独立音乐的批判和创新精神与主流流行音乐泛滥的情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根据我国目前的广播电视审核制度来看,能够进入大众媒体传播的独立音乐作品都必须是通过严格审查和筛选的。这意味着带有亚文化特质的独立音乐中的“雷鬼”、“朋克”、“硬核”、“迷噪”等强调自身风格独特性、在年轻群体中带有强大身份认同感的小众音乐类型很难被普罗大众所接受。从摇滚发展成为一种音乐形态的独立音乐,在发展过程中除了音乐形式不断更迭,也继承了反叛和激进的摇滚精神。在地下状态时,音乐人的表演可以不受拘束,但在广播电视渠道上,受到把关人的程序化审核后,不符合播出标准的音乐内容将会被删减。在2016年播出的《中国之星》(第一季)中,在崔健推荐的三支独立摇滚乐队里,只有说唱乐队“子曰秋野”的《乖乖的》被如期播出,另两支硬核乐队——“舌头”乐队和“痛仰”乐队的作品在重新编曲填词后也没有通过审核。可见大众媒体对独立音乐保持着谨慎开放的态度。借助大众传播渠道进行独立音乐传播,既要考虑到广大受众的接受程度,也要能符合广电部门的审查标准。
结语
以传播媒介为手段、按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流行文化产品,虽然能够使大量普通受众获得日常文化形态的感性愉悦的音乐体验,但其实质正如阿多诺所言,文化工业在大众传媒和日益精巧的技术效应的配合下,大肆张扬带有虚假光环的整体化观念,将情感纳入统一的模式,纳入包装巧妙的意识形态,使人的个性无条件地淹没在平面化的生活方式、时尚化的消费行为和肤浅化的审美趣味之中。音乐流行的本质是音乐行为的连锁性感染以及模仿,是个体迫于外界群体压力而产生的一种心理强制。从众可以使个体适应群体的心态和行为方式,在心理上获得平衡和归属感。而这种平衡感和归属感却是通过放弃自我核心的方式取得的。
长久以来,受到资金和传播渠道的限制,那些优秀的独立音乐作品无法有效地到达受众。而且,独立音乐在传播上有着天生的“劣势”,因为独立音乐创作更多地以音乐作者自身的态度为取向,为保持其艺术价值,不刻意迎合流行音乐市场的需要。甚至从某些方面来说,独立音乐具有一定的反市场特性——很多独立音乐人较为明显地表现出了对面向大众而创作的厌恶,形成了独立音乐的多样性与小众性。可喜的是,随着户外音乐节、独立音乐厂牌运营机制的不断完善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独立音乐有了快速、低成本到达受众的渠道。
从目前来看,独立音乐已经形成三条完整的传播路径。其一是地下形态的封闭循环。这类音乐的传播路径相对比较封闭,无法通过其他传播方式吸引大量受众,主要以“雷鬼”、“迷幻”、“后摇”、“死摇”等不能被大众审美所接受,但能符合小部分受众发泄和调整情绪需求的音乐形态为主,如“葬尸湖”、“颠覆M”等重金属乐队的创作。通常这类带有偏激态度和实验色彩的音乐在国内受众较少,但这些受众普遍带有强烈的群体身份认同感。强烈的现场演出效果和观众台下互动方式,使其适合在Live House以及户外音乐节等音乐现场中进行。其二是独立音乐厂牌与新媒体支持下的开放循环。独立音乐厂牌通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运营模式:线下帮助旗下独立音乐人制作、发行、宣传唱片,通过户外音乐节、Live House巡演的方式给独立音乐人提供演出机会来传播其作品;线上利用各种社交媒体发布唱片、演出信息吸引受众。独立音乐人也能自行通过“微博”、“豆瓣”等独立音乐爱好者聚集的平台与受众交流,分享自己的生活起居、演出创作进展。“网易云音乐”、“虾米音乐人”等独立音乐人平台,在帮助独立音乐人推广作品的同时也对作品版权进行保护,既让更多人接触到独立音乐作品,也通过付费下载的方式使独立音乐人获得了版权收益。这种开放循环使独立音乐人不依靠大众传播渠道的帮助依然能够形成传播的良性循环。其三是主流流行音乐的“收编”与大众媒体的开放传播。主流唱片公司的萧条,带来的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长期的青黄不接,受众急需符合精神文化需求的音乐作品,与此同时,大量带有流行属性的独立音乐无法有效地到达大众,而这类音乐作品一旦被主流流行音乐捕获,很容易获得流行。《董小姐》、《南山南》等独立民谣作品通过电视真人秀节目走红,独立流行乐队“逃跑计划”登上央视中秋晚会舞台,都证明了独立音乐融入主流文化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独立音乐的传播可以根据独立音乐人不同风格类型和传播需要来合理选择传播路径来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文化审查部门也能够以此合理引导独立音乐,取其中佳品传播弘扬正能量。
[1]中国音数协音乐产业促进工作委员会《2015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中国传媒大学项目组2015年编撰。
[2]陈长华《中国大陆户外音乐节发展现状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3]周丹《Live house——中国内地流行音乐产业的新救赎》,载《大众文艺》2014年第23期。
[4]葛云璐《国内Live House的分析和发展研究》,南京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6年。
[6][美]罗洛·梅著《人的自我寻求》,郭本禹、方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胡乐野《独立的声音》,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8]段似膺《上海的独立音乐及其文化价值》,载《上海文化》2011年第6期。
[9]马娟《中美地下音乐的传播模式比较分析》,载《通俗歌曲》2013年第5期。
(责任编辑:韦杰)
赵贺佳,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新闻传播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传播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