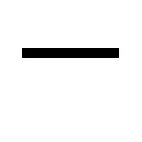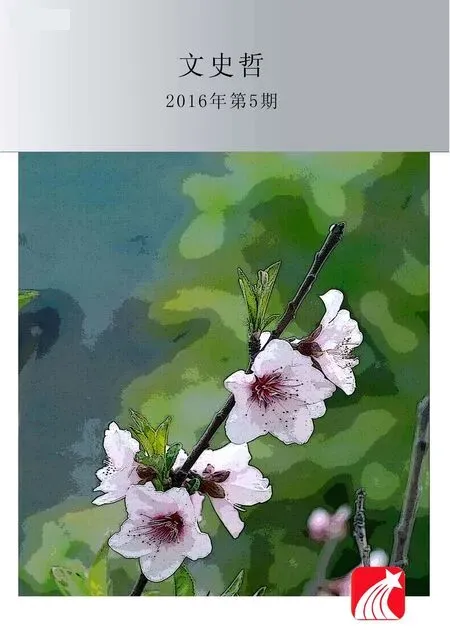用脚表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的另类叙事
马俊亚
用脚表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的另类叙事
马俊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中国乡村危机的论说达到了惊人的数量。但对乡村危机的描述,相当部分集中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这些叙述把世界市场带来的暂时性经济波动视为社会不可消除的终极矛盾。事实上,即使是危机时期,近代江南工商业经济仍蕴藏着无穷的活力。中国乡村社会真正的危机,不是苦于世界市场的波动,而是苦于与世界经济的隔绝。在一些灾患较少的农耕地区,农家经济确实苦于内卷化;而灾患深重地区的农民,则更苦于不能内卷化。农民通过脚来表述的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更加真实地揭示了中国地区性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中国乡村社会的本质矛盾。
乡村危机;农村破产;世界市场;江南地区;内卷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中国乡村危机的描述可谓汗牛充栋。一部中小学教材沉痛地写道:“创巨痛深的农村,完全走上死亡的尖端(原文如此——引者注),这是何等严重的现象呀!”①张健甫:《四年来中国农村破产的概况(小学高级及初中用社会教材)》,《中华教育界》第22卷第6期(1934年12月),第69页。邓飞黄指出:“遭了八十多年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侵略,……中国农村经济,现在已到了山穷水尽、万劫不复的境地了。”②邓飞黄:《从农村破产到农村改造》,《中国经济》第1卷第4、5期合刊(1933年8月25日),第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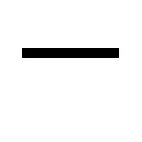
一
学者所述的危机大量发生在江南地区(主要是以上海为中心的苏南浙北)。有人写道:“江苏农民,早已由天堂而入地狱。江苏最繁华区域之无锡,亦时时发生抢米风潮。”*青士:《我国农村破产之状态及其原因》,《北辰杂志》第4卷第10号(1932年12月20日),第6-7页。众所周知,江南是当时中国经济最繁荣地区,人们不禁要问,时人所述的乡村危机真的存在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总的说来,像江南这类工商业经济发达的地区,资本主义产业日新月异,充分享受了全球化的益处,事实上得到了中央政府更多的政策优惠。加之这里较多的公益组织、良好的社会福利,与传统农耕区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只是在1929年以后,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发生大萧条,作为全球经济组成部分的乡村经济作物的价格大幅下跌,农民收入锐减。这也是危机论者强调较多的方面。
显然,危机论者强调江南地区的乡村危机,既有工商业暂时性萧条的历史事实,更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考量。马克思认为,小生产“正常的补充物即农村家庭工业,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09页。,这一论述是当时左翼学者对中国乡村家庭经济破产的终极解释。
其实,江南乡村家庭手工业的衰落,不是廉价的资本主义工业品对手工业制品打击的结果,而是较高的资本主义工厂工资对乡村劳动力吸引的结果。嘉定县方志称:“自交通便利,各工人受雇于上海者日多。本地几供不应求,故工价逐渐增涨。”*黄世祚纂:《嘉定县续志》卷五,1930年铅印本,第2页下。南汇县“各乡镇渐讲育蚕,近日工厂林立,妇女多务织袜、织巾”*严伟修:《南汇县续志》卷二十,1929年刻本,第9页上。。张艺新、沈毓庆等人1900年在川沙县开设经记毛巾工厂,“招收女工,一时风气大开”*黄炎培总纂:《川沙县志》卷五,1936年刻本,第25页下。。
工厂纷纷设立,招收的工人动辄成百上万。杨树浦大纯纱厂南、北二厂共有工人数千名*《大纯纱厂工人互哄》,《申报》1905年4月30日,第10版。。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员达1000人,男女工友约3500人,各省分支馆局职员、工友1000余人*吴葭修:《宝山县再续志》卷六,1923年铅印本,第21页上-下。。宝山华丰纱厂和永安纺织公司第二纱厂两厂工人数达5000余名*吴葭修:《宝山县再续志》卷六,第21页下-22页上。。1919年,“上海一隅,各业工人数达二十余万”*《各界对外之消息》,《申报》1919年5月18日,第10版。。据上海农村居民在1929年的回忆:
工厂开始在附近设立的时候,经营者派人到村里招工,有些人放弃农活进入工厂。……后来,工厂招收女工,在这里招了许多人,于是只剩下我们这些习惯于干农活的老年人在家种田。因为许多人移居城市,村庄日益缩小了。*H. D. Lamson,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ization upon Village Livelihood,”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vol.Ⅸ, no.4 (October 1931), 1059.
上海农村那些进厂工作的妇女,原来多是农村的手织者*Ibid,1060.。像真如地区,“女工殊为发达,盖地既产棉,多习纺织。……自沪上工厂勃兴,入厂工作所得较丰,故妇女辈均乐就焉”*王德乾纂:《真如志》卷三《实业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3),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本,第233页。。宝山县,“向恃织布,运往各口销售。近则男女多入工厂”*钱淦纂:《江湾里志》卷五《实业志》,1924年刻本,第1页下。。川沙县“向以女工纺织土布为大宗”,“今则洋纱洋布盛行,土布因之减销。多有迁至沪地,入洋纱厂、洋布局为女工者”*黄炎培总纂:《川沙县志》卷五,第25页上。。众多的手织女工被吸纳到工业中来,江南乡村手织业焉能不衰落?
工业的发展,使“有土斯有财”的传统财富观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那些有职业者,基本能够维持自己的生活;“田少者,或作工艺,或种种杂贩,亦能自赡”*黄炎培总纂:《川沙县志》卷十四,第7页下。。因此,江南乡村手织业的衰落,不但不是农村破产的表现,恰恰是乡村获得跳跃式发展的证明。据对上海纱厂工人的调查,有地家庭每年从土地获得的收入每亩为3元,但家主一人的年薪可达432元(月薪36元)*H. D. Lamson,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ization upon Village Livelihood,” 1064-1065.。据对上海农村的调查,各农家来自工业的收入相当于农业收入的2.48倍,相当于手工业等收入总和的2.55倍,相当于农业与手工业等收入总和的1.26倍。在家庭收入中,工业收入已居主导性地位*据H. D. Lamson “The Effect of Industrialization upon Village Livelihood”一文第1071页表格计算。。
另外,从晚清维新思想家开始,许多学者把中外买卖方双赢的商业视为你死我活、你胜我败的经济战争或零和博弈,是以“商战”理论长期主导中国的政治经济行为。1932年6月7日,在上海国货展览会开幕典礼上,代表实业部的国际贸易局副局长何炳贤所作的训词淋漓尽致地阐述了商战者的思维。他称:战争有两种:一种是军事战争;另一种是商业战争,“这种敲精吸髓、杀人不见血的商业战争,是百倍、千倍惨过军事战争。军事战争的失败,是政治上的亡国,我们还可以徐图恢复。商业战争失败,就是经济上的亡国,这就是万劫不复的”。外国企业家在中国获取的正常商业利润,被视为远比从中国抢劫财富还要恐怖,甚至被视为农村破产的肇因:“我国自与外国通商以来,年年都是入口超过出口。……但是这笔款子,是流到外国去了。所以弄到我国的农村破产、工业凋零,商业更奄奄一息,完全在帝国主义的鼻息下生活着。到了现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破产地步了,我们快要经济亡国了。”*《实部训词》,《申报》1932年6月7日,第9版。这种商战理论,与后来冷战思维实有异曲同工之处。直到今天,学界已对后者作出了较多的反思,但对前者则大多奉之若素,因此有必要指出,二三十年代的国际贸易绝非中国乡村危机的祸首。相反,不管是出超还是入超,外贸都对中国乡村的商品流通、货币增加、劳动力调配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国际市场隔绝的农村地区,所受的危机只会更加惨重。
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论者强调最力的证据,是机器工业打垮了乡村手工业。事实上,作为中国家庭传统手工业最重要的棉纺织业,已被证明并没有被机器工业挤垮。传统手织业中,花费时间最多、效率最低的工序是纺纱,5人纺纱才够1人同时织布;一名手纺纱工人的效率相当于机纺纱工人的八十分之一。而农家手织工人与工厂机织工人的效率则相差不大。在江苏通海,山东潍县,河北高阳、宝坻等地区,大机器工业替代了家庭手工业中效率极低的“纺”,而极大催生、扩大、提高了“织”的效率。在更加落后的苏北、皖北、鲁西南等地区,大机器工业使原来乡村“男耕女不织”的形式,转变为男耕女织结构*Ma Junya and Tim Wright, “Industrialization and Handicraft Clo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Jiangsu Peasant Economy,”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44, no.5 (2010): 1337-1372.。
机器业挤垮手工业的最典型事例,在缫丝业等行业中确实大量存在。以江南地区而言,“以前缫丝制经,多用人力木车。故育蚕之家,多自行缫制。及机缫方法采用后,即渐移至上海、无锡等都市丝厂,人力缫制,反不重要”*钱承绪:《中国蚕丝业之总检讨》,1941年出版,第96页。。1900年前,每年新丝上市,无锡各丝行纷纷派人在各交通要道拦住农民抢收;十数年后,机器缫丝厂兴起,“土丝日渐减少……如无锡一带,土丝绝迹”*《江浙粤丝业调查》,《农商公报》第3卷第9册,1917年4月15日出版。。费孝通对吴江县开弦弓村调查后指出:该村684名妇女中,过去至少有350名妇女从事缫丝工作,在工厂制度下,同样数量的工作,不到70个人就能完成,将近300名妇女因此失去了工作的机会*Hsiao-tung Fei, Peasant Life in China, 231.。
这种用简单的加减法来概述工业化时代的乡村经济,实为莫大的误区。且不说一家近代缫丝工厂作为龙头对周边交通、运输、电力、商业、饮食、幼抚、教育、娱乐、医疗等产业的催生与拉动,单就收入而言,有足够的数据证明,失去了手工缫丝的农民家庭的收入不降反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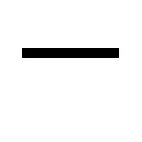
农家从蚕茧副业中获得的收入大幅度提高,显然是因为机器缫丝业对原料茧的大量需求造成的。据1928年统计,仅无锡45家丝厂年用茧量即达129400担*据高景岳、严学熙:《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第62-65页。。这种对蚕茧的大量需求,是手工缫丝所无法比拟的,也就是说,在手工缫丝没有被机器工业打垮的时期,农民不可能从养蚕育茧中获得那么高的副业收入。
实际上,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土丝业并未因机丝的兴旺而绝迹,农民收获蚕茧后,会留下一部分干茧自家缫制土丝。据1950年的调查,吴江震泽、严墓地区,“农民所抽的土丝,多直接售于震泽的土丝行(震泽全区有土丝行十四家),再由土丝行售于纺经行(亦算加工整理场,全区有纺经行十二家),由纺经行加以纺摇,便成纺经,即可销至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内部资料),1952年,第385页。。浙江也有类似情形,据对各类丝织物产量的调查,土丝织物的数量在1946年以前竟远远超过厂丝织物的数量*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内部资料),第205页。。
农家保留土丝业,并非缫制土丝能带来更多的收益,而是用来应付茧市低落。手工制丝的存废,并不取决于大机器工业的排挤,而是取决于机器工业收购蚕茧时的报价。如在浙江地区,“土丝产量,年各不同,概依茧价之高下而有消长,如茧价高时,虽土丝价格亦随之升腾,但茧农均乐于售茧,而不愿自制土丝;如茧价低时,蚕农则不愿售茧,率多自制土丝”*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七编,上海:华丰印刷厂,1934年,第46页。。所以,农村土丝业缩减之时,正是茧价极高,农家收入也最高之时;而在农村土丝业盛行时,也正是茧市低落,农家收入降到最低点之时。可见,农家土丝业的消减,并不表明农家收入的减少,更不表明农家经济的破产。
其他像面粉、碾米、酿造等行业中,家庭手工经济的存续,根本无法证明乡村经济的和谐兴旺,相反,家庭手工经济的消失,却极易证实乡村经济获得了良好的发展。
实际上,即使遭遇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江南地区的乡村状况也远好于其他农耕区。因此,中国乡村危机绝非在江南最为严重,也不是二三十年代才出现,其根源更不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竞争的结果,反而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在较长时期里促进了江南乡村经济的协同增效*详见马俊亚:《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经济的现代演变》第一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三
可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最严重的乡村危机,不是发生在受到资本主义侵入的地区,而是主要发生在资本主义无法“侵入”的地区。
笼统地说,中国每个王朝的衰败,均与乡村危机密切相关。因此传统的统治者总是把农村问题放在首位,制订了各种救灾机制,重视农桑,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使民以时,等等。清后期以后,中央政府采纳了“商战”理论,从原来抑制工商的极端,转向了工商崇拜、乃至后来的GDP崇拜的另一极端,抛弃了传统王朝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重农减灾等正确而又必须的做法。因此,随着近代GDP的暴增,乡村危机愈加严重。
在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没有“新”经济成分产生的传统农耕地区,由于不能创造出国家趋之仰之的财税收入,理所当然地被国家所忽略,发生了极为普遍的危机,远较江南地区严重。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危机远在二三十年代以前就已大量存在,却甚少得到学者的关注。这些传统农耕区的危机,也不是苦于西方学者(如黄宗智教授等)所说的“内卷化”——乡村人口增加,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投入到一定数量的土地上,造成边际收益不断下降。危机地区的农民更像是苦于无法内卷化!即虽拥有土地,却苦于无法投入太多的劳动力。如与江南相比,江苏北部地区显然与世界市场更加隔绝。早在康熙年间靳辅治河时,就发现淮北地区的土地大量荒废,任其长草。靳辅计划把沿河荒地募帮丁垦种,但当他准备使用这些荒地时,当即就有田主出认,并有合法田契和纳粮的凭证。经靳辅调查得知,淮安、徐州、凤阳等地种田“全不用人力于农工,而惟望天地之代为长养。其禾麻菽麦,多杂艺于蒿芦之中,不事耕耘,罔知粪溉,甚有并禾麻菽麦亦不树艺,而惟刈草资生者,比比皆然也”*靳辅:《生财裕饷第一疏(开水田)》,《文襄奏疏》卷七,见《钦定四库全书》“史部六”,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1页下。。乾隆年间,江苏巡抚陈弘谋指出:“淮徐海境内,地土非尽瘠薄,可以种植。地土一望无际,只因河流未通,一遇天雨,是处弥漫。或广种而薄收,或有种而无收,一年妄费工本,次年遂弃而不种。所以民间土地不甚值钱,亦不甚爱惜,……地皆旷土,民习游惰。”*姚鸿杰纂修:《丰县志》卷十二,清光绪二十年(1894)刊本,第8页下。而农民任其长草,是因每年必定发生的水灾所迫。
1906年,两淮地区发生了“近四十年未有之奇灾”,推原其故,“由于旧有之引河失修者已多历年所,一遭水患,致令此极广阔、极繁盛之区顿成泽国”。铜山、邳州、宿迁、睢宁、萧县、海州、清河、桃源、安东、阜宁、山阳等州县,受灾极重,垂死的灾民有150万人*镇江关税务司义理迩:《光绪三十二年镇江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光绪三十二年通商各关华洋贸易论略》(英译汉第48本)下卷,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印,第41页上-下。。1910年,江苏淮海及安徽凤颍等地,“屡被水灾,闾阎困苦,惨不忍闻”。每日饿死达五六千人,该年秋至次年2月,饿死七八十万人,待毙者四五十万人。1911年,江苏淮海与安徽凤颍数万饥民,“寻觅倒卧路旁将死未气绝之人,拉至土坑内,刮其臂肉,上架泥锅,窃棺板为柴,杂以砻糠,群聚大嚼,日以为常”*张廷骧:《不远复斋见闻杂志》卷十,1915年刻本,第1页下-第2页上。。此类记述在史书中不绝于载。
太平天国之后,太仓州“招江北人垦荒”*王祖畬:《太仓州镇洋县志》卷三,1919年刊本,第4页下。;苏州胥门内百花洲,“多江北人,搭盖草棚以居”*《皮匠失妇》,《申报》光绪八年四月十五日(1882年5月31日),第2版。。
除了天灾外,苏北等地的人祸也比江南地区严重。据1930年的统计,仅流落在江北的各种枪械就达20万支,其中约三分之一至一半掌握在土匪手中*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续),《东方杂志》第27卷第7号(1930年4月10日),第65页。。时人指出:“凡是土匪盘踞之处,农田往往荒芜,是即农民被迫离村之象征。凡有土匪之区域,几莫不如是。江苏北部所谓江北各县,在三年前(系1934年——引者注)亦为各种盗匪猖獗之地。是时江南都市中各种工人与苦力之充斥,大部都是此种江北人。”*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东方杂志》第34卷第15号(1937年8月1日),第18页。
有学者指出:“查江北占全省面积四分之三,人口只及全省总数三分之一,今反有源源自江北而来江南谋生者,其以不堪匪扰为主因,固不待言。”*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东方杂志》第34卷第15号,第18页。青浦乡村雇工,“大半来自丰、宁、兴化,俗称之为江北人”*于定修:《青浦县续志》卷二,1934年刊本,第26页上。。1930年,有人写道:“生长在江南的儿女们,年年看见江北人的来到于江南各县的城市做小贩,做厂工,做黄包车夫,做一切下贱的事,在一只破烂的小船里边,住宿,吃饭,养小孩子。”*吴寿彭:《逗留于农村经济时代的徐海各属》(续),《东方杂志》第27卷第7号(1930年4月10日),第69页。拉黄包车被视为在江南的苏北男性最普遍的职业,另外,“做苦力,逢有婚丧喜庆,为人家奔步打杂等一切下等职务”。某县北门外,有一个较大的旷地,“聚居在那个旷场上的江北人,大都以编织芦席为业,以此得名。那里住着的江北人,总不下一二百户人家,草屋接二连三,望衡对宇,不着火则已,一家起火,就得烧个全场。……前后也已不知烧过了多少次”*青霜:《江北人》,《申报》1936年12月18日,第15版。。
赛珍珠小说中所反映的淮北流民向“南方”逃荒的情景,就带有极大的历史真实。他们逃荒时,家中不断有人饿死,有些人家甚至开始人吃人*赛珍珠:《大地》,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第60、65-71页。。闻一多描写逃荒后的临淮关梁园镇:“他们都上哪里去了?怎么虾蟆蹲在甑上,水瓢里开白莲;桌椅板凳在田里堰里漂着;蜘蛛的绳桥从东屋往西屋牵?门框里嵌着棺材,窗棂里镶石块!”*闻一多:《荒村》,蓝棣之编:《闻一多诗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48页。
这些背井离乡的农民,并非无地耕种,而是在淮北无法耕种,他们是乡村危机最真实、最客观的体验者,他们用脚所作的表达,远胜于书斋中带有各种意识形态色彩的学者用笔所作的叙述。
江南与淮北这种地区性贫富分化的二元结构,比中国自然地貌的区别更加明显。令人浩叹的是,当时的话语权和国家调控政策更多地掌握在大都市、发达地区的学者和官员手中,造成了对中国贫困乡村的极大隔膜和误解,国家的政策资源较多地流向了发达地区,客观上引发了地域发展中的马太效应。
四、结 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人口移动的规模非常惊人,可以说,大部分地区乡村人口的移动是农村破产的结果。
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是中国近代经济的核心地区。20世纪前期,即使在其最低谷阶段,也远未沦落到破产的程度,特别是其工商业经济,仍然蕴藏着无比的活力。因此,即便在在江南农村经济最萧条的时候,也从未见到江南农民向内地其他地区大规模地避灾,反而是江北等地区的农民一如既往地向江南移动,充分说明江南地区的乡村危机要远轻于中国其他地区。因此,在江南苦于资本主义市场的波动时,像苏北等地区更苦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隔绝。这是两种不同层面的经济,过于渲染资本主义市场波动的负面影响,掩盖了中国乡村更本质、更深刻的经济困局和社会矛盾。
即使同是农耕区,学者们的认识也存在不少误区。在一些灾患较少的农耕地区,农家经济确实苦于内卷化;而灾患深重地区的农民,则更苦于不能内卷化。农民通过脚来叙述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更准确地揭示了中国地区性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及中国社会的本质矛盾。
[责任编辑扬眉]
马俊亚,南京大学抗日战争协同创新中心首席教授、中华民国史中心教授(江苏南京 21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