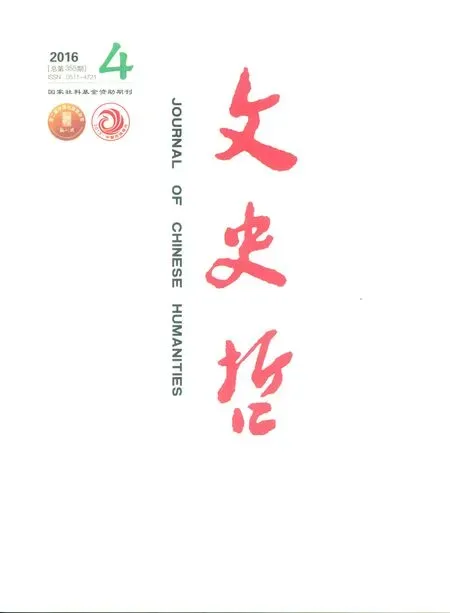“世界文学”的同与异及中国的境遇
亚思明
“世界文学”的同与异及中国的境遇
亚思明
摘要:“世界文学”源自歌德近二百年前的文学设想,存在着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结构性矛盾,同时也呈现出一种反乌托邦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这一概念不断为后世学者所解读、分析和阐发。对于中国而言,自“五四”时代开始,知识分子就在为汉语语言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流通体系作着开创性的努力。直至高行健、莫言相继问鼎诺贝尔文学奖,西方文化霸权以及世界文学空间内部的不平等关系并未得到显著改变。为了摆脱全球文化产业链的低端地位,实现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复兴,中国一方面应该避免创作及研究上的“自我他者化”;另一方面也应警惕全球市场驱动下的同质主义的文学倾向,努力确立“汉语语言文化”为“世界文学”的特别媒介。唯此,中国才能从“世界文学”中获利,重建自己的民族文化自信。
关键词:世界文学;世界诗歌;诺贝尔文学奖;莫言;高行健
一、歌德的“世界文学”设想
“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于1827年通过若干文章、信件和谈话首创的一个文学概念。作为一名广泛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歌德认为,“世界文学”的使命是通过倡导相互理解、欣赏和容忍来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这并不意味着各民族归于同一,而是说他们应意识到各自的存在,即使互无好感,也应容忍对方。”*Fritz Strich, Goethe und die Weltliteratur (Bern: Francke Verlag, 1946), s. 13.为了这一目的,歌德设想了一个由作家和学者组成的国际社区,团结在“社区行动”的口号之下以追求建立在“基本人性”共识之上的“普遍性的容忍”*Fritz Strich, Goethe und die Weltliteratur, s. 13.。德国学者弗瑞茨·施特里希(Fritz Strich)在其1946年出版的专著《歌德与世界文学》中指出,歌德确信正是民族差异促进了国际合作,并称“使个人和群体保留其特征是达到普遍性容忍的必然途径”,但歌德对差异的关注显示了一种反乌托邦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倾向,“世界文学”的发生地点在此成了核心问题:
在歌德对世界文学概念的思考里,有两个段落表明他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第一段作了如下的界定:“如果我们斗胆宣称欧洲乃至世界文学的存在。”第二段简明扼要地说:“欧洲文学即世界文学。”……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歌德的矛盾:在他看来,世界文学的起点是欧洲文学,而且已包含在欧洲自我实现的过程之中。产生于欧洲多种文学和欧洲人民相互之间的交流与影响的欧洲文学是世界文学的开端,以此为中心而发展形成的系统将最终囊括全世界。*Fritz Strich, Goethe und die Weltliteratur, s. 16.

歌德对于“世界文学”的设想存在着互为背反的两极:一方面,差异性与多样性是民族之间互换文化珍品的世界文学市场存在的基础,而翻译将充当这一流通过程的中介:“每个翻译都是一个中间人。他应刻意提倡全球性精神交换,并以推动这项一般性贸易为己任。”*Antoine Berman,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Culture and Translation in Romantic German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57.法国文学理论家、拉美文学及德国哲学的翻译家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认为,歌德试图确立“德国语言文化为世界文学的特别媒介”,或照歌德原话,“为各民族奉献其商品的市场”*Antoine Berman,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eign, 56.;另一方面,“广袤的世界,尽管其广阔,也只是祖国的延伸。……它所给予我们的,不会超过祖国所赋予我们的”。时空差异并不妨碍人类基本情感和伦理道德的相通,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不意味着抵制超民族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普遍意义的世界文学是“从异质成分融合发展而来的”*[德]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歌德论世界文学》,查明建译,《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2期。,正如德国文学自身的发展历史。简而言之,世界文学是普遍人性的反映,也是人类交流的结果。
二、“世界大同”的文学理想
继歌德之后,围绕着“世界文学”的同构或异质,世界各国的作家及学者也从未停止过讨论。例如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呼应了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认为随着资本输出和全球市场的开拓,各民族文学也将呈现一种走向普遍联合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印度诗人泰戈尔在其发表于1907年的《世界文学》一文中,将世界文学喻为一座“由建筑大师——具有世界意识的作家——领导下建造的”神殿,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作家都在其指挥下劳作。“没有人能设计出整座建筑的蓝图,但有瑕疵的部分不断被拆除,每位建设者都发挥其才能并将其创作融入整体设计,竭力符合那张无形蓝图的设计要求。这就是他的艺术探索所创造的东西,这也就是无人给他支付普通工匠的薪酬但却授予他建筑大师的原因。”*[印]泰戈尔:《世界文学》,王国礼译,见[美]大卫·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2页。大约十五年后,作为中国最早系统阐述世界文学的学者之一,郑振铎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文学是“人类全体的精神与情绪的反映”*郑振铎:《文学的统一观》,《郑振铎全集》第15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42页。,虽有地域、民族、时代、派别的差异,但基于普遍的人性,文学具有了世界统一性,这便是世界文学。郑振铎的“世界大同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五四”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与之相应的是,1917年以来的白话文学的全面推广不仅是一项语言革命,更是一种将书面汉语纳入世界流通体系的努力,进而成为一个在语言功能上与西方话语同构的开放性系统。
到了20世纪下半叶,歌德的世界文学梦想已经几近成为现实。1960年,《现代诗博物馆》编者、德国诗人恩岑斯贝格尔(HansMagnusEnzensberger)注意到,从1910至1945的35年间,“诗的国境线日渐消弭,‘世界文学’的概念前所未有地光芒四射,而在此之前的任何一个时期,这都是无法想象的事情”*Hans Magnus Enzenberger, “Vorwort”, Museum der modernen Poesie (Frankfurt a. Main: Suhrkamp, 1960), s. 6.。究其根本,跨境迁徙和“流散写作”(DiasporaWriting)日益普遍,通讯技术推陈出新,不同国家的文化基因彼此“杂合”(Hybridity),打破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本质主义观念,即不再将一国文化看作固有的本源。
《现代诗博物馆》集结了世界二十多个国家96位诗人共计351首作品,首版发行并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地位和价值如同现代诗歌史上最丰厚的馈赠一般趋于恒定。在恩岑斯贝格尔看来,该选集更像是一本激励德国作家创作的写作指南——旨在自“二战”后的文学废墟之上重建辉煌。
除却诗集本身在德语文学圈内至今无人超越的影响力,恩岑斯贝格尔还敏锐地意识到“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1910年左右发生的一连串诗歌爆炸性事件撼动了欧美文坛。如1908年庞德发表了第一部诗集,一年以后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CarlosWilliams)也自费印行了他的首本诗集;同年,法国诗人圣琼·佩斯的《克罗采画图》(Image à Crusoé)问世,意大利诗人马里内蒂(FilippoTommasoMarinetti)在法国《费加罗报》发表《未来主义宣言》。1910年德国《狂飙》(Der Sturm)杂志刊发了表现主义宣言和其他理论著述。俄罗斯诗人克勒勃尼科夫(V.Chlebnikow)、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卡瓦菲斯(C.P.Cavafis)也相继印发诗集。1912年接踵而至的还有阿波利奈尔(GuillaumeApollinaire)、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Benn)、马克斯·贾克伯(MaxJacob)等人的作品;一年后又迎来了翁加雷蒂(GiuseppeUngaretti)、帕斯捷尔纳克(BorisPasternak)……诗的苍穹突然布满了璀璨的繁星,这无疑表明:“现代诗不再只是关乎个别作家作品,也不再只是时间之河里偶然漂来的悬浮物,而是已然成为一种时代的气象。与此同时,这些在西方世界里此起彼伏、乍看起来似乎是零散而自发的出版著作很快就有了国际性的互文关系。”*Hans Magnus Enzenberger, “Vorwort”, Museum der modernen Poesie, s. 5.
恩岑斯贝格尔因之而在诗集前言中提出了所谓“现代诗世界语”(WeltsprachedermodernenPoesie)的构想:
现代诗的进程导致——正如这部选集的文本所呈现的那样,通过不同国家的反复对比——一言以蔽之:一种诗的世界语的形成。这一结论并不意味着,世界语的表达会造成丰富性的减损。本书所证实的国际语言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并不排斥创奇出新,更多意义上是将创奇出新从民族文学的禁锢之中解放出来。*Hans Magnus Enzenberger, “Vorwort”, Museum der modernen Poesie, s. 6.
不过,恩岑斯贝格尔也承认,“现代诗世界语”无意间被盖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印戳,因为现代诗的发展进程基本与工业文明同步,而那些以农耕文化为主的“前现代”国家要到1945年以后才始现“世界诗歌”端倪,这也正是亚洲、非洲的大部分国家未能入选《现代诗博物馆》的主要原因所在。
三、中心区域与边缘地带


除了中国古诗,庞德从芬诺罗萨那里继承来的文学遗产还有日本能剧*能剧,日本最早的剧种,产生于12世纪末宫廷、寺院的演艺大会和农村的艺能表演,14世纪初出现许多演“能”的剧团。古典“艺能”实行世代相传的“宗家制度”,他们保持各自流派的艺风。“能”的流派是17世纪以后形成的,共有观世流、宝生流、金春流、金刚流、喜多流五个流派。、俳句,庞德的《诗章》(Cantos)就有一部分取材于能剧。在越界采撷东方文化因子的同时,早期现代主义者也从古希腊那里找寻传统。“现代美国诗歌的源起就像是希腊遇见中国”*北岛:《越界三人行——与施耐德、温伯格对话》,《古老的敌意》,第135页。,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国际性,异质因子之间的碰撞和交流是异常活跃的,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文学形式的革新。
不过,吊诡之处在于,当现代诗的浪潮波及中国内地,告别文言走向白话的汉语新诗却深陷身份危机,所开启的现代更新的进程更是屡遭数典忘祖的质疑。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当属1990年11月,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发表的一篇书评,题为《全球性影响的焦虑:什么是世界诗歌?》,称:“正如在所有单向的跨文化交流的情景中都会出现的那样,接受影响的文化总是处于次等地位,仿佛总是‘落在时代的后边’。西方小说被成功地吸收、改造,可是亚洲的新诗总是给人单薄、空落的印象,特别是和它们辉煌的传统诗歌比较而言。”*Stephen Owen, “The anxiety of global influence. What Is World Poetry?”, The New Republic (November 19, 1990). 中文译文参见[美]宇文所安撰,洪越译,田晓菲校:《什么是世界诗歌?》,《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此番言论引发海外直至国内诗坛围绕新诗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纠结,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辩论。在这场国际争论中,不少汉语诗人和诗歌学者做出了相当愤怒的回应,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奚密的《差异的忧虑——一个回想》。文章指出:宇文所安将“中国”与“世界”对立,“民族诗歌”与“国际诗歌”对立,这种中西二分法过于简单僵硬,以至于忽略了文学影响的复杂进程。奚密举例说:“一些所谓中国现代主义的诗人同时也表现出浓厚的传统色彩(如早期的卞之琳、废名、戴望舒,台湾的痖弦、杨牧等)。用‘民族’和‘国际’来严格界定诗歌无异将它们视为两个截然对立、封闭的体系。”*奚密:《差异的忧虑——一个回想》,《今天》1991年第1期。
另一种批评的声音来自跨境文学的研究者,例如周蕾1993年出版的论文集《流散写作——当代文化研究中交涉的战略》*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在这本书的“前言”里,周蕾没有从否认地域差异的角度来批驳宇文所安,而是对他在颂扬中国传统遗产的同时所表现出的对中国当代文化的鄙视,以及从中流露出的一种在东亚研究领域里显然已经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倾向表示不安。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研究专家安德鲁·F·琼斯(AndrewF.Jones)则认为,宇文所安1990年的文章对有兴趣探讨世界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之关系的人们提出了一些富于挑衅性的新问题,这些问题事实上是由歌德思想体系派生而出的。确切地说,如果世界文学实为文化资本的国际交换,盈利或亏损便不可避免。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在世界市场上流行?谁来建立并维护一套价值标准?世界市场究竟在哪里?有没有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剥削的问题?国家之间产品分工的问题?最后,文学生产与贸易的跨国经济是否假定了某种内在的依赖理论?*参见[美]Andrew F. Jones:《“世界”文学交换中的中国文学》,李点译,《今天》1994年第3期。
这一连串的尖锐提问直指世界文学空间内部的不平等关系。欧美现代诗作为时代性的历史归化进程的终端产品,作为多样性的交叉文化生成的经典范例,已被包装进世界文学体系;而具有象形特点的中国汉字和丰富意象的古典诗词仅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发挥作用,意图簒越的汉语新诗则被视为一种“过时的西方模式衍生物”,一辆“第二次发明的自行车”*这是瑞典学者约然·格莱德尔的比喻。参见[瑞典]约然·格莱德尔:《什么样的自行车?》,陈迈平译,《今天》1990年第1期。,在世界文学的海洋里似乎总是难以翻腾起更耀眼的浪花。
四、作为世界文学指标的诺贝尔奖


但作为指标的诺贝尔奖同时也清晰呈现了世界文学全球格局的严重失衡状况。从首届颁奖的1901年到2015年,全世界共有112名作家荣膺桂冠,就洲际分布而言,其中83人出自欧洲——毋庸置疑的全球文化中心,法国更是凭着15位获奖者成为世界文学最大的受益国*原则上是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奖时的实际国籍归属进行统计,双重国籍获奖者两国各按1人计算(2008年获奖者勒·克莱齐奥拥有法国和毛里求斯双重国籍,2011年获奖者略萨拥有秘鲁和西班牙双重国籍)。2012年以前的统计数据参见朱安远:《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概览》,《中国市场》2012年第44期。,这正应验了歌德两百年前的预言:“法国摒弃了狭隘和自高自大观念而取得的长足进步,真令人惊奇。……世界文学诸多因素间的相互关系,非常紧密而奇特。如果我说得不太错的话,法国人将会受益于这种关系,从而眼光会更加远大。”*[德]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歌德论世界文学》,查明建译,《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2期。
而对于汉语文学来说,1940年出生于江西赣州的法籍华裔作家高行健2000年问鼎诺奖可谓实现了零的突破,其长篇代表作《灵山》在1982年夏天初稿于北京,1989年9月完成于巴黎。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高行健可能受益于自己在中国的不幸冷遇,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冷遇可能增加了他的国际文化资本,并且加强了他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美]张英进:《世界与中国之间的文化翻译:有关诺贝尔奖得主高行健定位的问题》,崔潇月译,见[美]大卫·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第260页。因此,宇文所安指出:“高行健的获奖再清楚不过地体现出了一个相当明显、然而我们以前不曾注意到的事实:这是一个欧洲的选择,不是中国的选择;或者像人们常说的,这是个‘瑞典的奖项’。在中国,人们似乎开始意识到,所谓的世界文学或者世界诗歌都是在地方上形成的,是在欧洲或者美国,从一个根据自己的价值取向来作出判断、进行中介的文化中心。”*[美]宇文所安:《进与退:“世界诗歌”的问题和可能性》,洪越译,田晓菲校,《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
虽然高行健的作品并不乏“中国性”(Chineseness),他本人也承认《灵山》浸润着“以老庄的自然观哲学、魏晋玄学和脱离了宗教形态的禅学”为代表的“纯粹的东方精神”,以及长江流域包括羌、苗、彝等少数民族遗存文化在内的“民间文化”*高行健:《没有主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201页。,但作者更倾向于一种“超民族”的立场。他说自己“追求的是另一种中国文化,另一种小说的概念和形式,也是另一种现代中文的表达”*高行健:《没有主义》,第114页。。欧洲现代主义作家(如普鲁斯特、乔伊斯和弗吉尼亚·伍尔夫)被他尊为创作灵感的来源,心理进程的“短路”趋向则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弱点”*高行健:《没有主义》,第139页。。为了克服这种缺憾,《灵山》被构思成了“一种新鲜的文学,一种基于东方人民的认知和表达方法,但也沉浸于一个现代人的意识中的现时代文学”*高行健:《没有主义》,第107页。。换句话说,高行健所追求的创新方式正是具有“流散写作”的文化翻译、文化旅行、文化混合等特点,同时也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其他得主,如奈保尔、伊姆雷、库切、耶利内克、帕慕克、克莱齐奥、略萨等人一道,将来自不同文化的异质因子整合为一个生趣盎然的有机整体,从而完成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正因如此,瑞典文学院在对高行健颁奖时特别强调他作品的“普遍价值”:“通过它的复调音,它对不同流派的融合以及写作的细致,《灵山》复活了德国浪漫主义关于世界诗歌的崇高概念”*[美]张英进:《世界与中国之间的文化翻译:有关诺贝尔奖得主高行健定位的问题》,崔潇月译,见[美]大卫·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主编:《世界文学理论读本》,第256页。。
与此同时,高行健对自己作品的成功“世界化”使得他的获奖并未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诺贝尔奖情结”。相形之下,土生土长的莫言2012年的荣膺更被视为中国文学的胜利。但琼斯警告说,葛浩文(HowardGoldblatt)英译莫言小说被接受的例子表明“歌德世界文学设想中内在的结构性矛盾直至今天还伴随我们”,譬如《红高粱家族》的故事发生在山东省高密县,“英译却把它的副题改为‘一部关于中国的小说’。这一举动等于在预告此书推销和批评的战略”*[美]Andrew F. Jones:《“世界”文学交换中的中国文学》,李点译,《今天》1994年第3期。。诺贝尔奖委员会成员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读者一样,所接触的外国文学只能是优秀翻译家和学术经纪人介绍来的文学,“它们不能太有普遍性,也不能太异国情调;它们必须处于让读者感到舒适的差异之边缘”*[美]宇文所安:《进与退:“世界诗歌”的问题和可能性》,洪越译,田晓菲校,《新诗评论》2006年第1辑。。
莫言小说正符合国际市场的这一需求。谭恩美(AmyTan)和奥维尔·席尔(OrvilleShell)在护封的短评(因他们的中国权威地位而入选)向读者保证莫言完全有资格进入世界文学之林,他的“高密东北乡”既与众不同又具有“普遍性”。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小镇一样,莫言借助一种类似于法国新小说、美国后现代小说的实验形式,以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荒诞、怪异,且又不乏叫座的性爱和暴力场景的文学世界。德国著名的文艺评论家伊利斯·拉迪施(IrisRadisch)也在《时代周报》上撰文断言:“这是‘世界文学’!中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小说是卓越而奇特的。”拉迪施继而写道,“取材于中国民俗文化的写作内容据莫言推测很难受到西方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喜爱。但他错了:莫言百无禁忌的书写将我们带回那段被人遗忘了的,充满惊悚、魔力和无休无止的故事的生命”*Iris Radisch, “Es ist Weltliteratur! Die Romane des chinesischen Literaturnobelpreistraegers Mo Yan sind grossartig und befremdend, ”, Die Zeit Nr. 43 (18.10.2012).。
这里依然体现了差异性与同一性二律背反的微妙共生。莫言蜚声国际最终和西方对中国的兴趣与想象相联系,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经济的腾飞也增强了中国文化的吸引力,许许多多的外在因素可以解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不断增长的声名。但莫言经验是不可复制的,莫言文学并不代表中国文学。中国作家和学者既应警惕全球市场驱动下的同质主义的文学倾向,也应避免创作及研究上的“自我他者化”,以免刻意迎合工业资本的利益或欧洲评委的趣味而深陷西方文化霸权的话语逻辑。为了实现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复兴,中国不妨借鉴歌德对日耳曼文学的设计,通过翻译使中国成为“世界文学”的集贸地,确立“汉语语言文化”为“世界文学”的特别媒介,唯此,中国才能从“世界文学”中获利,重建自己的民族文化自信。
[责任编辑刘培]
作者简介:亚思明,本名崔春,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讲师、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山东威海 264209)。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