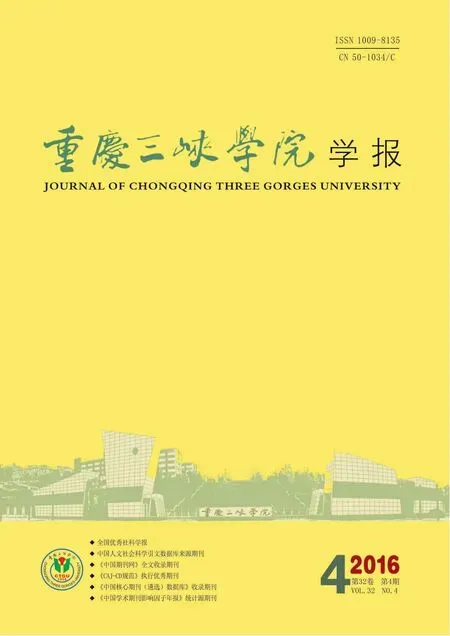近二十年重庆日租界研究述评
王 进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重庆 400043)
近二十年重庆日租界研究述评
王 进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重庆 400043)
摘 要:重庆日租界是中国近代史上列强在西部地区开辟的唯一租界,自1901年正式建立至1937年彻底废除,共历36年有余。1980年代初开始直到今天,有关重庆日租界的研究方兴未艾,取得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比如对租界内部活动的广泛探索、对租界回收过程的精确界定等等。在未来对重庆日租界的研究中,还应进一步探索重庆日租界设立过程中的两国外交谈判细节、重庆日租界内部企业及其活动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重庆日租界;外交谈判;内部企业;回收过程
租界是指两个国家议定租地或租界章程后,在其中一国的领土上为拥有行政权和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的另一国设立的合法的外国人居住地。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945年抗战胜利,租界的历史几乎贯穿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成为一段独特且重要的历史存在。
就日租界而言,比较公认的说法是中国近代史上有过5个日租界,分别为重庆日租界、苏州日租界、杭州日租界、天津日租界和汉口日租界[1]254。其中,重庆与苏州、杭州三地日租界的设立均源起于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约定“开放湖北省荆州府沙市、四川省重庆府、江苏省苏州府、浙江省杭州府为通商口岸”,需要说明的是,沙市这一通商口岸也曾在1940年6月订立过租界章程,但由于事实上并未真正有租界地为日方使用[1]44,所以一般不作为日租界来看待,因此就形成了段首所说的5地日租界的说法。
本文将结合近二十年史学界对重庆日租界的研究,全面综述重庆日租界的研究成果、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研究趋势。
一、近二十年重庆日租界研究脉络
笔者所能找到的有关重庆日租界最早的研究是1983年隗瀛涛与周勇合著的《重庆开埠史》,该书是重庆地方史的扛鼎之作。书中有两处直接写到了重庆日租界:第一章(重庆开埠始末)之第五节标题为“日本强迫重庆开埠”,此节首先提到了日本如何一步步走上殖民扩张的道路并开始侵略中国,然后论述了清政府甲午战败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重庆辟为通商口岸;第二章(帝国主义由点及面对四川侵略的全面展开)之第二节标题为“租界和租借地的设立——第一次在四川建立起国中之国”,此节详细论述了重庆日租界设立的过程以及租约的主要内容[2]22-28,33-37。
《重庆开埠史》首次厘清了重庆开埠的始末、重庆海关建立的时间以及重庆日租界正式设立的时间,为重庆日租界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8年3月,袁继成撰写的《近代中国租界史稿》出版,该书第二章(其他各地租界的建立)之第三节“八国联军侵华和租界的恶性膨胀”中的第四点单独论述了“日本划定重庆王家沱租界”的内容,从1901年订立租约说起,重点探讨了租约内容及日本方面获利之丰,提出“《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集其他专管租界所获中国权力的大成,并有所发展……根据这个约书,日本在重庆王家沱租界获得了一个独立国家所有的一切权力……其他国家按片面的最惠国待遇,自动的‘均沾’了日本在专管租界里的特权”。[3]103-104
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黄淑君与王世祥于1989年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重庆王家沱日本租界始末》一文,该文也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有关重庆日租界研究最早的学术性论文。文章由“王家沱日本租界的由来”、“日本帝国主义在重庆的侵略活动”、“王家沱日租界的收回”[4]三部分组成,完整论述了租界的由来、租界的活动、租界的回收等三大主干内容,由于较早地从学术高度对该段历史进行全面探讨,因此该文在重庆日租界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
1991年10月租界史研究领域诞生了又一里程碑式的学术著作——费成康主编的《中国租界史》,该书全面论述了中国各地租界开辟、拓展、收回以及租界和类似租界的地区的基本情况,严谨性与全面性都有明显提高。该书关于重庆日租界的论述有如下几处:第一章“租界的开辟”,以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事变为时间节点分四部分讲述了不同时期的租界开辟情况,在第四节“庚子事变后的年代”倒数第4段介绍了重庆日租界开设的大致经过,披露了一个重要史实:重庆日租界在开设过程中经过了长时间的交涉谈判。第七章主要讲“各国租界的异同”,其中第四节为日租界部分,开篇即点明了“日租界开辟较迟,商务不振,大多不是重要的租界”[1]254这一观点,又提出“由于租界位置偏僻,日商又财力有限,除天津日租界外,其余四个日租界(即重庆、汉口、苏州、杭州四地)均不繁荣”,对重庆日租界的评价为:“重庆日租界则从未出现过繁盛的迹象,界内建成的房屋屈指可数。直到20世纪30年代,当地只租出103亩土地,只占租界总面积的七分之一……”,最后总结为“不繁荣、不发达,是日租界的普遍状态”。第八章主要讲“各地租界的兴衰”,其中第五节“其他各地的租界”中提到重庆日租界时写到“位于王家沱的重庆日租界是唯一开辟于中国腹地四川省的外国租界……设在界内的工厂有生产红头火柴的有邻公司。规模较大的是在租界内外均有厂房的又新丝厂。……设立日清轮船公司的下属机构,使该公司的航线从上海经汉口一直伸展到重庆。1937年,连同日本领事馆的馆员在内,留在重庆城内、城外的日人总共只有20余人。根据这一数字来推测,尚在长江南岸王家沱日租界内居留的日人,至多只有数人。”[1]303,307最后一章即第十二章主要讲“租界的收回”,其中第四节“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涤荡”部分里写到“从(1937年)7月下旬、8月初起,日本侨民及领馆人员陆续从重庆、汉口、苏州、杭州等地撤退,当地的日租界均交中国政府代管……不过,此时苏州、杭州已经沦陷,不久,汉口也陷于敌手,这3地的日租界又被恢复。在此期间,真正被中国收回的仅有重庆的日租界”。可以说,《中国租界史》对重庆日租界的研究可谓既全面又准确,涉及到了其设立、内部工商业状况及最终的收回,于学术研究的贡献可谓既往开来。
1992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共收录租界史研究相关论文60余篇,其中关于上海、天津、汉口等东中部大城市的论文数量较多,其他城市的比较少,与重庆日租界相关的仅有艾新全的《重庆日本租界》。该文从王家沱本身地理位置说起,记叙了从甲午战争重庆开口到租界设立直至抗战胜利租界收回的整体概况,中间较多写到日方在租界内的殖民暴行。
1998年10月邓沛的文章《重庆日租界的收回》在《民国春秋》上发表,该文主要论述1937年抗战爆发后重庆日租界得以收回这一史实,其他内容仅作为铺陈来叙述。另外,该文并未提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租界回收,而是直接着眼于抗战爆发后的彻底回收并明确了租界回收的最终时间[5]。
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由茅家琦和张远鹏先生主编的《百年中国史话》丛书,该丛书第三辑是《租界和租借地史话》,本书与1991年费成康的《中国租界史》结构类似,也是以租界开辟、租界内殖民罪行、租界收回这三大内容为主线,内容比较详尽全面。有关重庆日租界,书中主要提到了其开设与收回的相关内容,具体内容与《中国租界史》大致相同。
2001年7月,《文史杂志》刊载了一篇有关重庆日租界的文章,题为“不能忘却的记忆——1901~1937年重庆日本租界剖析”。该文作者王德昱与日租界毗邻而居,且真真切切亲眼见过那段历史,故而文章具有口述史的优点。开篇这样写道“……这里特将这篇回忆奉献给读者,算是了却一个当年与日租界毗邻而居,曾耳闻目睹日本人所作所为的老人多少年来的心愿”。从内容上说,文章的亮点在于披露了一些微观具体的有关重庆日租界内在活动的细节,比如租界内部怎样私卖军火、如何倒运鸦片毒品、如何利用“色情”收集情报等等,对于火柴业、丝织业等的经济掠夺也叙述详细。以往的研究对于重庆日租界的收回时间未能确指,大多只是含糊地说成7、8月间,但本文继邓沛之文后再次明确重庆日租界的收回时间是1937年8月1日晨,在这一天日本人最终撤离重庆。文章最后还写到“是日,我和家人与众多民众伫立于江岸上,本想看到日本人狼狈离去的样子,没想到却是这样的情景!那日本船在驶入昔日租界江段时还停机举行降国旗,鸣长笛,全体肃立的告别仪式……”,[6]39短短数语令人身临其境,仿佛将读者拉回到了几十年前的那个历史结点,感人肺腑。总之,本文观点独到、鲜明,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2001年是重庆地方史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由周勇先生主编的学术性通史专著《重庆通史》出版,在出版说明中作者指出“在研究的整体思路上,我们坚持厚今薄古的原则,在古代悠久而丰厚的历史积淀上,浓墨重彩地论述近代历史”,[7]7这一研究思路本身就道出了重庆这一地区之历史的整体特点。相对古代史而言,重庆的近代史更为精彩斑斓,“开埠”这段历史是其“锁钥”。在重庆开埠这段历史中有两大内容很重要,一是老牌殖民帝国英国先后通过1876年《烟台条约》和1890年《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强迫重庆开埠,另一则是新兴帝国主义国家日本通过甲午战争的胜利彻底获得“最惠国待遇”特权,从而达成自己梦寐以求的在中国与西方诸强“利益均沾”的目标,在《马关条约》中把重庆明确列为四处通商口岸之一,并在条约签订后的几年里经过一系列交涉之后建立了“重庆日本专管租界”。
《重庆通史》的第二卷之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有较大篇幅涉及重庆日租界的历史,如第一章第二节在论述日本强迫重庆开埠时指出“日本轮船可以从湖北宜昌溯长江而上至四川重庆,这就实现了几十年来英国人梦想通航川江、上驶重庆的宿愿”,[7]288充分点出了“最惠国待遇”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破坏;第二章第二节在直接论述重庆日租界建立及日租界本身时,对日租界建立的过程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说明,比如提到了四川总督如何委派张华奎接手谈判事宜等内容。
同为长期从事重庆城市史研究的重庆籍学者张瑾于2003年出版了自己的博士论文:《权力、冲突与变革——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该文探讨的内容虽是1926—1937年重庆的城市化和现代化问题,但主要内容之一为“开埠通商”。这部分论述绕不开重庆日租界,不仅是因为重庆日租界的建立本身就是重庆开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由于重庆日租界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才正式由国民政府收回[8]52,所以单从时间上说其本身就处于作者的研究范围之内。该文对重庆日租界的论述大致分为“租界建立”、“租界发展”、“租界收回”三大部分,并以一个重庆人的视角思考日租界对重庆城市现代化的影响和作用,认为“重庆日租界的‘现代’示范效应极其微弱。由于史料的局限,笔者无法就日本如何在重庆的租界内统治的实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应该说,开埠口岸的一般特征,重庆基本都具备了,但是,日本在重庆租界的特殊状况,使得它远未发挥出现代的示范效应……”,[8]50,52这种说法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殖民、殖民地”的双面性,也就是说殖民与殖民地对于被侵略国家来说首先是一种剥削掠夺,但另一方面它对当地的现代化进程又确确实实发挥着或多或少的作用。
以上为重庆日租界研究领域的主要的一些专著和论文,除此之外,《重庆与世界》杂志在2005年和2012年刊载了两篇相关文章——《沉寂在大宅门中的重庆南岸王家沱的来历及其故事》与《百年沧桑看王家沱租界》,前者主要以王氏家族的发迹与衰落为主线,有关与日租界交集的内容只是简单提及,后者则以重庆日租界的设立、租界内部活动及租界的收回为主线,但内容实与前人研究无异。
二、主要研究成果
前文细致梳理了重庆日租界二十年来的研究脉络,相关研究成果大体有如下几点。
第一,明确了重庆日租界的设立时间、地点、租界范围及租约内容,即重庆日租界设立于1901年9 月24日,租界选址于王家沱地段,所订租约《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中规定“西界自江流、自岩坎接至江流长五十丈之处,划成直线以为限,幅宽百零五丈二尺;南界沿税务司基地界线划成直线,向东至距西界深四百丈为止;北界自水沟注江中心,即距南界百零五丈二尺处,划成直线与南界直线并行,向东至距西界深四百丈为止;东界从南北线尽处划成直线以为限,丈尺与西界相同”。
第二,明确了租界正式设立前中日两国确实进行了漫长的交涉。即重庆虽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时就已经辟为通商口岸,但直至1901年9月才正式设立了租界,粗略算来交涉时间长达五六年,正如费成康先生在《中国租界史》中写的“……本来应在甲午战争后的阶段中就被开辟,只是因交涉的时间较长,才被拖延到1900年以后”。
第三,对租界内部活动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内容涉及行政管辖、经济侵略、殖民暴行等诸方面,可以确定借租界开的比较大的公司有“又新丝厂”、“有邻公司”、“日清公司”等,这些公司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以重庆为首的中国西南地区进行经济掠夺的急先锋。日轮横行川江时常给当地人民造成生命财产损失,日本侵略者时常借军舰的威吓迫害华人、私卖军火、倒运鸦片、开设烟馆妓院等罪行昭然若揭,披露了重庆日租界的开设对国民经济与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
第四,明确了租界收回的过程,即重庆日租界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不久,在当地人民声势浩大的反日浪潮压力下曾短暂收回,日领馆也被关闭;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日方据此协定得以重开租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7年7月31日至8月1日晨,日侨及领事终于全部撤离,重庆市政当局接管王家沱日租界,至此,中国人民将盘踞祖国西南地区长达36年之久的重庆日租界正式收回。
三、研究成果中存在的分歧
纵观重庆日租界长达二十余年的研究脉络,不难发现这期间产生了一个较大的分歧——重庆日租界的具体收回时间。
1988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租界史稿》指出重庆日租界的日侨及领事人员是在抗战爆发后不久先撤至武汉后经上海回国的,但其撤离重庆的详细时间并没有明确给出。然而,在1989年刊载的《重庆王家沱日本租界始末》则把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的那次回收租界当成是重庆日租界的收回时间,“1931 年10月22日,日领遂率领日侨乘日本军舰离渝回国……重庆人民为收回王家沱日租界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取得了光辉的胜利……”。[4]122两年后即1991年出版的费成康先生编著的《中国租界史》里间接提到重庆日租界收回的时间是1937年的“7月下旬8月初”,虽没有敲定具体时间,但是与《近代中国租界史稿》中的说法相吻合。1992年出版的论文集——《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完整的叙述,“(1931年)10月24日,刘湘派军警接管了王家沱租界……1932年,《淞沪协定》签订后……日本派领事卷土重来,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警察局再次接收了王家沱日租界”,[9]394但是仍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1998年邓沛的《重庆日租界的收回》在这个问题上有了巨大突破,首次明确给出了重庆日租界收回的具体时间为“(1937年)8月1日凌晨”,但该文仅考证了1937年抗战爆发后彻底收回的时间,而忽略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首次收回时间,可谓美中不足。2001年,王德昱老先生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和记忆也给出了日侨及领事撤离的具体时间是“8月1日晨”,中国政府接管的时间是“7月31日”,该说法与邓沛之文基本一致,二者可彼此参证。
至此,有关重庆日租界收回时间的研究基本达成了。2012年刊载的《百年沧桑看王家沱租界》一文中也写到“九一八”事变后收回、“一二八”事变后又恢复,以及抗战爆发后最终收回这样一个过程,但与邓沛、王德昱之文稍有不同的是,该文里日侨离渝的时间是7月31日而非8月1日,这只是极细微的差别。
四、深化研究的必要性与未来的着力点
今天重庆已经成长为中国西部地区的龙头城市,因此,研究重庆日租界不仅有学术意义,更有现实意义。由广域视角来观之,重庆日租界的这段历史是重庆抗战史、重庆近代史及重庆对外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0]。纵观重庆日租界的研究性论文与著作,很多内容承袭前人,突破性成果较少,研究工作进展缓慢甚至趋于停滞,与上海、天津、汉口等地区的同类型研究相比相差甚远,仍有较大空间需要我们去努力。
在未来的研究中,至少有两处需要加强:第一、谈判交涉:1895年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中重庆就已经辟为通商口岸,次年即1896年即开始了设立租界的正式谈判,但直到1901年9月重庆日租界才正式设立,从谈判到成立时间跨度长达五六年,这期间的谈判经过与细节究竟是怎样的?有关于此,尚无细致和成熟的研究出现。第二、租界内部情况:虽然对于租界内的一些重要公司及经济掠夺、日本殖民者的不法罪行等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对于存在了长达36年之久的重庆日租界来说,目前的研究仍没能足够清晰的复原其内部情况,比如其侨民人数的变化、侨民的日常生活与文教设施、日方间谍以租界为掩护搜集情报的状况等等,这些问题的研究亟待加强。
五、结 语
从1983年隗瀛涛与周勇所著《重庆开埠史稿》问世到今天,有关重庆日租界的研究可谓绵延不绝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重庆日租界是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西部地区建立的唯一租界,是设立最晚的租界之一,也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政府在事实上收回的第一个租界(其他租界均处于沦陷区,故实际上没能收回),故其本身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当然,深化对重庆日租界的研究,需要借鉴前人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更需要在此基础上广泛挖掘新史料、全面的运用新理论,如此,研究工作方可取得突破性进展。
参考文献:
[1] 费成康.中国租界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2] 隗瀛涛,周勇.重庆开埠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
[3] 袁继成.近代中国租界史稿[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4] 黄淑君,王世祥.重庆王家沱日本租界始末[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3):112-122.
[5] 邓沛.重庆日租界的收回[J].民国春秋,1998(5):26-27.
[6] 王德昱.不能忘却的记忆——1901—1937年重庆日本租界剖析[J].文史杂志,2001(4):37-39.
[7] 周勇.重庆通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
[8] 张瑾.权力、冲突与变革——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9]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列强在中国的租界之重庆日本租界[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
[10] 李永东.情陷上海洋场的外乡人——评《海上花列传》[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87-91.
(责任编辑:张新玲)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135(2016)04-0109-05
收稿日期:2016-02-11
作者简介:王 进(1981-)男,重庆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馆员,西南大学2014级近现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
Review of Studies on Chongqing Japanese Concession in the Past Twenties Years
Wang Jin
(Chongqing Hongyan Museum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Chonging 400043)
Abstract:Chongqing Japanese concession is the only concession in the western areas of China, opened by the imperialist powers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The concession existed for 36 years, from the formal establishment in 1901 to the complete abolition in 1937. Since early 1980s, studies on Chongqing Japanese concession have been on the rise, yielding a series of results, valuable studies, such as extensive exploration on activities at the concession, well-definition on the process of recovering concession, etc. However, the details of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he process of setting up Japanese concession, internal enterprises and related activities at the concession should be further explored in the future study.
Keywords:Chongqing Japanese concession;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internal enterprise; recovery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