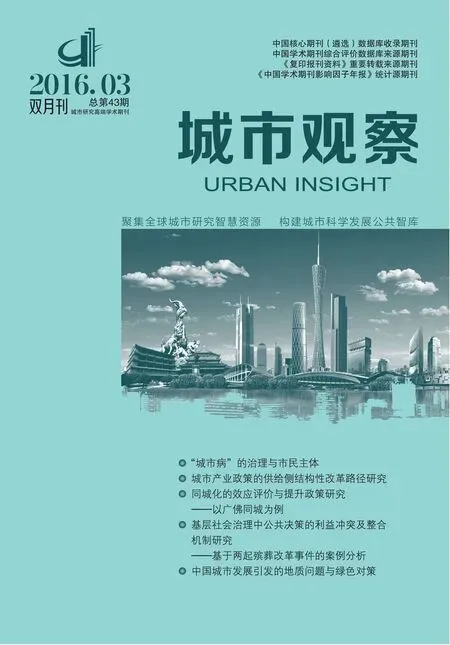“城市病”的治理与市民主体
◎ 董小麟
“城市病”的治理与市民主体
◎ 董小麟
摘 要:城市化进程既带来城市人口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同时也衍生了“城市病”。城市在发展中产生的“城市病”,其防与治必须依靠市民主体,通过提升市民素质来完成,这应该成为我国实行有效城市治理的基本理念。市民教育和提升市民主体意识参与城市治理,必须依据中国国情和各市的市情,从提升市民对城市治理的参与度和话语权、把城市看作是一所大学并加强社区教育功能、把市民教育更好地纳入国民教育、强化中等收入阶层市民主体培育和以城市文化凝聚市民主体精神中来实现。
关键词:“城市病” 城市治理 市民主体 市民素质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之一,随着全球城市化率在2007年跨越50%,按常住人口计算,中国也在2011年越过50%大关,并呈现持续较快的发展势头。今天的城市,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各国的城市特别是其主要城市,已经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表,就如人们以北京代表中国,以纽约代表美国,以孟买代表印度,以里约热内卢代表巴西……
在中国等人口众多的新兴经济体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新时期,世界为之聚焦。城市史权威学者科特金(Joel Kotkin)在2005年为其《全球城市史》中文版写的序言指出:“中国在从事着世界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城市建设活动,……这种变化的速度是突破性的。随着农民迅速地离开农村,农业经济转变为工业甚至是后工业经济。中国试图在二三十年的时间内完成西方世界用150年时间才完成的事情”;“环境问题,从潜在的气候变化到人类健康和演进问题,都可能危及中国城市化的质量和走向。在这样的环境下建设城市文明是一种巨大的挑战。中国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决定未来几十年内国家繁荣的问题,也将在全球范围内决定未来的城市生活”。科特金所说的挑战,是基于城市发展,特别是快速发展中的伴生品——“城市病”的困扰。
城市化进程如何在充实经济社会发展的正能量的同时,尽可能降低城市发展内生或外部性效应所带来的“城市病”的负能量,是城市治理中必须直面的重大现实问题。阿尔·戈尔(Al Gore)在《我们的选择》(2009),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在《城市的胜利》(2011)等专著中,对此表达了相应的关注。2015 年12月,中央召开了时隔30多年的首次最高层次的城市工作会议,会议关注了城市治理中的“城市病”,在会后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直接作出了“‘城市病’蔓延加重”的判断。同时《意见》还明确指出,要“以加强和改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提升市民文明素质推动城市治理水平的不断提高。①”因此,不仅城市发展为了人,城市发展更依靠人;城市在发展中产生的“城市病”的防与治必须依靠人,通过提升市民素质来完成,这应该成为我国城市化迅速推进中,实行有效的城市治理的基本理念。
二、“城市病”的表现
一般认为,“城市病”是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城市迅速膨胀而造成的一系列环境与社会问题。刘易斯·芒福特(Lewis Mumford)在《城市发展史》中阐述道:“在1820年至1900 年之间,大城市里的破坏和混乱情况简直与战场上一样,这种破坏和混乱的程度正与城市拥有的设备和劳动大军数量成正比例”②。对“城市病”的具体表现,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分析。近年来,国内关注“城市病”的学者不断增多,相关的分析也逐渐丰富起来。
王格芳(2012)把“城市病”归结为五大表现:交通拥堵严重、能源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安全基础薄弱、社会矛盾凸显。杨卡(2013)提出,“城市病”有“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城市贫困”等问题。倪鹏飞(2013)认为,“城市病”是指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在中国所表现出的特征有: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贫困失业、住房紧张、健康危害、城市灾害、安全弱化等。笔者认为,这些观点虽然并不意味对“城市病”分类的完成,但本质上覆盖了城市自然环境与城市社会环境两大领域的症结,应该成为我们观察“城市病”的基本视角。但是,像其中部分学者所指的住房紧张,实际上主要集中于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和超大城市,对于二三线城市和小城市,这个问题不突出,而且通过这些年来二三线以下的城市房价走低、去库存压力大,可以得到印证;至于贫困问题,中国目前需要精准扶贫的主要分布在农村,城市占贫困人口的比重小,而且中国基本避免了众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大城市形成庞大贫民窟的困扰。
一些学者基于实证研究的需要,尝试对“城市病”的表现进行测度,构建一系列指标体系,并引入一定的样本进行研究。这些指标的设计同样体现了研究者对“城市病”的分类。李天健(2012)按自然资源短缺、住房紧张、环境恶化、交通拥堵四项指标,对我国9座重要城市的“城市病”,分五级进行测算;但这个指标体系对城市社会性问题明显覆盖不足。王宁(2015)只用两大指标——通勤指标(含通勤时间、通勤时间成本/房租)、效用指标(含实际购买力、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来构建城市空间结构指标体系,未免过于简单,因为通勤是否通畅,与环境空气质量指标等直接相关,这种自然环境受影响的指标是不应该被忽略的。齐心(2015)提出7个层次的指标体系(含城市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破坏、基础设施不足、公共服务紧张、公共安全弱化、生活质量下降、社会隔离加剧),并对北京市2008—2012年的“城市病”状况行了实际测度。但他所拟的一些二级指标存在缺陷,如把城市人口密度提升作为“城市病”正向指标,实际不完全符合当今城市集约化、紧凑型发展以利低碳城市建设的趋势;把万人供水管道长度、万人集中供热管道长度等作为“城市病”的反向指标,也存在同样性质的不妥。
武占云等(2015)尝试用城市“亚健康”的概念替代“城市病”的表述,提出了中国城市健康发展指数的范畴,它建立在健康经济、健康环境、健康社会、健康文化和健康管理五项指数测算基础上,并以此对2013年除拉萨市、三沙市以外的287个地级及以上建制市的城市健康发展状态进行综合评价,做了大量工作,应该说不无启发,有正面引导意义;但毕竟“亚健康”用词的分量太轻,而且变量设计不完善,某些设计不够客观,如把“万人在校大学生数”列为变量之一,显然忽视了我国高校布局受行政干预大而分布很不均衡的特点,这种变量对多数城市可能是不公平的,如果改用“每万人口中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则更合理。
笔者认为,“城市病”的内涵和外延是丰富的,实践发展也将引起变量的调整,但这些“病症”主要表现在城市发展进程引起的自然环境质量和社会环境质量两类问题,并且会随着城市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点和程度;但自然环境质量在城市也基本属于人类社会活动所造成,这里只是根据病征的表象进行区分。在中国现阶段,城市特别是根据新拟订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调整方案》③所列的那些城区超过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超过1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城市病”比较突出,其它城市也多存在轻重不一的“城市病”。其中城市自然环境质量问题主要涉及城市空气、水系(含地表水质与地下排水系统、污水处理系统)、噪声、光污染和热辐射、垃圾、自然灾害的化解等问题;社会环境生态问题主要涉及居民的文化与文明程度、交通因素、治安、公共服务质量等。
三、市民作为治理“城市病”主体的意义
虽然造成“城市病”的因素有很多,但总体属于人类活动所使然。因此,解铃还需系铃人,“城市病”的治理还需要人的努力,市民就是治理的主体。
解释城市治理中的市民主体,必须从现代法治社会中关于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相对等的基点出发。如果割裂权利与义务,城市治理的良性环境就难以营造。比如,滥用公共资源,不重视节电节水,不注意垃圾减量和垃圾分类,等等,在自己权利的行使中,忽视或漠视自己的公民义务,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城市释放出负的外部性,恐怕不是少见的现象。近年来,关于农民工进城应该享受城市居民权利的观点发表较多,但对其应该履行市民义务的讨论则较少;实现新老市民权利与义务的平等,应当是引导市民发挥城市治理主体作用的必然要求。
在城市化先行的发达国家,自18世纪的欧洲,到19世纪末的美国,由于城市规模扩张,外来移民急剧增加,新加入城市的移民对自己权利的关注度较大,但对如何在新的城市里尽市民的义务则往往忽视,而且对权利的关注也由于对权利内涵及权利边界的认知模糊,出现自身权利行使不足或权利滥用的状况。因此,公民教育问题首先在城市治理领域得到重视。从1791年法国宪法最初列入公民教育,到1889年亚当斯(Jane Addams)在美国创办赫尔会所,后者着重向以来自欧洲的新移民构成的劳动阶级提供融入社会和接受教育的机会;再到后来,欧美国家把公民教育普遍列入从小学到大学的课程体系。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针对其社会当中个人主义过于强化的趋势,再次调整和加强了公民教育课程的设计,将培养公民的责任感作为对发展公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萌发于西方的公民教育的概念,本质上更适用于全民,应该覆盖城乡,而非仅仅针对城市;尽管城市的公民教育投入会更多,但笔者认为还是应该把城市的公民教育寓于市民教育之中,而不是简单把公民教育概念取代市民教育,以明晰城市公民教育的特殊性,包括结合各城市文化、经济与人口结构的特点而开展市民教育,在国情背景下结合市情来构造现代市民主体意识和主体责任。
国内外的实践和我们自己的发展愿景,都告诉我们: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城市化的本质也同样是市民的现代化;城市的现代化有利于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促进着城市的现代化;城市向市民不断注入现代化的元素,而市民的人的现代化,则将源源不断地为城市的发展注入着现代化的理念与行为。
比如,从“城市病”的一些表现看,在交通堵塞方面,既有城市规划和政策引导的因素,又受制于市民对公共交通的支持和参与程度;在建设低碳城市方面,既有城市设施的改造需要,又受制于市民是否积极节能减排、控制那些会产生污染的消费;在垃圾“围城”方面,既有城市对垃圾的处理能力需要提升的要求,又受制于市民能否参与循环经济的行动和使垃圾减量化,并自觉参与垃圾分类;在公共服务资源方面,既需要政府组织高效、充分的服务资源,又受制于市民是否学会公共财富的分享和避免滥用;在城市秩序与治安保障方面,既需要城市建立一定的管理队伍和治理设施,也需要市民自觉遵守城市秩序,并像北京的“朝阳群众”那样有群防群治的观念和行动;即便是一些论者所提出的城市中的贫困问题一旦出现,除城市规划建设中必须强调产城一体化、创造就业机会和对确实需要救济的必须由政府和社会解决外,还受制于市民是否积极参与给自己的“劳动能力的贫困”进行脱贫的学习,如此等等。因此,“城市病”的治理,既需要城市规划的合理、政府管理的到位,更需要通过市民的现代化,使之成为广大市民的责任和义务,最终成为市民的自觉,这也符合了哲学意义上的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
四、城市治理中市民主体意识的培育
“城市病”的治理是全部城市治理活动的组成部分,对市民在城市治理中主体意识的培育,必然包含了市民参与甚至主导“城市病”治理的意识觉醒和行动自觉。有效的城市治理应该更好依托并更好教育市民行使相应的治理权利和治理义务。
(一)提升市民对城市治理的参与度和话语权
中央的《意见》所提“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在实施中需要解决外因与内因互动的问题。在城市对市民提供外部教育环境的同时,更需要激发市民提升自身素质以融入城市的主观能动性,解决市民在城市治理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以利激活其主体意识,从而促进其从城市的“客家”转变为城市主人,而主人对自己的“家”总会自觉爱护的。因此,城市对市民主体综合素质的提升,必然具有不亚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义。
广州市自2013年起组建的重大城建项目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简称“公咨委”),是一个开放型的不分阶层的组织,被誉为体现“草根”参与城市管理决策的组织,其发挥作用的舞台大,社会公众反响好;而且其两年一届的换届间隔,有利于保持其成员参与的广泛性和活跃度。这个经验值得推广,建议可以进一步在设区的城市设立市、区两级类别的组织,甚至在社区,在现有的街道、居委会的基础上,也可以组建社区公共事务咨询监督委员会(或小组)。这类发挥市民在城市治理中的主体作用的组织,本身也具有重要的教育功能,参加这类组织,自身素质的提升必然得到一种激励和鞭策,而它的作用的发挥也是对广大市民提升参与度和话语权,乃至增强责任感的一种示范性的素质教育。
(二)确立“城市是一所大学”的概念
笔者一直倡导“城市是一所大学”的理念,因为加入一个城市,成为其市民,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该城市文化、秩序、法规等的影响或制约,从而导致自己观念和行为的某些改变。而越是大城市,这种“城市大学”的教育氛围就越是强烈;越是治理水平高的城市,这种“城市大学”的教育功能就越是有效。
在国内,一些主要城市已经把城市大学的概念化为实体,如上海自2008 年起先后在18 个区县建有社区学院、每个街道建有社区学校,构成全覆盖的社区教育体系;杭州等城市把社区教育分为市的社区大学、区(县)的社区学院、街道的社区学校和居委会的教学点四个层级。为加强对社区教育的组织领导,宁波江北区等地还成立了区的社区教育委员会。
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城市和社区中有相当比例的人对公共生活的秩序,对公共生活有序参与的重要性缺乏基本的认识。这种状况显然直接影响到城市和社区软实力的建设。在讨论农民市民化问题上将公共生活规范和公民教育提上日程,不应小视这些有关公共生活规范的教育,它不仅涉及个体素养提升的层面,而且有可能是牵涉到一个社区、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竞争力的大事(缪青,2009)。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不然,对新移民集中的城区特别是所谓城乡结合部即俗称“城中村”的地区,就无法解释为何其“脏乱差”比较突出。所以有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在城市化加快发展的阶段,进入城市的新居民,除属于引进人才或高校毕业生就业以外,大量的是来自比这个城市的发展水平低的乡村、县镇和小城市的居民,他们原有生活工作环境的社会规矩较现在新进入的城市为宽松,原有生活方式会与新进入城市的生活方式产生“文明的冲突”,因此,对他们的教育,无疑是城市的责任,特别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责任;而且城市规模越大,这种责任越重,新市民学习的过程也越长、要求越高。因此,如宁波江北区的新市民占比达50%以上,自2008年起,该区着力加大新市民教育培训的力度,促进新市民教育系统化、规模化,并启动“十万新市民素质提升工程”。成都龙泉街道也由于外来新市民比重较大而成立了新市民教育学校。但对于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而言,在市民教育中没有刻意把新市民身份过于突出,而是建立覆盖全体市民衔接记录个人各类受教育信息的终身学习账户,实行市民教育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的全覆盖。
(三)把市民教育更好地纳入国民教育中
目前,在各级各类学历教育课程中纳入公民教育内容,是许多国家的做法。但不同国家对这类课程的归类有所不同,从“公民教育”到“社会教育”、“历史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都有。内容主要涵盖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社会发展、权利义务、人格修养,乃至一定程度的职业与就业教育。
如前所述,用公民教育范畴替代市民教育,存在一定的不足;因为公民是全体国民的属性,而城市居民是公民的一个组成部分,毕竟与公民概念具有哲学意义上的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因此,要把一般教育与特殊教育结合起来,特别是在我国城市分类中属于特大与超大城市的,应该辅之以自己城市的市民读本,因为这些城市在城市体系中不仅具有较大影响力,而且其市民构成的复杂程度也远高于小城镇;市民教育对多种移民来源、多种阶层、多元文化的协调、凝聚作用更需着力,而且城市文化的提升和城市秩序的优化,也需要花更大力气。
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实践教育是一个重要领域。美国许多州设有学区,一个学区的范围内包含了不同层次的学校,学区对学生在课外的学习特别是实践教育发挥重要作用,笔者曾经考察过美国俄勒冈州的某学区,该学区的中学生直接承担了社区公园的规划(已实施)、社区排污设施完善方案的设计等许多体现市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工作。这样的活动,能够使城市的青少年更快意识到自己的市民主体身份,对城市治理的全民参与,具有积极的影响。
(四)强化大中城市中等收入阶层市民主体的培育
在一个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大国,其城市体系总体上应该呈金字塔结构,即有若干处于国际国内城市规模和能级顶端的重要的中心城市,有一批大型和中型城市,有大批的小城镇。其市民结构也由此而体现出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差异。对大中型城市而言,特别是对于居城市层级顶端的国家和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它们在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发展中,具有引领作用和核心地位,它们尤其要把做大做强中等收入阶层作为提升市民素质的重要路径。因为中等收入阶层是最具有财富创造能力和上进动力的阶层,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且自主学习能力较强,是城市治理最主要的依托力量。
格莱泽指出:“当一个地方提供了贫困人口所特别看重的便利设施时,那么这个地方可能会继续贫穷下去”④。其本质含义不是说不要给贫困人口解决问题,而是反映了城市市民结构的重要性。对重要的中心城市、特大城市的城市入户门槛还是需要的,要把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并使之逐渐壮大作为这些城市优化人口结构的主要方向,这是高端定位城市的必然选择,因为它们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引擎,而科技文化及其掌握者的强大,就是中心城市能够承担其发展使命的核心竞争力。
(五)城市文化应该成为凝聚市民精神的基础
芒福德指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⑤。由于城市发展中,新移居人口来源的多元化(城市越大、有越强的经济、政治功能,其人口来源的多元化程度越高),带来了多元文化的碰撞。而文化或文明的冲突,可能产生城市中的不和谐甚至带来矛盾的激化、地域性群体的割裂以及族群矛盾;但有学者指出,城市文化通过世世代代的市民的语言传递和其他文化载体,能够超越历史的时空、突破人们心理的防线,形成一种润物细无声的社会文化环境,对置身其中的每个市民都产生同化作用。特别是作为城市文化核心的城市精神,具有凝聚人心、规范行为、形成共同价值信仰的作用,能培养一代又一代对该城市具有强烈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的市民(黄月细等,2014)。历史上,欧美国家的公民教育,也是以强化认同感为首要主旨的。
在国内,上海的市民教育也很注重认同感,其新市民融入城市的教育活动更多依托于城市文化的凝聚力,包括推动中心城区各街镇普遍设立市民学习和沪语交流的社区教育平台,让新老市民之间的文化隔阂得到更大程度的减除,而新市民对于沪语及其代表的文化的接受,往往也出于对这个城市的热爱,这对于超大中心城市而言,与“推普”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的。
认同感、归属感是很重要的,但不是市民精神和市民主体意识形成的惟一理念。我们必须同时看到,多元文化在一个城市里的并存,同时具有积极意义。所谓文化凝聚力,如果没有集多种文化的优势而形成城市文化特色,则失去了凝聚的本意。所以,一个城市的文化特色以及它带来的凝聚力,也是既传统又现代,既有历史积淀,又不排斥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而随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起来。例如广州,既有长达两千年的互惠互利、开放包容的商埠文化,对海丝文化的贡献极为巨大;又有近代以来民族精神的弘扬、共和文化的孕育、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酝酿,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敢于先行的创新文化的再培育。
城市文化的载体是极其丰富的,从物的载体看,从文化设施到建筑风格,无处不可感知;从信息载体看,从城市网站及其内容,从城市语言和市容市貌的形象设计,无处不能透视;从人即市民的载体看,市民言谈举止的文明修养,无处不在体现。城市文化在内容结构上,至少包括四个层次:一是城市构造的风格与景观,建筑与布局,人文与自然的匹配,这属于城市的“脸面”;二是城市文化遗产、文化设施及其层次、规模、比重,也包括城市的文化产业的水平与特色,这属于城市的骨骼;三是城市的精神风貌,本质上不是包装出来的,但可作为城市的CI设计(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包括理念、行为和视觉识别,这是城市的韵味;四是文化对城市的人和事物的渗透、融合,这是城市的灵与肉的交融。
因此,正因为文化力量即使无意主动布局也会存在,那还不如积极布局而促进文化正能量的凝炼。从城市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看,正能量文化的集聚、交汇和创新提升,是城市这所“大学”的校园氛围,是对市民实施素质教育的无形或有形之手,也是引导和激发市民主体参与城市有效治理的“软实力”。
注释:
①http://www.scio.gov.cn/zhzc/3/32765/Document/1469105/1469105.htm .
②刘易斯·芒福特(Lewis Mumford):《城市发展史》,中译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第462页。
③国务院2014年10月29日《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
④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城市的胜利》,中译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第81页。
⑤刘易斯·芒福特(Lewis Mumford):《城市发展史》,中译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第582页。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http://www.scio.gov.cn/zhzc/3/ 32765/Document/1469105/1469105.htm
[2]乔尔·科特金. 全球城市史(中译本)[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刘易斯·芒福特. 城市发展史(中译本)[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4]爱德华·格莱泽. 城市的胜利(中译本)[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5]阿尔·戈尔. 我们的选择(中译本) [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6]克雷明.美国教育史:城市化时期的历程,1876-1980(中译本)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7]王格芳.我国快速城镇化中的“城市病”及其防治[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5).
[8]杨卡.基于自组织系统论的“城市病”本质、根源及其治理路径分析[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0).
[9]倪鹏飞.中国部分城市已患上严重“城市病”[J].中国经济周刊,2013(8).
[10]李天健.城市病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研究[J].城市观察,2012(4).
[11]齐心.北京城市病的综合测度及趋势分析[J].现代城市研究,2015(12).
[12]王宁.特大城市空间结构缺陷与“城市病”治理[J].区域经济评论,2015(1).
[13]武占云,单菁菁,耿亚男.中国城市健康发展评价[J].区域经济评论,2015(1).
[14]唐晶晶.城市化进程中公民教育问题研究[J].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4).
[15]李朝阳,周菲菲.美国城市化进程中公民教育的途径、内容及启示[J].当代教育科学,2014(3).
[16]缪青.农民市民化要重视城市文明教育和公民教育[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3).
[17]黄月细,贺忠.论城市文化的教育功能及其意义[J].社科纵横,2014(12).
(责任编辑:李钧)
【中图分类号】F299.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16.03.001
作者简介:董小麟,二级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副校长,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执行院长,广东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国际经济与城市经济。
Treatment for Urban Diseases and Citizens as the Subject
Dong Xiaolin
Abstract: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not only has increased urban population and promote urban civilization, but has also generated urban diseases. These urban diseases developed along with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must be treated with the help of citizens themselve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effective urban governance is by improving citizens’ quality. Citizen education and enhancing their awareness of active involvement in urban governance must be based on the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different cities. A city is like a college, where its community educational function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so as to include citizen education into national education, cultivate a better middle-income group and create citizen spirit through condensation of urban culture.
Keywords:urban disease; urban governance; citizen; citizen qu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