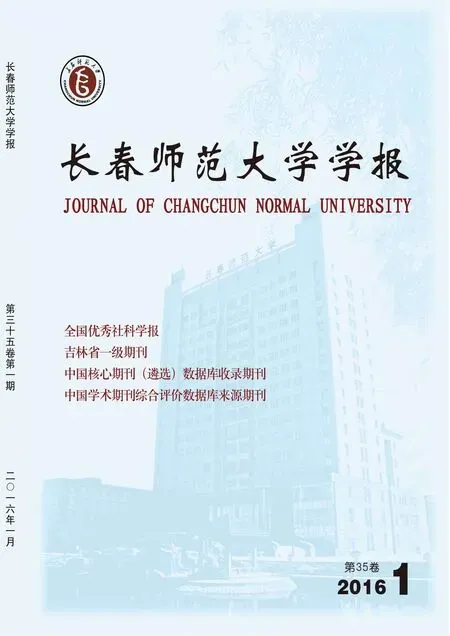论梭罗生态思想的三个维度
李韶星
(清华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84)
论梭罗生态思想的三个维度
李韶星
(清华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84)
[摘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问题。早在19世纪中期,美国哲学家梭罗就以其在瓦尔登湖畔的生活实践和一系列的文学著作表达出他的生态思想。本文通过对梭罗及其相关作品的剖析,归纳、探讨了梭罗生态思想的三个维度。研究梭罗的生态思想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当代社会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梭罗;瓦尔登湖;生态思想;维度
亨利 ·大卫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是19世纪美国著名的自然主义者、文学家和哲学家。梭罗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实践写出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河上一周》《缅因森林》《瓦尔登湖》和他的个人日记等。梭罗于1845-1847年远离繁华热闹的城市,隐居在瓦尔登湖边由自己的双手搭建的小屋,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梭罗的作品文字优美、意境深远。出自于其笔下的瓦尔登湖带给我们一种纯粹的原始自然美。他的经典著作流露出对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思考。研究梭罗的生态思想,有利于我们加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认识。
一、简朴生活,回归自然
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梭罗曾阅读过印度、中国和波斯等国的典籍,对中国的古典文化特别感兴趣。梭罗对东方文化的钻研,使得他的思想与中国传统道家文化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
在生活方式上,梭罗与老子的思想都可以用一个“朴”字来概括。道家主张节制物欲,轻视物质利益给人带来的强烈诱惑,强调返朴归真、享受人生中恬静淡雅的生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会到生命的真谛。梭罗也看到大部分人是为了追求物质上的满足而生活着,他们整天为物欲所累,过着一种可悲的生活,对金钱的追求达到极致,精神世界却极度贫乏。和老子一样,梭罗认为改变这种错误的生活态度的方法就是“简朴、简朴、再简朴”。
《道德经》提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认为这些外在的形形色色的东西给人们带来强烈的物欲感,容易使人沉溺其中。在老子眼中,圣人但求温饱和安定,摒弃物欲带来的冲击而保持知足的生活。因为圣人明白,过分追求感官刺激与享乐,会影响人的身心健康,甚至会让其沉溺其中而无法自拔,丧失原本的自我。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宁静、祥和的精神家园一旦被这样的生活方式所吞噬,就会完全堕落为一种受官能欲望所摆布的存在,也就失去了生活的内在价值。为了给人们指明生活的方向,老子倡导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明确了人的生命本相及人性之本然,人所应当确立的适当精神向度,自然也就昭然若揭了,那就是老子所说的‘见素抱朴’,返朴归真。”[1]道家思想的另一位大家庄子也认为清淡简朴的生活是人生的理想。“夫恬淡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庄子·刻意》)。可以看出,庄子觉得追求恬淡宁静的生活才能使人摆脱物质诱惑的困扰,从而达到内心的平静。不仅是圣人应该抵御外物的困扰,对国家的管理者来说,排斥纯物质追求也一样重要。庄子有云“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庄子·让王》),即“大凡是圣人的一举一动,必定要明察自己所向往和自己所做的是什么。”[2]因为统治者的行为,不仅代表其个人意志,也会影响到百姓生活。如果国家统治者沉迷于对奢侈品的追求、对物质的占有,那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变得人欲横流。
梭罗也倡导一种简单质朴的生活。在他所生活的年代,美国西部领土的开发呈现出良好的势头,发展前景一片光明,许多人通过自身努力实现了“美国梦”。 “原先受到种种束缚的平民百姓不仅迅速扩大了参政权,而且理直气壮地在争取经济上的平等和发达,这种社会能量的释放无疑极为惊人。”[3]随着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目光早已不仅仅局限在基本的生活用品层面,而是去追求更加华丽和奢贵的东西。美国社会也由原本简朴、注重道德的农业社会过渡到强调商业利润、追求奢侈的消费型社会。社会贫富分化迅速加剧,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也不择手段,一时间“美国梦”褪变成了“发财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梭罗冷静地提出了简朴生活的目标。梭罗觉得这些奢侈品和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反而会阻碍人类的进步,因为过度追求与占有物质财富会使人们的生活朝着单一的目标迈进,他们有忙不完的活,却不能采集生命的美果,除了做一架机器外,没时间来完成更有价值的目标。“我们看不到人类休息片刻,除了工作,工作,工作,就什么也没有了。”[4]在对待金钱方面,梭罗视钱财为自己生活中极为轻微的一部分,没有迎合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去尽可能获取财富,而是选择一年只工作六个星期,只要能应付自己的开销便足矣。简朴清淡的生活是梭罗自由选择的结果,也是他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梭罗在瓦尔登湖边搭起了一座木制小屋,自己种植土豆、玉米、豌豆等简单的作物,安静地生活着。他独居湖畔,并不是要过隐士的生活,而是有目的地探索人生、阐述人生的规律。他的生活是简朴的,可他的精神是富有的。他告别了城市的喧嚣,摆脱了金钱的束缚,内心更加宁静与充实,与生态自然融为一体,享受着大自然赐予的快乐。这正是一种与道家相似的返朴归真的生活态度。
19世纪上半期的美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机会与黄金并存的地方,对美元的占有量决定了一个人的成败。在财富向心力的吸引下,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到追逐利益的洪流中。可是,没有保持人身自由、不被外物束缚的精神动力,缺乏追求高质量、高层次生活的奋斗目标,人们只能终日惶惶不安,迷失在自己制造的种种需求中,在物质的罗网里苦苦挣扎。所以,梭罗才会觉得“不懂如何利用它,也不懂如何摆脱它,因此他们给自己铸造了一副金银的镣铐。”[5]14因此,梭罗对现实生活持一种批判态度。回归绿色生态自然,成了他毫不犹豫地选移居湖边生活的动因。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物质财富空前繁荣,世俗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这样的外部条件远胜过当时的美国。梭罗的思想在当今受到极大的重视,因为他提供给我们一种不同的声音,让人们保持清醒的大脑,它时刻在提醒着我们:我们是生活的主人,我们自己去决定生活而不是物质在主宰我们,人要保持精神上的独立,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而不知所措,“一个人越是有许多事情能够放得下,他越是富有。”[5]77
二、对爱默生自然观的超越
超验主义哲学家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既是梭罗的老师,也是梭罗要好的朋友,他的自然观深深地影响着梭罗。梭罗是爱默生哲学身体力行的实践者,甚至在一些方面超越了爱默生的自然哲学观,彰显出一种浪漫主义的生态思想。
爱默生是超验主义哲学的旗手,认为世界的本源是精神性的。自然是人类普遍精神存在的产物,自然的存在是同人的灵魂的存在结合在一起的。自然界是一种高度抽象的东西,是人与上帝进行交流的中介物。用他的话说,“每一个自然事实都是某种精神事实的象征。自然中的每个现象都和某种心灵状态相对应,而这种心灵状态只有把自然现象当成自己的画像时才能被描述”。[6]20因而,自然存在的意义必须从它和人的精神联系上去理解。在爱默生那里,人是通过灵魂与自然界和谐一致的,只有接近自然、感受自然,人的灵魂才得以体现出来,同时,自然也才能显示出它的价值。“世界只是为了满足灵魂渴望才存在的,我称这种要素为终极目的。”[7]可以看出,爱默生视自然为一种虚幻、非实在的东西。
如果说爱默生是一位书斋式的学者,那么梭罗则是生活在自然中的思索者。梭罗所发现的自然是清晰、实在、具体的,它本身就是自己存在的目的和理由,而非被升华的精神上的东西。在他的笔下,有生命的东西都是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个体,是人能看得见、感受得到的。“一个湖是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天性的深浅。湖所产生的湖边的树木是睫毛一样的镶边,而四周森林蓊郁的群山和山崖是它的浓密突出的眉毛。”[5]174在他的笔下,瓦尔登湖及其周边的景物相互协调,构成了一副和谐、生动的画卷。
其次,爱默生的自然观是以“人”为中心的,高度突出了人的自然主体地位。“人被置于存在的中心,从其他每一样事物中发出的启示之光都照向他。若无这些事物,就不能理解人;同样,若无人也无法理解事物。”[6]21爱默生把人居于生态系统的首要位置的价值观,显示出大自然构成要素的不平等地位。“大自然完全是中介物。它天生是为人服务的。它接受人的主宰,驯服得像一头任由救世主跨骑的毛驴。它向人提供它所有的财富,以便它把这些原料改造成有益的东西。”[8]爱默生把自然看作一种实用性的工具, “我们可以把自然作为方便的标准来利用,作为我们升降的标尺。”[9]他的这种自然观符合当时人们为了发展经济而对自然无限扩张的欲望,本质上是一种非生态的世界观。
梭罗则不同,他是以万物地位平等来对待自然的,认为人只不过是大自然中的一份子,人与自然界中的生物群共同构建和组成了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梭罗首先追求的是,他看到的(如果还谈不上完全发现的话)一个不同于人类而且比人类大得多,同时又通过类比在道德上和人类相连的自然——是一种比感情上的支持更具有深义的‘同源物’。[10]他把大自然比作“人类的母亲”,一切动植物的生命都寄生在这个地球上,都是大地的孩子。他看到蚂蚁间的战争时心痛不已,因为他把微小的动物也当成了家庭中不可缺少的成员,蚂蚁是他的朋友;他也不能原谅自己为了收获栗子而用石头掷树,因为树是他的远亲,人毁坏树是没有道德可言的。自然是神圣的,人属于自然。“他反对将人从自然界中超拔出来,用贬低或充满敌意的眼光来看待自然,认为人类真正所需要的不是这种对待自然界的贵族般的傲慢,而是谦卑、平等地对待自然物的道德感。”[11]他愿意把时间交给大自然,在其中他能享受到最大的乐趣。
三、保护自然环境,平衡生态结构
梭罗的生态思想维度还体现在对生态环境的关怀上。19世纪前期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开展工业革命的时期,美国也不例外。随着人类掌握越来越多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对自然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逐渐由对大自然的敬畏、依赖发展到对自然的扩张与征服。这种转变促使生态价值观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成为主导思想。可以说,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我们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给自然环境造成无情的伤害。梭罗创作《瓦尔登湖》的年代,也是美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和西部领土扩张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在“工业文明”的刺激下,为了进行铁路建设,需要从自然界不断地索取原材料,而瓦尔登湖边生长的优质树木便成为被砍伐的对象。1844年铺设的康科德至费茨堡(Fitchburg)的铁路经过瓦尔登湖的西面,造成康科德地区的森林植被遭到大量砍伐,瓦尔登湖附近的生态系统遭到了人类无情的破坏,自然的景色逐渐失去它自身的美丽。梭罗看到这一切时感到悲伤,发出哀叹:“我第一次划船在瓦尔登湖上的时候,它四周完全给浓密而高大的松树和橡树围起……可是,自从我离开这湖岸之后,砍伐木材的人竟大砍大伐起来了。从此要有许多年不可能在林间的甬道上徜徉了,不可能从这样的森林中偶见湖水了。我的缪斯女神如果沉默了,她是情有可原的。森林已被砍伐,怎能希望鸣禽歌唱?”[5]179
梭罗认为,自然是个人保持精神独立性的避难所,是个人灵性生命的源泉。他把人类对自然的破坏等同于社会对生态成员的扼杀,是物质主义对自然的美感、诗意和灵性的破坏。人们在享受物质上的满足时,对生态环境关心不足。科学同样是人类认识自然的重要手段,科学的进步丰富了人们的知识,而科学一旦超出了适度的界限,就会成为破坏生态平衡的工具。梭罗起初并不反对进行科学研究,赞成把自然界的动植物当作研究对象。他自己也有一把猎枪,并且亲自参与对飞鸟的捕杀。在发现这样的方式会破坏生态平衡后,他便反对以科学研究的名义杀死其他生物。“科学是无人性的。我们在使用这些窥视工具的同时,也扰乱了大自然的平衡与和谐”。[12]在梭罗看来,各种生物的地位是平等的。他反对随便杀死任何动物,因为动物跟人一样有生存的权利。在对生命的渴望上,所有生物都相同,“兔子到了末路,呼喊得真像一个小孩。”[5]199人类和动物在地位上没有高低之分。
当时的美国人,正欢喜于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也憧憬着工业文明带来无限美好的前景。唯有梭罗,作为自然家庭中的一员,很早就开始思索工业文明与自然生态环境间的关系。梭罗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哲人的眼光看到了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梭罗不反对工业化,只是觉得人类在创造了一种文明的同时,也在伤害另一种文明。怎样在发展工业经济的过程中保障生态环境的安全,是需要引起人们重视的。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复杂多变的。在农耕时代,人类畏惧自然。到了工业时代,人们在理性科学知识的引导下,开始认清大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前进,人类以强大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化大生产为武器开始征服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甚至于把人和自然完全对立起来。在大多数人得意忘形之时,梭罗却在思考、反思。“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我们会发现一种重要的浪漫派对待地球的立场和感情,同时也是一种日渐复杂和成熟的生态哲学。我们也会在梭罗那里发现一个卓越的、对现代生态运动的颠覆性实践主义具有精神和先导作用的来源。”[13]梭罗重新树立了生态伦理思想,强调了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类的母亲,生态系统内各个有机元素都是平等的,人类只有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才能在自然的关照下健康合理地发展,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梭罗的生态价值观在当时是进步的,在当今仍是我们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一种参考模式。当前,回归自然、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绿色GDP已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在这种生态道德观的引领下,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不是自然界的主宰者,人与自然应维持一种和谐的状态。因此,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梭罗的生态思想在当下显得十分重要。评论界认为,“梭罗最先启蒙了美国人感知大地的思想。《瓦尔登湖》被誉为是现代社会的“绿色圣经”,梭罗则被称为是‘绿色圣徒’,成了美国文化的偶像。”[14]
梭罗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不仅属于美国,更属于全世界。他的绿色生态思想,与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观是一致的,这无疑对我们的实践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李远国,陈云,衣养万物:道家与道教生态文化论[M].四川:巴蜀书社,2009:288.
[2]杨柳桥.庄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85.
[3]钱满素.美国文明散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88.
[4]Henry David Thoreau, Life Without Principle, Great Shorts Works of Henry David Thoreau, edit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endell Glick[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2:360.
[5]亨利· 大卫· 梭罗.瓦尔登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6]Ralph Waldo Emerson: Essay & Lectures[M]. 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3.
[7]爱默生.美国的文明[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2.
[8]爱默生.自然沉思录[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32.
[9] R·W·爱默生.美国学者:爱默生讲演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86.
[10]罗伯特·米尔德.重塑梭罗[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149.
[11]李培超.伦理拓展主义的颠覆:西方环境伦理思潮研究[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2 .
[12] 梭罗.梭罗日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201.
[13]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81-82.
[14]Lawrence Buell, 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 Literatur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U.S. and Beyond[M].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7.
[作者简介]李韶星(1986- ),男,博士研究生,从事生态环境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602(2016)01-0013-04
[收稿日期]2015-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