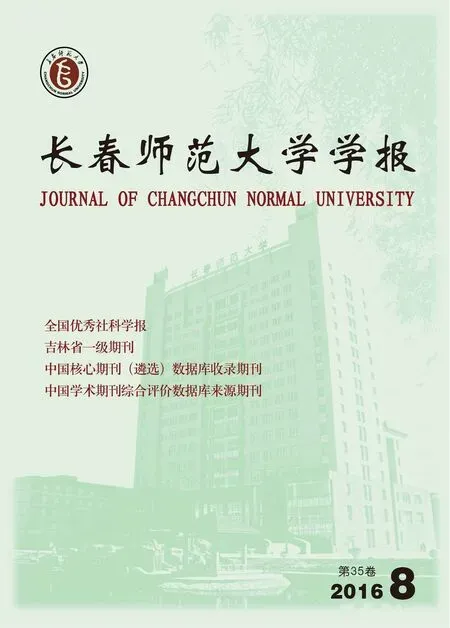中国武术特有思维型构的探讨
张 蕾
(吉林体育学院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学院,吉林长春 130022)
中国武术特有思维型构的探讨
张 蕾
(吉林体育学院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学院,吉林长春 130022)
武术,是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武术的境界在于制止杀戮和暴力,而不是杀戮和暴力。在“和”文化型构的影响下,武术体现了虚与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武亦有七德: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武学的本质在于止息杀戮和暴力而非暴力和杀戮。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要部分,已然承载起推广传播中国文化精神的重任。
中国武术;传统文化;思维型构;探讨研究
武术是中国民族的文化瑰宝,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很多武术派别和武术招式,不同的武术类别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与艺术之美。可以说,武术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招式和动作本身就是一种蕴含美的艺术形式,具有无限的美学意蕴和哲学思辨。从艺术本身发展的情况看,艺术的形式和内容不是二元对立的,它们是相互作用的,任何形式都是有意味的形式,背后拥有一定的艺术蕴藉,展现给我们更为深刻的美学思考,而内容也有赖于形式的有意味表达,才能以完美的视觉效果进行艺术和审美的有效传递,进而实现艺术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辩证互动。
1 武术是“道”“德”文化意蕴的形态呈现
武术,作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源远流长,“武”字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解释为“从止从戈”,从字面的意思上来看,是放下武器、停止战争的意思。这表明在中国武术的产生并不是为了凭借一技之长和动作优势争强好胜,逞一时之英雄,而是强调武术有平息干戈、保家安民的重要作用。在《左传》一书则详细地解释了“武有七德”之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1]这里更加强调武术不是一种暴力的呈现,它自身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对“德行”和“品行”的实践与坚守。安民、合众及丰财也是从更高的道德层面上指出了武术虽然作为一种连贯动作的动作展示,其自身也承载着“国家大事,在戎在祀”的现实使命,也包含着建立在自我防卫基础上通过武术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重要方式。武术的本源和武德之说奠定了中国武术在动作美学之外更深广的道德品格和文化品格,武术不仅是个人性的突出武术修为和内心修行的活动,同时也是国家理想的实现方式,这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和传承性。在此基础上,武术不仅是为了自立和自保的方式,还具有了更多重要的作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兵家占据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孙子兵法》中的“知人知彼,百战不殆”、“致人而不致于人”、“以正合,以奇胜”等等讲述了很多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内蕴的武学思想。而在墨家所提倡的“兼爱”“非攻”的思想中也包含着武术中的“侠”“义”观念,强调用武术来息止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进而实现仁义的普及和推广。可以说中国早期的武术思想从产生之初就确定了武术的基本内涵和社会追求,这也为武术在后世的发展打下来良好的基础。在《太平广记》中专有一“侠义卷”,讲述那些为人鸣不平、为社会求正义的侠义之事,他们通常武功高强,具有侠义心肠,秉承着儒家的进取精神实现匡正时弊、锄强扶弱的社会理想。在《聂隐娘》中讲述隐娘武功高强:“一年后,刺猿狖,百无一失。后刺虎豹,皆决其首而归。三年后能飞,使刺鹰隼,无不中。剑之刃渐减五寸。飞禽遇之,不知其来也。”[2]但是,隐娘秉持着侠道精神,在其师傅的命令下,锄强扶弱,劫富济贫,“某大僚有罪,无故害人若干。”聂隐娘半夜入室,决定斩其头颅,“又携匕首入室,度其门隙,无有障碍,伏之梁上。至瞑,持得其首而归。”动作之干净利落,不禁令人惊叹其武功之高强,也更让人们感受到透过武术这个动作媒介,感受到中国武术的人性关照与社会关怀。类似的武术作品《红线传》《虬髯客传》等也同样被收录在《太平广记》之中,武学功夫与侠义思想相结合塑造出了一位又一位武功高强而又品行高尚的侠客形象。
中国的武术博大精深,但并非是逞凶斗狠,而是和“道”相结合,不论是《说文解字》中的“止息战争,放下武器”,还是《左传》中的“武有七德”,及至后期的传奇小说中的狭义故事,武术向来都不是暴力的代名词,相反它是用来治暴的,而且与中国的儒道学问相结合,中国的武术不仅拥有其精神内蕴,也拥有着无限的美感,通常是飞檐走壁、身轻如燕的,杜甫在《送蔡都尉诗》中赋道:“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中国人对“武术”有着特殊的情怀,除了传奇诗歌之外,亦然有很多话本小说等诸如此类的文本讲述着中国武学的精华,无论是《三国演义》中关云长的“我于千枪万刃之中,矢石交攻之即,匹马纵横,如入无人之境,岂惧江东群鼠乎!”还是《水浒传》中武松的“一双眼光射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胸脯横阔,有万夫难敌之威风;语话轩昂,吐千丈凌云之志气。心雄胆大,似撼天狮子下云端;骨健筋强,如摇地貔貅临座上。如同天上降魔主,真是人间太岁神。”都令人对中国的武术精神心生崇敬之情,到了现当代文学时期,港台文学异军突起,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作家将中国的武侠与奇幻想象文学结合,其后武术美学又越出其文本之外,进入了光影的世界,从《功夫熊猫》《功夫》《卧虎藏龙》进入西方人的视野,到中国留学生程腾创作的一部中国武侠动画片——《天外有天》(Higer Sky),初出茅庐便一举斩获第41届美国学生奥斯卡银奖,中国的武术作为载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要部分,已然承载起推广传播中国文化精神的重任。
2 武术是二元哲学辩证思想的的真实反映
中国武术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包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哲学思想,通过哲学上的互动关系,既实现了武术理论和招数的丰富与多变,也使武术的哲学与审美内涵变得更加多样化。在中国传统的武术派别中都广泛地使用了阴阳辩证理论,即“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动与静、虚与实、进与退、攻与受等对应概念。这些对应关系在确立和转化中实现了不同要素之间的重组,使中国武术呈现出张弛有度、攻守兼备的特性。比如在太极拳理论中指出“开合虚实即为拳经”“一开一合,有变有常,虚实兼到,忽现忽藏”“一动一静,是尽拳中之妙”等武术与哲学理论。而在《太极拳论》中则更为明确地指出“阴不离阳,阳不离阴;阴阳相济,方为懂劲”。这些哲学思想的融入和动作实践,使中国武术不仅是动作上的攻守转换,同时也是学习哲学提高内心修为的过程。从更大的层面看,当个人的武术动作与哲学内涵上升为两军的军事对弈之时,这种武学的“虚”与“实”辨证观念便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与实践。《孙子兵法·虚实篇》中为我们讲述了武学灵活变通的思想,“虚”与“实”两个武学观念并非是能脱离开一方而独立存在的,它们是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开宗明义,善于打仗的人往往是善于计谋的,他们总是会驱使敌人跑来跑去优先占据主动地位。“虚”在《孙子兵法》中通常指的是“破绽、劣势”,而“实”则与之相反,通常是“优势、有利”,“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进攻时敌人是无法防御的,那是因为攻击了敌人最薄弱的环节。于此同时,“虚”与“实”是矛盾对立互相依存的,“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3]其中,“形人”与“无形”、“专”与“分”、“一”与“十”、“众”与“寡”分别都是“实”与“虚”这两个哲学观念的变体,当敌人的兵力分散而数寡的时候,我方的兵力呈现出集中而众多的形势,此消彼长。这样的趋势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虚”与“实”之间是相互转化的,此时之“虚”很有可能就会转变成彼时之“实”,就像“天外有天”一样,没有人会永远处于优势而常胜不败,“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故五形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五形和四季之间还是轮番更替,白天的时间有长有短,月亮有盈有亏,兵家的形势和人的胜负自然也是常常发生变化的。从《孙子兵法·虚实篇》中的用兵御人之道,便让我们能明确中华武学思想中辩证法运用的精妙之处,这和《周易》中的太极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4]。中国武学乃至哲学中的辩证法不同于西方,西方的辨证法多是强调矛盾对立,而中国古人从《周易》开始的辨证思想更多的是强调二元之间的对立和转化,注重根据形势的变化随时调整战略措施,善于变通,灵活应对才是常胜之法。
3 武术是以“和”为主导的思维理路
中华武术博大精深,作为东方传统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它其中蕴含着深层的理路。中国人的武术思维可以说是一种以“和”为主导的思维方式,它和西方的骑士精神、日本的武士道有着根本上的差异,西方的骑士精神是伴随着忠君、护教、行侠目标之下勇猛与荣耀的彰显,日本的武士道讲求“名、忠、勇、义、礼、诚、克、仁”,这些品质被日本的武士看成是作为一位武士应有的基本美德,这些美德亦是荣誉的载体,丧失了荣誉便是丢失了灵魂。日本的武士和西方的骑士将荣誉看得至高无上,为了追逐荣耀而展现其风度和美德,而中华的武术更看重的是“和”的精神,“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切磋武艺的时候更多是人心境界上的比拼和切磋,《叶问》中叶师傅和廖师傅之间的惺惺相惜和相互尊重便是“和”精神最好的体现,两个人切磋比试是本着“赐教、受益”的心态,而并非是“打斗、输赢”,廖师傅一句:“多些赐教,获益良多。”叶师傅回一句:“彼此,彼此。”玉树临风、高风亮节的君子武者形象跃然纸上,当比试结束之时,还不忘叮嘱一句:“慢走。”儒雅的风度气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正是中国武者所追寻的,叶问在和日本军官打斗的场景,他选择收手而不置对方于死地,甚至不愿将其变成残废之人,都是中国武术“和”之精神的展现。事实上,在中国武术形成和发展的思维理论和武术人格潜在的建立中,武术的境界在于制止杀戮和暴力,而不是杀戮和暴力。在“和”文化型构的影响下,中国的武术呈现出了独特的美学意蕴,这是一种高层次上的境界之美,这与中国古典哲学中讲求“天人合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5]。要与大自然融合为一体,顺势利导,根据自然的法则而行武,刚柔并济,动静相宜,虚实相生,最终彰显自己高昂的气度和情操,不以胜负输赢定宗师,即武学的宗师首先要是人学上的宗师,参悟人道方能参悟武道,进而以高尚的道德情操为家国天下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4 结语
武术不仅是建立在招式上的动作美学,同时也在其自身的产生和发展中包含着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朴素的哲学辩证法思想。在中国武术学习和实践的思维理路中强调内心良好的道德修为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是武术实践与发展的先决条件与精神内核,在这样的思想与精神的指导下实现武术安民、安天下的的社会责任,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武术与人格境界,这实际上与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思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也使中国武术在形成和几千年的发展中成为建立在动作美学基础上的艺术之美的生命呈现,成为武术习练者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方式,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和社会价值。
[1]何福仁.历史的际会─先秦史传散文新读[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36.
[2]李剑国.唐宋传奇品读辞典[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899.
[3]张岱年.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132.
[4]孙成岩.论传统哲学对中华武术发展的影响[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8(5):79.
[5]王岗,郭海洲.传统武术文化在武术现代化中的价值取向[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6(3):53.

2016-05-07
张 蕾(1983- ),男,讲师,硕士,从事民族传统体育研究。
G852
A
2095-7602(2016)08-008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