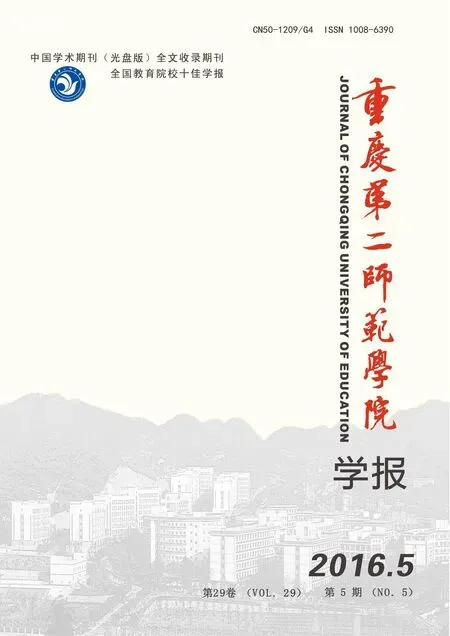苏轼号“东坡”与白居易之关联
贾 琪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苏轼号“东坡”与白居易之关联
贾琪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苏轼经历“乌台诗案”后被贬至黄州,始自号“东坡居士”。“东坡”的来历当可追溯至白居易忠州种花种树之东坡。由苏轼诗集可知,苏轼第二次出蜀时走水路沿长江而下,经过忠州,并在忠州停留。考察苏轼“东坡”之号,与白居易忠州之东坡有关。此外,苏轼倾慕白居易,自认其在人生经历及出处方面与白居易有诸多相似,且在诗风、人格、处世等方面都向白居易学习,故苏轼取号“东坡”是对白居易的一种仰慕和趋步。
苏轼;白居易;东坡;忠州
一、苏轼滞留忠州的确凿证据
白居易在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由江州司马迁忠州刺史,次年春到忠州任。在任职忠州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勤政爱民,种花种树,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是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白居易在忠州东坡种树种花,并在诗中多次提到东坡。其《东坡种花》二首云:“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而东坡栽花种树之后,一派繁花似锦的景象,引得蜂蝶、鸟儿满山坡:“红者霞艳艳,白者雪皑皑。游蜂遂不去,好鸟亦栖来。”诗人在闲暇之余,闲步东坡,甚至整日待在东坡,沉醉于东坡的美景而不忍离去:“花枝荫我头,花蕊落我怀。独酌复独咏,不觉月平西。巴俗不爱花,竟春无人来,唯此醉太守,尽日不能回。”由此可见,白居易对在忠州开辟出来的东坡甚是钟爱。其在忠州任满,将要离开时,又满怀深情地写下《别种东坡花树》两绝句:
二年留滞在江城,草树禽鱼虫有情。
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
花林好住莫憔悴,春至但知依旧春。
楼上明年新太守,不妨还是爱花人。
诗人就要离开忠州,离开他念念不忘的东坡,但仍寄望于将来的新任太守,希望他也是一位喜爱花草,勤政爱民的接班人。甚至诗人在返回京城就任新职之后,仍然挂念着东坡上的那些花草树木,写有《西省对花,忆忠州东坡新花树,因寄题东楼》,表达对东坡的无限怀念:
每看阙下丹青树,不忘天边锦绣林。
西掖垣中今日眼,南宾楼上去年心。
花含春意无分别,物感人情有浅深。
最忆东坡红烂漫,野桃山杏水林檎。
诗人虽已经在长安,远离忠州,可是却心系忠州,尤其怀念忠州东坡上自己栽种的花草树木。诗人在临别忠州之际,寄希望于未来的忠州长官,希望他们能延续种花植树的习惯。现在的重庆忠县环境优美,树木繁茂,盛产柑橘、荔枝,这都得益于当年任忠州刺史的白居易带领州民种花种树之举。
忠州位于长江上游地区,长江自西向东横穿而过,苏轼与忠州亦颇有渊源。苏轼与其弟苏辙在第二次随父苏洵出蜀时,坐船走水路,忠州乃必经之地。笔者梳理苏轼诗集,可知其出蜀路线大概为:嘉州(《初发嘉州》)——犍为(《犍为王氏书楼》)——戎州(《戎州》)——渝州(《渝州寄王道矩》)——入峡——涪州(《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韵》)——丰都(《仙都山鹿》)——忠州(《屈原塔》)——夔州(《永安宫》)——武宁县(《过木枥观》)——巫山(《巫山》)——出峡。由此路线可看出苏轼出蜀经过忠州,并在忠州停留过,有诗《严颜碑》《屈原塔》《竹枝歌》为证。在《严颜碑》下苏轼自注:在忠州。而《屈原塔》尤其值得注意,它提供了苏轼滞留忠州的重要证据。全诗如下:
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
精魂飘何处,父老空哽咽。
至今沧江上,投饭救饥渴。
遗风成竞渡,哀叫楚山裂。
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
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决。
南宾旧属楚,山上有遗塔。
应是奉佛人,恐子就沦灭。
此事虽无凭,此意固已切。
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
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
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
此诗有苏轼自注:“在忠州。原不当有碑塔于此,意者后人追思,故为作之。”[1]24这一自注颇有说服力,如果苏轼只是指出屈原塔在忠州,而不是说明他自己到过忠州,那么下文应当写成“原不当有碑塔于彼(那里)”,不用“彼”而用“此(这里)”,恰恰表明苏轼亲到忠州屈原塔凭吊。因为指示代词“此”是近指,只有人在附近,才可用“此”。指示代词“彼”是远指,人不在附近,就应用“彼”。此外,《屈原塔》中有:“南宾旧属楚,山上有遗塔。应是奉佛人,恐子就沦灭。”关于“南宾”,王注子仁曰:“南宾,古之巴子国也。查注:《太平寰宇记》:山南东道忠州南宾郡,理临江县。梁大同六年,立临江郡,后魏改临州。唐武德二年,分武宁置南宾县,属临州。天宝元年改南宾(县)郡。乾元元年复为忠州。忠州即南宾也。”[1]24-25忠州本来不应有屈原碑塔,与苏轼同行的苏辙也有《屈原塔》一诗:“屈原遗宅秭归山,南宾古者巴子国。山中遗塔知几年,过者迟疑不能识。”[2]5表达了同样的疑惑。从这些描写来看,苏轼、苏辙若非亲到忠州,在信息远不如今天发达的时代,不可能知道深山之中还有屈原塔,更不可能如此亲近、历历在目地描写“山上有遗塔”、“山中遗塔知几年”。这首《屈原塔》显然可以作为苏轼亲到忠州的铁证。
可见,苏轼乘船经过忠州,曾在忠州停留,在此凭吊屈原和三国时的严颜,并创作了《竹枝歌》一篇九章。苏轼此时尚无诗篇涉及白居易,笔者认为,苏轼出蜀,刚二十岁,是满怀雄心壮志去京城一展抱负的。他沿途经过诸多名胜古迹,观其时之诗,大多为写景或怀古之作。当时的忠州可能还没有专门纪念白居易的祠堂或碑石,直到明崇祯三年,忠州知州马易从因敬重白居易,为之建立祠堂,即现今忠县白公祠。但是苏轼自“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始自号“东坡”,则与白居易有关。苏轼黄州之贬,与白居易在忠州刺史任时的年龄、心态、经历等方面有诸多相似,值得考究。
二、苏轼之号“东坡”与白居易忠州之“东坡”
苏轼“东坡”之来历,宋人已有论述。周必大《二老堂诗话》有“东坡立名”条云:“白乐天为忠州刺史,有《东坡种花》二诗,又有《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著,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3]2-3周必大在此明确指出,苏轼敬爱乐天,并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与乐天相似,其“东坡”之号,必起于白居易忠州之作。此外,洪迈《容斋三笔·东坡慕乐天》亦云:“苏公谪居黄州,始自称东坡居士。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白公有《东坡种花》二诗云:‘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又有《别东坡花树》诗云:‘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皆为忠州刺史时所作也。苏公在黄,正与白公忠州相似。……则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东坡之名偶尔暗合也。”[4]575由此来看,宋人已普遍认同苏轼“东坡”与白居易在忠州东坡种花的关联。
苏轼自比白居易,对其多有仰慕,而苏轼之号“东坡”,则自黄州始,联系白居易任忠州刺史之背景,与苏轼谪居黄州之背景,刚好吻合。苏轼谪居黄州,正与白居易在忠州相似。白居易因宰相武元衡遇刺,上表请求皇帝缉查真凶,而被认为越级言事;又因其所做诗中有“赏花”、“新井”字眼与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暗合,遭人诽谤,即所谓“新井诗案”,而被贬江州司马。在江州司马任上三年,升任忠州刺史,表面上看是升迁,实际上是明升暗贬,因为忠州比起江州,离京城长安更远了,且忠州地处西南僻壤,交通闭塞,远远比不上京都地区。白居易在忠州任上虽也竭力为百姓做事,但心态已有了转变。可以说,在忠州之东坡种花种树即是其心态转变的体现。这从白居易还朝后,其政治热情已不如前期那么高涨,亦可看出其心态变化。此时的白居易开始把眼光更多地转向自然,转向“独善其身”的道路,其《中隐》诗便体现了诗人在历经官场沉浮后的心态选择。
黄州对于苏轼亦是一大转折。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到了黄州,本是戴罪之人,虽有官职,但俸禄微薄,难以维持生活。苏轼《东坡八首》其序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1]1039王宗稷编《苏文忠公年谱》亦云:元丰五年壬午“先生年四十七,在黄州寓居临皋亭,就东坡筑雪堂,自号东坡居士”[1]2542。可见苏轼并不是一到黄州,就自号“东坡”的,而是居黄州两年后才有了“东坡”之号。我们可以据此分析一下苏轼在黄州时的心态。乌台诗案之前的苏轼,书生意气,满怀自信,有兼济天下的志向。其在熙宁七年(1074年)写给苏辙的词中回忆兄弟二人初到长安时的豪情万丈:“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然而经乌台诗案贬黄州之后,诗人躬耕于东坡,心灵境界有所改变,其《赤壁赋》云:“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说明诗人在经历生死劫难之后,对官场、生活已有所了悟,心灵的天平已更多地转向自然之趣味。又黄州时所作《临江仙·夜归临皋》亦云:“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经历过“乌台诗案”之生死劫难后的苏轼,居黄州时已萌生归隐之意,更向往心灵无拘无束之所在了。故白居易之忠州是其仕途上、心路上的一个转折,苏轼之黄州亦是其心灵上一大转折。
对与苏轼居黄州与白居易居忠州的相似境况,白居易种花种草之忠州“东坡”与苏轼躬耕之黄州“东坡”,以及苏轼从此自号“东坡居士”的内在关联,前人多有述及。苏轼认为自己在黄州时的境遇、心情同当年白居易在忠州颇为相似,多次以乐天自比,“独敬爱乐天”,肯定会研读白居易的诗文,并且对其诗甚是熟悉。苏轼第二次出蜀在忠州没有写关于白居易的诗文,但黄州时期的苏轼在遭遇和心境方面都与他一直敬慕的乐天极为相似,这时他靠朋友的帮助有了自己可以耕种的土地,可以种树种花种粮食,还可以筑屋(东坡雪堂),自然而然就想到了白居易在忠州种树种花之东坡。又苏轼获罪被贬黄州,其心情和白居易忠州之任是一样的。白居易在《自江州司马授忠州刺史,仰荷圣泽,聊书鄙诚》一诗中云:“遗簪存旧念,剖竹授新官。乡觉前程近,心随外事宽。生还应有分,西笑问长安。”白居易自江州司马改任忠州刺史,虽然忠州处西南蛮荒之地,但对白居易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他为朝廷还没有忘记自己而高兴,“乡觉前程近”,“西笑问长安”,诗人觉得忠州之任,朝廷还记挂着他,回长安也很有希望了。事实果然如诗人所期盼的,忠州任满,“元和十五年(820年)夏,白居易被召还长安,除尚书司门员外郎;长庆元年(821年)任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长庆二年(822年)为中书舍人;长庆三年(823年)请求外放,任杭州刺史。”[5]110-140白居易晚年仕途顺畅,忠州之任成为其仕途的转折。而苏轼贬黄州,与忠州时的白居易有相同的期许。“乌台诗案”使苏轼九死一生,他觉得朝廷没有对他判处死刑,而是贬谪黄州,说明朝廷并没有要置他于死地的意思,苏轼希望自己也能像白居易忠州之任一样,迎来人生仕途的转机。后来苏轼果然在仕途上有新的转机,黄州之贬后,哲宗元祐元年,除中书舍人;元祐二年至四年,任翰林学士;元祐五年,请求外任,知杭州。因此,居黄州两年后,苏轼有意效仿白居易忠州种花种树之东坡,也在黄州城外开辟数十亩荒地,躬耕于此,并以“东坡”为号,当是其对白居易在忠州东坡垦地种花的一种仰慕和趋步。苏轼自号“东坡”,后还有“居士”二字,在“定似香山老居士”下王注师曰:“香山寺在洛都龙门,白乐天晚年自称香山居士,以儒教饰其身,佛教治其心,道教养其寿。”[1]1425苏轼既然认为自己与白居易有诸多相似,也有意学习白居易之处世态度;苏轼一生纵横于诗词文,出入于儒释道,随缘自适,比白居易更为旷达。因此,苏轼之号“东坡”,与在黄州时心态之转变和倾慕白居易有极大关系。
那么,苏轼之号“东坡”,除了与白居易忠州种花之“东坡”相关联外,还与白居易有无其他方面的联系呢?笔者认为,苏轼自号“东坡”,不仅受白居易忠州东坡种树种花的启发,更与二人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相关联。苏轼的人生经历与白居易相似,似乐天而东坡;做诗效法白居易,效乐天而东坡;在人格、处世方面敬慕白居易,慕乐天而东坡。
三、苏轼之人生经历——似乐天而“东坡”
苏轼认为自己与白居易人生际遇有诸多相似,常常在诗词中以乐天自比。如《赠写真李道士》云:“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赠善相程杰》云:“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去杭州》云:“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序曰:“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苏轼认为自己与白居易有诸多相似,主要体现在仕宦经历的相似。苏轼在元祐二年(1087年)所写诗《轼以去岁春夏,侍立迩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继入侍。次韵绝句四首,各述所怀》中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而苏轼自注曰:“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某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似,庶几复享此翁晚节闲适之乐焉。”[1]1425此时苏轼已还朝任翰林学士,大约由自己的仕宦经历而联想起白居易,觉得自己与白居易经历极为相似。
此外,白居易和苏轼都曾任职杭州,亦有诸多相似。苏轼赞赏白居易任职苏杭的经历,在离开杭州之时作《次韵答黄安中兼简林子中》云:“老去心灰不复燃,一麾江海意方坚。哪堪黄散付子度,空羡苏杭养乐天。”[1]1674这是苏轼第二次任职杭州,将要离开,对杭州留恋至深,对白居易在杭州留下的美名钦羡不已。白居易在苏州任上为便利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现在“七里山塘”已成为苏州著名一景;白居易任职杭州刺史时对整治西湖颇为在意,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使老百姓大受其益,他在行将离开杭州时所作《别州民》诗写道:
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
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
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
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在离开之际,诗人犹记挂西湖,希望经过治理后的西湖能造福百姓。苏轼有文章专门记录六井,且提到白居易在杭州治湖浚井的功劳。《钱塘六井记》云:
潮水避钱塘而东击西陵,所从来远矣。沮洳斥卤,化为桑麻之区,而乃久为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陆,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恶,惟负山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广。唐宰相李公长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后刺史白公乐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赖之。……熙宁五年秋,太守陈公述古始至,问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给于水,南井沟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应。”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圭办其事。……明年春,六井毕修,而岁适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罂缶贮水相饷如酒醴。而钱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龙山,北至长河盐官海上,皆以饮牛马,给沐浴。方是时,汲者皆诵佛以祝公。余以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井竭,非岁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故详其语以告后之人,使虽至于久远废坏而犹有考也。[6]379-380
白居易任职杭州,治湖浚井,并有石刻记录此事。陈述古任杭州太守时亦派人修缮六井,且在大旱之年保证了杭州百姓的用水。苏轼对白居易和陈述古两位太守在杭州疏浚六井的举措深表赞赏,其任杭州太守时,亦疏浚西湖河道,建有苏堤,“苏堤春晓”已成西湖十景之首;苏轼守杭州时正值水旱、饥疫并作,其发私囊作饘粥药剂,遣吏分坊治病;还请于朝,乞减免上供米,兴修水利,疏浚西湖,造福杭州人民。杭州人感激苏轼,“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7]684。其政治作为与白居易任职苏杭并无二致,都心系百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苏轼当是有意学习白居易的为官之道。
张海鸥在论及白居易与苏轼之相似时说:“白44岁贬江州,48岁任忠州刺史,49-50岁还朝,官至中书舍人。51岁自请外任,任杭州刺史,54岁除苏州刺史,55岁以眼病归洛阳,56-57岁复入朝至刑部侍郎。58岁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75岁去世。苏44岁谪黄州,50岁起知登州,旋入朝任礼部郎中,51岁累迁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53岁兼侍读,权知礼部贡举。54岁自请出知杭州,56岁知颍州。仕履波折的确相似。”[8]苏轼认为自己与白居易在人生际遇、仕宦经历等方面有诸多相似。关于这一点,袁中道的《白苏斋记》从“心”“趣”“才”“学”等方面有所论述:
两公真有大同焉者:吾观乐天、子瞻为人,大约皆真实淳笃……是其心同也。乐天典大郡,所携不过天斋石、华亭鹤、折腰菱,晚年买履道里宅,至鬻骆马;子瞻虽处颠沛,不轻受人丝毫,无田可归,竟至流落……是其操同也。若夫醉墨淋漓于湖山,闲情寄托于花月,借声歌以写心,取文酒以自适,则乐天、子瞻萧然皆尘外人……是其趣同也。乐天、子瞻,其文词皆为一代宗匠……是其才同也。乐天、子瞻虽现宰官之身,皆契无生之理……是其学同也。[9]533
苏轼与白居易在“才、学、心、趣”方面相同,其与白居易有相似的人生轨迹,由人生经历似乐天而取号“东坡”,亦是对白居易的一种追慕和认同。
四、苏轼之诗风——效乐天而“东坡”
苏轼推崇白居易,在做诗方面向白居易学习,深受其影响。苏轼诗句常化用白诗。据有关统计:“苏轼诗篇2389,其中与白居易有关的457,所占比例为19.13%。”[10]兹举例如下:
白诗:所以刘阮辈,终年醉兀兀。/苏诗:不饮胡为醉兀兀。(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87页)(以下引用简称《合注》)
白诗:去复去兮如长河,东流赴海无回波。/苏诗:已逐东流水,赴海归无时。(《合注》127页)
白诗:相悲一长叹,薄命与君同。/苏诗:无言赠君有长叹。(《合注》231页)
白诗:烟波浩荡摇空碧。/苏诗:潋潋摇空碧。(《合注》321页)
白诗: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琵琶诗序: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苏诗:青衫不逢湓浦客。(《合注》513页)
白诗:抱膝灯前影伴身。/ 苏诗:二年相伴影随身。(《合注》1050页)
白诗:我学空门非学仙,恐君此说是虚传。/苏诗:区区分别笑乐天,那知空门不是仙。(《合注》1902页)
白诗:花光焰焰火烧春。/苏诗:焰焰烧空红佛桑。(《合注》1985页)
白诗:下饭腥咸小白鱼。/ 苏诗:病怯腥咸不买鱼。(《合注》2124页)
白诗:洗刷去泥垢。/苏诗:洗刷沮洳泥。(《合注》2430页)
苏轼诗大量化用白居易之诗句,正可见苏轼对白居易之欣赏。莫砺锋在《漫话东坡》中评苏轼之诗风:“东坡本人的风格或平易晓畅,或飘逸奔放,在唐代诗人中与李白、白居易等人较接近。”[11]222大体上说,苏轼诗风既有豪放恣肆的一面,又有平淡自然的一面,而平淡自然则近于白乐天。白居易诗有通俗易懂、明白晓畅的特点,号称老妪能解。谢桃坊在评价苏诗时也认为:“苏轼后期平淡古朴的诗作在艺术渊源上显然吸收了白居易的浅易。”[12]195
此外,在苏轼词中也有对白诗的化用。如《一丛花》:“衰病少情,疏慵自放,唯爱日高眠。”其中“疏慵”一词出自白居易《闲夜咏怀因招周协律刘薛二秀才》诗:“世名检束为朝士,心性疏慵是野夫。”另,《醉落魄·席上逢杨元素》“同是天涯伤沦落”,用白居易《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句意;《西江月》“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语出白诗“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菩萨蛮》“我已无肠断”,出自白居易《山游示小妓》“莫唱杨柳枝,无肠与君断”。由此可见,无论是做诗还是填词,苏轼都有向白居易学习的地方,由做诗效法乐天而取号“东坡”。
五、苏轼之人格、处世——慕乐天而“东坡”
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第三卷“乐天对酒诗”云:“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13]287张再林在其书中也谈到:“在宋代,对白居易的敬慕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而苏轼则是这种普遍现象中的典型例子。”[14]9苏轼本人在《书乐天诗》中也曾表示对白居易的仰慕,其文如下:
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元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遥想高僧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唐韬光禅师自钱塘天竺来住此山,乐天守苏日,以此诗寄之。庆历中,先君游此山,犹见乐天真迹。后四十七年,轼南迁过虔,复经此寺,徒见石刻而已。绍圣元年八月十七日。[6]2113
绍圣元年苏轼贬官惠州,经过虔州,游天竺寺。他想起当年白居易在杭州时送给韬光禅师的这首《寄韬光禅师》。其诗《天竺寺》亦可证实此事。《天竺寺》并引:“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归,为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乐天亲书诗,笔势奇逸,墨迹如新。’今年四十七年矣,予来访之,则诗已亡,有石刻存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诗。”[1]1944-1945苏轼在十二岁时听父亲说曾在天竺寺看到过乐天真迹,“笔势奇逸,墨迹如新”,而47年后,苏轼再来时,只有石刻了,已无缘得见白居易真迹,却是一种遗憾了。
此外,苏轼对白居易多有称誉,对其人格、道德、处世态度等都极为推崇。《仇池笔记》有一则故事记载苏轼为白居易辩护:“白乐天为王涯所谗,谪江州司马。甘露之祸,乐天有诗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不知者以为幸祸。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也。”[15]218大和九年“甘露之祸”,王涯遭灭族,白居易时以太子少傅分司东都。苏轼认为白居易绝非幸灾乐祸之人,而是为因反对宦官弄权而惨死的王涯悲伤。这则故事正表明苏轼对白居易道德人格之深信。其《醉白堂记》赞赏白居易:“乞身于强健之时,退居十有五年,日与其朋友赋诗饮酒,尽山水园池之乐。府有馀帛,廪有馀粟,而家有声伎之奉……忠言嘉谋。效于当时,而文采表于后世。死生穷达,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苏轼羡慕白居易晚年之闲适,对白之忠、谋、文采、操守、道德称赞有加。苏轼除了对白居易人格、道德方面的赞美之外,他对白居易最大的认同,应该是白所奉守的“中隐”的处世态度。白居易《中隐》诗曰: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
……
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
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苏轼在熙宁五年杭州任时作《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五有:“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1]319苏轼认同白居易“中隐”之处世心态,并在后来的仕宦生涯中,保持内心的泰然,并结合自身的思想修养,加以提升,在处世态度上达到旷达而疏狂的境界,比白居易更进一步;哪怕是晚年不如白居易那么闲适安乐,一再遭到贬谪,亦保有乐观豁达的心境。
六、结语
苏轼“东坡”之号,与白居易忠州任上开辟的东坡及苏轼倾慕白居易有关。由苏轼诗集可确知,苏轼在第二次出蜀时就经过忠州,并在忠州作有凭吊严颜、屈原的诗和《竹枝歌》一篇;苏轼至黄州两年,开辟数十亩营地而躬耕其中,始自号“东坡居士”。苏轼在黄州时心态之转变与白居易忠州时心态有诸多相似,其“东坡”之号取自白居易忠州种花种树之东坡,确属无疑。此外,在谪居黄州及以后的岁月里,苏轼觉得自己在人生经历和处世心态方面都与白居易相像。苏轼一再称自己与乐天相似,对乐天的倾慕是不争的事实,其人生经历似乐天而东坡,诗风效乐天而东坡,人格方面慕乐天而东坡。苏轼取号“东坡”是对白居易的一种仰慕和趋步。
[1]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苏辙.栾城集[M].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周必大.二老堂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容斋三笔.
[5]朱金城.白居易年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7]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8]张海鸥.苏轼对白居易的文化受容和诗学批评[M]∥莫砺锋.第二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328-329.
[9]袁中道.珂雪斋集[M].钱伯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0]王域城.宋诗对白居易的受容与超越——以苏轼诗为中心[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11]莫砺锋.漫话东坡[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12]谢桃坊.苏轼诗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1987.
[13]罗大经.鹤林玉露[M].王瑞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张再林.唐代士风与词风研究:以白居易、苏轼为中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5]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东坡志林仇池笔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责任编辑于湘]
2016-06-01
贾琪(1989— ),女,河南郑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I206.2
A
1008-6390(2016)05-007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