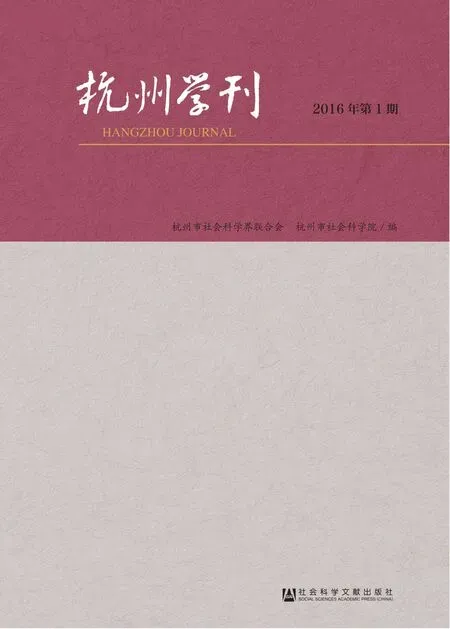《黄元秀日记》稿本述略
◎ 仇家京
《黄元秀日记》稿本述略
◎ 仇家京
黄元秀一身兼具辛亥革命志士、武术界前辈与佛教居士之名,颇有传奇色彩。鲜为人知的是,杭州图书馆收藏其日记的手稿本达十五册之多,远远超过《辛亥革命老人黄元秀传》一书中所提及的“目前保存的四册”之说。这不仅是我们了解传主的第一手资料,亦是解读其心路历程的重要文本。本文就稿本的形制、内容以及相关诗文残稿进行梳理,旨在彰显乡贤之嘉言懿行,或有裨于世道人心,或可供研究者取资。
黄元秀 日记 稿本
作者仇家京,杭州图书馆研究馆员(邮政编码 310016)。
黄元秀(1884~1964年),原名凤之,字文叔,号山樵,杭州人。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陆军士官学校。为推翻清朝统治,曾抱有“揽辔望中原,投笔觅封侯”的宏愿,协助孙中山先生等组建同盟会。清亡后,又参加讨袁、护法、北伐等运动,事迹散见于《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等回忆录之中。因已出版的《辛亥革命老人黄元秀传》一书,系由作者黄韵海采访传主之子、媳口述所得,部分内容则“由黄元秀公的法本、日记中摘录、整理出来”,且附有年谱,介绍生平事迹比较全面,故本文无须赘述。现仅就馆藏《黄元秀日记》进行梳理,并按时间顺序,分为抗战间流寓重庆(1941~1945年)与定居杭州(1952~1963年)两个时期来解读。此外,另有稿本《松窗随笔》一册,收录了1930~1950年的部分诗、文、联、偈,真实地记录了黄元秀早年的情志与思想蜕变的轨迹以及1950年入狱后的感遇。因其内在精神可与日记相互表里,颇多可采之处,故一并叙述。
一 《黄元秀日记》的稿本形制
杭州图书馆收藏的《黄元秀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手稿本,十五册。约八十余万字,用魏碑书体写成。封面原题《沪渝旅行记》(1册)、《旅渝日记》(2册)、《勤笔勉思》(2册)、《松窗随笔》(9册),并分别署有年月,钤有“常乐我静”“虎林黄氏”“黄山樵”印记(另一册为下文提及的《管制目录》,因馆藏索书号不一,故未列其中)。记事时间自1941年1月起,至1963年7月止,跨度达二十二年之久。其中有些年份缺失,如1942年、1943年、1946~1951年、1953年、1961年,并不完整。据1956年6月17日的《日记》所载“整理以前日记,少48、49、50三年三册,不知如何遗失”之语,可见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即有亡佚。《日记》前有简目,记录日常生活中较著之事,当系日后整理编写。如民国三十年的《沪渝旅行记》,目录依次为“一月卅一日新春词”“二月十一日起申友饯别”“二月二十日离申赴港”“二月廿五日游九龙香港”“三月三日飞重庆(四月一日奉委)”“四月十七日杨说坐功所见”“五月三日初遇空袭”“五月廿三日遇圣露上师”“六月二日派在铨所”“六月六日大隧惨剧”等。《日记》正文天头或版心处,标有与目录对应的文字。与通常日记不同的是,《日记》中多夹有与记事相关的票据以及时事剪报,如《大公报》《重庆新民报》以及旅途中的机票,乃至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生活拮据时的典当票据以及浙江政协的会议通知书等。除了以志备忘以外,可以看出黄元秀为人细致入微的一面。
耐人寻味的是,另有《管制日录》一册,时间为1951年10月至次年11月,正值黄元秀被居地派出所宣布管制二年期间,其中未有一言述及放生礼佛之事。而在存世的1952年的《日记》中,有载“元月廿二日,为余去蜡出狱纪念日,买三小鸟放生,俗名 ‘黄头’。彼之去也,如我之归。彼此形态不同,而性灵上未有差别,是同一法性。但愿此去翱翔于宇宙间,得享自由之乐……今年曾出汗多次,仍是大咳。不知年龄关系,抑受寒过于往年?如此年华,如此疾病,非佛学有深切功夫,不能旷达观念、解脱烦恼”。从这些情节与片断中,可以想见撰者的谨饬以及平和的处世态度。而从残存《日记》的思想脉络来看,佛学无疑是其内心世界的重要支柱。
二 《黄元秀日记》主要内容概述
(一)流寓重庆,情系家国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势艰危。是年秋季,黄元秀奉命赴温州任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职。冬季,得悉其子黃正裕在淞沪抗战期间,因亲率轰炸机队迎敌时殉国,深受刺激,神经几乎失常。“自后国军日退,瓯江日危,无力支持,晋省请辞,未准。因代得脱。”遂辞职赴上海就医。事后他在《日记》中回忆道:“所恨老母卧病,因年届九旬,未便奔波。抵申即闻杭省沦陷,母妻兄嫂皆沦于敌中,心如刀割。又闻城内谋立伪组织,故未敢遽返,防被其牵连也……继则妻女来沪,租住环龙路三楼。翌年次女隹庆病,医治年余而逝世。于廿九年底,借贷俱尽,幸卖去西湖地一方、宋高宗墨卷一局,由卅年三月由港飞蜀。”
1941年2月21日,黄元秀自上海乘船,后取道香港赴重庆。《日记》云:“余年已在五旬以外,国事如此危弱,强邻如此横暴,国际外交不顺利。江天在望,忧心如捣。”日寇强敌压境,蒋介石国民政府心存的媾和幻想破灭,这正是其离乡流亡伊始时忧郁心境的真实写照。是年清明时节,“念乡不已。回思廿七年在沪,清明节游法公团时,挂念杭州沦陷区家属。是日天气晴和,风物鲜美,奈何情绪不安。今到重庆,虽家室有托,个人有职,而此心追念弃养之老母,及亡过之二兄,及次女,悬想未成之。抗战何日结束,仍是沉闷不已。”
黄元秀赴渝后,在军事委员会铨叙厅任职。当时重庆屡遭敌机轰炸,多见载于《日记》。如“五月三日进城……讵知敌机来袭,交通中断。由王继河局长领往临江门山崖防空洞暂避。午后出洞,知被炸市屋甚多(桂花街、都邮街、观音石、两路口、巴县中学、国府路、曾家岩等处)。余寓亦受震荡,屋顶洞穿三处”。“六月六日晨,阅报知昨日敌机落弹四次,大街十八梯隧道中,窒息死与踏毙者,有数千人……”此即“重庆大隧道之惨案”。
1944年,黄元秀进入花甲之年,《日记》相继载道:“岁月悠悠,已经六十甲子,回想儿时度岁光景,历历如在目前。当年生活虽低,而家人团叙,亲友交欢,其心中愉快,有不可思议之乐。今则暮年远戍,国土残破,家人离散,茫茫劫数,何日得了。”“今日为旧历谢灶日,儿时此日已解馆,放假家居,饱赏年景。今则烽火遍世界,有国不宁,故乡沦陷。东望家山,欲归不得。”“春光明媚,故乡西子不知若何?东望家山,神驰不已。”1945年2月22日,黄元秀接到国民政府任命其为军事参议院参议的任命状,并无喜悦之色。随后记道:“人生百年,若白驹之过隙。所以异于禽兽者,礼义而已。以诸葛之怀抱,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不遇正统,不求闻达也。”
(二)拜访上师,研习密宗
黄元秀善根深厚,与诸多高僧大德多有交往,法谊深厚,且遍及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如汉传佛教界有虚云老和尚、弘一大师、太虚大师、弘伞法师、海灯法师,藏传佛教高僧中则先后皈依白普仁尊者、九世班禅、诺那上师、圣露上师、督噶上师、贡嘎上师等。他在《日记》中多有拜访上师、研习显密之心得等内容。
1841年5月23日,“重庆遇圣露上师”。
1944年1月9日,“参加莲花精舍,请明觉活佛行灌顶礼并照相。所灌者,系金刚刹多顶”。
1945年3月15日,“今晚韩大载继续昨晚之六波罗蜜”。17日,“晚间听大载讲显密二宗差别,甚详……但密宗义理,全出于显教经典,并非祖师所撰。如本来清净(体性即自性),本来心佛众生无差别。显教是去染求净,是多生多劫,薰习方成。密宗是当下即是,根据本无差别,本身即佛。可以即生成佛,仅方便不同,即方法不同(《圆觉经》上说种种无差别, 《心经》上说不垢不净,无智无碍无得)。18日,“今晨往听韩大载先生续讲密宗戒文”。19日,“显宗十住十行十回向、信解行证,与密宗共;观苦、现无常,观空,与密宗不共。显宗用对治方法,如对贪用布施,对生死用湼般,所谓离垢取净。而密宗用转变法,即以生死为湼般,以烦恼为菩提,以五蕴为庄严。因自性本来清净,法性平等故,此密宗与显宗之大别”。26日,“晨起读《六祖坛经》数品。经中所示,皆云自性即佛,不向外求。迷时是众生,悟时即佛。恶念起即地狱,善念起即天堂。一切皆由自性自心”。6月13日,“余为七十六人中之第二人开顶,草甚正中,不禁惊喜交集。于廿六年夏季,圣露师来杭州传法,时原约秋间再来开顶,后为战事中止。卅年夏,余闻圣露师在渝,当求续学,师嘱赴蓉加入同修,讵知圣师在渝缘绝。由来八年之愿,今日得偿,欣慰之私,莫可言喻”。并为此而吟诗云:“云迷来路熟个开,借他瑞草顶门栽。肉盆打破空无有,悟得拈花见如来。”对佛法的开悟,犹如阴霾驱除,正所谓“天气大晴,旭日一轮,春光遍照,见四山青绿,溪水潺潺。唐诗云 ‘溪声常在耳,山色不离门’。当此乱离之世,得此清闲境界,直是尘世仙境。读《坛经》一遍,听鸟语,移时饱餐麦饭一顿。闲步山头,听樵子歌唱而归”。愉悦之情溢于言表。
(三)日本战败,亲历见闻
1945年8月,黄元秀欣闻日本投降消息,“郁闷顿除”,《日记》接连载道:
民众狂欢,满街爆竹,悬旗志庆。想杭州必同日知悉,其欢喜之情,不下渝沪。吾家眷属,定必翘望余归矣!
东京广播,盟国对于日本接受投降之复文,已送达东京。日本政府即开阁议。此项复文,限日政府二十四小时内答复。日阁商议后,即令内外海陆军停止抵抗,并派全权代表遵照盟国所指地点签订降书(约在军舰上签订降书)。占领日本本土之盟军,已奉令准备,其中有我国劲旅一师,由空运到菲岛集中。
倭皇昨日正式签降书,答复四国并亲口广播,通告国内外所属,于是只有派代表签约矣。
前日到湖南芷江,投降代表日人今井武夫少将、桥岛芳雄中佐、松原喜八少佐、前川国雄少佐等八人,在休息室中对人说:“日本虽被中国战败,但不仇恨中国。中日是同文同种,都是亚洲人。”他们将“中日亲善”旧套搬出来重念一番。濒依抚水的芷江骤然热闹,县城门上悬一联曰:“庆五千年未有之胜利,开亿万世永久之和平。”商店中有写“日本投降了,天下太平矣”白话联。
1945年9月16日,“空军司令张廷孟、地区司令张伯寿等十七人飞台湾,接收机场。五十一年来,含垢忍辱,今日始归祖国。终将国旗飘扬于杆头,实足快慰吾人之心”。继而深情地回忆并感喟道:“往年九一八,有许多悲愤抑郁之情。今年今日,只有感谢上苍与戮力之同胞及贤明之领导也。余之六十年中,见国土之失而复得者,所谓饱经忧患,深尝世故矣。”寄厚望道:“惟吾国抗战已毕,建国未备,千头万绪,正待贤豪努力也!”
抗战时期,当中华民族遭遇日本侵略而处于存亡绝续的关键时刻,心境焦灼,情系家国者的忠义之士固然有如黄元秀者。而投降变节,在变乱中苟且偷生,或贪图荣华富贵,充当汉奸者亦复不少。《日记》云:“昨日报载汉奸名单,与今日所载不同,有项致壮、张韬、许建屏三熟人,想不至于不实。此乃一念之差,所谓一朝失足千古恨。不知如何结局。”“午后汪京伯兄来,云范悯黔因充敌伪统税局长,报载榜上有名,已在杭通缉。余与范,曩曾同事,此君素来贪污,此次所为,意中事耳。”“又阅报中赵正平曾充伪职,避匿甬东,近传自杀。此公聪明有余,智慧不足。一生立足不稳,致有此结果。”在以上平实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其所秉持的取义成仁的民族文化人格和理性精神。
黄元秀入川以来,位居闲散之参议,并无一定办事之处所。自谓“任职三载,备位而已”,且“连年疾病,初患泻,后患瘧,继患咳,仅今夏未卧床席”。因其谦逊的品格,《日记》中不乏坦诚反思之语:“近数夜,月明如昼。游子思乡,征人怀旧。月色皎皎,长夜漫漫。回思入川五载,每年劳劳碌碌,不知所为何事,所成何果。外则于国家,内则于身心,实无所得。”“年来虽无案牍劳形,而每日亦未清闲,杭俗所谓无事忙也。回思六十年来,于国于家毫无裨益,于个人亦然。”
1945年12月,日本战败后,黄元秀将要告别5年的离乱生活之际,《日记》中载道:“天大雾。昨夜月色如昼,望四山如画,园中芙蓉盛开,月下观之,更觉艳丽。衬以修竹,清雅与娇艳并陈,殊非凡境。此时得舞剑其间,剑光与月光迸射,舟有美人吹笛于旁,此景此情,非世间庸碌者所能领会。”所描述的尽管是恬淡、清幽,甚或隐逸之境,仍难抑其内心的喜悦之情。
(四)甫脱囹圄,又遭管制
1950年底,黄元秀因曾任国民政府“少将参议”等职,被逮捕入狱,次年获释。在其《松窗笔记》残稿中,有《庚寅年仲冬被羁口占》六首,兹节录如下。
其一:……多生事业随心转,莫认无常作有常……其三:……消劫莫如三宝力,余生惟愿乐安康……其五(余甲申年生,今岁庚寅,星相谓天比地冲。仲冬正是交运脱运):天比地冲战甲庚,居家住狱两酸辛。其六:老大年华入囹圄,何因何果遭坎坷?年来事事清三业,想是前生宿业多。其七:宽大仁风下九重,黄童白发喜相逢。家家爆竹浑除旧,浩荡新春在眼中。
从诗中可以看出,时年67岁的黄元秀将其牢狱之灾视为“前生宿业”,能与家人团聚则感恩于政府的“宽大仁风”。1952年初,黄元秀被属地居委会指定“扫街、拔草”,7月被派出所宣布“管制二年”。被勒令做日记,内容分劳动、思想、学习、经济(每天收付账,如家用等事)。且平时有事外出三小时以内,需口头报告本区小组长;三小时至八小时,书面说出事由、地点,报告治安委员会;超过一天则报告派出所。除了按日常指示在规定地段扫街拔草外,每两周到辖地派出所,汇报劳动、学习、思想心得以及家中情况。黄元秀另撰有《管制日录》,需“每十天呈送治安委员检阅”,所记内容为管制期间的劳动、看报学习等琐事。而在1954年的《日记》中,则载有“体力不耐劳”“疲乏不堪”等字样,且录有“复云南弘伞和尚缄”,称“俗自解放以来,虽遭坎坷,幸皆无恙。而浮生七十,精力衰退矣。每日早晚课外,无可告述。各友皆已星散……沧海梦田,成住坏空,末劫时期,任运而已”。透露出被管制期间无可奈何的伤感情绪。
(五)“放庐”充公,生活拮据
坐落在涌金门西子湖畔的“放庐”建于1925年,因黄元秀出省北行而未居住,先后租于浙省盐务稽核所长水次惠等人。1929年,黄元秀奉母率眷居住两年余。1937年杭州沦陷,“放庐”即为日寇机关占用,继而又被日本大九洋行租住。“所存家具与楼藏字画书籍等皆不翼而去。”迨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杭州时,“放庐”由国民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李默庵及眷属、幕僚、卫队居住。未几,经交涉归还原主后,部分用以自住,部分放租以维持生活。1949年后,相继为军区、新华社租赁。1954年,“放庐”以“郊区地主多余房屋”的理由被公家没收。《日记》云:“日来为放庐被没收问题,影响吾家日用开支(放庐每月租金百五十万)。虽是身外之物,然心中深受刺激。患得患失之思,时起时落。此佛家所以抛去家室,可免去多少牵累。”此后,家庭支出改由其子女负担。虽有部分稿费所得,但是仍入不敷出,《日记》中不乏借典卖旧物贴补家用的记载。
托严利生代售羊皮统一件,估价十八万元。时已近冬,不知有主顾否?
售出旧书十一斤,得价壹万六千五百元,合一斗米价。
晨携先母绣花礼服及内子新嫁衣服并其他绣件,到天宝寄售行代售上列各物。富时视为珍品,穷则视同敝屣。
携家藏古磁天福罇(晋磁)到陈伯衡家,谈家景拮据,想出售于杭州文物保管会。
售衣服连内子绣衣裙,共售五十二元。余心中颇不舍,但为拮据,不得已而为之。
余携张大千山水一幅,托任福元代售卅元。
下午,带山水磁屏到西泠印社托韩登安代售。
即便如此,每月仍是入不敷出,亦无力接济他人。如“接外甥顾芝生来函云,日来生计艰难,乞借两斗米。若照往年,区区之数,不足计较。而今则非当年可比矣”。一次,友人“严济宽来借钱,适值身无半文。转向女佣借二角与之。幼年有此窘状,不谓年老七旬,又尝此穷味”。于是叹道:“此中窘况,非局外人所能了解也。”
1954年7月,同为辛亥革命先驱的吕公望去世,黄元秀在《日记》中载道:“余与其自前清宣统间在杭垣督练公所同事,吕在统计处,我在参谋处,皆属科员。至今已有四十余年,彼此浮沉军政界,不知多少幻梦尘劳……家产已无,身后颇萧条。据闻棺殓窀穸,皆为友人帮助而成。”
1955年11月6日,黄元秀长女归来告知,“昨日校中以蕃薯代午餐,师生饱飡一顿”,闻之竟“欣羡无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的生活困顿情状,于上述遭际中可见一斑。
(六)弘法护生,反躬自省
佛教是注重培养慈悲心的宗教,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强调要普度众生并戒杀茹素。黄元秀皈依佛门后,积极学法、弘法、护生,不渝其志,正如其诗所云:“朝夕无他事,顶礼我佛前。精诚无敢怠,愿消宿业愆。”《日记》中所录放生活动,比比皆是。
四十岁时生日,余到西湖招贤寺习静,念佛三五天而归。五十岁生日时在南昌,是日命仆人买大小龟数十只,放之江中……六十岁生日,抗战在渝,晨与淳儿到罗汉寺礼佛,放鱼数尾于江。
即便是依靠典卖以维持生计的五六十年代,亦未尝中辍。部分文字颇为生动,饶有意趣。
在湖边买得野鸭一对,需千元,到放庐中放之湖中,在水中左顾右盼,悠然而逝,其意甚乐。
余到西湖放鱼十二尾,在湖边遥瞻放庐,辄生遐想不已。
是余七十年前出生之日。晨买鲤鱼十六尾放之西湖,愿其安乐,庆其重生也。
今日是立春节,又是莲师诞辰,买三只麻鹊放之。
到公园放小鱼三枚,见其攸然之乐,人物无异也。
余买断尾螺放之。虽已断尾,其中尚有小螺,冀其母子重生。
当1958年全国性的“围剿麻雀”运动波及杭州时,《日记》载道:“本日杭城围剿麻雀,青年学子满布山中,余遥望唏嘘而已。”这对认为“世间善举莫如放生。济贫是救穷,放生是救命”的黄元秀来说,情何以堪。
黄元秀信奉佛教,重视个人修养,不尚空言,并在《日记》中记录其学佛心得。
何谓学佛?即是由解起行,即是将所了解之佛法来实行也。就是由闻而思,由思而修。行起解绝,由解起行,须实行实做。众生中有智门入手,有从行门入手。从智门入者,大半利根人;从行门入者,纯根人。可是从智门者易为聪明误,所谓觉于口而迷于心,不如从行门入手为可靠。谚曰:劝人修行,未有劝人修智。实际上行的功夫到家,自然生智慧。因众生本其妙智妙慧,无须外求。只要行得坚固,妙观察智,自然显发,六圆镜智,自然现前。
余多年省察:事到临头便无把握,足见养气之难;遇刺激而不动心,实非易事。古人所谓言之匪艰,行之惟艰耳。
1954年,因各房祖产、“放庐”被公家没收,乃至影响到生计,不免产生牢骚,于是在年底的日记中反省道:“今回溯一年来之大事:自身学佛修持,未有所得。所谓戒定慧者,依然如故;贪嗔痴亦如故。”
(七)广交时贤,评议时闻
黄元秀交游颇广,如其所称“余自弱冠奔走四方,六十年来,江湖滥交,上自岩穴修士,下自贩夫走卒,无所不交”。仅1949年以后,《日记》记载时相过从的有马一浮、张宗祥、余任天、韩登安、蒋裳、徐映璞、周启人、张焕伯、阮性山、项雄霄、田宿宇、黄宾虹、田宿宇、严济宽、盖叫天等人,或讨论学术,或请益,几乎囊括了当时杭州的知名人士。如“余偕徐元伯兄赴蒋庄访马一浮兄谈天。余问:佛经云人身第八识从何而有,所谓无始自何而起?马答:皆《楞严经》中语。三界唯心,一切惟识。山河大地,四圣六凡,皆由心造”。“途遇老友沈培滋,谈佛门中事。沈述古德云:‘理可顿悟,事须渐修’。余颇钦佩。凡百学术,无不如此。能修寂照,所差无多。但须颠沛必如是,造次必如是,难矣。”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命运蹇涩的黄元秀仍有着异于常人的观察与思考,兹举《日记》数例以见之。
在书肆中见有《太平天国文钞》上册,承店主朱醉竹赠阅。觉得太平天国举义排满,是种族主义,而政治文化,似非正宗。每事行祷告,时以天父天兄为依靠,天兵天将为护卫,且在成败之间发生内讧,王太多,官爵太滥,有此三弊,宜其速亡,非曾国藩等能败之,实由自败也。
时值“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文艺界政治整肃运动、“反右”、“大跃进”时期,《日记》相继载道:
近半月来,各报纸登载胡风集团往来函件,寻章摘句,阅者莫名其妙。
近日来大鸣大放……批评中共过分,被集中围剿。每日各报揭载反批评,措辞甚激。浙江民革亦举出吴惟平、马文车、杜伟、何柱国、江天蔚、叶芳六人。民盟中宋云彬皆为右派分子。
各报满载反右派文字,陈腔滥调。
此四天斗右派会,均有小报披露会情(民革整风反右派会,声色俱厉,会场空气极紧张)。到东坡路参加民革反右派大会。右派分子吴惟平上台坦白分辩……日报上说吴惟平有罪行,未指犯何罪(究系民事、刑事,所犯何条)。若无实据,司法未曾起诉,何可在报上公然侮辱,于宪法有碍。
到张冷僧家……谈龙兴路西首,即现在医学院内,张将军(保)、王将军(横)、岳孝女三墓,中两墓移葬,孝女墓毁弃。中央明令保存古迹,而今如是,真不可思议。
报载各地区兴办铁工厂木工厂,风起云涌,不知能长期工作否,供销相当否,否则浪费物力人力。
上述对时事的评议或感慨,情见乎词,尤其是在当时特定情势下所表达出来的独立见解,已被今天的历史发展所证实,颇为难能可贵。
三 从辛亥革命志士蜕变为居士的人生历程探析
早年的黄元秀为推翻清朝政权,协助孙中山等志士组建同盟会。黄兴以诗句“当风纵怒马,跨海屠神鲸”相赠,可谓豪情干云。至中年何以蜕变为居士?在《日记》或其他稿本中或可窥见其动因。
1930年,黄元秀诗云:
人生行乐耳,世事若浮沤。富贵欲何为,执鞭徒自羞。
少壮受诗书,非为稻粱谋。何况叔季世,功名烂羊头。
众醉我独醒,斯人非吾梼。回忆卅年来,仆仆胡不休。
揽辔望中原,投笔觅封侯。慷慨谈胞与,后乐忧先忧。
岂知意愿违,与时不相侔。归来照明镜,星星白发稠。
深悔东隅失,桑榆冀可收。我爱当涂高,淡泊无所求。
天沦叙至乐,肥遯托高流。烟云销壮志,花月恣情游。
扁舟日容与,杯酒时吟讴。独善已有余,仍为饥溺愁。
减膳振哀鸣,宏愿济神州……
诗作的背景,据《辛亥革命老人黄元秀传》一书所附年谱,正是在杭州创办实业时期。诗歌回顾了作者从早期投身反清革命,如何从“揽辔望中原,投笔觅封侯”的宏愿,转变为“烟云销壮志,花月恣情游”的缘由。而“众醉我独醒,斯人非吾梼”以及“岂知意愿违,与时不相侔”,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作者虽已看透世事,抛弃功名,追求悠然于山水之间的意趣,但并没有以超然出世姿态自处,或停留在“独善”的“自了汉”境地,仍抱有“减膳振哀鸣,宏愿济神州”的悲悯情怀。二十多年后,他曾经有过这样的自白:
我们中国革命党,在前清时代不满意满洲人统治中国,所以起来革命,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组织老同盟会,我是其中一分子。到辛亥年推倒满清皇朝,达到三民主义之种族革命。对于民权主义,以为代议制度五权宪法可以做成了。对于民生主义始终模糊……过了多年(看了袁世凯做洪宪皇帝,看了北洋军阀专横,看了陈炯明倒戈,于是中山先生在北方去世,从此对于政治不感兴趣,在家乡办实业过日子)。
……我自从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对于革命事业上脱了节……因此孤陋寡闻,终年为一家生活上忙碌。办长途汽车公司、办云龙农场,以为实业可以救国,并可维持一家生计。从此三十年来,抛去了党的观念,散失了革命立场,从唯心主义进入了佛教门头,因此人生观愈走愈远了。
上述文字除了在被管制特定时期“委曲求全”的意味,与诗作的旨意无疑是相通的。
1941年,黄元秀由香港转道赴渝后,在军事委员会铨叙厅任职。是年正值抗战中期的国势危难之际,新闻媒体对国民党上层的腐败丑行时有披露。12月4日《日记》为此载道:“沈钧儒来说,各参政弹劾孔部长。其人之贪不可及,其夫人买外汇,美国报纸登其内幕。家人拼开百龄餐所,堂堂国民政府部长,不能整肃家规,任凭子女招摇瞎闹。其在人之能为,亦可见矣。”抗战胜利后的当年十一月,黄公办妥退役之事即启行回杭。途经上海时,与曾在浙江光复时担任浙军总司令的周赤忱会晤。交谈后在《日记》中记曰:“周赤忱兄来访,谈五年来在沪沦陷之苦……为民族计,虽受尽辛酸而无怨。讵知日寇投降来,三月中接收受降等工作人员,真令人失望。列举种种贪污敲诈之事。”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的政治生态复杂,也是其离职的原因之一。
黄元秀早在四十岁前就与佛结缘。在残存《日记》透露的信息中,有“四十岁时生日,余到西湖招贤寺习静,念佛三五天而归”之语,可看出端倪。当时招贤寺方丈弘伞,即指程中和,与李叔同为师兄弟。而黄元秀与弘一法师相交有年,在闽南同安专员任上,有往还赠诗的经历,并称其“出家前后行状,堪为近世居士比丘模楷”。程中和在“讨袁之役”曾任师长一职,后看破红尘,出家为僧。同为辛亥革命同志而皈依佛门者,尚有老友屈映光(法名法贤)以及曾为秋瑾敢死队一员的侠女张馥贞,即“耀真师太”等,这些人的经历均会给他带来一定的触动与影响。又因其佛缘殊胜,且常在寺内聆听僧众诵经念佛,心中感到宁静自然,法喜充溢,于是促使黄元秀皈依佛门,成为佛教四众弟子中的优婆塞。
黄元秀用佛教的六度法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去度人利众,常做有益于社会之善举,未尝懈怠。在习武授艺方面,因其早年与武术界名师多有交往或请益,学成后则冀望于流传勿失。1929年,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礼聘李方宸将军来杭主持全国武术比赛时,黄元秀“执贽门下,凡进退击刺诸端,亲承指授”。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其整理的《武当剑法大要》《武术丛谈》先后问世。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已届古稀之年,仍不废义务教拳与传授剑法。
到柳浪公园教薛家三弟兄太极拳。七七年华,非为名为利,为此艺流传于世耳。
何长海、许炳和二人来尊我为师,学太极拳与武当剑也。余已七十有二,技击一门已非当年所能,仅能将各师所说者略为解说而已。
蒋玉堃、何长海、黄士信、许大鉴来习剑法两小时。
再访老拳师刘百川,谈拳技中各事……古来各老祖师,遗传下来各种绝技,目下已不可多得。此系中国武术中宝贝,西洋各国所无。但愿已得者,务必多传;已学者务必多练。保存原有技巧,使勿失传,永远传流不绝。
海灯师带徒寂诚来学剑法,余续教第五路……
黄元秀在“放庐”充公之前,经济尚宽绰,《日记》中有“托润师侄汇寄海师三万元”“汇三万元与贡师,作冬季炭金”等礼敬上师记录。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困难时期,仍有赠送公共图书馆书籍之事。如“上午携《密宗要诀》十一本、《外内密戒手册》两本、《精忠小志》一册,并《岳王初瘗志》一册、《武术丛谈》一册,共十六本,到图书馆长张冷僧家,请其交西湖图书馆收存”。“上午带《莲邦宝筏》一本、《大宝法王事略》二本、 《佛持世陀罗呢》及《大悲心呪》各一册,到张冷僧家,请其交图书馆。”
抗战期间,黄元秀在重庆亲逢上师亲传法数十种,因皆无完善印本,故拟将督噶上师所传《恒河大手印》等缮稿付印。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孜孜整理密宗法本,意在印刷流传。《日记》有“整理旧书与密宗法本,共六大本六小本,合一箧。余历年来所学密法,除印有单行本外,皆记录于此”,“接得印度陈健民师兄来函,欲余将密宗法本全部寄伊保存。伊说香港风云不靖,不如印妥。余思多年所得七八十种密宗法本。希望有经济者集印流传,不仅保存而已”,“整寄刘锐之法本十二册”等记载。馆藏尚有《金刚乘学》稿本(十册),即为其存世手稿之一。
1951年,时年68岁的黄元秀在《自题照相》中曾为自己一生做了总结,姑抄录于此,以为本文之结束。
业海浪花一小沤,乱世舞台充角色。唱做念打未成功,回去西方拜我佛。京剧中本以唱做念打四事包括之,而余之唱,是唱佛歌;余之做,是指做人德行;余之念,是念佛、念咒;至打字,是打太极拳也。故四字虽同,内容与京剧不同。借彼四字以括余之一生,浮生若梦也可,生世如戏也可,如是如是而已。
黄元秀:《松窗笔记》(稿本),杭州图书馆藏。
黄韵海:《辛亥革命老人黄元秀传》,香港恒明出版有限公司,1999。
黄元秀《黄元秀日记》(稿本),杭州图书馆藏。
黄元秀:《管制日录》(稿本),杭州图书馆藏。
黄元秀:《李方宸剑师外传》(稿本),杭州图书馆藏。
(责任编辑 王立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