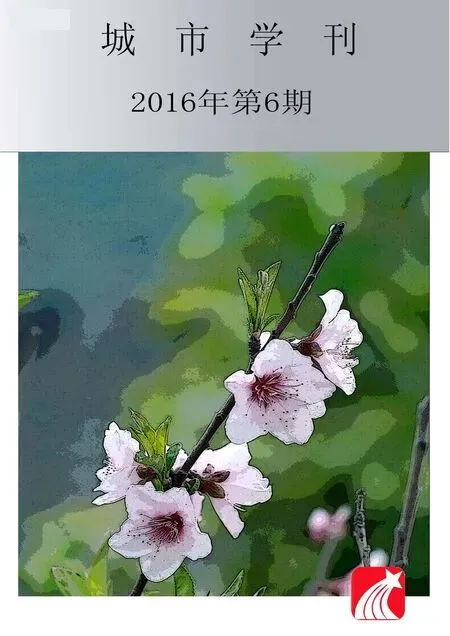时间态:地方戏曲的一种现代样态——以湖南花鼓戏“半台班”为例
周 勇,刘新敖
时间态:地方戏曲的一种现代样态——以湖南花鼓戏“半台班”为例
周 勇,刘新敖
(湖南城市学院音乐学院,湖南益阳 413000)
“半台班”是花鼓戏发展历史阶段的一种特殊艺术形式。“半台班”的产生和发展见证了花鼓戏游离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历史处境,其主动或被动的艺术革新之中,花鼓戏实现了与地方大戏的有机融合、表演形式的创新及戏剧结构的完善,使其孕育了城市化的因素。其后,在“半台班”的熏染下,花鼓戏开启了其城市化之路。通过革新与交流,打破了艺术本体的城乡壁垒;通过融汇与规范,满足了受众的多层次期待;其广博与采纳的艺术包容性,亦使其在乡村生活的基础上,走入城市市民和文人情怀之中。
半台班;花鼓戏;艺术;城市化
在花鼓戏的现代化进程中,“半台班”的出现和发展功不可没。湖南各地花鼓戏的发展,均经历过与流经地区古典剧种的艺术交流,产生了一种花鼓戏历史发展中的特殊形式,即“半戏”(地方大戏)、“半灯”(花鼓、花灯、采灯)的半台班组成或形式。各地对此称呼不一:或“半灯半戏”、“半调半戏”;或“亦湘亦花”、“亦花亦汉”;或“阴阳班子”、“阴阳堂子”等。简而言之,所谓“半台班”,即花鼓戏兼唱地方大戏(弹腔)的班社组合。如长沙花鼓唱湘剧、常德花鼓唱“汉戏”(武陵戏)、岳阳花鼓唱巴陵戏(俗称大、小丝弦)、衡州花鼓戏唱衡阳湘剧、邵阳、零陵花鼓戏则兼唱祁剧等,各地“灯与戏”合班的时间不太一致,但都在“三小戏”发展、繁盛以后,而较普遍的“半台班”多出现在清同治末至光绪中期(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而正是在这一时期,湖南花鼓戏逐步由乡村走向城市、由稚嫩走向成熟,“半台班”促进了花鼓戏的大发展并逐渐向专业班过渡,花鼓戏呈现出新的艺术特征,在这一时期得以快速发展。正因此,立足于“半台班”这一特殊的花鼓戏发展的阶段性艺术形式,考察、分析它的声腔、剧目、表演、语言、班社和演员在各个时期的动态,探究花鼓戏城市化进程的历史阶段及其影响因素,对于了解花鼓戏的艺术本质,探寻地方戏曲与城市、乡村之间的复杂关系,不无裨益。
一、“半台班”的产生:游离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花鼓戏
湖南花鼓戏的“半台班”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是花鼓戏为求生存的现实写照。“半台班”正是产生于清代官方压制之下的逼仄空间之中,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烙印在花鼓戏的发展进程之中。
清代官方虽“崇雅抑花”并于嘉庆初年下令禁止“花部乱弹”在北京演出,但因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懂,其言慷慨,血气为之动荡”(《花部农谭·序言》),京都人“厌听吴骚”(《梦中缘传奇·序》)而喜听花部戏曲,故“禁令”很快失败。就连清宫内部也逐渐以京戏为尚,集中了余三胜、陈长庚、张二奎以及杨月楼、汪桂芬、孙菊仙、谭鑫培等一代艺术大师。那么,民间流传的梆子、乱弹、皮簧和高腔剧种,就自然“合法”了,因而公开组班,城乡皆能演出。
花鼓、采茶、花灯等民间小戏剧种则大为不同。从它的萌芽状态,上自清代官府,下达乡绅、警宪,都把它当成“花鼓淫戏”,又明令禁演。嘉庆九年(1829)石门夹山寺残碑中就刻有《禁令》“禁演花鼓夜戏”。同治十一年(1872)《巴陵县志》载:“唯近岁竟演小戏,农月不止”,“实为地方大患,则士绅与官府所以急文禁绝之也”。[1]光绪三年(1877)《善化兴志》记:“游民演出茶戏,每年二、三月,分僻聚现,海淫失业,殊为恶习。近日奉示严禁,此风稍息”。到了清末,禁花鼓更烈。宣统元年(1909)《长沙日报》记岳州官府禁演花鼓戏消息:“花鼓淫戏,大于例禁,平日尚且不敢演唱,何况国制限内。现在该邑两个奉扬团,擅敢违禁,演戏淫戏。梁大令访悉,随即严饬”,“将会首等一并解案研讯重惩”。从各个时期方志、报刊的零散记载可以看出:花鼓、采茶均为禁戏,就连春二、三月季节性又在僻路山上的演出活动,也被官府、乡绅当成“诲淫恶习”、“地方大患”而奉示禁绝。可想而知,都市、城镇就鲜有花鼓戏立足,受迫害更深,花鼓戏的演出是“非法”的。只能走乡串村,躲避稽查。乡村和城市,对花鼓戏的发展来说,也是一种无法避免的二元对立和历史宿命。
二、半台班的成熟:孕育了城市化因素的湖南花鼓戏
在城市中面临被“禁绝”的命运,花鼓戏的发展只有两种选择:或逃离城市,在乡村的土壤中滋养自身,再以其艺术的力量在今后的发展中,获得在城市中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就是在政治的挤压中,失去人民大众的基础,选择向主流的意识形态或者精英的生活方式靠拢,而脱去底层百姓所需的精神外衣,转型披上华丽的规则衣裳。显然,花鼓戏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选择了前者,“半台班”在逃避和反抗政治压制的过程中形成了新的花鼓戏样式,在艺术形式或被动或主动的创新中,孕育了城市化的因素。
(一)新的表演形式的形成
生存空间的逼仄,迫使艺人把“半台班”当成了对付“禁戏”、与反动军警做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半台班”多同弹腔结合,俗称大筒戏(花鼓戏)、好小筒戏(弹腔戏)。花鼓戏主奏乐器为大筒号,是被“禁”的戏;弹腔主奏乐器是“二弦子”(小筒),照“理”是合法的。“半台班”艺人兼唱花鼓戏与弹腔(南北路)戏,以花鼓戏为主兼会两种艺技;场面上设大筒、小筒两种琴,各为主奏:唱花鼓戏时,小筒二弦子反把为配琴。反动军警禁戏抓人,台上马上改唱“大戏”:湘剧、祁剧、武陵戏、巴陵戏、二弦子即成主奏乐器。两种声腔转挨,十分方便。又因花鼓戏的锣鼓点、唢呐曲牌相同,剧种轮换也不为军警所能发现。大筒戏、小筒戏兼同,很自然成了花鼓戏求生存的一种斗争方式。
(二)与地方大戏的有机融合
清道光、咸丰以后,花鼓戏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从两小戏到三小戏,花鼓戏已基本上具有了一个戏曲剧种的诸种因素:声腔、剧目、表演、装饰与场面都较定型。但戏曲的发展规律注定了花鼓戏需要向更高的艺术水准演进,比如:声腔要完善、行当要发展、剧目要扩大、行头要美化、演出条件要改善、班社需专业化等,这样才能满足广大观众(包含城市观众)的欣赏要求,为最后进入城市做好艺术上的准备。而此时,花鼓、采茶戏都是发展中的剧种,它像一个飞速长身体的青少年,需要吸收各种艺术营养,使得它正常发育,健康成长。相邻的地方大戏正好可以满足这种客观需求。它们流行地区相同,有着共同的语言,观众的欣赏习惯与戏剧审美近似。声腔构成的音乐材料与艺术风格,颇具共性。横向借学,方便自然,这样,“半台班”促进了花鼓戏的大发展并逐渐向专业班过渡。
(三)新的戏剧结构的形成
“半台班”的出现,使花鼓戏的戏剧结构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其一,花鼓戏的声腔趋于完备。川调、打锣腔均发展了相应的板式变化,扩大了花鼓戏的表现能量;其二,增进了花鼓戏行当的完善。在小生、小丑、小旦(含二旦)的基础上增加了生、净、成为生、旦、丑、净、末诸行齐舍;其三,剧目由三小戏的演出(折子戏)为主,变为搬演故事完整的大本戏,内容又兼有历史故事题材;其四,吸收了更多戏曲化的表演程式与各行当的表演功法;其五,借鉴了地方大戏的全套锣鼓点与表现程式,伴奏曲牌与使用方法等。
三、“半台班”的熏染:行进中的花鼓戏城市化之路
民间小剧种的发展历史有一个共同规律:在乡镇形成、成长,进入城市后发展成熟。湖南的花鼓戏亦不例外,在经历了“对子花”、“两小戏”、“三小戏”的艺术准备和发展、成长后,它又以“半台班”的组织形式扩大艺术交流与传承,促进了它走向成熟的戏曲剧种过渡。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离开乡村原发基地,向城市进发的必然趋势,不过,这一过程的时间跨度较大,约经历了清光绪后期至1949年的半个世纪。
(一)革新与交流:花鼓戏的城市化开端
城市,久已是花鼓戏的禁区,特别是大城市。花鼓、采茶戏、民间小戏,从清中叶形成,就不间断地向城市进发。道光三十年以前,汉口曾演“四川灯戏”[梁山调],兰恬居士题笺的《汉皋竹枝词·梁山调》曰:“芦棚试演梁山调,纱幔轻遮木偶场,听罢道情看戏法,百钱容易剩空囊”。道光十年(1830)湖南石门县唐代夹山寺残碑,“德洋悬溥”,亦刻有“禁唱花鼓夜戏”,称“城厢市镇乡村人烟稠密处,有花鼓戏班到境”。最早进入省会长沙的戏班,是成立于光绪年间的王三洛“新太班”。民国十九年(1920),又有赵少丰的“义和班”进入长沙演出。但均不能持久,[2]一为被禁,二曰条件差,故1934年卓之在《湖南戏剧概观》中记载“近来在长沙有牗民社专演花鼓戏,终以难侵汉班势力范围,一现而止。”[3]究其原因,卓之认为,仍是官厅认为其为淫戏,因禁入城市。“致使花鼓戏之名称,乃不直于社会人士之口,良可慨也。令人动辄曰:‘到民间去!’‘到农村去!’”又曰:“花鼓戏所注重者为小生、小旦、小丑三项”,“大概每剧只三数人出场较多”,“扮演装束,亦尚农村本色”,“所演剧本内容,纯系民间故事”;“以近代后起之汉班视之,诚瞠乎其后”。[4]条件差,艺伎简陋,又兼被禁,花鼓戏要不断进入城市,也只能“一叹观止”。
湖南的官府,军警的“法令”,都曰“禁止花鼓演戏或采茶戏”。为了谋求合法性,花鼓戏进城之始,就只好打着“楚剧”的招牌。楚剧,乃湖北省的地方剧种,原称黄孝花鼓或两路花鼓,清中叶传入武汉后,改称楚剧,大约是取古楚国之剧而称,故艺人也把湖南花鼓戏亦称“楚剧”。如1927年邵阳花鼓戏以何银尘为首组班远征武汉,称为“湖南宝庆楚剧班”;1947年以何冬保、胡华松为代表的西湖艺人来长沙,合汇长沙艺人钟瑞章、段六生等,以“长沙楚剧改进社”之名,联合同业公会才获许可准演,得以在“绿萍书场”演出。长沙的《晚晚报》也曾有“昨晚在绿萍书场看花鼓戏《田氏世谋夫》”的报导。可以说,这也是“半台班”发展的一种具体表现。
花鼓戏之两小戏、三小戏虽很有特色,总因故事简练,设备简陋,“七紧八松九逍遥”的戏班只具“乡村本色”的装饰,均已不能适应城市观众之审美要求,即使现戏不被禁,也只能“一观而止”无法立根。自清末至共和国建立之前,各地进城之花鼓戏班,均改变旧习,增加大批“大本戏”,集中名角,组成二、三十人不等的班社,加之设法斡旋、力争,花鼓戏才能在某些城市演出。虽然不能长久,艺术的追求与提高,却加速了花鼓戏的发展成熟。
花鼓戏入城市演出,在1909至1949年这段时间。宣统元年甘绍盘《站上演花鼓戏》诗曾记岳阳事:“飞莺流转报春耕,站上如今谱郑声。极目可怜歌舞地,偷闲忙里咎和从?”宣统元年(1909)组班的邵阳“喜庆团”伍永班,集主要演员伍茂林(兼班主)、肖春秀、慈妹子、聪妹子(女伶)、炳伢子、伍水秀、唐九常、王志谦(祁剧艺人,旦行兼场面)等,其中女伶会唱花鼓戏,又兼唱调子。宣统二年(1910)该班曾在广西庆县、柳州、广东东昌、江西南昌、以及贵州等地演出。又,1927年,邵阳花鼓戏应武汉宝庆码头乡亲和商贾所邀,何银生为首组班,集20世纪以来邵阳东、南路著名艺人夏云桂、王伟云、王佑生、李鸿钧、罗林生、廖玉胜等20余人,排练《张公百忍》《七姐下凡》等一批整本戏,演于武汉新市场“二书楼”戏园,公开售票达半年之久。
省会长沙,曾有以钟瑞章、段六生为首的花鼓戏班,但只能演出《小姑贤》《蔡坤山犁田》等小型,虽能躲过官府禁戏,也因条件差,营业不佳而被迫停演,因此就有姚吾卿两次去西湖搬请艺人之举。1947年,以何冬保,胡华松、张汉卿、姚吾卿等十多人,应邀来长沙会令钟瑞音戏班,并整理出《三元记》《韦龙桥》《曹安殺子》《田氏谋夫》等大本戏,才得以在“绿萍书场”演出达半年之久而不衰。
这个时期,湖南的各种花鼓戏,都在做了充分的艺术准备之后,着眼于城市演出,并向邻近省份渗透,开拓新的活动地区,加强艺术交流。诸如零陵花鼓戏的“王世发乐昌传艺”、“四妹子连州扎根”、“冯初学恭城组班”;衡州花鼓戏经茶陵过界化垅,进入江西莲花、永新;岳州彭瑞生率花鼓戏班去湖北通城传艺并落户,形成咸宁“提琴戏”;邵阳肖顺生组班到闽西演出;以及长沙、常德花鼓戏同江汉本源花鼓戏艺术交流等等。这样,不仅花鼓戏本身得到了较大发展,也对使花鼓戏城市化的活力得以不断激发。
(二)融汇与规范:花鼓戏城市化的推进
在城市受到挤压,回到农村,再在农村中实现涅槃,对花鼓戏的发展来说,这是花鼓戏发展历史进程中的螺旋上升过程。“半台班”时期及以后,城市化的推进过程,就是花鼓戏的合流与规范的过程。
一方面是各路戏剧和班社的合流。花鼓戏曾有俗谚:“十里不同调,五里不同言”。它原形成于民间,以当地民间歌舞为基础发展。活动范围又局限于本乡故土,自然会形成多种风格,多种色彩。两小戏、三小戏时期基本上保留着原始风貌,因而形成不同的路子。剧种形成之后,各路子的艺术特点也还是长期存留。“半台班”以后,借助地方大戏发展,吸收借鉴了较为统一规范的戏路与表现技艺;音乐与伴奏(含乐队、乐器),特别是舞台语言的逐渐统一,向相近的大戏剧种靠拢,促使花鼓戏各路会流。邵阳的南路、东路、西路,光绪末年合流于邵阳市,成为统一的邵阳花鼓戏;道州调子与祁阳花鼓灯合流于零陵开始之为零陵花鼓戏;常德的沅水河与澧水河合称“喀喀调”即常德花鼓戏;岳州“小戏”(小丝弦)的岳阳、临湘两路调艺术上大同小异,也统称为岳阳花鼓戏;湘中地区的益阳、宁乡、西湖(南县、华容、安乡)、湘潭、醴陵诸路,虽然艺术上有较显著的特点,也同与长沙官话为统一的舞台语言,又流行于长沙府辖地,与湘剧共组“半台班”,今也统称为长沙花鼓戏;至于发生发展于衡州府辖区的花鼓戏,虽有语言的差异,衡阳马灯曾称衡阳花鼓,衡山花鼓灯也叫横山花鼓戏,也因声腔相近、同与衡阳湘剧共现,故统称为衡州花鼓戏。
另一方面是舞台语言的逐渐统一。舞台语言的逐步统一,有赖于地方大戏的艺术交流。相同流行地域的地方大戏与民间小戏,又常以该地的方言、官话为基础进行规范,也就说它们有共同的语言基础。弹腔兴起,虽有湖广音韵的别韵,但咬字仍保持了乡音的特点。因而有湘剧的“湖广韵、长沙字”;祁剧的祁阳方言规范的“单双空实”;武陵戏的“常德府前高山巷”(常德官话)语言咬字行腔。
这些传统特点,均被相关的花鼓戏剧种吸收。因此,湖南的六种花鼓戏舞台语言分属于湘语系和北方语系。其相互关系如下:长沙花鼓戏与湘剧:“长沙官话”(湘语系,湘方言的提炼);常德花鼓戏与武陵戏、荆河戏:“常德府与澧州官话”。(北方语系,西南官话的提炼);岳阳花鼓戏与巴陵戏:“岳州官话”(北方语系、湘北方言提炼);衡州花鼓戏与衡阳湘戏:“衡州府官话”(北方语系,湘南官话提炼);邵阳花鼓戏与祁剧:“宝庆府官话”(北方语系,湘南官话提炼。邵阳花鼓以祁剧语言为基础,吸收邵阳语言规范);零陵花鼓戏与祁剧:“永州府官话”(北方语系,湘南官话提炼。零陵花鼓戏以祁剧永河语言为基础,吸收零陵语言规范)。
舞台语言的规范化相对统一,各路花鼓戏艺人渐可相互搭班或共同组班;戏班活动也不拘于本乡故土;花鼓戏也就更能多方吸收、纵横借鉴,丰富传统加速发展,逐渐改变了“五里不同音”的旧限。如初建于清光绪年间的衡山“云开班”,就曾辗转衡山、湘潭、攸县、茶陵、安仁以及赣西的宁冈、莲花等县,20世纪20年代还到常德、华容等地演出。就是省会长沙,至1948年也曾有湘潭班、宁乡班、西湖班、益阳班、湘乡班、浏阳班等挂牌演出。彼此交流切磋艺技,相互吸收,取长补短,使花鼓戏的城市化进程加速。
还有就是声腔的规范。促进各路花鼓戏的艺术交流,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声腔的规范,包括结构形态的规范和曲调的筛选。花鼓戏的唱腔源于民歌、灯调,相应的声腔结构也是顺其自然而发展的。因而,客观地形成了湘南以调子腔为主,湘北重打锣腔,川调则为共同声腔。很明显,湘北为故楚地,“楚人好巫”,具有巫歌的特点,所以打锣腔为重;湘南古为百越,“调子随着狮龙舞”,故侧重为调子腔。以“川调”为共同声腔,是取其结构上的优越性,适应城市化的需求以及更广泛的表现需求。
(三)广采与博纳:花鼓戏城市化的深入
如果说,“半台班”的形成,除了在戏剧程式、戏剧语言等方面实现,直接催生了花鼓戏的城市化进程之外,那么,“半台班”时期及之后的历史时期,花鼓戏剧目及其表现内容的广采和博纳,则使花鼓戏城市化的进程进一步深化。
湖南花鼓戏的传统剧目,据1982年修订的《湖南地方戏曲传统剧目总册》录花鼓戏511出。这些剧目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中逐渐积累的。它是群众的集体创作,艺人代代相传并在艺术实践中增删。原以生活故事和民间传说为主,诸如《刘海戏蟾》《小姑贤》《访友·送友》《蓝桥会》《七姐下凡》《桃花洞·打刁救母》《湘子传·化斋·服药》《张古董借妻》《张广达上寿》等。
“半台班”以后,剧目题材有了较大的变化,它广为吸收、移植,不少历史故事的戏也占据了花鼓戏舞台。比如《孟姜女·池坊洗澡·道寒衣笑城》《秦三枚》《三元记》《芦林记》《清风亭》《葵花井》《孟日红割股》《柳毅洞庭传书》《东川寻夫》《黄金塔》《芦花休妻》《骡马桥》《张公百思》《合银牌》以及《宋江殺惜》《打仓救主》等等。内容包括了忠孝节义、才子佳人。这其中有的是话本、唱本的改编;有的直接源于“大戏”,或是高腔剧目的移植;也有弹腔剧目的改编;还有随打锣腔传入的清装戏《殺蔡鸣凤》《渔纲的扇江》《喻者的私情记》等;自然也有不少“提纲戏”(即搭桥戏),如《互车篷》《百鹤图》《七屠花楼》等等。如此看来,在“半台班”时期及之后,花鼓戏的题材既保留了之前的乡土生活内容,也开始有了适合城市市民和文人情怀的内容。
当然,城市化的进程,意味着内容的多元和广博。来源这样多,题材如此广,自然也带来了内容上的良莠并存。花鼓戏中也确有一些内容与表演均不健康的剧目。如色情低级的《黑手嫖院》《十八摸》《私怀胜》《瞎子闹店》;恐怖凶杀的《杀蔡鸣凤》《田氏谋夫》《大劈棺》及宣扬封建迷信、宿命论的《经堂变牛》《朱氏割肝》《张公百忍》等,特别是色情低级的戏剧内容与表演,所以,这又与其被禁有不可避免的联系。因此,花鼓戏的发展,着实是充满着矛盾与发展规律的一部精彩历史。
[1] 自龙华. 湖南戏曲史稿[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1988: 276.
[2] 刘松培. 关于新泰班进长沙演出的若干历史考证[C]// 湖南花鼓戏论文集.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4: 26.
[3] 卓之. 湖南戏剧概观[J]. 剧学月刊, 1934(7): 23-28.
Time Behavior:As a Kind of Modern State of Local Opera: Taking SeniorTheatrical Troupe of Hunan Flower Drum Opera for an Example
ZHOU YongLIU Xinao
(Department of Music, Hunan City University, Yiyang, Hunan 413000, China)
The Senior Theatrical Troupe is a special artistic form a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tage of Hunan Flower Drum Opera.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enior Theatrical Troupe witnesses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of the Flower Drum Opera which is wandering between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Under the activity and passively artistic innovation, the Flower Drum Opera achieved organic fusion with local drama, it achieved innovation of performance form and improved the structure of drama which gave birth to the factors of urbanization. Subsequently, the Flower Drum Opera opened its urbanization roa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Senior Theatrical Troupe. Through its innov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reaking the barrier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of artistic ontology; and its fusion and specification meeting the expected of multi-level audience; through its extensive and strong inclusivity, also making it step into city residents and literati feelings on the basis of rural life.
senior theatrical troupe; flower drum opera; art; urbanization
(责任编校:彭 萍)
J 805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6.06.001
2096-059X(2016)06–0001–05
2016-09-18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B015);湖南城市学院创新团队项目(湘城院发[2014]12号)
周勇(1966-),男,湖南益阳人,教授,主要从事高等音乐教育与地方戏曲研究;刘新敖(1981-),男,湖南娄底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文学及艺术理论与批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