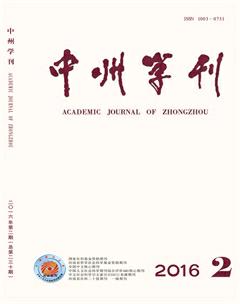南明阁臣王铎“贰臣”命运源释∗
翟爱玲
南明阁臣王铎“贰臣”命运源释∗
翟爱玲
摘要:在明清易代之际,身为南明弘光政权内阁大学士、位居次辅的王铎,因率众归降于清朝而成为后世数百年来人们讥议不已的贰臣。王铎之最终成为“贰臣”,既与其坦荡简易、不设城府的个性、久耽于文学艺术而注重现实感受、疏于政治理性的思维倾向有着直接关系,更与其在晚明腐败政治环境中日益感到人生追求和政治信仰迷茫有着紧密联系,而清初政治上压制和利用明遗臣的特殊需要则最终将他作为牺牲品而置于“贰臣”境地。
关键词:王铎;贰臣;文艺气质;政治人生
王铎是明末清初著名的书画大家和文坛巨匠。同时,在明、清两朝他都曾官至礼部尚书,在南明弘光政权中则官至大学士、内阁次辅。顺治三年(1646)五月,清军压境、进逼南京,南明弘光皇帝与首辅马士英等人仓惶出逃,王铎及诸多公卿大臣则选择了归降。由此,时人及后世对其一生毁誉纷然。或言其降清乃大节有亏,人品可鄙;或赞其人品、书品、学品之高。那么,应如何理解王铎的人生命运?个人品性与社会政治在促成他走向“贰臣”过程中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进而涉及到今天评价历史人物时如何把握立场的时代性转换?要理清这些问题,解开百年来聚讼争执的症结,还需要将王铎这一矛盾统合体的典型人物放置于其个性与社会的动态关系中进行考察和认识。
一、家族传统与天赋禀性
王铎,字觉斯,明万历二十年(1592)出生于河南府孟津县一个普通中小地主家庭。虽然父祖辈多以庠生从事举业,但仅有祖父之长兄王价曾中过进士,故王家在官宦阶层并无深厚根基。在经济生活上,王家富裕时曾有田二百亩,而贫时仅得十余亩。王铎年少时,有时“不能一日两粥”①。这种生活状况使王铎自幼便树立起刻苦学习,以图通过科举改变自己和家族命运的观念。
王家祖祖辈辈以耕读传家,且历来多有负才气与个性者。其六世祖王德“习风角奇门,傲睨,择人而友,不与常人交”②;五世祖王智“好言边事”,“夜燃灯读孙吴、《汉书》”;③高祖王鼎,“善大书,暮年临池,不见老人惫气。尝揶揄某富者,里中强暴侮公,公命僮键门匿避,不口舌争也”,“大书‘忍让’字,传之后”,④他因此得号“忍庵公”;王铎的祖父王作既负才气,又为人放达,其“读书一过终不忘,好古文辞”,“家道中落,踞弛不问生产”;⑤父亲王本仁,则“为人慈怛宽仁,不喜言人过”⑥。
出身于这种家族的王铎,在个性上颇有父祖之风。一方面,他性情宽恕而又有意气之禀性。他“为人外宽内毅,与人坦易而心意湛深”⑦。年少时读书之外,又喜骑马、击剑、游山。“少年学书剑,有心拥八方,男儿志弧矢,谈笑安九州”⑧,就是其青年时代意气风发的写照。另一方面,他自幼天资聪慧、刻苦好学,“五岁入小学,一目十行,悉记忆”,“三代秦汉经史,宋南北典籍,初盛中晚之篇,钟张羲献之体,无不愽通淹贯”。⑨“嗜坟索,入山寺,下帷讲诵,凡上古三代书无不究其指要。”⑩
王铎的这种个性对其从事文学艺术创作,无疑具有极大的助益。文艺的思维与表达方式需要意气风发,需要感悟与直抒胸臆而不是谨守规矩。王铎的个性特征恰是如此。青年时期,他虽然也走着先辈以科举求功名的老路,其志趣却以文史书艺为主。他喜好诗文书画,“以书为性命”,且毕生以“诗文托为命”,由此奠定了其“文艺人生”的基调。有这样的追求与天分条件,就不难理解他后来在文学艺术上能够取得辉煌成就。明人谈迁说他“耽翰墨、工诗,五言诗至万首”。钱谦益则从学、才、品三方面高度品评了他的书法艺术。这些赞誉虽不免有出于朋友之谊的恭维,却也与事实相去不远。
二、“艺术人生”强化文艺气质
王铎长期肆意于文学艺术领域,使其最终成为一代诗文大家和书法巨匠。而这个过程,对其个性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现实主义文艺风尚的追求对其率性洒脱、不守规矩的个性具有显著的强化和型塑作用。
大凡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以关注和反映社会生活现实、强调和渲染人的“真情实感”而取胜。王铎的诗文正是以其现实主义基础的率性、直捷、真实而见长。他有不少诗文描述明末社会动荡带给民众的苦难和官吏的贪酷、暴虐。如:“平岁不可得,年年经乱离。饥岁人相啖,枕死孰能支。诸吏若虎寇,攫取良不赀。骨髓尽为竭,追呼昼夜驰。蠭午聚探丸,操戈效赤眉。”有时其批驳的笔触还直指朝廷大僚和皇帝:“中枢多穴隙,誉至掩即墨。”“其心非为国,周岁谋颇密。欲以袭众人,虚徼赉功业。”“孤注巧护饰,异己为皋訾。”这种语句出自时任朝廷要职的王铎之口,决不单是出于胆略和锐气,在很大程度上还与其率直与富于意气的个性相关。这种个性,在其为官处事中表现得更为充分。天启年间,“魏珰窃柄,啖公纶扉,授心腹以十幅,屏语公曰:‘书此,揆席可立跻’”,他断然予以拒绝;又“时大珰窃太阿,睥睨朝士,兴大狱,缮《三朝要典》”,他作为翰林官与同年好友黄锦、郑之玄相约不与阉党合作;崇祯年间,兵部尚书杨嗣昌欲与侵边的清军通款,王铎数上疏劾之,以致杨嗣昌因嫉恨而鼓动皇帝要对他行廷杖。王铎不仅对宦官、权臣如此,甚至在皇帝面前也不知顾忌。崇祯十一年(1638)经筵秋讲中他借讲《中庸·唯天下至圣章》之机,“力言加派,赋外加赋,白骨满野,敲骨剥髄,民不堪命,有司驱民为贼,室家离散,天下大乱,致太平无日”,由此触怒以加赋筹饷为急务的崇祯皇帝。
由此可见,长期肆意于文学艺术的“真情实感”,使得王铎的思想意识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超越现实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严格规范而去感受、体会和反映人性的一般意义。因此,当社会民众生存秩序的追求与现实政治统治秩序的维护发生冲突与矛盾时,当诗人、文学家关乎生命现实的苦痛与当朝大臣忠诚于堕败政治的悲哀并存时,作为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更显文艺气质的王铎自然更倾向于顾及前者,这种不同于一般政治活动家的观念意识恰是导致他较之于一般官员欠缺那种官场“技能”的重要根源。
其二,长期从事文艺创作中对情感、情绪的极大调动与激发,使王铎在思维方式上更多地表现出感性化倾向,而弱化了自我控制的理性意志力。
王铎更倾向于感性思维的特点,在对《礼记》的研究与学习中就已表现出来。作为求取举业功名所选择的本经,王铎对《礼记》所包含的儒家政治理念与思想理应有深刻理解与认同。实际上,王铎的习《礼》与现实中孝亲、睦邻、和友等生活实践之间确实有着实际的联系。吕维祺就说:“觉斯道义砥躬,笃于孝友。”他对家人、亲友也充满着情感与依恋,“昆弟同居四十年,无逆色,无间言”。然而他并不善于、也不喜在理论上深究“礼”之“大义”。他的姻亲吕维祺,他的同年好友黄道周、倪元璐,同样都是在诗文和其他艺术领域有很高造诣和成就者,他们或以阐释四书五经之著述载誉学术领域,或以坚持鲜明而执着的政治追求闻名于朝臣之中。相形之下,王铎从学术理论中所获得的儒家伦理政治理念显然不够深刻、坚固。因此,他在政治斗争漩涡中常表现出一种摇摆不定的倾向:一方面,当身边和周围人表现出刚正节义精神时,王铎的正直禀性就会得到鼓舞与激发而能够做到持正敢言。如前述天启年间他与黄锦、郑之玄请辞修书之任,他对阉党的抵制,崇祯年间对杨嗣昌的弹劾,等等,都与当时朝中许多廷臣的抗争,尤其是像吕维祺、倪元璐、黄道周这些与他关系密切的官员富有刚正气节的表现联结在一起的。还有如规谏福王“停织造,止选淑”,实际上也表现出王铎自身一定程度的“守介”。
另一方面,王铎没有像吕维祺、黄道周等人那样从读书经历和现实磨练中达到对儒家一贯倡导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生境界的完全认同和接受。他仕政期间的一些正直表现,更多出于自然禀性,而非理想与信仰之坚定。因此,在遇到艰险困境时便会“稍稍易之”,或选择消极逃避,或随波逐流。崇祯十一年冬,清军大举入寇,京城戒严,一时人心惶惶,眼见朝廷情势日窘,他便生退隐之心,希图追求一种山居乡野“亦花亦竹,无是无非”,“亭皋木落,对之怡怀;峰首箫闻,乐而忘死”的平和而闲适的生活。事后局势稍定,他也就能苟安于现状。弘光初,因高弘图、姜曰广等人同在阁,王铎也颇有振兴之想,曾“力言蔡奕琛、张捷等不可用”,“及奕琛等秉权,意稍折”。可见,王铎为官处事中确实易于受周围环境之影响而缺少自我的定见与坚守。
综而言之,王铎那种坦易、率直的个性和务实、感性的思维特点,对他从事文艺创作显然是一种极为重要的优势条件。而在其以文艺为人生追求的经历中,这种个性和思维倾向又不断得到固化和增强,由此可以预见其文艺人生的美好前景。然而,身处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政治舞台上,这种个性特色并未促成他在政治上走向成功,却带来相反的效果。
三、政治环境影响政治信念
虽说王铎个性上显得有些缺乏定见与毅力,行事又较为务实,但对于像他这样长期受清流之士影响、身居朝廷权位中枢、盛名远播,且完全能够预计到降清之于个人名节的深刻影响的人物来说,作出这种选择,其更根本、深刻的缘由,则是其政治理念与人生追求的日趋迷茫。而这正是晚明黑暗政治影响的结果。
明代自中期以来政治已日益腐败,天启时期,朝政委于权臣与宦官,致使魏忠贤专擅、党争激烈、朝政浊乱。至崇祯后期,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矛盾更加激化,民众暴动,清军入寇,最后导致皇帝身死,北京失陷。南明弘光政权初立,曾受惠于王铎的福王朱由崧登上皇帝宝座,并用王铎入阁辅政。这使王铎颇以为有振兴之机。他曾作《誓关帝文》表示将“无论事之难易,一一衡诸道于心”。然而不久,他就发现自己又是一腔热血遭遇兜头冷水。马、阮秉权,“朝政浊乱,贿赂公行”。而弘光皇帝丝毫无意于修治政事,却是为虎作伥。君昏聩于上,臣党争于下,马、阮集团与东林复社等清流官员陷于无休止的政治杀伐之中,不到一年间围绕所谓“逆案”“顺案”“大悲案”“童氏案”“伪太子案”等一系列事件争斗不已。
在这种情形下,他渐对朝廷政治产生动摇、怀疑、无奈,进而至于反感与厌恶。弘光初年他在一份奏疏中说国家之败坏皆缘于朝廷大臣之腐败,而“臣受此任,居于纶扉,亦仍旧之泄沓隐默木偶与?必欲改弦而更张之以见太平与?”后来在《诘甲申事》中借与一位北来老人诘问北都之败根由而发出对“北都者,平日谋臣之高爵厚禄者画一策乎?武臣之眷注授者出一力乎?”的质问,甚至还明确提出了“上剥下,下亦剥上也”。“故君择臣,臣亦择君,孰肯以其身徒劳于是非黑白混淆之世、性命日侍于汤镬之前与?”的观点。
在这种思想认识基础上,很难设想王铎对明王朝的信仰与忠诚能坚守到何种程度。清军获福王,执至南京,“令诸旧臣一一上谒。诸臣见故主,皆伏地流涕,王铎独直立,戟手数其罪恶,且曰:‘余非尔臣,安所得拜?’遂攘臂呼叱而去”。或许这就是孟子所谓“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四、难以逃脱的“贰臣”境遇
在明清鼎革之际,王铎最终选择降清确实具有其个性与思想认识发展变化的一定基础。但他的“贰臣”命运实际上也是那个时期社会政治直接附加于他的。
首先,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的制度,特别是明代实行的科举取士制度将本应在艺术上显示其人生价值的他推到了政治之路上,并使他成为晚明朝廷权力中枢之一员。从此,在人生的舞台上,他避开所长而用其所短,演出了一场“政治人生”的悲剧。
在当时社会体制中,一般士人除了科举入仕,别无他途可以改变自身及家族命运、进而实现追求个人生活与价值的目标。同时,封建科举取士本身就是为官僚政治输送人才,登进士入仕者,必当以政事庶务为职事并以其处事能力与政绩为晋升之依据。王铎为人简易,自放,偏向于感性,又富于文艺气质,这些特点常常使他在官场中的为人处事显得不合时宜,以至于使人怀疑他的能力。弘光时期,他在内阁票拟时常用古典文学中的“尔”字称呼大臣却不顾忌所谓朝章规矩。一日,姜曰广对他说:“外人以‘尔’同内臣呼,如何?”他极为生气地回答:“《书》言:‘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后’,亦内臣耶?”并为此在当日票拟用“尔”字尤多。李清在《三垣笔记》中还记载说:“王辅铎工于诗,然票拟非长,拟旨或四字,止曰‘烦聒可厌’;或单句,止曰‘入监者何其太多?’何侍御纶疏陈文体,票有‘鬼语四六,不雅不奇,一味汉人胡语’等句,皆笑柄也。”这种情形,有时还会带来较严重的后果。如“法司奏大辟,辄除其罪。尝作奏误书‘皇下’,再被诘”,而当高弘图去职时曾说“大臣道不行,则去,毋俟人弹文也”,嘱咐他适时引退,他竟骇然不明就里。
据实而言,无论从王铎的个性还是思维倾向、思想意识来看,他应当更适合于“艺术人生”之路。他自己也曾表示过:“我毋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从政使他成为一个“写字的尚书,作画的阁臣”。明人谈迁曾说:“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为宰相则不足,孟津是也。”又称“铎本文士,处非其任”,这种评价应是公允而客观的。不过,谈迁也仅是从王铎个性出发看到了他不适合担任朝廷要职的特点,却没有也不可能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学而优则仕”对文人人生道路选择的制约。
其次,王铎最终陷于“贰臣”境地,又直接缘于清初对明朝官员利用、控制与打击的特殊政策。
清军入关之前势力日益发展壮大,其取明朝而代之的目标与意图已十分明显。然而,为了减小阻力,清初实行了旨在诱降明臣,尤其是军官和知识分子的政策和措施。摄政王多尔衮一入关即宣称:“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所诛者惟‘闯贼,’师律素严,必不汝害。”进入北京后,他又对崇祯帝及皇后实行国葬。此举蒙蔽了众多明官、明将。官僚士大夫中,除少数人抱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明朝正统观念而坚持抗清守节之外,其他大部分或出于自保身家性命,或出于对农民起义的敌视,选择归降。王铎及其兄弟子侄即属于后者。
早在崇祯年间,他们曾几次与农民军进行过战斗。相反,清军入中原,王铎之兄弟、姻亲大都归附之而少见有抵抗者。就在清军进逼南京城,弘光朝臣们在商讨如何应对之时,清军中就有王铎的弟弟王镆。显然清军的这种安排是有目的的,而王铎最终降清也绝非一时动念。所以,王铎降清之际就已知自我的“大节有亏”,尽管在清朝还能“拜官如旧”,但他却“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八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歌间作”。张缙彥说他在仕清的七年里,“溷迹牛马,寄情声歌,衣垢不濣,病不循医,桎梏其身,而怀御风行吾余生哉!”王铎这种自感愧辱和消极的人生态度,实际上正是背负社会舆论对其造成强大压力的反映。
应当说,清初实行的诱降、拉拢和利用政策,确实发挥了很大效能,它不仅迅速壮大和扩张了清军势力,而且还起到了迷惑南方抗清力量,集中优势兵力对付农民军的战略效果。然而,当清朝的统治渐趋稳定,民族冲突有所缓和、淡化,代之而起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时,清王朝政治上更需要“崇奖忠贞,所以风励臣节”。于是,便有政治策略的巨大转变:褒奖忠义、鞭斥失节。那些为效忠明朝而战死、自杀、被俘赴死者,都被赐谥、立传,而当年归降者则以“明臣而不思明,必非忠臣”的标准被打入另册加以鞭挞与声讨。
乾隆四十一年年底,刚刚完成《胜朝殉节诸臣录》以示对忠节者的褒奖,乾隆便诏令国史馆在所修国史中另列“贰臣传”,将明末归附官员依其表现分为甲、乙、丙三编。尽管这时王铎已故去多年,乾隆则称:“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将其列入“贰臣传”则“使不能纤微隐饰,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王铎等降清官员皆以“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腼颜降附”而被指斥,不复为“完人”。王铎被列入“贰臣传”乙编,并被削夺顺治年间所谥“文安”之号,以官方名义正式宣判了他“政治人生”的彻底失败。
这种富于狡诈的前后政策的灵活变换,昭示出清初诱降策略的暂时性、欺骗性。为了强化和稳固自身的统治,清统治者在继承以往封建伦理政治基础上更加强化了对忠孝节义的倡行,并以严酷的政治手段来实现这种强化,其结果必然是以牺牲某些个人为代价,王铎便是其中之一。
由于“贰臣传”产生的广泛影响,自乾隆年间以来,从官方到民间对王铎认识与评价大都将其归之为品行“鄙劣”之列,并因此对其曾在文学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也持鄙弃态度。清代纂修《四库全书》,将王铎《拟山园集》《拟山园文集》等尽行禁毁。与此同时,各种官私修撰中凡涉及他的痕迹也尽行删削之。虽然清代学者王弘曾充分肯定他早年的书法成就,却也说他“晚年为人,略无行简,书亦渐入恶趣”。可见,沦入“贰臣”之列也使王铎的文学艺术成就在人们眼中大打折扣。虽然这种状况至近代以来有所改变,但对其政治人生的评价,“汉奸”“败类”与“无德”“失节”之论仍长期伴随着他。
四、结语
我们通过以上对王铎“贰臣”命运形成历程的考察与分析,可以获得这样的认识:
首先,王铎是他所处封建社会政治的牺牲品。“学而优而仕”的制度不但不能提供给他“艺术人生”的正确出路,反而将他推向其并不擅长的政治舞台;晚明恶劣的政治环境又不断地销蚀了他原有的那些持正的禀性;清前期的专制政治出于统治需要肆意改变对他“政治人生”的评判。这三者便是最终造成王铎“贰臣”境地的总根源。
其次,明清鼎革之际王铎之选择降清而成为“贰臣”,是受其个性意识与思想认识水平的影响。他在文学艺术与心学思潮影响下的思想认识,既未达到如明末黄宗羲等人对君主政治认识的深刻程度,个性倾向上也不及于明中期李贽那样立足于体制之外对社会政治的抵制与疏离,更不同于与他交往密切的众多同官好友对儒家传统道义的秉持,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对清朝的降附,自觉踏上了一条政治的不归之路。
大千世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事业的领域空间。诗人与画家需要灵感的火花和浪漫的情愫以及肆意挥洒的思维,但政治家需要具备的是坚定的信仰、果决的胆识与无我的追求。王铎错误地选择了人生发展的道路,是他身陷“贰臣”命运的始端,是其主观世界的客观必然。
注释
①王铎:《拟山园选集·文集》卷七十四《祭陈具茨母舅文》,顺治十年刻本。②③④⑤王铎:《拟山园选集·文集》卷七十六《王氏谱》,顺治十年刻本。⑥⑦张缙彥:《依水园文集·后集》卷二《王觉斯先生传》,顺治十二年刻本。⑧王铎:《拟山园选集·诗集》第一册五言古卷三《愤》,台湾学生书局,1970年景印顺治江苏刊本。⑨《(康熙)孟津县志》卷三《名硕》,中国方志丛书本,成文出版社,1976年影印本。⑩张缙彥:《依水园文集·后集》卷一《觉斯先生家庙碑记》,顺治十二年刻本。吕维祺:《拟山园选集·序》,顺治十二年刻本。王铎:《拟山园选集·诗集》第一册五言古卷六《与弟》,台湾学生书局,1970年景印顺治江苏刊本。谈迁:《枣林杂俎·仁集·王铎》,“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8页。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中)卷三十《宫保孟津王公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105页。王铎:《拟山园选集·诗集》第一册五言古卷三《伤乱》,台湾学生书局,1970年景印顺治江苏刊本。李清:《三垣笔记·下·弘光》,第二册,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43、117、42、42页。王铎:《拟山园选集·文集》卷九《臣疾复发放归事》,顺治十二年刻本。王铎:《拟山园选集·文集》卷十《誓关帝文》,顺治十二年刻本。《明史》卷三百〇八《马士英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7941页。王铎:《拟山园选集·文集》卷十《三辞成命以全恬退》,顺治十二年刻本。王铎:《拟山园选集·文集》卷十八《诘甲申事》,顺治十二年刻本。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27页。《孟子·离娄》:任大援、刘丰注译,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4页。《清史列传》卷五《范文程》,中华书局,1987年,第258页。《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卷首《谕旨》,孔昭明:《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6辑,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第2页。萧一山:《清代通史》,商务印书馆,1932年,第739页。《清高宗实录》卷一〇二二“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庚子”条,中华书局,1986年,第709页。张升:《王铎著述考》,《河南图书馆学刊》,2002年第1期。王弘撰:《山志》卷一《王宗伯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13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2页。
责任编辑:王 轲
【中国共产党章程研究专题】
Expounding on the Roots of the South Ming Cabinet Ministers Wang Duo′s "Betrayer" Destiny
Zhai Ailing
Abstract:In the occasion of the Ming-Qing′s regime changing,as the second minister of Hongguang Administration of South Ming,Wang Duo led people to surrender to the Qing Dynasty.Thereby,he became "Betrayer" who was drubbed for a number of years.Wang Duo′s destiny was really derived from his personality,but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corroded his life and political beliefs,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fickle policy depended on its′interest eventually placed him in the "Betrayer" situa⁃tion.
Key words:Wang Duo;betrayer;literary temperament;political life
作者简介:翟爱玲,女,洛阳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洛阳 471023)。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明代洛阳地区文化发展的地域特征及其社会影响”(2015-JCZD-011)
收稿日期:2015-10-20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2-01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