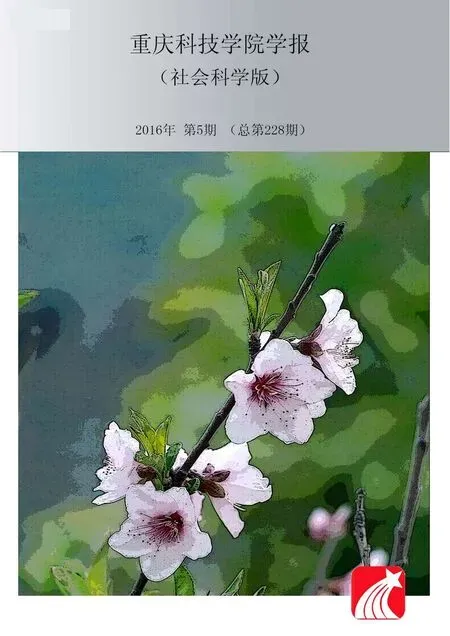游荡的灵魂
——叙事学聚焦理论下罗伯特·潘·沃伦诗歌研究
何欣
游荡的灵魂
——叙事学聚焦理论下罗伯特·潘·沃伦诗歌研究
何欣
摘要:聚焦是叙事学的核心概念。将聚焦理论用于对沃伦的诗歌研究,提炼出其诗歌“游荡的灵魂”的独特聚焦类型:作为诗中参与故事的重要叙述者;作为诗中观察故事的主要叙述者;作为诗中参与和观察故事的叙述者。这种聚焦不仅有利于主题意义的表达,折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而且有利于潜藏叙述对表层叙述的颠覆及不同时空的并置成为可能,丰富了沃伦诗歌的意蕴和表达。
关键词:聚焦理论;沃伦诗歌;“游荡的灵魂”
20世纪美国诗歌大放异彩,吸引了众多关注和研究的目光。罗伯特·潘·沃伦的诗歌作为其中的优秀代表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沃伦一生共发表了500余首诗,推出了19本诗集,其中《应许:诗1954—1956》和《此时与彼时:诗1976—1978》使他两次获普利策诗歌奖。此外,他还获得了雪莱纪念奖、西德尼·希尔曼奖、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奖、美国国家图书奖、博林根诗歌奖、哈里特·门罗诗歌奖、联邦文学奖等多项殊荣,并最终于1986年荣获美国首位“桂冠诗人”称号。沃伦的诗歌不仅得到官方认可,还像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一样获得了民间的喜爱,故其生前就拥有不少研究者和爱好者,在其去世后,美国更是掀起了新一轮沃伦研究热潮,有大量论文和专著问世。研究角度涉及新批评、新历史主义、历史编纂学、弗洛伊德心理学、女性主义和性别学、酷儿理论、非裔美国人研究、政治学和伦理学等[1]。国内学界对沃伦诗歌的关注则主要体现在他的渗透哲学观、时间观、南方诗人的身份等方面,尚未有对沃伦诗歌聚焦方面的专门研究。因此,本次研究拟以叙事学中的聚焦理论为基础对其诗歌进行解析,作为对新世纪“理论复兴”和“美学转向”产物的“新形式主义”的一种呼应。“新形式主义”关注形式问题,既从传统形式主义理论中借鉴阐释方法,同时又提倡语境批评,揭示形式蕴含的社会历史意蕴[2]。此次对沃伦诗歌的研究也包含这2个方面。
一、聚焦理论及其对沃伦诗歌的适用性
视角(perspective)、视点(point of view)、聚焦(focalization)——这些现代文论常用词汇虽外表各异但内核一致,皆指叙述故事时观察的角度[3],常被用来分析小说的创作,是叙事学的核心概念。正如珀西·卢伯克所说:“小说技巧中全部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从属于视点问题,即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问题。”[4]但迄今为止很少有研究者用这种方法来探讨诗歌的创作。一方面由于“视角”真正走入学术视野源自对19世纪福楼拜创作的《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创作技巧的探讨,再经由亨利·詹姆斯及其追随者珀西·卢伯克和后继者韦恩·布斯、热奈特等的大力推动才拥有今天的地位,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以小说作为探讨的平台;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意义上诗歌的叙述者给人留下的印象都较单一化,多为显性或隐性的第一人称“我”(如舒婷的《致橡树》、惠特曼的《草叶集》中的大部分诗歌……)或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如泰戈尔的《飞鸟集》中的部分诗歌、兰波的《奥菲利亚》……),而令人觉得没有太多研究价值。虽然有一些研究者把聚焦理论应用于诗歌研究,比如对诗歌中视角变换的探讨等,但总体处于零星分散的状态。可事实上,诗歌一路发展走来,同小说一样多元而丰富,对于创作手法的创新在国内外现当代诗歌中比比皆是,聚焦的运用也不再仅仅是一种创作技巧的问题,而是拥有了更多可探讨的内涵,所以这种隐形的壁垒理应被彻底打破。
视角理论的发展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福楼拜与亨利·詹姆斯作为现代小说理论的奠基者,首先注意到了“限知视角”或“人物有限视角”并运用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卢伯克则是第一位系统阐释视角问题的文学批评家,他在1921年发表的现代叙事学之作《小说技巧》中将视点问题视为所有小说技巧的根本与关键,认为小说的不同效果皆源自作者对不同视点的选用,奠定了视点问题在叙事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他在视点理论上有开山之功,但没能注意区分“以谁的视角观察”与“以谁的声音叙述”,而这一点在布鲁克斯和沃伦1943年出版的《理解小说》中得到了厘清。后来,受结构主义影响,逐渐形成了所谓的结构主义叙事学,视点问题成为重中之重,不同角度的视点分类层出不穷[5]。有奥地利文论家斯坦采尔在《小说类型》中的3分法,瑞典文论家伯尔梯尔·隆伯格在《第一人称小说叙述技巧研究》中的4分法和美国文论家诺尔曼·弗里德曼的8分法等[6],共核都是根据叙述者的人称和参与方式来划分,比如“第一人称叙述观察者式”等。1961年韦恩·布斯发表了《小说修辞学》,这是关于视角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对视点、叙事者、隐含作者等作者干预阅读的种种手段进行了深入探讨,还指出小说中作者通过对视角变化的调节来控制读者的信息接受、价值判断和情感体验。1970年苏联出版的乌斯宾斯基的《结构诗学——艺术文本的结构与结构形式的类型学》一书明确提出当对视点表达叙述者(或隐含作者)的意识形态进行评价时,读者的主体性也在被建构着,即叙事是制造身份和意识形态主体的方法之一,彻底打破了文本的自足性而涉及文本以外的世界;他还将视点问题视为各类艺术文本的共性问题,不仅存在于语言艺术文本,也存在于造型艺术文本之中,拓展了视角理论的范畴。乌斯宾斯基论述了视点分为意识形态层面、话语层面、空间与时间的特征描写层面和心理层面这4个层面,阐释了不同层面视点的关系及结构共性问题。总之,他对视角理论的论述有了质的飞越。在后结构主义或后现代叙事学时期,对视点问题的探讨进入了整合或精细化阶段,比如1983年里蒙·凯南发表的《叙事虚构作品》就是对以视点问题为核心的叙事学研究成果进行初步综合的专著。其中的杰出代表热奈特在1972年发表的《叙述话语》和1980年发表的《新叙述话语》中对之前混淆“谁看”和“谁说”的术语“视点”提出了批评,并用聚焦和叙述来代替,这对“眼光”和“声音”的区别一目了然。而且,他还明确提出眼光的聚焦绝非单纯的感知问题,而是蕴含了思维模式、情感、立场和认知程度等[4]。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对视角问题的探讨大多是学科理论和方法交叉的结果,比如解构主义、心理分析、性别批评等,具有女性主义批评背景的米克·巴尔就是其中的一例。
聚焦理论对分析小说的有效性毋庸置疑,大量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就是例证。那么,聚焦理论是否适合对诗歌的分析,具体来说,是否适合对沃伦的诗歌分析呢?诗歌是否存在聚焦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与不变是否有特殊的意蕴当是衡量的基准。有诗歌专家提出“现代诗有一个强健的‘胃’,就内容而言,举凡生活的方方面面,诗人们都敢于吸纳进来;在形式上,叙事性、戏剧性、口语等因素作为亚体裁纷纷出现,诗歌越来越体现出某些综合性的特征”[7]。而传统诗歌中也不乏有聚焦存在变化且这些变化与不变有特殊意蕴的诗歌,这就为聚焦理论应用于诗歌研究奠定了可行性基础。具体到沃伦的诗歌,哈罗德·布隆姆在《罗伯特·潘·沃伦诗歌全集》的序言中称:“从一开始沃伦诗歌的典型模式就是戏剧—抒情诗(dramatic lyric),从诗人60岁后他把戏剧元素内化了,与时间较量、与文化和家族历史较量,尤其重要的是与自己较量……沃伦非常擅长讲故事,其叙述技巧修习自康拉德和福克纳,情感上则更趋近巴洛克式的而不是艾略特式的。”[8]在这段对沃伦诗歌的经典评价中,那些醒目的能指都提示了沃伦诗歌不同于一般抒情诗歌的特点,那就是富含叙述元素和操控技巧,且充满张力和变化,这给聚焦理论分析留有充分的施展空间。此外,沃伦的诗歌以反思社会现状与人类困境而著称[9],他选择的诗歌形式与历史社会语境相关联,而不仅仅是为形式而形式,这也使得聚焦理论的应用可解读出更丰富的内容。因此,以聚焦理论为基础来解析沃伦诗歌是恰当合理的。
二、“游荡的灵魂”:沃伦诗歌的重要聚焦
沃伦的诗歌以丰富的语言和想象、多变的风格和契合时代精神的书写而闻名。这从他在诗歌中对聚焦的运用就可见一斑。“游荡的灵魂”聚焦的使用不仅是沃伦诗歌的重要写作技巧和形式特点,也是他诗歌内容有机的组成部分,在反映其主题的同时,还是特定时代文化语境的一种折射。参考诺尔曼·弗里德曼根据叙述者的人称和参与方式来区分的叙述视角,“游荡的灵魂”的聚焦可分为3类。
(一)“游荡的灵魂”作为诗中参与故事的重要叙述者
沃伦约55年(1943—1953年有10年的诗歌空挡期)的诗歌创作,以前后诗风的2次明显转变为界可分为早(前20年,1923—1943年)、中(中15年,1953—1968年)、晚(后20年,1969—1988年)3个时期。《记得的野餐》①是其早期诗歌的一篇代表作,已然体现出沃伦诗歌对聚焦的灵活运用和特殊用意,是“游荡的灵魂”作为诗中参与故事的重要叙述者的典型例子:
那天,树叶、山峦、天空,
那么纯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它们的结构是如此和谐
如此纯洁,在它们面前我们所忍受的一切
都变得如儿戏般微不足道,
现在被搁置一旁,而所有令我们抓狂的
悲伤和恐惧也随之消失了。
这首诗开篇以第一人称复数“我们”作为参与故事的内聚焦叙述者出现,勾勒了从“我们”视角望去的绿树、青山、碧水、蓝天。大自然具备神奇的治愈功能,以造化的纯美、和谐消除了“逃逸”至此的人们在都市城镇生活的矛盾与不公。让“忍受的一切”变为“微不足道”,让“令我们抓狂的”也“随之消失”。卸掉了心灵重负的“我们”享受着与大自然的亲近,于是第2诗节中“我们”从大自然的观察者转为参与者,徜徉伫立其中——
我们伫立在如画的林木间:
琥珀色的阳光沐浴着树木,也沐浴着我们;
或许是那光如此沉静,
如此稳定,我们的肉体,
像镶在琥珀中的孪生飞蝇一般,
以完美的状态一动不动嵌在其中
笑傲时间那令人惊奇的跟踪。
第2诗节第1行沿用了传统的第一人称内聚焦叙述者,但视角从第2诗节的第2行开始有了变化,“我们”不再作为主语出现,转为宾语,而自然界的阳光成为了主语。此刻叙述观察的角度从第一人称的内聚焦转为第三人称的外聚焦,而实现方式就是主语和宾语位置的悄然置换。琥珀色的阳光既沐浴着树木,也沐浴着“我们”,“我们”成为了和树木一样的客体。接下来把“我们”描写成“镶在琥珀中的孪生飞蝇”的一段则更是神来之笔,强化了“我们”由看的主体变成被看的客体的感觉,和被端详的昆虫并无二样,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合为一体。
……
或我们是否已死,被阉割的我们
是空虚的,而我们最清澈的灵魂
疾驰而去,在静止不动的社会里
肩并肩、手拉手地游弋着那一度
我们,也,在其中徜徉的场景,
而我们现在继承了新的领地,即
爱的荒原,这片被遗失的地下国土。
诗歌的中间两诗节(略)在描述“我们”在大自然中游泳、嬉戏的一系列动作画面时,又切回第一人称内聚焦,以形成与之前林中静态画面的对比和跳跃;而在描述黑暗降临到大自然和我们胸中时又换成第三人称外聚焦,与之前阳光照耀树木也照耀我们相呼应,仍是表现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手段。到了第5诗节,叙述者背后的操控者则发挥了更大的效力,把叙述者的肉身直接阉割掉,将其变成“游荡的灵魂”,成为从生动的大自然回归麻木城市生活的人们的写照。此时,我们这些游荡的灵魂“肩并肩、手拉手地游弋着那一度/我们,也,在其中徜徉的场景”。正因为叙事者是以“游荡的灵魂”为视角,所以得以穿越时空,飞到曾经美好的家园,俯视那片曾经美好的土地变成现在这片“爱的荒原”。这种灵魂飞升飘荡、将不同时空并置在目光之下的内聚焦的特殊体验是沃伦诗歌的特点之一。再看第6诗节:
那时、现在:每一个都是对方的
纪念碑,包含着,死去的,对方。
或者灵魂是否就是一只鹰,展开
闪着微光的翅膀逃离视觉的路径,
向在这里的我们反射最后一缕光
虽然太阳已经坠落而黑暗也已临近
——那未知真理的高高的记录仪?
在此诗节中,前2行继续保持着“游荡的灵魂”的视角,将过去与现在并置,看到它们互相渗透,是彼此的纪念碑;当读者还沉浸在这种“游荡的灵魂”的宏阔视角中时,诗人又独具匠心地把“游荡的灵魂”这个看的主体偷换成了鹰这个被“我们”看的客体,而实现手法就是基于“飞”这个共同点的暗喻(“灵魂是否就是一只鹰”),并且以扩展性暗喻的技巧继续渲染翅膀、反光等,暗示了现代的人(通篇的复数“我们”隐喻这是共性而非个性的体验)不但肉身被阉割成为“魂”,而且连这个“魂”也都将飞逝而去,留下一片黑暗(“太阳已经坠落而黑暗也已临近”)。但好在诗人并非完全绝望,所以还留下了那反射的“最后一缕光”指引我们去追寻光明。
从以上分析可知,这首诗中“游荡的灵魂”的视角给予读者一种全新的审视人与自然关系,审视过去与现在对比的途径。它既是旁观者冷眼评判,又是参与者飞荡其中,最后还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肉身,即“鹰”的肉身,从而得以超越现实引领人们追寻光明。可以说,这不仅是沃伦创作诗歌的重要形式技巧和有机内容,还折射了处于现代荒原中的人丢失了美好的过去,无所皈依,但仍力求追寻一线希望的社会历史内涵。把“游荡的灵魂”作为诗中的叙述者之一参与故事的还有沃伦的《夜曲》等诗歌。
(二)“游荡的灵魂”作为诗中观察故事的主要叙述者
沃伦的晚期诗歌《内伤》组诗描写了一位黑人老年妇女的遭遇,乍一看只是一般的全知叙述视角,但细读后会发现诗人巧妙地借用一种可以任意移动位置的“游荡的灵魂”作为诗中观察故事的主要叙述者,即使用的是限知性视角的外聚焦,并借此以深层文本颠覆表层文本达到更深刻揭露社会不公的目的。例如组诗之一《事件》:
黑鬼:年纪老了,又是个
女人,好像这还不够苦,又是个
穷人,鞋底上有个大洞
(我看得很清楚,你瘫
躺在地上,是右脚);加上
诗歌开篇的“黑鬼”一词是文化上的禁忌语,带有强烈的种族歧视色彩,作为体现意识形态的词汇,暗示叙述者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由此为读者开启了表层文本带领读者一起嘲讽这个黑鬼妇女的模式——从外聚焦的全知视角来看,她又老,又穷,还邋遢(“鞋底上有个大洞”),接下来第2诗节继续沿着表层文本的聚焦模式嘲讽这个黑鬼妇女的种种不光彩:
孤苦无依(女儿远在
底特律,三年没音信。儿子
在河上游的监牢里,至少还知道
他在哪里),无亲无友,再加上
既然是貌似传统的全知视角聚焦,那当然可以不遗余力地写出这个黑鬼妇女无依无靠是因为她的女儿不理她,儿子身陷囹圄,还无亲无友没人关心。就在这个老女人已经外在和家庭2个方面都不够光彩之际,第3诗节(略)中她又遭逢因“盗窃”而“被解雇”,且是“(……只不过是看我的肤色/就认定是我)”这件更加不光彩的事。这下黑人妇女连经济来源都没有了,基本生存都无法维系。诚如诗中外聚焦全知视角所感叹的,“做人到这种地步”已然太过失败了!但这种白人至上主义者式的奚落还未就此停止,还要在第4诗节中把这种种失败归结于她自己,而丝毫不提及社会对她的不公和鄙视——“真够受的(是的,六十八了,/只好是什么样/就什么样,是的,瞧瞧/镜子,那就是/你自己,多少年/不做祷告了?)光活下去”——她是个长期懈怠于祷告、没有精神信仰的人,难怪只能勉强“活下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活,把失败和不光彩都归结于这个黑鬼妇女让她连抱怨都无从谈起,因为一切皆是她自作自受。这些还嫌不够,下一诗节还要再添上她身体被汽车重撞的一笔,并在一系列细节上再度嘲弄她:
就够受的——耶稣,
光活着就够受,难道还要让人把尿(的确是
这么回事)从你身子里
压出来,用一辆1957年黄色
卡迪拉克车,开车的是个
波多黎各人,他来自
新泽西?
被汽车撞到连尿都压了出来,人的基本尊严丧失殆尽,而撞她的连个白人都不是,而是和她一样的少数有色人种。至此,诗歌表层文本以表面的全知视角对这个黑人妇女极尽嘲笑挖苦之能事,宣泄了一种白人旁观者式的居高临下和幸灾乐祸。
可诗人要写的就是这些吗?不。细读文本会发现,所谓的外聚焦全知视角只是表象:第一个词“黑鬼”(Nigger)是斜体的,这种陌生化的文本标记昭示了深层文本上的视角是不认同这个带有种族歧视的概念的。接下来的每个诗节都有一个显著的重复使用的文本标记,那就是小括号,每次括号中的聚焦者和叙述者都提供了一些主体信息以外的补充信息,时而会俯身去观察她的伤势(瘫躺,伤在右脚),时而仿佛和她对话来宽慰她的孤苦无依(至少还知道儿子和女儿的下落),时而转换为“她”的内聚焦视角,一起谴责肤色政治(今天的事太不公平)……这种视角在空间位置的自由转移和对部分事情的了解(知道黑人妇女的背景和解雇事情的真相等,但不了解黑人妇女自身的感受和痛苦,即黑人妇女本人的诸多感受和痛苦是失语、不在场的)的外聚焦限知性视角为读者揭开了深层文本的真相,那就是黑人妇女经历了种种遭遇和痛苦却得不到聆听和同情,身体遭受的“外伤”远比不上冷漠歧视带给她的“内伤”,至此,诗歌题目“内伤”的含义才得到了比较深入的解读。而这些正是借助于一个隐形的可瞬间位移、知道背景和其他地点(不同于车祸现场的黑人妇女工作地点)发生的事情真相,却不知道黑人妇女本身的思想与感受的“游荡的灵魂”的视角才得以实现。这种独特的视角契合了沃伦诗歌对暴力的谴责,尤其是对无形的种种暴力的谴责。在沃伦诗歌晚期的代表作《文字梦》中,“我”神游到《苔丝》小说中观察老年苔丝的描写等也是这种“游荡的灵魂”作为诗中观察故事的主要叙述者的代表。
(三)“游荡的灵魂”作为诗中参与和观察故事的叙述者
沃伦诗歌中“游荡的灵魂”有时是以上两种功能兼备的,而这些诗歌也是沃伦的一大特色。比如中期代表作《我梦想着一个白色的圣诞节:一个幻象的自然史》[10]:
不,不是那扇门——根本不!但是,
进来,看。藉着
褐色的空气,宛如旧式银版照相法……床。
它曾在的/地方。现在成了过去……一条红色的
彩带,很久以前因欢乐而系上的,
在灰色壁炉里飘着犹如/熔了的保险丝……我曾
在的地方,
现已不在。现在是
率直的群众推推搡搡、挤挤撞撞、拖拖拉拉、磕
磕碰碰的地方,
眼含敌意。
在这首诗中,沃伦对美好的童年以画面定格和灵魂回归的方式进行了一番特殊的巡礼,后又随灵魂游荡回“眼含敌意”的现今生活,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丢失的水车池》等诗歌也是这种典型的视角,即“游荡的灵魂”既作为故事的参与者承担内部聚焦的功能,又带着成人的灵魂视角对过去的一切进行观察和评论。这种聚焦穿梭时空,把过去、现在和未来串联在一起,形成彼此之间的映照,并在映照中含蓄表达出诗人“逃逸与追寻”的主题和重建完整和谐自我、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世界关联模式的愿望。
以上3种“游荡的灵魂”是沃伦诗歌中重要的聚焦模式,在其早期(如《记得的野餐》)、中期(如《我梦想着一个白色的圣诞节:一个幻象的自然史》)和晚期(如《内伤》)诗歌作品中都有呈现,总体比例不相上下,是对传统视角或聚焦模式的某种叠加和创新。这不仅是沃伦诗歌的重要写作技巧和形式特点,也是构成他诗歌内容的一部分,折射了诗人对现代人失去归属感“无根飘荡”以及依旧执着地“逃逸与追寻”的感知。
三、结语
沃伦诗歌这种“游荡的灵魂”聚焦可独立存在撑起一篇诗歌,也可和其他聚焦结合,相应生辉。这种“游荡的灵魂”聚焦打破了时空的束缚,营造了似梦似真的氛围,让想象随意驰骋,帮助内聚焦与外聚焦之间的切换,让第一人称聚焦模式中嵌入第三人称聚焦的“聚焦越界”少了些生硬,让第三人称聚焦模式内出现第一人称聚焦时更加的自然。这种聚焦的选择有助于表达他诗歌的“逃逸与追寻”主题——对都市城镇的“逃逸”及对自然乡村的“追寻”;对暴力暴行的“逃逸”及对和平和谐的“追寻”;对迷茫无知的“逃逸”及对内外认知的“追寻”;对现代荒原的“逃逸”及对理想世界的“追寻”[9]。该聚焦既折射了现代人无根漂泊却又执着追寻的形象内涵,又体现了他的新批评诗学思想中对“反讽”的重视(隐含作者的视角与叙述者视角不一致时反讽就得到了凸显),是沃伦诗歌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
注释:
①未列入参考文献的沃伦诗歌皆为笔者翻译。
参考文献:
[1]吴瑾瑾.生之必然渗透:罗伯特·沃伦的自我认知哲学观与文学创作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8:11-19.
[2]王丽亚.什么是“新形式主义”:《新形式主义与文学理论》述评[J].外国文学,2015(5).
[3]申丹.视角[J].外国文学,2004(3).
[4] LUBBOCK P. The Craft of Fiction [M]. London:Jonathan Cape,1921:21.
[5]苏畅.对视点问题的重新认识:关于乌斯宾斯基的《结构诗学》[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3).
[6]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21-122.
[7]汪剑钊.诗歌的乌鸦时代[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7.
[8] BURT J. The Collected Poems of Robert Penn Warren[M]. Baton Houge:Lo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8.
[9]何欣.逃逸与追寻:罗伯特·潘·沃伦诗歌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3:10.
[10]沃伦诗选[M].周伟驰,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110-120.
(编辑:文汝)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6)05-0060-05
作者简介:何欣(1982-),女,博士,天津外国语大学(天津300204)英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英语教育。
收稿日期:2016-03-08
基金项目:2015年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美国现当代诗人罗伯特·潘·沃伦诗歌研究”(TJWW15-030);2015年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改项目“新时期英语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方法协同改革研究——以英语诗歌教学为例”(TJWD15B22);2015年天津外国语大学“十二五”规划项目“20世纪美国文学巨擘罗伯特·潘·沃伦诗歌研究”(15QN0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