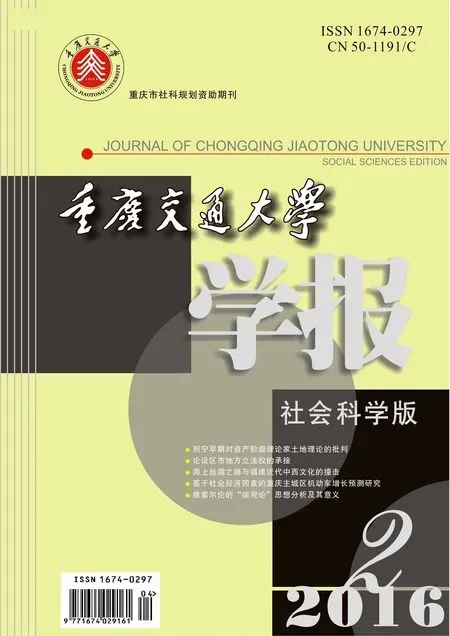中英首次正式外交中百灵致两广总督信件的翻译问题
刘 黎(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400074)
中英首次正式外交中百灵致两广总督信件的翻译问题
刘 黎
(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重庆400074)
摘 要: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弗朗西斯·百灵致两广总督的信件拉开了1793年中英首次正式外交的序幕,其中译文直接影响着乾隆对使团的态度和对访华事件的理解。本文通过考析史料,深入讨论百灵信件翻译的几个重要问题:信件是如何翻译的,译者是谁,不同中译本间有哪些异同,信件中译本给中英双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研究这些问题,能够更深刻地认识18世纪末中英首次正式外交接触前夕翻译事务的形态与特征。
关键词:马戛尔尼使团; 百灵; 信件; 翻译
一、引言
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George Lord Macartney)率领庞大的英国使团访华,这是中英两国正式外交往来的发轫。伴随着此次外交事件的翻译活动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1994年葛剑雄发文对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里的英方文件与保留于清宫档案中的原始译文进行对照分析[1],可视为对1793年英使团访华翻译研究之滥觞。之后,有学者或较全面讨论了使团访华的翻译问题[2],或分析了此次外交事件中翻译活动的特征[3],或考析了访华事件中一些具体文书的翻译问题[4-7]。可以说,对1793年英使访华翻译活动的研究已初具规模。
在这次外交事件里,时任东印度公司董事长弗朗西斯·百灵(Francis Baring)致两广总督的信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署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郭世勋奏明乾隆皇帝英国使团来访,并附百灵信件原件和译件各两份,这份奏折在众多史学家看来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开端[8-11],而百灵信件也成为中方接收到的第一份直接来自英方关于使团访华的文件。对百灵信件翻译现有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斯当东的纪实中摘有该信件部分内容,叶笃义在翻译时仅在脚注中作了简单评价[12]39;有学者在对勘叶译信件和清宫存档译文时,只是粗略地指出“原来平等的行文被译成了下级对上级的呈文,而且一些重要的词句不是未全部译出,就是作了一厢情愿的修改”[1],缺乏详尽的分析;王宏志曾撰文较正式而全面地探讨了马戛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对百灵信件也有较详细的分析[2],但因限于篇幅,该文对百灵信件翻译问题的研究仍有诸多不明之处;还有学者局限于信件不同译本的简单比较,缺乏史料考证[13],难免有失偏颇。百灵信件拉开英使访华的序幕,但其翻译无论从过程、译者、方式等都与英使团其它文书的翻译有所不同,具有其特殊性。本文通过考析史料,深入讨论百灵信件翻译的几个重要问题:信件是如何翻译的?译者是谁?不同中译本间有哪些异同?信件中译本给中英双方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通过研究这些问题,我们期望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18世纪末中英首次正式外交接触前夕翻译事务的形态与特征。
二、百灵信件及译本考证
当英国政府作出派遣使团访华的决定后,马戛尔尼于1792年1月4日向国务大臣邓达斯(Henry Dundas)就使团使命及访华目的提交了一份书面意见,他认为为了不让北京朝廷感到意外,应先行通知中方英使访华的消息[14]214。马戛尔尼的信被转给百灵,后者说已经派出人员组成了秘密监督委员会(Secret and Superintending Committee,简称密监会),可以完成通知中方的任务[14]216。3月17日,马戛尔尼向邓达斯呈交了下达给密监会委员的指令以及致两广总督的信件草稿[15]287,信件大意是在乾隆皇帝八旬大寿之际,驻广州英国商人未派出代表团贺寿,英国国王深感不满,现派马戛尔尼率庞大使团赴华祝贺,因携带大批礼品,不便从广州上岸、陆路进京,故请总督大人转奏清廷,批准英使团从天津或附近港口上岸,并请中方安排相关接待。4月19日,马戛尔尼会晤百灵,提出公司董事会主席致总督的信件应该有英文和拉丁文两个文本[15]289,拉丁文本于4月27日完成,该信件的最终文本与之前马戛尔尼提交的草稿并无二致[15]290[16]231。
在1792年4月11日的训令里,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指派成立密监会,以更好地管理广州业务,该委员会有三名成员:波郎(Henry Browne)、欧文(Eyles Irwin)、杰克逊(William Jackson),其中波郎为主席,他们是清宫文件中提及的英夷波郎、亚里免、质臣(原文件加有口字偏旁)[17]279[18]612。委员会成员乘坐“忒提斯号”(Thetis)于9月21日到达中国①[14]194,这正是马戛尔尼使团从英国出发前5天。9月24日,密监会告诉行商文官②[19]4(Munqua)和潘启官③[19]262,264(Puankhequa),他们有一份重要的信件要呈给两广总督,并要求行商安排他们与总督会面。当时的两广总督福康安正在西藏平息叛乱,故两位行商带着密监会委员于10月10日④[17]279拜会了广东巡抚郭世勋和粤海关监督⑤[20]盛住。密监会主席波郎亲自将百灵致两广总督的信件交到郭世勋手上,由于该信件只有英文和拉丁文本,故郭世勋马上叫人将这两份文件译为中文⑥[15]313。拉丁文文本交给一位中国人翻译[15]313,至于这位中国人是谁,就现有的资料无从考证,有论者质疑“广州的中国通事怎可能有精通拉丁文的”[2],这可能是受郭奏折里“随令通事及认识夷字之人译出原禀二件”[17]279等语的引导,但郭世勋这句话说得很笼统,且极有可能他口中的通事就是指陪同委员们的两位行商,因为据英方资料记载,他们是以翻译的身份前往的[15]313,下文即将谈到,他们负责英文文本的翻译。故笔者认为完成拉丁文本翻译的这位中国人不一定是通事,倒有可能是具有宗教背景、谙习拉丁文的中国教徒。英文文本返给密监会三位成员和行商蔡世文与潘有度共同翻译,这两位行商虽为中国人,但经年与英国人做生意,习得一些英语。英文文本译出后官员们理解很费劲,而拉丁文文本译得明显好多了[15]313。当郭世勋等官员了解信件内容后,于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初七(1792年10月22日)立马将此事上奏乾隆,并附上百灵信件的两个文本和两个译本[17]216,217,279-280[18]611-616。朝廷接到这些文件后,又让在京西洋传教士重新翻译。十月二十日(1792年12月3日)军机处奏片称,西洋传教士不习英文,只译出拉丁文文本,内容与郭提供的两个译本大致相同,并附上西洋传教士的译本[17]91-92[18]611-617。至此,存于清宫档案中百灵信件的译文总共有三份。
三、百灵信件各译本比较
有学者认为,百灵信件的三个译本都“将原函平行的口气译成以下对上的禀帖口气”[12]39,三份中译本文辞谦卑恭顺,称呼尊人贬己,文书格式严格遵照清廷官方文章要求,但与信件原文[16]375-377(原信“Letter from the Chairman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o the Viceroy,27th April,1792”,下文引用信件原文不再赘注)对照,三份译本都“于原书辞气事理未能吻合”[18]617,“存有很严重的问题”[2]。下文将对照原文,详细分析这三份中译本。为方便论述,将由在京西洋传教士从拉丁文译成的中译本简称为A译本,郭世勋上奏从英文译成的中译本简称为B译本,郭世勋上奏从拉丁文译成的中译本简称为C译本。
原信开头是董事会主席百灵对总督大人的问候以及对英国国王的介绍,其中谈及英方时用到许多浮夸溢美之词,比如The Honorable the President,Our most Gracious Sovereign,His most excellent Majesty,whose fame extends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等。在B、C译本中这些表达全不见了,仅变成“英咭唎国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咟灵”“我本国国王”“我国王”;A译文更加简单,连对百灵的工作职责(“管理贸易”)、对总督大人的问候(“均安”)和英国国王管辖的领土(“管有呀囒哋嘧吨咈囒哂嗳倫等三处地方”)都略去不提。类似的情形也体现在对特使马戛尔尼的介绍上。原信中有一大段对马戛尔尼的介绍,用了一连串的the most来描述他,列出他的贵族身份、渊博学识、高尚品德和过人能力。然而三个译本都不约而同地省去这些华丽的介绍:A译本为方便中方理解,将马戛尔尼称作“宰相”,显得不伦不类;B译本用“辅国大臣”一笔带过;C译本则直接将其贬为“贡使”。
关于乾隆八旬大寿英国未遣使祝寿一事,原文表述为:“…,having heard that it had been expected his subjects settled at Canton in the Chinese Empire should have sent a Deputation to the Court of Pekin,in order to congratulate the Emperor on his entering into the eightieth year of his Age,and that such Deputation had not been immediately dispatched,His Majesty expressed great displeasure thereat.”
1789年10月,时任海关监督额而登布和两广总督福康安曾建议英国大班们派出代表团从广州进京贺寿,其中一位大班同意前往,但之后广州官员并未再提此事,最终贺寿一事不了了之[14]177-178,182。原文意为未能进京祝寿是驻广州英国大班的过失,英国国王对此很不满意,但B、C译本把这个信息处理得很模糊,没有把it had been expected明确翻译出来,且表达出因国王未遣使进京深感惶恐不安的意思。而A译文则更加出格,擅自添加了一些原文中没有的信息,如“……欲遣人进京恭祝,因道远未能赶上”。
原信提到此次派遣使团的目的是“being desirous of cultivating the Friendship of the Emperor of China,and of improving the connection,intercourse and goo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Courts of London and Pekin,and of increasing and extending the Commerce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subjects”,并最终“promote the advantage and interest of the two Nations of Great Britain and China,and to establish a perpetual harmony and alliance between them”。这无疑是想要在两国间建立平等的外交、商贸关系。然而这些重要的出使目的在三个汉译文中都带上了“准令通好”“施恩通好”等乞求口吻。三个文本在处理这些信息时也有所差别:A译文把这些信息简化后全放在文末处,变成了英方恳请大皇帝收下礼品、准许中英通好,显得太过简单;B译文基本保留了信息在原文中的顺序,但信息有不必要的增补,如“但望生理愈大,饷货丰盈”,这应该是译者(东印度公司在华商务管理者和行商)自己的愿望;C译文则将以上信息糅杂在一起,放在原文中第二个目的的位置,语气被大大地弱化了。
接下来看看英方礼品的描述,这是英方声称使团船队不能在广州靠岸,要直接停泊天津的原因。原信是:“having several presents… ,which from their size,nice mechanism,and value could not be conveyed through the interior of the Country…”该描述强调礼品的三个特征:体积庞大、精巧、贵重,但这三个特征在三个译本中都没有得到全面准确的体现。译文A只表达出“贵重”这一点,却凭空加上“钟表”等信息;译文B体现出“贵重物件”“大件品物”,少了“精巧”,且该译文用“进贡”一词体现出对使团性质的定位;译文C也是笼统地描述为“极大极好”,同样将礼品定义为“贡物”。
之后,百灵在信中请总督大人将消息转告朝廷,并要朝廷下令给予使团合适的接待。原文使用了语气较强硬的词request、trusting,体现出英国作为西方第一强国、海上霸主的强势和自负。汉译本则不约而同地将这种语气改头换面,成了“求转奏”“恳祈”“恩准”,而且都对要求接待一事闭口不提。
信件最后是具有明显基督教柔性特点的惯例表达:“And so praying the Almighty God to grant you all happiness and long life,and to take you under his heavenly protection,We bid you heartily farewell.”这句话在译文A、C中都没有与之对应的内容,只有在译文B中被转化为更符合中国人认知的“我惟有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
综上所述,百灵信件的三个中译本都有很大的问题,但这三个译本又各有特点。A译本最为简单,只能算是把内容要点大略翻译出来了[2];其中不乏错译和添加,如“恩准赏收,俯鉴微忱”;且该译文缺少另外两个译本里对“天朝大人”的恭敬,而对“大皇帝”有讨好奉承之嫌,这与该译件将跳过郭世勋直接送呈御览有关。B译文最详细,撇开三个译本共有的以下对上的卑恭口吻不谈,它基本保留了原文的信息顺序,而且相对完整地传达出原文本的信息;除了上述分析中的例子外,B译本还具体音译出英国管辖的三个地方名称“呀囒哋嘧吨咈囒哂嗳倫等三处地方”,并以“冀早日到京”和“另有差船护送同行”译出另外两译本未传达出的proceed without delay和properly accompanied等信息;然而B译文的行文措辞显得不正式,有“着人进京”“十分欢喜”“包管……永远相好”等口头化表达,这与呈送中方高级官员的正式信件不相宜。C译本在信息的完整性方面不及B译本,但其表达流畅正式,符合清廷官方文书的行文要求,难怪官员们觉得拉丁文译本更胜一筹[15]313。顺带提及一下,《掌故丛编》除了收录这三份译本外,还有一份编者重译的文本[18]617-619,该文行文流畅、言辞达意,称得上百灵信件的上佳译作,但在翻译马戛尔尼的头衔之一 Knight of the most honorable Order of the Bath时,译者处理为“巴斯(地名)勋位”,实属谬误。Bath并非地名,The Most Honorable Order of the Bath源自中世纪骑士称号授予仪式传统,仪式前被授者必须要沐浴净身,故有Bath一说。
四、译本对中英双方的影响
百灵信件的汉译本对中英双方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如论者所言,从中华文明早期直到19世纪中西相遇,朝贡体系一直确定了中国对外关系的态度与实践[21]。在乾隆眼里,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只是一次朝贡事件,当他读到来自英方的第一份文书——百灵信件汉译本时更加固了这种认识。在收到军机处奏片同一日,即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二十日(1792年12月3日),乾隆马上发出廷寄,称“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宽容地“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乾隆考虑到“海洋风帆无定,或于浙闽、江苏、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帆亦未可知”,故令各地督抚一旦发现有英国贡船到口,就“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18]619;乾隆还对使团到达时间不定、使团大船难以进口等可预料的困难进行了妥善安排。在其后的几份廷寄里,如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初二日廷寄(625-6)、六月初九日廷寄(627-9)、六月十七日廷寄(633-4)、六月二十日廷寄(634-5)等,乾隆皇帝处处为使团着想,妥当安排,怀柔远人之心跃然纸上。乾隆皇帝对英使团格外开恩、宽容迁就,是因为他从当时收到的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直接来自英方的文件——百灵致两广总督的信件里读出了英国远夷恭顺谦卑的输成向化之意。殊不知,乾隆皇帝读到的并不是真实的信件,而是信件汉译本,汉译本经过重重修改,早已改头换面。从这个角度来说,乾隆皇帝受到百灵信件汉译本营造出的假象的误导,从一开始就对英使团有错误的认识。
百灵信件汉译本对英方同样产生了负面影响。使团筹备之初,马戛尔尼明确向邓达斯提出,对付清廷这样一个傲慢的朝廷,必须给其皇帝和大臣留下庄严华丽的印象[14]214。因此,来自英方的文件,从百灵信件到后来的英国国王致乾隆皇帝的国书、英使团礼品清单等,无一不透露出英国作为西方雄主的炫耀。然而在中译本里,无一例外,英方用以震慑中方的自夸之词全都不见踪影,英国海上霸主、西方强国的形象被扭曲成卑躬屈膝的清廷附庸形象。就百灵信件而言,不管是郭世勋找来的认识拉丁文的中国人、行走在英国商人和清廷官员之间的行商(尽管他们与英国人的关系非常亲密⑦[14]220[19]360),还是清廷指派的西洋传教士,他们归根到底都是为中方服务,所以出自他们之手的百灵信件汉译本都极力迎合清廷,成为地地道道的禀文。这样的后果是,英国人提出建立平等关系的诉求得不到传达,英国从一开始就成为中方眼中乞哀告怜的朝贡小国,显然与英国的初衷背道而驰。然而,英方对信件的改头换面却束手无策,一来是因为密监会委员与郭世勋会面是在前者刚到中国不久,他们没有充足的时间组织人翻译;二来是当时英方根本没有自己的翻译⑧[14]209,只能非常被动地将信件交由中方翻译;更重要的是,面对强势颟顸的清廷,为了尽可能地达到出使目的,英方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事实上,就算是后来英方有了自己的翻译,英方文件也并没有按照原样翻译出来,要么是清廷审查后进行了重译(如英国国王致乾隆皇帝国书),要么是英方译者自作主张删掉原文中的溢美之词(如礼品清单),要么是英方主动要求把文书翻译成中方官方文书格式(如礼仪照会)。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日(1793年9月14日)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为维护本国尊严,他坚决不愿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但他何曾料到,从英方递交给中国的第一份文件起,英方不知已经向中方书面“磕头”过多少次了。
五、结语
英语是当今世界通用语,汉语是全世界使用者最多的语言,英汉两种语言的翻译研究早已成为时代显学。两个多世纪以前,这两种语言的交流却因为特定的历史语境和时代背景历经重重困难,东印度公司董事长百灵致两广总督的信件翻译则是当时译事困境的一个缩影。囿于语言障碍和政治、历史等因素,百灵信件经由不同的人操刀翻译,最终形成三份汉译本存于清宫档案中。三份译文均不同程度地损害了原信的信息和口吻,成为清廷文书中司空见惯的禀文,这既给乾隆皇帝营造出英国远夷入贡的假象,又使英方建立平等外交、商贸关系的诉求无法闻达于清廷。
百灵信件的翻译折射出中英正式外交接触早期翻译事务的弊端:一是缺乏合格的翻译人员。无论是充当密监会委员与郭世勋等人会面口译的行商,还是持笔翻译信件的中国人、行商以及在京传教士,他们都不是职业翻译,其语言水平和翻译能力都值得怀疑,从客观上决定了百灵信件译本质量低下。二是担任翻译工作的人员职业道德缺失。他们受制于中国政府,为清廷效忠,不敢也不会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传达出百灵信件的真实意图。事实上,这两个问题在后来马戛尔尼使团抵达中国直至离开一直未能解决。可以说,中英首次正式外交接触是在双方缺乏清楚的相互认识中进行的。
注释:
①在Pritchard所著的《The Crucial Years》里,密监会到达广州的时间是1792年9月20日,但鉴于《The Crucial Years》一书多引自Morse的《The Chronicles》,故本文如遇两书说法不一致的情况,均以后者为准。
②经查证,文官就是万和行蔡世文,粤音读“文”为Mun,他在当时居于总理洋行事务之总商地位。
③据考证,这位潘启官是同文行潘振承的次子潘有度,他沿用其父商名,报官注册名为潘致祥。潘启官和文官掌控着当时最显著的两大商行,他们都担任过总商。
④根据中方文件,双方会晤的时间是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初三,即1792年10月18日。
⑤英文资料里为Hoppo,Hoppo是西洋人对粤海关、粤海关监督或粤海关官吏的称呼,常音译为“河泊”,也有讹译为“户部”的。
⑥根据相关资料推断,这两份文件应该是在会晤现场翻译的:密监会和行商于10月10日上午10点半到达衙门,等候一小时后见到巡抚郭世勋并呈递信件,下午1点左右,郭世勋便了解了信件内容并询问密监会成员关于使团的相关信息。
⑦由于行商地位不断提高,其与英国大班的友谊益厚,相互敬重,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行商与大班的关系已至互相信赖之最高点。据英国人记载,文官蔡世文曾被清廷指派充当接待马戛尔尼使团的通事,但蔡世文舍不得广州获利丰厚的生意不愿前往。蔡世文到澳门后曾向英国人诉苦,密监会委员告诉他马戛尔尼带有翻译,并宽慰他不要着急,可见当时蔡世文与英国商人关系之亲密。
⑧长期以来,英国商人与中国官员交涉都必须通过中国通事,但中国通事大都英文水平低下,交流极为不便。后一英国人洪仁辉(James Flint)偷学中文成功,成为东印度公司的翻译,英国人尝到由自己人担任翻译的甜头。但1759年“洪仁辉事件”之后,清政府更加严厉地控制华夷交流,英国人又只有回到以前通过中国通事与中方打交道的局面。密监会委员来到中国后,迫切地希望能拥有自己人做翻译,他们曾选出三名东印度公司职员跟着一位中国人学习汉语,但这位中国人非常害怕自己教授外国人汉语的行为被官府发现,故学习过程困难重重,无疾而终。
参考文献:
[1] 葛剑雄.世界上不止有中文:《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与《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之对勘[J].读书,1994(11):185-188.
[2] 王宏志.马戛尔尼使华的翻译问题[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9(63):97-145.
[3] 刘黎.一场瞎子和聋子的对话:重构英使马戛尔尼访华的翻译过程[J].上海翻译,2014 (3):81-85.
[4] 王辉.天朝话语与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书的清宫译文[J].中国翻译,2009(1):27-32.
[5] 王宏志.大红毛国的来信:马戛尔尼使团国书中译的几个问题[M]//翻译史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37.
[6] 王宏志.“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翻译与马戛尔尼的礼物[C]//张上冠.知识之礼:再探礼物文化学术论坛论文集.台北:政治大学外国语文学院翻译中心,2013:77-124.
[7] 刘黎.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礼仪照会翻译之考析[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37-139.
[8] 佩雷菲特.序言[G]//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10-22.
[9]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M].王国卿,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10] 秦国经.从清宫档案看英使马戛尔尼访华历史事实[G].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23-88.
[11] 戴廷杰.兼听则明:马戛尔尼使华再探[G]//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89-150.
[12]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M].叶笃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13] 陈显波.主题文化对译者的影响:以弗朗西斯·百灵致两广总督信件翻译为例[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5):175-176.
[14] MORSE H B.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53-1834[M].Oxford:Clarendon Press,1926.
[15] PRITCHARD E H.The cruial years of Anglo-Chinese relations,1750-1800[M].New York:Octagon Books,1970.
[16] PRITCHARD E H.The instruction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o Lord Macartney on his embassy to China and his reports to the company,1792-4[C]//Patrick T.Britain and the China trade,1635-1842.London:Routledge,2000.
[1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G].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
[18] 故宫博物院掌故部.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奏[G]//故宫博物院掌故部.掌故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90.
[19]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20] 季压西,陈伟民.中国近代通事[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101.
[21] 何亚伟.怀柔远人:马戛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M].邓常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0.
(责任编辑:李晓梅)
Translation of Letter from the Chairman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o the Viceroy of China in the First Sino-British Diplomatic Contact
LIU L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74,China)
Abstract:Letter from Francis Baring,the Chairman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to the Viceroy was the prologue to the first Sino -British Diplomatic contact in 1793.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is letter greatly influenced Qian Long's attitude to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Embassy.By study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several cruci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translation of the letter are discussed:How was the letter translated?Who translated it?What 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Chinese versions?What impacts were brought about by the Chinese versions on China and Great Britain?It is hoped that,by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we will more profoundly understand the forms and features of translation at the first encounter of the two powers in the late18th century.
Key words:Macartney Embassy;Baring;letter;translation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297(2016)02-0133-06
* 收稿日期:2015-09-29;
修订日期:2015-10-13
基金项目: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一般项目“基于外语类专业教学改革的特色英语专业建设研究”(143025)
作者简介:刘黎(1980—),女,重庆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史、外语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