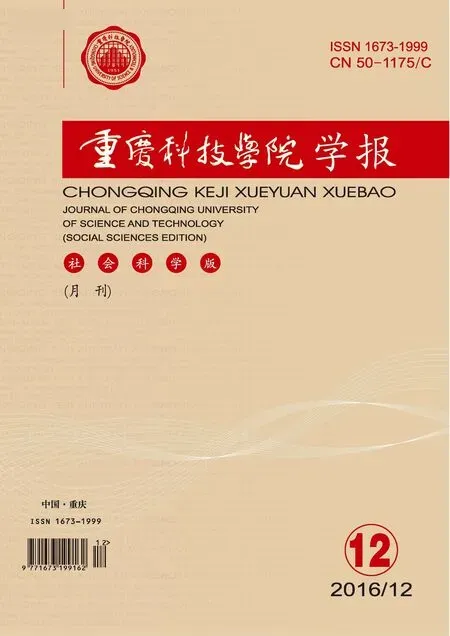《史记》中母子性别关系及其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范明英,彭体春
《史记》中母子性别关系及其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范明英,彭体春
《史记》对母子关系的叙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社会中的母子关系格局或其时的观念对于母子关系的理解。在《史记》中,上古帝王的母子关系呈现了周前“夫妇不分”的性别关系;近世帝王母子关系显现了周代以来社会政治对于母子关系的性别建构;在中下层社会的母子关系中,母亲担当了儿子道德培养的职能并成为儿子生命的守护者。总体而言,《史记》中的母亲在母子性别关系结构中处于从属地位。
《史记》;母子关系;性别关系;传统文化
《史记》在叙写女性尤其是母亲形象上极具特色。白寿彞在《史记新论》中指出:“在写妇女历史方面,司马迁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1]74《史记》中的女性形象非常丰富。据统计《史记》中所载各类女性有199人[2]107,其中有母亲身份的127人,占女性总数的64%。《史记》对母子关系的叙事,已成为极具文化意义的论题。
学界对《史记》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大多预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偶涉母亲形象时也概莫例外。植根于西方当代文化语境的女性主义理论,未能也不可能关注到中国古代家国同构的社会格局,一夫多妻的性别结构,阴阳和合的性别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女性母、妻、妾、婢等性别层次,特别是母亲作为女性家长的特殊身份。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在提到中国古代社会时,通常将父权或男权作为两性关系的全部,将父子关系等同于君臣关系,并作为封建性的根本[3]33。在此意义上,照搬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女性,特别是中国古代女性显然有理论上的“水土不服”。“性别”一词尽管也是外来语,但性别研究与女性研究不同,它不仅研究女性,也研究男性,并揭示两性关系被社会文化规范、限制的方式和过程,“旨在检验‘男性’与‘女性’如何在具体的时空中拥有某种具体的含义,并且它强调这些含义的相互关联以及由此生成的意义。”[4]84《史记》对于母子关系的叙事,内蕴了其时人们对于母子关系的性别认知,提供了中国早期两性关系特别是母子关系的叙事文本。《史记》所叙母子关系,根据儿子的社会身份可以分为帝王母子、将相母子、平民母子三类。其中的帝王形象,根据《史记》的叙事,又可分为感物而生的上古圣君和感梦而生的近世帝王两类。
一、感物而生与上古圣君的母子关系
《史记》中感物而生的帝王,其父亲身份不明或语焉不详,因而此类帝王的出生极具传奇色彩。需要注意的是,母亲只是此类帝王身体来源的母体,母子关系的纽带是生孕关系。
这类帝王大多来自神话传说,其父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但与生孕无关,所谓“圣人无父,感天而生”。如华胥氏履大人迹生伏羲、女登感神龙生炎帝、女节感流星生少昊、女枢感流光生颛顼、附宝感雷电生黄帝、修已梦流星并吞神珠薏苡生禹,以及秦人祖先大业来于其母女修吞玄鸟之卵而生等。还应注意到,《史记》除了叙述此类帝王母子关系外,也有父亲出现,但语焉不详。据《殷本纪》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司马迁自称“余以《颂》次契之事”,即所叙来于《诗经·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但该诗中未出现的父亲帝喾却在《史记》中出现了。与之相似,《周本纪》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姜嫄为帝喾元妃。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其所叙来于《诗经·生民》,该诗中未现的父亲帝喾也在《史记》中出现了。在此类生孕关系中,父亲虽有出现,但父亲与生孕帝王无关。与此同时,此类帝王之母除孕子之外,在帝王建立丰功伟业的过程中几乎消失,母子关系的纽带仅依靠感物而生予以维系。
学者对《史记》所记此类帝王母子关系有议,特别是《史记》之后的一批儒家知识分子对此多有贬损之辞。例如,班固言《史记》“是非颇缪于圣人”,究其原因,认为是司马迁主观上“先黄老而后六经”的尊道抑儒观念所致。班固之说虽被沈括否定:“班固乃讥迁‘是非颇缪于圣贤’,论甚不慊……实有见而发,有激而云耳。”[5]13但班固对《史记》内蕴黄老和六经之言不虚,或如沈括所言,当为“有见而发”,即汉代初期黄老之道和儒家之说并行,这在《史记》对此类帝王母子关系的历史叙事中得到了体现。
儒家经典“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传·系辞下》)言及男女双性繁殖,但《史记》化用神话传说,言之凿凿地叙及帝王知母不知父,这与汉初黄老之说盛行有关。《老子》云:“儿独异人于人,贵食其母”“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在《老子》中,母亲既是作为人的个体化的母亲,也是滋生万物的自然。不难理解在这类母亲孕子的过程中父亲身份的缺席,因为“女人—母腹—土地—创造力之间的结合,要比男人—男性生殖器—天—创造力之间的结合更为久远。”[6]26叶舒宪指出:“在老子关于道的创生功能的各种表述和象征语汇的背后似乎潜伏着某种单一雌性生殖观念”[7]50。李长之认为,司马迁的“根本思想是道家的自然主义,所以他的政治哲学便建立在无为上,他觉得最好是顺其自然”[8]206。
实际上,在儒家经典肯定双性繁殖的同时,对母亲生子之功也不绝赞辞,如《易》所谓“至哉坤元,万物滋生”。《史记》将母子关系简化为生孕的单一关系,应该是来自于对儒道思想共有的母子关系的原始理解。这种关系或如司马迁所言“究天人之际”,将神圣帝王视作天地交合的产物,母亲成为不能回避的生育母体。因此,我们难以看到母子之间或父母之间基于两性性别差异所造成的性别冲突关系:“男女两性的结合被看成一种阴阳交合或天地交合,随着阴阳交合、天地交合而来的是万物的孕育与生长,随男女结合而来的是人的生命的孕育与成长……正因如此,在先秦思想家那里,男女之间极端对抗的意识十分罕见。”[9]253
二、感梦而生与近世帝王的母子关系
太古荒遐,传闻悠悠。周前的神异帝王多为感物而生,而同样神异的近世帝王《史记》所叙则为感梦而生。在母子关系之外,父亲开始出场,有的还成为生孕帝王的重要因素。据《高祖本纪》记载:“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虽有高祖来于其母感梦而生之叙事,但刘太公作为父亲身份不仅在场,而且“往视”。汉武帝之母王夫人也梦日入怀而生。据《外戚世家》记载:“太子幸爱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时,王美人梦日入其怀。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贵征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此处太子先幸爱之,王美人后梦日入怀。
除商周先祖与汉代开国之君来自于父亲在场时母亲感物感梦而孕之外,晋国的唐叔虞更是来自于其父母交会时,母梦神谕,其父周武王遵神谕将唐封之。据《郑世家》记载,郑缪公之母燕姞梦得神谕,其父郑文公遵神谕与其母交会,生郑缪公。在后两例中,无论是叔虞还是缪公,均来自于父母双性繁殖,神谕在帝王出生上不再是关键因素。
由上可见,《史记》对于神异型帝王母子关系的叙事,至周代之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除母子关系外,父亲出现并逐渐成为生孕帝王的重要因素,母子关系中的现实色彩因之逐渐加重。与之相应,帝王母子关系也不再仅限于简单的生孕关系,出现了其他关系。例如:刘媪梦与神遇而生蛟龙汉高祖,寓意汉代开国之君实为真龙天子;王美人梦日入怀,汉武帝得此“贵征”以承大位;叔虞之母通过神谕使儿子获得了封地;郑缪公之母燕姞通过神谕使儿子成功做了郑国国君。
《史记》对于高祖与其父母的关系叙述饶有意味,父亲刘太公与刘媪所获得的来自于儿子的尊崇有明显区别。项羽威胁杀刘太公,刘邦应之:“杀分我一杯羹”。刘邦封妻荫子时,封母亲刘媪为“昭灵夫人”,却不封刘太公,极为反常。后来在家臣的帮助下,刘太公才被封为太上皇。《史记》中记载的刘太公与刘邦淡薄的父子关系,既有刘邦对父亲早年待其不公的报复,也与《史记》所叙刘邦的出身不无关系。钱钟书曰:“按宋人《昭灵夫人祠》诗云:‘杀分我一杯羹,龙种由来事杳冥。安用生儿作刘季,暮年无骨葬昭灵!’……意谓汉高既号‘龙种’,即非太公之子,宜于阿翁无骨肉情,运古颇能翻新。汉高即位后,招魂葬刘媪,追尊‘昭灵夫人’。”[10]280在高祖的母子关系中,有感物而生的上古神话之影响,也有汉代兴起的谶纬迷信的因素。徐经在《雅歌堂文集》卷四《书高帝本纪》中说:“自古帝王受命而兴,必征引符瑞以表其灵异,而谶纬之说,由此兴焉。”[5]358谶纬迷信兴起之源,在于配合上古圣君受命而兴的政治意涵。由此可见,周代以来,在帝王母子关系中,上古神话中生与被生的母子关系,被赋予了君命承于天的新的政治寓意。
可为反证的是,《史记》将褒姒与其母感物而生的传说相联系,并称其为“祸”。褒姒之事,《诗》已有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屈原在《楚辞·天问》中提出了疑问:“周幽谁诛,焉得乎褒姒?天命反侧,何罚何佑?”《史记》之《周本纪》和《外戚世家》叙褒国二龙到周复仇留下的唾液,化为玄鼋,玄鼋附于褒姒之母身上,历经周历王、宣王两代五十年而生褒姒。感龙漦而孕,母腹五十年,其出生神异处自然也被赋予社会政治内涵:“实亡周国”。
由此可知,母子之间的性别关系,在周代以后不再简单与生理联系,而是被赋予了社会政治意义,成为被建构的性别。显然,儒家伦理参与了对感物而生的帝王母子关系的改造:“经历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的意识形态的严重变革……生者、死者、仙人、鬼魅、历史人物、现世图景和神话幻想同时并陈,原始图腾、儒家宗教、和谶纬迷信共置一处。”[11]76惟其如此,近世帝王的部分母亲直接干政。例如,汉武帝刘彻为太子前,其母王美人联合长公主排挤太子刘荣之母栗姬,并终使刘荣太子之位被废,刘彻太子之位得立。刘彻为帝后,其母贵为太后之尊,干预政事更加激烈,逼死前朝重臣窦婴,重用外戚田蚡。还有吕太后、薄太后、窦太后等,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在近世帝王母子生孕关系中,社会政治意义已然加深。周代以前,夫妇之间的性别界限并不明显,有时甚至“夫妇不分”[12]107在今存卜辞之中,还可见到夏商之际妹嬉、妇好、太姜等直接参与军政的记载。从周代开始规范夫妻关系,“把父、长子关系作为纵轴,夫妇关系作为横轴,兄弟关系为辅线,以划定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次第的‘家’。”[13]35
三、生养之功与中下层社会的母子关系
相较于帝王之母据后宫之利多深陷宫廷斗争、直接干政、用尽心机辅佐儿子登上高位,而将相之母则只能利用自身的人格魅力,甚至生命影响儿子。这类母子关系在《史记》中共有27对,约占母子总数的21%。王陵母子、赵括母子、韩信母子、霍去病母子、陈婴母子等均为此类。
汉相王陵之母以死明志保得王陵一生平安。王陵之母,深得项羽尊重,东向而坐。但显而易见的是,王母所获尊位并非来于王母自身的社会地位,更非来于项羽的主动尊老,而是因为王陵“以兵属汉”为前提。换言之,王母社会地位的获得与其子紧密相关,王母因之在王陵与项羽的斗争中成为人质。富有意味的是,《史记》并未详述王陵对其母进行营救的具体措施,只用一句“陵使至”带过。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王母在自知可能成为儿子的负担后,为避免王陵“持二心”而选择“伏剑而死”的方式,以助儿子。更富意味的是,王母临死之前设计了儿子未来的政治之途:王母泣告王陵“汉王,长者也”,务须“谨事汉王”。王母之泣告含有生离死别的不舍,这反映出普遍的母性;而她之泣以及此后之死,更体现出一种要求儿子与项羽划清界限的政治姿态,要求儿子务必跟随刘邦的决然态度。《史记》中王陵对刘邦的态度极为复杂和摇摆,初为富豪时“不肯从沛公”,刘邦定天下后又“无意从高帝”,若非王母死前泣告明志,很难想象“少戆”的王陵能够得以封侯,甚至能够在得罪吕太后以后还能得以善终。就此而言,王陵之母不仅以自身的死作为一种感情策略和政治姿态为王陵明确方向和坚定决心,更是以自己之死保全了儿子此后的政治生命。从表面看来,王母之死演绎的是人类社会至今仍然存在的母性之爱,但王母为儿子而生而死的生存选择,其实质依然是工具性的。
赵括之母为救儿子性命,在众人皆认为赵括可堪大用赵母劝阻不能时,赵母直接上书于王:“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饮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赵括之母亲历数儿子脱离士兵、脱离实际、注重名利诸劣迹,表面看来是自我羞辱,在斥责儿子、大义灭亲的表象之下,赵母将教育儿子的家庭养育职能置于朝堂之上,实际上是将战争失败的后果提前交由众大臣和赵王分担,强行将赵王与儿子“捆绑”,试图为儿子赵括留下一条生路。尽管赵括因为刚愎自用而败死沙场,但“赵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诛也”。
淮阴漂母是《史记》所叙甚简的母亲。漂丝妇虽非韩信生母,但其“一饭之恩”对韩信影响甚深,且韩信一直将其视同母亲,故将其认同为韩信之母。漂母目睹韩信之饥而生母性之爱,数十日不辍为韩信供食养之,履行了培养儿子道德和理想的职能。故听闻韩信称自己为母时,漂母培养韩信理想的责任感促其怒责韩信,以此激发韩信的理想。钟惺对此评论说:信喜而言报,母怒,此一怒,何其有品也。所谓“品”是指这种为人之母的道德责任感。更为可贵的是,漂母怒责韩信徒有大丈夫之态而无大丈夫之心,这种责骂其实是否定之中的肯定,其中的肯定更为可贵。她肯定韩信是一个“大丈夫”,韩信确实有大丈夫之态。《史记》对此多有记载。例如:藤公“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齐人蒯通也谓“相君之面,不过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贵乃不可言。”无论是藤公还是蒯通对韩信的肯定,均不如漂母的肯定更能鼓舞韩信。因为漂母之肯定排斥了任何功利性目的——“岂望报乎”,而非蒯通等人有求而来,故其肯定应为发自内心,令人鼓舞。其次,彼时韩信正处落魄潦倒之际,漂母的赏识对于激发韩信走出困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这种理解和关切对韩信之后的人生道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由此不难理解,韩信被封为楚王后,最先想到的是报答漂母。
将相及其母子关系在《史记》中往往着笔不多,寥寥数语带过。但这种寥寥数语中包含了深刻的内涵。这类母亲因儿子的地位相较于国君要低,故难以直接参与政治斗争,或对儿子进行言传身教,或在儿子面临危境时,不顾自身安危以一己之力拼命保全儿子。此类母亲不图私利全心养育儿子,颇能代表中国古代母亲的自我牺牲精神。当然,这种牺牲也体现在母子性别关系中,即便是伟大的母亲也只能是儿子政治生活中的工具性存在。
极为可惜的是,由于中国古代正史多以上层人物为中心,因而平民母子关系在《史记》中所叙数量极少,且所叙也极为简略甚至其事迹无叙。如孔子母子、孟子母子、聂政母子、万石君母子等,其中吴军某士卒母子可为代表。
吴起军中某士卒姓名不详,其母也因之无详情可查。《史记》叙吴起为将时,与士卒同甘共苦:“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襄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某士卒之母“闻而哭之”。至于哭的原因,应该是极为复杂的。故其面对质询“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明确答复其哭非为感动:“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蔡师信评论说:“卒母前有丧夫之痛,后有失子之忧,也都毫无怨尤,而连称‘吴公’两次,以示衷心尊崇,该多不易。”[14]151此段评论说明,某士卒之母深明大义,也尊崇她并不了解的吴起将军,因而士卒之母实为烘托吴公之贤,这种分析不无道理。但是,对首领的尊称可能是下层社会中的普遍现象,因此仅凭称呼则断言其哭以体现尊崇似可商榷。求生乃人之本能,士卒既是国家之士卒,也是母亲的儿子。士卒舍身报国,其直接原因并非因为国家,而是因为吴起,因此在士卒心中,“士为知己者死”,吴起的地位显然超过了家中的母亲。而对于母亲来说,儿子在其生命中具有重要意义,可见“毫无怨尤”之说似有不通。某士卒之母其哭为何,应已昭然。其中既含亲情不舍,也含为母之悲。尽管这后一层悲不一定为她自觉,但按常理推之,也应是一种潜意识之客观存在。
四、结语
综上可知,《史记》中的帝王母子关系从简单的生产关系到社会意涵逐渐加深,呈现了性别建构由弱至强的发展轨迹。上古神话中的帝王母子关系,内蕴了上古时期人们“夫妇不分”的性别关系认知。而周末至汉初的近世帝王母子关系,内蕴了儒家伦理等参与建构性别关系的现实状况。无论感物而生的上古神帝,还是感梦而生的近世帝王,无论其父不在场所导致的帝命承于天,还是其父在场而强化的君命神授,其母子关系的内核均是为帝王地位的合法性获得具有神异色彩的支撑,母亲不过是神圣帝王得以出现的生殖载体。就此而言,无论是母仪天下、风光一时或争权夺利、结局凄凉的帝王之母,还是舍身救子的将相之母,抑或身份低微的平民之母,就其与其子的关系来看,莫不是通过儿子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史记》中的母亲们,在演绎一段又一段舔犊情深的佳话时,也在为自己的生命添加一个又一个附属于或遮蔽于儿子之身份的注脚。
[1]白寿彝.《史记》新论[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
[2]高发香.试论《史记》中的女性形象[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6.
[3]MILLETK.SexualPolitics[M].London:ViragoPressLtd.,1977.
[4]王晓路.性属理论与文学研究[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2).
[5]杨燕起,等.历代名家评史记[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6]高罗佩.中国艳情: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M].台北:风云时代出版有限股份公司,1994.
[7]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8]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9]贺璋瑢.两性关系本乎阴阳:先秦儒家道家经典中的性别意识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6.
[10]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9.
[11]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12]李泽厚.美学三书:美的历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13]赵玉宝.先秦性别角色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4]蔡师信.话说《史记》[M].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5.
(编辑:文汝)
G122
A
1673-1999(2016)12-0067-04
范明英(1971-),女,硕士,重庆科技学院(重庆401331)人文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对外汉语教学;彭体春(1972-),男,博士,重庆科技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2016-10-18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儒家伦理的固化与中和——《史记》中的母子关系研究”(13SKQ08);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巴渝竹枝词雅俗文化嬗变及互动研究”(2013YBWX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