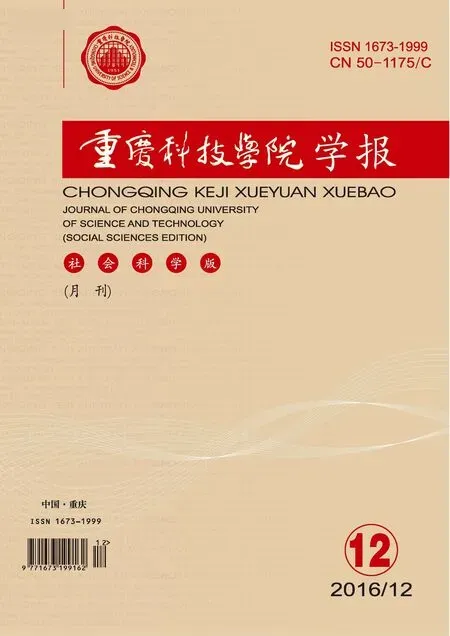中国西北乡村的水墨风俗画
——评贾平凹新作《极花》
戚慧
中国西北乡村的水墨风俗画
——评贾平凹新作《极花》
戚慧
贾平凹新作《极花》不仅关注被拐卖女子胡蝶的所见所闻和心路历程,也思考乡村光棍们的生存处境。小说中的意象丰富,极花、血葱、何首乌、剪纸等事物与胡蝶、老老爷、黑亮等人物构成一幅精致的圪梁村水墨风俗画,传达了贾平凹对中国西北村民的生存状态和命运的关怀,体现了作家悲悯的情怀和深切的思考。
贾平凹;《极花》;人物形象;意象;人性关怀
作为中国乡土文学的创作大师,贾平凹写过不少农村题材的小说,如《商州》《浮躁》《土门》《怀念狼》《秦腔》《古炉》《带灯》等。在这些作品中,他对中国乡村保持了持久的关心,并进行了具有个性的表达与记录。现今,城市文明的快速发展加速了乡土文明的衰败和瓦解,中国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的精神家园一去不复返了。面对社会的急速转型,身处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贾平凹拒绝对农村进行诗意般的描绘,而是裸露其野蛮残忍的一面,反映传统伦理观念的深刻变化,表现出直面现实的勇气。《极花》就是一部带有强烈的现实感和当下性的力作。
《极花》的故事背景没有放在他熟知的故乡陕北商州地区,而是放在更遥远的西北地区一个荒凉闭塞的山村——高巴县圪梁村。小说以女主人公胡蝶的口吻讲述了被拐卖的经历、遭遇。贾平凹在小说后记中谈到故事是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的,事情发生在他老乡女儿的身上,老乡女儿刚进入城市就被拐卖到贫苦山村,被公安解救回城后又回到了被拐村庄。贾平凹在十多年前听到这个故事,像刀子一样刻在他的心里。为何多年后才提笔写这个故事呢?贾平凹解释道不想把这样的事件“写成一个纯粹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故事”[1]。读过《极花》的读者不难发现,这部小说不是单纯的拐卖妇女的故事,贾平凹无情地揭示了乡村文明的愚钝和落后,表达了对中国农村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生存状态的关怀和忧虑。他密切地关注着当代中国农民的命运与处境,体现了当代作家博大的悲悯情怀和深切的思考。
一、圪梁村的人物风情
《极花》从女性角度叙述全文,女性一直是贾平凹小说中美和理想的象征,是诗意的寄托。虽然整个世界沦落了,但对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仍寄寓着一份幻想。小说前半部分主要叙述了被关在窑洞里的胡蝶对未知村庄的所感所闻,并插叙了她被拐前的身世。胡蝶怀着朦胧的希望从农村走进城市寻找生路,在找第一份工作时就被拐骗了。胡蝶的被拐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缩影,与许多女孩被拐经历相似,她们初入城市,没有生存经验,爱慕虚荣,不知城市的险恶。小说的后半部分讲述的是走出窑洞的胡蝶以她的眼睛来观察和审视所处的村庄。胡蝶被黑亮强迫占有后生下儿子,她对圪梁村由最初的厌恶与嫌弃到逐渐的认同。胡蝶的叙述充斥着日常生活的琐碎、絮叨的话语与细节的呈现,表达了她对乡村文明的认同感。小说结尾,胡蝶在梦境中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还乡”。她的被解救演变成一个荒诞的寓言,回城却面临着是要儿子还是要娘的选择悖论——人性与母性的分离,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创伤。胡蝶返城后遭受了更大的心理压力,成为“被看者”,没有退路的她只好选择回到圪梁村。从农村走进城市,从城市被拐骗到农村,从农村被解救回城市,再从城市返回农村,她像游魂一样在城乡之间飘浮。胡蝶最终并没有找到来寻她的娘,在风中她像纸片人一样贴在窑洞的墙上。她的名字是一种暗喻,她是胡蝶也是“蝴蝶”,只有经历了破茧后的疼痛才能完成成长与蜕变。正如贾平凹在接受采访时所说:“胡蝶不一定是要‘认命’才能达到与现实的和解”“能够得到认同更重要”“人的烦恼和痛苦往往来自不了解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如果城市让胡蝶无所适从,圪梁村的人情风物或可给予她安慰[2]。
圪梁村还有一群像胡蝶一样被拐卖来的女人,她们在生育后代的同时,还担任繁重的体力活,精神与活力被男人和土地消耗着,承受着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双重伤害。贾平凹曾谈道,胡蝶可能是訾米姐,可能是麻子婶,中国乡村有太多这样的胡蝶,她们过着悲惨的生活。大地以宽广、深厚、坚韧的精神抚平人们心灵上的伤口,平息着人类的愤怒和不安。在《极花》中,圪梁村的土地是贫瘠的,大地的力量转移到女性的身上,女性成为繁衍的母体。
城市化的发展加速了农村的衰败,外出打工的农民越来越多,留守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贫瘠多灾的土地上想着如何生存下去,他们为各自的生财相互算计、唯利是图、目光短浅、心灵扭曲。村民丧失了淳朴的本色和善良的本性,异化成山林的动物,弱肉强食。他们通过购买女人来满足原始的欲望发泄,光棍们的家门口都刻着石女人像,希望可以招来女人。村民的家里挂着写上“德、孝、仁”字的葫芦,墙上挂着装极花的镜框,门口放着石刻的女人像,各个窑洞门雕刻成男人的生殖器状,原始乡村所推崇的美德无法满足男人的欲望。男人们抱怨城市吸走了村里的女人,使他们沦为光棍。贾平凹并没有把笔下的村民写成极恶之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们的苦衷与不幸,因而给予了他们更多的宽容和同情。
黑亮作为乡村有知识的新农民,一方面秉承传统农民吃苦耐劳的品德,另一方面他有野心和胆略,善于抓住商品经济的机遇。黑亮勤劳上进,一心想把日子过好,在村里娶不到媳妇,他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了拐卖媳妇的行列中。黑亮也有善良的一面,他爱护胡蝶,从镇上单独买白面馒头给胡蝶吃,挣的钱交给胡蝶,被胡蝶骂后独自哭泣。黑亮爹是传统农民的代表,吃苦耐劳又因循守旧,他的生活经验促使他做人行事都小心翼翼,对任何人都客客气气,一心想给儿子娶个媳妇传宗接代。瞎子叔的存在让人感动,他眼睛虽瞎但心不瞎,是一个善良也容易被忽视的人。乡村的男人们或遭遇横祸死去,或懦弱无能苟且地活着,或自私自利。作为农村基层的管理者,村长自私自利,狡猾奸诈,在村里作威作福,好色猥琐,长期霸占村里的寡妇,与村里的媳妇私通。老老爷无疑是山村智者的化身,也是乡村伦理及其信仰世界的建构者和维护者,他企图建构一套维持乡村和谐、稳定的宗法制度。他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构成民族总体文化必须有天、地、人三个层次,只有天时、地利、人和乡村才能和谐发展。在乡村文明凋敝和淳朴民风丧失的背景下,他只能是孤独的坚守者。圪梁村不再是乡风淳朴的村庄,它黏糊、浑浊。在这个人性爆发恶的年代,老老爷注定是要失败的,但他毕竟疗救了一些村民,并尽力维护人伦道德,祈求乡村的和谐与安稳。
贾平凹在《极花》的后记中追问道:“偷抢金钱可以理解,偷抢财物可以理解,偷抢了家畜和宠物拿去贩卖也可以理解,怎么就有拐卖妇女儿童的?社会在进步文明着,怎么还有这样的荒唐和野蛮,为什么呢?”[1]在中国大转型的年代里,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寻找发展机会,尽管他们的境遇很差但不愿意再回到乡村,乡村人口越来越少,光棍越来越多,购买被拐卖的妇女成为他们满足欲望的途径。贾平凹坦承“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他同时看到“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1]贾平凹在关注被拐女人的同时,也在担忧着乡村里光棍们的婚姻问题。城市文明的发展吸走了乡村的女人,城市里的男人享受着多余的女人,乡村的光棍们依赖土地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却无法娶妻生子,无法满足性需求。这种买卖是违法的,但乡村的延续如何解决,乡村里人都没了,到哪里去为乡风民俗招魂?这并非危言耸听,“空心村”现象并不在少数。《极花》不仅关注现实,还关注个体存在的境遇、死亡、自然生态的状况、人性细微的变化等方面。面对衰败的乡村,贾平凹着力呈现的是在具体、细节处灵魂的挣扎,满怀悲悯地看待他笔下穷苦的人们。
二、丰富而隽永的意象
《极花》中意象丰富,充满了象征意味。正如贾平凹在小说后记中所说:“我的小说喜欢追求一种象外之意,《极花》中的极花、血葱、何首乌、星象、石磨、水井、走山、剪纸等等,甚至人物的名字如胡蝶、老老爷、黑亮、半语子,都有着意象的成分,我想构成一个整体,让故事越实越好,而整个的故事又是象征,再加上这些意象的成分渲染,从而达到一种虚的东西,也就是多意的东西。”[3]贾平凹认为他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水墨画的本质是写意的,体现艺术家内在的自我修养,成为内在灵魂的载体。水墨画是中国的传统绘画,贾平凹善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创作元素,把水墨画的艺术追求转化为文学上人格理想的建构。文学可以直面苦难并超越苦难,拯救自我,体现作为作家的贾平凹对生命的关怀和人道主义的理想。贾平凹曾说:“小说就是要写这生活的黑白之间,人心里极难说出来的东西。”[2]他借助极花、血葱、何首乌、星象等意象呈现这些极难说的东西,构成一种虚化的意境,却又是真实的、实在的。
《极花》中的高巴县圪梁村地处闭塞的西北地区,是一个在连绵不绝的黄土高原上的苦寒的村子窑。圪梁村无疑是中国广阔大地上残破古老村庄的缩影,村里的4棵白皮松像是水墨画中的静景,见证了乡村的历史发展。走山是这里常发生的自然灾害,贫穷荒凉的山村加上频繁的自然灾害,卑微的人们更加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凸显出一种悲凉的无力感。在贾平凹早期的小说中,他常常营造一种平静的乡土生活氛围,表达对乡风民俗的挚爱,对淳朴人性的赞美,总体上显示的是和谐光明的一面。恬静灵动的田园诗、田园梦融入商州山川和风情民俗之中,当然也并非水波不兴,冲突和矛盾更像是水面上的涟漪点缀其上。《极花》中的圪梁村更像是一潭死水,水下涌动着各种躁动、不安和欲望。贾平凹认为传统乡村的组成包括4条线:基层政权、法律、宗教信仰、家族。小说中这4条线都扭曲了:以村长为首的基层政权,无法发挥正常的组织作用,村长贪色重利,更像是一个乡痞恶霸;以派出所所长为代表的法律体系,因地方偏僻难以实现法律的效力;老老爷是乡村宗法信仰的建构者和坚守者,面对乡村的凋敝,他注定是失败的;家族之间、同姓兄弟之间因利益纠纷争吵不断,人物的命运与乡村风俗、文化、伦理、宗法制度相裹挟、拉扯。乡村传统信仰的象征——庙宇,早已毁于一旦,只剩下断壁残垣,乡村只能走向无序和衰落。
极花和血葱是小说中两种特殊的意象。极花是西北地区的特产,是一种虫草,在冬天是虫,在夏天是草,类似于冬虫夏草。当村民认识到极花的价值时,大量采挖,以至极花越来越少濒临绝迹。村里的光棍想女人,纷纷效仿黑亮在墙上挂上装有极花的镜框,希望可以招来女人。极花是一种女性的精神象征与命运写照,极花和村里的女人一样也越来越少。极花是胡蝶的寄托与希望,她把极花看成是和外界的特殊通讯物。极花在冬夏之间可以转换寓意,胡蝶也会完成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身份转变,极花在寒冬和酷夏都能顽强生长则象征着女性的坚韧与强大的生命力,表达了贾平凹对女性悲悯的情怀和人性的关怀。血葱象征男性的生命力,被看成可以增强性欲的神奇植物。血葱似乎是不幸的源泉,张老撑被砍死了,立春、腊八两兄弟在血葱生产基地被山体掩埋了。经历走山后,男人们继续筹划建立新的血葱生产基地,但基地还未建立,男人之间就因利益分配相互制衡和纠缠。“食色,性也”。圪梁村的男人们性欲尤其强烈,过剩的欲望无处发泄,被拐卖的女人则成为他们的眼中肉。血葱与男人的性欲、商品经济的追求相互交织,渲染着躁动不安的氛围,欲海难平。
星象是《极花》中重要的意象,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观星象变化以占测人事吉凶福祸的传统,为了自身的生存从未停止对星象奥秘及其与人事之间关系的探索与追问。星象学不是单纯的天文自然科学,它与政治、宗教、民俗等方面相互联系,体现人类原始的天命观、宇宙观、人生观。《易经》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星是天的象征,天、地、人构成乡村文明的3个层次。在这3个层次中,天是最高级的层次,人类代代不断繁衍生息,天自远古便见证了人类的生存历程,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终极生命关怀。小说中多次出现老老爷夜晚坐在磨盘上抬头观看星象的场景,天上的星辰和地上的人事密切相关,不仅可以指导农业上的观象授时,细化为占星有术,考察地域分野,还可以得知个人命运的吉凶祸福。星对于胡蝶是一种安慰与希望,象征着认同感和归属感。广阔深邃的夜空,抬头仰望星空,寻找属于自己的星,表达了一种豁达的生命观。贾平凹在《极花》中借老老爷的星象观来表达文学与星象、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扩展了小说的内涵意蕴。
小说中的石磨和水井是农耕文明的象征,具有时间静止性的特征,在静静的历史长河中,见证着村庄的发展和村民的繁衍生息。自古民以食为天,石磨是生命延续的重要纽带。毛驴拉着石磨,在原地不停地转着圈,石磨深深扎根在土地上,象征着乡村的封闭与守旧。石磨是石器时代的产物,破损的石磨默默对抗着城市的商业文明和科技文明。水井是维系村庄生存的根本。在原始社会中,每个村落往往只有一口水井,人们聚居在水井附近繁衍生息。水井是村庄的象征,在客观上和精神上有一种聚合的内在力量。因水井本身的特点,代表了村庄里的村民们走不出去的思维和困境。黑亮家的水井像是老古董,打水费时费力,只能拉出半桶带泥的水。水井是村民生命繁衍的源泉,生命之水面临枯竭预示着大地上人脉的衰弱。黑亮爹每天晚上不厌其烦地用绳子把胡蝶的高跟鞋拴吊在水井里,第二天早上再把高跟鞋从水井里提出来。这一举动似乎是在进行某种仪式,为胡蝶招魂,赶走她身上带来的城市里的气息,把乡村的气息带给胡蝶,让她安安稳稳给黑亮当媳妇。黑亮爹的行为无疑是可笑而愚昧的,只是想祛除他心头的鬼魅。
剪纸是西北地区的民俗。村里供神奉祖、祭奠死人必须献花朵和瓜果,然而圪梁村常年缺水多旱,花草瓜果少,为图省事用剪纸来代替。剪纸又被村民称为“剪花花”,成为一种装饰,贴在家里的门上、窗上、墙上、炕壁上等地方,祈求辟邪压鬼。麻子婶迷恋剪纸,被丈夫打骂也不改剪纸的爱好。剪刀在她手中旋转自如,原本平整的纸面却可以剪出各种动物、景物。她把剪纸当成敬神,在走山中昏死后复活,剪纸手艺如有神助而更加精湛。麻子婶对剪纸的痴迷体现了一种艺术的生活哲学,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妥协。
人活着总要有一种希望,麻子婶把活着的乐趣寄托在剪纸上,正如她自己所说的没心没肺才能活下去。胡蝶拜她为师学习剪纸,继承了这一传统习俗。剪纸成为麻子婶、胡蝶等人心灵的安慰。不难发现,贾平凹对剪纸等民间艺术的热爱与赞美之情,他借乡村女性对剪纸的向往表达了乡村物质的贫乏阻挡不住人类心灵对丰盈与充实的向往与追求。贾平凹对中国神秘文化,特别是对民俗文化中带神秘色彩的内容有着浓厚的兴趣。小说中的狼、红狐、野马、野驴、黄羊等动物的出现,胡蝶的梦、看到的黑洞、麻子婶的复活等,都营造了一种神秘和虚化的氛围,体现了作家对世界、自然、死亡、神秘事物的敬畏。
三、悲悯而博大的人性关怀
《极花》不仅关注了被拐卖女子胡蝶的所见所闻和心路历程,也思考着乡村里光棍们的生存困境。在贾平凹的笔下,对村民生活的描写几乎是一种原生态的呈现,写出了日常化、生活化,写出了真情,写出了人性的扭曲,写出了个体生命的生存困境。小说意象丰富,极花、血葱、何首乌、剪纸等事物和胡蝶、老老爷、黑亮等人物构成一幅精致的圪梁村水墨风俗画。贾平凹对自己的写作一直有强烈的反思情结,他的创作冲动不仅来自内心,也来自对日常生活的感悟和体验,他希望通过《极花》传达出胡蝶的控诉。原生态地呈现是贾平凹的梦,是他文学的根,是流淌在他体内的血液,也是他无法割舍的牵挂。他在文学中呈现的缺失与痛感是真挚的,他的真情流露是我们无法拒绝的。
文学总是关注人的,关注人的命运。文学在暴露生活的同时,应该给社会、给人提供一种文化的终极关怀。他没有在小说中指出谁该为拐卖妇女、乡村衰败承担责任,更多的是茫然、无奈、困惑和反思。也许总有一天乡村里的人们要隔断与大地母体相连的脐带,在城市开出自己的花。贾平凹没有写出故事的结尾,而是给出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实际上他也在思考胡蝶、村民以及整个中国乡村发展的出路与未来。贾平凹相信“中国农村是历史逐渐形成的,它就应该有它维系和自我修复的东西”。他无法开出一剂救世的良药,现今的状况他无法预料,但他清醒地意识到乡村的过去和现在,却不预知它的未来。当下对性的写作需要勇气、胆量和决心,贾平凹恰恰是一位有担当的作家,他以自己的文字书写在文坛上坚守着,他的写作不仅仅是为了平息躁动的灵魂和不安的内心,更重要的是在写作的过程中赋予文字坚韧的美、力量和精神。
[1]贾平凹.《极花》后记[J].东吴学术,2016(1).
[2]毛亚楠.贾平凹:《极花》不仅仅是拐卖和解救的故事[J].方圆,2016(6).
[3]吴娜.贾平凹:“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N].光明日报,2016-04-15.
(编辑:文汝)
I207.42
A
1673-1999(2016)12-0061-03
戚慧(1991-),女,武汉大学(湖北武汉430072)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2016-0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