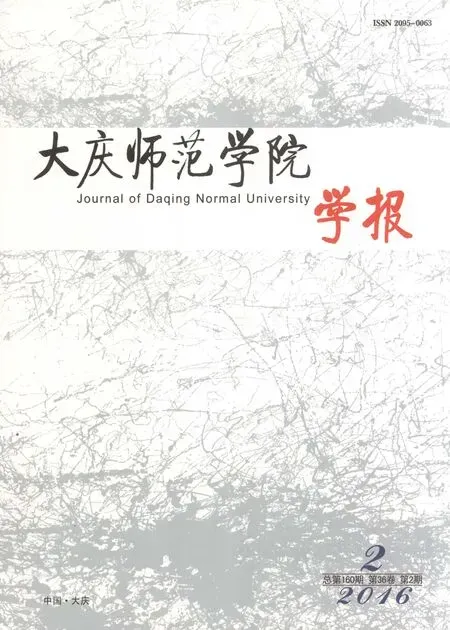当代历史小说的影像化叙事
袁 园
(洛阳师范学院 河南文化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洛阳 471934)
当代历史小说的影像化叙事
袁园
(洛阳师范学院 河南文化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河南 洛阳 471934)
摘要:随着视觉文化时代的来临,影像逻辑渗透历史小说叙事内部,如叙事语言、叙事情节、小说文体等诸多环节,使得印刷文化语境下历史小说的叙事技巧遭到改写。日益边缘的纸媒历史小说接受影视剧的收编,将影视叙事手法与视觉思维引入到历史小说写作之中,从而催生出大规模的影像化叙事潮流。
关键词:历史小说;影像化叙事;视觉文化
20世纪90年代随着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印刷文化语境下的历史文学生态。影视艺术把枯燥的历史转换为通俗易懂的画面,迎合大众的口味讲述故事,其叙事的平面性、娱乐性、感官性、瞬时性特征,使得印刷文化语境下历史小说的叙事技巧遭到改写、删减甚至淘汰。纳塔丽 · 萨洛特指出:“由于顽固地坚持过时的技巧,小说已经变为一种次要的艺术了。现在应当采取类似现代画的行动以寻求小说独特的创作途径和特有的表现方式,把不属于自己范围的东西让给其他的艺术。”[1]面对影视艺术的竞争,如果历史小说再顽固坚持印刷文化时代的叙事技巧,不能有所创新,其生存就会成为问题,文化语境的变革迫使历史小说必须改革叙事方式,以适应视觉文化的需要。另一方面,从具体的实践层面说,“随着电影在 20 世纪成了最流行的艺术,在 19 世纪的许多小说里即已十分明显的偏重视觉效果的倾向,在当代小说里猛然增长了。蒙太奇、平行剪辑、快速剪接、快速场景变化、声音过渡、特写、叠印——这一切都开始被小说家在纸面上进行模仿。”[2]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边缘的纸媒历史小说为了生存被迫接受影视的收编,遵循文化工业的生产法则,迎合导演与受众进行创作。以影视剧改编为动机的历史小说创作,影视逻辑势必进入历史小说内部,将影视剧叙事手法与视觉思维引入到历史小说写作之中,从而催生出大规模的影像化叙事潮流。具体说来,历史小说的影像化叙事突出表现出以下四个方面:
一、历史叙事语言的视觉化效应
历史小说改编为影视剧,首要环节就是将抽象文字符号转换为可见的图像语言。对于影视剧拍摄而言,越是写实的、造型性的与形象性的语言,就越容易拍摄为画面;反之越是抽象、多义、模糊的语言,就很难转换为图像。为了适应影视改编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历史小说极力凸显小说语言的镜头感、画面感与空间感,尤其注重小说语言的视觉形象性。作家普遍转换创作思维方式,以形象思维取代深度模式,避免大段的抒情、意识流与心理分析描写,减少议论性、说明性和抒情性的文字,尽量将笔下的写作对象以视觉的、造型的、形象性的语言予以表现。“它不限于某一特定的语言系统和叙述方式,可以运用声(音响、旋律、节奏)、色(色相、色度)、形(线条)等多元语言系统的自由交叠来描述形象,从不同的感觉、知觉范围(视、听、味、触觉),引起读者(经过艺术通感的联觉)的视觉效应,而使形象构成获得立体的质感和美感。”[3]具体说来,作家遵循语言与图像相互模仿的机制,顺应语言与视觉图像的逻辑关系,借鉴构图、光影、色彩、线条来描述形象,从而激发读者的视觉效应,获得立体形象的阅读感受。“新批评派”理论家维姆萨特提出“语象”( Verbal icon),用来指代以语言为媒介刻画的视觉形象,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提出了语言图像论,阐释了语言与图像的对应关系,又被称“图式说”( Theory of Picture),如果说上述研究还停留在形而上的理论层面,那么在实践层面对于历史小说影像化叙事,历史何以通过语言被外化为图像,或者换句话说,历史图像在以何种方式被言说。
历史小说将影视剧的历史图像以书面语言为媒介予以转换,实现语言文字的抽象性与图像的直观性对接,具有影视语言的镜头感、画面感和动作感,从而实现了纸质媒介上的影像表现,不仅激发起读者的视觉效应,而且方便了导演的影视改编。比如莫言《红高粱》运用影视拍摄的全景镜头,凸显鲜明的色彩反差,如火红的高粱、瓦蓝的天空、洁白的云彩、暗红色的影子,形象地描绘出如火如荼的高粱地场景,如同一幅油墨重彩的油画映入读者眼帘。孙皓晖《大秦帝国》中的服饰描写如同影视的特写镜头,细致地展示了主人公的装束,作者的笔触如同一台移动的摄影镜头,慢慢地扫过古代服饰的细节部分,逼真再现了古人的服饰。二月河《雍正皇帝》中众人搭救落难民女乔引娣的描写,如同蒙太奇剪辑的三个镜头:众人将乔引娣抬放在大殿,有人给乔引娣灌酒以及乔引娣气色逐渐恢复,三幅画面之间逻辑连贯衔接自然,使读者产生现场感。凌力《少年天子》为读者描绘出皇帝出行的盛大排场,通过礼仪、器具、服饰的相关描写,极力突显出视觉的冲击力:在造型上,有单龙、双龙、圆形、方形、鸟翅形等诸多形状的扇子;在色彩上,有黄、红、白、青、黑、紫不同颜色的伞;在具体意象上,有幡、幢、麾、节、氅、枪、戟、戈、矛、钺、星、卧瓜、立瓜、吾仗等种类繁多的出行仪仗器具,以上描写可以毫不费力地被导演转化为影视语言,运用中景与近景镜头的衔接替换,再结合镜头的推、拉、摇、移,全方位再现皇帝出行的历史图景,给观众以强烈的视觉震撼。
二、历史叙事故事情节的凸显
回溯五四以来的历史小说,无论是现代文学时期鲁迅《故事新编》、冯至《伍子胥》、施蛰存《将军底头》、郁达夫《采石矶》,还是新时期以来的新历史小说如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李晓《相逢在K市》、苏童《1934年的逃亡》、格非《迷舟》、王小波《红拂夜奔》,以及女性历史小说赵玫“唐宫三部曲”、庞天舒《王昭君》、王晓玉《赛金花·凡尘》、王小鹰《吕后·宫庭玩偶》,上述作品都是在印刷文化语境下创作,沾染着浓重的现代主义、精英文化与审美文化色彩,这突出表现在文本的深度模式上:淡化故事情节,不注重趣味性与可读性,模糊人物性格,深入发掘历史人物的潜意识、生命感受与精神世界,以及对历史人物生存境遇的深刻反思。
米尔佐夫指出:“印刷文化当然不会消亡,但是对于视觉及其效果的迷恋(它已成为现代主义的标记)却孕生了一种后现代文化,越是视觉性的文化就越是后现代的。”[4]如果说印刷文化滋生现代主义文化、精英文化和纯审美文化,那么随着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后现代文化、消费文化与大众文化成为文化中心,全面地改写着历史小说叙事法则。印刷文化语境下的历史叙事策略,由于注重深度发掘人性与潜意识,既不具备观赏性也缺乏趣味性,给小说的影视化改编带来极大难度,不可避免地被视觉文化所改写。为了迎合读者的欣赏习惯,考虑制片方的要求,以及增加被改编为影视的概率,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历史小说叙事情节性显著增强,内心独白、议论、心理分析、意识流描写比重降低,呈现由内到外、由深度到平面化、由可思性转向可视性的转换趋势。
与新历史小说不同,作家普遍放弃先锋叙事策略,高度重视情节的编织与矛盾冲突的营造,大量运用故事情节编排技巧,如安排故事悬念、穿插偶然性巧合、延宕冲突高潮等,突出叙事的故事性、戏剧性与观赏性,激发读者的期待心理,力求对读者产生吸引力。
比如二月河《雍正皇帝·九王夺嫡》中康熙的诸多皇子为争夺皇位,无不明争暗斗跃跃欲试,宫廷内外杀机四伏扑朔迷离,太子党、八爷党、四爷党、年羹尧、隆科多诸多势力彼此之间相互倾轧,不同派系相互拉拢又彼此争斗。二月河围绕雍正争夺皇位作为主要矛盾冲突,设置了跌宕起伏的情节,运用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条,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矛盾冲突尚未结束,另外一个矛盾瞬间激化,当读者原以为情节走向会按照所想象那样发展,却不曾料想情节急剧转折情形突变。作者二月河借鉴明清白话小说章回体式,将故事情节设计得峰回路转疏密有致,力求使得每一个章节都有看点,因而非常适宜改编为电视连续剧。
熊召政《张居正》开篇就描绘隆庆皇帝驾崩后各派势力的激烈争斗,张居正联合太监冯保驱逐首辅高拱,高拱在朝廷根基深厚岂肯就范,召集党羽共同弹劾冯保,并借审问妖道王九思扳倒对方,激烈的矛盾冲突围绕三人之间展开。当高拱带领百官敲响登闻鼓呈上弹劾冯保的奏章,马上就要取得权利斗争的胜利,没想到剧情突然逆转,高拱被勒令解除首辅职务,原来在关键时刻,张居正秘密觐见李太后,赢得了皇后的支持,最终取代了高拱的首辅的位置,为以后推行万历新政埋下伏笔。
刘和平《大明王朝1566》以扳倒权倾朝野的奸相严嵩为故事情节的主线,全方位展现明朝嘉靖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历史时期,从朝廷到各级官府不同政治势力的博弈,以高拱、张居正、胡宗宪、戚继光、海瑞、徐阶为代表的忠臣集团为了拯救天下苍生,痛斥严党把持下的朝政贪污盛行土地兼并,而以严嵩、严世藩、郑泌昌、何茂才为首的严党势力瞒上欺下,对忠臣集团展开了疯狂的打击报复;身处矛盾斗争幕后的嘉靖皇帝,表面上修道炼丹不问朝政,暗地却密切监控着朝廷各个派系的举动,软硬兼施恩威并重,巧妙地平衡着不同派系的政治势力。诸多人物之间亦敌亦友,关系错综复杂,彼此之间相互利用尔虞我诈,如何在重重困难之下扳倒严嵩,成为推动故事情节矛盾冲突发展动力,营造出波谲云诡的故事悬念,适合改编为影视作品,如作者所言:“我写的小说,利用了电影手法,充分地故事化、情节化。不仅有故事,有情节,而且故事情节发展地有声有色,叫读者意想不到。我写的小说最能改编成电影。”
三、历史小说文体的剧本化倾向
历史小说与影视剧本是两种不同的叙事文体,影视剧本是用文字来表现尚未拍摄的影视情节内容,从而为导演提供拍摄蓝图和工作大纲,影视剧本由四个基本要素构成:场景描写(Scene)、人物(Character)、对话(Dialogue)和动作描写(Action),剧本以场面为叙事基本组成部分,每个场面又由若干通过蒙太奇剪辑镜头构成,是影视创作的脚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小说作家兼职或专业做编剧,为了方便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历史叙事手法借鉴剧本的创作方法,小说文本出现了大量的场景、人物、对话与动作描写,作为时间艺术的小说与属于空间艺术的影视剧本文体混溶,叙事呈现出鲜明的空间感、视觉感与动态感。
刘斯奋《白门柳》开篇描写了女性闺房的环境,典型地对应着剧本中的场景描写,呈现出鲜明的空间化特点。这个场景描写包含五幅画面:放置着桌椅的地板、铜火盆边的屏风、墙壁上的古画、古琴和线装书、一只冒着烟的香炉。作者的笔触如同电影拍摄的摇镜头手法,通过镜头角度和方向的变化,用蒙太奇手法将五幅画面剪辑,全面地再现闺房内的摆设,为人物的出场交代了具体的地点与场景,不需要任何加工就能转换为影视语言。二月河《乾隆皇帝》借鉴了影视剧本中的人物描写,作者对清代市井人物的样貌服饰细致的描写,呈现出鲜明的视觉化效果,尤其是对人物的细节描写,类似于影视剧本的中的特写镜头,逼真地再现了清代人物的穿着打扮、容貌特征以及性格气质。小说的人物描写从中景拉近到近景,最后定格到人物的某个局部,以大特写的镜头结束,典型地呈现出空间距离的变化,给读者留下栩栩如生的视觉化印象。都梁《亮剑》逼真再现八路军战士与数名日本鬼子的拼刺刀的场面,凸显出动作的连贯性与造型性,作者将视点始终聚焦在八路军战士和尚身上,逼真再现其一连串的动作:捅刺、仰面倒地、360度的摆动,充盈着视觉的冲击力,如同运用长镜头连续拍摄画面,跟踪捕捉八路军战士的连贯性动作,使观众的眼睛始终锁定在激烈的打斗动作上。薛家柱《胡雪岩》中的对话描写,典型地表现出影视剧本对白的艺术特征,比如人物对话简短凝练,比如王有龄看见讨债人的反应就是一个感叹词:“啊?”并且引用民间谚语诸如“躲得过十五,躲不过三十”,“不见棺材不掉泪”,富有浓重的生活气息。此外人物对话具有强烈的动作性、情绪性和性格特征,诸如摆手、冲到床边、喷着吐沫星子等细节描写,不仅有效地烘托了历史人物形象性格塑造,而且交代了小说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四、历史叙事的空间化特征
与摄影、雕塑、电影强调空间造型的艺术门类相比,小说是时间的艺术,叙事必须在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双重制约才能产生意义,福斯特指出:“小说把时间摒弃后,什么也表达不出来。”[5]尤其是以历史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对故事时间要求更为严格。作家必须在严谨历史考证基础上,遵循线性连续的时间链条展开叙事,如果小说中的人物、事件、习俗、器物等细节与历史时间不符,不仅被视为违背历史真实,而且证明作家历史基本功底欠缺,历来为历史小说创作所忌讳。
然而,随着视觉时代的到来,历史小说创作呈现出空间化叙事的倾向,突出体现在历史叙事的时间逻辑让位于空间逻辑,降低甚至取消对历史时间真实性考证,割裂时间的连续性与整体性,将过去、现在、未来的人物与事件并置,情节发展并没有承前启后的逻辑关系。此外,线性的时间让位与视觉化的空间,历史场景以及环境描写比重增加,其重要性由陪衬位置上升为艺术本体,从而迎合大众对于历史文学的视觉化需求。因此,经典历史文本留给读者深刻印象的并不是历史故事情节,而是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历史场景,比如莫言《红高粱》渲染的如火如荼绵延不断的高粱地,苏童《1942年的逃亡》描绘的红罂粟遍地的枫杨树故乡。
新世纪以来,穿越历史小说的勃兴更是为空间化叙事推波助澜,文字的画面空间感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瞬间的空间体验与时间感的停滞、视觉感官的充分展开以及深度审美体验的丧失,是空间化叙事给读者带来的第一印象。穿越历史小代表作品无论是《回到明朝当王爷》《梦回大清》《唐朝好男人》,还是《三国之最风流》《窃明》《1911新中华》,或者《诛仙》《北唐》《极品家丁》,都打破按照历史时间先顺序组织情节的叙事模式,而是将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与事件并置在同一空间,以空间逻辑来展开叙事。上述小说故事情节通常是现代时空的主人公因为意外,穿越时空回到特定朝代或者虚拟时代,线性时间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被打破,拥有现代知识的主人公置身于千年前的历史空间,从而产生陌生化与反差性的艺术效果,不同于传统历史叙事,衔接故事情节的是频繁的场景转换,人物、事件、意象描写均在历史空间展开,从空间维度而不是时间维度建构美学特征。
因此,历史空间叙事不仅迎合了读者轻松愉悦的接受心理,而且很大限度方便了影视改编,蕴含着鲜明的视觉文化内涵。从根本上说,视觉文化时代无孔不入的影像,在强化了人们视觉感官的同时,也抑制了其他感官功能,改变了人们感受世界与接收信息的方式,人们对空间的视觉化形象感知取代了深度审美模式,从而导致历史小说空间叙事的勃兴。
[参考文献]
[1] 纳塔丽·萨洛特.冰山理论与潜对话:下册[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565.
[2] 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4.
[3] B·普多夫金.论电影的编剧导演和演员[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32.
[4] 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3.
[5] 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7:69.
[责任编辑:金颖男]
Image Narration of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Novels
YUAN Yuan
(Henan Cultural Transmission Research Center,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Luoyang, Henan 471934, China)
Abstract:As the era of visual culture comes, the image logic permeates the narration of historical novels, and is seen in its language, plot, style, etc, which changes the narrative techniques of historical novels in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printing. Marginalized paper historical novels are influenced by movie and television plays by absorbing their narrative skills and visual thinking, which creates a massive image narration trend.
Key words:historical novels; image narration; visual culture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063(2016)02-0074-04
收稿日期:2015-11-20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历史小说影像化叙事研究”(2014BWX035) 。
作者简介:袁园(1977 -),男,江苏徐州人,洛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当代历史文学研究。
DOI 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6.0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