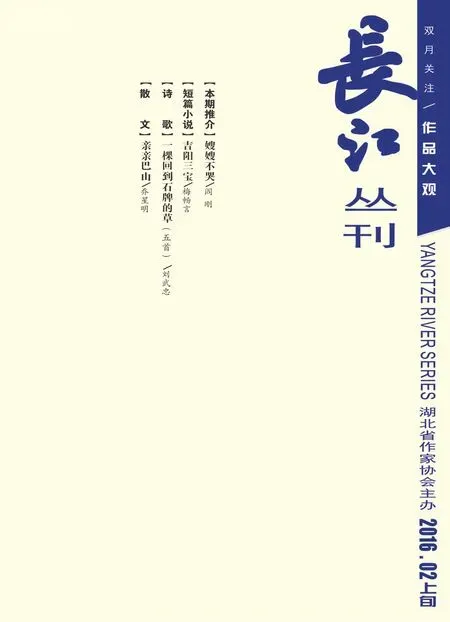吉阳三宝
■梅畅言
吉阳三宝
■梅畅言

梅畅言,湖北安陆人。自由职业者。16岁在《中学生课堂内外》发表处女作《惜食》。在各类报刊发表过散文《唠叨》、《初为人父》、《村头那棵皂角树》、《故园之恋》,小说《树上的鱼》等。
吉阳山,地处鄂东北大别山桐柏山脉尾尖。站在山顶,往南一看,卧一狭长集镇,便是吉阳古镇。因有山,交通十分不便。但只一条安应公路贯穿其间,除此只能走一羊肠小道,与应山、孝感两县接壤,乃鸡鸣三县之地。而三县衙门皆对之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自娱自乐。正是得益于这等无拘无束的宽松环境,便造就了这穷乡僻壤里的乡民血性刚烈,民风强悍。当年,乡民自发组织的游击队,几十条火铳,百余杆梭镖,配合新四军把日本鬼子打得立不住足,败退到德安府里趴了窝。解放后,当地政府于吉阳山下,修一座抗日烈士纪念碑,李先念亲笔题写了碑文。可见,这鸟不下蛋兔子不拉屎的地界,着实让人不敢小瞧,不光涌现出许多的抗日烈士,还出了几个奇人异士。烈士自有正史记载,但这些个奇异之士,却不见经传的,常被乡人们拿来佐酒这就口耳相传下来。
赵三帖
赵三帖,吉阳赵冲村人,原名赵三。五岁那年,父母像商量好了一般,前脚跟后脚地上了黄泉路,乡人们合计着,将其潦草葬了。赵三在乡人们的提点下只知道磕头,却不晓得哭。末了,便跟下葬的队伍走。等到人散尽了,赵三才发现只剩下自己一人,和斜阳下孤零零的影子就伴。
再后来,拖着自家影子的赵三,挨家挨户的乞讨。看谁家烟囱冒烟,便期期艾艾地挪上来,依门不动,把黑黢黢的手指头舔得惨白,两小眼睛直勾勾地看人。乡人怜之,每每唤到屋里,加一副碗筷待之。赵三也不客气,端起碗来,就把头埋了进去,状似饕餮。吃完,一抹嘴,趴地上,冲主家咚咚咚磕仨响头,起身离去,不做些丝盘桓。那时的他,只记得磕头,更知道肚子饿。如此吃百家饭,穿百家衣,勉强度命。
也不知是哪一天,去吉阳街赶集的乡民发现,朝阳观里的薛老道不再孤身一人了,身后跟着个背包袱的半大小子,亦步亦趋的似条尾巴,有眼尖的认了出来:“那不是赵家的小三么,怪不得几天不见人影,原来跟着薛老道了。”
再看赵三,污糟的乱发变得干净顺溜了,面色红润了,显得眉清目秀。一身灰布道袍,略显肥大了些,想是薛老道拿自己的旧袍改做的,可穿在赵三身上,却有了几分仙气。
据吉阳街上的老人说,薛老道六十多了,听口音像陕西的,又像是山西的,没个准儿,来朝阳观快三十年了。每逢集日,薛老道便到吉阳街布医施药,他不凑热闹,不占其他作行的地面,在街北头打开包袱,就地摆上十几味草药,端坐于蒲团上,敛神静气,接待病患。薛老道医术高明,头疼脑热的小病不在话下,尤其善治跌打损伤,正了骨,顺了筋,几贴膏药敷上,旬月即癒。病患给钱就收,无论多寡,没钱随便给点东西,也行。到正午,集上的人都散了,病患也一一去了,赵三便收拾包袱。一两块铜板,两双布鞋,七八块火烧粑,一小袋米,一瓶菜油,两罐子醚豆腐……赵三系了包袱,背上,随薛老道回道观。
光阴荏苒。如今的薛老道,拄着杖,齁着腰,跟在赵三后面,成了赵三的尾巴。走在前面的赵三长成了身材高大的精壮汉子,宽面阔鼻,虎背熊腰,轩昂而行。到了街面,依旧铺了包袱,师徒俩各坐蒲团上。薛老道似尊泥塑,闭目养神。赵三接待病患,应付自如。偶尔,薛老道似在睡梦里呓语:“加蛇蜕一张,土蜂窝一吊!”赵三便对病患说:“门前屋后,梁上檐里,自个找吧。”有婆婆说关节疼,赵三抓了药,叮嘱说:“日喝两次,三天就好。不好,再来。”有棒小伙做活不惜力,扭了腰,赵三双手抵于腰眼上,不一刻,便见小伙头冒白烟,嗵嗵嗵放三个响屁,众病患大笑。赵三道一句:“好了。”小伙满脸彤红,站起来,扭了扭,嘿,没疼了。有当家汉子上树砍桠子,不小心摔断了腿,赵三仔细检视了一番,让汉子坐于墙根,背抵墙。汉子已冒冷汗,闭眼咬牙,等待即将来临的彻骨疼痛。赵三左手握紧汉子脚掌,右手似钳,扣住跫骨,左手一拉,一扭,再一托,只听得咔的一声,骨已合位,动作一气呵成。汉子还没来得及叫疼,就听赵三道:“好了。”汉子睁眼道:“好了?”赵三贴了膏药,上了夹板,拿了两帖膏药递给汉子说:“三天换一帖,歇半月,就好。”薛老道又魇仄仄道:“每日烤土鳖十只吃了!”赵三接了话茬:“灶屋灰膛里多的是。”
从此,赵三被称为赵三帖了。
日本人来的那年,薛老道早已作古。赵三帖也五十有六了,仍是孤家寡人,承了师父衣钵,独居朝阳观。
某一天,一日本军官从惊马上摔了,断了胳膊肘,在德安城医遍了,也不见好。小日人(汉奸)乡长侯日朝自告奋勇地举荐了赵三帖。日人将信将疑地说:“那就叫过来试试。”侯日朝为难的说:“老家伙日怪,从不上门瞧病,要瞧病,得到吉阳街,还得逢了集日。”无奈,日本军官只好坐了小车,摇晃着来了吉阳街。
小车在赵三帖地摊前停了。侯日朝哄开一圈病患,拿了马扎,请日人坐了。此时,赵三帖微闭双目,正给一老者搭脉。侯日朝叫道:“起开,魏屠户,太君来了,让太君先瞧病!”老者惊恐,欲起身。赵三帖身不动,目不睁,手掌改搭为扣,按下了老者。侯日朝又待发作,日人一摆手,便不作声了。片刻,赵三帖睁眼道:“您老怕是有翻仓的症兆,少吃猪下水。”遂抓了药,包好,递给老者:“日三服,灶堙子半勺作引,锅底刮去。”
老者刚起身,侯日朝急道:“该太君瞧病了!”赵三帖看了看日人说:“先生是远客,破个先来后到的例吧,请解了纱布夹板。”侯日朝忙上前帮日人解了,弄得日人呲牙咧嘴直哼哼。赵三帖便拿手指头隔肉戳了戳日人的伤臂,开口道:“接是接上了,但还是有些错位,得散了重来。”让日人反身坐在马扎上,倒扭了胳膊,用力一抖,一送,咔咔两声,疼得日人一脑门子汗水直滴答。侯日朝见状,骂道:“老不死的下重手!”
赵三帖也不理会,双手十指对着日人的胳膊轻叩,似惊鸟啄食,上下翻飞,迅如闪电。完毕,贴了膏药,重又绑了夹板纱布,对日人说:“先生再试试。”日人把胳膊试抬了几下,一脸的惊讶和欣喜,连道:“疼的没有,你的,高明的大大的!”回头又对侯日朝说:“快快的,大大的赏!”侯日朝忙掏出一大叠票子说:“太君有赏,接着!”赵三帖不卑不亢地接了,也不看,揣进道袍里,又拿出两贴膏药递给日人说:“三日一贴,歇两月,就好。”
日人起身,朝赵三贴一鞠躬:“多谢关照!”遂去。
赵三帖给日人瞧病的事,当日就在吉阳街上传开了。有人说:“几好个人,么就给日人瞧病,丢吉阳街的人,也丢薛老道的脸!”还有人说:“剑老无芒,人老无刚,没骨头了……”
又逢集日,早起赶集的人发现街北头的老皂角树上挂了颗人头,人们一窝蜂跑上前去,要看个究竟。有眼尖之人惊呼道:“那不是找赵三帖瞧病的日人么?”人们纷纷说:“对对对,是是是。”再看,粗大的树腰上贴了条幅,有识字的人高声念道:“找我瞧病,患者也,该医。杀我族类,畜生也,当诛!杀人者:赵三。”
此后,吉阳街上,再也没了赵三帖的身影。
杜吉莫
杜吉莫,吉阳街“问茗轩”茶馆老板。年轻时,不务农业,性好赌,常在邻近的陈巷镇赌场泡着,十天半月不见人影。一回家,就躺在床上,一个大字朝天。过不几天,堂客拿米升子,把米缸敲得梆梆作响。杜吉莫二话不说,掮上褡裢便出门。再见到他时,肩上的褡裢鼓鼓涨涨的,是粮食。
一日,堂客拿了菜刀架在儿子的细脖上,对杜吉莫说:“要赌,还是要命根子,你选!”
独生子杜世章一脸的幸灾乐祸,吸着鼻涕说:“要赌,还是要命根子,你选!”听着,像是他妈的回音。
“我要这个家。”杜吉莫回答得斩钉截铁。
命根子要,赌,也要。能两全其美,非开茶馆莫属,这是杜吉莫早就有了的念想,便跟堂客说了。堂客听后,一阵冷笑:“穷得卵子当凳儿坐,还想开茶馆,做秋梦!”
杜吉莫扭头进了后院的猪栏,在猪槽底扒拉了几下,取出了一个油布包。转身来到堂屋,将油布包一抖,一堆现洋呛啷啷地在桌上打着滚儿,泛起的白光刺得堂客睁不开眼。半晌,堂客骂道:“个龟孙儿,背着我窝私食呢。”骂归骂,心里却暗夸自家男人有存心,归了正道。
茶馆开张不久,杜吉莫便增加了长牌、麻将、摇骰子一应的营生,惹得堂客又一顿臭骂:“狗子断不了茅司路!”
骂归骂,骑虎之势,哪能下得来?
早起,洗漱毕,扣了瓜皮帽,套上长衫,偎在柜前圆椅上,端着水烟筒,拿火媒子嘬嘴一吹,吃烟,一副掌柜派头。水烟筒呼噜呼噜作响,匀称悠扬,似杜吉莫的好心情。
半晌,便有客人进得屋里,杜吉莫起身,哈腰上前问:“您老闲省了!里座,还是打外场?要尖子,还是大叶子?”嘴上如此地客套,心里早就断定了来者的身份了,但还得这么问候。为么?不能贬伤了客人。能进里座,就有点闲钱,打麻将,摇骰子,自然就上尖子茶。打外场,兜里没几个“王眼儿”(小币值的铜钱),玩玩长牌,只能喝大叶子粗茶了。开茶馆的人,就得精明,三教九流,都应酬得圆转彻趟。
堂客上身罩一件对襟枣红大袄,下穿一条肥大的展腰裤,颠着一双菱角般的小脚,烧水,沏茶,伺候客人,里里外外团团转,似陀螺。杜吉莫只管吩咐吆喝,当甩手掌柜。偶尔得闲,挤上场凑个角,过把瘾,止止手痒。如此,日子过得还算滋润。
戊寅年,吉阳街上跑日人,人们纷纷逃进山里躲避。杜吉莫舍不得自己的茶馆,让堂客带了儿子逃走,堂客哭哭兮兮地拽他。杜吉莫说:“两条腿的人我都能应付得彻趟,四条腿的畜生我还怕了不成?大不了和先人留下的老屋同归于尽!”强把堂客孩子推出了门:“快走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话是说的硬锵,可日人没到,杜吉莫便忙了起来,撕了块白大布,杀鸡取血涂抹了个太阳,绑了竹竿插在门面上。隔壁豆腐坊的张顺遂说:“不圆呀,伙计,看着像赵三贴的膏药,没见过这样的门面幌子。”杜吉莫说:“你也没走呀?”张顺遂说:“我有生意,么走得了。”说完冷哼一声进了自家屋里。
在小日人侯日朝的带领下,日人气势汹汹进了吉阳街。满街早已空荡荡的,一片死寂。看到日人小队长的脸拉胯成了驴脸,侯日朝瘦黄的小脸便直淌汗。到了街中腰,就望见一面太阳旗,尿片子似的在风里晃荡。侯日朝一下子跳了起来,捯着小短腿,退着碎步叫喊:“太君太君,良民的有,良民的有!”
近了,见杜吉莫哈着腰,抱着双拳,打躬。侯日朝说:“哎哎哎,招手招手,喊欢迎欢迎!”杜吉莫一脸迷惑,不知如何动作。日人小队长骑着马到了跟前,一脸的微笑,竖起了大拇指道:“你的,大大的良民!”侯日朝麻溜地扶着小队长下了马,涎着脸说:“太君,这家茶好,歇个脚,品品茶。”回头又对杜吉莫吼道:“愣怔么,快上尖子,要好的!”
品着茶,日人小队长一脸的安逸,不停地说好的好的。杜吉莫便到柜上取了水烟筒,递给小队长说:“您老慢用!”小队长看着水烟筒似是看怪物一般,讶然道:“你的,这是什么的干活?”侯日朝抬脚踢了杜吉莫屁股说:“腌作东西,也配拿来给太君用,找死么?去,把麻将拿出来,太君好这口,陪他老人家玩几圈。”
几圈下来,杜吉莫发现日人的牌玩得蛮溜爽,便不紧不慢地悠着,似钓鱼一般,既不让日人赢得痛快,也不让日人输得难堪。一个时辰之后,日人赢了,杜吉莫保本,侯日朝和翻译输了。日人把面前的一堆票子推到杜吉莫的跟前说:“好的好的,你的牌打得好的好的,改日的再玩,你们的还要陪我!”杜吉莫不敢接。侯日朝说:“接着,太君赏你脸,还不麻溜兜着。”说完又涎着脸请日人先行,自己屁颠颠的殿后。杜吉莫趁人不注意,把票子塞进了侯日朝的裤兜里,大声道:“太君您老慢走,侯乡长你老慢走!”
从此,日人小队长就常来找杜吉莫打麻将,厮混得越发的熟套了,那亲热劲儿,连侯日朝看了都恨得牙根儿直发痒。这可犯了众怒,街坊们暗地里也把杜吉莫叫小日人了,还给他起了个日本名字:杜边三条!有人说:“该把杜吉莫狗日的赶出吉阳街。”还有人说:“把狗日的剁了,干脆。”连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老伙计张顺遂也骂他:“杂碎,畜生下水。”
一日,侯日朝同几个手下在茶馆打麻将,不一会,他连襟董德贵急急忙忙跑进来,同侯日朝咬了一阵子耳朵。侯日朝跳了起来,朝外间喊道:“刘驼子刘驼子!”刘驼子进来了,侯日朝又同他咬了阵耳朵。刘驼子听后一急,道:“来回百把里路,一个时辰么样够?”侯日朝给了他一脚,骂道:“快,骑我的马去,误了老子的大事,剁了你狗头当夜壶!”
彼时,张顺遂正提了卤水罐往豆缸里点卤。卤水一线直,似粉条儿。杜吉莫悄不声儿的站在他面前,说:“忙呢。”
张顺遂头也不抬,回说:“忙。”卤水依旧一线直。
“跟你打听个事?”杜吉莫说。
“说!”
“侯日朝的连襟董德贵是哪垯的?”
“是董冲的么。”张顺遂仍旧不抬头。
“哦,他刚来找过侯日朝,像是有急事。”
卤水罐子一颤,一线直的卤水拧成了麻花状。
杜吉莫说:“侯日朝派刘驼子去德安城了。”
话刚落音,只听一声“嗵”,卤水罐砸缸里了,溅了张顺遂一脸,似花猫。
杜吉莫看着张顺遂,一脸坏笑地说:“你忙,我走了,得去服侍侯日朝他们。还有,莫忘了把脸擦擦。”
是夜,街上响起了电驴子的突突声,骡马的蹄声,还有人群的踢踏声,逶迤向街西北的董冲方向去了。
晨起,街上又响起了电驴子的突突声,骡马的蹄声,还有人群的踢踏声。一队日人和小日人的队伍蔫答答地回德安城去了。
望着远去日人的队伍,杜吉莫和张顺遂相视一笑,各自进了自家屋里。
后来,日人又来吉阳镇地界扫荡过几次,无一收获。
一天,许久不见的师弟段国玉突然到来。兄弟俩寒暄过后,段国玉便直奔主题:“师兄呀,你这开茶馆,靠赌,么时才能出头呀?师父他老人家也曾说过,赌不养家,只能败家。如今是日本人当家,你也该金盆洗手,换换汤头了。不瞒你说,我如今是陈巷乡的乡长了。一门师兄弟,兄弟在皇军面前为你谋了个前程,但你得答应个条件。”
“么条件?”
段国玉咔咔咳了两声,作为难状:“就怕你不同意呢。”
“兄弟间有么不好说的,说嘛。”
“皇军看上了你的象牙麻将,你要能送给太君,兄弟我保你个乡长。”
杜吉莫听后,一脸寒冰,问道:“师父留给你的紫檀木牌九,送给日人了?”
段国玉脸似猪肝,不知如何作答。
杜吉莫呼的一起身,提起棉袍的下摆,嘶啦,裂帛声锥心。然后指着大门口对段国玉道:“滚,我没有欺师背祖的兄弟!”
第二天,日人小队长来到了茶馆,脸色不大爽朗,侯日朝也似遇到家丧一般。茶毕,小队长道:“听说你的玩骰子的不错,我们的今天就切磋的切磋。”说完一摆手,侯日朝捧了一个红木匣子,打开,里面是一套骰盅,揭了盖,是两粒黑亮的骰子。
小队长又说:“我们今天的不要赌钱,要的赌物!”说着从腰上解下王八盒子,拍在桌上:“我的赌这个。”
杜吉莫笑道:“太君,我家可没么值钱玩意儿呀?”
侯日朝气汹汹地说:“太君说了,就赌你的象牙麻将。”
杜吉莫一脸的煞白,知道来者不善,今天怕是躲不过了。一咬牙,进了后房,抱出个大红包袱,放桌上,解开包袱,露出个檀木匣子,从侧面小心翼翼地抽了盖子,里面整齐地码放了一枚枚麻将子,泛着淡淡的温玉般的光泽。
小队长一脸的微笑,说:“好的好的,我们的五局三胜。你的是主,我的是客,我的先坐庄。”说完,双手捧起骰盅,哗哗哗摇了数个来回,啪,礅在桌上,说:“大。”杜吉莫说:“太君押大,那我就押小。”
开盅,是大。小队长赢。
“得罪了!”杜吉莫一把握了骰盅。一上手,便觉有些古怪,遂一发力,一气摇了十余个回合,再一灌气,轻轻置于桌上,说:“小。”小队长说:“我的押大。”
开盅,是小。杜吉莫赢。小队长脸上有了异色。
第三局,小队长坐庄,小队长赢。
第四局,杜吉莫再坐庄,杜吉莫赢。小队长脸上微颤。
第五局,小队长深吸一口气,略一凝神,捧着骰盅摇了不下二十回合,将骰盅放在桌上,准备揭盖。突听杜吉莫大喝一声:“慢,来而不往非礼也,你是客没错,但赌具是你带来的,这一局骰子也是你摇的,让我来揭盖,可否?”一旁的侯日朝骂道:“你他妈找死么?”
小队长一摆手说:“好的好的,你的揭。”
杜吉莫缓缓地伸出胳膊,手背之上,血管状如蚯蚓,手掌离盅寸许,略一沉吟,五指轻搭盖面,扣牢,缓缓上提,似有千斤重。
再看盅内,两枚骰子破为四瓣!
众人满脸错愕。
杜吉莫朝小队长一抱拳:“这局太君是庄,打平了,也是太君赢。”抱了麻将匣子,双手呈向小队长:“甘拜下风!”侯日朝忙接过了匣子说:“太君太君,打平也是庄家赢,是这规矩。”
小队长抱了匣子道:“承让,改日的再切磋。”说完转身离去。
张顺遂凑近来道:“唉,可惜了你那宝贝。”
杜吉莫怅然道:“只要四爷们(新四军)好,值!”
“四爷他们都好。”张顺遂道:“四爷带话了,说日子长着呢,你也要好。”
“好。”杜吉莫道:“不是立秋了么,我赌狗日们的弹跳不了几天!”
张顺遂道:“你总忘不了赌。”
“不瞒你说,我还从没失手过!”杜吉莫自信地道。
仝仕荣
外地人来吉阳街做生意,少不了和当地乡民咵天儿,了解些本地风土人情。街上乡民就说:“您老猜猜,在吉阳街,么生意最杠?”
“钱庄!”
“错啰,吉阳街面苦寒,没这号生意。”
“当铺!”
“又错啰,都是些破铜烂铁的,值不了几个王眼儿,金银首饰就一两件,还藏着掖着的,难得一见。”
“这我就糊涂了,你说么生意最杠?”
“牛行!”
“哦?!”
“再问您老,除了茅司猪栏阴沟叫花子的屁眼儿,么东西最脏?”
“堂客们的裤裆!”
“嘿,又错了不是?说你不信,是仝仕荣的袖筒儿。”
“哦,么讲究?”
“看您老说的么,牛经纪做的是袖筒里的生意,成天和农人勾手,能不脏么?这叫袖里乾坤。”
外地人道:“那他不赚死了?”
乡民脸放红光傲然道:“那还谈,古有伯乐相马,今有仕荣相牛!”
“那我得拜见拜见这位高人。”
乡民手一指:“街东抹角牛行里找去。”
仝仕荣,吉阳镇外廊嘴人,半岁时丧母,缺奶,父亲以米汤喂之,瘦似猴。适值家有母牛产子足月,爬了前去,同小牛挣奶,小牛愤怒,一头将他撞开,仝仕荣倒地哇哇大哭。母牛蹭开小牛,卧于仝仕荣身旁,仝仕荣止了哭,趴在母牛奶上,嗞嗞贪吮。小牛也哞哞前来,跪下,衔了另一只奶头。父归,见此景,泪如泉涌,长叹道:“马是忠信,牛是仁义,我儿好福分!”
及长,仝仕荣天天放牛。牛吃草,仝仕荣也不闲着,拿镰刀割嫩绿的丝毛叶,扎成小捆,带回作母牛的夜草。有时尿憋了,也舍不得拉,跑到母牛跟前,照牛嘴里撒,母牛接了,尿完,母牛意犹未尽,巴巴嘴,直舔周遭。冬天,仝仕荣时常瞒了大人,将家里的黄豆塞进草把中,喂母牛。母牛嚼着草把,仝仕荣看见它眼角下有两条线,细看,分明是泪。
仝家的牛养得膘肥体壮,通体油亮,似缎子面儿,还是个高产的母亲,每年下头牛仔,惹得乡人们羡慕不已,连地主杨金山也赞叹说:“仝家小子通了牛性,会服侍牛。”
十岁那年,母牛老死,父亲在后山葬了。仝仕荣趴在母牛的坟头大哭,那情景把四邻的乡人也感动得泪涟涟,说:“哭娘呢!”
过了几日,杨金山来到仝家,开门见山地说:“让仕荣帮我家放牛吧,不亏你,给双份工。”仝仕荣就成了地主家的放牛伢。
杨金山田地多,旱地水田近百亩。牛也多,黄牛水牛十六头。牛多,一般的硬劳力都照看不过来,一天下来,累得腿抽筋。可仝仕荣经手三天,牛都变得听话了,温顺了。早起,仝仕荣在前走,一群牛在后面跟着,似训练有素的队伍。晚归,牛走前面,仝仕荣押后,不用训斥吆喝,不错门,乖乖儿进牛栏。这本事,少见。
十八岁那年,岁末,结了工钱,仝仕荣站在杨金山面前踌躇着。杨金山便问:“么,工钱不对?”仝仕荣嗫嚅道:“对着呢,主家公,我牛服侍得可好?”杨金山说:“冇得话说!”仝仕荣又道:“您老看我能不能当个牛经纪?”杨金山一晃脑袋,眼珠一转,说:“牛服侍的好,不见得就能吃牛经纪这碗饭,那家伙,门道深得很。”仝仕荣说:“是很深,可我想试试,求您老成全。”杨金山问:“有本钱么?”仝仕荣答说:“差点,这不求您老么。”杨金山又一晃脑袋一错眼珠,半晌说:“行,先借你五块大洋。不过要说好,五分利。”仝仕荣说:“好,都依主家公的。开年还得请您老跟牛行的魏行头说和说和,我请酒!”杨金山道:“行么。”
刚入行,没人把仝仕荣放眼里。俗话说,十年树个读书人,百年难成个生意人,一个毛头小伙儿,能翻几大个浪?仝仕荣也不计较同行的闲言碎语,双手插兜里,默默地坐在板凳上,看人来人往,牛牵来牵去,六块现大洋在兜里捂出了水。一连三天,没开张。
第四天,有老农牵来一头水牛牯,两角宽阔,顶泛黄,双眼似铜铃,耳廓尖直,大似扇。骨架粗大,前高后低,足沉蹄圆,四膊四旋,仝仕荣一看,便认定是头好牛,却瘦得让人伤心,只一张皮斑驳地敷在身架上。其他同行看了看,皆摇头走开。日当顶,老农见自己的牛无人问津,牵了牛欲走。仝仕荣几步上前道:“您老慢走!”拦下了老农。仝仕荣注意老农半天了,一直没上前谈,按行话说,叫绷价。老农绷不住,仝仕荣的生意就来了。
仝仕荣站在牛后,掐尾巴,看便门。再绕到牛前,掐牛嘴,看牙口。看完,来到老农面前,都伸出袖筒,拿捏了半天。最后老农说:“就了,依你。”银货两讫,仝仕荣牵牛回家,存栏。
之后的日子里,仝仕荣隔一两天做一笔生意,即买即卖,不贪多,只求小赚,混个人缘。
过半月,仝仕荣又做了桩生意,是头母黄牛,头顶双旋,盆骨宽大,一线白毛通脊,两眼温润,母性充溢,只是也瘦得让人伤心,像是落入寒门的大家闺秀。仝仕荣将其牵回家,依旧存栏。
又两月,再看两头牛,皆膘肥体壮,阳光下,皮毛闪着亮儿,踏踏地跟仝仕荣走。到了杨金山家门口,喊一声:“主家公,牛来了!”屋里走出来两人,杨金山,后面跟了魏行头,是杨金山请他来掌作的。魏行头一看牛,讶然道:“仕荣,哪儿弄来的?”仝仕荣微微一笑:“行里牵的,没人要,我就收了。”魏行头脸上有些不自在,不再言语,朝仝仕荣伸了袖筒。掐捏一番,魏行头道:“杨东家,八块现大洋,不亏!”杨金山当场掏了钱,仝仕荣只收了三块,说:“主家公,本钱还您老了,利钱年底还,成么?”
三年后,二十一岁的仝仕荣当上了吉阳街牛行的行头,风头旺健,一提起名来,乡人便竖拇指哥。
三十二岁那年,正值仝仕荣的牛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之时,日人来了。烧杀抢掠,生灵涂炭,吉阳街几成废墟。百业萧条,牛行亦无幸免,仝仕荣精心相中的二十几头存栏牛,也被日人征去了,替正修建的安应公路拉石碾压地基,运送物资,还强行押了他去喂牛看牛。
照看牛不累,可牛们累,月余,就累死三头,被日人拖走,杀了吃掉。夜归,提了潲水喂牛,看着疲惫不堪的牛们,仝仕荣忍不住挨个抚摸,牛们直舔着他的手,回应着他。摸着摸着,仝仕荣直掉泪:“对不起呀伙计们!”牛也哭。只是,人哭有音,牛哭无声。
一日午饭,仝仕荣没吃,便集结群牛,往水塘边去。水塘前面的稻场上,日人围了几圈,正吃着。近了,两个站岗的小日人持枪拦住,问:“搞么?”仝仕荣点头笑答:“赶牛喝水呢,老总方便下。”小日人放了行。
离稻场十余米,仝仕荣轻喝一声:“哇着!”牛们站住。仝仕荣抬脚往地上用力一踏,手指向正在吃饭的日人们,大喝一声:“哧——嘚!”牛们似离弦之箭,疯也似的冲向日人。没等日人们回神,牛们已冲到面前,一个个被冲撞践踏得噗噗作响。有被牛角扎穿胸膛的,有被踏破脑袋的,有慌不择路,直接跳进了水塘的。仝仕荣如神附体,依旧脚踏手指:“哧——嘚——哧——嘚!”有日人慌乱中抱了机枪,一阵扫射,牛纷纷倒地。仝仕荣仍旧呵斥:“哧——嘚!”牛们挣扎站起,不支,又倒下。“哧——嘚!”仝仕荣泪眼模糊,只是“哧嘚”个不停,没倒下的牛继续横冲直撞,又有日人倒下。有日人躲在角落,抬枪朝仝仕荣一阵狂射,霎时,身如筛,血如注,仍强力撑住,含着满口鲜血奋力道:“哧——嘚——哧——嘚……”踉跄地扑倒在一头尚未断气的牛旁。
人和牛,相望无言,各自两行泪。
责任编辑:郑 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