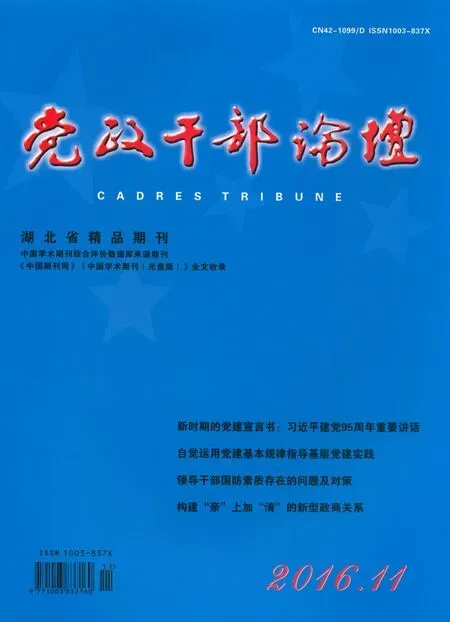涉法类新媒体事件:生成、原因与消解※
○向长艳
涉法类新媒体事件:生成、原因与消解※
○向长艳
随着网络普及率的提高,我国网民数量不断上涨。截止2015年6月30日,中国网民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达到88.9%[1]。可以说,网络新媒体尤其是移动新媒体已经很深刻地影响着转型、深入改革时期的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网络信息的快速流动、便捷获取,以及公民的权利诉求意识不断增强,以网络作为主要传播媒介的新媒体事件不断发生,其中涉及公民权利保护、公权力监督、公共秩序维护、公共道德伸张等重大社会问题。如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孙志刚事件”直指公民权利保护和公权力监督等深层次问题,并推动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而有关统计显示,新媒体事件中有相当一部分直指现存法律制度、执法部门以及正在进行的司法审判活动,对我国法律生态有一定的影响,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有一定的作用。因此,对这部分直接与法律有着各种关联的新媒体事件做深入探讨和研究,是顺应目前法治发展的大势所趋。
一、新的传播格局下的涉法类新媒体事件
(一)概念的区分
目前,学界对新媒体事件的研究比较深入,但对新媒体事件的进一步细分研究还不够,如对于涉法类新媒体事件的研究大多在涉诉涉法信访问题研究中可见其身影。从大的概念范畴上来分,涉法类新媒体事件属于新媒体事件。按照学者的定义,新媒体事件可有多种划分。如邱林川、陈韬文主编的《新媒体事件研究》中,把新媒体事件分为民族主义事件、权益抗衡事件、道德隐私事件、公权滥用事件四类。而孙永兴在《新媒体事件:机制、功能与法律规制》中以一种开放的思维按照多种标准对新媒体事件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按照媒介主体种类的不同分为网络媒体事件、移动媒体事件、新型数字媒体事件;一类是按照内容不同分为娱乐性新媒体事件、道德指涉类新媒体事件、政治类新媒体事件;一类是内容是否涉法分为涉法类新媒体事件和非涉法类新媒体事件。由此可以看出,对新媒体事件概念的精确界定并非易事,同一起新媒体事件的发生同时涉及多个领域,纯粹因娱乐而起的如“杨丽娟”事件,最后也涉及道德评价问题,纯粹因道德争论而起的如“范跑跑”事件,都或多或少涉及个人隐私等私权的侵害问题,政治类事件同时也是民族事件或权力制约事件等。可以说,对新媒体事件进行细致地分类几乎不可能。笔者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不断推进,公民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法治理念逐渐进入社会生活,从这个角度来看,广义上可以把新媒体事件分为涉法类和非涉法类似乎更为直观。然而事实上,无论哪类新媒体事件,其发展都有个度,超过必要的限度都会成为法律问题,都会与法律相关,都将成为法律权益争议的焦点。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从更狭义的角度,将涉法类新媒体事件定义为围绕诉讼活动而发生发展的新媒体事件。
(二)新的传播格局下网络民意对司法的参与
民意与司法的关系问题并非是新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情理法传统背景下,二者的关系似乎从来没有真正辩清过。在新的传播格局下的网络民意与司法的关系表现出了新的特点,更加复杂。这里首先明确两个概念,即民意与司法,他们是理解涉法类新媒体事件的关键。民意其实具有不确定性和非理性特征,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表达出来的方式也不同,很难聚合起来。但是民意同时具有群体性,即民意是多数人意见的反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司法,按照学界的通说,指有专门的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使用法理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特指法院的审判活动。在我国法院和检察院被认为是当然的司法机关。民意通过多种途径对司法进行参与和渗透。传统传播时代,英美法系主要通过立法或制度设计对新闻媒体干预司法审判进行处罚和限制,大陆法系国家则鲜有立法规定或制度调整。随着新闻自由保护力度的增强,二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加大。
在新的传播格局下,网络民意对司法的冲击力更大。网络民意是指借助或通过网络这一信息平台表达出来的社会公众思想舆论的趋向和导向。在新的
传播时代,信息的快速流通和便捷获取,让民意更容易焦聚,对于民众关注的焦点问题更容易因焦聚而发酵,从而引发新媒体事件。
当下的时代是一个信息多元的时代,信息多元造就了传播素材的充沛。而新媒体的便捷性、公开性、互动性、及时性等特征完全契合了公众对“信息”的欲求以及对期望参与社会生活的满足。这种参与充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公域私域概莫能外,尤其是与公民个人权利息息相关的司法活动更受关注。当人们还偶能感受被传统媒体和民意判处死刑的张金柱案(1997年8月张金柱交通肇事,1998年被判处死刑)的余波冲击的时候,从传统媒体发展到网络媒体,最终被传媒和民意免罚的邓玉娇案(2009年),已经显现了网络媒体参与司法的强大威力。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微博用户不断上升。2010年被称为中国的微博元年,而随即由微博舆论引发的媒体事件不断增长,据有关统计,与2010年相比,2011年微博舆论事件增长了52%。在这些事件中,由学者余秀才等根据人民网、中国知网主体论文所涉及案例等方法所搜集到的自2009年至2013年的200件案例中,按照政府管理、官员腐败、涉警涉法、社会民生、企业经营、事故灾害、国际关系、公共道德、网络谣言九个方面所进行的分类显示,涉法涉警类事件占比最高,为38%[2];而据人民网舆论监测室数据,2014年全国舆情热点话题中关于司法案件有93起,仅次于吏治反腐、社会安全,位于第三。这说明,司法机关作为裁判机关掌握着“社会公正”的裁判大权,容易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民众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司法活动中来。移动互联网的产生和技术上的实现,微信的广泛使用,更进一步便捷了信息的传递,公民表达有了渠道和空间,对于感兴趣的话题尤其涉及公民权利的话题进行交融和碰撞,容易引起民意激荡,并进而影响司法活动。尤其是当传媒借助新的传播技术一定程度裹挟民意,参与司法裁判前的评论报道时,更容易形成网络舆论热点,顺应着沉默地螺旋理论的扩散效应,形成舆论强势,逼视司法活动,形成涉法类新媒体事件。
二、新的传播格局下民意偏好司法的原因
民意对司法的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上所述,如果说借助于新的传播技术,网络民意广泛参与司法可能成为涉法类新媒体事件产生的表象的话,那么,随着民众法治理念的觉醒,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是涉法类新媒体事件的内在原因。
(一)对社会正义的需求
司法活动作为一项特殊的社会活动,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经过长期专业法律训练的社会精英控制的,法官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封闭的隔离于社会的判断者。即便是有着特殊的专业训练经历,但法官首先是个生物的人,他难免会受到个人的认知、情感、阅历尤其是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无处不在,尤其是在我国长期以来司法权低于行政权这样大的司法环境下。如此导致的结果是,司法权的行使经常有违背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的情况发生,只不过在信息流动不是很顺畅的传统传播时代,这些情况都会内部消化内部解决。随着法治国家建设的推进,随着公民法治意识的提高,特别是新媒体平台的便利,公众对社会事务的参与更加广泛,他们利用法律正义外在的社会价值,有时也透渗自己的价值判断,以表达自己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对公共权力行使的关切、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希求。司法正义是社会正义的代表,是最大的社会正义。正是这种民众对社会正义的普遍需求,促使他们对网络热议事件产生极大关注,从而推动网络舆情的发展,并推动着司法公正的进步。
(二)对个案正义的关注
有学者统计,涉法类新媒体事件包括以下几个类型:一是司法人员刑讯逼供、践踏人权,典型的案例如赵作海案件;二是司法人员枉法裁判、徇私舞弊,典型案件比如七十码事件;三是司法人员知错不改,一再拖延,典型案件例如聂树斌案;四是司法人员贪污受贿,典型案例如亳州法院法官“窝案”等[3]。可见,涉法类新媒体事件的发生首先是从民众对个案的关注开始的。由于这种冤假错案本身的存在,并通过历史积淀长时间以来民众会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这种怀疑会通过民众自己的认知和现实体验对个案进行判断,尽管这些判断可能常常是基于道德的判断,但他们自己更相信这种大众的判断,而不相信司法机关的判断。正是这种怀疑,积极影响并推动了个案正义的实现。因此,个案中民众的广泛参与对个案正义的实现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有助于查清案件的事实,如个案经过报道后,形成舆论,有助于细节证据的收集,有助于社会各界尤其是学者参与讨论等,有助于减少司法腐败,个案公布于众后,审判过程处于阳光之下,部分个案还会有来自上级领导的压力,便于快速公正解决。民众通过良知对案件的判断并不比职业法官差,如亚里士多德的“众人智慧甚于一人智慧”理论、民众的生活经验和社区经验知识弥补司法工作人员经验和知识的不足等都有助于案件的公正解决。
(三)情理法背景是民众参与司法不可忽视的原因
当代中国司法的重心仍然是解决纠纷,而道德文化的历史传承和传媒承载的民意情理对个案的处理依然不可小觑。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司法更多的是承载着解决社会冲突的重要角色,面对深化和激化社会矛盾的可能危险,司法一般选择不公开,而案件
一旦公开进入公众视野,带着各种价值判断的民意便参与其中。而中国历史上司法对民意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偏好,在“国法”中渗透着“天理、人情”,那些被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清官断案”的例子便是明证。也有研究表明,中国古代的民事判决大都是与民间的习惯规范相一致的。它与中国古代的礼法社会传统密不可分。受传统文化浸淫数千年的国人,在司法领域,依然有着不可摆脱的“情理法”情结——民众都或多或少地对司法判决产生一种预期。当这种预期与真实的司法判决大相径庭时,便会产生一种怀疑,进而产生民愤。当这种因同情、怜悯、怀疑等引起的舆论焦聚在网络,便可能会引发设法类新媒体事件。
当然,涉法类新媒体事件的产生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诸如司法人员自身素质低下、非知情网民的盲从或部分网民的别有用心以及司法部门对网络舆情应对不够重视等,但这些表象都是在整个大的社会环境对公平正义的要求下得以推进。如果正义能暴露在阳光下,如果正义能被社会公众看得见,则很多可能的事件将在源头上被发现和处理,就不会引发新媒体事件。
三、能动司法的建立:涉法类新媒体事件的消解
从预期的结果上来看,民意与司法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实现司法正义。但鉴于网络民意的诸多缺陷,如不真实性、极端言论等,有可能会误导司法正确裁判,在规避网络舆论负面效应的同时,为避免涉法类新媒体事件的发生,必须从根本上加强司法队伍的管理和教育,必须从宏观层面,将传媒、司法置于新媒体时代的公共领域乃至整个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中进行考量。
(一)建设司法队伍,实现司法公正
司法队伍是司法审判活动的源头,是涉法类新媒体事件的源头,在立案、调解、庭审、执行等各个环节,都体现着司法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素养。中国网络舆情监测网《2011年中国网络舆情指数年度报告》显示,裁判不公、冤假错案等涉法负面话题占全年热点话题的67.2%,这个数据显示的不仅是公众对司法的关注度,更透出司法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素养。由此可见,司法人员的队伍建设尤其重要,净化源头,清澈源头,努力建设一个健康和谐的诉讼环境,是消解涉法类新媒体事件的关键。要推进法治建设,营造大的环境,增强司法自信;加强司法职业道德教育,杜绝“人情案、关系案、选择性办案”,提高司法廉洁和司法良知;加强司法公正理念,规范司法审判流程,提高庭审驾驭能力;加强法官业务技能培训,细致工作作风,端正工作态度,做到公平公正地处理各类案件。
(二)落实司法公开,畅通信息渠道
司法是否公开可以说是我国司法环境的一个试金石。司法审判作为一个特殊的权力机关——它关涉公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因此,公众对司法活动会有更多的关注,也会对司法的廉洁性有更大的期求。因此,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司法公开是唯一直面网络的方式。最高法院《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为司法公开指明了方向,即“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审务公开”。落实司法公开,需要建立司法网站,公开司法信息,及时更新、跟进对相关案件的解释和阐述;推进庭审公开,传统和新媒体同时发布庭审过程,对一些公众关注的案件可邀请媒体参与旁听,及时传播真实信息,从而遏制虚假信息和不实言论;充分利用自媒体,对庭审公告、审判流程等实现网络上及时公开,裁判文书上网等;建立法院新闻发言人制度,对案件的进展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及时发布信息,对公众的疑问及时释疑,让法院的权威信息得到及时传播[4]。
(三)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畅通公民意见表达
如上所述,做到司法公开,要推进网络、移动媒体等及时发布信息。信息的发布,其作用除了告知,另一个功能会及时形成相应的正向舆论氛围,也就是说占领舆论的主动权,避免舆论有所偏向,并及时跟进,保持更新,把握正确的导向。如果说“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向精英化的司法民主方向发展的话,新媒体民意对司法的参与则是平民化的司法民主方向。而一直以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功能发挥在我国并不十分理想,在司法体制改革迫切的今天,作为“庭外民主”——广泛的民主参与也是一种选择。我们要做的是,提供民意表达的渠道,引导民意的方向。同时,庭外民众的广泛参与,也是实现个案正义的主要途径。学者研究发现,在2005-2009年的50个影响性诉讼案件中,民众参与起到影响作用、实现个案正义的占到42%。比如,因为民众的参与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法治的进步,如乙肝携带者就业歧视案、推动城市拆迁条例修改的唐福珍案等。
[1]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余秀才,朱梦琪.微博舆论事件传播行为与特征研究——基于2009~2013年200起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案例[A].新媒体社会责任蓝皮书[C]294.
[3]孙永兴.新媒体事件:机制、功能与法律规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李娜娜.网络问政的优势、局限与突破:以网络民意选择性机制为视角[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4,(1).
(作者单位 河南省委党校)
(责任编辑 崔光胜)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法治视角下自媒体意见表达与法律规制研究》(14BFX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