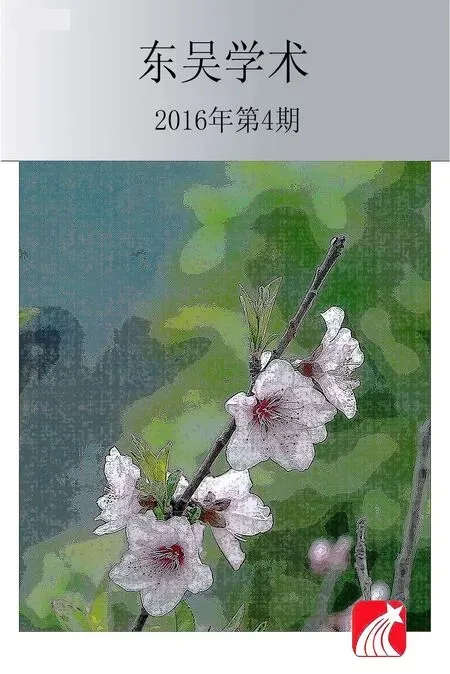“吴”初义辨正与先秦吴文化研究创新
倪祥保
东吴研究
“吴”初义辨正与先秦吴文化研究创新
倪祥保
以往对“吴”字构形初义的错误诠释,妨碍了对有关经典文献内容的正确理解,造成了对先秦吴人及先秦吴文化乃至春秋吴国的片面认识,也影响了相关的学术研究。根据甲骨文、金文的造字构形分析和先秦经典文献有关语词的意义佐证,“吴”的初义应该表示先秦吴人具有吴侬软语、歌声(舞)优美的特征,这既表征着先秦吴文化与太湖流域鱼图腾文化以及当时当地相对精雅的文化生活艺术的密切相关,也可以很好地映证先秦吴人历史悠久的崇文传统。
吴;先秦吴人;先秦吴文化;春秋吴国
为了论述对象及范围比较明确清晰,本文所谓的先秦吴人及先秦吴文化,特指春秋吴国及之前那个历史阶段中的,也就是说,它既涵盖春秋吴国六百年,又包含“泰伯奔吴”之前的(被有的专家称为“先吴”①何光岳:《先吴的来源和迁徙》,《宝鸡文理学院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部分,但是不涉及吴王夫差被灭国之后的部分。
先秦吴人及先秦吴文化研究,有很多重要学术问题至今没有达成很好的学术共识。比如,先秦吴人是说话粗狂喧哗尚武好勇还是已经具有吴侬软语、崇文尚艺之特色的?春秋吴国的文化主流是崇尚礼邦治国还是戮力于雄邦称霸的?究其原因,其实都与对汉字“吴”构形初义的诠释和理解密切相关。
一、“吴”构形初义与先秦吴人语音特征及文化形象
“吴”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出现,其构形演变历史比较清晰完整。《说文解字》:“吴,姓也,亦郡也,一曰:‘吴,大言也。’”②许慎:《说文解字》,第2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就先秦经典文献相关使用情况来看,它的基本意义有这样四个:姓氏;族群及语言;地域及国名;说话大声喧哗。这与《说文解字》的注释基本相同。其中第一个意义和第二个意义密切相关,乃至可以看作浑然一体而密不可分的,只是从逻辑上来说,第一个意义应该具有一定的先在性;第四个意义对于诠释“吴”造字构形初义非常重要,只是这个诠释其实并未允当,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先秦吴人形象和春秋吴国文化的全面正确认知。
汉字由中原人创造,汉字“吴”构形表意有关先秦吴人说话特点,应该完全从先秦中原人对当时吴人的直接感觉而来。从苏州籍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认为以苏州为核心地域的吴歌不晚于《诗经》⑥王卫平:《论吴文化的基本特征》,周向群主编:《吴文化与现代化论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的观点,可见与以优美见长的吴歌密切相关的吴方言,其实应该很早就有“醉里吴音相媚好”的特点,不可能具有粗狂喧哗的特征。这种柔声细气、音调好听的吴语特征,其与中原人说话相比,正是体现吴侬软语不同特征之所在。因此,无论是“吴”构形以说话具有柔声细气、音调好听这个特征来指称吴人,还是以人说话像歌唱一样好听来指称吴人,那实在都是抓住了在外形上与中原人几乎毫无区别的吴人最为主要、特别鲜明、易于把握的一个主要特征。
本文的上述新解诠释,也可以在先秦经典文献中找到比较有力的佐证,这首先涉及到对“吴”具有“大声喧哗”意义诠释的新解。关于先秦吴人说话具有“大声喧哗”而异常粗狂特征的权威解释,主要来自对《诗经》有关“吴”字的相关训诂。《诗·周颂·丝衣》:“不吴不敖,胡考之休。”《毛传》:“吴,哗也。”《郑笺》:“呉,旧如字。《说文》作吳:‘大言也。’”朱熹《集传》:“吴,哗也……能谨其威仪,不喧哗,不怠敖,故能得多寿考之福。”对其中“吴”的训诂,自古而然,至今没有改变。《诗·鲁颂·泮水》:“烝烝皇皇,不吴不扬。不告于,在泮献功。”《毛传》:“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扬,伤也。”《郑笺》:“烝烝,犹进进也……吴,哗也。”朱熹《集传》:“烝烝皇皇,盛也。不吴不扬,肃也。不告于,师克而和,不争功也。”①以上引文均来自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影印版。对其中“吴”的训诂,郑玄与前面一致,朱熹没有明确,其实也可看作与前面一致。相比诠释时间最早的《毛传》在这里没有给出明确意见,但是对历来注家很少特别注释的“扬”字,却做出了一个比较特别的解释,这非常耐人寻味。在关于“不吴不敖”、“不吴不扬”这两句的有关训诂中,历来注家其实都自觉一致地将“不吴”和“不敖”看作同义语,将“不吴”和“不扬”看作同义语。在此基础上看,如果《毛传》将“扬”诠释为“伤”是有依据的,那么有关“不吴不扬”的解释将进行颠覆性改变:将“不吴不扬”之“不扬”解释为“并不忧伤哀怨的声音”,那么作为同义语的“不吴”的解释就应该是“并不低沉细弱的声音”才比较好。这也就是说,“不吴不扬”中“吴”表示说话声音的特点,应该是表示低声细气而不是大声喧哗的了。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完全不同于其他诠释的意义表达,却特别符合孔子关于《诗经》具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文化品性,也比较符合当时重要礼仪场合的说话不能喧哗、不能低声的语音规范,因此是完全通达可行的。
也许换一种论证也可以非常有力地证明“吴”表示说话方式应该是指柔声细气的,并且这样的新解在《诗经》语言环境中也完全站得住脚。在《诗经》中,诸如“不吴不敖”、“不吴不扬”这样的句式,其语意结构可以是同义联合的,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不稼不穑”、“不狩不猎”和“不日不月”;也可以是反义联合的,比如“不竞不”、“不刚不柔”和“不僭不滥”。这就是说,关于“不吴不敖”、“不吴不扬”句中“吴”的文字训诂,既可以将其看作与“敖”、“扬”同义联合的角度来解读,也可以从反义联合的意义来诠释。从反义联合句式的角度来看,“吴”就是“扬”和“敖”的反义词,即其表示声音及语气的意义应该是“不扬”、“不敖”。《诗·鲁颂·泮水》在“不吴不扬”句前面有“无小无大”这样一句,可见本文关于从反义联合角度来新解“不吴不扬”是合理可行的。如果“扬”强调声音非常高亢喧哗,“敖”表示声音非常粗狂雄放,两者都不是上古正规礼仪场合应该有的典雅中和之声,那么“吴”作为“不扬”、“不敖”的意思则可以解释为轻声细气——同样不符合上古正规礼仪场合的语音语调要求。此外,从诗句语言表达效果层面来说,强调在正规场合说话“既不能大声喧哗、也不能细声细气”的表述,显然比“既不大声喧哗、也不大声吼叫”那样的表述更好。因此,“吴”在《诗经》那两首诗中表示说话的语音特征,确实应该是指柔声细气的意思而不是大声喧哗的意思。
从语言语音学角度来看,一个地方的语言语音作为其重要的交流工具和文化内容表达之一,在人口流动不是巨大和不同方言交流不是非常频繁持续的情况下,一般都与生俱来而相伴长久,不会轻易出现很大改变。同时,这种相对稳定的语言语音,还会非常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到这个地方人群的诗歌艺术和音乐艺术。以先秦吴地为诞生地的“吴歌”,以委婉优美的抒情性见长,在先秦时代被称为“吴歈”,②宋玉《招魂》:“吴歈蔡讴,奏大吕些。”见朱熹《楚辞集注》,第14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其出现时间,据顾颉刚考证应该不迟于《诗经》。③王卫平:《论吴文化的基本特征》,周向群主编:《吴文化与现代化论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这说明“吴侬软语”很可能开始于春秋吴国期间及更早时期,与本文关于“吴”构形初义诠释的历史文化事实完全相符。从汉语语言语音学角度看,凡是直接表示和大声说话或喊叫意义相关的字,其韵母一般都是让人比较容易大声说话的开口呼,比如叫、啸、嗷、嚎、唱、喊、骂等,很少会用“吴”这样无论在上古还是现代都从字音上无法大声读出来的字。所以,对“吴”作“大声喧哗”的训诂,也得不到来自汉语语言语音学方面的支持,即不符合相关的语言语音历史事实。由此可见,特别具有“吴侬软语”特征的苏州一带吴语方言,不仅是历史悠久的,而且也是其能够更好地演唱以精雅绮丽、轻柔唯美见长的古老吴歌以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弹等的语言语音的重要条件。
值得补充说一下的是,先秦中原人对先秦吴人能歌善舞、声色娱人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会比较自觉地将“吴”放在创造那些能够表示“美好”、“娱乐”相关意义的字的构形中。比如声旁为“吴”、义旁为“女”的“娱”字,简单而直接地说,显然就是从先秦吴地的女子特别能歌善舞这个历史事实基础上被创造出来的,并在此基础上可以引申出或者是“歌舞”(《诗·郑风·出其东门》:“缟衣茹蘆,聊可与娱。”①朱熹:《诗集传》,第5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再版。)、或者是“娱乐”(《九歌·东君》:“羌声色兮娱人。”②朱熹:《楚辞集注》,第12、13、17、4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的意义(这与前面关于“吴”构形初义具有“载歌载舞之人”的意思密切相关)。同样,既形声又会意的“误(悮)”字,则有美妙动听的言语(美好上心的人)容易使人迷恋乃至上当误事(如妲己、西施误国)的意思。这些与形体、声音美好意义相关的造字,都与“吴”相关,可见在先秦时代创造汉字的中原人看来,在身材和声色方面,吴地之人确实相对而言都显得更加秀美迷人(更多指女性),所以中文很早就有诸如“吴娃”、“吴姬”和“吴娘”等指吴地美丽女子的词语。顺便提一下,还有一个表示舞蹈姿态优美而被误解的“俣”字,其实也能提供这方面的佐证。《诗·邶风·简兮》:“硕人俣俣,公庭万舞。”历来对其中“俣”的解释都和“硕”一样,是“大”的意思。③《辞源》,第1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修订本。按照“俣”具有“硕大”这样的诠释去理解该诗,不仅会感到意义重复,而且觉得毫无美感。汉代郑玄似乎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于是牵强附会地加以区别说:“硕人,大德也;俣,容貌大也。”④阮元:《十三经注疏》,第30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影印版。其中所谓“容貌大”的意思,实际上换汤不换药,依然没有确切。依诗意来看,不管诗中所写“硕人(健硕男子)”以“干戚”跳“武舞”,还是用“羽翟”跳“文舞”,他的舞姿非常优美应该是必须的——不然他就不会在诗歌中被称为“美人”而受到充分的赞赏。因此,该诗句中作为描写“美人”身姿的“俣俣”,不应该叠床架屋地再表示其身材健硕,而应该表示其舞姿的舒展流畅和吸引眼球的优美。《诗经》此处描写跳舞“美人”的“俣俣”,其实与柳宗元《弔屈原文》之“娱娱笑舞”⑤转引自《辞源》,第409、1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修订本。中的“娱娱”相同,只是因为《诗经》中描写的是男性军人的舞蹈之美,所以不能用女字旁的“娱”来加以形容而已。正因为“硕人俣俣”中的“俣俣”应该和他们在“公庭万舞”时的舞姿优美相关,所以《韩诗》引此句时作“扈扈”,其意义与司马相如《上林赋》“煌煌扈扈”⑥转引自《辞源》,第409、1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修订本。中的“扈扈”相通,主要表达形体美好、鲜艳夺目的意思。可见在大诗人司马相如心目中,“硕人俣俣”就是指男子的舞姿美好,“俣俣”所形容的应该是舞姿优美而不是身材健硕。要之,只有相当于字根的“吴”本身具有表示诸如“形态美好”、“声音动听”这样的原初意义,古人才能够比较自然地赋予“娱(俣)”、“误(悮)”等字也表达美好娱人的相关意义,因此“吴”字构形表示说话的基本意思,确实应该与粗狂喧哗无关,而是与柔声细语、比较好听相关。
关于“吴”初义的上述新解,可以使人认识到,以苏州为核心区域的先秦吴人应该很早就具有说话声气柔美、擅长精雅歌舞艺术的特征,并且与其历史悠久的崇文传统密切相关(详见第三部分论述)。中国近代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刘半农说过:“自从六朝以至于今日,大约是吴越的文明该做中国全部文明的领袖罢。吴越区域之中,又大约是苏州一处该做得领袖罢。”①苏简亚、张澄国:《苏州文化概论》,第35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至少就文化艺术方面来说,这也许确实没有言过其实,并且完全可以如顾颉刚先生关于吴歌诞生时间的说法,上溯到《诗经》乃至更早的时代。这就像“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发现,使人突然认识到这样一点:“上海这个当今闻名于世的大都市,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它是近代以来迅猛发展起来的,其实,这里同样有着悠久的古代文明发展史……”②王广禄:《良渚遗址遍江南》,《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16日第5版。因此,本文的相关研究,犹如给以苏州为核心的先秦吴人及先秦吴文化研究的探索创新开启了一扇能够迎风延晖的别样花窗,具有很好的学术价值。
二、“吴”古今语音语意与先秦时代的苏州文化
无论是历史学家提出的“先吴文化”还是春秋吴国文化,其起源地和中心区域都应该与太湖密切相关。据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可知,太湖流域的人类文明可追溯到一万多年前,其中位于苏州市吴中区三山岛、工业园区草鞋山和吴江区梅堰等文化遗存,是其最为久远的主要代表,这可说明苏州从“先吴”时代开始就应该是“先吴文化”的中心。历史地看,苏州这个名字从隋朝开始使用,其先前的称谓中大多带有“吴”字,比如吴城、吴都、吴墟、吴趋、吴中、吴郡等,其辖地中也多有吴县、吴江、吴市、吴塔、吴巷、吴趋坊等带“吴”字的命名。这个情况在历史上最宽泛的吴文化区域内都是无与伦比的,特别值得关注和探究。有研究表明,上古吴地先人最初以鱼为图腾,③王卫平:《论吴文化的基本特征》,见《吴文化与现代化论坛》第1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上古汉语“吴”与“鱼”同音,该语言事实目前依然保留在苏州方言中(可能是唯一的),这似乎可以说明上古时代表示“吴地”、“吴人”和“吴语”的“吴”字,其最早被命名与被定义,应该与当时生活在苏州一带先秦吴人的生产与文化密切相关。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④《左传》第44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可见中国通常第一个纪元“夏朝”之前,还有“虞”这个朝代。关于这个朝代,按旧说主要等同于舜所建的“有虞”,其实更加可能的是指那个时代与先人主要从事渔猎生活相关。“虞”的义旁为“虍”,其表述意义应该与渔猎相关。在先秦文献中,无论是关于“虞人”、“虞师”、“虞官”、“驺虞”、“无虞”等常见的词汇,确实无一不是都和渔猎相关。从舜曾经到过越地上虞,其后代又被封于上虞,⑤见百度百科“上虞”词条。大禹陵位于绍兴,上古吴越同族⑥何光岳:《先吴的来源和迁徙》,《宝鸡文理学院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百度百科“吴”词条。等历史情形来说,夏朝之前的虞朝,不仅与中原之地和吴越之地都关系密切,而且与“吴”姓族群的关系也特别亲切。⑦何光岳:《先吴的来源和迁徙》,《宝鸡文理学院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百度百科“吴”词条。“虞”字取声于“吴”,与“吴”、“鱼”均音同义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诗·周颂·丝衣》:“不吴不敖。”《史记·褚少孙补孝武纪》引《诗》作“不虞不骜”。⑧《词源》第26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修订本。泰伯弟弟仲雍,又名虞仲、吴仲,其安葬地因此得名虞山。这些也都是很好的佐证。因此,古老的“虞”王朝时代与先秦早期的“吴地”、“吴人”确实应该密切相关,从相对可能的意义上说,其最初的族群渊源除了和舜相关,也很可能跟著名的治水之神“鲧”和“禹”及其原始族群相关。
“鲧”和“禹”这两个字,目前暂未见到有甲骨文,以其相关金文(其构形刻画特征与甲骨文非常相近相似)来看,“鲧()”表示以网捕鱼,“禹()”⑨金文“禹”字形中的鱼,像头部较大的鲶鱼,它们在长江中下游各地的品种和数量非常多。这类鲶鱼无鳞有须,肉细腻肥美,游动时身体弯曲摆幅很大,就像该金文字体构型所表示的那样。其习性喜欢在夜间呆在离岸很近的浅水区捕食,梅雨季节更是会大量进入稻田沟渠,相对比较容易被抓获。则表示用手或者用叉抓鱼。这说明他们父子都属于以鱼为图腾的传人,非常识水性,所以会被懂得合理使用人才的帝王委派去治水。根据《尚书》等先秦文献记载,大禹治水的对象之一是太湖(震泽),所以苏州以太湖旧称“震泽”命名的震泽镇上至今建有一座著名的“禹迹桥”。曹锦炎先生《从青铜器铭文论吴国的国名》一文指出,在目前出土的吴国铸造的二十九件青铜器铭文中,对于吴国的称谓有六个版本:工䲣、工□、①这个空格中的字是“䲣”字去掉右边“反文旁”的那个部分,因字库里没有,所以借用“口”替代,下同从略。攻五、攻敔、攻吴和吴。②曹锦炎:《从青铜器铭文论吴国的国名》,《东南文化》1991年第12期。其中作为与“吴”同音通假的字中间,有五个字都和“䲣”一样在构型中带有表示吴地先人图腾的“鱼”字;另外铭文中用“□”替代的那个字,是“䲣”的左半部分,也有“鱼”。苏州市吴江区,有一个与此密切相关而历史悠久的别名叫“鱸(魲)乡”,在那里的方言中,不仅“鱼”、“吴”同音,而且第一人称“我(吾)”和表示数字的“五”,也一直和“鱼”、“吴”同音。这种情况也存在于苏州其他部分郊区方言中,但是不存在于苏州之外的其他方言区。想来,这也很可能就是“攻五”、“攻敔”中以“五”、“敔”代指“吴”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公元前五八五年,吴王寿梦登基,吴国从此有确切的纪年开始,而“寿梦”这个称号的意思是“长久牢固的渔网”,③见江苏广电总台出品的6集电视片《回望勾吴·肇建吴国》。只是此前从来没有人关注过这个名号背后所蕴含的地域文化信息。至于苏州的“苏(穌、蘇)”中本身也有“鱼”字,更是不用赘言。其中所蕴含的图腾文化秘密似乎有迹可寻,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苏州为什么从隋朝开始会被命名为苏州的重要而深刻的文化原因之所在,也是其以后几乎没有更改地一直沿用至今的主要理由之所在——因为以苏州命名的这个鱼米之乡,在华夏大地上实在是非常独特而自古以来一直像一颗最为耀眼的明珠。因此,很早就有专家坚定地认为无论是字形、字音和字义三方面来说,“吴”就是“鱼”,并且被有的专家认为“此乃千古不刊之论”。④周国荣、周言:《“吴”名考辨》,《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3期。
值得赘言的是,以中原地区基本对应于相传中关于黄帝、尧舜以及夏朝立都区域的仰韶文化来看,其中鱼的形象及图案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⑤如其中《人面鱼纹盆》等很多器皿上都有鱼或者是人鱼的图案。如果说世界上很多民族早期都有鱼崇拜文化是很自然的话(第一,鱼是早期人类相对比较容易获得的动物性食物;第二,古人特别害怕和鱼密切相关的水患;第三,鱼的繁殖能力特别强,古人祈求像鱼一样多子多福),那么说华夏民族很早就有鱼文化的影响也很自然。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左传》所谓“虞”那个朝代,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是“鱼”图腾崇拜朝代,所以“治水”是当时的经国大事之一。事实上,中华龙的形象中有不少鱼的因素(形体上的鳞片,属性上与水密切相关),所以自古就有“鱼龙混杂”的说法。可见苏州一带以鱼为图腾的先秦吴文化,尽管相对缺乏直接而比较可靠的相关文字记载,但是相关考古发掘可以看出其文明的起步也许并不落后于中原地区——这从“三山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一脉相承可以获得很好的证实——只是这里的地理气候环境决定了某些上古文化遗存的自然保留会特别困难,因此缺乏相对齐全的文物实物资料及相关记载,也影响了相关学术研究的很好开展。
三、不可忽略春秋吴国一以贯之的崇文传统
春秋吴国从泰伯、仲雍兄弟开始,此后一直到寿梦王之间的相关记述非常少见。泰伯是历史上公认的仁者贤士,一直受到高度赞美,但是有关记述相对空泛。使吴国开始强大的寿梦的最小儿子季札,虽然没有其先祖泰伯的名气那么大,但是其在《左传》相关历史记载中所展现出来的诗书礼乐素养及才华,则不得不让人觉得实在是先秦时代神州大地上少有卓越的文艺评论家。近年来,很多吴文化研究者,几乎都不怎么留意春秋吴国文化发展从泰伯到季扎之间可能有的特色与传承,却津津乐道于春秋吴国的“尚武”传统与“雄邦”策略。①比如江苏广电总台出品的6集电视片《回望勾吴》关于“吴”造字初义的诠释。其实真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至少是其所见所说不够全面。
上古春秋吴国早期很少战事,为什么会从寿梦开始“操吴戈兮披犀甲”而“始(强)大”?《春秋谷梁传·哀公十三年》对此有过专门评述:“吴,夷狄之大国也,祝发文身。欲因鲁之礼,因晋之权,而请冠端而袭。”②阮元:《十三经注疏》,第24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影印版。雄才大略的寿梦在中原朝觐之后,很想在周王室日益衰落的情况下,以自己是周王室血脉相传之后的身份来争取获得周王室的地位与荣耀,于是吴国从此南下、西拓和北上的征战步伐连续四代没有间断,一时间影响很大地凸显了“吴国始大”的剑气啸傲。这确实是不争的历史事实。然而,对于春秋吴国及先秦吴人形象的全面了解,不能偏执于某些因时因地有所侧重的历史记述,不然的话,就会谬以千里。作为非物质形态的人类社会文化,一般都具有很强的可延续性,往往不会在很短的社会发展阶段出现较大改变,甚至也不会因为改朝换代或剧烈动荡而立即发生明显改变。因此,在研究先秦吴文化和春秋吴国文化方面,有一个问题非常值得思考,那就是:夫差被灭国后,以苏州地区为核心代表的吴文化为何能一再以崇文特色卓然自立于华夏大地?这是因为春秋吴国文化在公元前四七三年后出现了巨大的改变,还是因为以苏州为核心的先秦吴文化本来就有注重诗书礼乐和崇文习艺的另一面?
历史地看,如果说“操吴戈”、“带吴钩”曾经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春秋吴国军人骁勇善战这一面的话,那么,客观的历史现实同时也在生动地映现春秋吴国社会生活崇尚礼乐教育、追求华美艺术和精细生活的另一面,并且后者也许应该更为主要。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访问“请观于周乐”的记载,其中非常详情地记录有对《诗经》、《象箾》、《南籥》、《大武》、《韶濩》、《大夏》、《韶箾》等当时最为著名的礼乐篇章进行全面正确而简洁精当的评论。这在先秦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而进行这次名扬华夏历史的著名文艺评论的人,就是使“吴国始大”君王寿梦的小儿子季札。③《左传》,第251-253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由此,季札的才华、学识和德行不仅当时就获得中原绝大部分诸侯国君王与大臣的高度认可及另眼相待,而且日后也特别获得孔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高度赞美。后世一直并不缺乏对季札这方面的赞美,但是与此同时却很少有人认真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能够培养出如此一位满腹诗书礼乐、德才文采并茂而卓然独立的君王公子,需要怎样的社会文化教育基础及艺术氛围?或者说,如果春秋历史时期的吴国长期在社会礼乐文化艺术教育方面非常粗鄙落后,其短时间的强大,就像一个暴发户式的土豪,其年轻的公子怎么能被造就得令中原文明之地的各国君王大臣都刮目相看?更加值得强调的是,季札的父亲寿梦,既是第一个让吴国开始实现春秋五霸基业的君王,也是第一个开始亲自考察中原文化、研究当时中原正统礼乐的吴国君王。为了延续吴国的千秋大业和实现他光复周王朝的政治梦想,寿梦有意违反当时长子嫡传的礼数,处心积虑地设计了能够让小儿子季札成为吴国君主的王位传授安排。这个重大的历史行为非常明确地昭示人们,寿梦对吴国要逐鹿中原永续霸业的战略认知,是非常注重君王在诗书礼乐和道德文章方面能力水平的。寿梦这样的认识及行为,与其先贤泰伯、仲雍的思想文化精神其实一脉相承。可惜连孔子这样的大人物都只看到了寿梦努力称霸的军事行动,根本没有注意寿梦其实特别器重季札的道德品行与礼教才华。这个无可辩驳的史实应该可以充分证明,吴国在开始以兵法、武器、军队的先进而称霸一方之前及同时,应该一直充分地继续保持着对礼乐政治和文化艺术教育方面的重视及先进性。
目前保存在镇江博物馆的青铜“凤纹尊”,其图案结构与雕镂的精细华美确实令人钦佩,使它成为国宝级的一件文物。笔者想强调的一点是,如果说上古制造各种数量众多青铜农具和武器的水平,能够很好地体现当时冶炼锻造技艺水平的话,那么制造青铜礼器的水平,则能够很好地体现当时社会审美水平和文化艺术水平。如果说上古那些制作相对粗放而具有李泽厚先生所谓“狞厉美”的青铜器一般都对应着相对原始粗莽社会文化的话,那么制作工艺精良、图案纹饰优美的青铜器则应该对应相对更为先进的社会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举世闻名的“吴王剑”也值得一说。在制作技术层面来看,其布满剑身精美纹饰的技艺在吴国灭亡以后一直失传到二十一世纪。将出土的吴王剑和西汉刘向编写《新序·杂事卷七》记述的“季札挂剑”故事对照来看,“吴王剑”的制造确实能够很好地说明当时吴地苏州的工艺水平和审美文化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所以会有“干将莫邪剑”的历史传说。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的著名春秋吴国青铜器“邗王是野”戈,设计制作异常精美;在太湖三山岛发现的春秋吴国青铜“蓖齿镰刀”,居然至今锋利可用……从文化艺术层面来说,吴王剑其实既是武器,也是礼器。著名的“季札挂剑”故事告诉我们,季札之所以在完全清楚徐国国君很想得到季札随身佩剑意愿的情况下,不得不到他拜访中原诸国结束返回的时候才能将自己的佩剑送给徐国国君,就是因为他作为吴国公子去拜访中原诸国时,随身佩剑是当时不可缺少的礼仪规范要求之一。总之,吴王剑的精美,既体现了春秋吴国青铜器铸造的艺术水平,也很好地折射了当时春秋吴国社会文化艺术精美的历史真实,或者说很好地反映了当时吴国的崇文传统及其社会氛围。
以先秦时代有关历史记载、文学描述和考古发掘来看,春秋吴国的玉器文化、船橹文化、饮食文化的先进性及精美程度也都很早就著名于世。一九九二年,吴王寿梦墓在苏州真山被发掘,其中出土的“玉覆面”和“玉甲饰”,被考古学界认为是后世“金缕玉衣”的前身,其制作的精致程度,可谓空前,与至今享誉海内外的苏州玉雕技艺遥相呼应。①见江苏广电总台出品的6集电视片《回望勾吴·肇建吴国》。据最新考古发掘证实,苏州木渎镇附近建造的一座城池也设计有军民两用的水陆城门,这可以说明吴地水上交通设施及工具制造技术在当时的先进与发达。屈原《涉江》有这样两句诗:“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而击汰。”②朱熹:《楚辞集注》,第79、147、1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可见“吴榜”和“吴戈”在屈原的心目中以及当时社会里,应该同样很有名气。屈原《大招》:“吴酸蒿蒌,不沾薄只。”《集注》:“言吴人工调醎酸,爚蒿蒌……其味不醲不薄,适甘美也。”③朱熹:《楚辞集注》,第79、147、1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宋玉在《招魂》中也有相关记述:“和酸若苦,陈吴羮些。”④朱熹:《楚辞集注》,第79、147、1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要知道,在吴国被灭国后几百年,远离吴地但热爱艺术与精雅生活的楚国大诗人们还在歌颂吴歌优美的同时,也忘不了对吴地菜肴精致美味进行特别描写,这确实可以让后人充分感受到春秋乃至更早吴地文化艺术精美优异这个历史事实的客观存在与影响深远。这与前面所述先秦吴地歌舞艺术特别优美先进的历史事实完全契合,都能非常自然而有力地折射出先秦吴文化相对精雅的先进程度和先秦吴人相对精细的文明生活程度。
(本文为“苏州市文化研究征集项目”《苏州文化与吴文化基本关系研究》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刘浏)
倪祥保,男,江苏常熟人,一九五三年四月生,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