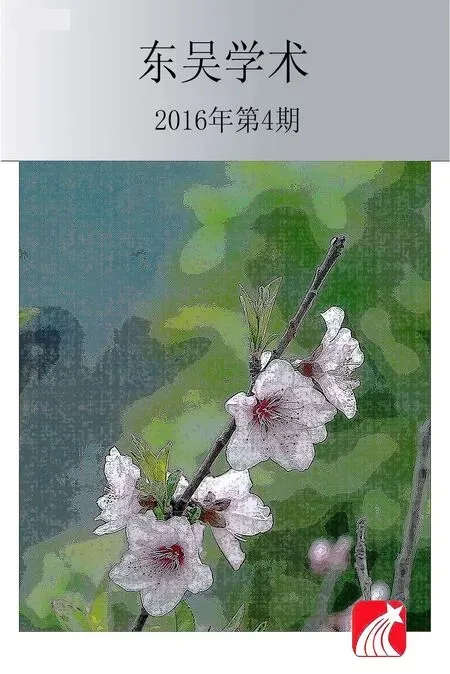论叹息
——以杨键“足音”系列画作为中心
敬文东
诗学
论叹息
——以杨键“足音”系列画作为中心
敬文东
本文以杨键的“足音”系列画作为解剖、分析对象,详细阐明了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在怎样以叹息的方式对待时间;叹息是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核心之一,在被杨键进行现代转换后,变作了对付现代社会的垃圾实质的重要武器。在中国当代艺术追随西方艺术走入绝境之后,杨键对传统的转换为当代中国艺术起到了起死回生的作用。
杨键;叹息;“足音”;系列画作;垃圾
一
杨键①杨键,1967生于安徽马鞍山,1995年获首届刘丽安诗歌奖,2000年获柔刚诗歌奖、作家杂志奖、长江文艺方文奖,2003年出版诗集《暮晚》,同年被南方都市报评为全国十大好书之一。2006年获宇龙诗歌奖,2008年诗集《古桥头》获第六届华语传媒诗人奖,2011年在南京艺事后素举办水墨个展,2013年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道之容颜》水墨个展,2014年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办《冷山水》个展。长期深居简出于安徽马鞍山,潜心于佛事,问道于西洋绘画。在跟友人夏可君一次略带抒情性的艺术对谈中,杨键却舍弃西洋绘画,专门谈到了令他钟爱的传统水墨精神:“水墨就是心性的呈现。有什么样的心性就有什么样的水墨……水墨是特别适合中国人的,中国的文化向来就是在心性上下功夫,儒家的内圣与佛家的见性,说到底就是为了让心性自然全然流露。生命品性其实是心性的品性。水墨就是这种品性的呈现。”②杨键:《冷山水》,第114页,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4。杨键对水墨精神的如此嘉许、如此理解,同中国传统艺术向往的境界如出一辙:水墨精神等同于道心;③见敬文东《从心说起》,《天涯》2014年第5期。道心等同于心性上的“静”,所谓“人生而静”,④《礼记·乐记》。所谓“静时是性,动则是情”。⑤《礼记·中庸》孔颖达《正义》引梁贺玚。而心性上的“静”则意味着绵长、醇厚、从容的内陷之力,意味着暗中酝酿、起意的凸起与反弹,也意味着洁净和纯静。
中国传统水墨精神愿意“坦开的仁慈”,⑥柏桦:《往事》,第100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愿意公开的秘密无非是:面对处处陷阱的小人社会,水墨精神的如许脾性必将从隐喻的角度,体现为画者在心性姿势,或精神身位上的侧身横站;横站却必须以水墨精神的如许脾性为靠山,以致于纵横捭阖、吞吐八荒。惟其如此,才对得起水墨精神给予它的信任,也才能被水墨精神委以重任。在此基础上,横站方有能力成为心性与水墨精神的交汇点,才能让绘事者与水墨精神浑然一体,或合为一体,达到类似于剑在人在、剑亡人亡的不离不弃之境。面对平庸、不洁的凡间尘世,面对嘈杂、喧嚷的传统生活之俗,水墨精神的被掌控者早已在心性的层面上,摆出了侧身横站的姿势,以便从凡间尘世(或小人社会)全身而退,从肉体到精神,但尤其是精神。随着水与墨游走并定型于宣纸或其他材质(比如关晶晶喜欢的坦培拉),①见徐冰《齐白石的工匠之思与民间智慧》,《今天》2014年第2期,第58-60页。绘事者的心性姿势(即横站)被转化为水墨定影,被化作清癯、绵远,且惹人遐想的氤氲之气,孤高、幽深、澄澈,没有一丝尘埃与俗气,只在宣纸(或其他可能的材质)周边的荒寒极地处,能隐隐听闻凡间尘世的鸡鸣、狗吠、蛙叫,以及萧索柴门被叩响时,发出的清冷、旷远之声。
作为“冷山水”、“足音”、“荒寒”等大型水墨系列画作的绘制人,杨键对水墨精神与画者心性间的水乳关系既了如指掌,甚至熟悉它的每一条纹理、每一块肌肤,也洞若观火、明察秋毫,谙熟其嗜好与脾性。杨键由此深知:受水墨精神提调,也受制于水墨精神难以解释的情怀与性情,侧身横站能带出,或已经派生出了两种相互依赖、恰成掎角之势,有时又相互平行、并且相对独立的精神气质:蔑视与叹息。不用说,即使从词源学的维度考察,②“蔑”自古就有“没有”、“无”(比如《诗经·板》:“丧乱蔑资,莫曾惠我师”)、“轻视”(比如《国语·周》中:“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等义(见《词源》,第270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蔑视也只能是斜视的眼神,轻盈、快疾、冰冷,对被蔑视之物既看见,又故意性地不屑于看见;叹息则是响动不大的声音,大多数时刻生发于内心,在更多的时刻,却为内在之耳所捕获(此为内听,其构词法模仿了内视)。应和着光线从其内部发出的指令,也呼应于光线为自己认领的癖好,斜视的眼神没有重量;响动不大的声音也只能像马克思调侃过的那样,顶多震荡着空气。但在古典大师们眼里,叹息和蔑视不仅力量超群,而且意义重大,何况水墨精神就像卡内提(Elias Canetti)笔下的“宣告国王女”那样,其“鄙视的储备用之不竭”。③卡内提:《耳证人》,第1页,罗丹霞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也许从逻辑的层面上暗示过:蔑视和叹息就像语言一样,也应当是特定的世界观,是“对时间和世界的解读”,④乔治·斯坦纳:《乔治·斯坦纳回忆录》,第111页,李根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而且还应该是视角特殊、目光独具的“解读”。在杨键迄今为止几乎所有水墨性质的画作中,这两种精神气质都现实地存在着:有时是蔑视和叹息相交织,难解难分,耳鬓厮磨并彼此声援;有时因主题、对象的变化,更偏重蔑视,更愿意将斜视的眼神寄为腹心(比如“冷山水”系列);有时则因心境、语境上的差异,更宠幸叹息,寄希望于响动不“大”的声音,能够肩负起更“大”的伦理作用,而不仅仅是获取差堪匹配的美学功效(比如“足音”系列)。
作为不乏绝对特性的精神气质,叹息与蔑视既是水墨精神更具体、更精细入微的展现,也是一派看似无形,却实际存在的氛围。它是嗅不到、摸不着,但能“看”得见的精神或艺术的丝丝缕缕,却无需借助舍斯托夫(Lev Shestov)大力称颂的二重视力——一种源自神学的超验之力,一种来自上帝的绝对之光。⑤见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第23-97页,董友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作为寄居于中国传统水墨精神的土著症候,蔑视与叹息来自无神(但并非唯物)的此岸世界,且只能来自此岸世界。虽然它们在“远心”、“天游”的鼓励下,有看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外貌或表象,却既无神秘气息,也无超验特性,当得起艾斯特哈兹·彼得(Esterhazy Péter)的睿智之言:“拥有独特命运的民族是不承认救世主的民族。”⑥艾斯特哈兹·彼得:《赫拉巴尔之书》,第92页,余泽民译,2010。事实上,这个自打出生伊始就多灾多难,却屡屡浴火重生的民族,从未“亲聆”过神在“山上”给予的“垂训”(Sermon onthe Mount)。①见J.B.伯里(J.B.Bury)《思想自由史》,第107页,宋桂煌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因此,蔑视与叹息只忠贞于无神论和经验性的此岸、此刻,不离不弃;对超验或神性的彼岸、彼刻,既无兴趣,也缺乏了解,但更主要是缺乏兴趣。叹息和蔑视不过是水墨假手横站,对经验性情感或情感性经验的氤氲气化,与作为伟大概念(或观念)的虚,有异曲同工之妙——想想关晶晶对虚进行现代转换后形成的现代烟云吧。
* * *
像“情怀”或“性情”一样,“天意”神秘难解,但也是一个管用的概念。从很早开始,中国的古贤哲就“天意”性地热衷于命运知识,视必然知识为低等之物,或形下之物(比如他们对名家,尤其是对公孙龙子所持的鄙夷态度)。②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97-111页,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在烟云密布的旧时中国,之所以会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③《孟子·滕文公上》。的身位差距,或许就有“劳力者”更需仰赖必然知识的原因在内。因此,中国的古贤哲们倾向于相信,对于至高之道,人们必须做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④《孟子·公孙丑上》引告子言。——是为儒家;如果对道仅仅“听之以耳”以得言,“听之以心”以得意,不过是“小知”(智)而已,只有“听之以气”,方能体会道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⑤《庄子·人间世》。——是为道家。杨键与夏可君那番不无抒情色彩的艺术对谈,似乎已经暗示,甚或十分干脆地表明了杨键的艺术信念:气化而成的氛围(而不是物象或体态上的形似),才是杨键所理解的水墨精神更乐于经营的东西。有如看似神秘复杂、高不可攀的圣人也不过是朱熹所谓的“一‘团’天理”⑥《朱子语类》卷二九。那般简单、直白,氤氲气化也没多少神秘难解之处,仅仅是一“团”惹人心动的情绪气流,有如能看见、能感知,却不可触摸的暮色。而暮色,犹如一位年轻女诗人以第三人称诉说自己年幼的孩子:“我看见他,他还在无边无际的睡眠与风里”⑦夏午:《与子书》,未刊稿,上海,2014。——“他”对“我”的存在一无所知,对“我”的到来与“我”对“他”的观看毫无兴趣。
对于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画学成就及其出源地,弗洛伊德的断言也许称得上恰如其分:“列奥纳多对自然的研究可能开始于为他的艺术服务;为了确保掌握对自然的模仿,并向别人指出这条道路,他直接努力于光的性质和法则、色彩、阴影和透视画法的研究。”⑧《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第52页,张唤民等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与达·芬奇的“科学”做派大为不同,也跟达·芬奇视绘画为必然知识的产物迥然有别,⑨中国的山水画强调光,据信始于20世纪的大画家李可染,这显然是来自西方绘画的观念(见王鲁湘《书卷山河》,前揭,第94-95页)。中国“古人之作画也,非以按城域,辨方州,标城阜,划浸流。本乎形者融,灵而动者变,心止灵无见,故所托不动,目有所及,故所见不周”。⑩罔村繁:《历代名画记译注》,第329-330页,愈慰刚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以夏可君之见,中国传统绘画向来不以透视为枢纽,也不以“光”为轴心组建的明暗关系为主导,转而以“触觉以及触觉化的味觉”为圭臬。⑪⑪夏可君:《平淡的哲学》,第53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⑫中国古代也有追求形似的工笔画。诗歌语言具有自指性(language calling attention to itself),即要让读者关注语言自身,不仅仅是关注诗歌传达的意思(见周英雄《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第124页,香港:东大图书公司,1983)。仿照自指性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工笔画仿佛使用了说明性的文字,是为了把事情说清楚,画笔不存在自指性。文人水墨画与它刚好相反。⑬约翰·伯格:《观看之道》,第11页,戴行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这等艺术哲学上的得道之言意味着:中国传统绘事活动由此滑向以蔑视为主旨、以叹息为核心的氛围论,而不是以光为出发点的透视论(或聚焦论、焦点论),在逻辑上就是再顺畅不过的事情,不存在任何延宕、妥协之处。⑫⑪夏可君:《平淡的哲学》,第53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⑫中国古代也有追求形似的工笔画。诗歌语言具有自指性(language calling attention to itself),即要让读者关注语言自身,不仅仅是关注诗歌传达的意思(见周英雄《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第124页,香港:东大图书公司,1983)。仿照自指性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工笔画仿佛使用了说明性的文字,是为了把事情说清楚,画笔不存在自指性。文人水墨画与它刚好相反。⑬约翰·伯格:《观看之道》,第11页,戴行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虽然透视法一如约翰·伯格(John Berger)认为的,“以观看者的目光为中心,统摄万物……一切都向眼睛聚拢,直到视点在远处消失”;⑬⑪夏可君:《平淡的哲学》,第53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⑫中国古代也有追求形似的工笔画。诗歌语言具有自指性(language calling attention to itself),即要让读者关注语言自身,不仅仅是关注诗歌传达的意思(见周英雄《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第124页,香港:东大图书公司,1983)。仿照自指性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工笔画仿佛使用了说明性的文字,是为了把事情说清楚,画笔不存在自指性。文人水墨画与它刚好相反。⑬约翰·伯格:《观看之道》,第11页,戴行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虽然氛围论需要仰仗更“感性”的“气化”过程,需要对“目光中心论”持大不以为然或大不敬的态度,但这等看似针锋相对的情形,却不能轻易被认作氛围论更靠近命运知识,透视论更倾心于必然知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与直白,思虑也不该如此机械、板滞和教条。不用说,氛围就是心性的水墨化实现,就是道心消融于水与墨,犹如盐之溶于水;就是精神身位或心性姿势暗中充任水与墨的精、气、神,恰如筋骨之于血肉。氛围呈现出来的境界,必定与心性、道心的境界成正比;或在它们两者之间,至少应该具备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如果正比关系在精确度上要求过于苛刻的话。杨键之所以敢冒险指责“油画的玄妙性不够”,①杨键:《冷山水》,前揭,第110、111、113页。很可能就是基于水墨精神的氛围论立场,对油画的透视论律令发出的质疑——油画的伟大与辉煌,或许当真不在“玄妙”,更有可能寄居于别的特征之上。
和更加看重解剖术、透视术的西洋绘画相比,中国绘画(尤其是文人山水画)一向视氛围的完善、再完善、更完善为至高境界。所谓氛围,就是“触觉以及触觉化的味觉”,但尤其是能够将“触觉以及触觉化的味觉”展现、铺陈出来的那种氤氲气化。和《蒙娜丽莎》遵循或追求的形似原则大异其趣(但这种形似的结果,又不能被认作黄宾虹指斥的“欺世盗名之画”),②王伯敏编:《黄宾虹画语录》,前揭,第1页。以蔑视和叹息为主旨的氛围论既意味着中国古人心目中的绘画之善(这是中国艺术思想之根本),也意味着绘画之真,最终,才格外(而非额外)地意味着绘画之美。③中国绘画强调真、善、美是一体的,尤其以善为最重要。在前孔子时代,“‘美’与‘善’两字在不少情况下是同义词,所谓‘美’实际上就是‘善’。”(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1卷,第7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孔子较为严格地区分了善与美,但在他和原始儒家那里,善不仅大于美,还是美的主要出源地,比如《论语·八佾》有云:“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美是善与其表现形式的完满统一。无论是对于中国的绘制者,还是绘事活动的观看者,传统文人水墨画的真、善与美,都存乎于对氛围的感觉中,而不存在于聚焦或透视中,甚或光的明暗深浅中。所谓对氛围的感觉,只能是一种来自于全身心的感觉,跟心尖的震颤与快速收缩尤其相关,不是单纯或单一的视觉效应——单一或单纯的视觉效应,只能是西洋古典艺术作品(比如《蒙娜丽莎》)对画者和观者提出的要求。弃西画而从水墨的杨键很清楚:对西洋艺术来说,所谓震撼人心的真,以及建立在真之上的善与美,在更大的程度上,正等同于照相般的写实。它对光有精细、独到的研究,更有高度的依赖,恰如黑格尔所言:惟真为美。也许是有感于此,杨键才敢背靠蔑视和叹息,背靠氛围论斗胆放言:“西方绘画是‘五色令人目盲’,中国绘画‘直指人心’”;甚至不惜发出“中国随便一张仕女图都可以超过”《蒙娜丽莎》的豪言壮语,或夸张言辞。④杨键:《冷山水》,前揭,第110、111、113页。虽然杨键曾长期问道于西洋绘画和透视论,但若许年来,他隐遁于偏僻且适合偏安的安徽马鞍山,像关晶晶一样,也在致力于对中西两种绘事余产的化合作用,以便孔武有力地表达现代社会(或当下中国),为陷入绝境的当代中国艺术——这总学问或垃圾学的组成部分——找到出路。
* * *
尽管中国传统画论倾向于“把画的本质归结为诗的本质”,⑤高尔太:《论美》,前揭,第294页。杨键甚至从八大山人的画作中,读出了李后主凄凉、悲怆的词意,⑥杨键:《冷山水》,前揭,第110、111、113页。但在古旧时期的中国,不同形式的艺术门类仍然各有所司,也各有侧重。文载道,诗言志,小说、戏曲、民间笑话表达乡野闾巷中凡俗的人情世态,⑦见敬文东《牲人盈天下》,前揭,第346-409页。词被认为最能“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⑧张惠言:《词选序》。刘东对此有过很精辟的观察:“翻检一下《全宋词》,就会发现,原来被宋诗超越了的‘悲哀’,全躲到宋词里了。这里,简直是一片愁的海洋……毫无疑问,这里是集成着曹植的‘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年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箜篌引》),继承着阮籍的‘清露被皋兰,凝霜沾野草。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叹咏怀》),也继承着李白的‘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古风》)的,是对自己之有限生命只能享有有限快乐的懊丧和惋惜。”(刘东:《思想的浮冰》,前揭,第220页)绘画则以蔑视、叹息等精神样态为至高规格的氛围追求,以显示文人士夫的浩淼情怀,孤高不与的精神操守与道德诉求。在中国古代可以想见的一切艺术形式中,惟有绘画(尤其是文人水墨画),敢于一尘不染,至少敢于在表面上远离一切不洁之物(比如死亡、外部的灾难,以及内部的人性之恶),①也许枯败的残荷是难得的例外,但这跟残荷被寄寓时光流逝的感叹有关(见市川桃子《莲与荷的文化史》,第5-13页,蒋寅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专事于描绘“沧霞倒景,饵玉玄都”②《文选》(郭璞:《游仙诗》),李善注。一类高妙、高迈之境。也惟有看似绝尘出世的绘画,能够免于逃避现实、躲避责任和远离“噬心主题”的指控,免于深陷寂静主义(quietistism)和软骨头艺术的责难。但那仅仅是因为绘画独占了作为精神和艺术氛围的蔑视与叹息,并且将它们当作了自己的注册商标,别的艺术品类不得轻易染指。钱锺书说:“相当于南宗画风的诗不是诗中的高品或正宗,而相当于神韵派的诗风的画却是画中的高品或正宗。”③见钱锺书《七缀集·中国诗与中国画》。诗、画取径相似,立意等同,结局却如此大异其趣,也许不失为这方面一个上好的例证。
高尔太有言:中国文人山水画是“对官与禄表示轻蔑和反感、追求自然美、追求孤高澹泊的生活理想和人格理想的艺术”。④高尔太:《论美》,前揭,第298页。徐复观似乎说得更直白,也更为详细:“中国的山水画,则是在长期专制政治的压迫,及一般士大夫的利欲熏心的现实之下,想超越社会,向自然中去,以获得精神的自由,保持精神的纯洁,恢复生命的疲困而成立的,这就是反省性的反映。”⑤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前揭,第5页。依高、徐两公之睿见,蔑视意味着画者仰仗作为心性姿势(或精神身位)的横站,视外部世界的嘈杂为乌有,视凡间尘世的喧嚷为无物,友山友水,友鱼友荷,以孤绝而不容商量的态度与心性,只在一个轻描淡写的眼神间,就遗弃了现实世界中一切可以被俗和媚俗来界定的人、事、物,就战胜(而不是消灭)了被形容术礼赞过的一切情与事——“的”字投靠的形容词当更不在话下,因为它不过是形容术的跟屁虫,但说成奴仆可能更准确。嵇中散有言:“知名位之伤德,故忽而不营”;“识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顾。”⑥嵇康:《养生论》。马麟《静听松风》、马远《山径春行图》等画作中的人物衣髯飘飘,面色平和、表情轻松,于无声处,孤沉独往于山水松风之间,一副自得于“天地之大美”而睥睨世事的模样,分明是蔑视的绝佳造型,但更是一派清冷、孤远、人迹罕至的精神氛围,笼罩在“远心”之中,寄居于“天游”之下。嵇中散诗曰:“蝉蜕弃秽累,结友家板桐……长于俗人别,谁能睹其踪?”倪云林的《虞山林壑》、董其昌的《秋山图》,恰如中散大夫所言,全无俗人出没,更无俗事、俗物打扰,像“剩山”系列画作中的大多数作品一样,只有透明的空气、烟云,还有无声的山水、泉石,构成了看似柔软的水墨氛围,以其弹性、内陷之力和暗中起意的凸起,嘲笑着竞相奔走于仕“途”和世“途”的内热之“徒”——“里急”之人就更不必细说。
作为“冷山水”系列、“足音”系列……等大型水墨画作的绘制者,杨键深知:虽然都是传统水墨精神假借横站制造的好结局,叹息在精神气质上,依然不同于(甚至迥异于)蔑视——尽管叹息与蔑视相互联手,近乎完美地成全了水墨精神的伦理意涵,满足了水墨精神的道德胃口。蔑视凭靠斜视着的冷眼,让目光越过世事之巅,以至于视世事为无物;叹息依靠横站捎带而来的侧眼余光,既瞥见了残存于凡间世事中令人不舍、不忍之物(比如流逝着的光阴与生命),也看见了令人不屑、不齿之物(比如生活之俗,尤其是生活之俗中的打眼部分亦即对名利、富贵的追逐)。叹息倾向于对不舍、不忍之物持沉吟与惋惜的态度,既悲悯,又隐隐有几分仁慈;对不屑、不齿之物持一种比同情多一点愤怒、又比愤怒多一点同情的心态,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小体量恼怒杂于其间,大体上可以称之为对不屑、不齿之物的轻度焦虑吧。而所谓焦虑,受仁慈、悲悯之托,就是为被焦虑者深感遗憾,和表征唾弃的愤怒与不屑大有差别——如果不是说完全不同的话。但无论蔑视,还是叹息,它们之所以有这等个性,有这等超凡脱俗的精神造型,都源自“静”与凹面,源自心性上的内陷之力,一句话,源自中国传统文化赋予水墨精神的基本任务。就像物质世界中没有永动机存在,精神世界里也不存在没有能量来源的蔑视与叹息,毕竟“有如黄河鱼,出膏以自煮”①苏轼:《读孟郊诗》。的状态既难得一见,令人叹惋,也难以持久。②见敬文东《依靠内心生活的人》,《天涯》2004年第2期。作为水墨精神一心追求的艺术氛围,蔑视以其孤高不与、彻底否定尘世之俗显示自己的力量。它志在冰雪、凌空蹈虚,既无焦虑,也无惋惜与沉吟(比如杨键的“冷山水”、“荒寒”等系列,比如关晶晶的“剩山”系列)。叹息则以其恻隐、悲悯,还有对不屑、不齿之物怀有的些许焦虑之心,显示自己的力量高出凡间尘世不只一筹,也不只一个档次,尚不需要拒敌于一个眼神之间的蔑视亲临现场(比如杨键的“足音”系列)……
因为对这两种精神气质都有深入的体察、持久的感悟,杨键十分清楚:与干脆利落、性情坦率的蔑视相比,叹息在看似的柔弱、絮叨与拖沓中,反倒有可能更见力量——一种柔软、绵长的内敛之力。沈周的《策杖图》中那位缓行于山间的戴笠者,侧身面对悄然消逝的光阴,任其自然而平心静气,像生活对自身的暗自期许一般,不露半点声色。但画者和观者对时光消逝的轻微叹息,却发自心间或喉头,被内在之耳小心而尽情地捕获,也被内听所吸纳;叹息声掩映其间,并因树木的枯荣、流水的渐行渐远得到了不动声色的映衬。八大山人的《古梅图》主杆枯朽,空其腹心,且将哭而未泣,有卡在喉头间的呜咽,犹如喜龙人(Osvaid Sirén)谈论李成的画作《读碑窠石图》中的枯枝:它“像受缚的龙一样虬曲翻腾,扭曲的枝条如锋利的巨爪般伸向天空,仿佛在为自己反抗衰老、腐朽和僵滞的斗争寻求援助”。③巫鸿:《时空中的美术》,第46页,梅玫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面对山河失色、江山易主的故国家园,朱耷寄寓于古梅的焦虑抚之可感,但又被控制在极为节制的范围内,既容不得半点夸张,也不允许有丝毫铺排。蔑视以其决绝的心性,不屑的冷眼,也许会令观者和画者畅快淋漓;它在内敛之中,在“静”与“纯净”中,大有快意恩仇或快刀斩乱麻的痛快感(比如“剩山”系列对垃圾的态度)。叹息以其温婉悲悯、沉郁顿挫的艺术氛围,则令画者和观者也在“静”与“纯净”中,感慨唏嘘、一咏三叹,既如“绕树三匝、何枝可依”的乌鹊挥之不去,也如闻《韶》后“三月不知肉味”的孔子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二
杨键二〇一〇年完成的“足音”系列画作,以水墨为媒介剂而留存于纸面的,是一对对状态各不相同、形状同中有异的足印(或足迹)。它们像圆睁的眼睛(陈丹青认为更像蚕豆④陈丹青:《你的资源就是你自己》,《东吴学术》2014年第4期。),既专注、痴情、认真,又略微有些哀婉和吃力。有时像是即将滑倒于泥土,仿佛道路缺少足够强劲的摩擦力以稳住脚步;有时像是要黏滞于泥土,仿佛道路纲纪松弛,以致于泥泞不堪,带有很强的黏着性,拖累了步伐,也沦陷了步伐。不用说,经由中西两种绘事余产化合而来的这些画面,已轻度偏离了传统水墨更乐于倡导的安静与和睦;跟“剩山”系列画作中的情形十分类似,凹面和内陷之力也显得不太从容,有些许的吃力感,甚至结巴感夹杂其间,和烟云在“剩山”系列画作那里获得的下坠感性质相同。这很可能是因为“足音”系列的绘制者在现代社会遭遇的情形,远远超过了古代的大师们在农耕中遭遇的情形。后者与不断轮回更替的灾难、饥荒、文字狱、权力开出的筹码、诱惑良心下坠的道德窘局,还有险恶难测的人心碰头聚首,一句话,与农耕之俗反复会面,却无缘得见力道更为强劲的现代社会特有之俗,也没有机会一睹垃圾之“芳容”,更不用说倾向于和垃圾同在的单子之人——这仅存于抛弃型社会的尤物。他们形单影只,或形影相吊,行走在现代社会的价值荒原上,踉踉跄跄着,踯躅徘徊着……
很容易发现,“足音”系列画作的构图与布局,既深得水墨精神支持的氛围论之大旨,也深得氛围论芳心独赏,但它化合中西两种绘画余产获取的美学效果,也必须考虑在内。寄居于每幅画面的,通常只有一对足印,像两个面面相觑的豆荚,又像一只大眼瞪着另一只小眼,孤单、落寞,恰若失群的孤鸿。它们仿佛是要急于逃离某种令人不安的状态,抑或是迫切着心情,想进入某种让人心醉的境地,反正都对眼下的境遇抱持不予信任的态度。每对足印细看上去,都有些许的哀婉、焦虑和性急,还有从含义深广的压抑中,侥幸逃逸出来的嘶喊。它们嗓音沙哑,声带微颤,有贴近地表的音量,或来自皮肤的声响,能被内听或内在之耳所把捉,具有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谓“显白”(the exoteric teaching)与“隐微”(the esoteric teaching)这两种深浅有别的精神症候,①见迈尔(Meier)《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施米特的学说与施特劳斯的论题》,第218页,林国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就看立于画面前的观者悟性如何,就看他们究竟是“深人”还是“浅人”,因为“深人观浅法,浅法亦成深”。②智旭:《梵室偶谈》。反之亦然:“浅人”观深法,深法亦成浅,犹如在动物的眼里,人也是动物。
依儒家教义,处于纲常网络之中的每个人,虽然都处于关系之中,都必须以他人为条件,却都不是自己身体的所有者,只是身体零部件暂时性的托管者。每个人对自己的身体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有权被认为归之于父母。因此,每个人都得为父母负责,看管自己的身体,保护好这堆人肉,否则,就是不孝。此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③《孝经·开宗明义章》。亦所谓“父母遗体宜宝之,箕裘五福寿为最”。④胡文焕:《类修要诀·孙真人卫生歌》。此中情形,也恰如星云大师所言:“人对于自己的生命其实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使用得越充分越好,生命的价值就越高。”⑤王鲁湘:《书卷山河》,前揭,第400页。不用说,星云大师是从更高、更邈远的维度,谈论身体的所有权,但思路或运思方式,却既不外于也不异于儒家。从可以想见的远古时期开始,作为运动系统的终端之物,作为人身上最靠近大地与尘埃的部位,足与趾就这样囚禁于鞋,被鞋——这脚的相契之物——所保护,体现了纲常网络之中的人对待器官(即暂时的托管物)的正确态度。赤脚行走被认作对双足的虐待,有史以来,它仅仅被革命话语所赞美。有那么一阵子,革命话语赞同赤脚的贫民(而不是平民)精神,称颂依附于衣、裤、鞋、帽、袜之上的补丁所焕发的道德光辉。⑥见敬文东《姐姐们都老了》,《书屋》2008年第12期。裸足的托钵苦行僧则被中国文化全方位排斥。因为裸足、苦行,都是对父母之产权的冒犯,至少是不珍惜,距离不孝恰在咫尺之遥。因此,最终是鞋代替双足在泥土上留下了痕迹,是为足印(footprint);也是鞋代替双足在光阴身上留下了看不见的印痕,是为足迹(trace)。在此,“足音”系列画作首先暗示的是:足印为实,足迹为虚;足印为本体,足迹为喻体。在“足音”系列画作中,足印以氤氲气化的氛围为形式(而非体态上的形似),被杨键以水墨为媒介剂固着于宣纸;足迹却只能浮现于面对足印的观者之脑海。那是观者对足印的全身心感觉造成的效果,也是身与心被画面(即“足印”)同时震荡所致——在一个难以计算的激灵间,或在一个无法估算或算计的心尖收缩中,观者将兼具氛围性与视觉性的足印,疾速转化为脑海中非视觉性的足迹,隐喻性的足迹,虚化的足迹。而时光,或时光的某个虚薄性的切片,则被完好地寄寓其间。传统水墨精神的修习者和欣赏者被告知:通过来自于全身心的感觉(而非单一性的视觉),氛围终归会化作并非虚幻的实有,宛若某个一闪而过的印象,虽然浮光掠影,却实实在在,仰仗着影子的重量和权威。氛围性的足印到底是在等待轻微的感慨,还是在悄悄酝酿感慨?杨键很清楚,无论等待还是酝酿,它都不可能蔑视光阴,只因为蔑视光阴者,必将被光阴所战胜。
能指性的足印经过全身心投入其间的感觉转换,终将成为所指性的足迹:它是画者或观者脑海中的一道闪电,既疾速、明亮,又细微而氤氲。在此,雅克·德里达(J.Derrida)难得一见的质朴观察值得一提(他的观察一般都深奥繁复):“肉体是时间化的运动。”①见夏可君《身体:从感发性、生命技术到元素性》,第2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对于这个可以被直观的精彩洞见,“足音”系列画作表达得既清楚、干脆,又率直而坚定,在抽象中,偶尔还会显现出貌似“形似”的那一面。足印是鞋子在迈动中或迈动后,馈赠或奉献给地表的轻微擦痕,稍纵即逝、间不容发,有如昌耀的咏诵:“所有道路都被一宿风声洒扫/天下好像不曾走动过脚踵。”②昌耀:《极地居民》,《昌耀诗文总集》,第483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足迹则仅仅是光阴打劫鞋子,但更有可能是鞋子挽留光阴造就的结果:它对光阴有轻轻地拉拽,羞涩中有些许大胆,大胆中有些许羞涩,但也仅仅是希望光阴能将步伐的行进速度损毁一点点。这令人难以忘怀的氛围,存在于水墨营构的氤氲气化之中;它以轻微的焦虑,存在于“足音”系列的每一双足印,宛若坐落于二郎神杨戬眉宇间的第三只眼,看得见无形的事物,尤其是事物的眼泪,还有事物头部散发的炊烟。
* * *
和梵高(Vincent van Gogh)绘制于画布的鞋子不同,也和海德格尔视域中与天、地、人、神紧密相关的梵高之鞋大不一样,杨键的水墨足印(它的所指形式是足迹)与天、地、人有染,与光阴有染,与现代社会独有的垃圾以及单子之人有染,却与神或一切超验之物无关,毕竟水墨所依附、所投靠的“中国文化的主流,是人间的性格,是现世的性格”。③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前揭,第1页。儒家一向主“敬”,宋以后的儒门据信尤其强调“敬”。虽然有证据表明,“敬”在远古时期,确实跟祭祀耳鬓厮磨,和巫术礼仪两相厮守、相敬如宾,却仍然不同于宗教性的虔诚或虔敬,④见李泽厚《己卯五说》,第53-54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因为即使是“在敬之中,我们的主体并没有投注到上帝那里去,我们所作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仿佛在敬的过程中,天命、天道愈往下贯,我们的主体愈得肯定”。⑤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征》,第20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4。“敬”只针对具体的人,比如父母;⑥比如《论语·为政》有言:“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而坚守此岸世界的中国古人,更乐于秉持“人能弘道”⑦《论语·卫灵公》。的修身立场,坚信“道不远人”,⑧《礼记·中庸》。甚至“道在屎溺间”,⑨《庄子·知北游》。与西方信众膜拜的上帝弘人之观念(亦即救赎),刚好方向相反。对于传统水墨精神,李泽厚特别注意到它的在世性格:“创作和欣赏山水画的,主要并不是出家的和尚或道士,而仍然是士大夫知识阶层……这些知识分子面对山水画,体会和感叹着自然的永恒、人生之若旅、天地之无垠、世事之无谓,而在重山叠水之间,辽旷平远之地,却也总有草堂半角,溪渡一张,使这审美领会仍然与人世相关。世事、家园、人生、天地在这里奇妙地组成对本体的诗意接近。”⑩李泽厚:《华夏美学》,前揭,第197页。因此,以横站为心性姿势的水墨精神在其极致处,甚至倾向于祛除通常意义上的人性,独留轻盈向上的灵性(灵性是人性的升级版或人性的精华部分,也是对人性持不信任态度后的产物),怎么可能给彼岸之神留下空间呢,也不可能为彼岸本身独辟容身之地。鉴于现代社会的紧迫性,以及它极端严格的“去魅”癖好,再加上单子之人孤苦、孤绝的处境,“足音”系列画作必然首先意味着无神论的时间、世俗性的时间,而非救赎性的时间——“足音”系列中的时间与弥赛亚无关。足迹(而非能指性的足印)对光阴的祈求、劝阻,甚至轻轻地拉拽,只在世俗的层面上进行;足印(而非所指性的足迹)固执而无所驻心地将自己“印”在泥土表面,也只可能发生在凡间尘世之中。和梵高留于画布的鞋子不同,杨键留于宣纸的足印只是器物的反光,不是器物的本相,甚至不是器物的留影或水墨定影,仅仅是器物呈氛围状态的印痕或踪迹——所指状态的足迹只有依靠观者对氛围的全身心感受,才能浮现于脑海,印现于心田。
梵高的鞋子首先不是作为氛围,而是作为近乎于写实的静物,出现在厚实,甚或不乏“粗野”特性的画布上,大体遵循的是光的明暗原则和透视原理。它不仅是静态的显现,而且比通常的静态还要多出一些静,以至于或沦落或升华为“静极”的境地:它是被静态展览的某种人生状态,类似于被囚禁在橱窗中的文物。在此,“静极”一词模仿了“北极”或“南极”的构词法,亦即静的极点,或极限点。由此,整个画面陷入了一种类似于宗教性的冥思,并在冥思中,将自身向世界敞开,但更应该说成让自己与世界彼此间相互涌现,相互交融。否则,海德格尔就不会认为梵高绘制的那双鞋当真能跟天、地、人、神扯上关系,或认为梵高的鞋子能“把大地本身挪入一个世界的敞开领域中,并使之保持于其中”,就更不用说能“让大地成为大地”(Das Werk lasst die Erde eine Erde sein)。①海德格尔:《林中路》,前揭,第30页。杨键化合中西两种绘画余产绘制的足印(而且,首先是能指性的足印),从表面上看,似乎也是静态的呈现,但细察之下,尤其是在观者全身心的感受中,正好是对静态所做的减法。它像奥卡姆的剃须刀(Occam’s Razor),在一步步削减静,直到将静削减到极限(而不是“静极”),直到无限接近于动——是将从画面上动起来的那种“动”,不是被观者的心“眼”有意阐释出来的“动”。被阐释豢养或宠幸的“动”,只是“动”的固定状态,或仅仅是被固定在某个瞬间的“动”——那终归是一种静态的“动”、冒牌的“动”,或近乎于山寨版本的不实之“动”。将从画面上动起来的“动”则是“动”的酝酿状态,是从静中出走,而且正好走到动与静的临界点上的“动”,也是蠢蠢欲“动”所表征的那种“动”,但依然不能算作“动”的亡灵状态,或休眠状态。它是“动”的日出,不是黄昏。“动”的日出更靠近摄氏零度以上,但又高不过摄氏零度以上多少体温的叹息,而不是冷眼蔑视——蔑视更倾向于同冰雪相厮守,相偎依。
* * *
和杨键基于氛围论立场对透视论律令发出的质疑恰相反对,侨居巴黎的华人艺术家熊秉明对他钟爱的水墨,有过轻微的指责,有过美中不足般的遗憾:“一个中国传统画家,隐迹于岩岫之间的,见到了伦勃朗的《屠后的牛》,如果也能有所感动,发生憬悟,他一定会有双重的惊异:一是西方画家能通过‘得其形’而达到‘得其神’;二是西方画家能在泥泞血污中看出画意来。”②熊秉明:《熊秉明美术随笔》,前揭,第89页。熊秉明实在没有必要替水墨感到遗憾,因为至今难解其情怀的水墨,自有运行和展现自身的逻辑,哪怕它在不少时刻确实拥有排异性能(但哪件事物又没有排异性能呢?)。即使没有透视术或解剖术撑腰,没有纯形式化的必然知识从旁压阵,③被通俗总结出来的勾3、股4、玄5,亦即所谓的勾股定理不是纯形式化的;X²+y²=Z²(X、y、Z分别代表勾、股、玄),亦即毕达哥拉斯定理才是真正的纯形式化。而这,刚好是中国古典思维所缺乏的。中国传统绘画并非没有写实能力,并非没有表现污秽事物或恶毒场景的热情。栩栩如生的春宫图,酣畅淋漓的秘戏场面,因极度快感而扭曲的面部,阎罗殿上被锯成两截的人体……逼真、生动、淫荡,构图精准而不失故意性的夸张,更不用说在故意性的夸张中,还不乏引人入胜的邪恶气息④见高罗佩(R.H.van Gulik)《秘戏图考》,杨权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这也许能够道说或坐实不少问题,起码可以让熊秉明的遗憾变得不那么强烈。但中国传统水墨精神确实更愿意相信横站带出来的蔑视和叹息,相信叹息和蔑视比直接从“泥泞血污”中看出“画意”更有力量,也比通过“得其形”而“得其神”更直接、更有效,并且更有可能拒癌细胞于画面之外——越过事物粗糙的表面,直接触及隐匿于事物内部的精华,往往更能获取直指人心的功效。蔑视不是物质层面(比如兵器),而是精神层面的胜利,叹息也是。仿佛来自天启或天意,中国水墨精神似乎从诞生伊始,就开了“天眼”、打通了“小周天”:它相信精神大于物质。“虽千万人,吾往矣”所指称的,不是肉体上能敌过千万人,而是精神上的强大又何止千万人相集结。寄居于水墨精神的蔑视尤其具有这种力量,以致于历代的水墨大师们纷纷相中了它。物质大于精神,或者精神受制于、被奴役于物质,是唯物主义的势利性主张。不用说,唯物主义是一种既典型,又彻底的欲望哲学,①见敬文东《写在学术边上》,第294-300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它对现代社会的特有之俗,对欲望在自我繁殖中生产匮乏特性,对多余物观念的出现……支持得格外卖劲,呐喊得唾沫横飞,最终,为抛弃型社会的出现和壮大,立下了汗马之功。蔑视与叹息构成的艺术氛围远在“吾往矣”之上:它是对“吾往矣”的超越;它越过物质之维,否弃了“其形”,否弃了“血污”中显现的“画意”,在西洋绘画崇奉的思路之外,找到了与自身的情怀,与自身的心性姿势或精神身位(即横站)相融贯的另一条道路。
W.本雅明说得好:“社会环境(milieu)与风景只向某些摄影家显露,因为只有他们才晓得如何捕捉社会环境和风景在人脸上的无名流露。”②本雅明:《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前揭,第39页。与此性质相近,又略有差异,中国古代的大师们之所以不大可能直接画足印,更不用说像杨键那样突出、夸张足印,首先是因为足印向任何一位古代画家“显露”的特征,它在不同画师那里的“无名流露”,差不多是一样的。瘸腿者、跛足者——但不包括令人沮丧的蹩脚者——的足印一只深一只浅,拖泥带水,看上去颇具个性,好像有点特别,细细想来,并无新奇之处,顶多值得同情,顶多有几分喜剧色彩。“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而乐欤!”③《庄子·知北游》。虽然清人赵翼有“地经三闾草亦香”的夸张性名句,但古人行走于山林、皋壤留下的足印,包括以香草、美人自喻者制造的同种痕迹,既谈不上“血污”或其他性质的不洁,也说不上带有麝香味的尊贵与庄严。在没有垃圾存在的帝制中国,在人人尚处于关系之中的农耕时代,足印仅仅是自然之物,或仅仅是“自然”之物“自然”而然留下的痕迹,有如空气和水,有如蛇或蚕在发育、成长过程中褪下的皮,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人注意它。这跟水墨精神的蔑视、叹息本能没有关系,跟内陷之力和暗中酝酿的凸起扯不上瓜葛。正常之物只有在遭遇不正常的时刻,才会被注意,心脏只有出问题时,才会成为聚焦的对象——这条定律,对野生于道路或山岳的足印照样管用。“足音”系列画作正是对这一规律的正面使用。
在马麟(《静听松风图》)、文徵明(《寒林钟馗》)、盛懋(《秋林高士图》)、赵孟頫(比如《自写小像》)……等古典名家笔下,足印是隐匿的,或者是倾向于隐匿的,没有任何打开感,也不存在打开自己的念头与愿望。足印消失于画面人物的走动之中,或被时光在时光自身倾向于流逝的某个瞬间所蒸发。足印的隐匿特性(即不在场的在场性),受妙到毫巅的中庸主义之教,正得之于它介乎高洁与不洁之间这个简单、明快的事实:不高洁,所以不值得颂扬,更不值得动用内陷之力与凹面;又并非不洁,所以不值得施以蔑视或叹息,因为那实在太夸张、太浪费,类似于对横站的抛弃与出卖,更是对叹息和蔑视的大材小用。足印以其隐匿特性为方式寄居于画面意味着:在尚未进入全球化的旧时中国,意欲高洁之人的行走是健康的,倾向于脱俗之人的步伐是饱满的,没被打扰或破坏,也不会有任何俗物、俗务能够打扰或破坏。足印被专门突出,像特写镜头一般被摘取,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事件,有一种于平静之中让人瞠目结舌的力量或功效,像一只悠闲踱步于院落的小母鸡,突然被一双大手双管齐下,卡住了脖子。所谓现代性,就是在一个猝不及防的突然间,出现了前所未有并且喜新厌旧的人或东西。他们撞中了光阴的腰身,伤到了光阴的肺腑,让它成为不明不白、不三不四的光阴,成为耷拉着脑袋的光阴,直到成为光阴中的犬儒主义者,要么愤世嫉俗,要么玩世不恭。④见邵燕君《中国当代青春文化中的犬儒主义》,《天涯》2015年第1期。
* * *
杨键的艺术心计掩藏得并不算深:“足音”系列画作中的足印是纯粹个人性的;每幅画面上的足印只有一对,似乎在有意呼应单子之人在现代社会上的真实境遇。画面上能指性的足印时而一前一后,时而相互平行、彼此对望,颇有“行行重行行”的韵味;时而摆出八字步的阵势,似乎在显示行走的艰难,思绪上的彷徨、徘徊与凝滞……总之,都与单子之人或mass的基本内涵相对仗。德勒兹或许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中获取了某种启示,他为呈系列性的现代绘画给予了准确的界定:“系列是共时性的。”①德勒兹:《感觉的逻辑》,前揭,第45页。“足音”系列画作以其创作上的实际行动,大体同意或坐实了德勒兹给出的界定:寄居于每幅画面的足印,看上去只“共时性”地属于某个具体的单子之人;但考虑到单子之人的mass特性,或单子之人总不免要沦陷于mass之彀,足印又几乎同时属于所有的现代人。这既合于“共时性”的本义,又像面具或脸谱,几乎人人都能佩戴;既大于得“形”、得“神”,又秉承传统水墨精神,或部分性地效忠于水墨精神,从而远离了“泥泞血污”,还奇迹般地拒绝了符号化。很不幸,以齐泽克之见,所谓“符号化”,“就是‘符号性谋杀’(Symbolic murder)”。②斯拉沃热·齐泽克:《斜目而视》,前揭,第39页。“死于”符号化,意味着被“谋杀”于毫无个性的千人一面,但更意味着消失于mass,或自动加入“无面目”的群众之列。
足印的隐匿性表明的是:它主动走向山水,走向镶嵌在山水周边的烟云,不存在任何凝滞感和酸涩感;它与山水、古典烟云相互交融,未曾有过须臾分离;它闲适、从容,更倾向于和光阴——尤其是光阴的自然特性——打成一片,不被光阴算计,也不曾有意挽留光阴。时间内在于足印,犹如盐之溶于水,算计和挽留都是多余的,一切情势都自然而然,不被打搅,不被纠缠。足印(暂时不忙说足迹)被单独摘取、被单独突出表明的是:在现代社会(比如当下中国),单子之人(即个人)连意欲高洁的念头都难以“成”活与“存”活;他与他寄居其间的环境是分离的,是相互排斥的,不说以对方为寇仇,起码是彼此不相待见,彼此视对方为自己肠胃中的苍蝇,正处于将被消化而来不及消化的当口。甚至在个人内部(尤其是在个人内部),也存在着类似于左手反对右手的情形。卡尔维诺真有先见之明:他早在《被分成两半的子爵》中,已经对此有过生动、辛辣、幽默的陈述。但歌德是不是更早呢?梅菲斯特和浮士德可不可以分别充任那位子爵的左右两半?
齐泽克以反讽的语气,调侃过现代社会中单子式的个人:“愿你生活在趣味横生的时代!”(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③斯拉沃热·齐泽克:《迎接动荡的时代》,《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3期。在齐泽克的老家斯洛文尼亚,“趣味横生的时代”只有在反讽的意义上才能成立。它真实、准确的意思,据齐泽克透露,刚好是糟糕透顶的年月。杨键化合中西两种绘画余产而被刻意摘取出来的足印意味着:在“趣味横生的时代”,在交通工具便捷、发达的现代社会,行走反倒更艰难,“动”起来更费力。似乎所有的“动”,看上去都是同一种模样,同一种造型,甚至拥有同一种发式,连“艰难”本身都未曾易容、变形,保持着不变的腰身与曲线。杨键对现代社会的主要特性多有思虑、多有体察,他想必很清楚:他炮制的足印还意味着行走是被迫的,就像某个演员被迫认领了某个不喜欢的角色,领取了原本不属于他,但最终仅属于他的道具。在此,“被迫”俨然是“正确”或“合理”的同义词,从相貌到血液,都未曾真的得到过改变和位移——这既是“趣味横生的时代”的魅力之所在,也是它的滑稽性之所在。
足印的非隐匿特性,亦即足印受到如此空前的器重,显然是不祥的:它代替鞋子及其主人漂泊于垃圾遍地、污染横行的现代社会。而鞋子的主人,或被鞋子保护之人,却没能如雅克·阿达利(Jacques Attali)确信地那样,“漂泊者在穿越迷宫般的沙漠时,发现他到哪里上帝就在哪里”。④雅克·阿达利:《智慧之路——论迷宫》,第41页,邱海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更没能为价值荒芜的当下中国,发现某种具有“增”魅或精神安慰功能的一神论——那种稀奇古怪的东西原本就不属于远古华夏,又何况什么也不信的当下中国呢。梵高的鞋子也许在道说人和大地之间的亲密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在海德格尔看来,不乏悲壮感或悲剧性;杨键炮制的足印则在较为浓郁的抒情氛围中,通过能指(足印)向所指(足迹)的感觉转换,道说个人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尴尬关系:个人不仅“被抛入”冰冷的世界,还被迫卷入垃圾遍地、单子之人饱受孤独浸润的现代社会。“被抛入”是被迫,“被迫卷入”当然是双倍的被迫,是加了着重号的被迫,值得大写或动用黑体字——这丧礼上的字型和字号;“冰冷”是寒冷,“遍地垃圾”当然是双倍的寒冷,尽管看上去它是由更喧嚷、更嘈杂的欲望之声捎带出来的。在现代社会,因为资本逻辑与“竞于力”的振幅更高,所以,欲望之声才会是热到极致的冷,是热自身的冷。在当下中国,冷是热的心脏,冷在驱动热自身的血液,或冷至少居住在热的心脏处,是热之心脏客栈的永久住户,却又算不得鸠占鹊巢——别扯,人家才是真正的主人呢。
杨键说,作为垃圾的前奏,作为垃圾最主要的幕后推手和前台总指挥,“百年现代化运动就是在各个领域的反自然,反诗情,反画意”,而他画画,“白色为哀悼,黑色为哀悼,为山水招魂的时代到了”。①作为招魂的阶段性成果,作为招魂之作,“足音”系列画作诞生于当下中国,应当被视作一个意味深长的艺术事件。
(未完待续)
①杨键:《冷山水》,前揭,第109-110页。
敬文东,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