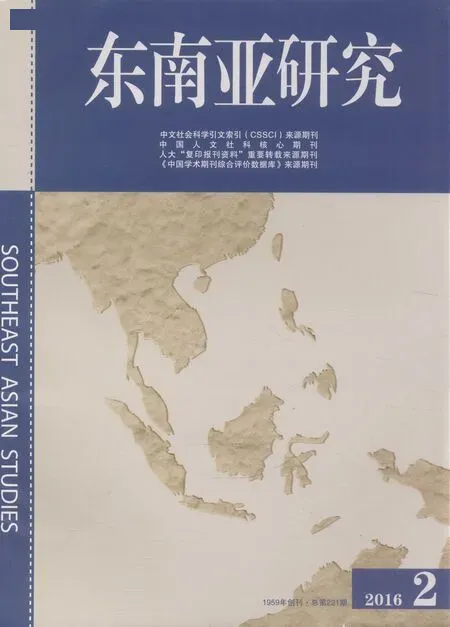诗巫的福州人:海外华人的模范
曹云华 程 荃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 广州 510630;暨南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 广州 510630)
诗巫的福州人:海外华人的模范
曹云华程荃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广州 510630;暨南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广州 510630)
[关键词]马来西亚;海外华人;福州人;华人文化;华文教育;族群关系
[摘要]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福州人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次文化群体。在马来西亚砂拉越州的诗巫市,活跃着一群福州人,他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代人,他们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长期以来,福州人与当地族群和睦相处,与本地族群一起,为诗巫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诗巫的福州人堪称海外华人社会的模范。
Abstract:In the overseas Chinese societies, the community of people from Fuzhou of China (Fuzhounese) is a very distinctive sub-cultural group. In Sibu, Sarawak State, Malaysia, a group of active Fuzhounese, having been living there for generations, take root, blossom and bear fruit. For a long time, Fuzhounese live in harmony with the local ethnic groups and mak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Sibu. Therefore, Fuzhounese in Sibu is praised as a model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诗巫是马来西亚砂拉越①“砂拉越”(Sarawak)在马来西亚华文中有多种写法,本文除文献和引用外,统一使用“砂拉越”——编者注。州拉让江中游的一个城市,位于拉让江和伊干江交汇点。诗巫是英文名称Sibou的音译,早在1863年布律克堡建成后就开始使用这个名称。最早在诗巫定居的是马兰诺人,早在19世纪中叶,他们就在甘榜南甲一带定居,1870年之后,诗巫的名称就经常出现于政府的《砂劳越公报》等官方文献中,是砂拉越重要的商贸中心,其地位仅次于首府古晋。因为诗巫是由福州人开发和兴旺起来的新兴城市,故又被人们称为“新福州”②这里说的福州人是指祖籍来自福建福州地区的华人。在中国清代,福州府下辖十县,包括闽县、侯官、长乐、福清、连江、罗源、古田、屏南、闽清、永福,故称福州10 邑。来自这些地区的海外华人,因为祖籍的缘故,他们被称为“福州人”。近年来,笔者曾经三赴诗巫调研考察,接触了各个阶层的诗巫福州人,深深为他们一代又一代不断发扬光大的“福州人精神”所感动,故写下此文,以资纪念。。据2010年马来西亚全国人口调查,全马有福州人341,342人,砂拉越州福州人有209,901人,诗巫有福州人89,964人。在诗巫市,福州人是华人人口比重最高的方言群,也是最有经济实力的方言群。
一黄乃裳与“新福州”
在福州人到来之前,诗巫还只是一个尚未开发的偏僻乡村,“那时诗巫只不过是一个村落式的小圩集,除政府办公处及官舍数间外,只有木造店屋20多间,大部分是闽南人经营土著生意,附近及上下游沿江各地,尚是荆榛满目,蛮烟荒野。仅有一些伊班族之长屋,疏疏落落零星地散布其间。”[1]诗巫的奠基人黄乃裳先生为寻找一块海外谋生之地,曾经从拉让江的出海口溯江而上,来到诗巫考察。他对当时的诗巫有如下描述:“嗣北行过拉让江口,见江流汪洋,揣其发源必甚长,乃沿江入,见两岸丛林蔚茂,土著不多,左右不见有山,知其原野广邈。及二百里,曰诗巫埠,英人设官其间,有漳、泉、潮、嘉等商人20余家,与土著之猎人形相交易。余沿江觅地,择其平原四百里之中,于诗巫附近之上下,流连十有三天,察其草木,尝其水土,知地质膏沃,无虎豹狼毒蛇害人之物。”[2]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看出,在福州人到来之前,诗巫还是一块蛮荒之地,仅有少数当地土著居住,一些华人在这里做生意。福州人大量的到来,迅速改变了这个地方的面貌,一个新兴城市在拉让江中游崛起。
福州人黄乃裳是诗巫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出生于福建闽清六都湖峰,曾经参加乡试中举人,参加过著名的公车上书,支持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产生到海外开创新天地的想法,曾经先后到新加坡、马来半岛、荷属东印度群岛(苏门答腊等地)考察,欲寻找一块理想的移民之地。未果,1900年4月间,又到英属婆罗州(即北加里曼丹)拉让江一带考察13天,对诗巫一带甚为满意,确定在这里开拓发展,遂与拉者(英国殖民统治者查尔斯·布律克,下同)商订开发事宜,签署了移民合同。合同共有17项,规定由黄乃裳负责在福州招收农工,英殖民政府负责建设基础设施,为中国来的农民提供路费,提供土地,20年内免税,由拉者指定一位华人担任“港主”,负责管理日常事务等。
根据上述协议,从1901年至1902年,先后分三批一共1118名福州人,在黄乃裳等的带领下来到诗巫,从事大规模的垦荒工作。第一批72名福州人于1901年1月21日抵达,第二批535名福州人于1901年3月16日抵达,第三批511名福州人于1902年6月7日抵达。黄乃裳被英国殖民当局任命为“港主”,负责福州人社区内部所有的事务。后来,福州人将黄乃裳亲自带领的第二批福州人到达诗巫的时间——3月16日,定为“新福州垦场纪念日”。
1901年,广东也有一批农民(803人)在邓恭叔的带领下来到诗巫南兰区垦荒种地,主要是种植胡椒,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912年,在福州人的影响下,101名福建兴化人在陈秉中、方家明两位教士的带领下,来到诗巫伊干江右岸的新珠山建立垦场,开荒种地,取得了成功。
这就是史料上关于华人较大规模的有组织移民到诗巫的记载。
二福州人对诗巫的贡献
福州人最初到诗巫主要是垦荒种植水稻,他们遇到了前所未见的困难,包括他们不熟悉的热带自然环境、疾病等。第二批移民中的林文聪牧师(卫理教会)在其日记中这样写道:“早期的生活非常艰苦,大片的森林需要砍伐,对于开伐丛林成为耕地一窍不通的垦民是件苦差事。”“许多随黄乃裳来的移民都不是农民,而且他本身对耕作也所知无几,更糟的是,中国的农耕法在诗巫低洼的土地完全使用不上。”“垦民播下的谷种都长得不好,农作物如每担5元的番薯,最后跌至每担3毛钱。土地是新开垦的,虫蛇鸟兽经常侵害种植物,垦民中的许多都染上疟疾而病亡。”“由于环境恶劣,在1901年总人数为1118人的福州垦民到1905年的四年之后,约有200人或病故,或迁移到古晋、新加坡、槟城、实兆远。”[3]
在经历了初期的失利之后,福州人向广东移民学习,开始改种胡椒、树胶等热带作物,取得了成功,并且巩固了基础。据当地殖民政府的年度报告书记载,“在1910年,福州人的地区已经打下了良好巩固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在1908年,他们已经种植树胶。这是福州垦民命运的转折点。最终,他们成为诗巫最为显赫和富裕的方言群,直到今天。”[4]
诗巫的经济发展进程主要有如下几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1800—1910年),以森林土产为主的贸易。一些早期的华人,主要是闽南人、潮州人移民以盐、布料、铁及其他奢侈品和土著交换各种森林产品,包括犀牛角、树籽、猴胆石等。
第二阶段(1910—1963年),以种植胡椒和树胶为主的经济活动。这类经济活动造就了一批富裕的福州人和土著,也可以说,正是这一段时间的经济活动,为后来诗巫的经济起飞和工业化积累了资金,换一句话说,这个阶段是诗巫向城市化和现代化进军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
第三阶段(1964—2000年),以木材加工与贸易为主的经济活动。在诗巫,少量的木材加工与贸易早在1870年就开始了,当时主要是由广东人将木材运往香港,在1917年出现了最早的锯木厂。但是,那个时候,这个行业并不吸引人,且行业风险较高。直到1964年之后,木材加工与贸易行业才开始起飞。这个行业的发展奠定了诗巫乃至整个砂拉越的经济基础,为后来诗巫和砂拉越的经济多元化提供了大量的资本。
第四阶段(2000年之后至今),诗巫经济多元化的阶段。在马来西亚2020宏愿的政策下,诗巫经济走向多元化和现代化,迅速发展成为新兴城市,旅游业、制造业、食品加工、造船等产业迅速兴起。
诗巫上述四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历程,都与福州人息息相关,正是福州人引领了诗巫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带领诗巫走向现代化,尤其是在第三阶段,福州人成为木材加工与贸易行业的领头羊。“当福州人发觉木材业的潜能时,他们不顾一切危险,全身投入这一行业。历尽艰苦、咬紧牙关。福州人很快就成了这一行业执牛耳的族群。虽然是门危险的行业,但福州人决心发展这一行业,同时眼光长远,知道这将改变他们一生和诗巫的将来。”[5]事实上,正是福州人在诗巫的经济活动,推动了诗巫的经济起飞,使诗巫迅速崛起成为一个新兴的、充满朝气与活力的现代都市,换一句话说,诗巫经济起飞与现代化的每一个步伐,都留下了福州人的足迹与血汗。
诗巫的福州人口也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增加,20世纪20年代初,种植胡椒和树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移民到诗巫及砂拉越其他地区的福州人大幅度增加,成为诗巫及至整个砂拉越州最主要的华人社群。“在砂州内福州人在华族中被公认为是最具有动力(精悍的)的一属。他们不单在商业与政治上的影响力迅速扩张,在过去40年中其在华族中的人口比例也由1947年的29%提高到1980年的33%。这段时间内只有极少数的外来华族移民。福州人的人口占全砂拉越的9%,是目前各华族籍贯中占最多者。”[6]据诗巫福州会馆的统计,在诗巫,福州人从20世纪初开始便成为当地华人中最主要的群体。1947年,诗巫的福州人共22,971人,其中在市区的有3068人,到1970年诗巫的福州人增至42,997人,其中在市区的有23,214人。到2011年,增加到89,964人,比1970年翻了一番多。
福州人不仅在人口上成为当地人口中主要的族群,而且在职业与行业上也处于领导地位,“到了1968年及1970年时,福州籍人士已在下列的行业中执着牛耳:银行与金融公司,进出口生意,批发商行,旅馆、酒吧与夜总会,印务与出版商,面包西果店等。甚至森林工业急速扩张之前,福州人即在森林业、伐木业、木材与树藤的制造业、家具制造业及建筑材料供应方面占多数。”[7]
福州人在诗巫的影响及其贡献从街道的命名也可窥见一斑,诗巫有19条以华人先辈命名的街道,其中福州人占了12条,它们分别是:陈立广路、黄鼎福路、罗寿珍路、林文聪路、刘钦侯路、庄仁穆路、许家栋路、黄乃裳路、黄景和路、保由路、林子明路、刘家洙路。其中黄乃裳、黄景和、刘家洙与林文聪四人为最早到诗巫的三批移民中的第二批抵埠者。在以福州人命名的街道中又以后来的黄乃裳街最为著名。1958年,为纪念福州人移民领袖黄乃裳对诗巫开发的贡献,诗巫市议会将新建的一条街道命名为黄乃裳街,黄乃裳街是衔接兰彬街与甘榜艾蒲路的一条横路,全长约200 米,已经成为全诗巫市最繁忙的主要街道之一。
三诗巫福州人为什么能够成功?
福州人,从最早的一千多移民,到今天发展成遍布诗巫市乃至整个砂拉越州每一个角落,人数多达数十万人的最重要的一个华人族群,为诗巫和砂拉越的开拓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得到了各民族的公认。福州人成功的奥秘在哪里?
1.福州人精神
由于最早到诗巫垦荒的福州人是在基督教会的帮助下取得移民和定居的资格与便利,他们在砂拉越的垦荒和定居也得到了基督教会的帮助,因此,砂拉越州的福州人也较早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在他们的笔下,福州人是华人中最有朝气、最有战斗力的一个族群。Craig Lockard认为:“即使以华人的标准,福州人也是克勤和有志气的垦民,其他华人对这批富有进取心的新移民的反感心态,持续至今。”[8]
诗巫的福州人具有哪些特质,或者说具有哪些特别的精神?福州人精神的塑造,最早应该归功于当时的移民领袖黄乃裳、富雅各等人,正是这一批先贤,为福州人精神注入了许多值得后人歌颂和继承的正能量,“黄乃裳先生竭力为同胞寻找新天地,辟蛮荒为乐土,使成千上万的后裔受惠。他没有为自己留下一寸土地,此大公无私、一心一意为自己族群谋求福利的崇高精神,备受后人尊崇与传颂。”福州人精神包括:“勇于冒险、敢于牺牲、顽强的斗志、刻苦耐劳、勤奋节约、慎终追远、爱好和平、乡梓情浓、热切为子孙后代追求更美好的世界的拓荒精神。”[9]
组织性和集体意识,是福州人在诗巫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而言,海外华人比较散漫,缺少组织和集体意识,而在这方面,诗巫的福州人显得与众不同,这首先要归因于他们移民的特殊方式,他们是有组织性的集体移民,正是这个特色奠定了他们成功的基础。福州人有组织性的集体移民,这在中国人向海外迁徙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后来也出现了广东人、福建兴化人向砂拉越的有组织性的集体移民,在沙巴州,也出现了广东客家人(主要是惠州、龙川等地的客家人)在巴色教会的组织下的移民。组织性和集体意识也使得福州人在商业上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优于华人其他族群并且取得成功。正是这种组织性和集体意识,使福州人在商业活动中更愿意抱团,发挥合作的优势。Michael Leigh在对各个华人族群所经营的公司进行比较分析后得出结论说:“从1986年的5000多个商行结构的分析中,显示福州人较其他籍贯人士善于利用合伙与公司结构,独资经营在潮州人与客家人中各占83%,福建人占80%,而广东人占79%。虽然福州人的独资经商者占67%,可是,福州人倾向于合伙及公司的方式,而不只单靠个别的经济能力来经商,这资料有趣地显示了,虽然福州人向来以竞争闻名,但却愿联合其同籍贯人士的资源,来达成其个别的经济利益。”[10]
Michael Leigh高度评价福州人的拼搏精神,他认为,福州人的成功应该归因于如下四个要素 :
第一,福州人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族群。在海外,早期的华人社群都相对比较封闭,他们以方言为纽带,自我封闭在各个方言群体中,各个方言群体很少往来,而福州人则冲破了方言的隔阂,善于与其他方言群打交道。“这不单是因为福州人能够比其他籍贯人士更有效地超越其行业的专长,个别的福州人也较客家人更能够超越阶级的界限,在客家人的地区,福建人与潮州人的商人往往控制较大的商行与企业,籍贯与同乡会的约束,使客家人不能超越一个固定的商业水平,相反的福州人在其主要的地区却不受此种限制,不需要太久的时间,福州人都能在他们的地区占有社会各阶层的地位。”
第二,早期福州人有组织性的集体移民的领导人都是受基督教精神影响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没有自己特殊的个人私利。“福州殖民是通过卫理公会的保护与提倡下来砂劳越,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他们的领袖(最先是黄乃裳,后来是富雅各)作为殖民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中间人,并没有从中获取本身的利益。最先来到第一省(古晋)的华族商人却几乎把他们所引进的劳工视为彼等的专利品。这些商人(从政府手上)获得大片的土地,给他们的苦力(劳工)来耕作,并且取得鸦片、米酒和赌博饷码的专利。这些特惠在第三省(诗巫)的福州垦殖民合约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土地是直接分配给新来的垦殖民,而不是给那些将他们引进来作劳工的人士。在合约中,殖民者并不给予那些签约者鸦片与赌博的特权。这两项活动很显然地会把社群的生产力浪费掉,而使劳力的成果为富有的商人所剥夺,那种清教徒式的卫理公会的理想,是不容许这种‘肉体的罪恶’,因而大大地造益了这批新来的移民。直到今天,那些贫困的移民能够积蓄所需要的资金来改善他们的命运。”
第三,福州人比较擅长沟通政商关系,通过影响政府决策,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商业环境。Michael Leigh观察得出结论说,福州人通过参政,在政府中赢得影响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福州社群中的主要分子活跃于政坛,并在新成立的州政府内赢得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地位。”“靠近政权使社群的领袖获得显著的利益。”
第四,勤奋与竞争。与华人社会中的其他族群相比,福州人更善于竞争和更敢于竞争。“福州人在其他的本地华族中是有名的勤力者,且具锋芒的竞争力。不单应用在福州人的社群内,也利用在对外的其他籍贯的社群中,他们精打细算要从彼等的努力中换取最大的利润,不论是20年代的树胶种植业和70年代的山地木材业都是基于这同一理由。”
Michael Leigh指出,福州人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70年代的木材业中胜出,能够比华族其他社群有更加优越的表现,并且可以说是几乎垄断了这一行业,除了勤奋与敢于竞争之外,最关键的因素,还是福州人与执政当局有良好的关系,能够从执政当局手上获得更多政策上的倾斜。“到了60年代末期,福州人除了其他原已操纵的行业外,又在森林砍伐、木材加工与产品的市场上,在全州各地迅速扩展其活动,福州人的精力与专家技术终于成为本州迅速开采森林的动力,福州商人成为了几乎与木材工业不可分开的核心,他们拥有,甚至制造该工业各阶层的机会——从执照到承包,机械供应,及木材业工人,土著的参与只是在该工业的最高层与最低层中。有良好的政治关系者,往往获得森林砍伐的执照,而许多达雅克人则受聘于繁重的砍伐工作。”[11]
2.教会的作用
基督教教会对福州人在诗巫的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诗巫福州人与基督教,尤其是与卫理公会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卫理公会不仅是诗巫福州垦场的推动者,也是主导者,同时还是诗巫福州人精神动力的提供者。“是什么因素使百年前福州人不远千里,自中国来到南洋,在蛮荒之地参与垦荒之举?是什么理由使重土为安的农民愿意背井离乡,成为福建省首批集体向海外移民的群体,跨越南中国海迈向未知之地,开辟新天地?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卫理教会,是垦场拓荒的主导动力。诗巫福州垦场的开发和进展与卫理教会有不能切割的关系。”[12]
基督教教会对诗巫福州垦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提供物质方面的支持;二是提供教化与精神支柱;三是作为组织者起到了团结与凝聚的作用。在这三种作用中,尤其是教化与精神的作用最大,它从如下几个方面奠定了诗巫福州人成功的基础:
第一,兴办学校,为诗巫福州人造就并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卫理公会是基督教在诗巫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教派,该地最早的一家英华学校就是由卫理公会于1903年在新珠山创办,同时讲授英文和汉语,首批学生达40多人。到1948年拉让江流域之初级中学12间,小学100多间,学生10,000多人,教职员400余名,其中由卫理公会直接或间接创办的中小学共50间,教员240多人,学生7300多人。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卫理公会已经成为当时诗巫乃至整个拉让江流域办学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天主教会在诗巫的教育发展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创办的学校都是当地的名校,如圣心中学、圣伊丽沙白中学、公教中学、圣心英小、圣心华小、圣玛丽小学、圣立达小学、华兴小学等。这些教会学校为诗巫垦场的建设和发展培育了各方面的人才,有力地促进了诗巫福州人的进步与素质的提升。
第二,防微杜渐,保持海外华人社会的纯洁性。
一般而言,在海外华人社会,黄赌毒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然而,在诗巫的福州人社区,这些曾经在海外华人社会中普遍流行的各种腐化、丑恶现象却几乎看不到,这是什么原因?无他,是信仰的力量。信仰为诗巫福州人种下了三颗重要的种子,第一颗是向善和博爱的种子,小小的诗巫,却创办这么多的学校,诗巫的福州人,以诗巫为基地,向砂拉越各地、向沙巴、向世界其他地方扩散,涌现出许多人才,包括企业家、银行家、科学家、教授等;第二颗是精神生活的种子,因为有信仰,明确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明确了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不过分追求物质和财富,把精神生活放到重要的位置;第三颗是敬畏的种子,受过信仰洗礼的诗巫福州人,永远都有一种敬畏之心,那就是头顶三尺有神明,人的一辈子只能做好事,不能做坏事,否则就会受到神明的惩罚。在海外华人社会,包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西部各州华人社会长期被人们诟病的一些恶习,包括卖淫、嫖娼、赌博、吸毒、黑社会等等,在诗巫福州人群体中较少见到,甚至绝迹,这不能不说是信仰的力量。黄碧瑶博士查阅了当时英国殖民统治当局出版的《砂劳越宪报》,引述相关报道说:1901—1902年的古晋,华人的赌博活动快速增加,而在诗巫的新福州移民却没有一个参与赌博,“拉让江边的新福州垦场给这个地区带来这么多新的期望,而且他们和其他华人移民不一样,他们更加清醒,有技能,工作勤奋。这些垦民不吸鸦片,也不赌博,这真是完全不一样的社区。”黄碧瑶指出,“宗教力量防止移民腐化,因宗教的力量,使得大部分的群众情绪稳定,团结一致。因此,基督教利他主义的精神给垦场带来这么多优势。有了这一个拓荒计划,垦民能够很快有经济独立的能力,他们不感染鸦片、赌博等恶习,垦场不受秘密社会控制,领导人也都尽心尽力带领垦场走上正确的道路。”[13]正是信仰的力量,支撑了诗巫一代又一代福州人,为他们提供了精神支柱,为他们指明了人生的方向,卫理公会会长陈泽崇牧师指出:“卫理公会之信仰,透过黄乃裳传道,富雅各教士和其他牧师们的传道,忠诚之会友们之生命,所发挥出来的能力,助长了新福州垦场之拓展和繁荣。先贤先圣所奠定之基业,后人一代又一代,继往开来又加以不断创新,发扬光大,而有了百年后今日之辉煌。”[14]
谈到基督教会的作用,不能不提到黄乃裳和富雅各两人。
早期的移民领导人黄乃裳本人就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黄乃裳(1849—1924年),又名九美,字绂丞,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湖峰乡。黄乃裳于1866年(18岁)接触了美国卫理教会传教士并且受洗加入教会,成为闽清县第一批受洗的基督徒。他前后招募的三批赴诗巫的1118名移民,其中三分之二为卫理教会教徒。一些研究者认为,黄乃裳带领福州移民远赴诗巫垦荒,完全是受一种利他主义思想的支配,是希望为福州乡亲寻找到一块理想的世外桃源,造福乡梓,而他这种利他主义思想正是来源于基督教的影响。“基督的信仰塑造他的利他思维,成为他后来一生处事为人的方针。”[15]“黄乃裳先生竭力为同胞寻找新天地,辟蛮荒为乐土,使成千上万的后裔受惠。他没有为自己留下一寸土地,此大公无私、一心一意为自己族群谋求福利的崇高精神,备受后人尊崇与传颂。”[16]
1904年,黄乃裳因各种原因回国,他的继任者富雅各*富雅各(1872—1935年),美国人,1872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法兰克林郡格林乡,1891年于美国师范学院毕业,1891—1900年任教于家乡,1896年为美国卫理公会年议会会员,1900年受美国卫理公会派遣到马来西亚槟城英华学院当教员,1903年被美国卫理公会委派为诗巫新珠山福州垦荒移民卫理教会牧师并开设卫理英华学校,1904年被砂拉越殖民统治当局封为砂拉越福州人首领并给予参政权,为福州人对政府表达下情的代表,1935年2月15日去世。牧师接替黄的工作,成为诗巫福州人的新领袖。黄孟礼比较客观地评价这两位福州人领袖的作用,“黄乃裳在诗巫三年(1901年3月至1904年6月),因为管理、货款、健康等因素回到中国,他本身未看到垦场的成果,不过其后来者,卫理公会委派的美籍传教士富雅各牧师继承其职责,被拉者(英国殖民政府的代表)委任为砂劳越福州人的领袖,终于把福州人带上成功之路。黄乃裳有带领、拓荒的功劳,富雅各教士的设教建校、引进技术工艺,提供了发扬光大的机会。”[17]诗巫福州人的新领袖富雅各既是诗巫福州人的精神领袖,同时也是垦荒与经济建设的组织者和杰出领导者,其对诗巫福州人的贡献是巨大的,得到了诗巫福州人的高度评价,尊其为诗巫福州垦场“发展之父”。为了纪念富雅各,诗巫福州人在他们最初的落脚点新珠山专门建立了一座富雅各纪念公园,公园里树立了一座巨大的纪念碑石,碑文这样写道:“富公雅各为卫理公会垦荒砂劳越诗巫第一任布道使,是砂州卫理公会奠基和发展的功臣,并受砂劳越政府拉者册封为砂劳越福州人之首领,他为天国效忠,为人民服务,他建立教会,兴办教育,关怀社会,开创工商,是诗巫福州垦场发展之父。他生前为拉让江流域建立了41间教堂,开设了40间学校,他为诗巫创下了许多第一:他为诗巫迈开文明,奠定了基础;他购进第一批橡胶苗;他带来第一艘汽船;他设置了第一架碾米机;他创办了第一家女校;他装设了第一家发电机;他设立了第一家农业学校;他引进第一架脚踏车;他设置第一架制冰机;他使用第一架锯木圆锯;他采用第一架无线电报机。”
黄乃裳和富雅各两人对诗巫福州人的贡献各有千秋,诗巫福州人尊前者为拓荒之父,后者是发展之父。“没有黄乃裳就没有新福州,没有新福州也就没有富雅各。黄乃裳完成了历史的使命,成功把福州人移往诗巫,富雅各继往开来,承先启后,把新福州垦场发扬光大。富雅各在诗巫32年时间里,把诗巫推上了文明、现代化及繁荣的列车。富雅各是一位全面的宣教士,不仅传福音也注重垦民物质的发展。他认为人类的物质生活应该与精神生活互相紧密联系。他的宣教工作包括了人生的各个方面,如宗教、政治、医药、民生、城市、道路建设、机械、轮船等。”[18]
3.特殊的移民群体
诗巫的福州人移民目的一开始就很明确,那就是在海外找一个能够永久安身立命的福地,因此,从移民的领导人到一般移民一开始就拥有落地生根的“永居心态”。黄乃裳的报告中说,1901年的三批共1118名福州移民中有130个家庭一起移民[19]。在富雅各牧师给教区的报告中也提到,第二批500多名移民中,有20位妇女[20]。富雅各在1926年8月的一份报告中说,经历了23年之后 ,福州人移民有1万多人,有1000名孩童上学,按照一个家庭有一个小孩上学的比例来估算,当时福州人起码有1000个以上的家庭[21]。这种情形与其他地区的华人移民大相径庭,当时绝大多数华人移民,都是“做客心态”,也就是单身一人,飘洋过海,出国谋生,最终还是要“叶落归根”的。诗巫福州人这种以定居和建立新的理想家园为目的的“永居心态”,可以克服一般海外华人社会经常出现的那些社会弊端,有利于移民社区的建设与发展,有利于处理与当地民族的关系,有利于移民在新的移居地的可持续发展。正如研究黄乃裳的学者黄碧瑶博士所说:“这种新福州家庭式的永久移民对整个垦场的发展确实有重大的影响。妇女的出现使劳工们注重平时饮食卫生,食物营养,有助于调解枯燥无味的劳苦,安慰离乡背井的心情,以及促进社会和教育机构的发展,如学校、教会、社团,这些组织都和家庭观念息息相关。”一般而言,绝大多数海外华人社会,都经历了从“叶落归根”到“落地生根”这两个阶段的漫长曲折历程,而诗巫的福州人却没有这种过程,他们的移民一开始就与家庭和孩子在一起,以在海外建立新家园为目的,这也是诗巫的福州人社会没有一般华人社会普遍存在的那些陈规陋习,能够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
结语
综上所述,诗巫福州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诗巫福州人居住集中。在诗巫,华人不是少数民族,而是主要民族。其实,砂拉越州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可以说没有一个民族的人口从数量上占绝对优势,据马来西亚2010年的人口调查,砂拉越的总人口为2,399,839人,主要族群有达雅人、华人、马来人等。其中华人有560,150人,占全州总人口的23.3%,与全马的华人比重差不多。在诗巫市,全市人口约20万,华人约占70%,单是福州人就有8万多人,几乎占了全诗巫人口约一半。“超逾20万的人口,包含了多元的原住民种族,如伊邦人、马兰诺人、马来人和高地的原住民。他们与方言众多的华人和睦共处。”[22]
第二,诗巫福州人更加顽强地坚守自己的文化,坚持使用福州方言。在诗巫,福州人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处于优势地位,福州话当然也就是华语中最重要的方言,甚至可以说是诗巫本地的商业语言和社交语言。诗巫的福州人在坚持自己的方言方面也是非常执着的,笔者访谈过许多福州人家庭,他们都表示,在家中,一般都会以福州话与其他家庭成员交谈。在诗巫,其他方言群的人,如客家人、潮州人、广东人,也都懂一点福州话,也能够使用福州话进行交谈,当然没有正宗的福州人那么流利。“这里主要的华人方言群体是福州、福建(闽南)、广东、客家、兴化、潮州,还有少数的印度人、欧亚混血籍人士等。大多数人都以华语交谈,但英语和马来西亚语也可畅通无阻。这里主要的方言是福州话和闽南话。虽然大部分人士广东话、客家话、兴化话、潮州话不甚流利,不过仍然能明白其意。”[23]
第三,诗巫福州人非常重视教育。海外华人把华文教育看作是本民族的根。在诗巫,华文学校和华文教育一直受到重视。诗巫华人重视教育,除了海外华人的传统使然之外,更多地还应该归因于卫理教会对教育的重视。早在1903年,诗巫福州人移民才2年,卫理公会便开办了一间学校,学生人数18人。到1918年,诗巫社区的华人达到了5000多人,有9间学校,学生人数达3302。到1935年,社区华人人口约10000人,学校多达40家,学生人数达到2500人。这些学校多为华文和英文并重。到1917年,诗巫已经拥有5间新式华文小学,包括:诗巫民德学校、诗巫光华学校、诗巫光楠学校、诗巫光安学校、诗巫中兴学校。目前,只有10多万华人的诗巫市,却有3家华文独立中学,即诗巫开智中学、诗巫光民中学和黄乃裳中学,其中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为黄乃裳中学。
第四,诗巫福州人保留了较多华人特性。与西马地区华人相比,砂拉越州诗巫的福州人保留了较多的华人特性,这是为什么?诗巫的福州朋友告诉笔者:(1)福州人到砂拉越诗巫等地定居的时间比较短;(2)福州人移民到砂拉越州诗巫的方式与西马华人有很大的不同;(3)砂拉越的福州人与中国福建家乡的联系比较密切,纵使是在20世纪50-70年代,中国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时代,砂拉越的福州人也经常回家乡看看;(4)更为重要的是,在砂拉越州诗巫及其他省,华人并不是少数民族,相反,华人是一个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占有优势地位的民族。
第五,福州人与当地民族关系融洽。诗巫及砂拉越州其他地区的华人与当地主要民族达雅族的关系相处得比较好,起码比西马的族群关系要好得多。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者林青青在一篇研究考察砂拉越华人与当地民族关系的历史的文章中这样写道:“砂拉越融洽和谐的族群关系向来为人所津津乐道,2014年大马首相署部长丹斯里就曾呼吁西马半岛人民向沙巴和砂拉越的人民学习宗教容忍及种族和谐。”[24]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记者也认为,与西马相比 ,东马两州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比较融洽与和睦,“容忍是东马的多元民族与宗教的社会能和平共处的方式,他们没有抱持‘自以为是’的态度。在东马,人民的日常生活,已跨越种族及宗教的界限和藩篱,真正的和谐已成为为一种日常文化,他们可接受不同的文化,一户家庭信仰不同的宗教,或异族通婚,都不是问题。”[25]
【注释】
[1] (马来西亚)邓万秋等:《诗巫福州公会106周年纪念历史回顾》,诗巫福州公会编辑出版《诗巫福州公会106周年纪念特刊》,2007年第二版,第17页。
[2] (马来西亚)黄乃裳:《七十自叙》,转引自黄孟礼著《福州人—拓荒路》,诗巫福州公会出版,2007年第二版,第82页。
[3][4][5] 转引自(马来西亚)潘德才撰《诗巫:塑造中的城市》,砂劳越诗巫民众会堂文化遗产委员会出版(书中没有标明出版日期),第46-47页,第59页,第60页。
[6][7][8] (马来西亚)蔡增聪主编《砂劳越华人研究译文集》,砂劳越华族文化协会出版,2003年,第104页,第112页,第42-43页。
[9] 诗巫福州公会编辑出版《马来西亚砂劳越诗巫福州垦场100周年纪念特刊(1901—2001年)》,2001年,第251-252页。
[10][11] (马来西亚)蔡增聪主编《砂劳越华人研究译文集》,第113-114页,第114-115页。
[12][18] (马来西亚)黄孟礼:《福州垦场拓荒背后的动力》,载诗巫福州公会编辑出版《马来西亚砂劳越诗巫福州垦场100周年纪念特刊(1901—2001年)》,2001年。
[13] (马来西亚)诗巫福州公会编辑出版《马来西亚砂劳越诗巫福州垦场110周年纪念特刊(1901—2011年)》,2011年,第236页。
[14] (马来西亚)陈泽崇:《宗教事业与垦场的关系》,载诗巫福州公会编辑出版《马来西亚砂劳越诗巫福州垦场100周年纪念特刊(1901—2001年)》,2001年,第318页。
[15][17] (马来西亚)黄孟礼:《黄乃裳设立的婆罗洲卫理公会》,载诗巫福州公会编辑出版《马来西亚砂劳越诗巫福州垦场110周年纪念特刊(1901—2011年)》,2011年,第212页。
[16] 诗巫福州公会编辑出版《马来西亚砂劳越诗巫福州垦场100周年纪念特刊(1901—2001年)》,2001年,第249页。
[19] (马来西亚)林柳青:《福州垦场:拓荒与利他精神》,载诗巫福州公会编辑出版《马来西亚砂劳越诗巫福州垦场110周年纪念特刊(1901—2011年)》,2011年,第237页。
[20] (马来西亚)黄孟礼编《婆罗洲的美以美》(第三辑),砂劳越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文字事业部出版,2001年,第28页。
[21] (马来西亚)黄孟礼编《婆罗洲的美以美》(第二辑),砂劳越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文字事业部出版,2001年,第85页。
[22][23] (马来西亚)潘德才:《诗巫:塑造中的城市》,砂劳越诗巫民众会堂就市华遗产委员会出版(没有标明出版时间,估计应该是在2000年前后),第16页,第16页。
[24] (马来西亚)林青青:《杆秤与巴冷的锒铛回响——浅谈砂劳越华人与达雅人的族群关系进程》,《婆罗洲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7月18日,第97页。
[25] 《尊重、包容、扶持:砂劳越各族同工共餐》,《星洲日报》2014年9月16日,转引自(马来西亚)林青青:《杆秤与巴冷的锒铛回响——浅谈砂劳越华人与达雅人的族群关系进程》,《婆罗洲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7月18日,第97页。
【责任编辑:邓仕超】
Fuzhounese in Sibu: Model of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Cao Yunhua & Cheng Quan
(Academy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Postdoctoral Research Station on Political Scienc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Keywords:Malaysia; Overseas Chinese; Fuzhounese;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Education; Ethnic Relations
[收稿日期]2016-03-23
[作者简介]曹云华,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程荃,暨南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暨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海外排华、反华的演变及其应对”(13JJD810003)。
[中图分类号]D634.3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16)02-007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