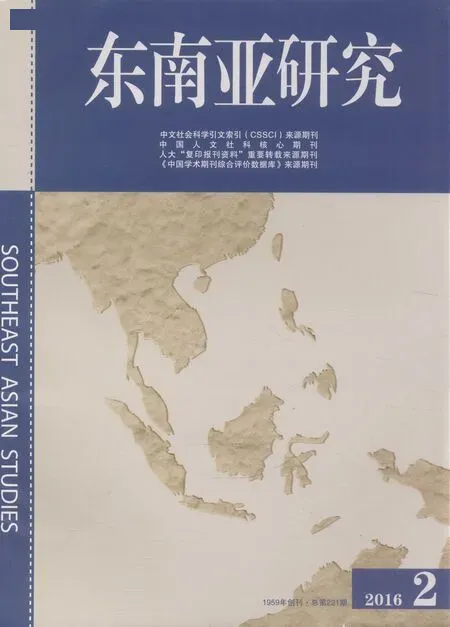“一带一路”倒逼中国外交决策机制改革
薛 力 肖欢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 北京 100024)
“一带一路”倒逼中国外交决策机制改革
薛力肖欢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北京 100024)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国外交决策;机制改革
[摘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促使中国外交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这要求中国外交决策机制进行相应的改革。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不足包括三个方面:信息的收集与分析、政策建议的筛选与综合、最终决策。其中政策建议的筛选与综合环节的不足尤为明显。为此,中国有必要从观念、制度、人才使用三个方面进行改革:走出“弱国无外交”认知误区,从整体与长远角度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强化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对外事务上的统摄功能,一名政治局常委任常务副主席兼任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负责对外事务,外交部长由一名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副总理兼任;建立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类制度,强化外交官的离岗培训,大量增加“外部人”,即把有经验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吸收到外交决策部门中来。
Abstract:China’s foreign policy agenda will change significantly from “keeping a low profile” to “proactively and enterprisingly striving for achievements” as it implements the OBOR strategy. It requires the foreign policy apparatus to make a response accordingly. However, the current policy-making mechanism has three flaws that include the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the selection and summary of policy suggestions, and the final decision-making, of which the second process is particularly obvious. Hence, China needs to reform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bureaucratic systems and talent selection of the foreign policy bureaucracy. Firstly, it should change the view of “no preferential diplomacy for weak country” and form wide-ranging political vision and long-term perspective in the relationship with surrounding countries. Secondly,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the NSC’s control over external affairs and appoint a standing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as deputy NSC chairman and deputy leader of the Central Foreign Affairs Leading Group. Then the official would be in charge of foreign affairs. In addition, the post of foreign minister should be held by a vice premier who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Politburo. Thirdly, it needs to separate political appointees and civil servants, to strengthen off-the-job training and to appoint many experienced specialists and scholars to its decision-making agency.
2015年3月在北京召开“两会”,引发了一个以前没有的新现象:对“一带一路”的讨论从31个省级两会会场汇聚到北京,并引发全球关注。在3月8日的记者会上,外交部长王毅称“一带一路”为2015年中国外交的重点。2002年历史学家章百家先生在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论证中国发挥世界性影响的方式是:“改变自己,影响世界”[1]。从那以后,中国的经济实力又有了明显的增长。 2008年西方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陷入衰退且迄今没有恢复元气。反观中国,在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后,经济继续高速增长,GDP在2010年超越日本,2014年已经是日本的两倍,美国的70%。可见,13年来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台阶。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将因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而更加凸显。原因在于,这一战略的实施不仅意味着大笔的对内对外投资,还意味着中国改变了数千年来的天下治理模式,尝试以和平方式掀起一波又一波的“中国涟漪”。因此,这一战略2015年逐步进入实施阶段后,以“韬光养晦”为特色的外交势必要大规模转型,以满足“有所作为”乃至“奋发有为”的现实需求。那么,中国现行的外交决策机制如何因应这一系列“中国涟漪”?
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涉外事务将出现诸多变化,不仅涉及的部门增加,涉及的事务增多,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主动谋划的事务与领域将明显扩展。而基于“外交决策通常是基于不完全信息”这一特点,相应未来外交决策过程中出现失误的可能性也会随之上升。
完全消除外交决策失误是不可能的,但减少失误是现实的。不过,要减少失误,首先需要改进涉外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强化政策建议的筛选与综合,提升相关决策的质量。这种改进洵非易事。
收集与分析涉外信息主要是研究人员、外交官与专业情报人员的工作,对所搜集的涉外信息进行初步的判断、筛选与综合是高级外交官与涉外事务中高级决策层的事情,而外交决策通常取决于最高决策层,尤其是重大外交决策。一般而言,涉外部门官员与附属机构研究人员的长处是掌握丰富的信息。但他们的不足之处在于:看问题容易受部门利益牵制;为日常工作所累,难以对相关问题深入研究,不容易对宏观战略问题进行思考。专业政策研究机构的长处是可以相对超越部门利益束缚;能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与战略思考;可以借鉴一些基础研究成果,例如,学术界的新理论、新方法以及一些新的基础数据。不足之处则是:对于一些只有政府部门才掌握的信息了解不够,研究与分析主要依据公开信息与个人调研获得的信息。当然,特定的委托研究项目例外。
与之相较,美国的外交事务研究与决策机制相对成熟,其外交研究与决策机制是:不同政府部门利用自己的特长进行相关信息的搜集与分析(有些是委托专业人员进行),提出政策建议;非政府的专业研究机构,特别是主要思想库,也依据自己的特长进行信息的搜集与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上述两类机构的建议经过外交决策层高级助手的初步筛选或者整合后,形成数量有限的几套方案,并列明其主要优缺点,有时候还会列出排序,供总统决策时参考。为了强化政策建议的筛选与整合功能,美国大量吸收专业研究人员出任外交决策部门的中高级职务,形成独特的“旋转门”现象,并被许多国家所借鉴。
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存在的问题
毫无疑问,中国外交决策机制有自己的特点与长处,但这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畴。本文关注的是中国外交决策机制中的不足,这种不足,从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到政策建议的筛选与综合,再到决策的做出,各个环节均有。中国与美国外交决策方面差距最大的很可能是政策建议的筛选与综合环节,其次是政策决定环节。在信息的收集与分析环节,中美之间的主要差距在于研究人员的素质,而非不同部门的信息共享。
在信息搜集与分析阶段,中国的情况是,包括军方在内的各个涉外部门及其研究机构,通常垄断自己领域的相关信息(这在美国也是痼疾),他们所给出的政策建议,通常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有时候则是基于本部门主要领导的意志(这方面中国比较明显)。外交部系统与中联部系统内,真正有水平、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专业研究人员数量不足,一些既有的人才没有得到充分使用。
中联部曾经拥有比较强大的专业研究力量。后来中联部的有些机构被划归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单位。目前,中联部的研究人员分布在研究室和各地区业务局。由于人员有限且要承担大量的党际联络等日常任务,对调研工作的关注度、资源投入和调研力量的储备相对较弱。下属的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有一些兼职研究人员,而专业研究人员数量很少,研究领域比较泛化,外事接待、办会与对外联络的非研究性任务较重。该中心2015年4月代表中联部成为“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的牵头与协调单位后,这一状况依然没有明显改观。当中联部的外交对象主要是数量有限的社会主义国家时,研究力量不足的副作用尚不明显,在大规模开展政党外交并逐步涉及公共外交、民间外交后,“研究力量难以支撑大量外交行为”的现象已经日益凸显。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或许与传统的惯性有关,中联部整体上显得相对封闭,与专业研究机构互动不多、不深,有一些把专家学者请进来的动作,但数量不多。在走出去听取意见与政策建议上更显不足。这方面即使与外交部比,也存在差距。一些外交(特别是对朝鲜外交)的效果不够理想,即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外交部虽保留着一些研究机构,但系统内的研究力量与研究成果难以满足现实需要。政策规划司、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外交学院是外交部下属的三个主要研究机构。其中从研究室改制而来的政策规划司理论上拥有的职能是:研究分析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中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拟订外交工作领域政策规划;起草和报送重要外事文稿;开展外交政策宣示;协调调研工作;开展涉及新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有关工作。然而,基于“外交无小事”的传统,加上人员配备有限、主要精力用于应对交办工作等原因,政策规划司在研究方面起到的作用比较有限,总体上扮演的是地区司、专业司之外 “剩余领域研究部”的角色,并且在研究深度、持续性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外交学院的研究力量相对强一些,两者都经常参与外交部委派的各类调研。在过去十多年里,外交学院除了传统的政策研究外,在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论研究上异军突起,成为国内这方面的一个重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侧重于政策问题研究与提供内部报告,但研究力量只是相当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一个大型研究所,许多资深研究人员系从外交官转换而来。这种人员结构的好处是了解具体的外交实践,不足之处则是欠缺写作学术文章所需要的专门训练,所写出的学术文章理论性不够强,方法论意识欠缺,对政策问题的分析不够深入,所提政策建议缺乏足够的理论与方法支撑。总体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人员数量与综合影响力似乎稍弱于“老对手”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一些问题不是这些机构所能克服的。与外交部的隶属关系也限制了外交学院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提出超越本部门利益的综合性外交决策建议,尤其是当这种建议可能有损外交部利益时。国外解决隶属关系带来的不足的方法是:委托外部机构进行研究。
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是,最近这些年外交部系统以外的专业研究机构在外交政策分析中的作用在明显提升,许多高校成立偏向政策研究的智库并发表研究报告,也接受一些委托项目。但是,大部分时候表现为少数著名学者以个人身份参与或者接受政策咨询。学者成名后从事研究工作的时间明显减少,其建言献策通常是基于经验积累,而较少基于专项研究成果。委托项目也开始出现,经济与金融领域此类项目还不少。然而,这类委托项目至少存在两个不足:一是要求提交报告的时间太仓促,导致学者难以进行深入思考与分析,有时候给出的答案属于“临时应答”,这在政治领域比较明显;二是委托单位的倾向性太明显,有些时候不过是借学术机构与学者的嘴为其主张背书,这在经济领域与地方政府委托项目中比较明显。
在决策层次也存在一些问题。最高层决策时,不是面对数量有限、特点分明、按照优先顺序排列的备选方案,而是:或者意识到某个问题重要,从上到下交代进行研究分析;或者面对数量众多但不够全面的政策建议;或者一时被某些部门与人物说服,采取有偏颇的政策。其后果是,委托研究的结果失之片面,众多的建议难以取舍,一时被说服做出的决策未能体现国家的整体利益,外交政策整体上缺乏连贯性。
而造成上述后果的关键原因其实也显而易见,就是缺乏一个对各种外交政策建议进行判断、筛选与综合的部门(以下简称“政策筛选机构”)。不容否认的是,一些政策的出台经过了对各种政策建议的判断、筛选与综合的过程,亚丁湾巡航就是多部门协商后形成建议并被采纳,实际运作也很成功。许多重大文件的出台,更是集思广益的结果。但从制度有效性的角度看,外交政策建议筛选机构的缺位影响长远。
理论上,中央外办应该扮演这个角色,但由于级别不够,实际上只起到执行机构的功能。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层级够高,代表性够广泛,但并非常设机构,也不易实现上述筛选与综合功能。中央政策研究室有时候扮演了这种角色,但全面扮演这种角色则并非制度设计的原意。毕竟,其主业可能是“受托进行政策设计与相关理论研究”,而非专门从事政策建议选择与优化。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原先被期待能顶上这个角色,但实际运行以来,学界的一般看法是,出现了过于侧重国内事务的倾向,而且程度在加剧。
至于外交部长,由于地位太低,其政策建议在决策中的分量不足,更难以扮演主要筛选者的角色。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国际关系学界许多学者大概都有这样的经历,向外交部领导提出某个建议后,这些领导的反应通常是:将向中央报告。个中原因在于,在一个党领导一切的决策系统中,负责外事的国务委员虽然是中央政府(国务院)分管外交事务的最高领导,但在钱其琛之后都不是政治局成员(现有25人),也不是负责外事的副总理(现在为4人)。在礼宾顺序方面,位于人大副委员长之后,“两高”(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与政协副主席之前。可见,在中国的重大问题决策程序中,国务委员的地位排在三十位以外,外交部长更不用提。就外交决策而言,分管外交的国务委员上面至少还包括政治局7个常委、与外事工作相关的政治局委员(至少5人),外交部长上面则有至少30人。因此,外交部的部长副部长听到某些政策建议后,头脑里想的是排在自己之上的好几打人,“向上报告”也就成了很自然的反应。
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还没有机制化,部门负责人的政治地位、行政级别、与最高领导人互动的频度等等,对于决策有明显影响。因而,实际运作中外交部从“决策部门”被“降格”为“主要执行部门”实属必然。中联部等外事机构也存在类似问题。中国在过去几年里采取的一些客观效果欠佳的外交行为,甚至发生一些外交部不知道的重大行动,也与此有重大关系。
中国正致力于构建地区与全球性功能机制,这需要有关国家的合作。和平时期国家间合作的实现依赖于大量的利益交换与互相妥协,这属于外交部(以及中联部与商务部)擅长的范畴。然而,由于外交部长说话的分量不足,难以协调出可供交换的利益与做出妥协的限度,进而形成政策建议供最高决策者参考。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在提供地区与全球公共产品方面进展不够快的一大原因。
外交决策机制改进的逻辑
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系中,“党指挥枪”无疑比“政府指挥枪”更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中国整体上也属于“文官治军”国家,但政策制定是个动态博弈过程。一般而言,强力部门解决问题时倾向于用硬实力说话,希望分出胜负;而商务部、外交部等倾向于用谈判、互相妥协的办法处理问题,以图实现共赢(至少是避免共输)。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内政外交中的重大问题通常需要政治局讨论通过。就外交决策而言,负责外交的国务委员的意见或许可以抵得上同样身兼国务委员的公安部长的意见,但整体分量上显然难以匹敌两个军委副主席、一个政法委书记等若干个政治局委员。其结果必然是,主张强硬不退让的外交决策者常常占上风。而且,一些强力部门的行动无需知会外交部。这部分解释了中国在过去若干年里为什么会采取一些效果不佳的强硬外交举措。外交部门空背“妥协部”、“投降部”的虚名而已。事实上,外交部即使想妥协也没有能力做到。
值得重视的是,作为一个体量巨大的崛起中国家,中国不但没有外敌入侵的忧虑,而且正处于力量快速向外扩展的过程中。周边中小国家对此疑虑与害怕是正常的,除非他们判断,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扩展不会伤害自己或对自己有利。如果不能成为同盟国的话,这就需要彼此建立信任。然而,这并不容易,对于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来说尤为困难。这种情况下,新一届中国政府基于自己的“不结盟外交”原则,提出与东盟等周边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这无疑有助于他们化解疑虑、增进信任。但要达到预期效果,中国所需要做的不是高调与强硬,而是身段柔软,展示可信与不可怕,并通过一些制度性安排,让自己的行为变得可预期,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自己的行为。有实力却没有制度约束者,难免让人不放心。“通过制度进行统治”是二战后美国治理世界的一大经验。中国不妨有样学样,先从功能领域着手,从周边做起。
人通常具有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因此,有时候需要换位思考。国家亦然。想象一下,中国周边出现一个人口100亿、国土面积是中国10倍的国家(以下简称“百亿国”),并且在快速崛起。中国对于百亿国,恐怕也有疑虑与害怕心理,非常希望百亿国对中国很友好,并通过一些制度性安排约束其行为。如果百亿国在中国附近海域画出一条“十一段线”,但拒绝告诉中国这条线的性质,声称不能只靠国际法来解决争端,要考虑到其数千年来对线内岛礁与水域的使用历史,强力主张除了国际法外,还要考虑历史性权利,并要求以一对一的谈判来解决争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周边国家抱团、探讨国际法解决途径、寻求实力超过“百亿国”的全球第一强国的安全支持,大概都是很自然的行为,而且不会认为自己是在联合第一强国遏制(contain)百亿国。
中国的自我定位,正在从“东亚国家”变为“欧亚大陆国家”与“亚洲中心国家”,这是一种地域观上的回归。回归历史上具有明显等级制的华夷秩序(或曰天朝礼治体系[2],西方学者则多数称之为朝贡体系),既不可能,也不可取。然而,中国成为当代国际体系的领导国之一,并非没有希望。虽然许多方面并没有实现,但“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已经成为当代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且,由于核武器的出现、全球和平意识的普及与内化,像历史上的崛起国那样通过战争实现崛起已经不可能,和平崛起是现实可行途径。而且,中国古代治理天下时所形成的天朝礼治体系,虽然有不平等等缺点,但毕竟是存在了几千年的一种“国际秩序”,肯定有其合理的一面,譬如,以礼服人、不追求大规模领土扩张。朝贡贸易中实行“薄来厚往”的原则,也属于“以礼服人”。把天下分为五服*“五服”为:甸服、侯服、宾服(又作“绥服”)、要服、荒服,其中要服与荒服居住的已经是蛮夷戎狄,即“蛮夷要服,戎狄荒服”,流放罪人也住在这两个服。参见《尚书·禹贡》、《国语·周语》、《荀子·正论篇》等篇。,承认前三服为文明开化的臣民居住地。把宾服之外的两服,看作化外之地,住的是蛮夷戎狄与流放罪人。对蛮夷戎狄的原则是“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也就是说,通过提高自己的道德文化水准等来增加对遥远邦国、偏远地区居民的吸引,让他们仰慕中华而接受教化,他们受教化之后即可纳入前三服之列。而为了防范戎狄入侵,还采取了修建长城等防护措施。这些都折射出,中国作为农耕文化为主导的帝国,整体上并不追求领土扩展。这显然不同于游牧文化,也不同于欧洲那些在商业文化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帝国。
因此,中国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实施外交决策机制改革,必须做到“自身优秀传统与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综合”,而不能仅仅顾及一个方面。中国的外交决策体制改革,需要体现在观念更新、制度改建,以及人才的培养、使用与调整等三个方面。
观念方面,要做的就是:首先,走出“弱国无外交”认知误区,意识到二战之后,国家的死亡率已经很低,弱国、小国的生存权已经有了基本的国际保障,国家的治理议题凸显,国家治理不善,人民将受苦,政府也会被更替,但这与“亡国”无关。第二,摆脱“受害者心态”,进一步确立自信,意识到“落后挨打”或许是历史常态,但已经成为过去,现在的中国已非吴下阿蒙,没有国家敢欺负中国。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已经初显中国在大国关系上的自信,但这只是一方面。提出建立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意味着中国意识到自己作为快速发展的亚洲中心国家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以及实现这种责任的原则。“带动”周边国家共同发展固然是好事,但首先要让周边国家愿意“被带动”。因而,取得周边国家的理解成为必要条件,如能获得其信任则更好。
这要求中国有大局观,谋大势而非局部利益,从整体与长远角度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特别是与中小国家之间的关系。其次是换位思考,理解周边国家的担忧所在,以及其希望从中国获得怎样的支持与帮助。一些人担心周边中小国家“狮子大开口”,这种可能性不大,即使他们提出,中国也有理由与能力拒绝。另外,政府有必要疏导国内的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不必动辄上纲上线。还应该时时警惕一些人在批判美国不能平等对待中小国家的同时,自身滋生出大国沙文主义意识,表现为:周边小国家没什么重要性,中国可以按照自己的国家利益行事;周边中小国家对中国即使不满意也无可奈何,最后也不得不接受中国的做法并承认结果。持有这种立场者通常注重相对获益,认为国家都是在为自己争取利益,因此,有意无意地强调在一切问题上都要做到本国利益最大化,哪怕是在与中小国家交往时。如在南海问题上,认为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强调寸土必争,维稳应该服务于维权,而没有在中国与东盟整体关系的框架下考虑问题,不考虑中国作为地区“带头大哥”应该如何行事才能服人,中国在下“全球大棋局”的时候如何处理“周边小棋局”。一句话,陷入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俗套。这种求小利失大端的做法显然不是在服务中国的整体长远利益。好在这种主张还没有成为政策研究界的主流认识。研究界主流与决策层的认知很可能是:“在地区与全球大局中看南海问题”;与时俱进处理南海问题;开放的地区主义比较适合中国。
有必要提及的是:与美国的双边军事同盟体系、TPP等排他性的制度相比,中国推动的亚太自贸区、亚信、亚投行等都属于非封闭机制,体现了中国治理天下理念的开放与包容。
制度层面,平衡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内与对外两方面的功能,强化对外方面的统摄功能。总书记兼任国安委主席,偏重统摄对内方面;由另外一名常委任常务副主席兼任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统摄对外事务。外交部长由一名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副总理兼任。外交部长作为政务官,未必要出身于外交官。在常务副主席的支持下,也可以对重大外交决策进行筛选、综合,并列出优先顺序。如是,最高领导人决策的质量与速度,以及中国外交政策的连贯性都将大大提高,中国也就有能力为地区乃至全球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从而成为地区秩序与全球功能制度的主导者。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世界大国的外交部长出身于职业外交官者乃少数,大部分情况下是由政治家担任,有时候是由企业家乃至学者担任。政治家型的外交部长更能起到“外交政策建议主要筛选者”的作用。事务官的长处是专业与精细,不足之处则是欠缺宏观视野、战略考量与综合判断。这是普遍现象,中国没有必要羞于承认。
考察美国的外交决策体系,国务卿在内阁中的地位,如果与中国的执政党系统类比,大约相当于排名第三位的政治局常委。如果与中国的政府系统类比,则大约相当于常务副总理。总统的外交决策,固然会倾听副总统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意见,有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非常强势(如基辛格与希拉里),有些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与总统关系特别密切(如两个赖斯),但国务卿历史上是首席内阁部长(secretary of state)*从功能角度看,美国建国后在外交上奉行孤立主义,外交事务并不多,国务卿的主要职责是国内事务,如参与制定并保管国内的法律法令,为国内行政部门的人事任命做公证,保管国会的各类书籍和文件等。随着美国实力的提升与对外事务的增加,国务卿的主要职责才转向对外事务,相应地,1781—1789期间的外交部从1790年开始改称国务院(the department of state)。但国务卿依然是内阁第一部长与总统首席外事顾问,负责协调除部分军事行动外的政府海外事务。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后国务卿是首席委员。现在的国务卿依然保留一些对内功能,如保管与使用国玺,一些联邦公告文件由总统和国务卿联署,甚至总统辞职也要向国务卿提交辞呈。,现在则是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行政官员。而且,国务卿在对外事务上可能比总统更为专业。因此,其意见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通常比副总统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更重要。
外交部与中联部强化自身与下属机构的研究力量也应提上议事日程,并赋予这些研究机构更大的独立性。毕竟,如果政府机构的自身研究力量不足、不强,就不容易与机构外的专家和机构进行高质量的交流互动,这方面中联部改进的空间大于外交部。
人才的使用上,外交部已经有某些问题或领域的若干专家型官员,部委领导中也出现了来自其他专业部委的人士。这说明外交部也意识到现有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不足并着手改进,但力度还远远不够。“打破外交部现有的相对封闭体系,大幅度增加非职业外交官在部局级人员中的比重”应该成为外交部贯彻落实“一带一路”战略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加快推进干部来源与构成的多元化。
从长远看,解决之道是建立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类制度,但这需要与其他部委统筹协调。中近期内,至少可以启动并实施以下两项措施:强化外交官的离岗培训、延长培训期限,以提升其专业知识与技能*2016年3月1日成立的中国外交培训学院,依托外交学院,将开展全国外交外事人员、国际组织后备人员培训以及相关国际交流合作。这显示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强化外交官培训的重要性。此前的外交官在职培训并没有规范化,专业性、时间性都有所欠缺,仅仅是不系统地进行一些学习培训,如自学。而在中央党校、外交部党校学习的外交官,也有机会聆听来自国际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知名学者的讲课。。更容易见效的是大量增加“外部人”,如增加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中非外交官的比例(刚刚换届的新一届委员有29位,其中只有6位非外交官),并考虑强化咨委会功能,甚至考虑将之升格为国安会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把有经验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吸收到外交决策部门中。这些人可以先出任司局级职务,并在一段时间后提升到更高级的岗位。
这方面,科技部、环保部已开先例,在教育部、卫计委及其前身卫生部更是常事。就国际关系领域而言,王沪宁教授的经历不应成为绝响,而应在一段时期过渡后,成为新常态。
当然,外交部现有人员的出路问题也需要考虑。在中高级岗位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大力推行人员构成多元化,将严重损害现有人员的职业预期。解决的办法是:多部门同时打破藩篱推进人员构成多元化,把具有丰富外交实践经验的人员有序分流到其他部委去从事与外事相关的工作(最近的一个好例子是:刘建超从外交部部长助理转任国家预防腐败局专职副局长);外交官在现有的“职业化”上增加“专业化”,依据年功序列增加收入,避免收入完全与职务挂钩;转行到学校、科研机构、大中型企业、咨询机构等部门;推荐到各类国际组织工作。
总结
“一带一路”战略是新一届中国政府为推进“中国梦”的实现而制定的对外关系顶层设计,旨在推动中国从“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发展为“综合性世界大国”。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的海外利益将大幅度增加,外交事务的广度与深度都将前所未有地扩展。中国外交的目的,将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转为服务于“中国梦”的实现,为此,中国外交势必从“韬光养晦”转向“奋发有为”。中国现有的外交决策机制已经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亟需进行大幅度的改革。
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信息的收集与分析、政策建议的筛选与综合、决策的做出等三个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二条: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策建议筛选与综合机构。外交决策机制的改革应该包括观念、制度与人才三个方面。
观念层面,努力走出“弱国无外交”的认知误区,摆脱“受害者心态”,进一步确立自信,意识到中国的志向是当综合性世界大国,为此需要经略好周边,构建战略依托带;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时,有整体与长远眼光,理解周边中小国家的安全关切,减少他们对中国的疑虑与恐惧,增加中国对他们的吸引力,使得他们愿意与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合作,而不仅仅在经济上获取好处。
制度层面,纠正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偏向于对内事务的倾向,强化其对外方面的统摄功能;由总书记兼任国安委主席,偏重统摄对内方面,由另外一名政治局常委任常务副主席,并兼任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负责对外事务;提升外交部长的级别,由一名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副总理兼任。
人才使用层面,建立政务官与事务官分类制度是长远之计。中短期内,可以采取的措施有:强化外交官的离岗培训制度,并延长现有的培训期限,以提升其专业知识与技能;大量增加“外部人”,把有经验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吸收到外交决策部门中来,形成中国的“旋转门”制度。
【注释】
[1] 章百家:《改变自己 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2] 黄枝连:《亚洲的华夏秩序: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形态论》(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责任编辑:邓仕超】
How Should China’s Foreign Policy Apparatus Respond to OBOR Strategy?
Xue Li & Xiao Huanrong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Keywords:OBOR; China’ Foreign Policy Making; Mechanism Reform
[收稿日期]2016-03-23
[作者简介]薛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副研究员;肖欢容,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16)02-0057-07
* 本文主要内容2015年3月9日发表于FT中文网,原文约5000字。作者感谢以下人士在本文写作与改写过程中给予的指点与帮助:王逸舟教授、王存刚教授、林民旺博士、左希迎博士、赵明昊博士、韩宏才先生、徐晏卓博士。当然,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