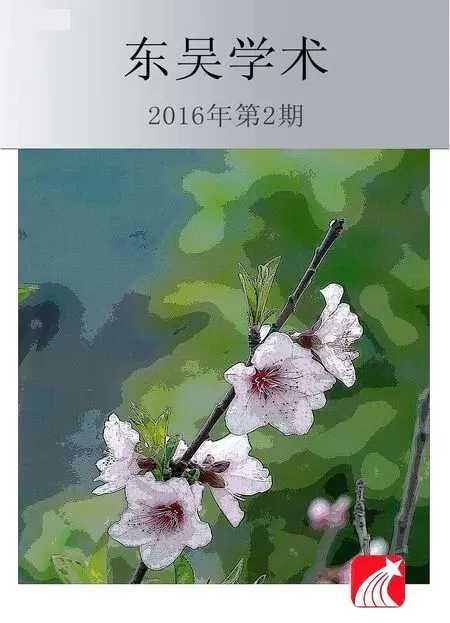形而上学的意义与命运①本文第一部分曾以《“形而上学”在西方主要哲学流派中的用法之贯通》为题在“形而上学:东方与西方”国际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2013年12月)上宣读。整篇文章系作者于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作访问学者时(2015年)最终整理完成。
戴 劲
形而上学的意义与命运①本文第一部分曾以《“形而上学”在西方主要哲学流派中的用法之贯通》为题在“形而上学:东方与西方”国际研讨会(华东师范大学,2013年12月)上宣读。整篇文章系作者于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作访问学者时(2015年)最终整理完成。
戴劲
本文第一部分力图贯通“形而上学”在西方主要哲学流派中的多重用法。首先,考察了形而上学如何由亚里士多德-康德的用法过渡到黑格尔以及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用法;其次,揭示出在尼采、海德格尔的批判中,形而上学与西方-欧洲的历史及其命运联系在一起。第二部分则从形而上学的自身怪圈来反观形而上学的本性,并思考形而上学的命运。
形而上学;辩证法;虚无主义;意义
从哲学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出现以来,几乎每位哲学家都批判以往的形而上学,但又都建立起、至少指望建立起自己的形而上学,这是一个怪圈。特别是自黑格尔之后更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将自己哲学革命的对立面称为“形而上学”,并通过对它的批判建立起自己的哲学。这样,“形而上学”就有了各式各样的用法,具有代表性的如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用法。本文首先拟将“形而上学”在这些哲学流派中用法的流变贯通起来。同时我想,我们应该作的是:从形而上学的自身怪圈来反观形而上学的本性,并思考形而上学的命运。
一、形而上学的不同意义
一提到“形而上学”,我们可能主要是从两种意义上来理解的:1、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与物理学相对;2、黑格尔意义上的:与辩证法相对。问题是:这两种用法之间是什么关系?第二种用法是如何由第一种用法过渡而来?
先对这两种用法做一说明:1、第一种用法开始没有主题意义,只有分类意义。安德罗尼科(Andronikos)在整理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时候将这类作品放在物理学作品的后面,因此被称为“metaphysics”。不过,后来的研究者认识到亚里士多德的这些作品具有一定主题意义,它是对物理世界的终极原因的研究。这门学问经过中世纪的发展日臻成熟。到了沃尔夫(Wolff)那里,传统形而上学被分为四部分:本体论、理性神学、理性心理学、理性宇宙论。2、第二种是黑格尔的用法。黑格尔那个时代是传统形而上学出现普遍危机的时代。黑格尔认为是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哲学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因而将“形而上学”指认为一种片面、孤立、静止的思维方式加以批判,并提出全面、联系、发展的思维方式,即“辩证法”。
康德那个时代,传统形而上学就已经深陷危机,实证科学以一种轻蔑的眼光看待它。康德用赫卡柏①Hecuba,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王后,特洛伊沦陷后被俘。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版序。的悲惨下场比喻这种“形而上学危机”。康德区分了两种形而上学:作为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和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他指出,纯粹理性有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倾向——超越现象去认识本体,由此产生先验幻相。在此,康德明确了纯粹理性的超验运用与内在运用:后者是正当的,就是说纯粹理论理性对知性的经验运用起范导作用;前者则是理性的僭越和滥用,是败坏形而上学名声的根源。在康德那里,形而上学被分为两种,并且这两种仅仅是对立关系。但黑格尔不是这样看待形而上学危机的,他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形而上学作为辩证论的一面和作为科学的一面。在他看来,理性有这种自然倾向不是坏事,通过自我否定获得自我超越乃是理性本身的特点,理性是一种通过自我中介而自我建立的运动、即在否定中建立自身的运动,先验幻相不过是自我建立的中介。问题在于如果停留在这种中介上,以片面、孤立、静止的眼光看待它,以为它是绝对的、永恒的,那就成了形而上学。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先验幻相的问题出在以知性的方式来认识理性,而知性的认识方式是非此即彼的、静态的、固定的,换句话说,本体不是不能认识,而是不能以知性的方式来认识。因此,不仅要将本体理解为实体,而且要理解为主体。从主体的角度来认识本体就是从辩证法的角度来认识本体,将本体理解为在现象(他在)中的自身反思。但以往那些形而上学或者人们对于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考都不错,它们由于成为了最高科学的一个环节而获得了自己特定的地位和价值。
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区分科学命题和形而上学命题为有意义的命题和无意义的命题,区分的标准为该命题表达的事实是否具有经验证实的可能性(能够证实或者证伪)。就此而论,逻辑实证主义只是抓住了康德讲的形而上学作为自然倾向这一个方面,进而将一切形而上学指认为不科学的。并且,逻辑实证主义与康德对“不科学”的理解不同: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不科学”是指不具有经验证实的可能性;而对康德来说,“不科学”指的是理性的非正当运用。其实,黑格尔同样不主张这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是科学。在批判先验幻相方面,黑格尔与康德倒是一致的:不能将理性自我认识的中介固定化。
可以说,黑格尔与逻辑实证主义者都是康德的学生。但黑格尔才算是好学生,他以批判的方式继承了康德。而逻辑实证主义者只是片面地继承。事实上,康德所梦想的还是未来有一种作为科学而出现的形而上学能够建立起来。这可能就是德国哲学的特点:不是因为形而上学容易使人陷入困境就避开它,只谈清晰明了的问题,只谈经验知识。形而上学的特点就是理性的特点,理性,我们是逃避不了的!
其实,黑格尔通过辩证法拯救形而上学危机有他的深层目的,有他出于时代的考虑。一八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中袒露了他对这个时代的心声:这个时代有一种“对于理性的绝望”的危机。这篇开讲辞主要是对科学启蒙的反思和批判,而在这种科学启蒙背后起作用的是实证主义。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不可知论导致了这样一种后果:我们对上帝不能形成知识,不能通过理论理性对它加以证明,只能信仰或期待。②黑格尔在1821年讲演手稿中反问道:我们不认识上帝,怎么能够信仰上帝呢?之后又批判道,把宗教仅仅作为某种主观东西加以考察和理解,这尤其是我们时代的态度与考察方式:“我们对上帝毫无所知,我们不知道他的任何内容,不知道他的本质和性质,就是说,这种往上帝去等于往一个对我们来说空虚的地方去。”见《黑格尔全集》第17卷,第5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这样上帝就从科学的领域被请出去了,我们就形成了两个领域:有限性的经验领域和无限性的超验领域。黑格尔在一八二一年夏季学期宗教哲学的讲演手稿中写道,“这一要求把上帝变成了远离我们的意识的一种无限幻象,同样,把人的认识变成了有限性的一种虚骄的幻象、幻影和现象的填充”。①《黑格尔全集》第17卷,第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这样,人们就流行起了一种风气:以获取越来越多的有限性的知识为骄傲(这时实证科学门类广泛建立起来),而认为认识上帝的本性和本质是愚蠢和徒劳的。黑格尔在一八一八年开讲辞中用拜拉特②Pilatus,审判耶稣的罗马总督(在《耶稣传》中被译为“彼拉特”)。见黑格尔《小逻辑》,第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又见黑格尔《耶稣传》,《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第14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的态度类比这种流行的态度:当拜拉特从耶稣口里听到真理这名词时反问道,真理是什么东西?意思是说,天地间有真理吗?黑格尔又在一八二一年讲演手稿中这样描述这一特征:“我们的时代却具有这样的突出标志:了解一切事物和每一件事物,而且是无限众多的事物,惟独不了解上帝。”③《黑格尔全集》第17卷,第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这让我想起了尼采对虚无主义特征的描述:现代人很忙,生活没有目的。现代人对所有事情都很勤劳,惟独对一件事情不勤劳,就是思考人生的意义。在此,黑格尔较早地涉及了虚无主义的问题。
实际上,黑格尔在形而上学权威性逐渐隐退和消失的背后看到了现代社会有一种最高精神的逐渐隐退和消失,这是他真正忧虑的。那就是对真理和绝对不追求、对永恒和神圣对象不置可否的态度,即对决定此岸的那个彼岸失去了兴趣。他在一八一八年开讲辞中说:“不去认识真理,只去认识那表面的有时间性的偶然的东西——只去认识虚浮的东西,这种虚浮习气在哲学里已经广泛地造成,在我们的时代里更为流行,甚至还加以大吹大擂。”④黑格尔:《小逻辑》,第35、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宗教上和伦理上的轻浮任性,继之而来的知识上的庸俗浅薄——这就是所谓启蒙——便坦然自得地自认其无能,并自矜其根本忘记了较高兴趣。”⑤黑格尔:《小逻辑》,第35、3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可见,黑格尔的哲学承担着一种神学意图:通过理性恢复起对上帝的证明,通过理性恢复起对绝对和永恒的信仰。Geist,在德文中既指精神,又指圣灵。我们知道,三位一体说是基督教区别于犹太教的标志。但如何理解“圣灵”,是三位一体说的核心。黑格尔就是要用“绝对精神”,用理性来解释基督教的“圣灵”。从黑格尔哲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哲学的反实证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又往往与批判虚无主义的因素相呼应。
尼采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批判形而上学的,他要将形而上学连根拔起。他认为,形而上学本身是虚构出来的,这是欧洲虚无主义的根源。它用一层层迷雾将自己包裹起来,逻各斯、道德、科学、绝对价值都在其中。它既是虚构的慰藉,又是枷锁。枷锁一旦打开,人们就像被取走灵魂一样不知所措。这正是尼采笔下的欧洲现代人形象。
“形而上学”一词,在海德格尔那里,比较复杂,他一方面批判形而上学,是从批判西方哲学的虚无主义着手的,但有时候亦称自己的哲学为形而上学。
他是说,作为虚无主义的形而上学“终结”了,但同时形而上学以变化了的形式从另一个开端开始“复活”。在经历了康德与黑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两次重大的批判和改造之后,尼采、特别是海德格尔对以往形而上学进行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批判,在这次批判中,形而上学不再是一种哲学门类、或者思维方式,而是一个基本事件,这一基本事件刻画了西方人的命运:虚无主义。海德格尔将西方形而上学的实质看作虚无主义,这与尼采将欧洲虚无主义的根源视为形而上学是一致的。“在海德格尔看来,西方形而上学的实质就是虚无主义,二者其实是一回事。虚无主义是形而上学内部隐藏着的一个基本运动,也是西方历史的基本运动。”⑥张汝伦:《〈存在与时间〉释义(上)》“引言”,第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似乎同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有一种时间上的错位:正当当代新儒家想要构建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时候,西方哲学却在批判、拒斥、企图消灭形而上学。⑦20世纪30年代正是逻辑实证主义盛行的时候。这种时间上的错位至今还以某种有趣的形式出现:据说2001年德里达来访中国,在巡回讲演中说到“中国没有哲学”,顿时引来中国学者非议。这意味着,当“哲学”在西方遭受置疑的时候,中国人却对它充满渴望、并因缺少它而感自卑。其实,如果将中西在民主和科学问题上的时间错位与在形而上学问题上的时间错位放在一起理解,那么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在西方,民主和科学的命运与形而上学的命运是一致的,或者说,民主和科学本身就隶属于形而上学,是形而上学的产物和表现,形而上学是民主和科学的根——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就是对美国主义的民主和科学的批判——而在我们大力接受民主和科学的时候正值西方人反思民主和科学的时候。这种时间上的错位就意味着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之路将更为艰难,同时就要求中国哲学在处理形而上学的问题上要更加谨慎。
二、意义与形而上学
由于世界历史的逼近,形而上学已经不再是一个欧洲的基本事件,而是一个全球化的基本事件。如此说来,全球化背景下的我们就不得不严肃思考形而上学的命运问题。
很多人了解“悲”,但不了解“悲”的必然性,因此达不到尼采的高度。正因为认识到强力意志是永恒轮回的,是必然的,才深入到“悲剧”的内在本性。但尼采的弱点同样在此:尼采需要“悲剧”,他靠“悲剧”疗伤。①如果按照尼采,那么悲观主义的层次并不高,其结局往往退回到佛老。如有人言《红楼梦》之结局,有真爱的最终全散了,无真爱的却凑合在了一起。整本流露出了作者对于“真爱”的失望乃至绝望,而并不深究这“希望”本身的虚无性。作者最后认为人生没有意义,其实只是他的一声悲叹。倘无挂碍,何来悲叹?见刘再复在《〈红楼梦〉与西方哲学》(《书屋》2009年第2期)中所写:“曹雪芹认定,人生没有意义,说到底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而已,这个世界到头来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什么也不剩。”悲剧是其生命中的最后一道光、引路之光!尼采认为“活”尚需要某种意义——没有意义的“活”是空虚的,人应该去信仰。因而,他的“活”是脆弱的,意义滋养着它。正因为他看到了意义的非永恒性、虚无性,才会时时感到人生的悲剧。“悲剧”是什么?就是强力意志之本性。强力意志是设定,悲剧是设定。他的问题在于从一开始就预设:人生应该是有意义的——“真理和人有什么关系?不相信自己拥有真理,人就不可能有最纯洁和最高尚的生活。人需要信仰真理”(《哲学与真理:尼采一八七二-一八七六年笔记选》)——一个人的灵魂只有寄托给某种信仰才会过得充实。尼采却将灵魂寄托给了绝望。但那还是一种寄托,他靠绝望活着。他绝望着,以此证明自己还活着。尼采宁愿承担起绝望的命运,亦不愿放弃绝望的权利。他在《论道德的谱系》中说,“它宁求对虚无的意愿,而不是不意愿”。②海德格尔解释道,“在这里,对‘虚无的意愿’意味着: 意愿缩小、否定、毁灭和荒芜。在这样一种意愿中,强力始终还为自己确保了命令的可能性”。他在另一处阐释中说,“意志所畏惧的并不是虚无,而是不意愿,是对它的本已可能性的消灭。对于不意愿的空虚的畏惧——这种“ horror vacui”“空虚之畏”——乃是人‘类意志的基本事实’”。见海德格尔《尼采》,第899、703页,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就是说,宁愿以虚无主义方式被经验为虚无,而不是根本就不再意愿、并因此放弃生命的可能性。
如果你说尼采这仍是一种形而上学,那我并不反对。但人不是上帝,因而谁能摆脱得了形而上学的迷雾?可贵的是有些人可以清醒地意识到深陷其中。动物免于形而上学的困惑,而人无往不住地活在欺骗之中。
一般的人都是在欺骗自己中活,如果你不想在欺骗自己中活,那就需要你真正地坚强,需要你从根本上认识到我们的内在世界是虚幻的,如此一切哲学就消失了,同样“人”就消失了。
因为人从自然界脱离出来之后,了解到真伪、善恶、美丑、彼岸、此岸、欲求、幸福、希望、应当……内心就变得十分脆弱,所以需要意义依托。哲学家们一直致力于揭露那些意义世界的虚无,但总是舍不得丢下手中最后一块意义手帕。
人一旦从意义世界走出来就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或者不称其为人。所谓“意义世界”,在西方被称为形而上学世界,在佛教中被称为娑婆世界。
对于“坚强地活着”,我不同意以下两种意义的活法:一种是将自己混同于自然界的存在,认为人与动物没有根本的区别,甚至在某些方面不及动物。这实际上是一种逃避内在世界的方式,实际上掩盖了他比活在意义世界中的人更加脆弱的本质。另一种是如加缪那样的主张:生活本来就没有意义,任何寻找意义的企图都是徒劳的。但他选择活下去。这种主张的缺陷在于并没有击穿“痛苦”的虚无性。
在我看来,对所有意义世界的抛弃应该是一种充实的抛弃,即其内在世界已然饱含了一切意义,从一切意义中走出来,而不是逃出来。那时,你将认识到哲学根本解决不了你的任何问题,不论是生存问题,还是意义问题,因为一切意义都是从它那里制造出来的。但必须通过这种种意义的尝试,你才能最终认识到意义本身的无意义性。
海德格尔讲,此在生于虚无。人来到这个世上,既没有来源,又没有目的,人的存在只能依赖于自己。这意味着一切意义出自于它自身,人只身行走于深渊之中。但正是因为既没有来源,又没有目的,人才不受制于必然。在此,你是否会想:人是最贫乏的,却又是最丰富的;人是最孤独的,却又是最充实的;人是最脆弱的,却又是最坚强的;人是最卑微的,却又是最伟大的。形而上学危机、信仰危机,说穿了是“人”的危机。人不敢承认自己为“人”,不敢承担自己的意义了。但当你了解到意义的真相之后,就会坚定地为自己是“人”而发出赞叹。
戴劲,一九八○年四月生,河北省秦皇岛市人,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香港中文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荣誉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