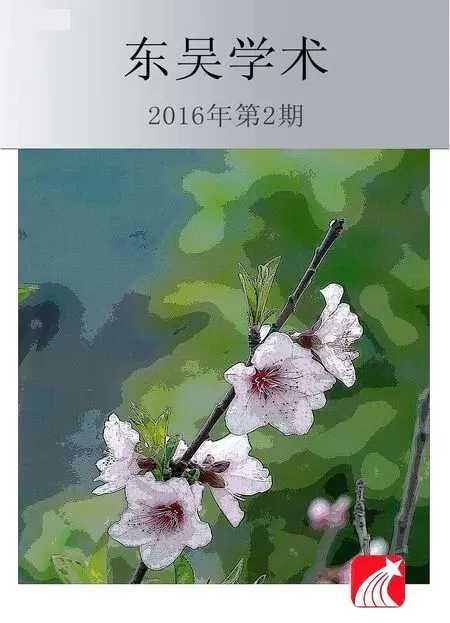《觉醒》中艾德娜的主体意识发展探析
金秋容
《觉醒》中艾德娜的主体意识发展探析
金秋容
凯特•肖邦最重要的小说《觉醒》呈现了主人公艾德娜的主体意识的发展过程。艾德娜挑战了男性权威将女性客体化的规定,重建了女性的主体地位,逐步确立了与男性同等的女性主体意识。在此意义上,她冲破了男权社会中男性主体/女性客体二元对立的藩篱。但此后,艾德娜作为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人,却表现出脱离同他人和社会一切联系的倾向。她片面强调人的主体意识的能动性,拒绝接受主体意识的受动性,她对脱离社会现实的绝对自由的追求,致使其主体意识最终陷入困境。艾德娜或许并非自杀,而是以竭力游向大海深处来逃离现实,追求主体能动性的最大发挥。
《觉醒》;艾德娜;主体意识
凯特•肖邦于三十多岁时开始文学创作,在此后不到十年里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近百篇短篇小说和大量散文及评论等,一跃成为美国著名作家。一八九九年《觉醒》的出版震惊评论界。它大胆描写了已婚女性的反叛,为当时的社会传统和伦理道德所不容,被斥为“卑鄙下流、庸俗不堪”的“毒药”,出版界将其封禁了半个世纪。近年来,《觉醒》被重新挖掘出来,得到了多角度的重读。过去,主人公艾德娜•庞蒂里耶常被看作软弱、自私和不道德的代名词。但如今评论家们普遍认为,肖邦对主人公如何在追求自我和顺从社会之间进退两难的描写技巧精湛、十分精彩。肖邦传记作者塞耶斯提德认为,肖邦“在美国文学中开拓了新的领域……揭示了关于一个女人隐秘生活的真相”。①Per Seyersted,Kate Chopin:A Critical Biography,New York:Octagon Books,1980,p. 198.
《觉醒》展现了艾德娜的主体意识逐步发展的过程。要探讨主体意识的问题,首先要明确何为主体。主体是一个哲学概念,在古希腊思想中已经孕育了主体意识的萌芽,但真正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的是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认为“所有的生物一般说来都是主体”;②[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67-168页,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费尔巴哈把立足于自然之上的现实的人确立为主体;而马克思则把主体性置于实践领域,认为主体是社会的、实践的,是现实的人,人的能动实践使人成为主体。主体意识“是主体的内在规定性即主体性的内涵之一”,是“人对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自觉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外部世界和人自身自觉认识和改造的意识”。①张建云:《试析主体意识的内涵》,《天中学刊》2002年第6期,第5页。主体意识是能动意识和受动意识的统一,“受动”一词来自费尔巴哈,受动意识即主体受制约受限制的意识。他认为“自我不仅是某种能动的东西,而且也是受动的东西”。②[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91页,荣震华、李金山译,上海:三联书店,1959。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性的存在,因此具体的人的规定性只能来自他生活的社会,主体是以能动性为主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
在人类历史上,女性的主体地位长期得不到承认。在探讨男性/女性主客二分的问题时,阿尔都塞的主体性理论提供了一定启发。③有关阿尔都塞对主体性的论述,见阿尔杜塞《哲学与政治:阿尔杜塞读本》,陈越主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阿尔都塞论述的主体性失去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意识形态决定论的色彩,但此处借鉴的是关于意识形态建构主体的论述。他认为人们对现实的认识由意识形态塑造,主体是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因此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男性为了确立主体地位,将女性贬为客体。女性受到男权意识形态的限制,失去了作为人的主体意识。在这个意义上,艾德娜主体意识的确立打破了男性主体/女性客体的二元对立。但与此同时,应该认识到确立了主体意识的艾德娜却表现出强烈的封闭自我的倾向,片面追求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却排斥主体意识的受动性,这使她的主体意识走向极端。基于以上认识,考察艾德娜主体意识的发展过程时,首先应当探究她如何挑战男性权威、冲破将女性客体化的规定并确立起身为女性所具有的主体意识。其次则应着眼于她作为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中的人所具有的主体意识。本文拟对艾德娜主体意识的发展过程进行分析,指出她确立女性主体意识的积极意义,并探讨她在扭转男权社会统治下女性被客体化的命运后,作为普遍意义上的人的主体意识所陷入的困境。
鹦鹉:主体意识的萌动
小说一开始便描绘了一只羽毛艳丽、聒噪不停的笼中鹦鹉。这只鹦鹉与故事开头的艾德娜极其相似。从表面上看,鹦鹉美丽的羽毛正如艾德娜华丽的衣饰,她过着富有的生活,不愁吃穿,不必担心生计;而且,鹦鹉作为其主人的所有物,被关在鸟笼中,已经失去了飞翔和觅食的能力。在传统的性别关系中,女性处于完全的从属地位,是“被压抑的他者”,④杨永忠、周庆:《论女性主体意识》,《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8页。男性把女性客体化,即把女性形象物品化,这带来的必然是女性主体意识的丧失。“无论是男性个体的发展,还是父权制,都部分植根于抵制女性权力和女性自治的需要”。⑤Jane Flax,“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atriarchal Unconscious:A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on Epistemology and Metaphysics”,in Nancy Tuana & Rosemarie Tong,eds.,Feminism and Philosophy:Essential Readings in Theory,Representation and Application,Boulder,CO:Westview Press,1995,p. 218.在十九世纪末期的美国,传统的维多利亚价值观盛行,女性及其一切私人物品都被认为是其丈夫的个人财产,社会不允许女性有任何个人追求。妇女的义务就是做一个“温顺听话的女儿、忠实可靠的妻子,谨慎周到的母亲”。⑥金莉、秦亚青:《压抑、觉醒、反叛——凯特•肖邦笔下的女性形象》,《外国文学》1995年第4期,第58页。庞蒂里耶先生恰恰将妻子视为私人财产。艾德娜从海滩回来,她的丈夫看着她,“好像在看一件受损的珍贵财产”。⑦Kate Chopin,The Awakening,New York:Simon & Schuster,Inc.,1996,p. 20.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该著作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庞先生很喜欢在家里来回走动,检阅他的私人财产,因为一切都是他的所有物,他拥有支配权。在庞先生眼中,他的妻子就和家里的装饰品一样。此外,鹦鹉也暗示着艾德娜话语权的丧失。话语权是人作为主体所不可或缺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莲娜•伊克苏提出,父权社会掩盖了女性话语,女性的表达能力被剥夺,处于失语状态。鹦鹉学舌,它只会重复别人的话,却没有自我表达的能动性。男权社会中的母亲是“他者,一个能保证孩子主体地位的客体”。①Julia Kristeva,trans. Leon S. Roudiez,Powers of Horror:An Essay on Abjec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2,p. 32.母亲或是妻子仅仅被视为其丈夫和孩子的主体地位的保证,得不到自己也身为主体的认可。艾德娜不过是满足丈夫和孩子需求的客体,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庞先生指责艾德娜对孩子照顾不周,艾德娜无力反驳,只能一个人坐在门廊边哭泣,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压抑”。(Awakening:24)这时的艾德娜还不清楚她感到痛苦的原因,证明她还意识不到自我的存在。
此时艾德娜的主体意识尚处于“自在自然阶段”,即“对自己的主体意识的认识尚不明确,还不能认识到自己是主体,主体意识尚处于‘潜在状态’”。②魏国英主编:《女性学概论》,第9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艾德娜的婚姻正是其主体意识缺失的标志。成为庞夫人使她拥有了中产阶级的地位,同时也意味着她成了丈夫的私人物品,成了男权意识形态统治下的他者。“男人不是就女人的本身来解释女人,而是以他自己为主相对而论女人的。”③[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第10-11页,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男性权威统治下的女性,只能是被建构出来的客体。然而,艾德娜和那只鹦鹉一样,有时会讲一种“谁都听不懂的语言”(Awakening:19)——这正代表着艾德娜蛰伏的主体意识。度假岛之旅为她日渐枯竭的心灵带来曙光,让她逐渐意识到自我的存在。
首先,度假岛的自然环境是促使艾德娜的主体意识萌动的一股强大力量。整个度假岛被大海环绕,而大海首先启发了艾德娜对自身的思考。艾德娜独自哭泣的当晚,海浪的声音促使她发泄出郁积于心的感情。大海吸引着艾德娜的灵魂,她渐渐审视起自己的内心。她乘船出游,当船驶过海湾,艾德娜感觉自己从紧锁的铁链中解放出来了,她已经多年未体会过这种随心所欲的自由感。学会游泳则成了她主体意识觉醒的里程碑。在经历了多次失败之后,艾德娜忽然觉察到自己学会了游泳。狂喜的感觉令她心醉神迷,她感觉终于能够“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了。(Awakening:47)艾德娜意识到她能凭自身的力量达成目标。在她学会游泳的那一刻,艾德娜不再是受丈夫和孩子支配的客体,而是拥有自主权的独立主体。她有了从被动接受转而主动争取的模糊意识,这正是她的主体意识复苏的表现。当晚庞先生要求她回房睡觉,以男性权威逼迫艾德娜服从。但她却回答:“我想待在外面。我不想,也不打算进去。别再那样和我说话;否则我不会回答你”。(Awakening:51)回屋就意味着再次沦为受丈夫支配的客体。如果说先前遭到无端指责的艾德娜还无言以对的话,学会游泳后的她已经开始重新掌握作为女性主体的话语权,希望和丈夫平等对话。她开始强烈质疑男性话语系统,将愤怒和反抗隐藏在失而复得的女性话语之中,拒绝接受男性将女性客体化的行为,重建女性的主体地位。
度假岛上的克里奥尔人是促成艾德娜从旧我之中解放出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些人之中,有两位女性加速了她对自己主体地位的觉悟。其一是阿黛尔•拉蒂诺尔夫人。拉夫人完全是英国维多利亚式的房中天使,作着丈夫和孩子的奴隶。米利特在《性别政治》中指出,处于男性权威压迫下的女性内化了男权社会的价值体系,以致不能认识到压迫的实质和根源。④See Kate Millett,Sexual Politics,Champaign: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0.拉夫人成了艾德娜审视自己的镜子,触发了她对自身的家庭、社会地位的思考。另一位克里奥尔女性、钢琴家芮芝小姐对艾德娜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芮芝小姐琴艺精湛、充满激情,极大地震撼了艾德娜。听着她的琴声,艾德娜感觉心中潜藏已久的激情受到了召唤,强烈的情感“摇动着、鞭打着她的灵魂”。(Awakening:45)无数的情感在艾德娜的身体里交织、翻滚,她终于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拥有自由感情的主体。而且,芮芝也完全不是人们眼中的传统女性,她特立独行,一举一动都是对男权社会加诸女性身上的不平等规约的挑战和蔑视。其后,芮芝还鼓励艾德娜突破男权社会的传统偏见,启发她找到自我价值的实现途径,可说是艾德娜的成长导师。
度假岛的经历使艾德娜产生了“作为主体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①魏国英主编:《女性学概论》,第9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她开始思考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意识到她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Awakening:31)主体意识开始萌动。她开始对自己作为女性主体的身份产生自觉,并有意识地扭转在男性权威统治下沦为他者的女性地位,这为她接下来真正确立与男性同等的女性主体意识作了充分准备。
鸽子:主体意识的确立
随着艾德娜主体意识的复苏,她开始把自己视为能依靠个人意志思考和行动的独立个体,她的主体意识从最初的自在自然阶段逐步发展至自知自觉阶段,即“主体意识的觉悟和发现”。②祖嘉合:《女性主体意识及其发展中的矛盾》,《社会科学论坛》1999年Z1期,第44页。艾德娜由主体意识开始萌动的鹦鹉长成了主体意识得到确立的鸽子,逐步意识到自我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开始充分发挥作为主体的能动性。
性意识是艾德娜主体意识的重要方面。在男权文化中,女性要么是贞女,作丈夫和孩子的奴隶,实现所谓的崇高使命——为人类的繁衍而生育;要么是荡妇,红杏出墙,伤风败俗。拉夫人就是贞女的典型,在小说中,她每两年就会生一个孩子。女性不能有性意识,一旦同“性”联系在一起,就成了不堪的妖妇。女性没有主体地位,作为人的本性遭到贬斥和压制。但艾德娜却在与两位男性交往的过程中确立起自觉的性意识,这无疑是她逐步确立作为女性的主体地位过程中的重大进步。首先,度假岛主勒布朗太太的大儿子罗伯特唤起了艾德娜对爱情的渴望,让她发现她是自己欲望的主人。两人去尚奈尔岛时,艾德娜一个人在岛上的小屋里仔细观察和感受自己的身体。她仔细端详自己裸露的手臂,欣赏那“结实的肌肉和细腻的皮肤”,“好像是头一回看到似的”。(Awakening:57)当艾德娜这么做时,她已经意识到她的身体为自己所有,她是自己欲望的主体。她沉睡许久,梦醒时分,感到自己像一只从冬眠中彻底苏醒的动物,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并“熟悉周围的新情况”。(Awakening:60)她感觉异常饥饿,狼吞虎咽下象征着耶稣基督血肉的酒和面包,沉睡的欲望终于重新燃起。不久,罗伯特突然离开度假岛,前往墨西哥闯荡。艾德娜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爱上了罗伯特。
如果说罗伯特主要是在精神层面上激发了艾德娜的性意识,那么阿罗宾则在肉体上充分满足了艾德娜的欲望。回到城里的艾德娜遇到了纨绔子弟阿罗宾,与他发生了婚外情。艾德娜对罗伯特的爱欲无法在精神和肉体层面得到双重满足,于是她只好把灵与肉分开。阿罗宾的情爱“像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般点燃了欲望”。(Awakening:106)阿罗宾发现,艾德娜“本性的需求”和“潜藏的肉欲”“像一朵冬眠后的花般绽放开来,热情又敏感”。(Awakening:128)艾德娜对爱情和欲望的肯定正是她作为女性主体的重大觉悟。她成了自身欲望的主体,不再是只能被动满足男性要求的工具。由此,艾德娜的性意识最终得到确立。
与此同时,艾德娜的个人意识也确立起来了。她开始追求独立和自由,完全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艾德娜回到城里,开始专心绘画,从中得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她放弃了婚后遵守了六年的家规——每周二在家接待丈夫在上流社会的朋友;她不再闭门不出,而常常外出观察城里的一切;她不顾丈夫的不满和反对,拒不拜访丈夫要她多加关注的权贵朋友,却常去看望她自己在度假岛结交的朋友。艾德娜的反叛更是在一个晚上达到了高潮。庞先生又以饭菜不合胃口为由离家去俱乐部游荡,留下艾德娜一个人吃饭。婚后的艾德娜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情形,但如今她认为作为女性主体,有权得到男性的尊重和平等对待,而不是被当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鹦鹉,只要丈夫觉得无趣,就“有权离开它”。(Awakening:19)艾德娜发现房间里的一切都极其压抑,因为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而她自己又何尝不是被当成一样东西放在家里?她强烈地憎恶这一切。她的眼中仿佛“燃烧着一团发自内心的火焰”,(Awakening:73)撕碎手帕,摔破花瓶,把戒指摘下扔到地上猛踩。她强烈地表达着追求自我价值和自由个性的欲望,下决心再不让步。从此,艾德娜开始质疑婚姻,寻找确立主体地位的途径。她决定凭自己的意志追求想要的生活,决不受制于男权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规定。
弗吉尼亚•伍尔芙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指出,一个女性要想获得真正的独立,首先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其次还要在经济上独立。①Virginia Woolf,A Room of One’s Own,London:Penguin,1993,p. 4.艾德娜个人意识的强化正印证了这一点。庞先生和孩子们因事离家,留下艾德娜一个人,恰好为她追求独立自由的生活提供了大好机会。她发现,偌大的房子从未让她产生过归属感,因此希望能拥有一片自己的空间。她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幢小得多的房子,并戏称其为“鸽子屋”。新居让她有了真正的归属感,给了她一处“自由的精神和物质家园”。②陈殊波:《超越局限——〈觉醒〉中空间意象释读》,《外国文学》1997年第1期,第87页。海德格尔曾在《筑居思》中提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就要有一处居所,居所定义了人性,人通过构筑自己的容身之所来为自己建构身份。也就是说,“建造居所是创造主体性所不可或缺的”。③Michael Worton,“Reading Kate Chopin through contemporary French feminist theory”,in Janet Beer,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te Chop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 107.搬家前夜,她在老屋里办了一场宴会,作为她与旧我决裂的宣言。她感觉自己“从社会的阶梯上走下来”,“从义务中解脱出来的每一步都增加了她个人的力量、扩大了自我的空间”。(Awakening:117)正如鸽子可以在一方蓝天自由飞翔,艾德娜也有了自己的生活空间。而且,与鹦鹉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家中不同,艾德娜常常外出观察周围的人和事,这不仅是生活空间的扩大,更是她作为一个女性主体,在用女性的眼光看世界。艾德娜的鸽子屋不仅给了她真正的安全感和私密性,还暗示了她的主体性和成长。除了飞翔,鸽子还能自己觅食。马克思认为,妇女解放的第一步便是从家庭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社会公共领域。艾德娜不仅搬了家,还找到画商,定期卖掉自己创作的一些油画,取得独立的经济来源。她就这样开始一步步追求独立和自由,扩大生活空间,实现个人价值。
女性主体意识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女性“处在主体和看的位置上”,是“选择自己生活道路的主动者”;第二,“肯定女性主体意识和欲望的存在”。④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第10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艾德娜开始以女性的眼光审视自我和周围,确定自身本质、生活意义和社会地位,其主体意识的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她在自我意识和性意识两个方面认识到自我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存在状态,一方面,她的性意识在两位男性的驱动下彻底觉醒;另一方面,她的个人意识得到确立。她已经从之前那个“无精打采的妇人”变成了“一只在阳光下逐渐苏醒的美丽而光滑的动物”。(Awakening:92)这时的艾德娜已经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一个只能受动的被动存在物”,而是能够“主动地……实现自己的目的”的主体。⑤祖嘉合:《女性主体意识及其发展中的矛盾》,《社会科学论坛》1999年第1期,第45页。
艾德娜主体意识的确立冲破了男权社会将男性和女性分别划归入主体和客体范畴的规定,她此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性别意义上的‘女人’”,而且还是“作为一个‘社会人’而存在”。⑥魏国英主编:《女性学概论》,第9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成为一个“社会人”也就意味着她通过建构与男性同等的主体地位,确立了作为人的主体意识。但是,此后她的主体意识却开始走向极端,陷入困境。
断翅之鸟:主体意识的困顿
在确立主体意识的过程中,艾德娜充分发挥了她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她不断挑战男性权威对女性的客体化,重建起与男性同等的女性主体地位,打破了男性主体/女性客体的二元对立。但是,能动性只是人的主体意识的一个方面。“人作为自然存在物……一方面……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是受动的和受制约的、受限制的存在物”。①[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受动性“既表现为人对客体对象的依赖性,又表现为客体对象对人的制约性……清醒、冷静的受动意识是主体意识应有之义”。②张建云:《试析主体意识的内涵》,《天中学刊》2002年第6期,第9页。受动性是能动性产生的基础,在现实意义上,主体性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艾德娜超越了男权社会加诸女性身上的不平等规约,成为与男性主体平等的女性主体,但人是社会的人、现实的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艾德娜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主体,仍然要受到社会普遍性规定的制约,即社会加诸主体的限制。然而,她不能正确认识社会对主体的制约,封闭自我,盲目追求所谓的绝对自由,把自我同他人和社会割裂开来。正是在这种片面追求能动性的极端主体意识引导下,艾德娜就像一只想飞到天外的鸟儿,走向了在她眼中能摆脱一切约束的自由之邦——大海。
促使艾德娜将其主体能动意识绝对化的,是她对爱情的理想主义幻梦的破灭。艾德娜所追求的爱情浪漫而不切实际,幻想着双方灵魂彻底的融合。这和她走向极端的主体意识产生了矛盾。双方的彻底融合意味着个性的丧失,但艾德娜已经下定决心不属于任何人,如果罗伯特请求庞先生把艾德娜让给他,那她“会嘲笑他们两个人”。(Awakening:132)罗伯特的不辞而别令她看清了自己内心的强烈渴望:追求一种只属于自己的自我,一种不受任何外部力量影响的自由。可见艾德娜已经走进了片面夸大主观意志的死胡同。她意识到,总有一天连罗伯特也会从她的生命中消失,她的浪漫幻想“会成为她追求绝对自由的另一个阻碍”。③Nina Baym,“Introduction to The Awakening”,New York:Modern Library,1981,p. xxxviii.目睹拉夫人痛苦的生产经历更令艾德娜将孩子视为对自己主体性的极大威胁。艾德娜认为孩子是阻碍她行使主观意志的绊脚石。身为女性的她已经成功超越了男权对女性的压迫,但身为人,她依然负有抚养孩子的责任。克里斯蒂娃曾提出,女人作为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但母亲的身份也能增强女人的主体性,“母亲对孩子无我的爱并不能与牺牲自我画上等号”。④Michael Worton,“Reading Kate Chopin through contemporary French feminist theory”,in Janet Beer,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Kate Chopi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 111.艾德娜不仅是在拒斥身为母亲的义务,而且发展到拒绝一切会束缚她发挥主观意志的社会规约。但人是社会性的存在,因此必然会受到来自社会的各种制度、规范、法律、道德等的限定和制约。社会普遍性的规定就是个体必须履行的义务,黑格尔认为人在这种义务中:
毋宁说是获得了解放。一方面,他既摆脱了对赤裸裸的自然冲动的依附状态……又摆脱了他作为主观特殊性所陷入的困境;另一方面,他摆脱了没有规定性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没有达到实在,也没有达到行为的客观规定性,而仍停留在自己内部,并缺乏现实性。在义务中,个人得到解放而达到了实体性的自由……义务就是达到本质、获得肯定的自由。⑤[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67-168页,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艾德娜正是陷入了“停留在内部并缺乏现实性”、“没有规定性的主观性”。听到拉夫人那句“想想孩子们……记住他们”,艾德娜觉得自己被孩子打败了。她能意识到自己作为现实中的人,必须承担家庭责任和社会义务,但是她拒绝接受这种受动性,在封闭自我的渴望驱使下,她只追求主体的能动性,意欲实现脱离社会现实的抽象自由。连天空都想超越的鸟儿,还能飞往何处?无法接受受动意识的主体意识是不完整的,艾德娜只有在这片天空中才能真正自由地飞翔。她只觉得外部世界的约束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只要生活在城市,内心对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的渴望就无法得到满足。对她而言,城市只代表禁锢。城市即是社会的象征,在艾德娜眼中,这是一个充满敌意又陌生的世界,她早已不属于这里。艾德娜最终的选择,反映了美国文学中的重要主题,即逃避。她决定逃离家庭,逃离社会,追求个人自治,不想让外界的任何束缚加于自身。
艾德娜最终离开城市,回到环绕度假岛的大海,有着显而易见的理由。无边无际的大海首先启发了艾德娜对自我存在的思考,同时象征自由与逃避,“融入大海就是完全投入自己的世界”。①曾晓覃:《大海的呼唤——析〈觉醒〉中的象征》,《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53页。她小时候,曾经为了逃避长老会的教堂礼拜从家中逃出,在似海的宽广草地里前行。作者将童年的艾德娜眼中的草地比喻成大海是有明确意图的。童年时的艾德娜逃避家庭对她的要求,不断拨开面前的长草,无拘无束地前进,离家越来越远;如今的艾德娜逃避的是一切现实约束,在真正的大海中前进,离现实社会越来越远。同幼时一样,如今她同样坚决反抗着现实社会加诸自身的限制。
需要指出的是,艾德娜或许并不是自杀,因为她是通过游泳来融入大海的。前文已经提过,学会游泳令艾德娜对自我产生了重大觉悟,正是通过游泳,她的主体意识才开始苏醒。游泳是艾德娜第一次作为主体的能动实践,因此游泳对艾德娜主体能动意识的确立无疑意义重大。如今艾德娜重回大海,依旧是通过游泳来维护她那存在主义式的主体性:不断的超越和绝对的自由,作为同社会现实相脱离的孤独个体存在。肖邦为《觉醒》起的原题《一个孤独的灵魂》印证了这一点。她越游越远,代表着现实社会限制的海岸也离她远去。艾德娜并不是绝望地自杀,而是以竭力游向大海深处来逃离现实中的一切,追求主体能动性的最大发挥,实现所谓绝对自由。如果她心如死灰,执意自杀,又为何要游泳?幼时的她穿行在草地里,感觉自己“必须永远向前走,却走不到尽头”,(Awakening:35)现在的她又何尝不是如此?她越是深入大海,就离她所想的自由越近,但注定达不到这个鹄的。下海游泳前,她脱下泳衣并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不正表明她对解除一切现实束缚的强烈渴望吗?她拼命维护主体的主观意志,想在大海中得到那种虚无的自由。在这样做的同时,她否定和拒绝了作为主体必须承担的受动性。艾德娜对自由的理解是抽象的,脱离社会的,她无限夸大了主观能动性,主体意识因而必然走向极端,陷入困境。如此一来,作为人的本质只能是虚无。最终,连天空的界限都想超越的艾德娜成了一只折翼之鸟,“在空中扑腾着,挣扎着,打着旋,不停地下坠,下坠……”。(Awakening:139)艾德娜一直到最后都在追逐自由,殊不知她眼中的自由已经偏离了正确的方向,注定无法实现。
逃不出走向极端的主体意识造就的思想牢笼,正是艾德娜最终结局的决定性因素。艾德娜已洞悉自己的现状,对周围的人事亦有深刻的理解,可是她对自己接下来该如何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人生活下去,却始终未能找到答案,只是在逃避中追寻虚妄的自由梦。一只渴望在不受任何束缚的情况下自由飞翔的鸟儿,注定要折断翅膀。
结语
凯特•肖邦的《觉醒》展现了主人公艾德娜的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一开始,艾德娜隐隐地感到一种模糊的压抑,经由度假岛之旅,她的主体意识开始复苏,是一只主体意识开始萌动的鹦鹉;接着,她开始思考自我的地位和价值,追求自我实现,成为主体意识得到确立的鸽子;最后,她的主体意识走向极端,指引她脱离同现实的一切联系,逃避作为社会主体必须承担的责任义务,追求无法实现的绝对自由,终于折断了翅膀。作为女性的艾德娜成功扭转了男权社会下女性沦为他者的命运,建立起与男性主体等同的女性主体地位,应当充分肯定;但在此基础上,作为普遍意义上的社会中的人,艾德娜却一味追求主体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忽视和排斥主体意识的受动性,在她作为社会人的主体意识陷入困境时,她靠逃避来追求脱离现实、无法实现的自由梦,因此,艾德娜的觉醒无疑是有局限性的。
(责任编辑刘浏)
金秋容,常熟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英语(师范)专业二〇一三届毕业生,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