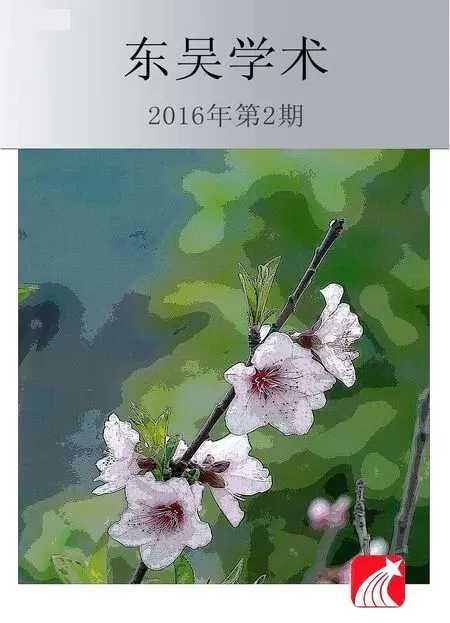晦暗、剧烈而幽深
——评谢尔•埃斯普马克《失忆的年代》
符树芬
晦暗、剧烈而幽深
——评谢尔•埃斯普马克《失忆的年代》
符树芬
《失忆的年代》是瑞典作家谢尔•埃斯普马克的一部系列长篇小说。作家采用意识流的表现手法,以一种知识分子的思考深度,为我们描绘了一张张生活在失忆的年代里的现代人的面孔。小说记录了瑞典社会的历史、人文和现实,但批判的是西方社会的生存图景,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命运,最后书写的是现代人的精神荒原。归根结底,小说书写的是集权主义。作家试图表明的观点是:我们需要一股强大的力量建立国家,但同时也需要另一种力量去护卫个人利益,只有公平的、给予个体充分发展空间的国家,才能建设一个繁荣的社会;在此基础上,社会的每一个组成人员也才有活着的尊严可谈。
失忆;意识流;瑞典社会;集权主义
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一九三〇-)的小说不好读。如果你读过他的《巴托克:独自对抗第三帝国》就会认同我所说的话——那哪里是小说?分明是一部构思精巧、辞意锤炼的散文诗。而事实上,作家本人也非常乐意如此定性这部作品。这就是说,阅读这样文体性很强的文章,挑战的不仅是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思维定性,更考验读者的知识结构、鉴赏水平、思考深度。
而《失忆的年代》①谢尔•埃斯普马克:《失忆的年代》(1-7卷),万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015。较之《巴托克:独自对抗第三帝国》,其阅读难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部小说很有嚼头,不容易被嚼烂。说到这里,就不得不对小说的作者多说几句题外话。谢尔•埃斯普马克,瑞典著名诗人、小说家、文学史家、瑞典学院终身院士,一九八七年至二〇〇四年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在其任职的十七年间,瑞典皇家学院给包括约瑟夫•布罗茨基(一九八七)、奥克塔维奥•帕斯(一九九〇)、托尼•莫里森(一九九三)、大江健三郎(一九九四)、君特•格拉斯(一九九九)、V.S.奈保尔(二〇〇一)、艾尔芙蕾德•耶利内克(二〇〇四)等在内的诗人和小说家颁发了诺贝尔文学奖。如果文学真的存在一条“金线”,②冯唐:《三十六大•大线》:“文学的标准的确很难量化,但是文学的确有一条金线,一部作品达到了就是达到了,没达到就是没达到,对于门外人,若隐若现,对于明眼人,一清二楚,洞若观火。”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2。那么毫无疑问,埃斯普马克对文学的这条金线最有发言权。他知道什么是好的文学,他知道好的文学的高度又在哪里。而事实上,他曾经出版过一部非常著名的文学评论——《诺贝尔文学奖:选择标准的探讨》,①谢尔•埃斯普马克:《诺贝尔文学奖:选择标准的探讨》,此书中文译名《诺贝尔文学奖内幕》,李之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探讨了诺奖评选的诸多标准。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对象,虽然阿尔弗雷德•伯恩哈德•诺贝尔在遗嘱中明确指出是“在文学方面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然而从历年诺奖的授奖词中,人们可以看出这些标准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而在谢尔•埃斯普马克任职诺奖评委会主席的十七年间,他进行了海量的阅读,可想而知什么样的作品他没有见识过?
因此人们会非常好奇,这个诺奖标准的制定者,其提笔写作的小说究竟会是一副怎样的光景。想必一定出手不凡吧,否则其何以成为文学最高奖项标准的制定者?当然这个问题充满悖论,正如同我们不能要求一位优秀的评论家同时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一样——但无论如何,作品已经摆在眼前。现在,就让我们翻开这部小说,进入这位身份殊异的瑞典学者笔下那个特殊的“失忆的年代”。
一
《失忆的年代》在形式上非常独特。这部长卷小说由七个相对独立而又完整的故事构成。由《失忆》(Glömskan)开启,涵盖《误解》(Missförståndet)、《蔑视》(Föraktet)、《忠诚》(Lojaliteten)、《仇恨》(Hatet)、《复仇》(Revanschen)诸篇,最后由《欢乐》(Glädjen)闭合。写作时间跨度为十年(一九八七-一九九七)。
小说结构严谨,各篇章相互呼应。表面上看起来,构成《失忆的年代》的各部分在内容和情节上互不牵涉,但这部作品的构架在整体上是十分紧凑的。在《失忆》的结尾,谢尔•埃斯普马克这么写:“在你现在已经准备好要走的时候,在我的全身,在我身体所有剩下的部分,我都感到你从我们这次会面能带走的全部东西,只是一种巨大的误解。”(《失忆》,第一百五十二页)小说由此进入到第二部《误解》中。《误解》在开头说:“请原谅我,这么往后退缩。你刚坐下来的时候,我没注意到,突然发现你这么近,真有点吃惊。别动啊,不用从我身边挪开啊!你误解我了。”(《误解》,第一页)这个开头紧承《失忆》,而在最后如此收尾:“但是,我感觉到你又远离了一两步。一个偷偷溜走的诈骗犯,只留下了你的背叛。好吧,那你就滚吧。带上我对你的蔑视。”(《误解》,第一百二十九页)小说由此进入到第三部《蔑视》中。“蔑视”之后是“忠诚”,在这里,“忠诚”并非一个带有崇高道德意味的褒义词,小说其实讲述的是一个建筑工人对自己人生所进行的反思,这反思与其说是对过往人生的反省,莫若说是“忏悔”更恰切些,因此反思之后不是“和解”而是“仇恨”(第五部《仇恨》)。于是乎,有仇恨必然带来“复仇”(第六部《复仇》),“复仇”之后是“欢乐”(第七部《欢乐》)。而这个所谓的“欢乐”,别以为人生在历经种种灰暗的挫败和不屈服的抗争之后终于获得喜悦和幸福,恰恰相反,这依然是一个被侮辱和被损毁的妇女在社会现实中的呼号,一个卑微得如同尘埃一般的底层人,如果说还能够倾诉就是“欢乐”,那么这样的欢乐委实是令人心酸。
你可以看出,“失忆”系列小说里,几个主题词书写的全是人性中的晦暗、负面和挫败。瑞典是目前世界上令大多数外界人向往的人间天堂之一。一个一切看起来都完美无缺的国度,社会福利令人满意,经济发达,人们生活得幸福而优雅。但读完小说我们发现,原来谢尔•埃斯普马克先生笔下的瑞典社会与人们想象中的样子大不相同。
这部小说带有强烈的实验性质。谢尔•埃斯普马克对小说的形式非常看重,他认为形式是现代性非常重要的体现之一。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日新月异,小说形式也在“与时俱进”,其“外部特征”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成为审美非常重要的组成要素。因此这部将近四十六万字的小说,在编排上虽然采取丛书的形式,但如果将其排布成一个大部头著作,那也完全不会影响到作品的完整性。
当下的读者越来越挑剔了,人们的阅读口味越来越刁钻。阅读传统小说觉得不过瘾的人,不妨来挑战一下这部《失忆的年代》。其间讲究的叙述语气,对小说艺术几近极致的探索精神,充满了文人作家气息的写作方式,总有其中一条,会让你大开眼界。
二
之所以说《失忆的年代》不好读,是因为小说在写作方式上,主要采用了意识流的表现手法,这不太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和欣赏习惯。谢尔•埃斯普马克在整部作品中,以一种知识分子的思考深度,为我们描绘了一张张生活在失忆的年代里的现代人的面孔。这些人物的内心有的焦躁不安;有的无可奈何;有的苦苦挣扎在失败的边缘但挣扎的结果是在失败的深渊里越陷越深;有的茫然不知所措如同伫立在陌生的十字路口忘了来路不知归途。
七部小说,既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也没有典型环境中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小说舍弃了情节和人物,那最后还剩下些什么?
是的,只剩下了一些看似杂乱无章的情绪、细节、氛围,一些模糊不清的形象、轮廓、幻象。最后只剩下了叙述者,和叙述者喋喋不休、嘟嘟囔囔的叙述。
七部小说都是以第一人称“我”的角度来展开讲述的。在第一部《失忆》中,“我”在一个政府机构里主持一项调查工作,对当代日益普遍的失忆症现象展开研究,但是,不久调查工作进入困境,这项调查让“我”越来越一头雾水,最后连“我”对自己的身份都无法确认;第二部《误解》,“我”摇身一变,成为一家报社的主编,“我”这个孤独寂寞又无人认识的人,在一个水汽氤氲的浴室里,因为不想被“误解”所以极力地为自己展开辩解;第三部《蔑视》,“我”,艾琳,一位卧病在床的老妇人,向读者讲述悲惨的人生是一幅怎样的景象;第四部《忠诚》,“我”又成为了斯德哥尔摩剧院附近的一个建筑工人,当“我”回望自己所走过的人生之路时,“我”开始反思自己当初所参与的工人运动是否正确;第五部《仇恨》,“我”的身份更是特殊,成为一位被谋杀的首相,既然演说艺术是“我”的强项,那么让“我”来告诉你们什么是“仇恨”吧:“我可以闻到仇恨,就像闻到来自卖鱼的柜台和腌鱼桶散发出来的臭气。”(《仇恨》第八十一页)第六部《复仇》,“我”是一个年轻的金融巨头,童年饱受同学的欺辱,父亲又遭人暗算而破产,长大成人之后腰缠万贯的“我”岂肯善罢甘休?最后一卷《欢乐》,“我”,一个徘徊在边缘社会苟且偷生的妇女,试图融入所谓的主流社会但是从来没有一次获得过成功,被摧残、被凌辱似乎成为家常便饭,作为叙述者,“我”向读者道出了一个底层人的痛苦心声。在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欢乐”可言啊!如果非要说有的话,那么此刻“我”依然还活着,还可以发出声音,这也许就是“我”所能感受到的最大的“欢乐”了。
除《忠诚》之外,其余六部作品均有一个特定的倾诉对象“你”,这使得倾诉者与倾听者之间的距离无限拉近,仿佛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彼此能够听见对方的心跳,能够感受对方呼吸的鼻息。这倾诉有时故作轻松甚至夹带点幽默;有时无比沉重伴随一声绵长的叹息;但小说读到结尾之处,你发现倾听者其实并不存在,你才是这些故事唯一的知情人。故事之中那些千头万绪、盘根错节的复杂和迷乱,最后在你的脑海里如同一泓清泉一样无比明澈和清晰。
便是如此。谢尔•埃斯普马克通篇采用第一人称手法,唠唠叨叨,喋喋不休,无头无尾,没完没了。愤恨之声、哭诉之声、指责之声、埋怨之声不绝于耳。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简直根本读不下去;如果对小说艺术的现代性不够了解,同样也可能会极度不适应这部小说。这种出自于“作家中的作家”之手笔的小说,注定是写给“读者中的读者”阅读的:他们需要具备专业的阅读技能和较高的阅读水准。尽管不是谍战或推理小说,但阅读这部作品同样挑战着阅读者的智性。其间无所不在的隐喻,作家庞杂而渊博的知识背景,西方社会(确切说是瑞典)的现实变化图景,阅读者若不具备一定的知识背景和文化结构,恐怕难以读懂作家在小说中所要表达的深层含义和良苦用心。
可以说,这部小说几乎包含了所有写作中的复杂性,其间既涉及到扑朔迷离纷繁复杂的案情,折射出当代西方社会在各自为营的利益团体中的立场(《仇恨》);也有对个人命运的讲述,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饱受凌辱立志长大以后报仇雪恨(《复仇》);小说既讲述了人与人之间不被信任、不可调和带来的冲突和误解(《误解》);又写了被侮辱和被损毁的如同蝼蚁一般轻贱的生命,是如何被践踏、被漠视的(《蔑视》)。而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被彻底异化了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人活着毫无尊严可言,良知可以被出卖,生命可以被随意损毁,恐怖袭击时有发生,政党可以为一己之私欲而轻率发动一场战争,弱国孤立无援,难民背井离乡四处逃亡,犯罪分子眼中布满邪恶和杀机,贫富悬殊巨大,腐败无处不滋生,金钱和权力成为人普遍的信仰……一言以蔽之,人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人只能在这样的悲剧里毫无希望地存活。存活下去成为最残酷的也是唯一的事实。
别以为这一切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不,这就是眼下我们所处的时代。
三
越过小说本身,最后让我们再来深思一个问题:既然这是一部充满野心的小说,那么谢尔•埃斯普马克的野心在小说中最终体现在哪里?
“集权主义。我写了一系列关于瑞典社会现实的小说,但那些问题世界各地都存在。我的观点是,你需要一股强大的力量建立国家,但同时你也需要另一种力量去护卫个人利益,我觉得制约平衡是必须的,只有公平的、给予个体发展空间的国家才能建设一个繁荣社会,这在我的小说中是核心。”①李乃清:《中国文学不落后——专访诺贝尔文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10月16日。
埃斯普马克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记录的是瑞典的历史、人文和现实。七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是生活在瑞典当下现实社会里的人,他们的存在本身便如同一台摄像机,见证和记录着这个社会的各种发生和变动。可以说,小说描绘的是瑞典的现实社会,但批判的是西方社会的图景,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命运,最后书写的是现代人的精神荒原。正如在《蔑视》中,“我”,北欧老妇人艾琳,为了两个儿子牺牲了一切;儿子们也希望能在社会中出人头地,还给母亲一个公道,但其结果呢?“为什么这种触摸是那么孤独的,这样独一无二的?为什么我从来不能够触及到自己的孩子们,而我不是触及到很多其他的人吗?为什么我的爱拥有的那些唯一的词语也要号召我去复仇?为什么我自己不会拥有语言呢?我总是说呀,说呀,说个不停——为什么我自己没有语言呢?”(《蔑视》,第一百五十八页)“我”抛出了这一连串的问题,却得不到一个答案。于是这些唠唠叨叨的絮语像刀子一样锋利起来,以至于每读一个字都令人极度不舒服,让人感觉像是刀片一样尖利地刺痛着我们的感官。最后,女主人公失声喊了出来:“我从这一生中到底得到了什么!”她的声音那么凄厉,在我们耳畔久久回响。这个问题有答案吗?没有。如果要说有,那答案已经包含在提问本身中,那就是:没错,你这一生什么也没得到。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瑞典女人,其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人格,是如何一点一点被家庭、人伦、道德以及整个社会所磨损、消耗殆尽的。七部小说从不同角度审视当代社会,中国作家盛赞这部小说是“卡夫卡式的寓言,有着加缪般的洞见”,之所以给出如此高的评价,我想是因为其中对人性的刻画,对社会的剖析,多多少少让我们看到了卡夫卡《变形记》中人的异化,以及加缪《局外人》的游离与冷漠。也唯其如此,作品才如此艰深、难懂、剧烈、幽深。
记忆原本就不可靠,更别说我们置身于一个“失忆的年代”里。在一个集体失忆的时代,沉默是无声的呐喊,失语是因为我们想要控诉的太多。而正是人生有那么多的艰难、创痛、残破、伤害无法被遗忘和原谅,正是因为人在现实面前是如此之无能为力和不堪一击,所以我们才选择性的“失忆”。这几乎成为了一个死循环。对于人生的绝望和挫败,如果要与之对抗,最好的方式也许只能是选择失忆和逃避。而忠实记录并维护着这一切的谢尔•埃斯普马克先生,他文学生涯里最大的价值之一,也许就是在这部长卷小说里留下我们曾经存活过的最后的记忆。
符树芬,云南大学文学院人文素质部。